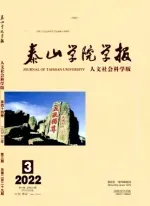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隋唐时期碑刻楷书的研究价值
李海燕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92)
隋唐时期是汉字楷书发展至为关键的时期。楷书在经历了六朝时期的剧烈发展演变之后,到隋唐时期逐步走向了规范定型,一直影响了现代楷书的基本形态。而历史上的隋唐时期各种书写材质并用,其中以碑刻数量为最多,向来是文字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本文试图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再来探讨一下隋唐时期碑刻楷书潜在的研究价值。
一、有利于总结楷书定型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异规律
“真书汉末已胚胎,钟体婴儿尚未孩。直至三唐方烂漫,万花红紫一齐开。”[1]启功先生这首诗指出萌芽于汉末的楷书,直到唐代才达到发展的顶峰,而汉字楷书在这七、八百年漫长过程中的发展演变还缺少详细的研究和全面的调查。其中,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是汉字楷书历经汉末萌芽,魏晋南北朝奠基后走向成熟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楷书的发展、定型、规范直接影响了隋唐以降楷书的发展演变,在汉字楷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社会上各种书写材质并用,其中以碑刻数量为最多、内容涉及最广、存留程度最好,也最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用字的实际情况,清晰地展现出汉字字体地发展演变过程。基于此,我们认为研究汉字楷书的发展演变历史,总结楷书在定型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异规律,隋唐时期的碑刻楷书是一个非常可靠、非常有必要的研究起点。通过对隋唐时期碑刻楷书的全面整理与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该时期碑刻楷书形体的个体特征和系统情况,探究碑刻异体形成的原因,进而总结出楷书定型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异规律。
二、有利于确定隋唐时期在汉字楷书发展史上的地位
六朝到隋唐时期作为汉字楷书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没有异议,但是对这两个阶段楷书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裘锡圭认为:“从各方面综合考虑,似乎可以把南北朝看作楷书阶段的开端,把魏晋时代看作隶书、楷书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2]齐元涛指出:“就汉字的发展来说,魏晋时期楷书萌芽,隋唐时期是楷书的成熟、定型时期。”[3]对这两个阶段楷书发展程度的准确判断,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楷书发展历史的讨论。我们认为,确定汉字楷书系统的发展程度,主要应从整字、构件、笔画三个层面作出具体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应该以该系统的可靠资料为研究对象,惟有如此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利用碑刻文献资料,由隋唐时期追溯到六朝时期,进而对这两段时期楷书发展演变情况的异同作出合理的判断,揭示出隋唐碑刻楷书传承与变异规律,是研究和探索汉字楷书发展演变历史的有效途径之一。现在所拥有的六朝至隋唐时期的碑刻材料比以往任何年代都丰富。一旦占有翔实的研究材料,即可展开历史比较调查,揭示隋唐碑刻楷书的传承和变异规律,比较准确地定位本时期社会实物用字的历史地位,为汉字发展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支持。
三、保存了大量的汉字楷书字形
刘敞在《先秦古器记》中曾经明确指出碑刻文献具有三种重要的史料价值:“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其中,确定某个汉字在历史上的出现时间,更是十分需要借助这批碑刻文献材料来扩大其取证的范围。隋唐时期是汉字字形发展至为关键的时期,楷书在传承六朝时期汉字字形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演变。本时期楷书的传承与变异对现代楷书的定型影响甚巨,后世楷书的许多形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直接源头。同时,只有建立在碑刻原始拓片基础上的研究才能为汉字字形的准确程度提供客观上的保证。而本时期的碑刻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汉字楷书字形资料,这样不但可以从客观上为汉字楷书的发展研究创造条件,而且也可以为现代汉字的整理与规范、古籍文字的整理和校勘、大型语文工具书的编纂与修订等提供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特别是隋唐时期碑刻楷书中的新增字形,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用字的真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对于当今大型字典的编纂和修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第一,它们可以直接反映出隋唐时期碑刻楷书传承字中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异形体。与六朝相比,进而反映出隋唐时期碑刻楷书传承字在形体结构上的整体变异情况。第二,新增字形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部分字形甚至可以作为字形断代的实物依据。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武后新字的出现和使用,如武后新字中“年”,由“千千万万”四个构件组成,为会意字,意指大周帝业绵延无绝期。这一批字均为“时代为之”,很快就随着王朝的覆灭而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武后新字的字数,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当时社会的使用情况等。第三,一些新增字形可以为大型语文工具书的编纂和订补提供参考。尤其是在增补漏收字形、提供适当语例、提供书证、纠正辨析失误,探析字形的源流演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汉语大字典》禾部“(字形为上禾下甘)”字下云:“同‘香’。《海篇·禾部》:(字形为上禾下甘),音香,芳氣也。”按《汉语大字典》此字形最早见于《海篇》,且没有文献用例。其实,隋唐时期的碑刻楷书中早有用例,唐景福元年《悯忠寺重藏舍利记》“填以異香”中,“香”的字形即写作“上禾下甘”。垉,《汉语大字典》仅引《龙龛手鉴》的反切注音,没有释义。在隋唐时期的碑刻楷书中已有用例,隋开皇四年《杨居墓志》“沉丹塗漆,埋琛垉瓉”,在此例句中“埋”与“垉”对应,应指埋葬之意。
四、出现了一批时代鲜明的新增字
人类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会增加许多新的内容,从而使每个时代显现出与众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语言文字作为记载传播历史文化的工具亦同样如此。隋唐时期碑刻楷书中除保存了大量的楷书字形以外,还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汉字,我们称之为新增字。新增字是该时期碑刻楷书文献中为记录新词而出现的新字。主要包括以下两类:(1)为记录隋唐时期之前的语言中从未出现的音义结合体而新造的字。其中包括该时期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特殊因素——人名专用字、音译佛经用字等都归入此类中。如袈、裟,《名义》无此二字。《宋本玉篇·衣部》:“袈,古牙切。袈裟,胡衣也。亦作毠(字形为上沙下毛)。”《宋本玉篇·衣部》:“裟,所加切。袈裟。”二者为梵文音译联绵词。二字的写法不固定,《宋本玉篇》就贮存了“袈裟、毠(字形为上沙下毛)”两种书写形式。其中“袈裟”这种书写形式与今天简化字中的形体相同。“袈裟”这种书写形式也出现于隋唐时期的碑刻材料中,如见于唐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国碑》“试殿中监赐紫袈裟”。这批新造字的出现与佛教在隋唐时期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2)由旧词分化出了新词或者旧字被借用来记录其它词,为区别旧字所承担的不同功能而新造的字。如,妐,《宋本玉篇·女部》:“之容切。夫之兄也。”《名义》所无。隋唐碑刻材料中,隋大业十一年《张志相妻潘善利墓志》“善事姑妐,能和姪娣”,已经出现“妐”字形,在隋唐时期以前,称呼丈夫之父时,写作“公”。由表示“公正、无私”之义的“公”来承担这一义项。后来,才专门为此造了“妐”字形。“妐”相对于“公”,为后起字。
这些新增字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部分字形甚至可以作为字形断代的实物依据。其中,与《宋本玉篇》新增字展开比较,我们可以直接判断《宋本玉篇》新增字中哪一部分字来自隋唐时期的社会用字,由此推测唐宋之际成书的《宋本玉篇》收字的来源,进而推断其大致的成书年代。因为《宋本玉篇》的现有规模是经过唐代孙强、宋代陈彭年在《原本玉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其修订主要的途径是增加字数、删除书证、修改注音等。其中,唐宋间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增字情况,仅以传世文献和《宋本玉篇》本身贮存的文献来讲,很难展开具体的分析。而我们所整理的隋唐时期碑刻楷书文献新增字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五、为现代简化字的来源提供依据
“简化字”是指由我国国务院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中所规定的一批规范使用的简体汉字。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一次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其中有简化字515个和简化偏旁54个。1964年5月,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编辑并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收录简化字2236个。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对个别简化字做了调整,收录简化字2235个。现行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是有历史来源的。首先,在隋唐时期的碑刻楷书中,出现了部分简化的汉字,即有些字形的部分构件和《简化字总表》公布的简化字部分构件相同。如,构件“门”、“夹”、“纟”等,其中构件“馬”、“鳥”虽然还没有完全简化,但与简化构件已经十分接近。其次,这批材料中还存在着许多与现代简化字的形体完全一致的汉字字形。如:贤、监、坚、诸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总结楷化规律、确定历史地位、保存楷书字形,还是从提供新增汉字、明确简化来源等方面,隋唐时期的碑刻楷书都有其潜在的研究价值。这些材料由于数量庞大、种类众多、书体繁杂、分布广泛,仅凭个人的力量难以展开系统的调查,因此,要为更多的研究者涉及此领域,尚需时日。
[1]启功.论书绝句[M].北京:三联书店,1990.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齐元涛.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