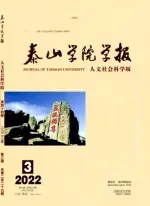《诗经》的艺术范型
林祥征
(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林兴宅先生在谈到《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说: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至今可见的文学创作的原始形态,它孕育并繁衍中国历代文学传统。其重要性恰似古希腊的戏剧和史诗之于欧洲文学的传统。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学,就不能不读《诗经》,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通过《诗经》的艺术世界,人们可以发现宇宙人生的奥秘和人类心灵的奇幻。人类的基本情感活动几乎都在《诗经》中得到某种形式的表现。它为历代诗人提供了表现各种情感的范型。抒情诗在《诗经》时代就达到使人惊奇的地步,这是令人深思的。[1]
这段精彩的论述,既讲清了《诗经》的价值,又指出其重要影响表现在“为历代诗人提供了表现各种情感的范型”这一方面。可谓独具慧眼,遗憾的是林先生并没有对《诗经》的艺术范型作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人类的基本情感活动几乎都在《诗经》中得到某种形式的表现,”恰恰表现在《诗经》所提供的艺术范型上。历史向前一步的进展,要求伴随着向后的探本溯源。在《诗经》学告别20世纪,而走上21世纪的今天,对《诗经》的艺术范型进行探讨是必要的。
所谓“艺术范型”,它是艺术手法的基元,是一种超越时空,具有情境的心理结构形式。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例如,泪是人情的流露,雨是天上水汽的降临,而诗人把它们构成一个范型,以抒发连绵不断的悲伤之情。《北梦琐言》记载徐月英诗“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并成为“雨与泪共滴”的艺术范型的祖构。后代刘媛《长门怨》:“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如雨断昭阳;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以抒写妃子被打入冷宫的辛酸。曾揆《谒金门》:“伴我枕头双泪湿,梧桐秋雨滴。”一个“伴”字把雨写活了,使该范型更有情趣。白仁甫《梧桐雨》第四折写唐明皇思念杨贵妃:“斟酌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煞,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把这个范型铺写得更加具体生动。它说明艺术范型能唤回人对生活的更深切的感受,是体验人的情感的创造性的形式。那么,《诗经》的艺术范型有哪些?并给后代以影响呢?
一、关于抒写思念的范型
(一)“思极而通梦”型
《周南·关雎》是一首著名的爱情诗,全诗5章,后两章“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当代学者认为是实写,《关雎》是首结婚歌。这个看法是错的,因为第3章的“求之不得”是关键词,哪来的结婚典礼?因此,最后两章是主人公在床上所作的美梦。梦见和淑女过着“夫妻好合,如鼓琴瑟”(《小雅·棠棣》)和谐美满的生活。心理学家认为,幸福的人很少幻想,梦是人生愿望的改装,是有心理依据的。后代相关的诗有《古诗十九首》:“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即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鲍照《梦归乡》:“寐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李白《白头吟》“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贺铸《菩萨蛮》:“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都说明梦是心境的延续。《小雅·斯干》是一首祝颂周王公室落成的诗,而颂祷是通过主人的美梦和占卜来完成的。梦见熊罴是好兆头;梦见蛇是交好运。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期盼。
(二)“谁适为容”型
《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意是“士为悦己者容”,而今“悦己者”远离而去,哪有心思梳妆打扮呢?真切地写出正值爱美年华的女主人公,爱人不在的空虚寂寞的心境和百无聊赖的情怀。《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和《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都是这种心境的流露。心理学认为,表现是指内心的情绪状态,通过外部动作或表情呈现出来,比如喜怒哀乐都会有不同的动作和表情。“谁适为容”型正是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因思念而无心做事的心绪。后代有徐干《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曹植《七哀诗》:“膏沐谁为容,明镜暗不治”。杜甫《新婚别》:“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等,而写得更好的是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狮子型的香炉),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梳妆匣)尘满,日上帘钩。”“慵”是该词的词眼,香炉的香懒得点,被懒得铺,头懒得梳。梳妆匣懒得拂拭,更无心去用里面的膏沐了,都是离情别苦的真切而生动写照。
(三)“在水一方”型
《秦风·蒹葭》是一首著名的爱情诗,诗的意境的构成是,求爱的对象在水一方,抒情主人公从上游从下游去寻找,始终没找着,从而产生不尽的思念。心理学告诉人们: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人们便越想得到它。诗中的“伊人”被置于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即,从而增加思念之情,增加诗的张力。西方美学家李普斯说:“当命运受到遏抑、障碍、割断时,人们的心理活动受到堵塞,从而对堵塞前的往事更加眷念。这种眷念有更大的强度和逼人性。”(《美学·美的方式》)这种“在水一方”的眷恋之情,不仅属于抒情主人公,也使读者产生对带有神秘感的“伊人”的思慕。这种诗境的建构后代有《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水的阻隔;欧阳修《踏莎行》:“楼高莫近危栏,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是山的阻隔。这种建构也用于方士对三神山的描述上,《史记·封禅书》记载,方士描述东海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这种可见而不可及的神山有很大的吸引力,难怪秦始皇非到东海寻找不可了。
(四)“月下怀人”型
《陈风·月出》是首月下思念美人的诗,这首被研究者称为“杰出的诗”,最大的特色是,诗的开头描绘出一个开阔而空灵的境界,并有意地把美人安排在月光下,让美人具有一种朦胧的美,使思念之情更加浓郁。浙江民谚:“月光下看老婆,越看越喜欢;露水地里看庄稼,越看越喜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晏几道《临江仙》:“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絃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夜,曾照彩云归。”也是把美人放到月光下,传达出依依惜别之情。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境更加广大,感情更加浓郁。是该范型的拓展。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经赞美“月亮是个大艺术家”,并用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的一段话加以印证,文中说,月亮能够移世界,山寺有了月色真美,幽华可爱,白天一看,“瓦石布地而已”。[2]从这个意义上说,《月出》的作者是我国文学史上发现“月亮是个大艺术家”的第一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创作美学:利用光影的若明若暗,能够增加艺术对象的美。拜伦有一首咏威莫特·霍顿夫人的诗,叫《她走在美的光影里》,正是利用光影的明与暗,而使霍顿夫人的形象更美的。17世纪英国诗人赫克里《水晶中的莲花》也说,方孔下的玫瑰、玻璃杯内的葡萄,清泉底的琥珀,纨素中的妇体等,都因光影的若明若暗而添媚增姿。从《诗经》中学习活鲜的美学,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此外,《王风·君子于役》是一首“黄昏思念”型的诗,抒写一位妇女在黄昏时候,看到牛羊从山上回来,鸡栖息于鸡窝,触景生情,思念久役在外的丈夫。后代采用这种范型的诗词是很多的。例如辛弃疾《满江红》:“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泪。最苦是,立尽月黄昏,栏杆曲。”还有被誉为“秋思之祖”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郑风·东门之墠》也是一首爱情诗,属于“室近人远”型。为什么心爱的人很近,反而觉得很远?陈子展《诗经直解》:“意味咫尺天涯,莫能相近,极言相思之甚也。”说明这种心理空间的抒写很能表达相思之情,后代有《西厢记》第2本第1折[混江龙]:“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等。
二、抒写人生痛苦的范型
(一)“落花伤感”型
《小雅·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毛传》:“苕,陵苕(凌霄花),将落则黄。”诗人见到凌霄花的凋零,联想到青春将逝,好景不长,从而发出深深地叹息。《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洛阳女儿好颜色,坐看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李煜《浪淘沙令》:“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清照《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林黛玉《葬花吟》:“花谢花落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大自然中,足以触景生情的事物很多,而花是其中的最常见一种。鲜艳美丽的花,从开放到凋零是如此明显而迅速,容易引起生命的共感,从而产生美(年华、美貌、理想等)的失去后的惆怅和悲伤。“岁华尽揺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的伤感就很有代表性。李建勋《宫词》:“宫门常闭舞衣闲,略识君王鬓先斑;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女主人公羡慕落花能够自由地流到人间,慨叹自己连落花都不如,其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孟浩然《春晓》是孺幼皆知的名篇,有的学者认为该诗是表现诗人“喜爱春天的感情”(《唐诗鉴赏辞典》),值得商榷,应该从“落花”型的视角去理解一生不得志的孟浩然的惜春之情。而龚自珍《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则是与古为新,别开生面。
(二)“局天蹐地”型
《小雅·正月》是一首周大夫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诗,诗中写道:“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其意:人说老天高远,可我不敢不弯腰;人说大地厚重,可我不得不小步走。诗人用反衬法,写在国家混乱、民不聊生状态下的窘态及痛苦的心情。《小雅·节南山》:“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戚戚靡所骋。”写法也一样。左思《咏史》八:“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穷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通途。”李白《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日本万叶时代著名诗人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虽云天地广,何以载我却偏狭?虽云日月明,何以照我天无焰?”等,都是从《正月》的范型演化而来的。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都有一定的客观性,不因人而异。但由于人的主观性,同一空间或时间的主观感觉 并不一样,文学心理学称之为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同一个人,由于心情不同,对于空间与时间的感受也不同。孟郊在失意时写道:“出门即有碍,谁云天地宽?”(《送崔纯亮》);而在中举之后,则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说明“局天蹐地”型是一种痛苦心理的真实抒写。而《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则属心理时间的描写了。何汶《竹庄诗话》记载有首《长夜吟》:“南邻火下冷,三起愁夜永;北邻歌未终,已惊初日红。不知昼夜谁主管?一种春宵有长短。”“一种春宵有长短”正是心理时间的反映。我们以往把文学定义为“文学是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看来并不全面。
(三)关于厌世的范型
1.《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人类是万物之灵,竟然羡慕起无情的草木的无知、无家室来,其痛苦、厌世可想而知。这个“羡慕草木”型的范型,后代有鲍溶《秋思》:“我忧长于生,安得及草木?”姜夔《长亭怨慢》:“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许。”《红楼梦》第113回,紫鹃道:“这活着真苦恼伤心,无休无了。算来竟不如草木石头,无知无觉,到也心中干净。”
2.“尚寐无觉”的范型:《王风·兔爰》2章:“我生之初,尚无造(指繁重劳役),我生之初,逢此百忧,尚寐无觉。”诗人在遭受苦难之后,希望长眠不醒,是对生活的绝望。由于生命的不可重复性,求生欲望便成为人类的最基本诉求。然而《小雅·苕之华》却喊出“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其悲怨与痛苦之情与《兔爰》是相通的。后代有戴望舒《生涯》:“人间伴我惟孤苦,白昼给我是寂寞;/只有甜甜的梦儿,慰我在深宵。/我希望长睡沉沉,长在梦里温存。”刘德华演唱《忘情水》:“给我一杯望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等。而米开朗基罗在著名雕塑《夜》的座上所刻的诗:“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一个在古代的东方,一个在近代的西方,所写的范型如此一致,是值得深思的。林先生所说“人类的基本情感活动几乎都在《诗经》中得到某种形式的表现”,可在这个范型中得到印证,同时也说明《诗经》的范型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它可在更深层次上探索人类心灵的历史。此外,《小雅·六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奚其适归”是最早的“悲秋型”的诗,后代相关的的诗词不胜枚举。而刘禹锡《秋词》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反悲秋的传统,唱出了让人精神一振的高歌。《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王子同归。”则是“伤春”型。王昌龄《闺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是因伤春而后悔的,而张仲素《春闺思》“袅袅边城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则是因伤春而忘采桑,各具特色。《卫风·氓》的《小序》:“花落色衰,复相弃背”,说明《氓》诗属于“色衰爱弛”的范型。与这个范型相反的是《郑风·出其东门》的“爱情专注”型,其诗是说尽管美女如云,但我只爱那个装饰简朴的女人。后代有《上邪》等。
三、分别情景的范型
(一)《邶风·燕燕》是一首卫君送妹出嫁的诗,属于“瞻望不及”型。在这首被誉为“万古送别之祖”的诗中,只写了一个“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的守望情景,其好处是:(1)“瞻望弗及”,写了用目力相送,直到看不见还在那里瞻望,就把惜别之情表达出来了;(2)诗中没有写分别的话语,钟惺说:“深情苦境,说不得,苦说得,又不苦矣。”后代有屈原《哀郢》:“望长楸而太息,涕淫淫其若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我唯见长江天际流。”苏轼《与子由诗》:“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等,而左纬《送许右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以诗寄之》:“水边人独立,沙上月黄昏。”可谓后来居上。
(二)《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可谓“杨柳依依”型,该诗是回乡战士回忆当年奔赴战场时与亲人依依惜别的情景。所谓“依依”是形容柳条柔长飘拂的状态,与送行时依依不舍挥手告别的情景相互交融。后代有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其一:“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而李嘉祐的“远树依依如送客”(《自苏台至望亭驿怅然有作》),李商隐的“堤远意相随”都是该范型的名句。诗是作者心的投影,对于事物的歌咏,无不以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心理特点等民族文化为背景。汉语中的“柳”谐音“留”,暗含着挽留的意思;垂柳向着地,象征期盼回归故乡;杨柳分布广,又易栽,预祝行人在他乡随遇而安。中国人喜集不喜散,但在人生旅途中别离又是常有的事,因此,杨柳成为古代诗词中常见的离别的象征,该范型更具普泛性。另外,《大雅·嵩高》是周卿士尹吉甫送申伯的诗,这篇赠别之诗,严粲《诗辑》评之:“每事申言之,寓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感情绵绵不尽,形之语言必然是回环反复,这种写法正是分别时情感的真实流露,有人批评其重复啰嗦,是不得要领的认识。
四、艺术手法的范型
(一)“画眼睛”型。《卫风·硕人》是一首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第2章对庄姜的仪容作了精彩的描绘:“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章被后人誉为“咏美人之祖”,在美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古代文论强调要写出人的灵魂,最好的方法是“画眼睛”,因为眼睛是脸上最能表达情性的感官,是心灵的窗户。诗中的前5句是形体美的描写,如果没有后2句,只能像庙里的观音菩萨;有了后2句,才把庄姜写活了。《硕人》是我国诗歌中最早“画眼睛”的艺术范型。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正是从《硕人》演化而来的。《楚辞·大招》“嫭目宜笑,蛾眉曼只”,陶渊明《闲情赋》“瞬美目而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李白《越女词》“卖眼掷春心”等,眼睛不仅会笑,会说话,还会挑逗,这些都是在《硕人》原型基础上的踵事增华。
(二)“取影法”型。所谓“取影法”,意谓只要有光,物体总是有影。静物写生、摄影都要顾及物体又取其影子,以构成完整的画面。“取影法”是王夫之在《姜斋诗话·诗绎》中,评论《小雅·出车》和王昌龄《青楼曲》时提出来的。《小雅·出车》是一首征人抒写随主帅南仲征伐猃狁凯旋归来的诗。最后一章表达征人凯旋而归的喜悦之情,却想象其妻在家中听到丈夫将归的期盼与欣喜。借妻子的喜悦写征人的喜悦,以虚衬实,收到由此及彼、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魏风·陟岵》是一首征人思念家中亲人的诗,而展现在主画面的却是家中父母、兄弟思念征人。好像电影的迭镜头,一幅银幕四个画面,扩大了诗的境界和感情空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小雅·巧言》),这种写法是有心理依据的。后代有王建《行见月》:“家中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亲》:“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游人。”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等。杜甫写《月夜》,当时他在长安,而诗中出现的却是家中的妻子思念他的情景,杜甫是深得取影法的旨趣的。如果说,以上写法是同一时间的此地——彼地——此地的往复的话,那么,李商隐《夜雨寄北》一诗,不仅有此地(巴山)——彼地(西窗)——此地(巴山)的往复,而且还有空间的今宵——他日——今宵的往复,对该范型作了新的拓展。
(三)“错觉艺术”型。该范型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艺术手法,其特点是把真当成假,把假当成真。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它是个体强烈愿望无法满足,处于严重缺失状态时所产生的。而最早运用这种手法的是《齐风·鸡鸣》,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警其夫,欲令早起,故终夜关心,乍寐乍觉,误以蝇声为鸡声,以月光为东方明,真情实境,写来活现。”[3]这种描写,确能传达其妻“终夜关心,乍寐乍觉”的精神状态。有学者认为“苍蝇之声”应该是“青蛙之声”之误,这是不懂错觉艺术所致。后代有《子夜歌》“长夜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明代民歌《认错》:“月儿高,望不见乖亲到,/猛望见窗儿外,花枝影乱摇。/低声似指我名儿叫。双手推窗看,/原来是狂风揺花梢,/喜变做羞来,羞变做恼”等。李白《静夜思》正是运用错觉艺术而成为名篇的。
(四)“无理而妙”型。在文学中,有情与无理常常是一对可以统一的矛盾。所谓“无理”,指违反一般生活常识或思维逻辑而言;所谓“妙”,则是指通过似乎无理的描写,更深刻地表达了特定的情感。《卫风·伯兮》是一首思念远征丈夫的诗,诗中“愿言思伯,甘心首疾”,“首疾”是痛苦的,哪有甘心痛苦的?这就是无理,但却表现出希望丈夫早日回到身边的强烈愿望。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秦风·黄鸟》为了挽救为秦穆公陪葬的“三良”而喊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跟《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样,都是“违情悖理”的话,但却真切地表达了特定情境下的愿望。它说明理性是对现实的认同,而情感可对外在现实加以超越。苏轼《水调歌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埋怨天上的圆月也是无理,但却传达出词人在明月之夜不能与亲人团圆的痛苦之情。
此外,还有《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言不喧哗也”,说明《车攻》是“以动衬静”型。后代有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维《鸟鸣涧》等,是心理学“同时反衬现象”在艺术上的表现。在题材上,《王风·黍离》开凭吊古迹,慨叹人生的先河。《豳风·鸱鸮》则是开咏物诗的先河。
结语
《诗经》艺术范型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抒情诗歌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艺术符号系统,它存在于艺术与人生的契合点上,是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与审美经验的结晶,它是先民在充满矛盾的人生中开放出来的心灵之花,是心灵世界的自觉表达,它承载着民族的情感、精神、气质、心理等内在的东西。同时,也使我们体会到先民有很强的情感体验的形象传达力,并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过去常讲《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的源头,了解《诗经》的范型,对这个问题将有更深的体会。对许多诗词的艺术手法和内部结构,也将有新的认识。从欣赏的角度看,既见森林又见树木,对提高鉴赏力、审美力也有助益。相传郭沫若从小读《诗经》,丝毫也没有觉的《诗经》的美感,后来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后,才感受到《诗经》同样的美妙,同样清新。我们单独读《诗经》,也往往不能感受到它的美,但联系后代的艺术范型,即可了解民族心灵发展史,又能感受到《诗经》的美感效应那么强烈,那么深入人心。
纵观《诗经》范型史,只有个别人的毫无生气地沿袭祖构,而大多数的作者都是在借鉴中力求创新。《桧风·素冠》:“庶见素韠(皮制的蔽膝)兮,我心藴结兮。”首倡用丝的缠绕抒写心中的郁闷与痛苦。后代有《楚辞·悲回风》“纠思心以为纕(佩带),编愁苦以为膺(胸前的饰物)”,施肩吾《古别离》“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系肠线”,张籍《古别离》“离爱如长线,千里系我心”,李煜《乌夜啼》“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姜夔《长亭怨慢》“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德得玛演唱的《蓝色蒙古草原》“轻轻牵起记忆长线,漂泊的白云唤起我的眷恋,梦里常出现故乡的容颜”等。都沿用“线”的意象,表达方式却千变万化。说明《诗经》的艺术范型之所以富有生命,与后来者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分不开。我们在肯定《诗经》的贡献的同时,对后继者的拓展也应给予正面的评价。一叶而知秋,我们从《诗经》范型史中能够揭示中国诗歌史的发展规律:即中国诗歌的历史是连续不断地继承中创造发展的历史。一味模拟复古和一味否定传统都失之偏颇,都是陈腐之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诗品》则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流别,则可以探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说明了探索学术的源头和流变是文学研究和评论的重要方法,这也可从本文中得到启示。同时,这个研究视角对我们探讨和认识我国民族心灵史也有一定帮助。
在19世纪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施旺提出细胞学说之前,人类对生物界的认识,只停留在不同个体的单纯描述阶段。细胞学说的提出,才使人类认识到,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之间存在一种共同的基本结构,它是一切生物存在和发展的基元,从而对生物结构的观察和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同时说明现代学术已经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即力图把握研究对象内部结构的大趋势,对《诗经》艺术范型的研究是符合现代学术的大趋势的。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中谈到《楚辞》对后代的影响时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或在三百篇以上。”这句话经常被文学史家所引用,反映鲁迅对《楚辞》的偏爱,但有失于片面。从题材上看,《楚辞》只局限于政治层面,大多抒发爱国无门的悲愤,而《诗经》反映的生活面广,战争、爱情、农业、征役、狩猎、政治感怀等;从创作成员看,《楚辞》只局限于士大夫,而《诗经》有天子、公卿、大夫、士、农夫、士卒等;从抒发的情感看,《诗经》中,既有宗教情怀又有世俗的喜怒哀乐,遍及内心世界的每一角落。《诗经》是先民时代的百科全书。有人说“还原鲜活的人生是文学永恒理想”,《诗经》正是一部反映先民鲜活人生的著作,并影响到后代的文学、诗话。甚至连皇帝的旨喻、大臣的奏章,科举的作文也广泛运用《诗经》的思想、典故和词句。《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式微》中的诗句)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柏舟》诗句)
在旧时代,连生活在最底层的奴婢,都能用《诗经》的词句于生活中,可见《诗经》影响之广。
[1]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