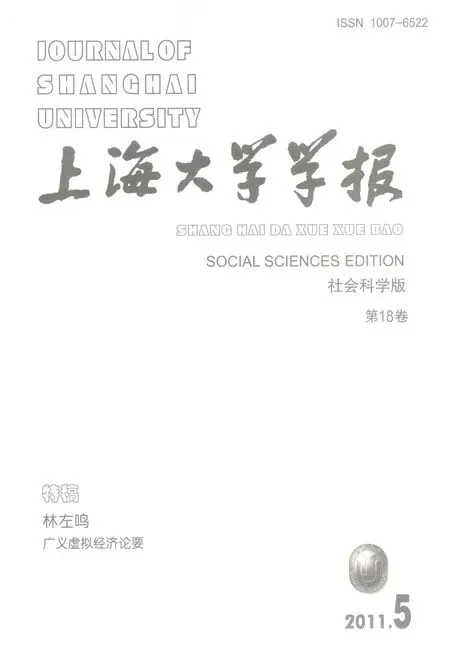《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傅 刚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通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秦汉时的文学体裁,主要是辞赋,作为史书的《史记》,却以记事和传写人物为后来的传记文学写作树立了典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述说自己的史书写作,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尽管《史记》的纪传之例,抑或有前代史书的渊源,但镕铸古例,成《史记》五体,以见古今成败兴坏之理,当然是司马迁的独创。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①参见李光缙.增订史记评林日本明治二年(1869)。对司马迁来说,他写《史记》,主旨是成就通史,继孔子删述《春秋》的传统,因此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互为依存和互动的因果关系,通古今成败兴坏之理。什么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呢?这是要从司马迁《史记》五体中细究的。《史记》一书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与古史的编年体例完全不同,反映了司马迁以人物为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而人类历史是由各个阶层人物共同创造的,司马迁《史记》正是由此出发,列传社会各阶层人物100余人,涉及到的达4000多,从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司马迁将探讨天人之际的关系、古今兴衰的变化原因,建立于对人物活动的叙述中,这是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刻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因此,《史记》一书是活的历史,义蕴深刻,虽历千年,其中的道理仍然揭发不尽,足给后人以各种各样的启迪。
司马迁人物传纪所具有的文学性成就,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司马迁本没有文学性的考虑,也没有后世人的文学观念,他只是努力将人物写活,抓住人物的精神,从人物的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露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他对历史的评判。但如何将人物写活,生动,有精神,这本身便开创了纪传文学的传统。由于司马迁深刻的历史思想和过人的史识,使得他的人物传记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的高度。
关于《史记》的文学成就,古人今人都作了充分的研究,比如叙事的曲折有致,语言的峻洁生动,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所有这些,都是司马迁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且为后世的叙事和记人提供了典范。但我们要关心的是,是什么使司马迁采取了这样的文学性手段?中国是重历史的国度,史学传统很早就建立了,这就是不隐恶的直书实录传统。实录的精神,应该是不需夸饰的,传世文献如《尚书》、《春秋》,的确是具有这样的特征。当然,即使是《尚书》、《春秋》,也往往为了加强力量而使用夸张的手法。《论衡·艺增》举《尚书·武成》记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事例说:“言血流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但这种夸张,并未脱离事实,是修辞而已,与后来传记文学的夸饰还不同。从《左传》开始,夸饰已经在史书中占有了极大的比重。比如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对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季隗说:“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夫妻间语,不入史书,史家如何知道?又成公二年晋、齐鞌之战,郄克、解张、郑丘缓间的对话,反映了晋国将帅间同仇敌忾的斗志,有助于突出人物的精神和性格,增强叙事的生动性。但这种对话,恐未必是史家实录,这都是作者根据叙事的需要,夸饰而成,然无损于整体事件的真实,反而加强了信服力。其实史书作者的记叙,从来都是有倾向性的,即使《尚书》,如上引武王伐纣的记载,分明反映了作者对武王的支持态度。根据作者的主观倾向,对历史事件进行一定的加工,这在孔子删述《春秋》中,就树立了史学的原则。孔子所删《春秋》,本来只是鲁国史书,但孔子在微言中寄寓了他的褒贬,从而使乱臣贼子惧。比如《春秋》隐公元年所书“郑伯克段于鄢”,书“郑伯”,书“克”,书“段”,都是有深意的。杜预注说:“不称国讨,而言郑伯,讥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郑伯虽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隽杰,据大都以耦国,所谓得隽曰克也。”在字词的使用上,寄寓作者的褒贬,成为后世史书传统。但微言未免难以领会,所以“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①《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中华书局标点本。重新将其褒贬之意,用具体的事件阐露出来。因此,《左传》的叙事,实际上是继承了孔子删《春秋》的传统的。
相对于早期史书的记言和简单的编年,具体的叙事都属于夸饰。但在不违背史事的真实基础上,生动的叙事,乃至在叙事中插入悬想性的细节,以及对话、心理描写,既是叙事艺术的需要,也是读者的要求。战国以后,史书如《国语》、《国策》,都是这种趋势的反映。简单的纪年,如秦史记,一方面是秦人文化落后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并不占当时文化的主要地位。因此我们说,《左传》、《国语》、《国策》这些史书的叙事,其实是出于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在这种产生过程中,显现了文学艺术的特征。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特征,产生于史学,是逐渐从史学写作中分化出来,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成熟并为独立的学科——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来说,这时期的文学学科还没有独立,他的史书写作,只是遵照着已有的史学传统而已。但是《史记》的写作,较之前有的史书,在夸饰艺术上,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为后世的传记文学开辟了道路。
司马迁之前,《左传》、《国策》在描写人物上,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产生了很多名篇。如《战国策》写荆轲刺秦王事,基本为司马迁《史记》所承袭。①关于荆轲刺秦王之事,《国策》与《史记》所记基本相符,后人因怀疑刘向撰次《国策》,在汉以后残阙,后人遂以《史记》文字补充,此节即抄录的《史记》。参见方苞《书剌客传后》,载《望溪集》卷二,《四库全书》本。但近人郑良树根据楼兰出土汉代帛书《战国策》残叶反对这一说法。说见《战国策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其易水送别一段,《史记》更是不改一字,可见《战国策》在塑造荆轲形象上的成功。荆轲易水之别,慷慨悲歌,形象生动,千载之下,犹如生人,但诚如前人所说,可议处颇多。姚苎田《史记菁华录》说:“《国策》荆轲刺秦王一篇,文章固妙绝千古,然其写荆轲处,可议实多。如聂政尚不肯轻受严仲子百金之馈,而轲则早恣享燕太子车骑美女之奉,一也;聂政恐多人语泄,独行仗剑至韩,而轲则既必待吾客与俱,又且白衣祖饯,击筑悲歌,岂不虑事机败露?二也;聂政抉面屠肠,自灭形迹,轲乃箕距笑骂,明道出欲生劫报太子丹之语,三也。至以虎狼之秦,而欲希风曹沬,约契不逾,其愚狂无识,更不足道矣。”②《史记菁华录》,清道光四年(1824)扶荔山房刻本。这个故事显然有所夸张,与事实不一定相符,但司马迁却写入《史记》,说明司马迁旨在突出人物精神的史学思想。司马迁不惜在细节上用力,以达到叙事的曲折和人物的生动效果,这在《史记》一书中,是俯拾即是的。比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胯下之辱一节,细细描摹,旨在突出韩信的沉毅和远大报负。大勇不及目前,这一点在《刺客列传》中也有表现。如荆轲游过榆次,与聂盖论剑,聂盖怒而目,荆轲遂走不复还。聂盖以为荆轲怯懦,实不知荆轲志尚高远,士不遇知己,徒死无益,为后来刺秦王之举伏下衬笔。这一细节,《战国策》不载,而司马迁采择而且重彩描摹,是司马迁立意与人不同。这与司马迁自己遭不测之祸,隐忍苟活,欲成《史记》的报负相符,所以司马迁不仅选择入史,而且密致经营,是有太史公自己的用意的。
从《国策》到《史记》,我们可以见出西汉初时的叙事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汉书·艺文志》特列小说一家,说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引如淳说:“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以街谈巷说的细碎之言为小说,当指其叙述故事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是司马迁选择的材料之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放失旧闻”,应该包括民间流传的故事。因此,《史记》一书叙事的曲折动人,也反映了当时民间故事的叙述水平,这也说明《史记》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综观《史记》的人物列传,虽以生平为线,但司马迁在选择材料,安排结构上,都独具匠心,尽量集中、鲜明,曲折有致。一些在本传中不适宜展开的材料,则巧妙地使用互见法。比如《高祖本纪》,多写其细微及灵异之事,而于定鼎平天下的大事,则置于诸功臣传中。此外,本传主旨在于突出传主之所以立传的事迹,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则置于别传中。因此阅读的时候,应该结合其它篇章,才能全面了解历史人物。比如刘邦,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述其败逃时,数次推堕孝惠、鲁元,显示刘邦危亡时连亲生儿女都不顾的狠毒。显然,这样的材料不适合用于本纪中。司马迁这样的安排,使本传叙事集中鲜明,又能够保持生动曲折的效果。否则如后世本纪,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卒读。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司马迁以人物为史记的思想,只有将人物写活,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发展变化的脉络,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准确描摹人物的性格、语言,都是为这个思想服务的。选择哪些事件、语言来勾划人物什么样的性格,则出自司马迁对人物的评判。司马迁对历史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他自己的判断,因此,首先在选择哪些人物入传上,他就全盘仔细地考虑过。而入选人物要表现他的什么作用,也都在材料的选择和人物的描写上传达得清清楚楚。司马迁《史记》全书选择一百余人列传,从传说中的五帝始,所选择人物都与作者志在探讨古今存亡迁变有关。从全书的布局结构看,《史记》显然是详今略古。这是有原因的,一者,司马迁持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古须为今用,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略推三代,录秦汉。”就是说对三代是略述,对秦汉间事则是详录。二者,上古文献,书阙有间,加上其中穿凿附会,怪异传说,荒诞不经之事甚多,司马迁本着信实考异的态度,不加使用。①《大宛列传赞》:“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事实上,作为传记文学,《史记》最吸引人的,也正是秦汉人物的描写。这些人物,经司马迁如椽之笔,一个个都栩栩如生。即使如秦始皇,其统一全国之后,专制雄决,一意裁断的霸气,毕露于《秦始皇本纪》文字中。至于项羽,更是司马迁倾尽心力之作。项羽未成帝业,而司马迁列于本纪,这一直受到后人的批评。但司马迁《项羽本纪赞》中明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正是项羽的历史作用,故司马迁破例将其视为帝王而入于本纪。《史记》以五体纪事,结构谨严,但时又有破例之处,如列吕后本纪,但不列汉惠帝本纪,又西周诸侯管叔叛逆,宗庙不守,但司马迁却列《管蔡世家》,如此等等。后人的批评虽有一定道理,但司马迁撰史自有他的考虑,司马迁所处的历史环境已非后人所能感受。秦汉之际,群雄逐鹿,陈涉首先发难,继而项羽、刘邦相争,均以布衣而翻覆强秦,当是时,三人均有可能成功的机会,但最终的结果是由刘邦统一天下,那么刘邦为什么会成功呢?陈涉、项羽为什么会失败呢?这成功和失败的究极原因是什么呢?这正是司马迁所考虑的。因此,司马迁特撰有《秦楚之际月表》,表示了他对由秦至汉之际,历史变化趋向的关注。以《史记》刘邦本纪和项羽本纪相较,我们明显感受到司马迁对项羽的偏爱和惋惜。他对项羽事迹的描写,时时充满着讴歌英雄的情感。他用“才气过人”概括项羽。在司马迁笔下,才气过人除指具有超越别人的才气外,还指富于创造性地敢做别人不敢做之事。《史记》中另一位荣膺此号的是李广,李广善射,但他“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这是常人所不敢为者。项羽表现得更为充分。如巨鹿之战,司马迁写他于晨朝上将军,即其帐中斩宋义头,随后号令诸将,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其勇决与大智,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气过人”。及败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英雄气概,顿让后人生出无限敬慕。相较于项羽,刘邦却有十分的流氓气,司马迁用“好酒及色”写他,虽在本纪中添加了那么多的神异符验之事,但刘邦的所作所为,的确不能算作英雄。司马迁有意为项羽和刘邦各写了一个初见秦始皇时的细节,项羽是英雄豪气:“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充满了艳羡的口吻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事实也确如这样发展,项羽最终取秦帝而代之,而刘邦则享项羽成果,当上了皇帝。《刘敬叔孙通列传》记刘邦按叔孙通为他安排的朝仪受群臣朝拜后说:“吾乃今知为皇帝之贵也!”其境界仅至于此,与项羽确不可相比。但问题就在于刘邦最终成功,而项羽却失败了,其间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这也正是司马迁所要探讨的。《项羽本纪赞》中,司马迁总结说:“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乗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是项羽的历史贡献。司马迁又说:“及羽背闗懐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是项羽终以不师古法,独以武力征天下而失败,是天助德而不助暴力也!
太史公深得《春秋》笔法,故读《史记》,要善于在字里行间读出太史公的用意。比如合传的安排,都是有深意的。如《老子韩非列传》,以老子、庄子、申子、韩非子四人合传,似为后人所不解,实则反映了太史公对先秦道家与刑名之学关系的看法。诚如宋儒真德秀所言,老子之术,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此阴谋之言也。阴谋之术,则申商、韩非之所本也。究其实,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老子》一书,乃君人南面之术。故太史公将四人合传,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韩非子》有《喻老》、《解老》二篇,诚是注脚。故太史公以四人合传,寓其对老子道德之弊流于刑名之深意。①参见李景星《史记评议》,济南精艺印刷公司,民国21年。
再如《张耳陈余列传》,借张、陈二人由交情至交恶,写利禄对人情的损害,作者对人世间真情挚谊的感叹,深寓其间。盖张、陈二人是秦汉之间最为天下人传诵之事,他们的刎颈之交,亦为天下人所赞叹。然而面对利禄,竟然成死敌,其事亦令人感慨。司马迁说:“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取卿相者。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一篇《张耳陈余列传》,主要围绕这个意思着笔。所以,陈余、张耳卒后,司马迁又以较多篇幅写了张敖宾客贯高之事。表面上看,似乎是张敖附传,其实张敖并不是主角,主角是贯高。司马迁用了许多的热情写贯高能够重然诺,有节义、侠气,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非常看重的。《史记》一书,往往有许多并不尽合于公家及王者思想之处,也就是说,司马迁抒写许多纯属个人感情和意气的内容。比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因出击雁门为匈奴所擒,后脱逃得归,免为庶人,一次在霸陵亭受亭尉呵辱。后李广重新起用,“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个细节起码不算光彩,却很典型地反映了李广嫉恶如仇的性格,同时也可见出司马迁对小人的厌恶。
再如《刺客列传》,实事求是说,司马迁《刺客列传》所列五人,的确让后人不甚理解。五个刺客,性质不尽相同,事迹亦无法让人感动。比如专诸,完全因为伍员欲借吴王报私仇,吴王不允,故进专诸于公子光以谋刺吴王。则专诸之剌吴王,并不值得称道。再如聂政,只因严仲子表面上尊敬他,且予以百金,即愿意赴韩刺杀韩相侠累。而严仲子之刺杀侠累,亦仅是个人间恩怨。那么司马迁要宣扬什么呢?在《传赞》中司马迁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比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司马迁是要宣扬他们所具有的义。但究其实,确是属于司马迁个人的思想。苏辙《古史》说:“周衰,礼义不明,而小人奋身以犯上,相夸以为贤,孔子疾之。齐豹以卫司寇杀卫侯之兄絷,①《春秋·昭公二十年》:“秋,盗杀卫侯之兄絷。”杜预注:“齐豹作而不义,故书曰盗,所谓求名而不得”蔡公孙翩以大夫弑其君申,②《春秋·哀公四年》:“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杜注:“贱者,故称盗,不言弑其君,贱盗也。”《春秋》皆以盗书而不名,所谓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传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类耳,而其称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故《史记》列传以伯夷、叔齐为首,意在表彰其让国,皆是一家之言。然伯夷、叔齐善人,却饿死首阳山,司马迁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蚤夭,天之报善人,其何如哉?”又举历史上行恶之人如盗跖,竟以寿终,故司马迁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对于这种现象,司马迁也只好说:“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称其欲“究天人之际”,实则在列传第一篇就表现出对这些现象的大惑不解,而感愤伤时,遂以伯夷列为第一篇。葛洪曰:“伯夷首列传,以为善而无报也。”①《增订史记评林》引。明治二年日本东京玉山堂版。《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故司马迁欲树伯夷以激世之廉让之风。李光缙《增订史记评林》引赵恒曰:“言夷、齐以烈士徇名,得夫子序列而名益彰,宜无怨也。惟夫岩穴之士,砥行立名夷齐者,后世不遇夫子,而名不传,为可悲可怨耳。通篇委曲感叹,子长盖自许而自伤也。趋舍有时,言其所趋在此,则所舍在彼,趋宝贵则舍令名,趋令名则舍宝贵。‘若此类’,若伯夷类也。”
司马迁对人物的喜、厌之情,表现得是十分地鲜明的。喜欢的人物如李广不称名,而曰“李将军”,韩信则称“淮阴侯”,对于他不喜欢的历史人物,太史公的厌恶之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如《李斯传》先从李斯见吏舍厕中食不洁之鼠而悟出人生哲理写起: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所言,道理当然是有的,但未免于落于鼠辈,且于食不洁中有悟,则其人品之低下,开篇便见分晓。至于李斯落败,乃与其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正如前人所评:“发端于鼠,结束于犬,是史公贱鄙李斯处,恰好首尾相应成趣。”②日本学者竹添井井评语,见《史记钞》第四集,《历代古文钞》卷十一。日本奎文堂,明治十八年二月。李斯思欲上蔡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而自己却成为秦二世所逐之兔,司马迁鄙视之意,可谓入骨矣。
《史记》的叙事艺术水平之高,可谓出神入化。我们可以说《左传》是为了传《经》,其所写人物及叙事,未必均有作者主观故意,《史记》的叙事却实在有作者的故意布局。我们可以《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例。
此传题为“廉蔺”,但其实却写了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等人,故蒲二田说:“题当作廉蔺赵李列传”。为什么这四个人列为一传呢?因为都是赵之良将,赵之存亡系此四人身上。储同人说:“以四人系赵存亡,合作一传,错综变化,出圣入神。”③《史记钞》引,上揭书。按照我们看到的后世的史书,同传的写法,无非是每人一传,各写各的,但司马迁不同,此传以廉颇开篇,但简单介绍以后即转入蔺相如。蔺相如传主要写了完璧、与秦盟会及廉、蔺关系之事,较廉颇传应该是非常详备的,人物精神也比廉颇鲜明。廉、蔺列传,但重在蔺上。然而廉颇在全文结构上却起着重要的勾连作用。蔺相如事迹写完以后,如何过渡到下文的赵奢传呢?司马迁用“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一军,居二年,廉颇复伐齐,拔之。后三年,廉颇攻魏防陵、安阳,拔之。后四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其明年,赵奢破秦军放阏与下。”由廉颇攻齐之纪年自然过渡到赵奢。赵奢亦是赵之良将,赵亦赖之而存。赵奢因功而封为马服君,司马迁这时加上一句:“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是赵奢亦与廉、蔺二人照应。赵奢之后,赵王任用赵括,兵败被杀,从而导致赵国由盛转衰。但司马迁转到赵奢传,亦由廉颇过渡,所谓“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于是赵王信秦人离间计,以赵奢子赵括代廉颇为将,于是引出赵括一传,而由赵括之败,亦带出赵国由盛转衰,这样的叙述,又是靠廉颇勾连的。由赵括至李牧,司马迁又以廉颇为牵引,写廉颇领兵击燕,燕割五城求和,于是赵封廉颇为信平君。其后六年,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乃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而后奔魏,遂乃引出李牧。对此线索,前人评曰:
秦赵交关是此传主笔,以四人系赵之存亡,直至秦灭赵,乃一篇归宿处,亦千古任将得失之林也。以赵之世次年月为线索,故忽而廉、蔺,忽而赵、李,极断续离合而无些子痕迹,彼以串插去陋矣。太史公列传中,其法无所不有,真千古妙文。①清高嵣《史记钞》卷三,乾隆五十三年培元堂刊本。
以世次年月为线索,确是司马迁贯穿传文的手段,然亦常有变化,既勾串全文,亦能引人入胜。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时代悬远,而司马迁以年代相勾连,既文脉绵延不断,亦寓有剌客精神之不断传承之意。诚如李景星所分析:
刺客列传共载五人,一曹沫,二专诸,三豫让,四聂政,五荆轲。此五人者,在天地间别具一种激烈性情,故太史公汇归一处,别成一种激烈文字。文用阶级法,一步高一步,刺君刺相,至于刺不可一世之王者,刺客之能事尽矣,是以篇中叙次,于最后荆轲一传独加详焉。其操纵得手处,尤在每传之末,用钩连之笔曰:“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上下钩绾,气势贯注,遂使一篇千言大文,直如一笔写出,此例自太史公创之,虽后来迭经袭用,几成熟调,而兰亭原本,终不为损,盖其精气有不可磨灭者在也。②参见李景星《史记评议》,济南精艺印刷公司,民国21年。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的确,《史记》一书掩抑悲藏,常常摧人泪下。这一是因为《史记》所述人物,多慷慨悲歌之士,其事迹照耀千秋,感动后人,二则与司马迁于叙事中寄托个人的激烈情怀有关。司马迁世为史官,年轻时就为做史官作了学术与阅历上的准备,但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去世时,以继《春秋》,述史记相嘱托,他才真切地体会到这一责任的重大。正当他埋头撰述,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遭遇了李陵一案横祸。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打击是刻骨椎心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隐忍苟活,“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③《文选》卷四一,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嘉庆十四年刻本,1977年版。撰述《史记》成为司马迁生命中唯一精神支柱,而他也把心中的沉郁悲愤,一一寄托于所传人物之中。忍辱负重,成就大事业,亦成为司马迁《史记》入选人物的一个衡量标准,如勾践、伍子胥、季布等人都是。在他们事迹的叙述中,司马迁都基于这一点加以赞扬和肯定,因为这与司马迁的精神是相通的。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中的人物描写,是服从于他对历史的思考的。描写中使用的手段,也都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主旨服务。达到了这一点,就是他所说的“成一家之言”。没有人能够具有他那样的史识和历史洞察力,所以他开创的人物传记写作手法,也就没有人能够继承。自班固以后,虽然继承了他的基本体例,但在人物选择和描写上,既没有能力,主观上也不愿意效法。但是,司马迁这样的描写,却开创了传记文学的传统,成为文学史上典范之作。自此以后至东汉,文学逐渐自觉,渐渐独立为一门学科,它有自己的特性,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学的作用和价值,那是司马迁以后时代的历史任务了。
—— 蔺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