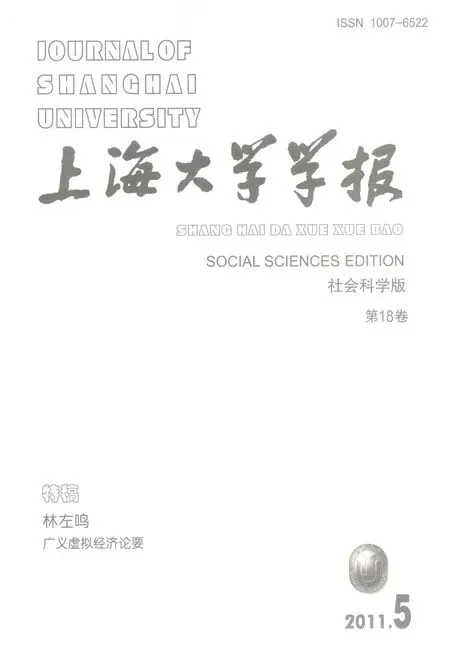试论华语电影的思想性危机
王志敏
(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学系,北京 100088)
据我的观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直至21世纪头十年的大约三十年间,华语电影经历了一个思想性探索的崛起及之后不断衰减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可以说,华语电影已经出现了思想性危机。这一过程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大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则是国际冷战思维的纠缠及其难以为继,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国际霸主行径的彰显对其自身形象的损毁。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证需要大量细致的研究,而我的论文只能通过对个案的简单枚举和勾勒式的描述对此现象进行阐释。
最近的一些媒体报道描绘了华语电影参加今年戛纳电影节的这样一幅图景:陈可辛导演,金城武、甄子丹、汤唯主演的影片《武侠》亮相于午夜展映单元,参加展映(展映影片数百部);除了陈可辛的《武侠》,成龙的《辛亥革命》、程小东的《白蛇传说》和徐克的《龙门飞甲》,都到现场卖片,徐克更是亲临现场。《武侠》在戛纳电影宫正对面高高悬挂起大型户外广告牌,亮底蓝字非常醒目,该广告位是电影宣传价格最昂贵的地盘之一,总之,该片是大力营销。此外,还有身着仙鹤红裙的范冰冰惊艳登场,身着紫色长裙的巩俐艳压群芳,两位华人杜琪峰和施南生加盟德尼罗担任主席的评审团耀眼阵容。虽然电影节贵在参与,众人乐在其中,但却无法掩饰在这次电影节20部竞赛影片中华语电影无一入围,华人再度沦为看客的尴尬。这一情景,对于当下华语电影现状来说,具有某种象征性。联系到16年前陈凯歌携影片《风月》参赛戛纳电影节时说过的豪言壮语,更加耐人寻味,陈凯歌说,他到戛纳,不是去“叫卖”,而是去参与,去挑战的,是为华语电影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的。
戛纳电影节的入围和获奖影片,历来以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重要指标著称。从近年来华语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中由“挑战”到“叫卖“的发展态势来看,先不论其艺术性状况如何,但确实出现了思想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华语电影的领军人物、风云人物、弄潮人物、标志性人物几乎是集体出现了作品思想性的明显衰减。最具标志性和具有表征意义的作品,是黄建新导演的一部影片《求求你表扬我》(2004)。此外,还有王家卫的《2046》(2001),李安的《色·戒》(2007),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三枪拍案惊奇》(2009)和《山楂树之恋》(2010),陈凯歌的《无极》(2005)和《赵氏孤儿》(2010)等等。这些影片都暴露出创作者思想性匮乏的征兆。
据说,为《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黄建新导演筹备了三年的时间。但是,他却在影片中给观众提出了一个假问题,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个并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影片的故事梗概是:家住农村的打工仔杨红旗来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要求在报纸上表扬自己,理由是他救了一个险遭坏人强暴的女大学生欧阳花。当古国歌找到欧阳花证实此事时,欧阳花却矢口否认了此事。古国歌在继续调查中发现,杨红旗的父亲是一位卧病在床却把荣誉视为生命的劳模,他渴望能在自己生命弥留之际,看到儿子得到一次表扬。面对老人的期待,儿子的诉求,女孩的名誉,古国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惘和困惑,丧失了判断力,不知如何取舍。
据黄建新导演说,他经常对某些东西判断模糊,当无法概括一件事的时候,只能用表述的方式。就像这部电影,强烈要求得到表扬的打工仔,一心想挖掘事实真相的记者以及不想让别人知道事实真相的大学生,每个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都没有错,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到最后每个人都背离了原始的初衷。尤其在现实生活中,实用主义已经代替了理想主义,不知道我的片子能否表达一些。本片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弄清一个事实。其实,对这部影片来说,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不重要的,而受害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黄建新曾经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导演。他的一系列作品向来都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现实生活,勇于探讨严肃的社会文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是一位少见的愿意肯定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勇于进行电影艺术创新和思想探索的导演。他的《黑炮事件》(1985)、《错位》(1987)、《轮回》(1988)、《站直罗,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几乎都是直面社会,探讨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他的作品试图由对具有政治涉指性问题的思考转入到哲学思考性的层面。他的“命运四重奏”:《埋伏》(1997)、《睡不着》(1998)、《说出你的秘密》(1999)和《谁说我不在乎?》(2001),虽然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却显示了他对政治叙事的突围努力,使他在第五代导演中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为什么一位曾经那么具有敏锐思考意识的导演,会给观众提出一个假问题呢?诉求表扬的劳模之子杨红旗难道不应该知道,当表扬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时候,应当有所限制吗?媒体记者古国歌难道不清楚他除了需要尊重事实之外,受害当事人的利益也在他最重要的考虑之中吗?古国歌难道会愚蠢到不会想到,欧阳花的矢口否认会另有隐情吗?古国歌和杨红旗在影片中难道不应该有更推心置腹的交流吗?受害人欧阳花作为一位当代大学生难道不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伤害吗?在这里难道能够看到所谓悖论的任何影子吗?导演为了让影片中所表现的问题变得具有可思考性不惜采取了让所有的关涉者,如杨红旗、古国歌、古国歌的妻子、欧阳花,还有欧阳花的毕业接收单位的负责人,都一致地“平均幼稚化“的手法。一般来说,这种手法并不是不可以在影片的创作中使用,但是,恰恰是在这部意在引起人们认真思考的影片中不应当使用。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部以思考的名义拍摄的其实不需要思考的影片,2005年获得了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特别奖和最佳编剧奖,还获得了CCTV6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探索精神奖和最佳剧情片奖。
这里还要提到黄建新导演的另一部几乎被人们忽略的影片。在他执导的影片当中,几乎全都是现实题材,只有一部是例外,这就是《五魁》(1993)。当年这部影片曾受到戴锦华、李奕明的严厉批评。他们一致指责这部影片的现实涉指性缺失。但是,当我们把这部影片同何平导演的影片《炮打双灯》(1993)和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风月》(1996)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指责可能存在的问题。
这些影片都是海外投资,表现的都是社会地位悬殊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表现的都是一个假定性很强的旧中国的历史性的故事。都相当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浓重的历史氛围。值得关注的是,评论者的评论与创作者关于影片立意的说明之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没有注意从创作者立意的角度来加以评论。他们都没有观察到,这三部影片事实上都在讲述一个“空转的故事”。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
《五魁》的故事背景是中国20年代西北农村。当采访者问到黄建新拍《五魁》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点的时候,黄建新这样说:“我当时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个善良的脚夫最后变成一个土匪的故事。由好人变成咱们观念所认为的不好的人,这样一个过程,有二律背反的关系在里头。当然原小说与影片差距很大,我对小说感兴趣的就只是这点——就是一个人物他定位的过程,而这中间的东西都可以替换。”[1]打个比方说,父亲是好父亲,子女是好子女,但放在一起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当采访者问何平拍《炮打双灯》的初衷和着眼点是什么的时候,何平也是这样说的,他提到两点,一是“正正相加得负”的人文思考,二是燕赵文化的苍凉感。关于第一点,他说:“小说提供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一个画年画的和一个做爆竹的,从事的都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喜庆行当,而两者的相加却产生了悲剧。也就是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人们的普通生活中,画门神、造爆竹,避邪驱患,辞旧迎新,都是百姓寄托美好愿望的事情,为什么两个延续千年的风俗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悲剧?……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最初偏爱上某种事物,决心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其它的乐趣在里面,不光只是电影的本身。”关于第二点,他说:“北方文化分两大系,从文化的悲壮上讲,一是齐鲁文化,一是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更接近豪迈,《水浒传》的英雄都是齐鲁文化的英雄,而燕赵文化则更接近苍凉,为什么冯骥才本人把自己文学的重点放在燕赵文化上,是因为燕赵文化比较接近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就是说,它悲壮里面加着浓重的苍凉命运感,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种人文精神,我们之所以要花费一笔资金去制作或者说去复制一段历史,一定是会与当今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周围的人,目前的这个社会在人格方面所缺少一种力量、一种典范或是说缺少一种精神、活人的精神,那是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希望去表现的。”[2]
关于《炮打双灯》的立意,该片美术指导钱运选在1995年《电影艺术》第1期上著文说:“描写贫富悬殊的男女爱情古已有之。外国的《简爱》、《茶花女》、《阴谋与爱情》,中国的《西厢记》、《牡丹亭》、《家》、《春》、《秋》,大都超不出一个定式,总要有一位家长式的人物或上层统治者的代表来扼杀和摧残纯洁的爱情,大多是下层人要‘革命’,上层人不准‘革命’。然而《炮打双灯》中春枝和牛宝的爱情故事却是主子要‘革命’,奴才不让‘革命’。《炮打双灯》的特色就在于此。”“春枝是能左右一镇兴衰的有三百年制炮历史世家的主子,至高无上,一呼百应,但却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与画工牛保的炽热爱情遭到了管家、掌事、王妈乃至奴仆的反对,由此演出了曲折感人的故事。”
陈凯歌在谈到《风月》时这样说:“《风月》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我们讲不谈政治,只谈风月,但在‘风月’两个字后面有更重要的人性内容。讨论在某一种社会形态下男女两性的关系。整部影片基本是在分析和判断,男女两性在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社会门坎时各自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这部作品保持着我过去一贯有的思考和判断,是一个处在由我们单独的个人所不能控制的社会变动期中间,人们的感情发生变化的故事。我是用我自己的观点比较细致地去说明男女两性现存的关系是什么,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看来很明显,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从个人的命运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强调了“个人所不能控制的社会变动”。[3]这部影片表现了一个女主子如何变成了一个植物人的故事,总之,这里陈凯歌强调的是社会批判。
评论者对这种表白是不感兴趣的,尽管这些表白中确实涉及到了结构问题。由于《风月》在戛纳电影节受到了冷遇,得分不高,评论者就更加不客气了。影片被认为是“玩弄技巧”,“制造空洞而无生命的故事”,“展示的只不过是用电影手段表现出来的虚伪假象”,“导演选择这样一个悲情故事,是为了制造一个空洞的谎言”,“虽然能从影片中感受到昔日中国的地道原味,但这种故事已经老掉牙了”。中国的评论家很容易就从影片中看到了一个并不新颖的已经“老掉牙的铁屋子”的故事。
戴锦华在提到《五魁》时说,《五魁》似乎是黄建新的一次“闪失”,一处“歧路”,一次对文化时尚的屈服;也许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与拓展。[4]李奕明相当明确地说,“第五代电影如今已风骨尽失,徒存皮毛。其证明就是一向与第五代若即若离的导演黄建新却在1993年拍了一部貌似经典第五代形态,实际上只徒有其皮毛的影片《五魁》”。[5]张颐武在评论影片《炮打双灯》时指出,该片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国风俗的奇观化;二是缺乏现实涉指。他认为,这部影片具备了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几乎一切经典的特征,“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有关‘中国’的寓言。它依然有一个闭锁的、巨大的院落,有奇异的民俗,有一条滚滚滔滔的大河,有生死的缠绵与人性的透视。它给我们看到了灿烂的烟火,美丽的男装的东方妇人,古老的手艺与严苛的家规。这一切再一次把‘中国’化做了一个‘民族寓言’。这里没有对中国当下语境的具体‘状态’的探究,而是以运动的长镜头不断地窥探一个静止的空间”。李奕明以张颐武《〈炮打双灯〉:寓言的困境》一文中的观点为基础,并进而批评这部影片“于今天大陆的现实及女性的生存境遇毫无涉指关系”。“这一寓言化的致命困境在于它与当下中国的信仰与道德重建毫无关联,支撑着这种寓言内部运作的男性/女性、压抑/释放、逃脱/落网等二元对立结构,并不能构成今天中国文化中信仰与道德的主要冲突,因而在大陆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并不具有历时性的意义,而只是一些共时的抽象主题,也就不能为今天国人的文化匮乏和道德困境提供任何启迪性意义和解决的路径,更无从为他们提供任何心灵上的精神抚慰。因此这种寓言性的主题就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和人生哲学。坦率地说,国人不需要这种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体验无关的寓言化的影片。”[6]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三部影片究竟讲述了什么样的“空转的故事”。
《五魁》讲了一个女子嫁人的故事,影片一开始表现一个年轻的女子要出嫁到一个有钱人家,路上遭到抢劫。这个女子要嫁的人家老爷已死,夫人和少爷尚在。在迎娶的同时,夫家遭土匪,少爷在与土匪打斗中身亡。出乎意料的是,年轻女子竟被其佣人五魁救了回来。影片故事构思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嫁人可以“照样”进行。这个家庭就好像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生命力表现在,当它的真正的主人已经不在了的时候,它还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具有运转能力,它还能像它的主人仍然存在一样维持运转。当然,我们还能够从这个故事中确切地感受到,它固然是在运转,但也是在“空转”。它的作用就是严格地保证一个女人与一块木头丈夫的“生活”。在这里,机构本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主人的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是已故主人的母亲,即她的婆婆。观众很清楚,她的婆婆像她本人一样曾经是这个机构的受害者。她就像《香魂女》中的香二嫂一样,过去是一个受害之,现在却成了一个施害者。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点金术,但使这一切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家庭机构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座落于浩瀚沙漠之中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孤零零的家庭的存在本身都令人怀疑。
由何平导演的影片《炮打双灯》同样对“家庭机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家族机构”)的“空转”现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影片中的蔡家“少爷”是一位19岁的美貌女子。她在蔡家爆业家族中的全部力量,只体现为她作为该家族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即主人被规定的力量,在这个家族机器的“正常”运转中,她是这个家族机器的代表,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机构的运转,并不取决于她个人的主观意图。为了有效地防止这个家族财产的外流,这个家族的祖上规定,她不能同外人结婚。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爱上了一个画年画的青年牛宝,更在于她竟然天真地相信自己同牛宝相爱的善良愿望能够为这个家族机构所允许。这个故事的悲剧性还在于,血气方刚的牛宝竟然相信他能够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赢得这个家族的主人的身份。其实,这种竞争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他绝对输的命运。在这一点上,牛宝采取的是认同这部家族机器的方式,而五魁却终于看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五魁是通过当土匪的造反方式,惩罚了婆婆,最终赢得了小姐。
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风月》对这种空转现象的探讨似乎更为深入。在影片中,江南大户庞氏家族的老爷去世了,少爷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家族的掌门人,但问题在于,不久,少爷被他的小舅子害成了“植物人”,使这个家族面临着与《五魁》和《炮打双灯》的故事中几乎是同样没有主人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由庞家的小姐来充任主人的角色,但是,当小姐也被害成为植物人以后,就只有选择一个属于庞家远支的实际上是一个下人的端午来充任这个位置。他倒不是一个植物人,但观众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并非植物人的活人在这个完全有能力自行运转的家庭机构中的作用,也只能是形同植物人。当观众体验到这一点以后,可能进一步体会到,即使小姐健康如往常,她的作用在实质上也仍然像植物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故事中,除了少爷的小舅子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戏剧行为的主动性,这个人恨这个家族,他甚至很有个人魅力,但对家族运转毫无办法。他可以害死这个家族中的某一个人,但他无奈这个家族本身。
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三部影片的故事是相当不同的,但是,都讲述了一个老爷去世以后的关于少爷(或少奶奶)的故事。这三个故事的一致性在于,老爷去世以后,少爷可以顶替老爷,但少爷也去世了,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少爷,这个家庭(或家族)还能运转吗?影片告诉我们,能运转,只要有一根木头,或者小姐,植物人也可以,或者随便什么人,只要家庭机构还存在就行。
可以看到,这些观影的体验,与前面提到的关于创作立意的想法确实具有某种关联性。比如,五魁为什么要成为土匪呢?年画的喜和生产爆竹的喜为什么最后成了悲呢?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家庭或家族的结构力量。
我们看到,这些中国最具思考力度的导演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结构的力量。结构主义承认结构是有力量的,但这种力量不一定就是进步的力量。就是说,一个人追求理想,仅有良好的愿望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看到的这些影片的确能够表明,导演已经关注到了中国历史及现实中的机构性“空转”现象。这些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必然要遇到的同时也是必然要提出的体制改革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些导演们对它只是有了某种不够清晰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观点,甚至可能来源于结构主义思想在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的传播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一再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式总是很快就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如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改革的任务必须不断地被提出。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影片基本上没有被从导演本人所表述的创作初衷的角度来加以评论。但须指出的是,尽管这些表述看起来还不够明朗,但是却为这些影片的“互文本“情况所暴露。也就是说,这些影片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需要思考但却不被思考的问题。
由此可见,导演的立意乃至作品本身的意蕴,并非没有关涉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当下迫切的现实问题。但是,导演本人的立意及作品意蕴未能得到批评家认同的事实,又确实能够表明,这些影片在表意方面可能存在某些重要的不足。比如说,创作立意的自觉性、故事本身的合理性、视听效果的考虑等等。特别是,从大面积的传播影响的角度来看,故事的合理性对于保证影片的最后成功,它的深刻内含被充分理解,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这三者的完美结合是确保影片成功的最有效的条件。
这些影片,尽管其创作意识尚不够清醒,而且也存在着某些不尽人意和难以解索之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真理置入作品”时遇到了困难。据芦苇说,陈凯歌曾找过他两次来承担《风月》的剧本写作,但是都被他推辞了。芦苇说:“因为我不明白它的指向,对它的形态也不清楚。”但是,这些导演勇于以电影手段表达对于现实的某种思考的努力,却不应该被忽视。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提出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课题已经进入了这些导演的艺术视野和思维之中。他们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想到”,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地“感到”了。尽管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叙事困难。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华语电影中还出现在了一些含蓄内敛、意在言外、富于弦外之音的作品,如李安的《饮食男女》(1994)和《卧虎藏龙》(2000),其中更有一些作品,则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和讽喻色彩,如《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边走边唱》(1991)、《霸王别姬》(1993)、《重庆森林》(1994)、《中国盒子》(1998)、《花样年华》(2000)等等。
李安的《饮食男女》(1994)一方面表明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了解,另一方面更表明他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通。
他在大肆铺排中国饮食、表现似乎是日常的司空见惯的父女关系的故事中,几乎是不着痕迹地隐含了一个“恋父情结”的内核。在这一点上他是自觉的。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证据。第一,他自己承认女儿们心中压抑着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们对多少年来一直不再婚将她们一个个抚养成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同时心中却交织着另一种超越父女之爱的复杂情感。”第二,在一次访谈中记者问:“请问‘卧虎藏龙’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您为什么要取这个片名?”李安回答说:“其实我认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是在表现被压抑的情欲,‘卧虎藏龙’这四个字带着很浓的弗洛伊德色彩。”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似乎并不希望十分明确地引导观众产生后一种联想。他更希望人们将之理解为女儿们对于父亲感情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极端复杂性。大女儿和二女儿对于16年不再续娶而将她们终于抚养成人的父亲的那种感激之情是缺乏自觉和反思的,而且是难以言说的。李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虚拟了或者说利用了一个弗洛依德式的恋父故事,但是却带有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因此,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就是表现父女关系的那种恰到好处的模棱两可的分寸感。影片在表现父女关系时既让人有所感觉,又让人感到莫可端倪,从而显示了李安作为一位电影导演的卓越的剧作功力。
影片开头就设下两个伏笔。第一是朱师傅的朋友老温师傅曾对他说过,如果他不把自己对家珍的真实的感情吐露出来,他说不定会生病的。第二是朱师傅已经丧失了味觉。在一般人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但在影片结尾,我们却看到,家倩要招待一家三口人,而姐姐和妹妹都没有来,只有父亲来了。当父亲喝汤时抱怨女儿做的汤姜放多了。观众们误以为,父女冲突又将重演。但随后观众就被告知,这恰恰证明父亲已经恢复了味觉。特别是在最后,当父亲要求女儿再给他一点儿汤的时候,他握住家珍的手说了一句:女儿啊!似乎欲吐露他对女儿的真情。观众以为他一定会说出些什么的时候,影片却戛然而止。父亲能对女儿说什么呢?对此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无法想像。但是父亲味觉的恢复却有让人回味无穷的效果。外面是中国的,里面装了一个西方的东西。
李安在《卧虎藏龙》(2000)采用的是同样的手法,正如唐代司空图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环寰中”,但是却达到了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这一手法在《色·戒》得到了同样的绝佳运用。在我看来,大多数批评李安的人都是不得要领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其手法的性质。由于叙事策略高超,李安毫发无损。最重要的是,这种叙事策略是中国化的,其精髓就是不露痕迹。这种手法在《卧虎藏龙》里面如此,在《色·戒》里面也是如此,他在故事里面装进一个内核,但是,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就是叙事策略,你想对他进行任何文艺批评,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看过李安的影片《色·戒》之后,很多的人都想批评他,网上也有人发表了大量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对于李安来说,除了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之外,几乎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几乎可以说,三言两语就能驳回去。如果想对其做出切中要害的批评可以说难度极大。因为李安的叙事策略是比较高超的,其精髓就是不露痕迹的指向。当然,这并不是说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但是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王颖的《中国盒子》(1998),影片的意图在片名和片头的处理中就有所表达,但是并不明朗。除了在影片片头外,我们在影片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有关盒子的表现。但是影片的含义还是表达了。这一点,只要有一点儿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懂得:香港终于被收进了中国盒子之中。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盒子并不是一般的盒子,而是一只很像棺材的盒子。这一处理也许可以说是这部影片的定音鼓。王颖是一位拍电影很有中国味儿的美籍华裔导演。《喜福会》被认为是他的杰出代表作。而这部影片所要告诉观众的却是,回归之后,香港人就将生活在不自由的统治之中了。影片着重通过一位香港大学生在1997年元旦之夜的宴会上饮弹自尽这样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不自由是无法容忍的。据一位香港的网客说,大学生自杀的事情,曾在多年以前发生过,但是,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反对香港回归的原因。我曾专门请教了一位香港电影的研究者,他认同了这位网客的说法。这位网客尖锐地指出,这部影片就是要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即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比在中国人的统治下要好。影片的故事是如何表达这个意图的呢?我们不难发现,影片刻意地而且甚至是有点儿恶毒地编造了一位由巩利扮演的曾经是妓女的角色“一女共事两男”的故事。虽然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英国商人(报商)在回英国之前希望娶她,但这个妓女还是嫁给了一个中国老板,据说是因为她喜欢香港。有意思的是,虽然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但是,她似乎更愿意同英国人而不是同她的中国丈夫共眠。从影片的拍摄手法上看,她同她的中国丈夫在一起的镜头往往都是“虚拍”的,而她同英国人在一起的镜头都是“实拍”的。这部影片一个潜在的不言而明的背景是,把大陆描写成虎狼之地。影片中张曼玉所扮演角色的主要目的就是控诉中国的现状。尤其是,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更是非常恶毒但绝对有力的一笔:男主人公在留给女主人公的信中说道,他已经清楚了香港的未来。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未来呢?影片随后就通过女主人公在街上看到的一条鲜活的已被宰割的而其心仍在搏动的鱼的镜头告诉我们,香港人今后的处境就是一种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说的“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所表达的处境。
王家卫更是一位对时间具有刻意经营意识的电影导演。《重庆森林》(1994)中人物口中的稀奇古怪、莫名奇妙的台词果真玄妙得那么难以理解吗?我们那些可爱的大学生影迷们,反复地吟咏和咀嚼着王家卫电影帅呆了、酷毙了的台词,越是不明其意就越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是,一旦当我们发现王家卫对于时间的病态的敏感性,一旦当我们自觉地了解到这是一位中国导演挥之不去的情结的时候,朦胧也许就会褪去,清晰也许就会呈现。人物口中念念不忘的日子表达的是对于一个日子的恐惧。这里纠结的其实不过是某种被称之为“97情结”的东西。我们也许会突然发现,这个日子到来之后某些事情就会变得过期了。有了这个发现,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在五月一日和七月一日之间没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也许可以想一想,倒计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全国人民所关注呢?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王家卫的那些充满了诗意惆怅、耐人寻味并被不断地贴上各种“现代”或“后现代”标签的经典台词吧:
罐头上的日子告诉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先生,这个罐头明天就过期了,你再换一罐吧!那边有很多。
我们分手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她开玩笑。我愿意让她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起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日才过期的罐头。因为凤梨是阿美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日是我的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她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请问有没有5月1日到期的罐头。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几号了?4月30日。明天就过期的东西我怎么会有?还有两个钟头啊!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要买也是新鲜的。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就是你们这种人贪新忘旧的。弄一罐凤梨化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又要栽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可想过凤梨的感受。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一样东西的上面都有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也会过期。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会过期。
就在5月1号的早晨,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在阿美的心目中,我和这凤梨没有什么区别。
在1994年的5月1日,有一个女人跟我说了一声生日快乐。因为这句话,我会一直记得这个女人。如果记忆是一罐罐头的话,我希望这罐罐头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我希望它是一万年。
但是,在王家卫的影片《2046》中,我们除了能够发现片名同“97回归”有关的50年不变的说法的关联以外,我们似乎再也领会不出什么了。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刚刚去世,香港一些人士心存疑虑。邓小平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因为廖公的去世而改变,请大家放心。邓小平当时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15年?”场内没有声音。又问:“30年?”还是没有反应。接着,邓小平伸出五个手指,提高嗓门说道:“50年?50年不变可以了吗?”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也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又强调一遍:“‘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又有人进一步问道:“50年是从哪一年算起?”邓小平回答说:“当然从回归日算起,50年不变。”我们知道,“2046就是50年不变的最后一年。
这一次,王家卫电影对于时间的高度敏感的诗意惆怅的咏叹调就从这一时刻开始:瞻念前程,无限惆怅,忆往昔,《花样年华》,峥嵘岁月稠。正如《阿飞正传》中那句光彩夺目的台词:“1960年4月16日下午三点前的一分钟,我和你在一起。我会记得这一分钟。我们就是这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你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你无法否认的。”这里,我们需要领会和思考的是,过去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哪怕时间被撕成了碎片,化为《东邪西毒》的英译片名“时间的灰烬”(Ashes of Time)。
俱往矣,30年之后,华语电影在经历了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思想探索的崛起及之后不断衰减的过程之后,终于走到了难以为继的思想性危机的地步。世易时移,沧桑巨变,过去那些国内外大的政治背景一去不返,不可逆转,而自此之后,华语电影能否适时地进行转型,完成由政治性的思想探索向学术性的思想开发转换,仍在人们的热切期待之中。
[1]柴效锋.黄建新访谈录[J].当代电影,1994,(2):37-45.
[2]沈芸.《炮打双灯》[J].当代电影,1993,(3):13-18.
[3]冯湄.气犹在,血未凉[J].电影艺术,1996,(1):31-35.
[4]戴锦华.思索与见证:黄建新新作品[J].当代电影,1994,(2):46-52.
[5]李奕明.世纪之末:社会的道德危机与第五代电影的寿终正寝:下[J].电影艺术,1996,(2):24-28.
[6]李奕明.世纪之末:社会的道德危机与第五代电影的寿终正寝:上[J].电影艺术,1996,(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