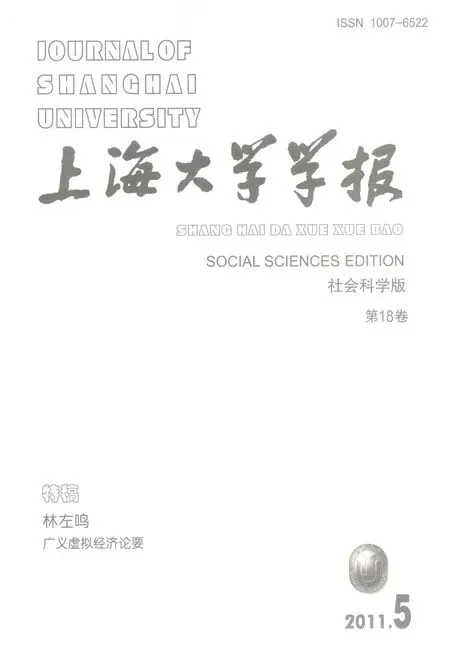《诗·郑风》系年辑证(上)——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七
邵炳军
(上海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诗》的断代研究,至迟从《诗序》产生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从《国语》、《左传》、《论语》等战国以前的文献中看到,春秋时期人们赋《诗》、引《诗》、论《诗》时,往往会提到《诗》中具体篇目的作者,自然亦明白某一诗篇的创作年代。因为,在《诗》之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要了解某首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首先必须了解其创作背景、创作缘由;也只有准确了解某一诗篇的创作背景、创作缘由及其创作年代,《诗》之研究方可做到“知人论世”,方可把握其时代特征,方可进一步考察诗歌创作流变的基本状况及其艺术规律。这就是自汉代以降至今人们依然关注《诗》的断代研究的基本缘由,亦是我们进行“春秋诗歌系年辑证”课题研究的初衷。①所谓“系年”,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考订作品的创作年代,将作品按照创作年代之序重新进行排列,为研究春秋时期不同阶段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奠定可靠的文献依据,从而探求每一个社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与诗歌创作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春秋时期诗歌创作发展、兴盛、衰亡的社会的外在因子与艺术的自身因子,归纳出春秋诗歌创作流变的一般规律。所谓“辑证”,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搜集、整理、归纳先哲时贤关于《诗》断代研究的诸种“异说”,并在此基础上,将诗与史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结合,或自立新说,或补证旧说,或择善而从,从而排定出一个比较可信的诗歌创作年代“谱系”来。《诗·郑风》凡二十一篇,为十五“国风”中篇目最多的部分,占全部风诗总数一百六十篇的八分之一多。本文拟以先哲时贤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我们对《诗·郑风·缁衣》、《遵大路》、《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女曰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九篇创作年代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郑大夫作《缁衣》
《缁衣》为郑大夫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作(毛《序》)。[1]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五说:一为阙疑说,《礼记·缁衣》载孔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2]《孔丛子 · 记义篇》载孔子曰:“(吾)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3]闻一多《风诗类钞》、[4]51刘燕及《新袍子怎么破旧了—〈诗经·郑风·缁衣〉议》、[5]杨凌羽《简论郑风》、[6]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7]皆同。①《礼记》、《孔丛子》之“好贤”说,《风诗类钞》之“赠衣”说,《新袍子怎么破旧了-〈诗经·郑风·缁衣〉议》之“男子对缝衣女的爱情诗”说,《简论郑风》之“爱情”说,《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之“祭歌”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二为郑武公三年(前 768年)之后说,毛《序》:“《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②宋朱熹《诗序辨说》(《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点校四部丛刊三编日本东京岩崎氏静嘉文库藏宋本,朱杰人等点校,2002年)卷上:“此未有据,今姑从之。”案:今本《竹书纪年》:“(周平王三年)王锡司徒郑伯命。”宋朱熹《诗集传》卷四、[8]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八[9]说大同,三家诗无异说,伪《申培诗说》阙文。[10]③朱《传》疑毛《序》“美武公”说,《吕氏家塾读诗记》以此诗为周人所作,然皆从毛《序》作世说。三为郑武公元年(前770 年)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缁衣》,美郑武公掘突也。犬戎弑幽王于骊山,并杀郑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竹书》‘王锡司徒郑伯命’在平王三年,此时武公已除服即吉,不应复以子称,且曰‘适子之馆’,明是周初迁都时栖止未定,故武公暂就客舍以居。然则此诗之作,当在武公初受封为伯而从王入成周之时,其必非在为司徒之日甚明也。”[11]四为泛言春秋中早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作者时代及其评价问题》:“可见,《郑风》恰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其中的大部分,当在春秋中早期产生。”[12]五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郑风》共二十一篇,其本事可考者仅《清人》一首。……此事约发生于公元前六六零年左右。可见《郑风》东周至春秋之间的作品。”[13]笔者此从毛《序》“郑武公三年之后”说。惜其具体创作年代难以详考,姑系于郑武公卒年(前744年)。
二、周公卿作《遵大路》
《遵大路》为周平王公卿欲留郑庄公之作(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五说:一为阙疑说,《文选》卷十九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14]④《登徒子好色赋》李《注》:“此郊,即郑卫之郊。……《大路》,《诗》篇名也。……谓道路逢子之美,愿揽子之袂与俱归也。称此《诗》者,此本郑诗,故称以感动。”宋王质《诗总闻》卷四、[15]朱熹《诗集传》卷四、元刘瑾《诗传通释》卷四、[16]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四、[17]明梁寅《诗演义》卷四、[18]胡广等《诗传大全》卷四、[19]清李光地《诗所》卷二、[20]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二、[21]范家相《诗渖》卷七、[22]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23]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24]及朱杰人《文化视野中的〈诗经〉情诗》[25]皆同,伪《子贡诗传》、[26]伪《申培诗说》亦同。①《登徒子好色赋》之“男女相悦”说,《诗总闻》之“同志相善”说,朱《传》之“淫妇为人所弃”说,《诗演义》之“淫妇留其所与私者之辞”说,伪《诗传》、伪《诗说》之“郐氏夫妇相弃之词”说,《诗所》之“妇人见弃”说,《诗疑辨证》之“朋友交谊之辞”说,《诗渖》之“同僚为君留贤”说,《诗经通论》之“故旧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辞”说,《诗古微》之“留贤之什”说,《文化视野中的〈诗经〉情诗》之“弃妇之诗”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案:朱《传》、《诗传通释》、《诗经疏义会通》、《诗传大全》皆引《登徒子好色赋》谓“亦男女相悦之词”,则其皆持两可之说。二为郑庄公之世(前743年—前701年)说,毛《序》:“《遵大路》,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②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此亦淫乱之诗。《序》说误矣。”三为郑庄公元年(前743年)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遵大路》,周公卿欲留郑庄公也。《左隐三年》:‘初,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君子曰:信不繇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按:《国语》、《史记》,当幽王之时,褒姒与虢石父比,实废平王。而《竹书》又载骊山之乱,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为携王,与平王并立;至平王二十一年,余臣始为晋文侯所杀。然则虢者,平王之仇,宜不得与东迁所依之郑庄等,王不知何意,反贰于虢。此郑庄之所以怨王也。既而王亦自悟暱虢贰郑之非,故有交质之事以自解于郑意。即此诗之所繇作。其后平王崩,桓王立,复欲畁虢公政,于是周郑交恶。庄公如周朝王,王不礼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子,谓郑庄公也。按:庄公以平王二十八年即位,初为周卿士。王贰于虢,当在此时。以即位未踰年,故称子耳。”四为泛言春秋中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作者时代及其评价问题》。五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何氏《诗经世本古义》“郑庄公元年”说。故系于本年。
三、郑大夫作《将仲子》
《将仲子》为郑大夫刺庄公之作(毛《序》)。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阙疑说,《国语·晋语四》载晋公子重耳妻姜氏曰:“《郑诗》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民在上,弗畏有刑。从怀如流,去威远矣,故谓之下。其在辟也,吾从中也。《郑诗》之言,吾其从之。’”[27]上博简《诗论》第十七简:“《(将)中(仲)》之言,不可不韋(畏)也。”[28]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引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卷四、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二及陆永品《略谈对〈诗经〉中爱情、婚姻诗评价的演变》[29]皆同。①《国语》、《诗论》之“畏人言”说,《诗辨妄》之“淫诗”说,《诗总闻》之“女辞男”说,《诗疑辨证》之“拒间其宗族者”说,《略谈对〈诗经〉中爱情、婚姻诗评价的演变》之“情诗”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二为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说,毛《序》:“《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②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事见《春秋传》。然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而说者又从而巧为之说,以实其事,误益甚矣。今从其说。”案:隐元年《春秋》:“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隐元年《左传》、《史记·郑世家》详叙此事,不具引。三家诗无异义,伪《子贡诗传》阙。三为泛言春秋中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作者时代及其评价问题》。四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毛《序》“郑庄公二十二年”说,且据今本毛《诗》篇次系于《叔于田》之前。
四、郑人作《叔于田》
《叔于田》为郑人刺庄公之作(毛《序》)。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郑庄公之世(前743年—前701年)说,毛《序》:“《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③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国人之心贰于叔,而歌其田狩适野之事。初非以刺庄公,亦非说其出于田而后归之也。或曰:段以国君贵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众,不得出居闾巷,下杂民伍,此诗恐亦民间男女相说之词耳。”《汉书·匡衡传》颜《注》、[30]宋朱熹《诗集传》卷四、《诗传遗说》卷二、[31]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五[32]说大同,三家诗无异义,伪《子贡诗传》阙。④毛《序》之“刺郑庄公”说,《汉书·匡衡传》颜《注》之“美公叔段”说,《毛诗稽古编》之“讥公叔段”说,诗旨解说虽有美刺之别,所美所刺对象亦异,然皆以为作于郑庄公之世。案:朱《传》、《诗序辨说》释《叔于田》、《大叔于天》之“叔”为“庄公弟公叔段”,“公”为“庄公”,则朱氏二说并存。二为阙疑说,宋朱熹《诗集传》卷四:“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说之词也。”《诗传遗说》卷二说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及骆惠玲《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浅议》[33]皆同。⑤朱《传》之“爱情”说,《诗经通论》之“美猎人”说,《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浅议》之“女子赞美她所爱慕猎手的民歌”说,作者、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三为泛言春秋中期(前 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作者时代及其评价问题》。四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毛《序》“郑庄公之世”说。兹补证如下:
就诗文本而论,诗之首章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次章曰:“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卒章曰:“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明孙矿《批评诗经》卷一:“‘巷无居人’句,下得煞是陡峻。”[34]的确,此所谓“巷无居人”、“巷无饮酒”、“巷无服马”皆写“叔”外出田猎于郊野之后都邑“巷”内情景,由下文三章皆言“不如叔也”可知,诗人所写此情景实非客观环境,而为由对“叔”衷爱之排他性所生之心理环境。作者通篇以自豪的心情夸耀“叔”为一位“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之举世无双之男子。“叔”究竟有多“美”,诗人未从正面描写其服饰、肖像等外在美,而是以“仁”、“好”、“武”等方面烘托其内在美,即“叔”为一位厚道谦让、气质超群、勇敢英武之贵族男子。作者这种侧面点化之法,起到了动静结合而正反相形之艺术效果,充分展现出“叔”在诗人心中之崇高地位,表现出诗人对“叔”纯真的爱慕之情。诗人之审美情趣反映出春秋时代以硕大、健壮为美之审美风尚,为春秋时代尚武任能精神之具体体现,也正好说明这个“叔”显然为那个时代之风流人物。①参见:董治安《漫谈〈叔于田〉、〈大叔于田〉的夸饰特色》,《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8—122页。《汉书·匡衡传》载衡上疏曰:“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②《汉书·匡衡传》颜《注》:“《诗·郑风·太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汝。’……公,郑庄公也。将,请也。叔,庄公之弟太叔也。……言以庄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献之。国人爱叔,故请之曰勿忕为之,恐伤汝也。”清崔述《读风偶识》卷三:“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35]此言不误。但通观先秦文献,女子称其情人或丈夫曰“叔”,晚辈称长辈曰“叔”,伯、仲、叔、季行次之别亦曰“叔”。故既然认为“叔”并非确指“大叔段”(即非行次之“叔”),那么似乎亦无确证让人相信“叔”为女子称其情人或丈夫之“叔”;既然“叔”这样一位厚道谦让、气质超群、勇敢英武之贵族男子,可以成为贵族女子所爱慕之偶像,何以不会成为士大夫所敬仰之英雄呢?况且,据隐元年《左传》、[36]《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郑世家》,[37]大叔段生于郑武公十七年(前 754年),少郑庄公三岁,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出奔共时三十三岁,正当盛年。故笔者以为,非毛《序》者诸说从诗文本入手提出有关新说,然均无确证可明毛《序》之误,此诗当作于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公叔段出奔共之前。惜其具体作年不可详考,姑系于公叔段奔共之年,即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
五、郑人作《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为郑人刺庄公之作(毛《序》)。③此篇丰氏本题作《叔于田》。案: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误。”宋苏辙《诗集传》卷四:“二诗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别之。”严粲《诗缉》卷八:“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长篇者加‘大’以别之。”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八:“‘大’当读如‘大’、‘小’之‘大’。古通以长为大,谓此诗较《叔于田篇》为长。”则篇名原当为《叔于田》,与上篇同名。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郑庄公之世(前743年—前701年)说,毛《序》:“《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④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此诗与上篇(指《叔于田》)义同,非刺庄公也。下两句得之。”《汉书·匡衡传》颜《注》、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五说大同,三家诗无异义,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皆阙。①毛《序》之“刺郑庄公”说,《汉书·匡衡传》颜《注》之“美公叔段”说,《毛诗稽古编》之“讥公叔段”说,诗旨解说虽有美刺之别,所美所刺对象亦异,然皆以为作于郑庄公之世。二为阙疑说,元刘玉汝《诗缵绪》卷五:“愚意谓郑民间旧有此诗,诗篇名、曲谱民常歌之。至是以‘叔’之名同,‘田’之事又同,故遂用之。既仍其篇名,又依其音调,即项氏所云以其篇名之同、义类之似而取其音节以为诗。”[38]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及杨凌羽《简论郑风》皆同。②《诗缵绪》之“民歌”说,《诗经通论》之“美猎人”说,《简论郑风》之“爱情”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三为泛言春秋中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作者时代及其评价问题》。四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毛《序》“郑庄公之世”说。兹补证如下:
就诗文本而论,诗之首章曰:“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次章曰:“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卒章曰:“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诗人先写“叔”田猎于郊野时之善御:“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两服上襄,两骖雁行”、“两服齐首,两骖如手”,辔齐如带,服马高昂,骖马雁行,纵马勒马,熟练自如。次写“叔”田猎于郊野时之善猎:火猎之始,林薮火举,徒手搏虎,勇猛非凡;火猎高潮,火把遍扬,驱车逐兽,射艺非凡;火猎尾声,火把高擎,好整以暇,神态非凡。可见,诗人写其御马,姿态优美,技艺娴熟;写其火猎,善于骑射,控纵自如,勇武过人,场面壮观。全诗“描摹工绝,铺张亦复扬厉,淋漓尽致,为《长扬》、《羽猎》之祖”(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三章均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场面赋写,全不着一字情语,却在具体描写初猎、猎中、猎毕全过程的字里行间脉脉流溢着诗人对“叔”之崇敬与赞美,迸发出对“叔”勇武有力、本领高强、能骑善射、品貌出众、态度从容的爱慕之意。又,《水经·漯水注》:“御圈,上敕虎士效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兽,即《诗》所谓‘襢(袒)裼暴虎’,献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图》也。”[39]的确,诗人以“叔”之勇武为美之审美情趣,反映出以硕大、健壮为美的时代风习,为春秋时代尚武任能精神之具体体现,亦为春秋时期现实审美观念之艺术写照。全诗写得“气骨劲陗,傲然有挟风霜意,便是战国后侠气发轫。诵之,想见其豪举自肆状。”(明孙矿《批评诗经》卷一)。况且,“公子吕所谓‘请除之,无生民心’,子封所谓‘可矣,厚将得众’,寻诗,若有此理。”(宋王质《诗总闻》卷四)。可见,《叔于田》与《大叔于田》两诗,一短一长,一为概写抒怀,一为具体描述。两诗所美之人、所写之事相同,则当为同一时期作品,故依今本毛《诗》篇次系于《叔于田》之后。
六、郑大夫作《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为郑大夫美贤夫妇相劝勉之作(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六说:一为阙疑说,毛《序》:“《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①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此亦未有以见其陈古刺今之意。”汉焦赣《易林·丰之艮》、[40]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四、[41]王质《诗总闻》卷四、朱熹《诗集传》卷四、《诗传遗说》卷一、卷四、杨简《慈湖诗传》卷六、[42]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一、[43]明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七、[44]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45]傅恒等《钦定诗义折中》卷五、[46]姜炳璋《诗序补义》卷七、[47]龚橙《诗本谊》、[48]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49]及闻一多《风诗类钞》(P63)、钱钟书《管锥编》、[50]张震泽《论〈诗经〉的艺术(上)》、[51]陈子展《诗经直解》、[52]宫玉海《诗经新论》、[53]97杨凌羽《简论郑风》、于雪棠《吉美贵善的综合载体——〈诗经〉玉意象论析》[54]皆同,鲁《诗》、韩《诗》无疑义,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亦同。②毛《序》之“刺不说德”说,《焦氏易林》之“无家而思配”说,《诗本义》之“贤夫妇相勉励”说,《诗总闻》之“妇人惟恐其君子不得良友”说,朱《传》、《诗传遗说》之“贤夫妇相警戒”说,《慈湖诗传》之“贤者隐处野外”说,《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之“妇人相其夫”说,《诗说解颐正释》之“美贤妻”说,伪《诗传》之“夫妇相戒以勤生乐善”说,伪《诗说》之“夫妇相警戒”说,《日知录》之“相警以勤生”说,《钦定诗义折中》之“尽妇道”说,《诗序补义》之“贤妇规讽其夫”说,《经学通论》之“贤夫妇帏房之诗”说,《诗本谊》之“淫女思有家”说,《风诗类钞》之“乐新婚”说,《管锥编》之“憎鸡叫旦”说,《论〈诗经〉的艺术(上)》之“农民夫妇相亲相爱”说,《诗经直解》之“弋人夫妇家常生活之诗”说,《诗经新论》之“青年夫妇的小歌舞剧”说,《简论郑风》之“情诗”说,《吉美贵善的综合载体——《诗经》玉意象论析》之“恋人相赠信物”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二为郑武公三年(前768年)之后说,汉郑玄《诗谱·郑谱》:“武公又作卿士,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又作。”[55]③《诗·郑风·缁衣》毛《序》:“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史记·郑世家》:“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武公二十七年)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今本《竹书纪年》:“(周平王)三年,王锡(赐)司徒郑伯命。”则郑武公三年(前768年),周平王命郑武公掘突继父职入为周王朝司徒,位居三公。班固《汉书·地理志下》说大同。三为郑庄公之世(前743年—前701年)说,《女曰鸡鸣》孔《疏》:“作《女曰鸡鸣》诗者,刺不说德也。以庄公之时,朝廷之士不说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诗陈古之贤士好德不好色之义,以刺今之朝廷之人。”《诗谱·郑谱》孔《疏》说同。四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二年(前770年—前722年)之间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女曰鸡鸣》,述郑贤夫妇相劝勉之辞。《溱洧》之反。”④何氏《诗经世本古义》系于周平王之世(前770年-前720年),正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二年之间。五为泛言春秋中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作者时代及其评价问题》。六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何氏《诗经世本古义》“周平王之世”说。惜其具体年代不可详考,姑系于周平王卒年,即郑庄公二十四年(前720年)。
七、郑大夫作《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为郑大夫刺太子忽之作(毛《序》)。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八说:一为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说,毛《序》:“《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①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今考之此诗,未必为忽而作。《序》者但见‘孟姜’二字,遂指以为齐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说,则忽之辞昏未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国,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其亦误矣。”案:据桓十一年《春秋》、《左传》、《史记·郑世家》,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五月癸未(七日),郑伯寤生卒;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四、清钱澄之《田间诗学》卷三[56]说大同,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皆同,三家诗无异说。②毛《序》之“郑人刺忽”说,伪《诗传》、伪《诗说》之“祭仲谏太子忽”说,《田间诗学》之“追惜忽如陈逆妇妫”说,作者、诗旨解说虽异,然其作世皆同。案:《诗本义》虽疑传世毛《诗》篇次有“差失”,然其作世仍从毛《序》说。二为郑昭公复立之世(前696年—前695年)说,宋范处义《诗补传·篇目》系于郑昭公复立之时。[57]③据桓十一年《春秋》、《左传》、《史记·郑世家》,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五月癸未(七日),郑伯寤生卒;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公子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祭仲遂立公子突为郑厉公。则其于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世子忽初立四月即出奔。又据桓十五年、十七年《春秋》、《左传》、《史记·郑世家》,郑厉公四年(前697年)六月世子忽又复立,厉公六年即昭公二年(前695年)十月被杀,复立后在位仅两年四个月。三为阙疑说,宋王质《诗总闻》卷四:“所见亲迎之礼,彼美之貌,似是与妇成礼而非惮耦辞昏者。”朱熹《诗集传》卷四、《朱子语类》卷八十、[58]明梁寅《诗演义》卷四、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七、清傅恒等《钦定诗义折中》卷五、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二、范家相《诗渖》卷七、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崔述《读风偶识》卷三皆同。④《诗总闻》之“亲迎之礼”说,朱《传》、《朱子语类》之“淫诗”说,《诗演义》之“男悦女”说,《诗说解颐正释》之“美国君新娶夫人之德”说,《钦定诗义折中》之“劝好德”说,《诗疑辨证》之“夸美新婚夫妇”说,《诗渖》之“刺亲迎者好色”说,《诗经通论》之“夸齐长女美而贤”说,《读风偶识》之“恋歌”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时世。四为郑庄公三十八年(前706年)说,宋杨简《慈湖诗传》卷四:“是诗深言孟姜之善,而亦不言同车者之不善,婉而彰,爱而忠。追考时事,则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忽曰:‘齐大,非吾耦也。’遂辞之。国人惜其失大国之助,故作是诗。”⑤据桓六年《左传》、《史记·郑世家》,郑昭公三十八年(前706年),郑大子忽帅师救齐,齐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辞之。五为郑文公十三年(前660年)之后说,清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有女同车》,刺文公也。文公始取齐姜,继欲结楚援,复昏文芈。自是贰中夏而事蛮夷,违三良之谏,蒙《春秋》之贬,皆文芈为之。故诗人睠睠齐姜,匪姜之为美,而中夏盟主之为美也。诗次文公《清人》之后,必非先世刺忽之诗。”《桧郑答问》说同。⑥据闵二年《左传》,郑文公十三年(前660年),郑人恶高克,使其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六为郑庄公二十九年(前715年)说,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五:“昭公辞昏见逐,备见《左传》隐八年如陈逆妇妫,诗所为作。”[59]①据隐八年《左传》、《史记·郑世家》,郑庄公二十九年(前715年),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七为泛言春秋中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产生及其评价问题》。八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毛《序》“郑庄公四十三年”说。兹补证有三:
其一,关于郑太子忽娶陈妫为夫人与两次辞婚于齐之年代。隐七年《左传》:“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隐八年《左传》:“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则郑太子忽娶陈妫为夫人事在郑庄公二十九年(前715年)。又,桓六年《左传》:“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则郑太子忽曾辞婚文姜当在此年之后。又据桓三年《春秋》、《左传》,郑庄公三十五年(前709年)鲁桓公娶文姜为夫人,则郑太子忽曾辞婚文姜于齐僖公在此年之前。那么,郑太子忽曾辞婚文姜当在郑庄公二十九年(前715年)至三十五年(前709年)之间。又,桓六年《左传》:“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则郑太子忽第二次又辞婚于齐僖公事在郑庄公三十八年(前706年),此时文姜归鲁已四年;况且,文姜淫乱,卒使鲁桓公被杀,诗人不当美之,则齐僖公所欲妻忽者必当为他女。②《史记·齐世家》、《郑世家》皆以忽第一次辞婚之言加于败戎师第二次辞婚之时,不可从。说本: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桓六年》,科学出版社整理原稿和清抄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资料室整理,1959年。
其二,忽出奔卫的确因无大援所致。据桓十一年《春秋》、《左传》,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五月癸未(七日),郑伯寤生卒,祭仲立邓曼所生太子忽为昭公;九月,宋胁迫祭仲立宋雍氏女所生公子突为厉公,昭公忽出奔卫。又,桓十一年《左传》载祭仲谏太子忽曰:“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子突、子亹、子仪三公子,其母皆有宠;③《史记·郑世家》:“所谓三公子者,大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司马贞《索隐》:“此文则数太子忽及突、子亹为三,而杜预云不数太子,以子突、子亹、子仪为三,盖得之。”而子忽为邓女所生,又娶陈女为嫡夫人而拒娶齐女为夫人,其舅家邓为小国,陈之国力又不如宋。故太子忽继父庄公寤生为君之后,却因无以为援被迫出奔卫,而公子突因宋之助得以继兄太子忽立为君,三公子更立乱郑由此始,“郑庄小霸”之衰亦由此始(桓十一年《春秋》、《左传》)。
其三,国人刺忽在其出奔卫(前701年)而郑乱之后。宋严粲《诗缉》卷八:“忽以弱见逐,国人追恨其不娶齐女。言忽所娶他国之女,行亲迎之礼,而与之同车者,特取其色尔。此女色如木槿之华,朝生暮落,不足恃也。而今也且翱且翔于此,佩其琼琚之玉,徒有威仪服饰之可观,而无益于事也。曷若彼美好齐国之长女,信美而且闲雅?向来忽若娶之,则有大国以为援,而不至于见逐矣。”[60]郑太子忽应陈桓公之请而娶陈妫为夫人事在郑庄公二十九年(前715年),鲁桓公娶文姜为夫人事在郑庄公三十八年(前706年),期间凡九年。故若按先秦婚制之年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周礼·地官司徒·媒氏》),[61]则齐僖公请妻文姜于忽不当在娶陈妫为夫人之前。①关于先秦婚制之年龄,《礼记·曲礼上》、《内则》、文十二年《穀梁传》、《大戴礼记·本命》、《白虎通义·嫁娶篇》说与《周礼·地官司徒·媒氏》同,不具引。而诗人将陈女与齐女并言,则不当在忽娶陈妫为夫人之时,而当在其娶陈妫为夫人又二拒齐女之后,故《有女同车》当作于忽出奔卫而郑乱之后。惜其具体作年不可详考,姑系于忽出奔卫之年,即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
八、郑大夫作《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为郑大夫刺太子忽之作(毛《序》)。②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俱题作《扶胥》。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十说:一为郑庄公二十九年至昭公二年(前715年—前695年)之间说,毛《序》:“《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③宋朱熹《诗序辨说》卷上:“此以下四诗及《扬之水》皆男女戏谑之词。《序》之者不得其说,而例以为‘刺忽’,殊无情理。”案:笔者以为,毛《序》所谓“刺忽”者有二:一即刺太子忽娶陈妫为夫人而两辞齐女,事见隐七年、八年、桓六年《左传》;二即太子忽复位之后。期间,正郑庄公二十九年(前715年)至郑昭公二年(前695年)之间。宋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一说大同,三家诗无异义。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之“伤无贤人”说,诗旨解说虽与毛《序》异,然其作世则从毛《序》说。二为郑昭公复立之世(前696年—前695年在位)说,《诗谱·郑谱》孔《疏》:“《山有扶苏》、《萚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贤,权臣擅命。忽之前立时月既浅,则此三篇皆后立时事也。”三为郑庄公三十八年(前706年)说,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四:“《山有扶苏》,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四为阙疑说,宋王质《诗总闻》卷四:“此妇人适夫家经历山隰所见,当是媒妁姑以美相欺,相见乃不如所言,怨怒之辞也。”朱熹《诗集传》卷四、杨简《慈湖诗传》卷六、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二、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及陈子展《诗经直解》[P260]皆同。⑤《诗总闻》之“刺媒妁之过”说,朱《传》之“淫诗”说,《慈湖诗传》之“刺国无贤俊”说,《诗疑辨证》之“朋友相规”说,《诗经通论》之“夸饰美人”说,《诗经直解》之“情诗”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五为郑灵公元年(前 605年)说,伪《子贡诗传》:“郑灵公弃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忧之,赋《扶胥》。”⑥据宣三年、四年《春秋》、《左传》、《史记·郑世家》,郑穆公二十二年(前606年)十月,穆公兰卒,子夷立,是为灵公;郑灵公元年(605)六月,郑公子宋(字子公)、公子归生(字子家)谋杀灵公,立灵公弟坚为襄公。此伪《诗传》、伪《诗说》即本于此文。又,子良,公子去疾之字,郑穆公庶子,灵公之弟,郑卿士,其后以字别为良氏,为郑“七穆”之一。伪《申培诗说》大同。六为郑子婴十二年(前682年)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愚按:此与《狡童》、《褰裳》三篇皆为祭仲足而作。据《左传》,仲足初为祭封人,因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盖君之嬖幸臣也。仲虽为卿,诗人本其进身之始而丑之。故有《狂童》。《狡童》之日,先是仲为庄娶邓曼,生昭公忽,以邓曼故遂立忽,忽固长也。已而,为宋人所胁,旋逐忽而立突,是为厉公。仲专政,公恶之,使其婿雍纠杀之,以谋泄,公遂出奔,昭公复立。不久为高渠弥所弑,立子亹,仲与焉。齐人来讨,高渠弥、子亹见杀,仲以智免,又逆子仪于陈而立之。其后厉公使傅瑕杀子仪而复入。因治与于雍纠之乱者,而仲已死矣。仲擅废立之权,犯不臣之罪,竟以善终,君子恨之。当时目之为狂狡固宜。”①郑子婴十二年(前682年),祭仲卒。事见《史记·郑世家》。七为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七:“五诗(指《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皆作于昭公奔卫之日,厉公窃位之时。而此一篇(指《山有扶苏》)则以‘子都’指忽,而‘狂且’目突也。子都,庄公时人,郑之美丽者也。故郑人以意所美者,即为子都。子充,犹子都也。《褰裳》后序以‘狂童’指突,其说是也。”顾镇《虞东学诗》卷三说大同。[62]八为郑文公元年至二十年(前672年—前653年)之间说,清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山有扶苏》,刺文公也。所美非美然。文公不从三良以亲齐,而宠申侯以昵楚也。”②据僖七年《春秋》、《左传》,郑厉公二十七年(前674年),楚大夫申侯出奔郑,仕为大夫,有宠于厉公;郑文公二十年(前653年),郑杀申侯以悦于齐。九为泛言春秋中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产生及其评价问题》。十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P218]笔者此从姜氏《诗序补义》“郑庄公四十三年”说。兹补证如下:
汉焦赣《易林·蠱之比》:“视暗不见,云蔽日光。不见子都,郑人心伤。”《巽之节》:“婴儿孩子,未有知识。彼(狡)童而角,乱我政事。”此“视暗不见”,即刺君不择臣;“云蔽日光”,即臣欺其君;“狡童”,即嬖宠之臣。可见,诗人刺斥昭公忽之意甚明,则毛《序》“刺忽”说不误。事实上,尊毛《序》者与疑毛《序》者争论的焦点是诗首章之“子都”、次章之“子充”为专用名词还是普通名词。毛《传》:“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良人也。”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子都必古之美人,故孟子曰:‘子都之姣。’”此皆释为普通名词。笔者以为,《诗·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皆为专用名词,且与隐十一年《左传》之“子都”为同一人。隐十一年《左传》杜《注》:“公孙阏,郑大夫。……子都,公孙阏。”则此隐十一年《左传》之“子都”,即隐十一年《左传》之“公孙阏”,名阏,字子都,郑公族,仕为大夫。庄公三十二年(前712年)郑会齐、鲁伐许之役,子都因与颍考叔有隙而射杀之,庄公明知射杀颍考叔者乃子都,然佯为不知,使军士诅咒之。作为“小霸”之君,庄公何以出此下策呢?因其人貌美,得庄公宠幸,庄公不欲加之以刑,故为平众怒计,使军士诅咒之。不仅《诗·郑风·山有扶苏》与隐十一年《左传》二“子都”为同一人,而且与《孟子·告子上》之“子都”亦为同一人。《孟子·告子上》:“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63]清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二曰:“孟子深于《诗》,其称子都正本于《诗》,而与易牙、师旷并举,则子都实有其人矣。”[6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八亦曰:“都、奢古同音通用。《荀子》:‘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子奢,即子都。《左传》郑庄公时有子都,《孟子》赵《注》:‘子都,古之姣好者也。’《孟子》以子都与易牙、师旷并举,则子都实有其人耳。”[65]则孟子将郑之子都与齐之易牙、晋之师旷并举,则其自然以“子都”为专名而非通名。当然,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与“秦罗敷”为美女通称一样,“子都”或为美男通称,就象“妲己”、“褒姒”指代女祸、“许穆夫人”、“昭君”指代淑女一样;但我们自然不能否定“妲己”、“褒姒”、“许穆夫人”、“昭君”是历史上原本就有的真实人物,他们由专名到通名都有一个语义渐次虚化的演变过程。我们说《诗·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即隐十一年《左传》、《孟子·告子上》之“子都”,亦即射杀颍考叔之郑庄公幸臣之“子都”,并不是说其作于子都射杀颍考叔时,只是说明《山有扶苏》之“子都”是专名而非通名,想说明姜氏《诗序补义》认为《山有扶苏》“作于昭公奔卫之日,厉公窃位之时”是有其史实依据的。由此我们进一步认为,《山有扶苏》与《有女同车》为同时所作,今本毛《诗》将其次于《有女同车》后,或正出于此因。故我们将《山有扶苏》系于昭公奔卫、厉公窃位之年,即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且从今本毛《诗》篇次系于《有女同车》之后。
九、郑人作《萚兮》
《萚兮》为郑人刺太子忽之作(毛《序》)。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十说:一为郑庄公二十九年至昭公二年(前715年—前695年)之间说,毛《序》:“《萚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①宋朱熹《诗序辨说》非毛《序》之说见本年“郑大夫作《山有扶苏》”条。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八说大同,三家诗无异义。②《吕氏家塾读诗记》之“群臣相唱和”说,诗旨解说虽与毛《序》异,然其作世则从毛《序》说。二为郑昭公复立之世(前696年—前695年)说,见上引《诗谱·郑谱》孔《疏》,宋严粲《诗缉》卷八、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九[66]说大同。③《诗缉》之“忧惧之辞”说,《大学衍义》之“群臣结党避祸”说,诗旨解说虽与孔《疏》异,然其作世则皆从孔《疏》说。三为阙疑说,宋王质《诗总闻》卷四:“或国与家,未可知。当是有乘微弱而谋倾夺者,有识有情,动念而力不能独办,故有求于为倡者也。”朱熹《诗集传》卷四、辅广《诗童子问》卷二、[67]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二引金履祥说、明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七、清傅恒等《钦定诗义折中》卷五、李光地《诗所》卷二、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二、范家相《诗渖》卷七、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及陈文钧《〈诗经〉的两首劳动情歌—〈摽有梅〉和〈蘀兮〉》、[68]陈子展《诗经直解》、卢治安《哀婉的悲歌——〈萚兮〉主题再认识》、[69]夏传才《学〈诗〉札记六题》[70]皆同。④《诗总闻》之“谋倾夺者有求于为倡者”说,朱《传》之“淫诗”说,《诗童子问》之“女亟辞”说,金履祥之“及时行乐”说,《诗说解颐正释》之“小臣愿忠于国”说,《诗义折中》之“望晋急郑”说、《诗所》之“男女相悦之辞”说,《诗渖》之“群臣结党避祸”说,《诗疑辨证》之“避祸逃难”说,《诗经通论》之“贤者忧国乱被伐而望救于他国”说,《〈诗经〉的两首劳动情歌-〈摽有梅〉和〈蘀兮〉》之“劳动情歌”说,《诗经直解》之“咏叹落叶之歌”说,《哀婉的悲歌——〈萚兮〉主题再认识》之“哀怨感伤之情歌”说,《学〈诗〉札记六题》之“女子领唱的邀和之辞”说,诗旨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四为郑昭公元年(前696年)说,明李先芳《读诗私记》卷三:“按:《史记》,祭仲立忽,宋庄公诱召祭仲,复立突;突后出奔,祭仲立忽,惧高渠弥害己。疑此时也。”[71]五为郑厉公元年(前700年)说,明朱谋?《诗故》卷三:“《萚兮》,……郑人思黜突而纳忽也。忽以世子践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郑人故不义突而赋此诗。”[72]六为郑厉公后元二年(前678年)说,伪《子贡诗传》:“公子五争,齐、楚交伐,郑国大乱。其臣谋欲谏而救之,赋《萚兮》。”①郑公子五争,事见: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庄十四年《春秋》、《左传》及《史记·郑世家》。又,据庄十六年《春秋》、《左传》、《史记·郑世家》,郑厉公二年(前678年)夏,齐以郑厉公攻宋、背鄄之盟,会宋、卫之师讨之;秋,楚文王以郑厉君复位,缓告于楚,讨之,及栎而还。伪《申培诗说》大同。七为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见上引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七,顾镇《虞东学诗》卷三说大同。八为郑文公二十年(前653年)说,清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萚兮》,刺文公也。鲁、卫、晋固伯叔兄弟之国,齐、宋亦伯叔甥舅之邦,若之何倡而不和、要而不从?始则见讨齐桓,继则见讨晋文,甘心背夏役楚乎?诗当作于宁母听命之后,乞盟请服之时。”②郑文公十九年(前654年)夏,齐侯会鲁公、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次年(前653年)秋,齐侯会鲁公、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甯母。事见:僖六年、七年《春秋》、《左传》。《桧郑答问》说同。九为泛言春秋中期(前697年—前546年)说,见上引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产生及其评价问题》。十为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前770年—前723年)之间说,见上引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姜氏《诗序补义》“郑庄公四十三年”说。兹补证如下:
《周礼·地官司徒·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③《周礼·地官司徒·媒氏》郑《注》:“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此可视为本诗创作之文化背景。昭十六年《左传》:“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柳赋《蘀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④昭十六年《左传》杜《注》:“《萚兮》诗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将和从之。”晋卿韩起(宣子)此所谓“郑志”,即指郑诗。⑤说详: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5—26页。韩宣子以《萚兮》为“昵燕好”之辞,此可证春秋时期用诗之义。
就诗文本而言,诗人以风比男,以萚比女,姑娘们希望男子能够象风一样吹到她们身边,互相应和,互相期会;同时,“叔兮伯兮”二次呼告,以热烈而亲切的称呼,使人想见一群男女欢乐唱和、清歌曼舞的热烈场面,表现出民歌善于渲染气氛之特色。可见,就文本而言,确为闺房之歌。然以男女私情比况国家大事者见于《诗经》及后世作品者甚众。况且,今本毛《诗》将其次于《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刺忽诸篇之后,或为同一时期作品,其必有所本。故我们将《萚兮》系于昭公奔卫、厉公窃位之年,即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且从今本毛《诗》篇次系于《山有扶苏》之后。
综上所考,《缁衣》为郑大夫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作,作于郑武公三年(前768年)之后;《遵大路》为周平王公卿欲留郑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元年(前743年);《将仲子》为郑大夫刺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叔于田》、《大叔于田》皆为郑人刺庄公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公叔段出奔共之前;《女曰鸡鸣》为郑大夫美贤夫妇相劝勉之作,当作于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二年(前770年—前722年)之间;《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皆为郑大夫刺太子忽(昭公)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太子忽出奔卫而厉公窃位之后。
[1]孔颖达.毛诗正义[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孔颖达.礼记正义[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孔鲋.孔丛子[C]//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51.
[5]刘燕及.新袍子怎么破旧了—《诗经·郑风·缁衣》议[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4):59-63.
[6]杨凌羽.简论郑风[J].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2):80-86.
[7]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J].文艺研究,1991,(1):55-69.
[8]朱熹.诗集传[C]//四部丛刊三编.长沙:岳麓书社,1989.
[9]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C]//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
[10]丰坊.申培诗说[C]//钟惺.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济南:齐鲁书社,1997.
[11]何楷.诗经世本古义[M].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溪邑谢氏文林堂刊本.
[12]赵敏俐.《诗经·郑风》的作者时代及其评价问题[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3):ll-18.
[1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218.
[14]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王质.诗总闻[C]//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刘瑾.诗传通释[M].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刘氏日新书堂刊本.
[17]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M].明嘉靖二年(1523)刘宗器安正堂刻本.
[18]梁寅.诗演义[C]//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胡广.诗传大全[M].国家图书馆藏明永乐十三年(1415)内府刻本.
[20]李光地.诗所[M].清道光九年(1821)李维迪刻榕村全书本.
[21]黄中松.诗疑辨证[M].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1986.
[22]范家相.诗渖[M].范氏遗书家刻本.
[23]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4]魏源.诗古微[M].长沙:岳麓书社,1989.
[25]朱杰人.文化视野中的《诗经》情诗[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76-81,75.
[26]丰坊.子贡诗传[C]//钟惺.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济南:齐鲁书社1997.
[27]韦昭注.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8]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9]陆永品.略谈对《诗经》中爱情、婚姻诗评价的演变[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1,(2):67-73.
[3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1]朱鉴.诗传遗说[M].清康熙间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
[32]陈启源.毛诗稽古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3]骆惠玲.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浅议[J].渤海学刊,1988,(1):100-10l.
[34]孙矿.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35]崔述.读风偶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7]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8]刘玉汝.诗缵绪[C]//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9]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0]焦赣.焦氏易林[C]//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
[41]欧阳修.诗本义[C]//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
[42]杨简.慈湖诗传[C]//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4.
[43]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C]//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44]季本.诗说解颐[M].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刻本.
[45]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46]傅恒等.钦定诗义折中[M].清乾隆二十年(1756年)刻武英殿刻本.
[47]姜炳璋.诗序补义[M].清嘉庆二十年(1816)尊行堂刻本.
[48]龚橙.诗本谊[C]//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9]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50]钱钟书.管锥编: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4-105.
[51]张震泽.论《诗经》的艺术:上[J].社会科学辑刊,1979,(3):145-161.
[52]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524.
[53]宫玉海.诗经新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97.
[54]于雪棠.吉美贵善的综合载体——《诗经》玉意象论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64-68.
[55]郑玄.诗谱[M].清康熙间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
[56]钱澄之.田间诗学[M].合肥:黄山书社,2005.
[57]范处义.诗补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8]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0]严粲.诗缉[M].明赵府味经堂刻本.
[61]贾公彦.周礼注疏[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2]顾镇.虞东学诗[M].清光绪十八年(1892)诵芬堂刻本.
[63]孙奭.孟子注疏[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4]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6]真德秀.大学衍义[M].明毛晋汲古阁本.
[67]辅广.诗童子问[M].北京:线装书局,2001.
[68]陈文钧.《诗经》的两首劳动情歌—《摽有梅》和《萚兮》[J].人文杂志,1958,(l):40-42.
[69]卢治安.哀婉的悲歌——《萚兮》主题再认识[J].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85,(4):58-60.
[70]夏传才.学《诗》札记六题[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4):26-32,39.
[71]李先芳.读诗私记[C]//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4.
[72]朱谋土韦.诗故[C]//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