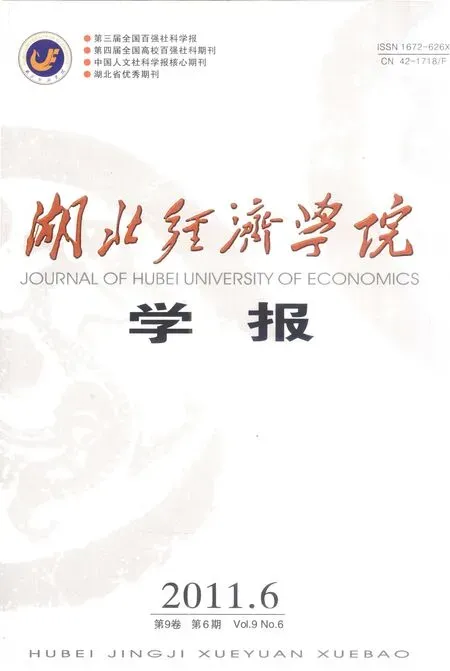诡辞为用:牟宗三对向秀、郭象《庄子》注的诠释路径
程 郁
罗义俊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20世纪30、40年代的魏晋玄学研究是魏晋玄学研究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开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想史教材、学术基础和形上学方向。尽管是草创性研究,后来的研究能达到其水平者已不多见;而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一书则是其中能从整体上给魏晋玄学以推进、深化和超越者。
罗先生特别指出,此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与西方形上学系统的对照比观,更通过对儒道会通的探微烛幽的次序分析,在哲学形态上论究异同,简别出道家和魏晋玄学的形上学为主观的实践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此一“简别”既孳乳于西学传统与中学内部的道玄儒佛传统,同时又借此宽阔的视野观待而得玄学区别于其余各家学说的特质——与儒家及西方实有形态的形上学和佛家的性空义理不同,道家和玄学乃是“自主观工夫上言无的理境”,“主观工夫上的无的智慧”,并特称此说“乃任何以实践为进路的大教之共法”,“千圣生命所共有”,为生命之学问。这一“发人所未发”的独特贡献,确如罗先生所说“从整体意义上深化与超越了牟先生以前的魏晋玄学研究,至今亦无出其右”,我们从方法论上研习牟先生的著作,拈出“诡辞为用”这一牟先生每每提及的道家、玄学诠释方法,同时也约略窥探出以牟先生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会通中西,圆融三教的旨归与胸怀。
一、“诡辞为用”之意涵
“诡辞为用”一词首先出现在牟宗三先生对庄老思想差异的阐释中,出处有三:
(一)庄老风格之异——牟先生认为老庄风格差异在于老子较沉潜而坚实,而庄子较显豁而通透。且庄子为“玄智玄理之彻底透出”,而为“圆而无圆”之圆教也。牟氏举《天下篇》“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为例,此段郭象注为“无意趣也”,意将庄子之学窈窕深远之状貌解释为圣人或得道之人的无所“用心”,无所趋向。牟先生则说“既‘毕罗’矣,而又‘莫足以归’,此诡辞也”。 对于郭注的“故都任之”和成玄英的疏“包罗庶物,囊括宇内。未尝离道,何处归根?”牟说:“此实极豁朗而透脱之极致。禅家一切诡辞亦不出乎此矣。此即谓玄智玄理之彻底透出,而为‘圆而无圆’之圆教也。 ”[1](P150)
(二)表达方法之异——老子以分解的讲法,庄子则以描述的讲法。牟先生提出老子哲学之三大端为对于道之本体论的体悟、对道之宇宙论的体悟,以及对道之修养功夫的体悟。而庄子之描述:一是卮言漫衍,重言为真,寓言为广;二是从混沌中见秩序(内藏“诡辞为用”之玄智);最后是“辩证的融化”,将以上玄智概念化,严整说出。在《老子》中,“知的问题,心的问题,性的问题,俱已透出”;“而‘曲则全,枉则直’之‘诡辞为用’亦彰显无遗。有与无是客观之玄理,‘诡辞为用’是主观之玄智。 ”[1](P151)文中提到“王弼作《老子微旨略例》,反复申明不过两义”:“《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重本息末而已。”本即无,末即有,去伪存朴,此一义也。又曰“……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仁而后仁德厚。”此诡辞为用也,此又一义也。本无为体,诡辞为用,体用两义,无不赅尽。至庄子,则“诡辞为用”,化体用而为一。其诡辞为用,亦非平说,而乃表现……彼将老子由分解的讲法所展现者,一起消融于描述的讲法中,而芒忽恣纵以烘托之,即消融于“诡辞为用”中以显示之。全部《庄子》,是一大混沌,亦是一大玄智,亦整个是一大诡辞。[1](P151)在牟先生看来,王弼对于《老子》的诠释用的也是诡辞为用的方法,但王弼之“诡辞为用”仅停留在方法即“用”上,以“本无”为体,而庄子则“化体用为一”,将其对老子思想的诠释和发展之内容与其诠释之方法一齐融汇在“诡辞为用”之中,于是整部《庄子》都成了一个“大诡辞”。
(三)义理形态之异——牟先生认为老子之道为“实有形态”之学,为积极建构之形上学,具备客观性、实体性、实现性三个特性。而庄子之道则消解了老子之道的以上三个特性,以“当体之具足”,从而转化“境界形态”。[1](P155)牟宗三将老庄之道规定为“境界形态的形上学”,并将之与今之自然或自然主义严格区分开来,而《庄子》之道正是根据《老子》之道而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所谓消融《老子》分解讲法之所展示而成一大诡辞者是也(成一辩证之融化)。”
综上所述,牟先生所言“诡辞为用”不外两方面的意涵:主观之玄智与辩证之融化,其特征则为强调主体之自足无待,富有实践品格与价值意义。将道之客观性分解,仅从主观层面予以解说,客观实有意义上的道成为 “修养境界上的”“虚一而静”的境界。老子之道在牟氏犹有客观性和实体性,而这一特性所构成的“积极建构之形上学”,仍然“似乎只是一姿态”,至庄子,这一姿态也被“化掉”,彻底成为一个主观视域中的境界形态,而这一“化掉”的过程正是“诡辞为用”的运用过程,是庄子对老子的进一步诠释和发展。在牟氏看来,庄老之间的哲学演变和发展,正是一个“诡辞为用”的过程,不仅如此,老子对于世界万物以及道的考察,后世王弼对老子的诠释,也都是一个“诡辞为用”的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牟氏的“诡辞为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读为我们当下所谓的 “创造性的诠释”,或曰“批判的继承”(傅伟勋语)。同时,“诡辞为用”也是牟氏解读向郭之《庄子》注的方法论。另外,也可看作是向郭“寄言出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以上阐释仅藉助“诡辞为用”一语在《才性与玄理》一书中出现的语境加以分析而得,在牟先生《中国哲学十九讲》一书中则对该词有着更为明晰的定义:“依道家的讲法,最好的方式就是‘正言若反’这个方式。(……)这个话就是作用层上的话。‘正言若反’所涵的意义就是诡辞,就是吊诡(paradox),这是辩证的诡辞(dialectical paradox)。”所谓最好的方式,我们首先分成两类,一个是分析的讲法,以分析的方式提出一些办法来(……)分析的方式提供的只是一个方策,一个办法,这个是属于知识的范围。第二种方式是正言若反,这种诡辞不属于知识的范围。这不是分析的讲,而当该属于智慧。(……)正言若反不是分析的方式,它是辨证的诡辞,诡辞代表智慧,它是诡辞的方式。因此照道家的看法,最好的方式是定在智能层上的诡辞,是诡辞的方式,不是分析的方式。[2](P111)
总结牟先生的意思,诡辞为用的意涵简单可以概括为:(道家的)一种言说道体或境界的独特方式——“正言若反”,与分析的方法不同(分析的讲法属于知识范围,诡辞则是智慧),辩证的诡辞是从作用层面进行发挥,而不是或不仅仅是 “提出”方策、方法,即不将所说内容予以实体化和对象化加以固定,而是从作用上活泼泼地展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牟先生是如何探析向秀、郭象注庄之“诡辞为用”,进而“诡辞为用”诠释向郭之注庄了。
(1)钢纤维混凝土拌和采用的是强制式搅拌设备进行,材料的投入顺序为:砂→纤维→碎石→水泥加入搅拌罐,并且进行1min的干拌,之后搅拌3min。
二、“诡辞为用”之用——解向秀、郭象注庄之法
(一)主体境界——以修养论诠释老庄之道与向秀、郭象之逍遥义
将老庄之学解读为境界的形上学,道视作修养境界,首先使人联想到庄子文本以及向郭注中的“逍遥”一词,诚然,无论道能否定义为客观实在的实体,抑或仅仅是形上学的预设,“逍遥”一词所囊括的涵义更多还是会被公认为圣人、至人所能达到的一种超脱放达的境界,这一境界也必然是主观的,是主体通过自我修养而达到的。牟宗三先生在解读向郭的“逍遥义”时将其分为三层,这三层分析同时也是牟氏破除“逍遥”在客观现实层面的存有,而重新定位为主观境界层面之意涵的努力:
1.逍遥的首要前提是“无待”,在《庄子》中,以宋荣子、列子以至“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的至人、神人、圣人等层层推进的手法,揭示真正的逍遥不仅不依赖于社会现实的价值评价,亦且连看似自由洒脱的“御风而行”也仍然不能摆脱“有所待”的命运。庄子描绘出大鹏的形象,成为逍遥的象征,并且与“腾跃不过数轫”的斥鴳对照,欲使人超拔出短视的现实,而有此小大之辨。但在郭象那里,这一小大之辨并不足以构成能否达至逍遥的障碍,大与小“各有自然之素”,“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因此也“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自尽”即可“逍遥”。
牟氏承续郭象之说,认为“小大之差是由对待关系比较而成”,仍然 “落于对待方式下观万物”,“则一切皆在一比较串中”:此为比较串中大小之依待,长短、夭寿、高下串中之依待亦然。此为量的形式关系中之依待。在量的形式关系中之依待所笼罩之“现实存在”又皆有其实际条件之依待,此为质的实际关系中之依待。在此两种依待关系下观万物,则无一是无待而自足者,亦无一能逍遥而自在。[1](P156)而逍遥必须是在“超越或破除此两种依待之限制中显”。牟氏认为这是庄子对于“逍遥”的“形式的定义”。在这个意义上牟氏肯定郭象所谓“放于自得之场……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即从庄子之超越逍遥转变而成的足性逍遥[3](P5-14),也是逍遥的形式之一。
2.超越或破除现实的限制网之后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真正之逍遥不是“限制中现实存在上的事”,而是“修养境界上的事”,是“属于精神生活的领域,不属于现实物质生活之领域。”牟先生借程颢之言进一步解释说:“故放于自得之场,逍遥一也”,此普遍陈述,若就万物言,则实是一观照之境界,即以至人之心为根据而来之观照。程明道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者是也。并非就万物真能客观地至乎此“真实之逍遥”,就万物自身言,此是一艺术境界,并非一修养境界。凡艺术境界皆系属主体之观照。随主体之超升而超升,随主体之逍遥而逍遥。所谓“一逍遥一切逍遥”,并不能脱离此“主体中心”也。[1](P157)
万物不可能真实客观地达到这样一种“逍遥”,而只能是依于主体境界的关照,随主体逍遥而逍遥。在肯定了逍遥是“修养境界的事”之后,牟氏进一步以“主体中心”的“观照”来解说万物自身角度的逍遥何以成立。主体依据“至人之心”为根据,“观照”于万物,得出万物“自得”、“逍遥”的结论,因此万物之逍遥绝非客观实有意义上的逍遥,而是以主体为中心“观照”的结果。这一说法颇有些类似于《坛经》中“心动则风、幡动”的故事,牟氏亦特于此做出区分。禅宗言“心动,则风、幡皆动”,则“一切皆落实于实际条件之依待中”,主体的变化最终仍然要落实在客观实际之中,有客观实际则有依待,与逍遥无待之境失之远矣。故庄子以至向郭之逍遥必定是修养境界层面的,与佛教禅宗思想的心物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抛开牟先生对禅宗公案的理解不谈,此处还有一个问题是“万物”在郭象原文中应当即是“万民”、“众生”的含义,而牟先生的主体逍遥说则将万物宽泛视为客观世界的全部对象,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即与郭象注本义不合,或者可视为牟先生对郭象注的另一种“诡辞为用”。
3.厘清和界定了逍遥的含义之后,庄子的圣人形象也获得了进一步诠释。在《庄子》文本中以“不食五谷”、“餐风饮露”、超然物外为特征的神人、至人、圣人三者合一的形象,在郭象的诠释中转化为颇有些儒家色彩的“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郭象原注作“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即圣人之治能使“有待”之万民“不失其所待”:不仅不“独自通”,亦且“与物冥而循大变”。这有些类似于关于尧之时“帝力于我何有哉”农人歌谣的传说所体现出的政治理想,但这一理想与儒家之圣王仍然有所不同,牟先生认为“不失其所待”的涵义应为“不以仁义名利好尚牵拽天下,则物物含生抱朴,各适其性”,与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积极意义之功化其实不相类,并且尤不是“牵动其欲望而满足之”之“不失其所待”。与儒家相比,道家理想的政治应为“道化之治”:道家之功化则为道化之治。道化之治重视消极意义之“去碍”……上下都浑然相忘,“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如是,则含生抱朴,各适其性,而天机自张。此即为“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也。在去碍之下,浑忘一切大小,长短,是非,美丑,善恶之对待,而皆各回归其自己,性分具足,不相凌驾,各是一绝对之独体。[1](P158)
牟先生由此将儒道两家之功化区别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形态,这里不妨通过与冯友兰先生对逍遥于无待的解释相比照,以进一步理解引文中牟先生的观点:冯先生将逍遥与无待解释为“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庄子“超越有限,而与无限合一,从而享受无限而绝对的幸福。”进而在与物和道的关系中到达“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而向郭注所作的功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把庄子只是暗示了一下的东西讲得更加明确”。“天是万物的总名”,“从天的观点看万物,使自己与天同一,也就是超越万物及其差别,用新道家的话说,就是‘超乎形象’”。[4](P195)
很难说冯先生的解释不是郭象思想之原义的展现,但若从多种解释相比较的角度来看,冯先生眼中郭象对于庄子的诠释,不妨也可视为冯先生自己对郭象学说诠释的方法。而在牟宗三先生的诠释中,这种解释也许会因其仍然执着于对客观现实的牵挂,而并未能达至真正的无待。幸福与自由未始不是仍然要依赖于客观现实而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显现的。在牟先生看来,这正是未能无待的表现之一。真正的无待应当是全然系属于所谓“主体中心”而言的,一切逍遥、无待,不过是在主体自足、无待的基础上,观照而然的结果。至人之逍遥无待,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万物亦在主体之观照下呈现“自得”与逍遥的状态。向郭诠释所构造的世界即以这三个层次次第显现,牟氏称之为“一整个浑化之大无待”,在此“大无待”中,“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此亦可说整个是一‘诡辞为用’之大诡辞所成之大无待。 ”[1](P160)
(二)当体具足——以主体境界概括向秀、郭象之天籁义
逍遥的前提是自足与无待,自足与无待的根本又当建立在万物如何生、如何有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向郭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是将万物之本体摆脱天地、无之生化的旧说,一改王弼以来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①认为天地不过是“万物之总名”,不能生万物,而“无既无矣”,“而不能生有”。冯友兰先生说“老庄的哲学,推到上帝,而立所谓‘道’。郭象则不但不承认有所谓上帝,他并且不承认有所谓道。”“事物终究是‘无故而自尔’”,“物皆自然而然,更无所待”,也就是郭象所说的“独化”。[5](P376)郭象这一“独化”论的提出,首见于《齐物论》“罔两问景”的故事中,郭象由“罔两”于坐起行止之“寻其所待”与“责其所由”皆“寻责无极”,得出“夫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且“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的独化结论。由这一独化论,郭象生发出对于庄子“天籁”的全新阐释。“天籁”在《庄子》中表达的是客观世界中万物千变万化的自然状态,郭象则进一步强调,万物的这种自然状态背后,并没有一个造物者或主宰,役使它如此。“天籁”之天不过是“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天自身尚且不能“自有”,如何有物,又如何能“役物使从己”?因此,天然的意思不过是说,“自己而然”,“非为之也”。牟先生以其主体境界说指出,在这里“仍先须知此”自然“是一境界,是由浑化一切依待、对待而至者”。“绝对无待,圆满具足,独立而自化、逍遥而自在,是自然义;当体自足,如是如是,是自然义。”
牟氏因此强调道家所谓的万物之自然实际上仍依待于主体,是一种主体的境界:道家之自然,尤其庄子所表现者,向郭所把握者,虽亦不经由超越的分解而客观地肯定一第一因,然却是从主体上提升上来,而自浑化一切依待对待之链锁而言 “自然”,故此自然是虚灵之境界。从主体上说,是“与物冥而循大变”,自冥,一切冥。故从客观方面说,是一观照之境界,根本上不着于对象上,亦不落于对象上方施以积极之分解,故个个圆满具足,独体而化。此即为绝对无待,亦即所谓自生、自在、自然,把超越分解所建立之绝对,翻上来系属于主体而为浑化境界之绝对。[1](P168)
郭象由此而将“天籁”也纳入他的“独化”理论之中,《逍遥》、《齐物》两篇也在同一宗旨下获得统一。牟先生也说“齐物者即是平齐是非、善恶、美丑,以及一切依待、对待而至之一切平平。一切平平,即是个个具足,无亏无欠,无剩无余。 ”“故‘逍遥’、‘齐物’,其旨一也”。“向郭在《齐物论》注中所发之‘天籁’义,实即《逍遥游》注中义也。”但牟先生也指出,向郭注《齐物论》,“只能把握其大旨,于原文各段之义理则多不能相应,亦不能随其发展恰当予以解析。”通于逍遥之义的毕竟只是天籁的一个方面,整篇《齐物论》所要表达的绝不只是万物之自然、自在这一层含义。牟先生也进一步将郭象的“天籁”也纳入之前构建的关于“逍遥”的主观境界理论中,并进而认为郭象所言“自己无待,一切无待;自己平齐,一切平齐”之境界,也不能被当作一种客观问题加以辩论,落于因果方式,否则就会远离郭象以“个个具足”来诠释“无待”之本义。
(三)虚静浑化——通达逍遥境界之工夫论(解读向秀、郭象之养生义)
牟宗三将向郭之养生义概括为通达逍遥境界的工夫论,并于庄子及向郭注中的“知”与“无知之知”两者特意加以诠释。而于此诠释的过程中,尽可看出“养生”一词在庄子,向郭注以至牟氏之诠释中,从“安时处顺”的生存之道,到“任其至分”的冥极之术,再到牟先生“虚静浑化”的工夫论之演变过程。《养生主》开篇即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郭注云:“故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也。”在牟先生看来,“知”是表示“离其自在具足之性分”而“陷于无限的追逐中。”而养生之义正要避免这种失当,消除这种追逐,做致虚守静的功夫,即“灭于冥极”:失当,则离其自性,此所以有知之名……凡陷于无限追逐而牵引支离其中性者,皆可为知所概括。……此皆所谓离其性之失当,亦即皆伤生害性者也。故养生之主,亦即在“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功夫,将此一切无限追逐消化灭除,而重归于其自己之具足,此即所谓“灭于冥极”也。[1](P177)
郭象的冥极之术在牟氏的诠释之下成为一种通达逍遥境界的虚静浑化之工夫。灭除了无限的追逐,而向自身之具足回归,人生之有限也在这个意义上变得“永恒而无限”,“绝对而无待”,“虽有涯而无涯矣”。玄冥、逍遥、独化由此而通贯起来,达成“养生”的最终目的“全生”。“全生”又并非或不仅限于世俗所谓福寿爵禄之谓,否则即落于牟氏所谓后世道教所禀之“第二义”,落于“养生”义涵的世俗化解释中。“全理尽年”非是直接落于“有涯之生”上,辗转于糗粮醪醴之中以全之尽之……盖其“全理尽年”,正是由冥极而灭失当,消除其无限之追逐,而回归于自在具足之境,此是由极深之虚静工夫而至者。[1](P177)由此也可将道家的工夫论总结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因此,老庄文本中看去玄妙不真的“天人”、“至人”、“神人”皆非后世道教通过种种肉身修炼之功夫汲汲于达到的在现实存在的、生命迹象上异于常人的神人、仙人,而是“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在主观境界上超越世俗的至人、圣人。
厘清了虚静的境界工夫论与世俗的养生法之后,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因无涯之知与有涯之生造成的矛盾,是否必然要以摒除对知的求取为解决途径,是否闭目塞听、无所作为就是唯一可以保全生命的方式?而这一方式是否真的合乎讲求“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之养生义的真相?庄子言“德荡乎名,知出乎争”,显然反对的是因好名和争胜而导致的“德”失真和“知”的外露。并非将合乎于道的“德”与“知”都一概摒弃。郭象因此说“故遗名知而后行可尽也”。牟先生指出,这里的“遗名知”即是“灭名知于冥极”。只有“遗名知”而“化于玄冥之境”,才能“德可葆,而生可全”,并以《人间世》篇“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之说,提出“无知之知”,即“无知而无不知”,并对有知之知和“无知之知”加以比较。有知之知皆出于歧出之失当,皆在无限追逐中表现:顺官觉经验而牵引,顺概念思辨而驰骛,在主客对待之关系中而撑架。“灭于冥极”者,即以玄冥而灭此牵引、灭此驰骛、灭此对待关系之撑架,而归于“无知之知”。“无知之知”即“无知而无不知”。根本是一个止,而即止即照。止是无知,照是无不知。[1](P181)
庄子的说法是“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即使耳目感官向内通达,而排除心机,牟先生解为“停止意必固我之造作”,心机、“意必固我之造作”正是郭象所谓之有知、有心。要排除这一有知,有心,即要“自知”、“自见”、“自生”,(原文为 “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为知以知之;世不知见之自见,因欲为见以见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将为生以生之。”)因此,庄子之“无知之知”在郭象即是“自生”基础上的“自知”、“自见”,牟先生也说,“‘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却非顺心知耳目追逐以自通,而乃‘灭于冥极’以内通。”郭象的养生最终归于他所假设的性分,冥极,即是任其自性,适其自性。在此冥极的基础上,冥合的不仅是知与生,有涯与无涯,更有人与天。“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泯灭无涯之追求,归与“知之自知”,于是乎天与人“相与为一冥”,“天即人”,“人即天”,“暗相与会而俱全”,方是“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牟先生说,“谈养生义止于此”。
(四)迹冥圆融与中西会通——从郭象注庄之方法论析出与佛教和西哲融合之契机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迹冥圆融与迹冥合一是郭象从庄子文本中析出的,“齐一儒道”、“任自然而不废名教”(汤用彤语)思想之方法,郭象从庄子文本中区分“迹”与“所以迹”,而将庄子中尧、许之形象扭转过来,重新树立起合乎自然的圣贤形象。牟先生却举出这一对概念,作为玄学、道家思想融通于佛教思想的契机,更将迹冥之关系分为观冥、观迹、迹冥圆融三层,并且认为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之说也不外此迹冥圆融之模型。牟先生说:“会而无执即为冥,冥而照俗即为迹。冥则成其无累之会,故体化合变而游无穷。迹则实其冥体之无,故冥非绝会,即在域中。游无穷,则会而冥矣,会而冥,虽迹而无迹……离迹言冥,是‘出世’也;离冥言迹,是入世也;冥在迹中,迹在冥中。是‘世出世’也。‘世出世’者,即世而出世,即出世即世,亦非世亦非出世也,是谓双遣二边不离二边之圆极中道也。”[1](P165)
向郭注有言,“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天下篇》注)可见其注庄之关注点仍在现实政治层面。汤用彤先生也指出“内圣外王之义,乃向郭解庄之整个看法,至为重要。 ”[6](P105)姑且不论这一关注点在向郭注庄之义理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仅作为背景性的思考,亦可提供一个分析的视角,即向郭对于在现实层面的考察。在现实层面,迹冥圆融或迹冥如一表现为 “德充于内,应物于外”。与《逍遥游》篇的尧许之辨相呼应,郭象也重新诠释了《德充符》篇中的“天刑”一词:今仲尼非不冥也。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夫顺物,则名迹斯立,而顺物者非为名也。非为名,则至矣,而终不免乎名,则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响也。影响者,形声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则名迹可遗。名迹可遗,则尚彼可绝。尚彼可绝,则性命可全矣。[1](P187)按郭注,政权的正当性在于“德充于内”,必然“应物于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郭注语)。牟先生也说“德充于内,如真是具体之德、具体之充,则必应物于外”。以“迹冥”说解之:自“德充于内”言,则谓之“冥”;自“应物于外”言,则谓之“迹”。 情尚于冥者,则以迹为己之桎梏,故必绝迹而孤冥。然绝迹而孤冥,则非其至者也。既非大成浑化之境,而冥亦非真冥也。非真冥者,孤悬之冥也,犹执着于冥也。此之谓浑化之大冥。大冥者,冥即迹,迹即冥,迹冥如一也。迹冥如一则桎梏之不可免。桎梏之不可免,则谓之“天刑”,“不可解”谓之“天刑”。[1](P188)牟先生又用佛教大小乘之区别为喻,说明“孤悬之冥”,犹如小乘佛教之“怖畏生死”,而“欣趣涅盘”。又“以大成圆教寄之于尧与孔子。”虽然儒道的差异由此得到了融通的诠释,牟先生仍然强调了儒家与道家、佛教思想的差异。如将道家归结为 “苍凉悲感之智者型”,佛家即为“含消极意义之通透圆境型”,独儒学“居宗体极”,“而乘悲心仁体以言圆”,富有积极意义。故能 “承体起用,开物成务”,“乃充实饱满之教”。
牟先生在对《应帝王》篇“壶子示相”一段内容的诠释中,借用了成玄英疏中使用的佛教 “四门决”,称为“四门示相”,而又强调此“四门决固出于佛教”,然而向郭注已然“其义俱备”,且“庄子本以四义示相,理之所在固应如此,非比附也。”且不必纠缠于庄子或向郭义是否俱备所谓 “四门示相”之争,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在以此四门决阐释玄学之圆教时,提到的“超越心体”的概念。与佛教之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及禅宗的“即心即佛”观念相对,牟氏举出一“超越之心体”概念,以为儒学之异于老庄、佛教之根本处,并言儒家不在智入,而自仁体之感通神话说,故无许多诡辞而亦平实如如也。“而道家,超越心体似不显”。“属超越之心境,而唯是自境界言,并不立一实体性之超越心体”。“佛教则立一超越之心体,此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乃至涅盘佛性,统摄一切法”,并认为儒学中的“心即理”、“心外无理”正是儒学“超越心体”的体现,“心性天道,无二无别”,因此才能“万物皆备于我”,才能“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但“在佛家,超越心体与般若智冥合为一”,而“在儒家,超越心体亦与仁之感通实践冥合为一”,至于道家则不立超越心体。牟氏认为“立一超越之心体,始真可言圆顿之教,为圆顿之教立一客观而严整之可能性,立一超越而形式之可能性”,并解释说:“但不立超越心体者,则圆顿唯是自诡辞为用之境界说,便无客观而严整之标准,圆顿便不免于虚晃,而亦易流于枯萎。诡辞为用之境界之圆顿虽可到处应用,然无超越而客观之根据以提挈之,则便无客观之充实饱满性。此只有主观性原则,而无客观性原则,故易流于虚晃与偏枯也。超越实体是客观性原则,仁之感通实践是主观性原则(般若智亦是主观性原则),主客观性统一方是真实之圆顿。此天台宗之所以列大成空宗为通教,华严宗之所以列之为大乘始教也,亦道家之所以教味不重、刚拔不足之故也,于‘天刑’、‘戮民’之词亦可以见矣。此固甚美,究非至极。”[1](P197)
在牟先生看来,道家“诡辞为用”的境界虽有极强的应用性,但较之儒家之“心即理”,始终是缺少一种超越性的、客观性原则或依据。牟先生立一“超越心体”据以分辨儒学与道家和佛教思想的根本区别,其依据是与儒学乃至佛教思想不无矸格的主客观两分的原则。另外,在牟先生的诠释中,无论是庄子的逍遥、天籁还是向郭之自足、无待,基本上都可以囊括在其所主之“主观境界”说之中。但庄子乃至向郭都更为关注的内圣外王、“应帝王”、“治天下之术”却难以涵盖其中,因此在分析庄子,以至玄学关切的终极问题上,我们或者也可以说牟先生的解读“此固甚美,究非至极。”
三、结语
牟宗三先生在其《现象与物自身》一书的序言中说“其初也,依语以明义;其终也,依义不依语。 ”[7](P7)按李明辉的说法是引用佛教的“四依”即“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可以看作是牟先生学术方法论的自我总结。对于“不依语”,牟先生自己的解释是“为防滞于名言而不通也。凡滞于名言者其所得者皆是康德所谓‘历史的知识’,非‘理性的知识’”。李明辉称之为“超乎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诠释学”,他说“依牟先生之见,哲学诠释的对象并非语言文字本身,而是语言文字所要表达的义理,而义理只能藉理性去把握。因此他以‘客观’一词所表示的与其说是‘合于文本(text)原义’,不如说是‘合于理性的根据’。 ”[8](P183)正是出于这一思想,牟先生才能将庄子乃至郭象之逍遥无待,诠释成为独特的主观境界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的玄学研究中独树一帜。②
注 释:
①魏晋玄学的本体论说法尚有争议,许抗生先生在《关于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的再研讨》一文中提出,玄学不能用宇宙本体论来概括,而应当讨论的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魏晋玄学中除何晏、王弼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宇宙本体论外,玄学家嵇康、阮籍并不讨论有无与本体问题,而向秀、郭象是反本体论的。参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期第58至63页。
②刘笑敢在 《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76至90页的《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一文中将各种对于老子的道的诠释分为四类,其中包括客观实有类、综合解说类与贯通类解说,而只有牟宗三先生一人主张“主观境界说”被称为“最为独特”。但刘文指出“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是牟宗三的创造,“突出了老子哲学的实践性格和道的价值意义,其理论融合在牟先生对整个中西哲学及儒释道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之中。但是如果我们集中于对老子的诠释,特别是主要依据《老子》文本对老子思想进行诠释时,牟先生的观点就仍有推敲斟酌的余地。”其实也是指牟先生的诠释是“合于理性根据”的诠释,而非“合于文本的原义”。
[1]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刘笑敢.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J].中国哲学史,2006,(3).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冯友兰.冯友兰谈哲学·郭象的哲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6]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8]李明辉.牟宗三先生的哲学诠释中之方法论问题[A].中国文哲研究集刊[C].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