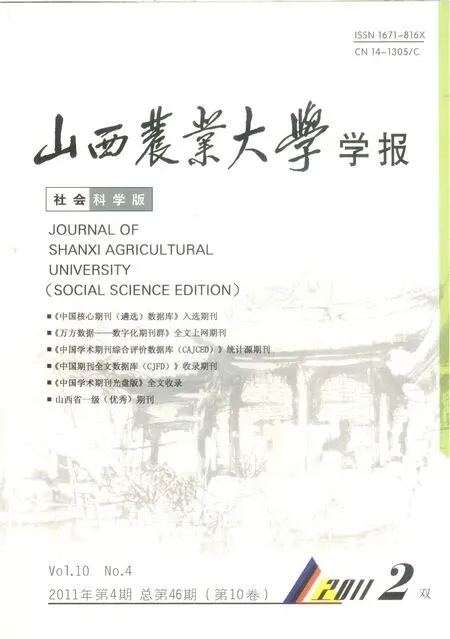诗意的言说:作为 “牧歌”的 《路得记》的叙事解读
雷阿勇
(闽江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108)
有人说,“如果将希伯来圣经的历史叙述比喻为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的话,那么 《路得记》就像是河套平原上恬淡、宁静的田园风光。”[1]的确,在希伯来圣经中,《路得记》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它是 《旧约》39卷书中唯一两卷以女性命名的记述之一。《路得记》叙述简洁,结构精巧,是一篇杰出动人的文学作品。《路得记》的作者本着鲜明的文体自觉,运用精湛的叙述技巧,用简洁诗化的笔触构绘了一个古代希伯乡间古朴、宁静、诗意的完整而自足的田园世界,并使之成为希伯来文学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一曲美丽而悠长的牧歌。因此,考之 《路得记》“牧歌说”的源流及实质内涵,无疑有助于对其 “诗化叙事”文学性的美学认识。
一、缘起:牧歌说的提出
德国诗人歌德(J.W.Goethe,1749~1832)曾赞不绝口地称 《路得记》是 “最可爱的小牧歌(loveliest little idyll)”。[2]他说,“《旧约》的许多篇章展现了一个热情高尚的心灵,是诗歌艺术中的瑰宝。……就拿 《路得记》来说吧,它试图为以色列的国王寻找一个体面的、有趣的血统;同时它又是一篇流传下来的最可爱的小史诗或小牧歌。”[3]歌德的“牧歌说”对《路得记》文体风格几乎定了调,后世学者大多引用他的提法。
正式提出 “牧歌说”当是理查德·摩尔登(Richard G.Moulton,1849~1924)。摩尔登出生于英国,曾任英国牛津大学诗歌教授。1892年他被美国芝加哥大学聘为英文教授,九年后转聘为该校的文论教授。摩尔登是 “作为文学的圣经(the Bible as literature)”第一个真正的践行者,虽然该词的发明者为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1822~1888)。[4]1895年摩尔登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了 《圣经之文学研究》 (The Literary Study of the Bible),首次以文学视角对圣经作了系统研究。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次年 (1896)即分别在美国波士顿和英国伦敦再版,之后又不断重印和再版。在该书中,摩尔登将《路得记》命名为“史诗体牧歌(Epic I-dyl)”。他写道:
“If the chief distinction of the Idyl be its subject matter of love and domestic life,then in all literature there is no more typical Idyl than the Book of Ruth.Following the Book of Judges,which has been filled with bloodshed and violence and heroism of the sterner virtues,it comes upon us like a benediction of peace.It contains no troubles of family life—exile,be-reavement,poverty;while its grand incidents are no more than the yearly festivities of country life,and the formal transfers of property that must go on although kingdoms rise and fall.”[5]
很难说摩尔登的观点没有受到歌德的影响。与歌德一样,摩尔登准确把握了 《路得记》的风格特色。1936年,摩尔登的 《圣经之文学研究》由贾立言、冯雪冰等人译成中文出版。该译本对上面引文作了如下翻译:
“假如说牧歌的主要特点乃是在乎它论述爱情和家庭生活的事情,那么在一切文学中没有一本书能比 《路得记》更能表现牧歌的特色了。那《路得记》是排列在 《士师记》之后,读过了士师时代那种血与铁、好武与仇杀的故事,再读下一卷平静温和的 《路得记》,无异是看过了全武行的三本 《铁公鸡》,锣鼓喧天,乌烟瘴气,忽地全剧告终,人声倏静,萧管一声,来了一出青衣小戏。”[6]
译文准确而生动,特别最后一句的翻译,运用意译手法,套用中国京剧的武戏与青衣文戏作比照,准确传达了原书作者对 《路得记》的风格评价,活脱出硝烟过后那份诗意的宁静,可谓达到了钱钟书所谓的 “化境”。
二、共鸣:牧歌说的溢流
由于歌德在西方文化史上巨人般的地位,以及摩尔登在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及突出成就,特别 《圣经之文学研究》在圣经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牧歌说”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后世学者在描述 《路得记》的文体风格时,都会提到“牧歌(idyll)”一词。1899年惠顿(James M.Whiton)撰文《路得和以斯帖》(Ruth and Esther),该文作为他与摩尔登等人合编《作为文学的圣经》(The Bible as Literature)一书第五章于当年出版。文中惠顿首次将 《路得记》与 《以斯贴记》放在一起对比研究,认为两者有诸多相似又有许多不同。惠顿认为这是一种“让人快乐的对比(happy contrast)”,他把《以斯帖记》比作戏剧(drama),同时称 《路得记》为牧歌 (idyl)。他认为 《路得记》在旧约圣经 《七十子译本》和 《武加大译本》中的位置编排十分得体,如同 “一片长着葱绿棕榈和淌着甘美井水的荒漠绿洲,”处在 “描绘血腥和痛苦景象的 《士师记》和 《撒母耳记》的两书之间”,是“一曲优美的散文诗(a sweet prose-poem)”。[7]
歌德和摩尔登的 “牧歌说”在我国的圣经文学研究者中亦有一定影响。我国现代文史学家、20世纪20年代最大文学团体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及实际领导人郑振铎极力称赞 《路得记》,认为是 “‘杂著’中的一篇最好的牧歌。”[8]“文学研究会”另一发起人周作人亦认为 “《路得记》有牧歌的优美。”[9]之后,国内著名圣经学者朱维之和梁工等人均高度赞美 《路得记》的牧歌特质。梁工盛赞 《路得记》“是一曲爱的颂歌。她在散发着田园泥土香气的优美意境中,塑造了几个以爱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感人形象,尽情赞颂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谅、彼此尊重、真诚相爱的美好感情。”[10]
三、泛化:“牧歌”的风格论说
观之源流, “牧歌说”所指的其实并不是《路得记》的文学类型,而更多是从风格内容而言。摩尔登的 “牧歌说”即出于这一角度。菲舍尔(Irmtraud Fischer)亦言,《路得记》被视为“牧歌”,乃是它主要营造了一种抒情的背景。[11]
其实,西方学界对文类的划分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将文学基本体裁按等级依次分为:歌谣、田园诗、长篇小说、史诗和戏剧。叔本华的“田园诗”主要是指 “抒情诗”,是归为 “诗”而非“文”。英文 “idyll”一词源自希腊语,是古希腊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抒情短诗,后来被用来指称具有田园诗风格的文类,常与“pastoral(牧歌)”互用,中文一般译为“田园诗”或“牧歌”。1908年凯莉(Angeline P.Carey)在其所著的《读者基础》(The Reader’s Basis)中对“idyll”作了详细解释:“田园诗(idyll)的特点常常是叙事性的,但它实际上是抒情诗、史诗 (叙事诗)和描述性诗歌的综合体。它是任何诗歌形式的微型体,是诗歌描述对象细节的完美体现。当田园诗主要描绘乡村生活和自然风景时,它就被称为牧歌(pastoral)。”凯莉认为 《路得记》就是 “一篇典型的牧歌 (a typical pastoral)”。[12]现代批评家常把那种偏于表现单纯、素朴生活,手法上强调抒情性、体现舒缓悠长等特点的作品,称作 “牧歌式 (田园诗式)”的作品。可见牧歌所表现的更多是作品的风格内容。它处于诗歌、散文、小说这几种文类的边缘交叉地带,可以坐拥这几种文体形式,具有无限的阐发的潜能和张力,因此牧歌最显著的文类特征也许就是 “跨文类”、 “泛文类”乃至“无文类”。摩尔登认为 《路得记》最具 “牧歌”特色,但他亦认为 “牧歌并不是一种明显的文学形式,乃是别种文学形式的变体。圣经文学中含有史诗体牧歌正如含有抒情体牧歌一样。”[13]这里摩尔登接受亚里士多德 《诗学》的观点,将“史诗”界定为一种叙事文体,因此“epic”一词也常译作“叙事诗”。由此可见,摩尔登的“史诗体牧歌”乃是指叙事体牧歌。
《路得记》所描画的恬静的田园风光及其流露的生活气息,带有 “牧歌”的风格特点。所以在描述 《路得记》的体裁风格时,学者更倾向于把 “牧歌”一词作为饰语。朱维之称 “《路得记》是一篇古希伯来人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14]朱维之的学生梁工教授进一步指出,“《路得记》是一部质朴优美、内容深邃的田园小说”。[15]被称为 “形式批评之父”的德国旧约学者衮克尔(Hermann Gunkel,1862~1932)在将《路得记》归为“短篇小说(novella)”同时亦着重指出:从内容上看,作为 “短篇小说”的 《路得记》接近于 “牧歌 (idyll)”这种文类,即故事情节简单,主要人物很少,没有反面角色 (evil character)。[16]尼尔森(Kirsten Nielsen)指出,衮克尔使用 “牧歌 (idyll)”一词,正是为了强调 《路得记》的诗性,也就是文学特性。[17]《路得记》的田园牧歌情调,使它卓然屹立于圣经文学之林,吸引众多论者的注意并为之执迷地解构和阐析。梅尔斯(Jacob M.Myers)[18]等现代学者努力追寻 《路得记》原初诗体的文本形态,进行皓首穷经式的溯源和解读。如果 《路得记》确有以诗体形式存在过,那么那种诗的形式现已幻化为寄寓在散文化文本中的一种诗化韵味与风格,如意境的诗化,平行、对称、反复及节律感的运用。
四、界定:作为 “诗化小说”的牧歌式叙事
虽然 “牧歌”的跨文类或泛文类风格使其坐拥了小说、散文等文体形式,但这种非文类化的“牧歌”显然无法作为 《路得记》确切的体裁界定。无可否认,《路得记》是一篇富有诗意且质朴洗练的 “叙事杰构”。诚如衮克尔和朱维之等人所论,从形式上看,《路得记》是一篇精巧成熟的短篇小说。因此,《路得记》现有文本所呈现出的牧歌式诗意情调构就了其 “诗化小说”的文体特征。
“诗化小说”的概念可追溯至法国象征派诗人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于1893年提出的原则:“小说是一首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19]不过古尔蒙并未正式提出 “诗化小说”的概念。到了20世纪20年代,“诗化小说”得到西方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及文论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进一步阐发。虽然伍尔夫亦未使用 “诗化小说”这一术语,但她将 “诗化”作为未来小说的样式。她认为:未来小说将用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写成, “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这种诗化的文学样式不注重写实,而是密切且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它不会仅仅或主要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将表达个人心灵和普通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在沉默状态的内心独白。伍尔夫进而指出,这种诗化的未来小说表现的将是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关系,人的想象和梦幻。[20]后来论者在古尔蒙和伍尔夫的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此种文类特有的叙述方式和诗意方式,提出了“诗化小说”的概念。
不难发现,《路得记》在许多方面拥有伍尔夫所述的 “诗化小说”的诸多元素和特点。历代诸多论者在评论 《路得记》的文体风格时常用“idyll”来形容,作家诗人更常在作品中对路得故事进行诗意的化用和解读,而西方画家亦常以《路得记》为题材,创作了许多田园牧歌风景画。《路得记》的牧歌式风格正源自本身的诗性特质。
其一,语言和结构的诗化。《路得记》语言准确而生动,具有散文的质朴简约,并富有诗歌的韵律感,是 《旧约》中运用对话比例最多的一卷书。其对话描写流畅、富有诗意又不乏幽默感,展现了希伯来文学的精彩对话描写艺术。尤其第1章第16~17节路得说服婆婆那段精彩表白,以抒情语调、明快节奏和反复、排比等修辞手法,令人印象深刻。语言学者瓦德(Jan de Waard)与奈达(Eugene A.Nida)盛赞这段话有如诗般的节奏效果。[21]《路得记》故事结构精巧凝练,首尾构成多重对比,展现了诗般的完美对称结构。不少学者认为 《路得记》曾为诗体故事。从现有文本形式看,《路得记》无疑是一篇精巧完整的短篇小说,因此曾经的诗体所内化的诗性,无疑使它成为小说与诗的完美结合体,从形式上达到了 “诗化小说”的外化要求。
其二,意象与意境的诗化。《路得记》的作者运用精炼的笔触,营造了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民俗环境和背景,构筑了一个宁静古朴、完整自足、充满诗意的古希伯来乡间的田园牧歌世界。《路得记》田园意境的描绘于不经意间构就了诗般柔情氛围,且经由画家绘画的形象演绎,更加丰富了其诗意的内涵。法国著名古典主义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晚年创作的历史风景组画 《四季》中的 《秋》即取材于路得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路得拾穗”这一田园牧歌的意象画面。因此,《路得记》诗化的语言形式赋予意象以诗意色彩,而意象的描绘及意境的营造反过来深化了诗意语言的美学效果。
其三,主题及思想的诗化。《路得记》是一篇抒情韵致的文学典范,其诗情流动的字里行间,透露了关于历史和生命的抽象命题。如果说语言的诗化和诗般意境的营造已构成 《路得记》“诗化小说”的文体特征,那么路得故事所含蕴的生命哲思无疑加深了其 “诗化小说”的特质。《路得记》的整个故事从几个原型母题进行延展,生动地容纳和展现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其展现的人与人之间温馨的爱已超越个体的命运关怀,凝练成一种深层的普世意义,引发了读者对生命意义及生活本质的思考。而这一层面的意义在《旧约》那充满铁血的历史叙事中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
总而言之,多层面的诗化叙事方式加上乡村田园意境的营造以及浪漫爱情故事的述说,最终构就了 《路得记》牧歌的风格特色。因此,就文体展现的浪漫诗意特征而言,《路得记》确可成为一篇出色的 “诗化小说”,而从故事内容涵容的丰富情感意绪来讲,《路得记》又称得上一曲动人的牧歌。
五、结语
《路得记》是一篇牧歌式风格的 “诗化小说”。《路得记》的作者用饱含情感的笔触,秉承着对文本形式鲜明的自觉,巧妙利用故事结构的内在张力,充分发挥驾驭叙事的精湛技巧,以诗意的言说营造了一种田园牧歌式隽永的意境。而历代文人和画家们对 《路得记》进行各种抽象及形象的解读和演绎,更是丰富了这个动人故事的诗意内涵。《路得记》是伍尔夫 “诗化小说”理论的完美预演。这预演在苍茫的历史时空中演化了两千多年之久,给多舛的希伯来民族和多难的西方社会吹来了一丝难得的诗意气息。这些正是作为“小说”样式的《路得记》仍勾起读者对其诗意的探索,且屡屡被赋予“牧歌”美誉的原因所在。
[1]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0.
[2]John Edgar McFadyen.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M].London:Hodder &Stoughton,1932:290.
[3]Alex Preminger and Edward L.Greenstein.Hebrew Bible in Literary Criticism[M].New York:Ungar,1986:3.
[4]David Norton.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76-277.
[5]Richard Green Moulton.The Literary Study of the Bible[M].London:Isbister &Co.,1896:253.
[6][英]摩尔登.贾立言,冯雪冰,朱德周译.圣经之文学研究 [M].上海:上海广学会,1936:154.
[7]James M.Whiton.Ruth and Esther[A].Richard Green Moulton,John P.Peters,A.B.Bruce and others,eds.The Bible as Literature[C].Boston,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mpany,1899:51.
[8]郑振铎.郑振铎全集·文学大纲 (一)[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55.
[9]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9.
[10]梁工.圣经文学导读[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92.
[11]Irmtraud Fischer.The Book of Ruth as Exegetical Literature[M].38th International Jewish-Christian Bible Week,23rd-30th July 2006:1-2.
[12]Angeline Parmenter Carey.The Reade’s Basis[M].Indianapoli:The Echo Press,1908:101.
[13]Richard Green Moulton.The Literary Study of the Bible[M].London:Isbister &Co.,1896:253.
[14]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88.
[15]朱维之,梁工.古希伯来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91.
[16]Hermann Gunkel.Ruth[A].Reden und Aufsätze[C],Gö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1913:84-86.
[17]Kirsten Nielsen.Ruth:A Commentary[M].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1997:5.
[18]Jacob M.Myers.The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Form of the Book of Ruth[M].Leiden:E.J.Brill,1955:33-43.
[19]周天锦.20世纪法国小说史[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37.
[20][英]弗吉尼亚·伍尔夫.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14-216.
[21]Jan de Waard and Eugene A.Nida.A Translator’s Handbook on the Book of Ruth[M].2ded.London/New York/Stuttgart: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