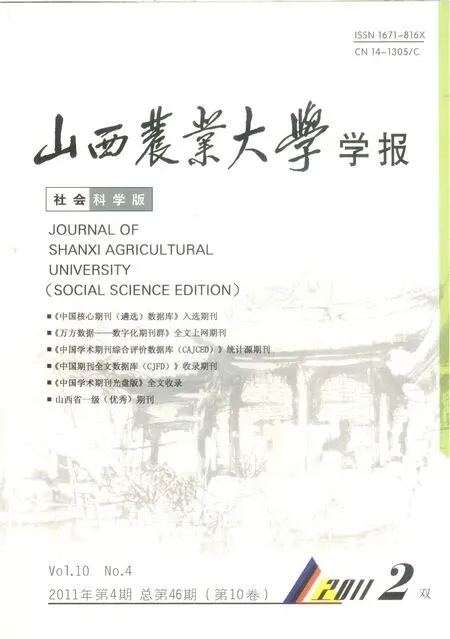符号学语言观指导下语码转换的翻译研究
张敏
(太原科技大学外语系,山西太原030024)
一、引言
“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是指同一语言活动中,说话者从使用一种语言或方言转换到使用另一种语言或方言”[1]。这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外研究者已从社会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会话分析和语用学各个角度对语码转换的发生原因、条件、动机和结构特征做出了大量深入的分析,但回顾历史文献可发现,其中绝大多数研究是围绕口语交际过程中的会话性语码转换进行的,对于文学语篇中的语码转换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少见有结合翻译研究讨论这种 “转换的转换”。然而,由于多种语码并存的复杂性,其翻译已经成为众多译者遇到的难题。本文将借助符号学语言观,对文学文本中的语码转换及其译本进行分析,尝试探讨以下问题:语码转换这种语言形式在文学文本中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这种语言形式的可译度有多高?译者在翻译语码转换的过程中应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手段?
二、语码转换符号学意义分析
符号学(Semiotics/Smiology)是研究符号传意的科学。符号学观点认为,整个世界就是由各种符号子系统组成的一个总符号系统,语言就是这个大系统中最为复杂、典型的一个子系统。由于翻译活动涉及到在不同语码系统之间进行符号的使用、阐释及掌控,因此,研究符号如何指意,对翻译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符号学中对指意的研究应属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莫里斯(C.W.Morris)的最为成熟。他认为,一个符号由三部分构成:符号所指(a represent of the sign)、符号载体(sign vehicle)和符号阐释者(an interpretant),这三部分分别对应三种符号学意义: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指称意义是指语言符号与其所描绘或叙述的事物的关系,是语言符号的表层意义,其核心内容是事物的基本区别性特征;言内意义考察的是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如发音、词汇、语法、句子、语篇等层面上的排列组合等安排;语用意义反映的是发出话语的人的信息,如身份、年龄、地理方位、态度、个性、意图等,这些信息不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隐含在语言当中,需要译者去发掘。”[2]这三个意义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意义,代表着承载信息的内容、形式与功能。
语码转换这种语言形式,从指称意义来讲,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语码相组合来表达最基本的表层含义,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其言内意义与语用意义却区别于单一语码,承载着相当丰富的内容:从言内意义来看,语码转换在视觉上是一种突显与前景化的表现,在听觉上具有一种非常规的冲击;从语用意义来看,语码转换是会话者有意为之,要么是为了适应情景因素,要么是用来达到 “显示身份、表现语言优越感、重组谈话的参与者、表明中立的立场、改善人际关系和谈话气氛等目的”[3],需要交际对象花费更多的努力来对其用意进行推理。
在文学文本中,作者选择语码转换这种表达形式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从言内意义来讲,文学文本中使用语码转换除了产生异码排列的视觉与听觉效果之外,还是文学作品 “陌生化”手段的表现方法之一。“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按照俄语构词法生造的一个词,指 “审美主体对受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感知起反作用,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其审美快感”。[4]在文学作品中 “陌生化”就体现为 “在创作中不落俗套,将习以为常的,陈旧的语言和文本经验通过变形处理,使之成为独特的,陌生的文本经验和符号体验”。[5]语码转换这种语言形式,由于其具有多语并存的新鲜感,便成为许多作家 “陌生化”的手段之一。如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作品的 《尤利西斯》便通过使用大量的语码转换来实现 “陌生化”的离奇、怪异的效果。该书共使用了三十多种外语,在英语的行文中,不仅出现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而且出现了希腊、拉丁、希伯莱、梵文等古文字。《尤利西斯》中的语码转换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它造就了一个客观呈现人物意识以及言语对话的真实语境,使得小说对人物心里意识的表现更加完整真切,小说的美学意味也更加曲折。”[6]
文学文本中使用语码转换大多是为了描绘场景与塑造人物性格。如钱钟书先生的 《围城》中,在刻画在洋行做事多年的张先生时有这么一段:“方鸿渐道:‘张先生眼光一定很好,不会买假东西。’张先生大笑道: ‘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工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hunch;看见一件东西,忽然what d’you call灵机一动,买来准O.K.。他们古董掮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fool我。O yeah,我姓张的不是sucker,休想骗我!’”[7]此例中,作者通过语码转换把张先生的崇洋媚外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并给予了极大地讽刺:“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可妆点,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的好,此外全无用处。”[8]
三、语码转换的翻译分析
纵观多数译者对文学文本中语码转换的翻译,不外乎使用同一语码以及保留不同语码两种处理方式,下面笔者将以具体译例进行分析:
(一)使用同一语码
1.取消语码转换
例1.原文:LYNCH:Damn your yellow stick.Where are we going?
STEPHEN:Lecherous lynx,to la belle dame sansmerci,Georgina Johnson,ad deam qui laetificat juventutem meam.[9]
译文:林奇:让你的黄手杖见鬼去吧。咱们到哪儿去呀?
斯蒂芬:好色的山猫,咱们找无情的美女乔治娜·约翰逊去,走向年少时曾赐予我欢乐的女神。[10]
这一段会话取自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会话中的语码转换发生在主人公斯蒂芬和林奇两人的问答之间。其中“la belle dame sansmerci”是法语,“ad deam qui laetificat juventutem meam”是拉丁语,剩下的行文是英语。斯蒂芬在会话中转用法语“la belle dame sans merci”修饰乔治娜,是因为乔治娜是个牧师的女儿,曾与斯蒂芬发生过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回避自己的隐私,免去尴尬。“ad deam qui laetificat juventutem meam”原本为天主教弥撒中助祭用语,但有一字之差,“神”改为了 “女神”。作者此处通过语码转换采用拉丁语进行了戏谑性模仿,真实呈现了主人公作为青年诗人特有的心态及才华。译文取自萧乾与文洁若的译本,译者为了使译文流畅易懂,没有保留语码转换的形式,全部译为同一语码,只在每一章的后面说明本章的语言特色。可以看出,译文虽传达出了指称意义,但 “形式是意义的体现”[11]。形式消失,意义也就变得不完整,原文由语码转换所实现的回避功能以及在人物塑造过程中起到的辅助作用也随之消失了。
2.将源语的外语嵌入部分用斜体字并加以注释
例2.原文:今天是作文的日子,孙小姐进课堂就瞧见黑板上写着:“Beat down Miss S.Miss S.is Japanese enemy!”[12]
译文:It was composition day.When Miss Sun entered the classroom,she saw written on the board[in English]:“Beat down Miss S.Miss S.is Japanese enemy!”
这是钱钟书先生作品 《围城》中孙柔嘉到三闾大学教授英文的一段。由于孙柔嘉只是个助教,没有什么资历,学生不尊重她,不仅课堂秩序不好,而且还在黑板上写下以上的英文针对她。此处作者进行语码转换是描绘场景的需要:学生们的胡闹跃然纸上,进而影射了当时学术界只看重文凭和资历的风气。译文取自Jeanne Kelly和Nathan k.Mao的英译本,两位译者将原文的外语嵌入部分处理为斜体,并以括号的形式注释了黑板上所写的为英文。采用斜体加注释的方法,能够表达指称意义,也能让读者了解原文中发生了语码转换,但是原文方块字与英文字母语码转换带来的视觉冲击消失了,读者并不能体会到原文语码转换所包含的精妙之处。
(二)保留不同语码
1.源语的外语嵌入部分不变
例3.原文:张乔治:(远远望见左门里面的刘小姐,老远就伸出手,一边走着,高声嚷着Bonjour,bonjour,mademoiselle!摇着手)——哦,我的刘小姐….
译文:GEORGY(catching sight of Miss Liu at a distance through the open door,he goes across,his hand already extended,exclaiming loudly):Bonjour,bonjour,mademoiselle!(With a wave of greeting)——-Ah,my dear Miss Liu.[13]
此例取自曹禺先生的话剧 《日出》,译文取自Barnes的英译本。由于目标语与源语的外语嵌入部分不同,源语中的汉法转换在译文中就很自然地成为英法转换的形式。但是源语中汉法转换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当时的英法留学生回国后都把自己的留学经历看作重要的资本,在人前人后都不忘利用外语炫耀一番。这里需要考虑的是:译文中英法语码转换的关系是否与原文中汉法转换的关系相等?法语在目标语读者眼中又承载者什么样的社会意义?英法转换能否表现汉法转换张乔治无比炫耀的心态而实现人物塑造功能?再如例1的句子,与萧乾和文洁若不同,译者金堤对其中的语码转换采取了原样保留的形式,并在附录中采取注释,译为:
林奇:滚你的黄手杖吧。咱们去哪儿?
斯蒂芬:淫荡的林中奇兽,去找la belle dame sansmerci,乔治娜·约翰逊,,ad deam qui laetificat juventutem meam。[14]
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再现原作,但可以看到这样一来,读者的阅读困难就大大增加了。
2.源语的外语嵌入部分转化为另一门语言
例4.原文:张乔治:(一步三摇地走近陈白露,灵感忽然附了体)哦!我的小露露。(上下打量着白露,指手画脚,仿佛吟诗一样)So beautiful!So charming!And so melancholic!
译文:GEORGY(going unsteadily and erratically across to Bailu,the spirit suddenly moving him):Ah!My little Lulu!(Looking her up and down and gesticulating,as if declaiming a poem)Si belle!Si charmante!Et sit melancolique![15]
此例也取自《日出》及Barnes的英译本。由于目标语与源语的外语嵌入部分相同,译者将原文的汉英转换译为英法转换形式。这样做牵强地保留了语码转换的形式,但是由于英法转换和汉英转换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并不相同,不仅会引起语用意义的偏差,而且会使读者对角色身份产生质疑:张乔治不是留美博士吗?怎么总讲一口法语?
四、结语
由以上译例分析可以看出:在语码转换的翻译过程中,使用同一语码能够使译文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减少了目标语读者的陌生感与阅读困难;但也不难看到,恰恰是这种看似处处为读者着想的做法,造成了言内意义的丢失和语用意义的大量亏损:作者的写作风格,作品中的人物特征,以及作品的诗学价值都因此大大打了折扣。而保留不同语码能够在译文中较大程度地重现原著,使译文读者感受到原著风貌;然而,也应该看到语码转换的语用意义并没有因为不同语码的保留得到对等,尤其是当语码转换中的外语嵌入部分与目标语相同时,如若引入第三种语码进行转换,作者所要传递的言外之意不仅有了亏损甚至出现了偏差。究其原因,便是语言差异和文化缺省所导致的可译性限度问题。语言文化差异越大,可译度就越低。语码转换由于形式较为发杂,承载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比较明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正视这一问题,既不应牵强为之,也不应放弃努力。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最大努力在最大程度上去再现三种符号学意义。具体来讲,当语码转换的外语嵌入部分与目标语不同时,应当保留不同语码,因为 “文学翻译要能对得起文学的美名,就必须既要传达原文的思想信息,又能体现原文的诗学价值。”[16];但是,当语码转换的外语嵌入部分与目标语相同时,就不必牵强地由译者选用第三种语码进行转换,而应当采用同一语码,因为牵强的转换虽然保留了形式,却造成语用意义很大的偏差,使译文与原文越来越远,从而陷入了误译的泥沼。
总之,在文学文本中面对语码转换这种语言形式,译者应正视可译性限度问题,在深入分析其三种符号学意义的基础上,反复推敲,灵活处理,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奈达提出的译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的对等标准。
[1]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45.
[2]沈毓菁.浅谈汉英翻译中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 [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1):12-15.
[3]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46.
[4]陈琳,张春柏.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 [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92-99.
[5]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4.
[6]王治江.《尤利西斯》中语码转换的文学意义论略[J].南开大学学报,2003(5):120-124.
[7]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0.
[8]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16.
[9]Joyce,James.Ulysses[M].Middlesex:PenguinBooksLtd.,1960:248.
[10]乔伊斯,詹姆斯,萧乾,文洁若译.尤利西斯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768.
[11]黄国文.英语语言问题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106.
[12]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03.
[13]Cao Yu.Barnes.Sunrise(Ri Chu)[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90-191.
[14]乔伊斯,詹姆斯,金堤译.尤利西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45.
[15]Cao Yu.Barnes.Sunrise(Ri Chu)[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348-349.
[16]王东风.变异还是差异——文学翻译中文体转换失误分析 [J].外国语,2004(1):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