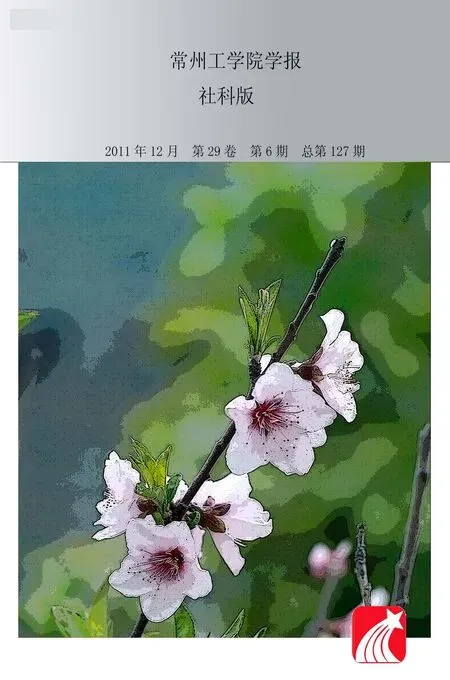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
——论清末民初时期的吕思勉
李波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上海 20024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巨变的时代。1901年识见敏锐的梁启超发表了《过渡时代论》一文,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过渡时代中国的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1]27-29。在这一过程中,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约二三十年的时间,是中国社会新旧转型、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知识阶层正是在此期间实现了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史学家吕思勉的早年即处于这过渡的中流之中。本文即以吕思勉为考察中心,探讨这一代学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轨迹,彰显其新旧兼融的学术品格。
一、家学渊源与旧学根基
吕思勉188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十字街吕氏故居。常州地区自古以来读书学习的风气就甚为浓厚,仅有清一代,在常州武进、阳湖等地,即涌现了洪亮吉、赵翼、庄存与、刘逢禄、屠寄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吕家就是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吕思勉自谓“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2]434,可见其家学的渊源。出生在世代读书的家庭,生长在具有浓厚学风氛围中的吕思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传统士人教育,后来在谈到自己早年时期学习的经过时,他总结道:“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2]407在父母、师友的教育熏陶下,吕思勉少时起就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各种古代典籍,好友徐哲东就讲他“于群经小学,诸史百家,靡不究贯,亦取异域之说相检度,此其为学之区域也”[3]260。单单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吕思勉就从头到尾通读过三四遍,此外他还攻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段注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等典籍,掌握了目录学、小学、经学的知识,这些在以后成为他治史的工具。他特别感念至深的还有《日知录》与《廿二史札记》二书,“前者贯穿全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都是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4]143毫无疑问,吕思勉通过前辈大师作品中的“金针线迹”已经掌握了治学的方法,并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予以了充分的利用。
吕思勉在《自述》中讲:“予此时(甲午战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至于技术,尤必借他人之辅助;仅能指挥策划而已。此在今日崇尚技术之时言之,实为不切实用,但旧时以此种人为通才,视为可贵耳。予如欲治新学术,以此时之途辙言之,本应走入政治经济一路。但予兼读新旧之书,渐觉居今日而言政治,必须尊崇从科学而产生之新技术,读旧书用处甚少。初从水利工程悟入,后推诸军事,尤见为然;又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性好考据,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2]435自这段述及如何走上了治史道路的文字中,可知吕思勉在专意于从史之前,向往“经济之学”,略知政务各门,能够指挥策划,并且喜好考据,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观念,只有这种“通才”去研究史学,方能够达到上下通贯、牢笼万端的较高境界,已经具备了这些素养的吕思勉从事史学研究,既是他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应为水到渠成的必然;至于欲研治新学术,兼读新旧之书,尊崇新的科学技术等行为与观念则可以看到时代所及于他的影响。
二、时代变迁与身份转换
吕思勉在《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一文中讲:“中国人感觉到遭逢旷古未有的变局,实自鸦片战争以来。此战爆发于民国纪元前七十二年,距今恰足一百年。此一百年之中,中国的变化比之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来的大,来的快。”[5]349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学说挟炮舰之威进入了中国,中国数千年一直傲视于世的文化优势遭到严重冲击,中国知识阶层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动摇,新的学术思潮渐次萌发。然而,从总体上讲,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保持着本体地位,就一般的读书人而言,所熟知的学问仍为旧时士夫之学,对于西学则所知极为有限,吕思勉曾回忆:“还记得甲午战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那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还有人说:日本的国土比朝鲜小。因为那时候,有一种箑扇上画着中国地图,也连带画着朝鲜日本。画到日本时,大约因为扇面有限,就把它缩小了。”而且说这些话的人,就是当时所谓“读书明理的士子”,那时候大多数的读书人,“真是除科举之学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3]6。由吕思勉的经历见闻可以想见,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真正明了世界大势的不过是极少数人,对于大多数读书人而言,其观念和行为仍然未脱离传统的旧轨辙。
1895年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约求和。战争失败所导致的领土割让之广与赔款数额之巨,均为前所未有。梁启超讲: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鼾睡之声,乃见惊起。[6]133
吕思勉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中也讲:
余年十一,岁在甲午,而中日之战起,国蹙师熸,创深痛巨;海内士夫,始群起而谋改革。[5]282
要想救亡图存,就要谋求彻底变革。以中日甲午之战为转捩点,此后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变迁最大的时代,从政治制度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七章《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把1898年和1919年视为中国思想史上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
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在天安门前的文人士子,企图变革政治制度的一次尝试。……1898年改革的锐利锋芒,直指历代传统的政治制度;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视为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冲击。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来自中国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从对传统价值观核心之点的怀疑,转向对传统价值观彻底的否定。[7]315
在清末民初的二三十年间,改良运动、立宪运动、民主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都是由知识阶层来引领和推动的,谋求变革的运动从政治制度深入到了思想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身份也从文人士子转换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时代的变迁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化,都是吕思勉所亲身经历的,不能不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设若不是这样一个时代,出身于世代读书仕宦之家的吕思勉,人生道路将与其祖先一样,科考做官或者教授乡里,这也正是父母对其人生的规划和期望。“十五岁时,尝考入阳湖县学,名义上为旧式之县学生。然旧式学校,从无入学考试之事,实系科举之初阶而已。”[2]435其父吕德骥由此更加注重对他的教育培养,要求吕思勉增加读书数量,而不再“兢兢于文字之末”。后来由于时局骤变,“予父喟然曰:世变亟矣,予有子,不欲其作官也。因谓予曰:隐居不仕,教授乡里最佳”[2]447。科考做官与隐居不仕是作为四民之首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两种道路选择,进则出仕做官,治理天下,退则隐居乡里,教化一方,即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然而,此次世变却与以往的历史变故有着根本的不同,吕思勉虽然没有走入仕途,但也并未隐居乡里,而是走上了一条顺应时代风潮的新途,转型为一位新式的知识分子。这一转型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角色的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可谓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使得读书仕宦、政教相连的传统中断了,传统的士大夫道路不再成为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读书人可以不必终生只盯着科举考试所限定的几本书,自由地追求各种知识;读书人也可以不必挤向那近乎唯一的成功的窄门,路途可以无限宽广,人们可以成为各种专业人士”[8]112。同时,新式报刊、新式学校与新的学术社团纷纷涌现,成为读书人存在的社会空间,“从长远看来,这三种制度媒介有两个影响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的启端,另一个就是舆论或公共舆论的展开”[9]109。恰在科举制废除的这一年,吕思勉在一所新式学校——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次年,父亲病逝,“家境益坏,乃真不得不藉劳力以自活”[2]436,吕思勉的教薪已成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吕思勉由此开始了一种迥异于先辈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吕思勉虽已在新式学堂任教,但在1910年之前,大体上限于常州境内,尚不违“教授乡里”的父训。然而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吕思勉最终还是离开了家乡,并于民国元年抵达上海,先后担任出版社编辑与大学教师等职务,自此他的人生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传统的读书人从家乡启程远走,一般还会回来,而新式的知识分子告别家乡后,多半将一直漂浮在都市之中,不再回来。吕思勉无疑已成为了后者①。
其次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从传统士人到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中,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角色的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但却并不完全同步,思想观念的转化明显不及身份角色的转变来得彻底。清末民初的文化学术界,西方学说已经大规模涌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巨大的历史文化惯性力量作用下依然深厚,转型中的知识阶层,常常新知旧学兼具。如前文所述,吕思勉早年接受的是完整系统的传统士人教育,没有入过新式学堂,“少时尚无公私立学校,十五后稍有之,然时视外国文及技术,均不甚重;故生平未入学校。于外文,仅能和文汉读;于新科学,则仅数学、形学,尝问业于徐点撰、庄伯行两先生,略有所知而已”[2]435。而在另一方面,则为:“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2]409从这种轻视科学技术、注重“经济之学”的问学经历中,可知旧传统已在吕思勉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的传统士人重视精神修养,讲求道德文章,心系天下忧乐,倡导经济之学,是其优长处;轻怠生产技艺,藐视下层民众,忽略社会现实,容易虚骄空论,则为其缺弊。这些在数千年时间里形成的品格特征,无疑仍然极大地影响着转型时代知识阶层的精神风貌。吕思勉晚年评论自己道:“予受旧教育较深,立身行己,常以古之贤士大夫为楷模。”[2]445虽然吕思勉常常不自觉地以古代贤士大夫为修身立行的榜样,但在理智上吕思勉向来对传统士大夫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个阶层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潮流②。如他品评康有为与孙中山等人时讲:“康、梁、章的改革手段都以中国的旧见解为基本的,虽然康长素变法之见,多得知于国外的观感。孙中山的民权、民生两主义,则其见解,都是植基于外国学问上的,虽然到后来亦将其和中国旧说相贯通。然则士大夫阶级的改革路线失败,而起于草野者卒成;从中国的旧观点出发的手段失败,而顺应世界大势者卒成,我们可以说:‘这可以觇世变了。’”[5]399
世变对吕思勉的影响始自中日甲午战争,战前的吕思勉“竟不能知德国所在”,从这一年,“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2]435,并广泛阅读新书,为“略读世界史之始”。时代的冲击,使吕思勉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使他的学术,在根本上迥异于以前的前辈大师们,他所瞩目的史事仍是中国自古迄今的史事,但作史的精神,乃是新的时代所赋予的。吕思勉曾经总结说,少时所得于父母师友的,只是在治学的方法方面;至于学问的宗旨,则反而受从未谋面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影响较深,世界大同的观念就导源于读康有为的著作,在具体论事的方面,则服膺梁启超的观点。自小在传统文化典籍陶铸下,已成为俨然之醇儒的吕思勉,从不乏获取新知的求知愿望,对待外来的文化知识,他认为:“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而能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交通梗塞之世,彼此不能相资,此乃无可如何之事。既已互向灌输,自可借资于人以为用。”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开明态度[10]3。生逢此时的吕思勉,一只脚仍然稳固地立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另一只脚开始迈入汹涌而至的西学的门槛,真正成为了学贯新旧的一代史家。这即是时代冲击所带来的史家观念的变化,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才使得他们的学术因赋予了时代的价值而产生出强大的生命活力。
三、为人品性与为学特色
评论吕思勉其人其学,港台著名史家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一文最具卓识,他这样写吕思勉:
我想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华,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11]86
在严耕望笔下,概括出了吕思勉平实质朴、忠厚谦和、淡泊名利的为人品性;冷静客观、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其实,严耕望从未与吕思勉谋面,不过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严耕望为吕思勉作写照、下断语,当然凭藉的是他深厚的学力和高超的见识,另外一层,也许更重要的是二人“才性”的诸多相契,故而惺惺相惜,进而能做出这样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的评论。为未曾谋面的前辈学者写评论文章,吕思勉也做过,他的《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评价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三位时贤,见解异常精妙,文中并且谈到寻访结交名人,对于学问并无增益,“我以为亲炙某种人物,对于道德、事功,很有裨益的,因为这不是纸上的事,能与之居,或见其人,其获益自较读其书为大。若学问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谈起,精深之理,繁复之事,岂能得知于立谈之间?若文章之妙,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更与见面不见面无关了。”[5]399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吕思勉品性的一面。
吕、严二位先生虽然“才性”相近,却并非完全相同。严耕望在此颇有几分以己度人,夫子之道,所以有些话语失之偏颇,也不足为奇。
其一,认为吕思勉“无才子气”。对照严耕望关于陈寅恪的评论“我想陈先生的大志不遂,……但另一方面仍不脱才子文士的风格,不是个科学工作者,所以虽有大志而似无具体计划,也不会能耐烦的去做一个有组织的大工作。至于俞(大维)先生所谓时代丧乱、生活不安,尚在其次”[12]116,可知严耕望这句话的意思,当是指吕思勉治学,有理想、有计划,又能够克服困难,不辞辛苦、不嫌刻板地去实践,身上没有旧式文人的习气,可以被称为“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严耕望此评适之于治学中的吕思勉非常贴切,不仅如此,吕思勉在具体做学术文章时,也从不矜才使气,而是做足考据的功夫,下笔也非常谨慎。但这不过是吕思勉性格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的吕思勉,在实际的生活中却并非这样简单刻板,而是很有传统才子文士的风格和雅趣。吕思勉自小就与亲戚师友作诗钟、对联句,诗词酬唱,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颇深,虽然谦称“下笔仍是宋人境界”,实际上足以比肩魏晋。宋明以来的士大夫诗作,常常以教谕的口吻讲义论理,道学气十足,反观吕思勉的诗作,却充满了文学的才情与灵性,自然、清雅、恬淡,一如其人。昔时章学诚曾言:“史所载事者,事必藉于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3]182作为史学家的吕思勉就是既深于学又长于文的,能写一手好文章,光华大学的同事金松岑教授称赞他“少年时代的文章,才华横溢,而又意境孤峭,笔锋犀利,近于王安石的一派”[11]176。吕思勉自谓:“予于文学天分颇佳。……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2]436他写文章不仅意境高远、文字雅驯,而且还有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的捷才,“予少时行文最捷,应乡举时,尝一日作文十四篇,为同辈所称道。”[14]688此外,吕思勉还通医道,并著有《医学知津》一书;善弈棋,曾为棋王谢侠逊《象棋秘诀》作序;在书法方面也很有功力。作为一位留下上千余万字著述的史学家,竟还能有这等多的才情,其人难免要为人所误解。这等才情,与史学研究之间,看似不相关涉,其实并不尽然,如陈寅恪之于诗歌戏词,钱穆之于山水景物,陈垣之于医学科普,这些素养、雅趣自然会影响到他们观察事物的眼光思路、心胸见识,成为其学术研究流域中的一处源头、一股活水。对此,顾颉刚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一株树木的荣茂,须有蔓延广远的根荄。以前我对于山水、书画、文辞、音乐、戏剧、屋宇的装饰等等的嗜好,就是许多条根荄,滋养着我的学问生活的本干的。”[15]98
其二,认为吕思勉“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吕思勉一生没有参与任何政务活动,也没有加入哪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而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并不能表明他不关注社会现实,没有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他为更好地尽责于社会,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的理智清明的抉择。辛亥革命前后,吕思勉“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2]437。然而,吕思勉却认为做官不能发挥自己所长,并对当时政坛的风气很不以为然,至于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遂于政治卒无所与”。对于自己的选择,他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他在《自述》中讲到:“在民国元年时,章行严君,尝在《独立周报》中自道曰:人之有才,如货物焉。货物当致之需用之处,人才亦宜自度所宜。有宜实行者,有宜以言论唱道者。予自审不能实行,故遂不躬与革命之役也。此言予颇善之,故尝自期,与其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2]448在吕思勉看来,治学与治事只是分工不同,自己可以凭性之所近,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重事功而轻学术,贵实行而贱谋划,只不过是社会上浅薄的见识。他认为,学术事业是国家富强社会兴盛的根源,学术的最终目的就是致用,他讲道:
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有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擿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昔人于此,观念虽未精莹,亦未尝毫无感觉。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5]356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的时代,时代的变迁,需要学术文化的变动,然而,时局的紧张,也容易导致人们舍弃纯粹治学的精神,转而“粗心浮气,冥行擿涂”,“职是故,中国近代,需要纯科学甚亟,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其去纯科学反愈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似无关实际,其实此为整个民族趋向转变的一个大关键。非此中消息先有转变,时局是不会有转机的”[5]356。反观20世纪的国史,中国遭逢的诸多苦难和挫败,国人的“粗心浮气,冥行擿涂”的确难脱干系,吕思勉在此时选择潜心于学术研究,正是为了移风易俗、推动社会前进而尽自己的责任,数十年不畏辛苦、锲而不舍的坚持,足见其使命感的强烈与迫切。
吕思勉回忆“小时候所遇之读书人,其识见容或迂陋可笑,然其志则颇大,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若以身家之计为言,则人皆笑之矣”[3]191。吕思勉后来的社会身份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转化,旧时读书人的识见,在他看来,已是“迂陋可笑”,但那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却依然为他所认同,并继承下来。1925年吕思勉《万顷堂》一诗:
管社山前湖水平,斜阳天际照空明。若非内热忧黎庶,便合渔樵了此生。[14]678
其救世济时,“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的人生志愿与治学旨趣尽显无遗。他对后来的读书人“几皆以得一职求衣食为当然”的观念持保留态度,认为知识阶层不应逃避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多欲而避事,乃藉口于学者不当于世务,以自逃责,而于权利之争,争先恐后,未见其无所知不暇及也。然则所谓遗弃世务者,得无其自蔽之烟雾弹乎?是则学者之耻也。”特别在国事艰难之际,“有大志者,理宜风起云涌”,以己饥己溺之怀,去识知世间的饥溺之事[3]191-193,由此可见吕思勉的胸怀和抱负的远大,亦可见其学术的根本所在。吕思勉认为:
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2]412
以上这段论述表明,吕思勉从事史学研究,是以社会现实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的,而且对于研究学问与关注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则又明显地具有新时代学科研究的眼光和思路。
严耕望对吕思勉的评论,细究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两代学人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出的治学观念与路径上的差异。20世纪以来学术转型,新的学科体制建立,专家之业逐渐取代了通人之学,写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和《唐代交通图考》这等皇皇专著的严耕望,正是专家之业、“为人之学”的杰出代表。而成长于清末民初转型时代的吕思勉,其治学风格则有着既顺应新学潮流又承袭旧学传统的双重色彩。
注释:
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吕思勉避居常州故里,这是非常时期被迫采取的行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吕思勉很快又重返上海。
②对传统士大夫的批判,在吕思勉的多种著述中都有体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18年《学风变迁之原因》一文,指摘中国士大夫具有好名好利的坏习气,又有虚骄不务实的缺点;再如1920年《士之阶级》这篇万余字的长文,从多个方面对“士”阶层的弊病进行了揭露批判。参见李永圻、张耕华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卷(未刊稿)。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书店,1992.
[4]吕思勉.论学集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5]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8]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M]//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9]张灏.张灏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0]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11]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2]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1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M].仓修良,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4]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