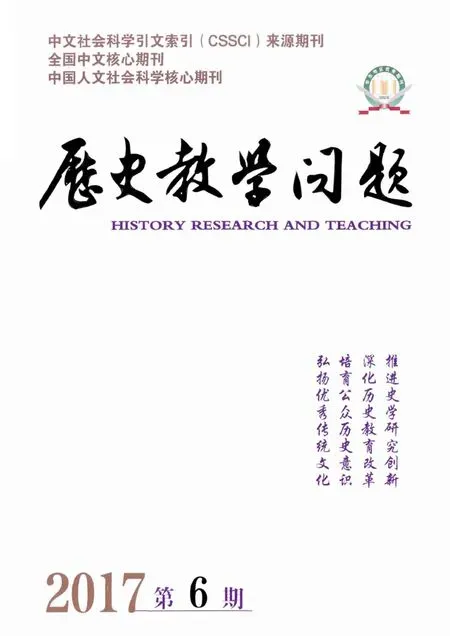吕思勉读书的经历与方法
李 波
吕思勉(1884—1957)作为中国学术新旧转型时期的一代学者,少时读书“得益于父母师友”,博览传统典籍,后又积极接受近代科学知识,阅读各类新书报章。他自蒙童至垂老,未尝一日废书,“于群经小学,诸史百家,靡不究贯,亦取异域之说相检度”,①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03页。他的学术成就,建立在其丰厚的旧学新知基础之上。回顾总结吕思勉当年读书的经历与方法,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吕氏学术的了解,而且对当下的读书人亦不无启发意义。
一
吕思勉出生在数百年“读书仕宦”的家庭,未曾进入新式学堂,其学问根柢植基于早年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家乡常州的学风氛围,父母师友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他读书治学的道路及其对学问与人生的态度。在经史子集各种古代书籍中,吕思勉对于史书“少时颇亲”,读来最感兴味。从蒙童时阅读《纲鉴正史约编》《纲鉴易知录》起,到23岁(1906年)决意于走治史道路之前,仅自首迄尾阅读过的史籍,就包括编年体方面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与《明纪》等;典志体方面的《通典》《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等;纪传体方面的所有二十四部正史。②相传吕思勉是近代学术界读二十四史遍数最多的学者,究竟读过多少遍则众说不一。据抗战初期他本人的说法,那时已经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各书均两遍。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80页。这样大规模的史籍阅读,为他从事史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吕思勉早年攻读过的古籍,还包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段注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古文辞类纂》《经世文编》《日知录》等等。由此,他掌握了目录学、文字学、经学、地志学、文学、经世学、考据学的知识,以后不仅拥有治史的良好工具,而且在这些方面都有建树。
吕思勉少时读书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在今天看来颇具特色。试举数条如下:
其一,初读书时,先由目录书入手,对于全体学术史“作一鸟瞰”,大略知晓传统学问的概况、分类、源流派别和重要书籍;须遵循《曾文正公家书》中的告诫,“读书如略地,非如攻城”,务求其速,不厌其粗,即便不能够记忆和理解,也无妨害。阅读时可以略读,但是不可以越过,因为越过是不读而不是略读,而且所读之书须用全本,忌用节本。①在1943年与友人的一则通信中,吕思勉曾经谈道,“尝见一北大派中人,其人在北大派中读书颇为广泛,而议论亦多窒塞不通,颇以为怪。继闻其自述读书之速率,为人情所不能有,而其人又非虚狂者流,更不得其解”。后来他才知道,此人读书“并非从首至尾,皆读一遍”,只有“为其所欲取者则细读之,否则阁过不读”。吕思勉很不认同这种不通读全书,不了解书中本意,仅仅从中查阅“有用”材料的做法,他认为“此仍是检书而非读书,故所涉虽多,仍与只知一门者无异”。参见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689、690页。
其二,在读书的起始阶段,可选读自己喜好的书,“吾所最好读之书,即吾所最宜读之书”。须先经过一段杂读、乱读时期,然后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和学问程度加深,进入“趋向略定之时代,则其读书,宜略带硬性”,带着一定的目标和任务读书。②吕思勉:《国文教授祛蔽篇》,《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2-343页。
其三,读经书与子书。这两种书的学术价值,虽然在近代已经相等,但仍宜先读儒家经书、后读诸子书,因为经书的注疏校证较多,相较而言,要比读子书容易。读经从汉学入手,要注意区分今文经书与古文经书,划为两组之后便于查寻线索、条理系统。③吕思勉出身于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发源地常州,读经的路径方法受今文派影响较深,但作为近代史学家,经学仅仅是他治史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他以史家立场看待今、古文各自的价值,能够做到(尤其在后期)在古史研究中兼采并用两种材料。因为经书多陈述事实,子书多阐明道理,所以读子书重在探求义理,并要注意子书不同于后世的文集,它是一家学说的汇编,而非一人的学术著作。
其四,读史书的次序。首先,读编年体史书,可兼读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作为辅助,以此了解各时代治乱兴亡的大势;然后,读典制体史书,了解古代典章制度的门类,并借以窥知当时社会状况的大略;再后,可以随意择读其他类的如历史地理、集部相关之书等;最后,读纪传体正史,因为正史虽然材料丰富且可信度相对较高,但过于零碎、割裂,“非已有主见的人,读之实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读”。④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4页。读正史时,要就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留意采择相关材料,其余内容则随意读过即可。
根据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吕思勉相信“学问之道,贵自得之”,做学问的门径是在读书过程中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必须自我发愤、多读熟读。吕思勉在指导青年学生读书时,曾经告诫他们:“读书至百遍而自熟,犹之练体操,为某式之运动,至若干次而筋力自强,此筋肉之强,断非由体操教练讲明其运动之理而即得”;在自己读书的过程中,可能会耗费很多时间而无所得,然而坚持下去,一旦获得了悟和自得,必能“同时数十百条有真确贯通之了解”;⑤吕思勉:《答程鹭于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669页。至于读书过程中的悟入和有所得之处,往往就在那些平时所不经意的地方,“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⑥吕思勉:《经子解题》,《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吕思勉推崇中国传统学者用功读书,治学注重积累而不急功近利的做法。他认为:“人之为学,所难者在见人之所不见。同一书也,甲读之而见有某种材料焉,乙读之,熟视若无睹也。初读之,茫然无所得。复观之,则得新义甚多。此一关其人之天资,一视其人之学力。为学之功,全在炼成此等眼光,乃可以自有所得。而此等眼光,由日积月累而成,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其所得者,亦有铢积寸累。未有一读书,即能贯串古今者也。故昔之用功者,只作札记,不作论文,有终身作札记,而未能成有条理系统之论文者。非不知有条理系统之足贵,其功诚不易就也。”⑦吕思勉:《大学杂谈》,《吕思勉诗文丛稿》,第350页。吕思勉依循前贤的做法,自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读书作札记的习惯,读书每有所得辄即记下,并不断增删修正使之完善,经年累月,撰写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他的很多学术论著就是在这些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
二
在谈及自己早年为何选择走入治史道路时,吕思勉说:“予兼读新旧之书,渐觉居今日而言政治,必须尊崇从科学而产生之新技术,读旧书用处甚少。初从水利工程悟入,后推诸军事,尤见为然;又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性好考据,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⑧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42页。自这段陈述中,可知吕思勉在专意治史之前,兼读新旧之书,崇尚科学技术,欲研治新学术,这些行为与观念可以看到时代变化所给予他的影响。清季民国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此时的学术界,一方面西方学说大规模涌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根基依然尚存,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往往兼具新知旧学。对待外来的文化知识,吕思勉认为“学术本天下公器”,现在中西各国“既已互相灌输,自可借资于人以为用”,①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59页。表现出拿来主义的开明态度和主动获取新知识的积极意愿。吕思勉后来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认为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等近代学科的知识对于研治史学具有重要作用,提出“居于今日而言历史,其严格的意义,自当用现代的眼光,供给人以现代的知识”。②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3页,第581-582页,第579页。
吕思勉自早年起就开始接收各种新思想、新知识。在科学方面,他曾专门学习数学、形学。在外文方面,他和文汉读,读了不少日文书,翻译过《勿吉考》等著作,民国初年在商业学校任职时,还曾经利用相关日文书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在现存《先考日记》残稿中,有其父就职上海时为他购置各类新书的多条记录,其中包括《英文典问答》和《泼拉买》等习读英文的书籍。吕思勉订阅新出报刊杂志,始自13岁(1896年),此后60余年从未间断。吕思勉读各种新书和报章,沿用了阅读古籍的方法,必加圈识,间作眉批和摘录,并将所需材料分类保存,直到晚年体弱多病,仍然坚持剪贴各种报章杂志。这些资料连同他的日记、札记等,数量非常庞大,可惜由于抗战时期常州故居炸毁,任职学校全焚,其中的大部分都没有留下来。尽管如此,劫余残存的部分,加上后来又不断新添的材料,数量依然很多。由于平日关注各种新出书报,吕思勉对近代出版界情形非常熟稔,曾撰写《三十年来之出版界(一八九四—一九二三)》《追论五十年来之报章杂志》等专文,藉此探讨近代中国的“风气之变迁,学术之进退”。③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一八九四—一九二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82页。
吕思勉并读新书旧典,兼具新知旧学,这使他的研究成果既涵有旧传统的丰厚底蕴,又具有新时代的生机活力。学术文化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对撞与冲突、交流与融合,体现在他读书治学的过程之中。诸如:
其一,关于读书与现实。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缺弊,吕思勉经常引用汉宣帝的一段话予以揭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安足委任?”自古以来迂儒所以误国,就因为他们的“学问止于读书”,拘囿于书本知识,不察实际,缺少变通,执陈方医新病,结果往往失败。鉴于此,吕思勉一再强调,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所以读书第一要留心书上所说的话,就是社会的何种事实,这是第一要义”;④吕思勉:《读书的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42页。而且“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⑤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3页,第581-582页,第579页。他主张阅读书本知识与观察社会现实要互为印证、交相为用,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学问。
其二,关于博通与专深。吕思勉少时所接受的是传统通才式的教育培养,“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⑥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3页,第581-582页,第579页。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科研体制的建立,分科之学和专家之业取代了经济之学和通人之才,学术界普遍注重仄专精深的研究。吕思勉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由混而趋于析”是学术进化的趋势,但同时他又强调,分科治学便利于进行深入研究,固然很重要,“关于全般之知识,亦极关重要”,因为“所谓精者,从多之中简练选汰而出之之谓也”;⑦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208页。“读书稽古,亦冀合众事以观其会通”。⑧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6页。所以,他主张“求学的初步,总以博涉为贵”。⑨吕思勉:《孤岛青年何以报国》,《吕思勉论学丛稿》,第362页。先读书后做学问,“由博返约,实为研究学问之要诀”。⑩吕思勉:《整理旧籍之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89-490页。吕思勉借用《尚书·洪范篇》“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两句话,概括所谓“专家”与“通才”二者在读书治学上的不同,他认为“走那条路,由于各人性之所近,然其实是不可偏废的。学问之家,或主精研,或主博涉,不过就其所注重者而言,决不是精研之家,可以蔽聪塞明,于一个窄小的范围以外,一无所知,亦不是博涉之家,一味的贪多务得,而一切不能深入”。参见吕思勉《读书的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42页。
其三,关于学问与道德。读书治学与修身立德,就中国传统读书人而言,是二位一体的,即所谓读圣贤书、行仁义事。这种读书“为己”的旧传统在吕思勉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他评论自己说:“予受旧教育较深,立身行己,常以古之贤士大夫为楷模。”①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1页。吕思勉在上海光华大学这所普通私立学校从教数十年,勤苦治学、不求闻达,尽管学术成就与外界声光并不相称,但他从来都不以此为意。他以古贤为标准要求自己:“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剥极则复,贞下起元。为之基者,则贤人君子之所以自处也。”②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352页,第315页。吕思勉认为“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真正的学者必须绝去名利之念,要以学问为目的,不能以之为手段,“其惟作官谋馆是务者,终必不能有成”。③吕思勉:《今后学术之趋势及学生之责任》,《吕思勉诗文丛稿》,第268页。对近代学术界所表现出的“今之求学、多为谋生”的种种现象,吕思勉极为不满,批评道:“不徒出版机关,滥用种种方法,以招致此曹投稿为不当;即学者如是其求速化,亦非大器晚成之道也。”④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一八九四—一九二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90页,第289页,第284页。对当时社会上惟重学校毕业文凭,尤其是出国留学经历,而不关注实际才学,“藉头衔以欺世”的状况,他也非常不认同,认为“今日是非,淆乱极矣!何谓有德?何谓有才?孰为有学?一以其冒耻自陈,及其私党之所言者为准耳”。⑤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352页,第315页。他比较清季民国学术界前后的变化,很感慨地说:“学问知识,诚觉后胜于前;然道德则似反不逮,信用亦较前为弱,此则著述界中人,所亟宜自警者。”⑥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一八九四—一九二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90页,第289页,第284页。这确为颇值深思的总结。
三
1920年吕思勉曾经撰文就井田制问题与胡适进行商榷。胡适不承认井田制的存在,认为它本为孟子凭空虚造的乌托邦,并由汉代学者逐渐增补而臻于完备。吕思勉不赞成胡适的观点,他认为“推行天下、延绵千载之井田,自然无有,而行之一时一地之井田,则不能谓其无有”。⑦吕思勉:《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652页。吕、胡二人不仅对井田制的研究结论不同,而且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不同。吕思勉运用文献材料考证古史,关注的是井田制的历史真相;而胡适重视的是关于井田论的演变,他认为“井田论的史料沿革弄明白了,一切无谓的争论都可以没有了”。⑧胡适:《井田辩》,《胡适文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第321页。双方分歧产生的重点,即在于对古籍材料价值认识的不同。作为从中国传统读书问学路径中走出的学者,吕思勉不否认古籍存在真伪问题,但并不因此而否定其重要性。然而,倡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胡适,则总体上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抱持“评判的态度”。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卷二,第555页。他认为“学者的任务只是去寻出井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最可怜的事。‘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假设’是最可怜”。⑩胡适:《井田辩》,《胡适文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第321页。在胡适的眼光中,许多传统典册不过是一堆亟待用科学方法整理的“乱七八糟”“无头无脑”“胡说谬解”“武断迷信”的旧国故而己。
对于当时已渐居学界主流地位的胡适发出的“整理国故”倡议,实际上吕思勉是非常认同的,而且作了积极回应。吕思勉认为近代以来,“欧化之趋势渐盛,而国故之论乃同时发生”,他支持研究国故,以之“为今日学术界之要图”;⑪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一八九四—一九二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90页,第289页,第284页。而且他认识到,“由于各时代利害关系之不同,因而其所致疑而求解决之问题亦不同”,所以有必要对旧时的书籍材料进行整理,以适应新时代学术研究的需求。但同时吕思勉又特别强调,要整理旧籍材料,“在研究此具体方法之前,又不能不研求吾人所欲整理之物之性质”。⑫吕思勉:《整理旧籍之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82-483页。在《整理旧籍之方法》这篇文章中,吕思勉提出的整理方法,是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分法,“就此四者分论之”。当年金毓黼在读此文之后,感到“立论平平,无卓识独见可言”,唯独对文章中讲及专门研究比通史研究易于成功的观点,称赞“此真不刊之名论也”。金氏的见解,正反映出近代史学界以新代旧、趋新求变的潮流。参见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259页。他所认可的整理方法,必须建立在了解古代书籍内容和体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远离或曲解古书本义,“六经注我”式的做法。吕思勉所著《群经概要》《经子解题》《史籍与史学》等介绍古籍材料及其读法的相关论著,都是在他阅读各种旧籍之后,根据原书状貌,加以自己的体会撰写而成的。例如,对于获得胡适、顾颉刚等盛赞的清代学者崔述的“疑古之功”,吕思勉即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崔氏所疑,虽若精审,然皆以议后世之书则是,以议先秦之书则非”,因为“先秦之书,本皆如是”,“崔氏之多言,正由其未达古书义例”。①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08页。吕思勉主张“古书自有读法”,“此非一言可尽,亦非仓卒可明。要在读古书多,从事于考索者久,乃能善用之而寡过也”。②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页。说到底,读通古籍的关键,在于必须下足读书的工夫。读书淹贯四部的吕思勉,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对古籍“能善用之而寡过”的近代学者。例如,他认为《鹖冠子》“今所传十九篇,皆词古义茂,绝非汉以后人所能为”;③吕思勉:《经子解题》,《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232页。“《六韬》及《尉缭子》,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④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559页。目前的考古发现,皆已经证明了他当初推断的精确。
1923年胡适与梁启超产生关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二人先后为青年学生拟定了两份不同的书目,梁启超并且指摘胡适所拟书目,将《史记》等史部书籍一概屏绝,却列入了《九命奇冤》等书,一方面“挂漏太多”,一方面“博而寡要”。⑤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三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集》卷三,第123页。对于这场争论,吕思勉支持梁启超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正史、九通等传统典籍具有重要价值,中国的大学问即在此中,应作为必读的基本书目。吕思勉批评胡适“胪列书名多种,然多非初学所可阅读,甚至有虽学者亦未必阅读,仅备检查者。一望而知为自己未曾读过书,硬撑门面之作”。⑥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史学与史籍七种》,第117页,第121页。如前文所述,吕思勉始终相信做学问的门径和方法是要先读书而后得的,他讲道:“所谓门径,是只有第一步可说,第二步以下,就应该一面工作,一面讲方法的。方法决不能望空讲,更不能把全部的方法一概讲尽了,然后从事于工作。譬如近人教人读史时,每使之先读《史通》、《文史通义》。此两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讲亦何从讲起?”⑦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史学与史籍七种》,第117页,第121页。吕思勉之所以认为梁启超所拟书目“好得多”,即因为在他看来,梁氏是真正读过这些书的。吕思勉认为指导初学者读书,“不患其浅,但患其陋”,因为“大抵浅而不陋之言,虽浅亦非略有工夫不能道,若乃实无工夫,却要自顾门面,抄了一大篇书目,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看似殚见洽闻,门径高雅,而实则令人无从下手”。⑧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32页。也即是说,指导他人读书之前,必须自己切实下过读书工夫,在读过之后才有资格谈所谓门径和方法,而不能直接拿似乎“新颖”却实非“高明”的方法指导他人。
当年梁启超与胡适为国学书目争论不休,令他们始料不及和尴尬不已的是,两份书目皆因为“程度”太高而不被青年学生认可,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大幅度消减书目以适应学生的要求。梁启超与胡适固然读书广博,学术水准和眼界远非学生可企及,但他们在拟定书目之初,未必不虑及学生的接受程度,这实际上反映当时青年学生的读书能力,已经比他们所预计的要低很多。章太炎也对民国学界读书风气减弱的现状非常不满,他哀叹《纲鉴易知录》在昔日被学者鄙视为兔园册子,今时能读者已可称为通人。他批评近代学术界趋易避难、急功近利的状况,“有二十四史而不读,专在细致处吹毛求瘢”。⑨章太炎:《历史之重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930页。吕思勉同样观察到民国时代的青年学生,自我阅读的能力已不及清末年间的读书人,“人人侈言整理国故,不能自读一卷古书”。⑩吕思勉:《国文教授祛蔽篇》,《吕思勉诗文丛稿》,第340页,第341页。他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学习所涉及的范围太狭太专,以至于稍稍涉及其他方面的知识,就茫然不解;二是学生习惯了读教科书和讲义,只能读句句看懂的书,不然就搁起不读。⑪吕思勉:《孤岛青年何以报国》,《吕思勉论学丛稿》,第362页。总之,在新的教育科研运行体制下,学生缺失了旧时那种博览通读的读书经历。
为提高学生读书数量和阅读能力,吕思勉当年曾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他认为学校教学“根本上之弊病,则在重讲授,重讨论,……而不重实际之阅读”。⑫吕思勉:《国文教授祛蔽篇》,《吕思勉诗文丛稿》,第340页,第341页。因此,他主张教师应“以‘令其(学生)自己读书’为第一义”。1920年代初在沈阳高师任教时,吕思勉教授学生读书的做法为:“(一)学生所读之书,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之所好可也;”“(二)教室内亦以学生自己读书为主。次之则学生质问,教员答。”他认为“最良之教师”应如《礼记·学记》中所讲:“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①吕思勉:《答程鹭于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668-669页。吕思勉还提出“以考试代学校”的主张,“每一地方,虽由公家设立若干校,然考试必另派员。学子之自修于家者,亦得与学校生徒,一体应试”,以考试成绩作为学问程度的评价依据。这是借鉴科举时代读书“初无一定程式”的做法,“千金而延名师于家,固读书;挟书匍匐,窃听于他家书塾之外,且致为其所逐者,亦读书也。及其合而试之,但问其程度如何,不问其何从学之”。②吕思勉:《考试论》,《吕思勉论学丛稿》,第300-301页。吕思勉冀望以此弥补新式教育带来的弊端和问题。
吕思勉以“蠹鱼”自称,毕生勤苦读书,其倡导的读书方法,都是根据自身读书治学的经历和体验得出的。他“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治学领域广泛,“淹博而多所创获”,③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第357页。为后人留下了达1200余万字的著述。吕思勉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告诉我们,他采用的读书方法尽管费时耗力,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这种“笨”工夫、旧方法却极有成效,也最难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