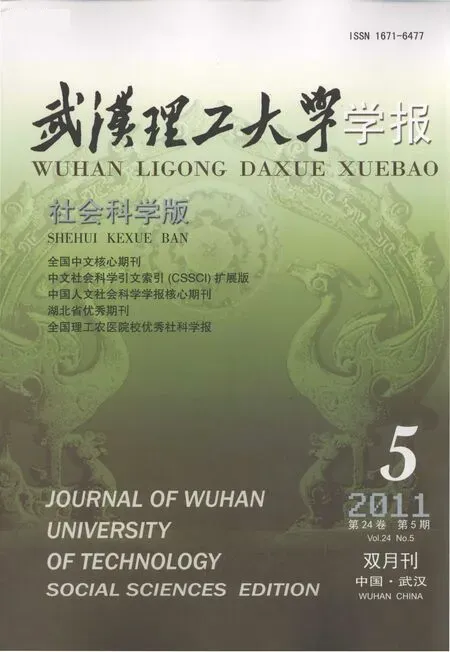宋明理学和谐思想探微*
韩美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宋明理学和谐思想探微*
韩美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道、佛”三教的融合与会通。学界曾对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心理关系、心性关系以及知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普遍探讨和争论。从和谐的视角来看,过去人们简单地批判“理本论”而肯定“气本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地评价“心本论”、“知行观”的做法都是较为偏颇的。宋明理学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华和谐思想:一是“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大学派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论证了宇宙和谐和天人和谐的思想;二是以心性论为重点深化了儒家的心性本体和心性修养的思想,为自我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以知行关系为主线,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知与行的内在和谐统一与人际和谐的关系。
宋明理学;本体论;心性论;知行关系;和谐
中华和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先秦两汉,经魏晋南北朝,历隋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宋代以前,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和谐思想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宋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的和谐思想的发掘则相对薄弱。事实上,尽管由于封建文化专制制度的禁锢,以及中国注经解读传统的制约,中华和谐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桎梏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樊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和谐思想在这一阶段就停滞或完全没有发展了。历史地看,自宋初开始直至明清之际的宋明理学家由于经历了“出入佛老,返诸六经”的心路历程,因而大多能自觉和自发地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三教的融合与会通。而中华和谐思想便在这种融合与会通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一、本体论上的天人和谐观
以“理”为核心,宋明理学家形成了“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大学派,对理与气、心与理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探讨,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论证了宇宙和谐和天人和谐的思想。
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虽然开始突破了先秦儒家不讲“天道与性”的陈规,从天道观上论证了封建制度和伦理的合理性,但这种论证还是粗糙的,并且渗透在政治道德思想之中。建立儒家相对独立的宇宙本体论,以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这是宋明理学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宋明理学家都怀有高度的历史担当。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入手,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极”氤氲,阴阳交合而生万物的辩证图景,并且以“太极”说明“人极”,阐明了“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宗旨,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程颐、程颢作为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自觉地把“天理”和理气关系作为儒家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和最根本的问题。程颐曾说:“吾学虽我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424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对于宇宙根本规律一般用“道”的范畴来表示,但从二程开始,“理”被赋予了“道”的涵义,宇宙本体论集中反映为理气关系。这种哲学范式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了宋代新儒家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思想家力图把宇宙本体论与心性论合为一体的旨意。
在理气关系上,“理本论”者以程颐、朱熹为代表,朱熹集其大成。“气本论”者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王夫之集其大成。程颐和朱熹都认为,“理”作为形而上之道,是构成事物的本原;“气”作为形而下之器,是构成事物的质料,天下无无理之气,亦无无气之理。但“若论本原,既有理而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气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2]3078。可见,理、气本无先后可言,说“理在气先”是就本原的逻辑意义上而言的。朱熹之所以把“理”作为万物的本原,是要强调“理”作为支配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内在根源性和本质性。以张载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者在论释理气相依、气不离理问题上和“理本论”者并无区别。张载明确提出,“万物皆有理”[3]4,王夫之指出,“气得其理之谓理也。气原是有理的,尽天下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4]666-667。但是,张载和王夫之都强调“气”是宇宙的本体,认为理是气之理,理依于气,理在气中,天下无虚托孤立之理。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辞上传》中论述道:“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洪荒,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5]1028在他们看来,有是器才有是道,“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随之而变。由此看来,“理本论”和“气本论”有许多共同点,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根本点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都以理、气相参来解释万物的生成,都运用相同的范畴体系来构建自己的宇宙本体论,其分歧之点在于是以“理”还是以“气”为本原来解释理气关系。其实,二者都有其存在的根据,问题仅在于从怎样的致思向度来探讨理气之间的关系,过去那种简单地批判“理本论”而肯定“气本论”的观点是片面的。
无论是“理本论”还是“气本论”,它们在和谐辩证法的深化和发展上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阴变阳合而化生万物的宇宙和谐图。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6]26这里,周敦颐不仅揭示了宇宙生生不息的运行过程及其阴阳矛盾的内在驱动作用,而且描述了“五气顺布四时行焉”的有序景象。张载在《太和篇》中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在宇宙太虚中气之沉浮聚散而“顺而不妄”的太和境界。他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7]298他还提出了“一物两体”、“动非自外”的命题,初步论证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根源。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于和谐辩证法同样作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他不仅论述了阴阳之道和明确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而且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其最杰出的贡献。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8]32这里所说的一理与万物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朱熹借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理一与分殊的关系。这就是说,好比天空中只有一个月亮,但散在众多江河湖泊之中,就印现出无数个“水月”。一月与无数“水月”的关系,就是一理与万理的关系。所以,万物与一理的关系既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也不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而是万物平等地和无所遗漏地分享了“一理”的全部。朱熹把“总天地万物之理”的“一理”叫做“太极”,故其常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这种部分包含整体的全部,整体和部分完全贯通,“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8]325的思想,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全息论,已被现代基因工程所初步证实。这种思想在哲学上的意义,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就和谐思想来说,朱熹关于一理与万理的“全息”关系的思想,更深刻地揭示了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穿、息息相通的深度的和谐关系。
王夫之作为“气本论”的集大成者,在和谐思想方面最闪光的思想是猜测到了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存在。他说:“(气)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9]63他还举柴火的燃烧为例形象地说明了物质不灭及其存在形态的转化。这一思想虽然只是臆测,但却从根本上说明了宇宙的物质和能量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与和谐的规律。
“心本论”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由王守仁集其大成。陆九渊提出的著名命题是“心即理也”。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0]228在他看来,心与理是合一的。“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10]4王守仁进一步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思想,并把人心具体界定为“良知”。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1]6他甚至把人的良知扩展到万事万物,将其看作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心本论”的这种观点是要强调理与人心的相通性和合一性,以及“理”与“物”的主体性的一面,以便消除心与理、人与天之间的隔膜。的确,人不仅能认识“理”,而且人心中的善性和良知的一面与“理”相融相通,特别是社会人伦之理就是人心中之善性和良知的扩充和实现。至于自然之物之理,也并不是与人无关的纯而又纯的客观之物理,它们都打上了主观烙印,纳入到了“属人世界”或“为我自然”。“心本体”者并不否定世界万物的客观存在,更没有简单断定山河大地乃我的主观精神的派生,而是把人的这种主观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突显出来,并揭示了主客观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对于补程朱理学之偏,深化人们对于天与人、心与理、物与我之间统一的和谐关系的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由此看来,过去我们对于“心本论”的评价未免失之简单。
二、心性论上的自我和谐观
以心性论为重点,宋明理学家从不同方面具体地剖析了心、性、情、才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大大深化了儒家的心性本体和心性修养的思想,为心性自我和谐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先秦孟子和荀子分别提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后来董仲舒和杨雄提出了人性的“善恶相混论”,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论”,人为地把人性划分为三等。这些关于人性的观点虽然从不同方面考察了人性的善恶,但都未能深入到人性的内部,分析人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其统一的关系。宋明理学另一理论成果就是运用理气、阴阳和谐思想剖析心性中的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以及心、性、意、情、欲、才、知、物之间的复杂的矛盾统一关系,把儒家的心性论思想推到一个高峰。
朱熹的心性论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无论圣凡及贤与不肖,其生都禀受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之而言之。未有此气,已有此性。”[8]43因天地之性专指理言,所以是纯善的;而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的杂合,所以有为善或为恶的可能。圣人气质清明,不易受浊气影响,因而能保持善性;而一般人等气质昏暗,易受浊气影响,因而善性受到蒙蔽,往往做出恶行。朱熹由此引出了天理与人欲的矛盾。天理全善,人欲则有善有不善,合理的欲望是善的,不合理的欲望才是恶的。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指存善性之理,去不善之欲。人之一心,有性有情,“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8]89。于是,朱熹又得出了心统性情的论点。在这里,心作为人之一身的主宰,将性与情统一于自身。其中性是心之体,是理在人性中的反映;情是心之用,是性的外在表现,这就是朱熹的性体情用的心统性情论。朱熹的这套心性理论第一次深入到人的心性内部,具体考察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以及心、性、情的矛盾关系,扬弃了以往粗鄙的单元和单维的人性论观点,是儒家心性理论的一个巨大进展。但是,朱熹的心性论存在着明显的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截然分开的二元论倾向,同时,他的心统性情论中“性”与气质之性中的“性”也存在概念上的矛盾。因此,后起的思想家包括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王夫之、颜元、戴震等都从理气相依和理气不离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在人身上实现的性、气、情、才是统一的,力图克服程朱关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但是,这种建立在以气为本的性一元论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无法说明人性之中理与欲、善与恶的矛盾,它们要么把这种矛盾外在化,将其归之于后天环境的影响,重新回到孟子那里去;要么将这种人性的矛盾解释为所禀之气有清有浊之故。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包括朱熹在内的所有这些心性之论特别是其中的人性论,都未脱离以“气”为万物(包括人在内)构成元素的古代朴素形态,亦未摆脱孟子先天人性论的影响,因此,在解释人性内部的矛盾时,就纠缠于理气之辩,无法逃脱因这种理论基础的朴素性和神秘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这就是中国古代心性论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剥离“气”元素说这个神秘的外壳,直接地论述人性内部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善与恶的矛盾,那就会剪除许多不必要的附加成分,还其人性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解读中国古代心性论的时候,应该深入其中进行具体分析,将其神秘的形式和现实内容区别开来。
三、实践论上的人我和谐观
以知行关系为主线,宋明理学家从“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等不同角度探讨了认识中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知与行的内在的和谐统一关系以及人际和谐的关系。
知行关系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等不同观点的论争。明清之际的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他根据《尚书》“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说法,从先难后易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行先知后”的知行说。他说:“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12]236他还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12]135。这就是说,行可以包含知,但知不包含行,因为知了不一定行,因而他的结论是“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12]146。
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知行观与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的知行观既相对立又相联系。在知行关系上,朱熹的思想有三个重要论点:就知行先后说,知先于行;就知行轻重说,行重于知;知行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朱熹认为,知先于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今人多数人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8]289。但是,朱熹在知行的轻重上,却强调行重于知。他说:“自古无不晓事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的圣贤。”[8]328他反对离开行而闭门独坐,说明他看重行,并且把行当作知的目的和归宿。在知行的关系上,朱熹提出了“知行相统一”的观点。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8]129把知与行的关系比作足与目,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谁也离不开谁。
为了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明代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和行不是分隔的,知的同时也就是行,而行的同时也就是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11]221他甚至提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此是我立言的宗旨。”[11]16
对于以上三种知行观,过去我们的评价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例如,只是对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它代表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高水平。对于朱熹和王守仁的知行观,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实际上,这三种知行观作为古代朴素认识论的标志性成果,都从一定的认知视域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规律。从认识的最终来源来看,任何认识都源于人类实践,离开实践,人类的认识既不可产生,也不可能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行先知后”是合理的。从人类认识的自觉能动性来看,人类的实践都具有自觉的目的并按一定的计划和方案实施的,人的头脑不是一块“白板”,在以往知识积淀的基础上,会形成一定的“认知图式”,人们会根据这种“认知图式”对来自实践的客观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建构,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合乎规律地进行认识和实践。所以,“知先行后”也有其合理的意义。从认识和实践的相互渗透来看,一般来说它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认识的过程,而认识的过程也就是实践的过程,根本不存在什么与认识或实践无关的“纯认识”或“纯实践”。在体脑分工特别是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被相对分隔开了,但即便如此,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也离不开科学实验或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而且其最终成果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知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地反映了认识和实践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由此可见,从认识和实践的多维的全面的关系来看,这三种知行观都内在地构成这一关系总体的一个必要环节,只有在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合题”,才较为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人类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和谐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真正揭示整个人际的和谐观。
[1]程 颢,程 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朱 熹.朱熹集:第5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3]张 载.语录:中[M]∥张子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8.
[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
[6]周敦颐.太极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张 载.太和篇[M]∥张子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8.
[8]朱 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张 载.太和篇[M]∥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王夫之.说命中二[M]∥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76.
Study on Harmonious Theory of Neo 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AN Mei-qun
(School of Marxism,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Hubei,China)
Based on Confucianism,Neo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as integrated“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We have generally explored and discus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knowing and doing,and so 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y,it is all comparatively biased that people in the past criticized simply LI Ontology and appraised QI Ontology,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one sided on Heart Ontology and knowing &doing theory.Neo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further deepen Chinese harmonious theory from three respects.
Neo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ontology;Heart Ontology;relationship of knowing and doing;harmony
B244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22
2011-04-10
韩美群(1975-),女,湖北省荆门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CKS010)
(责任编辑 文 格)
——《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