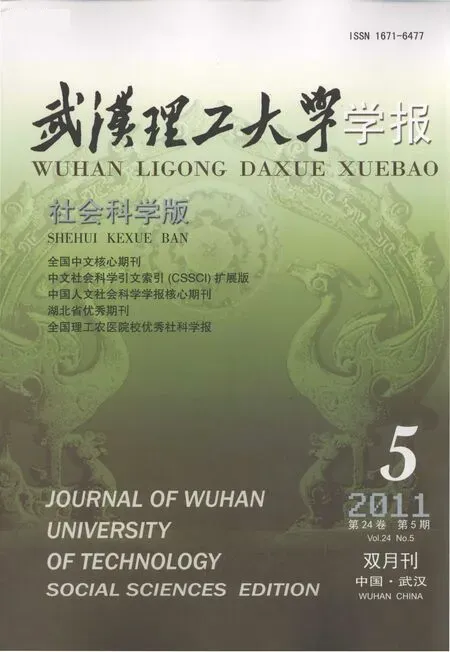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
王治河
(1.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洛杉矶 加州 美国91711;2.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哈尔滨 黑龙江150006)
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
王治河1,2
(1.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洛杉矶 加州 美国91711;2.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哈尔滨 黑龙江150006)
GDP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许诺的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景,相反却导致了贫富的鸿沟,带来了自然环境和社会共同体的毁灭以及虚无主义的弥漫。要破除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崇拜,超越现代榨取型经济,实现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就有必要反思以个人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为特征的第一次启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①。而建立在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自国与他国的“共同的福祉”为旨归的第二次启蒙,从尊重他者的立场出发,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所谓后现代经济是一种为了共同体利益的经济,一种生态经济,也是一种可持续经济,一种幸福经济。后现代经济有助于我们找回生命中久违的意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第二次启蒙;后现代经济;生态经济;过程哲学;有机共同体主义
一、现代经济主义的失败
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旗帜下,伴随GDP的快速增长,现代经济主义受到人们特别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追捧。经济主义视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鹄的,以至于经济增长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性。经济主义者深信,经济的增长能解决世界上一切最重要问题。经济主义迷信“经济增长”,坚信经济增长将改善人民的经济福利,能够克服贫困,能够创造工作机会,得到高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能够改善健康和教育状况,可以解决人口过度增长问题,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可以导致民主政府。
现代经济主义的确有其值得炫耀之处,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柯布博士将其殊胜处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减少了西方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是减少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之间的冲突;三是解构了夜郎主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一种全球视野思考问题。简而言之,经济主义让人们相信,经济发展是硬道理,随着GDP的增长,以往困扰人类的重大疑难问题都会得到解决,自由和平等一定能够得到实现。
然而,GDP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许诺的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景。以美国为例,虽然“经济学家们早就承诺,不断发展的经济能够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经济福祉,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而且自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后,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1]。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呢?首先,虽然旧的劳资之间的对立减弱了,但由于现代经济主义对人的评价完全是根据他们对市场的贡献来进行的,因此就导致了新的人群的对立,即参与市场的和不参与市场的人群之间的对立。新的贫困阶层的诞生就是这一对立的结果。相应地,也产生了新的贫困人口。其结果是,除了跨国公司的大老板和少数顶级富豪外,人人在经济上都是贫穷的,脆弱的和不安全的。现代发展模式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正在加深了第三世界的贫困。而贫富两极极度分化的世界必然是穷人产生绝望和愤怒的温床。在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GDP的高速增长而缩小,反而是在持续拉大,1995年是2.72∶1,2003年扩大为3.2∶1[2]。至今全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3]。
其次,经济增长往往是以剥削第三世界的穷人为代价的(例如几乎所有世界名牌都是在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通过剥削妇女和童工生产的),这使得经济增长背负了道德上“不义”的原罪。由于广大第三世界的农村经济不属于货币体系,该经济体系下人们的经济状况也就不属于国民生产总值(GDP)范畴了。但当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里找工作时,他们的家庭、社区和文化便开始瓦解,而且每个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情况变得更糟,国民生产总值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他们现在挣工资,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詹森教授曾引她的一个来自肯尼亚的学生的话说:“我们过去给孩子命名‘富余’,然后‘专家们’来了,告诉我们不要再靠种粮食养活自己,应该改种咖啡和茶叶去出口,这样我们就有钱了。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我们种出来的咖啡和茶叶还不够种植费用,更不用说养活我们自己了,树木没了,水质变坏了,土地退化了,我们的孩子挨饿了。”[4]结果是肯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上升了,该学生的同胞们的生活却更糟了。
第三,现代经济对传统社区和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中国日益严重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就是一个重要例证。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强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出现了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空心化”不仅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村人的家庭幸福。“家庭的温馨与欢乐越来越少,农民的家庭生活已经变得非常态化”[5]。虽然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并非任何代价都是不可避免的。以牺牲8亿农民为代价的发展未免过于残酷了。一个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幸福和自然的健康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是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同样,造就了5 000万身心与婚姻都亮起了红灯的“留守妇女”的发展也是不人道的,它是现代经济主义登峰造极的结果,这是跟“以人为本”的宗旨相背离的。
第四,对于现代社会中“虚无主义”的弥漫和“道德严重滑坡”的大面积发生,现代经济主义也是难辞其咎的[6]32-35。因为现代经济主义对经济的过分崇拜,势必导致拜金主义和“一切向钱看”思潮的风行,而见利忘义,制假造假,贪污受贿,坑蒙拐骗,制黄贩黄,走私贩私,卖淫嫖娼,见死不救,人情冷漠等严重道德滑坡的发生就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当金钱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时,为获得利益最大化,往食品里添加致癌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商学院前教授柯藤深刻分析的那样,“当一个社会不能满足其成员对社会纽带、信任、关爱及共享的意义感的要求的时候”,暴力,极端竞争,自杀,药物滥用,贪婪和环境退化等病态行为“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7]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所有辉煌的物质文明成果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主义所主导的现代经济在根蒂上是一种“榨取型经济”。现代经济在导致了GDP短期内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灾难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现代经济使得“地球表面的生命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人类行动的严重威胁”[6]37。因为正是现代经济运用科学技术把可再生资源变成不可再生的资源,将大量有毒的污染物质扩散到空气、水和土壤中,对地球和人类的健康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以现代农业经济为例,当我们通过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给土地下毒。同样,当我们借助电子工具、漂流网、水产捕捞船提高捕鱼产量时,我们实际上是以一种终结自我繁衍能力的方式来耗尽大海和河流中的水生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是一种“终结式经济”。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拼命发展核电站的日本所面临的成为核废墟的危险图景,就是对何谓“终结式经济”一词的最好注脚。
沉睡百年之后而崛起的中国,在不顾一切地拥抱现代经济之后,也不得不面对这种“榨取型经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今天,作为首席“世界工厂”,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就煤炭资源而言,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08年,我国煤炭消费量27.4亿吨,增长3.0%。一项研究报告说,2007年,我国每使用一吨煤,就会造成150元左右的环境损失,这还不包括巨大气候成本。我国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燃煤。燃煤制造了85%的二氧化硫排放量,67%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和70%的悬浮颗粒物。此外,每生产一吨煤还污染2.5吨的水,煤矿废污水占全国总废污水的25%。燃煤还造成了土壤污染和土地“虚劳”[8]。我们的先人是用铁锹挖煤,用马车运煤,以小煤炉烧煤,而我们用机械采煤,用火车运煤,用炼钢炉烧煤。我们30年来所消耗的煤炭总量大概要超过此前的3 000年!再以水污染为例,中国70%的河流与湖泊已然受到污染,其中1/3河流遭到严重污染,1/4近岸海域污染严重,以至于中国主要城市近一半饮用水不符合标准。其结果是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其中有110个严重缺水[9]。此外,近7年来,我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量的5%[10]。
虽然中共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转向和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意在挑战现代经济主义,发展一种认真考量环境并将民生放在首位的生态经济,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人依然深陷现代经济主义的迷梦中,他们坚信现代经济的神话,视经济增长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经济的增长是“硬道理”。这似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某种碰不得的“真理”。
要破除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崇拜,打破人们对现代经济的迷信,就有必要对作为现代经济理论基础的第一次启蒙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理、反思和超越。因为对于现代经济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的灾难,第一次启蒙难辞其咎。正是第一次启蒙为现代经济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例如,现代经济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崇拜就是第一次启蒙所推重的“只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而不管不顾他人的现代自主个体概念的具体体现”[11]。
二、现代经济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第一次启蒙的众多特征中,有两个维度直接构成了现代经济的理论基础。其一是它的个人主义,其二是它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
(一)第一次启蒙的个人主义
现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将人根本看做是个人主义的,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独立存在的,彼此间或与社会其他成员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人也被认为是“理性的行动者”,换句话说,人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作选择的。这种个人主义鼓励享乐主义和追求肉体享乐。经济的惟一目的就是开发自然世界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商品生产供人类使用。“这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关健的价值选择:惟一公认的好的标准就是个人的选择”[4]。
这种个人主义在现代经济的理论奠基者亚当·斯密(1723—1790)的理论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苏格兰的道德哲学教授,是“人都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始作俑者。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经济启蒙”。从牛顿力学出发,斯密认为人本质上是经济动物,是“经济人”,满足人的需要是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其他事物只有在作为工具满足人的需要目的意义上“才会得到考虑”[12]。在斯密眼里,整个人类社会都是由这些完全孤立分离的经济人构成的,它们或者购买劳动力、服务、商品或者出卖它们。将这一切组织起来的是“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对利润的追求,社会的进步得到自然而然的推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对市场的过分迷信,使这位道德哲学家对当时英格兰工厂工人“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持一种几乎完全“漠视”的态度[13]。
(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
所谓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和宰制与剥削的对象。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就高扬这样一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在他眼里是一个“被拷问”,“被命令”的对象,她只有“服从”的权利[14]。相应地,正如德里达揭示的那样,那些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听话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等“非人类生命”被视作“流氓”[15]。从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立场出发,“土地”变成了完全是为了“定居和占有的;土壤是为了耕种;森林是为了木材;河流是为了旅行,为了田园灌溉,为了发电;狼、熊和蛇等这样的动物的存在就是为了被猎杀;海狸、鹿、兔子、鸽子这样的动物则是为了提供毛皮或者食物,生活在溪水河流和海洋里的各种鱼类,是为了人类的捕捞”[16]。
在这样一种强势的帝国主义态度的主宰下,即使连最应该与自然亲近的审美活动也变得具有暴力倾向。例如“自然美的崇高”就被我们的现代美学家理解成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将它们历史地征服之后,对观赏(静观)来说成为唤起激情的对象。所以实质上不是自然对象本身,也不是人的主观心灵,而是社会实践的力量和成果展现出崇高”[17]。中国大跃进年代那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勒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则将这种霸气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
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不敬,对自然的否定态度,导致了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毁灭[18]。斯坦芬也认为人类今日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这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结果,是它的“可怕的社会代价之一”[19]。
而生态女权主义则进一步认为,对自然的压迫和统治,是内在地“与对妇女的压迫和统治联系在一起的”[20]。因为自然与妇女二者都被现代启蒙思想家看作是“非理性的,不确定的,难以控制的,模糊的。虽然启蒙思想家高调倡言人道主义,但‘成人’在他们那里,主要是,而且必须是“成为男人”[21]。因此,只要这种压迫和统治依然存在,妇女的解放和生态危机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
三、第二次启蒙的生态向度
正是第一次启蒙的上述局限导致了今日现代经济的种种弊端。因此要超越现代榨取型经济,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也就是呼唤新的哲学思维和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关于第二次启蒙的主要理论内容,我们在《第二次启蒙》一书中从学理上共概括了7点[22]。然而从核心价值的角度看,如果说第一次启蒙强调“高扬自我”的话,那第二次启蒙则欣赏“尊重他者”。这里的“他者”,不仅包括弱势族群和其他文化,而且包括大自然。如果说现代经济主义追求的是少数人的福利的话,那第二次启蒙则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自国与他国的共同的福祉。因此生态意识,就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理论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第二次启蒙称作“生态启蒙”。
(一)第二次启蒙的有机共同体主义
从过程哲学的“内在关系”概念出发,第二次启蒙倡导一种“有机共同体主义”。与第一次启蒙高扬个人主义的大写的原子式“个人”不同,第二次启蒙的“共同体主义”强调人的关系性,主张“共同体中的人”。“有机共同体主义”强调,他者与自我不是对立的,他人的健康恰恰有助于自我的健康。一个儿子在损害他母亲健康的条件下不可能通过获得更多的食物而获益,那些在损害其共同体的利益条件下获得财富的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我们是同一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个人的幸福和他者的幸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有机共同体的重要职责是创造一切条件使其成员活得健康幸福,相应地,共同体中的个人的职责是尽一切可能促进共同体的繁荣。双方之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二)第二次启蒙的生态意识
要高扬生态意识,就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鉴于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论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启蒙意在超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根据这种人类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态度,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并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去任意剥削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对自然横征暴敛。人对自身的理解基本是囿限于如何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不是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从后现代的第二次启蒙的角度看,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摈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
第二次启蒙的这种生态意识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与恒星、微风、岩石、土壤、植物、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古老的智慧。只不过长久以来被人类中心主义充斥大脑的现代人给遗忘了。印第安“西雅图酋长宣言”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生态意识。1856年,北美印地安索瓜米希族部落的首领西雅图酋长面对美国总统让其卖部落土地给政府的要求,做了如下答复:
对我的人民而言,大地的每一部份都是圣洁的。每一枝闪亮的松针,每一处沙洲,每一片密林中的薄霭,每一只嗡嗡作响的虫儿,在我人民的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树中流动着的汁液,载负着红人们的记忆。
河水就如同我们的兄弟,满足了我们的干渴。河水载运了我们的独木舟,并养育了我们的子孙。如果我们将土地卖给你们,你们必定要教导你们的子孙,它是我们的手足,也是你们的弟兄,因此,你必需对它付出关怀,一如你对待你的兄弟一样[23]。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及“民胞物与”思想所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生态意识。在中国学习多年的世界著名生态学家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则别开生面地将“人”理解为天地的“心”[24]。因此,心系大自然,为天地操心,就成为人的天职。
与传统的环保意识不同的是,第二次启蒙所要推重的生态意识要告诉人们的是:不是我们去保护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毁灭了自然,“我们也就毁灭了我们自己”[25]。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仅滋养我们的肉体,而且“安顿,滋养”我们的精神,陶冶我们的情操[26],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护她,而且要爱戴她,敬畏她。
四、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
从尊重他者的立场出发,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所谓后现代经济是一种为了共同体的经济,一种生态经济,也是一种可持续经济,一种幸福经济。
(一)后现代经济是一种共同体经济
如果说现代经济是一种个体经济,那后现代经济就是一种共同体经济。与现代经济为资本服务,为发展服务不同,后现代经济强调“经济应该为共同体服务,而且共同体的价值决定了那些被视为发展的东西。”[27]57相应地,与现代经济把焦点放在发展城市的工业,通过提供成本非常低廉的劳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不同,后现代的共同体经济将就重点放在繁荣发展地方共同体上。因为“地方共同体只有控制了其自身的经济,才能成为人类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中的一个健康和有效的共同体。”[27]48后现代经济的一般原则是,权力应该被局限于能够着眼当前问题而采取行动的最小共同体之中。地方控制更优于远程控制,因为它更能授权于人民。
这样一种后现代生态经济理论为企业的民主管理,为小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发展开启了空间,可能有助于一种更健康的经济。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做大,全球权力日益从政治控制转向经济控制,后现代的共同体经济对发展地方共同体的强调特别是对地区经济自给的强调,无疑符合各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二)后现代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经济
如果说现代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经济的话,后现代经济则是一种可持续经济。所谓可持续,按照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1990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操作性原则,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遵循这三个原则,那么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可持续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所有可再生性资源的开采利用水平应当小于或等于种群生长率,即利用水平不应超过再生能力;二是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应当低于自然界的净化能力;三是将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利用获得的收益区分为收入部分和资本保留部分,作为资本保留的部分用来投资于可再生的替代性资源,以便不可再生性资源耗尽时有足够的资源替代使用,从而维持人类的持久生存。
如果说,达利侧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阐释可持续经济的话,那么,柯布则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发可持续的。在他看来,“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仍然很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只要穷人还抱有他们将分有新的财富这一现实希望,他们就会忍受其贫困并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是,他们会接受一代又一代人之持续贫困吗?随着分有新的财富这一承诺失去了信誉,这个社会的可持续性逼供愈发可疑了”[28]。在柯布看来,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应该以谋求个体与群体的共同福祉为旨归,应该是个人与共同体的互茂共荣。
(三)后现代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
与可持续经济相联系,后现代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的。由于它的道德考量,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旨在“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生活质量的道德哲学”[29]。生态经济学家“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更大的有限系统的一部分。”[29]它强调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自然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枝枝相连,息息相通。柯布认为,内在价值并不只限于人类,构成人类存在的各种关系也不只限于人和人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以及其他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与现代经济理论把人跟自然的关系看做占有的关系不同,后现代生态经济理论强调,人是地球这个星球上的宾客。人类的一切都与自然相关,人与自然的这种血脉相连性也包括了人与其他创造物之间的血脉相连性,它们的幸福也有助于人自身的幸福。
(四)后现代经济是一种幸福经济
与现代经济理论漠视共同体和人的关系以及其惟一的目标就是日益增长的生产和消费相反,后现代经济寻求的社会是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30]。后现代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幸福”。据此,他们批评现代经济理论对自然环境的意义的忽视,对生活质量的忽视(GDP并没有说明生活质量),以及对经济“增长”之社会的心理的和生态的后果的忽视。后现代经济幸福经济学解构了财富增长等于幸福的等式。尽管有证据显示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不断上升,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自我评价的幸福感觉却在逐年下降。这说明更多的财富并不能带来更幸福的生活。事实上,证据显示,比起以前受到的很多生活紧张性刺激,包括不可持续的个人财政债务负担以及个人破产所带来的持续焦虑等,现在的美国人生活得更加有压力,更加消沉。
幸福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一个幸福的生活,50%取决于个人的成长和遗传的质量,40%取决于和家人、朋友以及同事之间关系的强度和质量,只有10%取决于收入和教育。2010年,在对加拿大最幸福团体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影响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归属感,即归属于当地团体的感觉,接下来分别是心理健康,身体活动水平,压力程度,结婚,新近移民,失业,最后才是家庭收入水平。研究表明,社会关系对于人类感知幸福和生活质量的作用超过金钱。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不仅要问:如果大多数人已经实现了物质富足,为什么经济还必须持续增长呢?
据此,后现代幸福经济学家马克·安尼尔斯基提出了“真实财富”概念,“真实财富”概念将美德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幸福和进步的标志必须与社会团体的价值观以及对居民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东西相一致。但是最重要的是,真正的进步是通过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以及他们对于真实幸福的体验而显现的。后现代经济学家推重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概念,认为它测度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东西[1]。
五、后现代经济对中国的意义——兼评“过瘾论”
尽管后现代经济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打压,本身也有不完备之处,但其探索是宝贵的,其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超越或突破一直被视作惟一正宗的天经地义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客观上为我们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开辟了道路。可以想见,这样一种后现代经济理念在中国一定会受到“过瘾论”的诘难。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中国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要崛起了,凭什么我们中国人民还没有富起来就要先过穷日子,还没有现代化就要开始搞生态经济,开始过绿色生活?在他们眼里,“绿色生活方式的要义是节制人的欲望”。“别人都还在拼命追求满足欲望,为什么我们要率先约束?”他们的结论是:“即使这样的生活不可持续,我们起码也得过把瘾,先现代化了再说。”[31]
这种“过瘾论”虽然伴随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流行,反映了眼下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从者如云,但理论上是颇成问题的,道义上也是不负责任的。
理论上,“过瘾论”显然是线性思维的牺牲品。认为中国应该先实行现代化,然后再来讲后现代化,讲生态文明,好像历史发展阶段一定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依照这种线性思维定势,生态文明,绿色生活方式是后现代社会要考虑的事,我们现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现今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现代化,是过上“现代生活”,尽管这样下去“地球确实难以支撑”[31]。显然,批评者的头脑中显然预设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不先实现现代化,哪里来的后现代,不先实现工业文明,那里来的生态文明?这些批评者不仅忘了列宁关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显然也遗忘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说,特别是意识具有超前性的学说。
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一直信奉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生活方式被“过瘾论”者视作唯一正宗的,天经地义的发展模式和理想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即使是火坑,我们也要往下跳。对近30年来无数来自后现代阵营的对现代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弊端的揭露与深刻批判,“过瘾论”者显然丝毫没有加以考虑。
其次,“过瘾论”在道德上也是不负责任的。这种责任感的缺席,一方面体现在对自然,对地球,对他人,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上。用我国有些学者的话说就是,为了发展经济,我们30年来所消耗的煤炭总量超过此前的3 000年!“如果这些煤炭取自本国,则我们在与自己的儿孙为敌,如果这些资源取自国外,则我们在与世界为敌”[32]。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先生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重复走西方发展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33]。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上。因为以消费主义为取向,以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其外在的华丽外衣下,其实是布满了千疮百孔的。这样说丝毫没有否认现代经济存在着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便利的一面,而是说它带来的问题远较这些便利多得多,也严重得多。
以美国的肥胖现象为例,拜现代生活方式所赐,肥胖已经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调查显示,60%的美国成年人超重,1/4的人患有肥胖症。每年大约有30万美国人过早死于与肥胖有关的各种疾病。
当我们抛弃了以粗粮、杂粮、蔬果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一心拥抱大鱼大肉白米白面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踏上了一条“苍白人生”的不归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上这样一把损人害己的“瘾”呢?
今天,对于环境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绝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难道在不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问题上,我们非要走发达国家先受害再回头的老路不成?沃尔玛的创立者山姆·沃尔顿临终前说他愿意以其所有的财富交换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惜他觉悟得太迟了,以至不能使自己受益。但我们其他人却能够从他以生命为代价所获得的体悟中得到宝贵的启迪。财富是必要的,但正如美国企业社会责任领袖大卫·施沃伦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财富是以一个人的健康和我们的地球的生机为代价的话,“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34]。
最后,“过瘾论”背后实际上是现代虚无主义在作祟。虚无主义是现代经济主义的孪生姐妹。当经济成为社会的唯一目的,金钱成为人生的唯一价值的时候,道义、信仰、理想和意义就被放逐了,信仰的缺席和意义感的消失,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的弥漫,过把瘾就死,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直接表征。它不仅在道义上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孝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理论上是反社会的,而且哲学上是自己“对生命犯下了叛逆罪”(维特根斯坦语)。
而第二次启蒙站在尊重他者的立场提出的后现代经济则有助于我们找回生命中久违的意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因此值得期待!
注释:
① 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贝克喜欢用“生态启蒙”来概括“第二次启蒙”,考虑到“生态启蒙”在贝克那里主要指要有更高的环境意识,要始终对科学及其使用的领域与范围保持警惕,而没有涵盖其他领域对启蒙的反思和超越,因此,我还是倾向于用“第二次启蒙”指称对第一次启蒙的全面反思和超越。
[1]Mark Anielski.Building Economies of Wellbeing[Z].Paper for Fif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laremont,April 28-29,2011.
[2]中经论坛(纵横).我们不需要一组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EB/OL].(2004-08-02)[2011-01-20]http:∥bbs.ce.cn/bbs/viewthread.php?tid=55521.
[3]汪大勇.我国成人文盲10年减少近1亿 文盲率下降到9%[EB/OL].(2007-07-31)[2011-01-11]http:∥edu.qq.com/a/20070731/000006.htm.
[4]凯罗 詹森.从怀特海的过程理论审视全球经济[M]∥王治河.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1.
[5]管爱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民的价值观转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153.
[6]John B,Jr.Cobb,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t[M].London,UK:MacMillan Press,1999.
[7]David C.Korten,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Kumarian Press/Berrett[M].Koehler Publishers,Inc,1995:261.
[8]何 兵.发展不是唯一的硬道理[J].民主与科学,2010(4):53-54.
[9]杜继昌.节水节水再节[EB/OL].(2001-07-18)[2011-01-20]http:∥www.cnnb.com.cn/gb/node2/newspaper/node38965/2008/7/node79989/node79993/userobject7ai1365745.html.
[10]赵胜玉.国土资源部:中国七年以来减少耕地面积一亿亩[EB/OL].(2004-04-09)[2011-01-20]http:∥news.hsw.cn/gb/news/2004-04/09/content_951647.htm.
[11]Herman Daly and John B.Cobb,Jr.For the Common Good[M].Boston:Beacon Press,1994:159.
[12]Herman E.Daly,John B.Cob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Boston:Beacon Press,1994:107.
[13]Charlene Spretnak.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M].New York:Routledge,1997:58.
[14]Water F.Baber & Robert V.Bartlett.Deliberative Environmental Politics:Democracy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M].London:The MIT Press,2005:206.
[15]Jacques Derrida.Rogues:Two Essays on Reason[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93.
[16]托马斯 贝里.伟大的事业[M].曹 静,译,张妮妮,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44.
[17]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61.
[18]Max Horkheimer &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Stnford:St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54.
[19]Stephen Crook.Postmodernization: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M].London:Newbury Park,Calif:Sage,1992:210.
[20]Andrew Dobson.Green Political Though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e,1995:187.
[21]David L.Hall and Roger T.Ames.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Dewey,Confucius,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J].Lan Haixia Wang.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2001,8(1):201.
[22]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38.
[23]Chief Seattle's Letter[DB/OL].(2011-01-15)http:∥www.synaptic.bc.ca/ejournal/wslibrry.htm.
[24]托马斯 柏励.《走向生态纪元》序∥李世雁.走向生态纪元.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1.
[25]Lynn Margulis.“Gaia and Machines”,in John B.Cobb.ed.Back to Darwin:a richer account of evolution[M].Wm.B.Eerdmans Publishing,2008:175.
[26]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27]John B.Cobb,Sustaining the Common Good[M].Ohio:The Pilgrim Press,1994:48.
[28]王治河.全球化与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7.
[29]戴利,弗蕾.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M].徐中民,译.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6.
[30]John B.Cobb,Sustainability-Economics,Ecology and Justice[M].Maryknoll:Orbis Books,1992:50.
[31]江晓原.中国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的两难处境[J].绿叶杂志,2009(2):61-66.
[32]何 兵.发展不是硬道理[EB/OL].(2010-05-14)[2011-02-03]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9130.
[33]潘 岳.用东方智慧寻找文明出路[M]∥廖晓义.东张西望——廖晓义与中外哲人聊环保药方.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10:3.
[34]大卫 施沃伦.建立一种有信仰的经济[N].世界文化论坛,2009-02-28(1).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Calling for a Postmodern Economics
WANG Zhi-he1,2
(1.Sino-American Post Moder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Los Angles 91711,CA,USA;2.Center for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Studie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6,Heilongjiang,China)
Although modern economics has been worshipped by liberal economists,it has not brought freedom and equality as they promised.On the contrary,it has brought us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and social communities,and the spread of nihilism.In order to transcend modern economics and eradicate the worship of growth,and move towar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we need a second enlightenment based on process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ive post modernism,which aims at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kind and nature,we and the others,our country and their countries.Such an enlightenment calls for a postmodern economics which is ecological and sustainable.Postmodern economics,as an economics for community and an economics for happiness can assist us to find the sense of meaning,belongings,and happiness lost for a long time.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postmodern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process philosophy;organic communitarianism
B15;F0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03
2011-05-10
王治河(1960—),男,山东省招远市人,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后现代哲学、过程哲学和第二次启蒙研究。
(责任编辑 易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