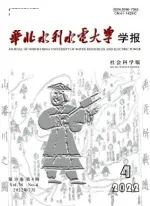政无为而法有为
——浅谈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特点
吴 涛
(洛阳师范学院,河南洛阳472000)
政无为而法有为
——浅谈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特点
吴 涛
(洛阳师范学院,河南洛阳472000)
西汉前期在无为而治的表象下,继承了许多先秦法家的特点,并对先秦法家进行了许多修正,抛弃了法家的刻薄寡恩,给法家政治披上了一件无为的外衣。
西汉前期;法家思想;无为而治
谈起西汉初年的政治总是首先想到所谓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可是又可以发现一些完全相反的记载,好象西汉初年的无为政治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一定的距离。取得政权后刘邦很快就发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就命令“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P1096),之后还曾命叔孙通加以补充成《傍章律》。吕后打击政敌的手段之残酷也很难让人与“无为”联系到一起。史书中称汉文帝省刑薄赋,但也有他“好刑名之言”[2](P3117)以及“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1](P1099)的记载,而且史书中关于汉文帝废除肉刑、腹诽和株连的记载恰恰证明了在此以前法令的严酷。仔细研究西汉初年的政治就会发现所谓的无为而治实际是对秦王朝的法家政治的某种修正,西汉的政治家们在抛弃法家刻薄寡恩作风的同时也保留了法家的基本精神,给法家政治披上了一件道家的外衣。
一
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对先秦的法家有着明显的继承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家维护绝对皇权的思想被完整地继承下来并被进一步加强。比如在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就对矫诏、矫制、不敬等侵犯皇权的行为都制定了严厉打击的措施。矫诏就是诈称皇帝诏书、诏令的行为,对矫诏绝对是严惩不贷,《贼律》中规定:“伪写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腰斩以匀(徇)。”对于伪写官印也要受到严惩,“伪写彻侯印,弃市;小官印,完为城旦舂”。与矫诏近似的还有一种行为“矫制”,就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违反,对于这种行为视后果给予不同的惩罚,“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任何对皇帝不敬的行为也要受到处罚,《贼律》中规定:“诸上书及有言而谩,完为城旦舂。其误不审,罚金四两。”
第二,法家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思想被继承下来并制度化。西汉初年法家强调专制统治秩序的思想被统治者所继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在汉景帝时代表当权的黄老派的黄生和代表在野的儒家的辕固在皇帝面前就汤武革命的问题展开了辩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2](P3123)从中可以看出,西汉初年对法家所强调统治秩序思想的继承。同时为了巩固统治秩序,西汉初年还继承了秦朝所确立的三公九卿的政治制度和二十等爵制,并有所完善。
第三,先秦法家所确立的法治主义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先秦法家思想家们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并且能够认真贯彻执行。他们认为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维护它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不能随意违反。这在先秦法家的典籍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这里就不赘述了。先秦法家的这一思想在西汉初年也得到了继承。这就体现出法家所强调的法乃天下之公器的思想。晁错也认为应该:“奉法不容私,尽力不敢矜。”他认为如果能够得到重用就应该:“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与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赏厚,功少者赏薄。如此,敛民财以顾其功而民不恨者,知与而安己也。其行罚也,非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故辠大者罚重,辠小者罚轻。如此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罚之至,自取之也。”[1](P2294)也就是要求以公心立法以公心执法就可以致太平。同时法家还极力倡导公正廉洁的风气,这在西汉初年的著名酷吏郅都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史记》称:“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不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2](P3133)
第四,法家重农抑商的思想被继承下来成为西汉初年重要的经济指导政策。在先秦韩非就认为商贾是对农业经济最大的破坏力量,他认为“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他提出的措施是“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舍末作”[4](P1075)。西汉初年重农抑商的政策得到了继承,“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P1418)。西汉初年工商普遍被认为是末业,只能使人“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对于巩固统治、增强国力没有用处,应当给以一定的限制。文帝时贾谊就主张:“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5](P103)而西汉前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晁错就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主张。他认为商人们不仅是造成农民贫困的重要因素,而且商人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1](P1132),是统治秩序的重要破坏因素。所以他主张使游食之民都回归到农业上去,具体的办法就是向国家交纳粮食可以得到爵位,犯罪也可以交纳粮食来赎罪,这样就会使农业得到重视,国家的积蓄得以增加,而一般农民的负担也可以得到减轻。汉文帝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汉家的三十而税一被历代的史家当作美谈,这和法家的重农抑商主张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第五,法家所强调的郡县体制被最终确定下来。西汉立国之初,刘邦为了战胜项羽而分封了若干异姓诸侯王,这些异姓诸侯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所以在战胜了项羽之后不久刘邦就先后解决了几个力量强大的异姓诸侯王。但在当时地方上的分裂势力还比较大,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还不足以实现对全国的直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也就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来填补异姓诸侯王所留下的空缺。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这些同姓的诸侯王在力量强大以后也纷纷走向了与中央对抗之路。所以西汉初年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积极地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贾谊就主张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处理诸侯王。态度最坚决的是景帝时的晁错。他主张不断寻找借口来削减诸侯王的封地,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会“天子不尊,宗庙不安”。虽然他为这一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打击诸侯王却没有因此而停顿,并在武帝时获得了最终的解决。从此以后的诸侯王国也就与郡县没有了实质上的区别。郡县制在西汉初年虽说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最终得以确立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主要行政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以晁错为代表的法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六,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了完善的法律制度,继承了秦王朝的残酷刑罚制度。刘邦初入关的时候为了取得民心而约法三章,但是当情况稳定下来之后就发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就命令“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P1096),之后还曾命叔孙通加以补充成《傍章律》。前些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使我们对西汉初年的法律有了一个更直接的认识,《二年律令》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相应地西汉初年也建立了一套十分严厉的刑罚制度,见于记载的有族诛、弃市、要斩、肉刑、笞刑、徒刑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汉初年刑罚的残酷,就连以宽仁著称的汉文帝也“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1](P1099)。到汉景帝时晁错也为西汉法律的完善做出了贡献,史称他对当时法令“多所更定”。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成为专制刑罚的牺牲品,西汉初年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晁错也受酷刑而死。同样是为打击地方诸侯王立下大功的周亚夫被加的罪名是“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2](P2079)。
二
那么汉初的政治与秦代是否没有区别呢?显然也不是,汉初的无为而治是在继承了法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对法家的修正体现在对“术”的运用。“术”本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家的忠实实践者秦始皇和李斯却更多地强调了刑罚的作用。在西汉初年经历了秦末的战乱,统治阶层的统治力量受到巨大的削弱,所以不得不有所退让,使法家“术”的思想受到重视。晁错就强调说:“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后世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制临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1](P2277)所以晁错认为对太子进行术数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所谓的“术”也就是有进有退的君人南面之术,当然也有人把它应用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比如敢于弹劾太子和梁王的汉初另一位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张释之就和“善为黄老言”的王生上演了一出双簧,王生故意让张释之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他结袜,王生说:“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果然收到了“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2](2756)的效果。以至于西汉末年当东平思王向朝廷要《史记》看时大将军王凤说:“《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1](P3325)这样翔实记载了汉初历史的《史记》也被看做不可轻易示人的秘籍了。
另一方面,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也吸收借鉴了一些儒家的思想。西汉初年在思想史上是一个不同流派之间充分吸收融合的阶段,这一时期法家也吸收借鉴其它学派的合理思想。这一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晁错在儒家经典《尚书》的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吸收儒家重视历史传统的作风,给自己所倡导的法治寻找历史依据。先秦法家十分强调“察今”,反对法古。晁错则借鉴儒家重视历史传统的作风,把传说中的先王改造成法家的理想统治者,使自己所倡导的法治获得了历史依据。其次,他吸收借鉴了儒家所畅想的所谓“三代”的理想目标,当然先秦法家本身也有自己的理想社会,但是不如儒家的社会理想那么高远,于是吸引力也就不大。晁错认同了儒家所倡导的社会理想,但他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社会的途径却是要强调法治。他还吸收儒家关于礼治的思想,给法治寻找伦理依据。儒家认为礼是圣人根据人情而制作的,礼与人是不相悖的。晁错则进一步发挥认为法也是神人根据人情而制定的。他说:“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筋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1](P2294)而且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所以西汉初年的法家抛弃了严刑峻法的主张,所以晁错说:“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人有期,后宫出嫁……”[1](P2296)这与先秦韩非的口气完全不一样。
综上所述,西汉初年的法家思想在继承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所修正,在西汉初年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秦因专任法治而忘所以汉人行法之实而不愿居法之名,所以西汉初年就搬出了所谓的黄老思想做门面。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后不过是给法穿上了另一件外衣而已。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4]陈其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阎振益.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Abstract:West Han Dynasty has inherited many thoughts from legalist school in Qin Dynasty.However,many amendments have been done to forsake the extremely harsh part.In this case,legalist school management was disguised by inaction government.
Key words:early West Han Dynasty;legalist school management thoughts;inaction management
(责任编辑:刘 明)
The Study on“Inaction Government”in Early West Han Dynasty
WU Tao
(Luoyang Normal Institute,Luoyang 472000,China)
K234.1
A
1008—4444(2010)02—0062—03
2010-03-04
吴 涛(1973—),男,河南郑州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同时为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