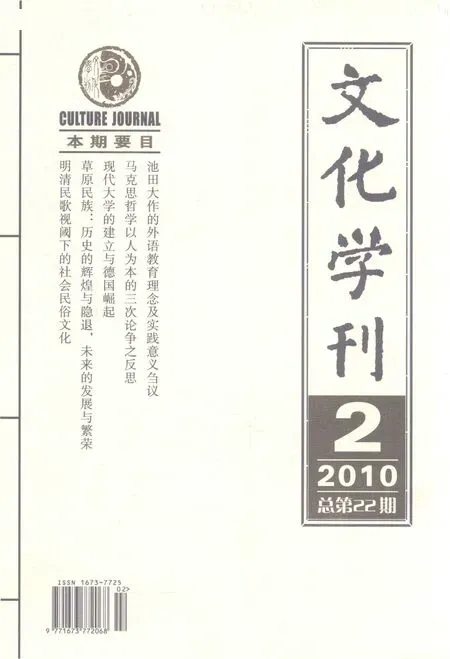《叫魂》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茆晓君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派克没到北京之前就说过:“不住上20年,谈不上写关于中国的书。”孔飞力先生通过一些清史资料与扎实的中文基本功却写下了在美国历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普遍被人们认为起到了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叫魂》。通过独特的视角,将1768年在江南地区盛行的“叫魂”恐慌事件进行了多层次分析,对君主与官僚、地方与中央、当地人与外来者、政治与权术等多重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先生的解读政治是否对现当代有借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叫魂》这部妄揣圣意的书,似乎在解读弘历的忧心、烦心、劳心甚至决心。《叫魂》的问题意识在于: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孔飞力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为美国汉学界“三杰”之一(其余两人为史景迁和魏斐德),主要从事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并参与《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
叫魂者——割辫巫术恐怖一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当时正值国富民强、百业俱兴、“康乾盛世”的乾隆朝鼎盛时期中叶。“叫魂”在国人传统理念中是一个不祥的词汇,与所谓的“迷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叫魂》所要梳理和解析的是发生在176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之为“妖术大恐慌”。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12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帝王、官僚、百姓对之反映不一,而地方乡绅又不愿卷入,于是一场纠葛和博弈在三方中展开。
从石匠贴姓名于木桩的传言、萧山和尚事件、苏州乞丐屈死狱中到胥口镇奇事,看似相互无联系的故事,孔飞力用“叫魂”联系起来,使下层民众与上层权贵受惑于此,这本身暗示社会上存在一个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康乾盛世之下,孔飞力揭示了繁华背后的阴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满汉之间的隔阂、国家对流浪者的失控以及人口的过度增长,对妖术的敌意莫不如说是对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焦虑和担忧。孔飞力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展现了乾隆时代的社会图景,清晰地勾勒出三种社会力量对权力的追逐与争夺,彼此互嵌而分裂,相互依存而背离,每一个行动逻辑背后无不存在悖论。三种力量都在“叫魂”中搏杀,而采用的方式和搏杀的理由却各不相同,目的的多样性导致结果的复杂性。
第一种力量,乾隆本人及其所代表的皇族贵戚。孔飞力开篇道出弘历的孤独与哀怨,高处不胜寒的困境。满族威权在缓慢而平静地消退,弘历意识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谋反和汉化。
在他的脑海中,谋反和汉化是采取一切政治行动的前提和根本,没有什么比维护爱新觉罗的江山更重要。虽然取得江山是非法的,但治理江山要合法;虽然本身权力取得是非正当的,但使用权力和赋予权力要正当。于是,《大清律例》承袭了《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从此“十恶”中可见对于危害帝国的行为,统治者是绝不会心慈手软,“不赦”体现了其决心和威权。从“留发不留头”的野蛮征服到“剪辫”的象征性反抗,可见统治者的嗅觉异常灵敏,既要维护皇族身份的合法性,又要维护征服者精英层本身的凝聚力与活力。统治者既仰慕汉文化的博大,又忌惮汉文化的涵化,于是经济与文化处于鼎盛的江南便站在了风口浪尖,统治者既赞叹又妒忌,既吸引又排斥。弘历究竟是忌惮满人汉化还是官吏腐败,无法言明,两者兼而有之。借助“叫魂”,整饬官吏、威慑江南、阻隔反叛倒是一个好的契机。弘历妄图拉住此马栓来个漂亮转身,于是揪根溯源探明究竟。“叫魂”作为谋叛“剃发”,到底有多少百姓跟从,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百姓对于满族统治到底持何态度,潜伏的反抗力量到底有多大。此外,作为帝国的统治机器,官僚们的工作效率如何,忠诚度如何,官僚制度是否腐朽不堪举步维艰,这也需要“叫魂”契机来检验。
第二种力量,官吏和官僚君主制。弘历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而官员既要营逢取悦皇帝,又要明哲保身,还要防止民众哗变,导致官吏陷入了“做得越少犯错越少”规避风险的窠臼里。克罗齐描述:“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官员要对付的是皇帝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官员的大考无疑是己身的官考政绩,优劣系于3年考绩。常年累月的考绩模式化、样板化,导致官吏之间无法清晰辨别,考评官员则是奉行“话越少越好,描述行为比分析人品更容易搪塞”的原则,致使弘历对常规控制失望,再加上官官相护体系以及权力庇护网络,更让皇帝忧心忡忡。非常规专制权力介入,通过觐见、任命、训斥以及“政治罪”将官员禁锢。于是可以理解官员对于“叫魂”事件的抵制,一则忽视,二则害怕仕途受损,三则耿直而无心迫害无辜,官僚程序阻止了对紧急事件的及时应对。官员们亦步亦趋、如履薄冰面对自上的鞭挞,也诚惶诚恐、百般忌惮处理自下的反抗。“夹心层”的诉求蜕变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第三种力量,平民百姓。德政盛世之下,底层百姓已经出现危机,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初现端倪。“叫魂”者试图通过其行为获得神明的力量来摆脱边缘人的尴尬,那些被社会经济压力挤压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中期望有另外的生存方式。而江南富裕地区的人们却又对外来人产生了恐慌,害怕自己的生活遭到威胁。两种心理导致的行为使“叫魂”扑朔迷离起来。当官府发起对妖术的清剿,“叫魂”却发生变异,成为了普通人的一种唾手可得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提供某种解脱、一块盾牌、成为奖赏、一种补偿、一种力量以及一种乐趣。这也体现百姓对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不利处境的怀疑,随处可见的枉法裁判更使民众对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动摇。
三种力量相互渗透,相互利用。孔飞力以“叫魂”为线索展开历史脉络的梳理,无情地挑开“乾隆盛世”的伪饰,揭示其专制政治深处的严重危机,并且预示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必将一次次引发更为惨烈的社会灾难和更为恐怖的社会疯狂。
令人诧异的是,在此次三方博弈过程中,居然少了地方士绅的力量,孔飞力的解释是在“叫魂”档案中看不到官职文人的身影,于是推测士绅们始终谨慎地置身事外,官方并没有求助于士绅,而他们也不愿自找麻烦去追缉妖术案犯,保护无辜民众,或调解争端。那究竟是不是事实,妖术的恐慌蔓延甚广,乡绅能安然不受影响,这一切是值得疑惑的。皇权与绅权是贯穿中华帝国的两条线,这里只是凸显了皇权的强大,而绅权被挤压。在“叫魂”案中,地方士绅的表现让人诧异,究竟是否如孔飞力所说值得质疑。
孔飞力在完成这部著作时,试图在完成一个超越传统意义的事件史,是一种整体史的体现。运用多学科、多角度看待1768年的事件,通过扎实的历史田野工作,呈现社会全貌。孔飞力在主位和客位中寻求平衡,体现历史的真实性。但是,他所依赖的通讯体系的资料大量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文笔《清实录》、《朱批奏折》等,其间的可信度如何?如何保持客观?值得反思。
孔飞力涉及的“叫魂”显示一种民间信仰,视角是自下而上。与之可作为比较的是王斯福的民间宗教研究,相应的视角也是自下而上。两者的视角是在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之间游走,其实二者的互动是双向而不是单向。孔飞力与王斯福之间共同点是突出民间宗教对于民众的信仰作用,国家力量如何渗透甚至左右民间宗教,这也是值得探讨的地方。
孔飞力通过《叫魂》让阅读者同样体会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恐慌,虽然中华帝国历经千年沧桑,所经历的恐慌不胜枚举,但是像孔先生这么鞭辟入里的分析——从皇权延伸官僚至百姓,一线贯之酣畅淋漓实为不多见。虽然孔先生由于偏爱的原因对于一些材料过分依赖,而对其他材料进行了遮蔽,甚至还渗入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但瑕不掩瑜,《叫魂》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海外汉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