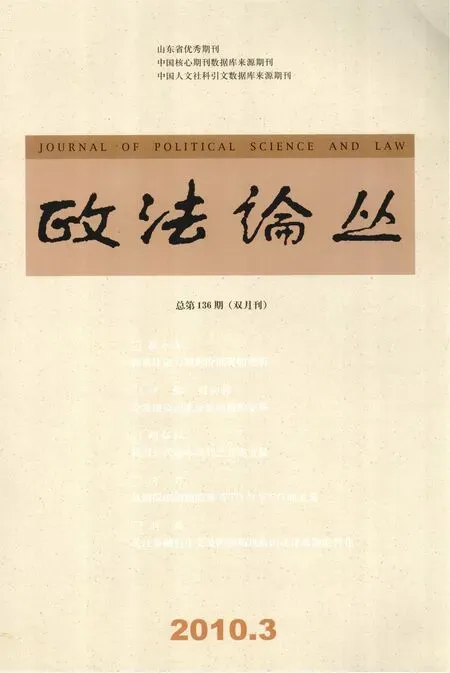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制约与影响
张明敏
(山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山东济南 250011)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制约与影响
张明敏
(山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山东济南 250011)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渗透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表面看来宗教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影响甚微,实际上宗教与传统司法审判制度有着深层的纠葛,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其对司法审判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司法理念层面、法律器物层面。
宗教文化 传统 司法审判制度
宗教作为一种涉及面极广的文化现象,一直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表面上看来宗教信仰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广泛与普遍,宗教对法律影响甚微,在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里,也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明定鬼神的地位。但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实践来看,在中国古代,鬼神力量一直在潜生暗长,鬼神思想深隐藏于法律制度的背后,鬼神信仰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的一种社会现象,法律运行中神灵的影响也一直挥之不去。本文试图从制度层面、理念层面、法律器物层面探讨传统社会中宗教与司法审判制度的深层关联,探究宗教文化对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实践活动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制度层面
(一)“神判”制度
“神判”制度即神明裁判制度,亦称神示证据制度,指借助神力进行审判的一种鬼神定罪的审判方式,它是人类社会早期司法活动中经常采用的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方式。“神判”制度是“天罚”法律思想在司法审判领域中的体现。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的原始社会,就普遍存在着对天地神鬼敬畏与崇拜的观念,先人们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在左右和支配着自己,神会佑护正直无罪者,处罚邪恶之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公共的神被改造,并与王权、君权紧密结合,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统治权和立法权、司法权说成是神的意志,任何触犯现存政权和法律的行为,都被视作悖逆鬼神天帝的元恶大罪,就要受到“天”的惩罚。
神判制度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实践活动的中,或强或弱地显示着其作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神明裁判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夏商时代,司法裁判的主要方式是神明裁判。根据古籍和甲骨卜辞记载,夏商“神判”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神兽定罪,二是卜筮决狱。神兽断案,相传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1]P231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里有一些提到诉讼时要由双方向神灵宣誓的内容,如《甘誓》中启即用“天剿绝其命”、“今予唯恭行天之罚”的旗号来讨伐有扈氏。对其士兵,则用“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2]P249在商代,鬼神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商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商人沉迷于鬼神,他们把鬼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我们从现存的史料就能窥见一斑。《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凡事无不通过占卜向鬼神请示,如战争胜负、官吏任免等。在司法审判领域,定罪量刑也要诉诸鬼神。卜辞有:“兹人井 (刑)不?”占卜是否执行刑罚。“贞其刖”[3],占卜是否处以刖刑。“贞刖百”[4],占卜是否对百人处以刖刑。对处刑的后果也进行卜问:“贞其刖百人死”[5],贞问对一百人是否处以死刑。商代统治者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进行繁琐的占卜,一方面反映出他们敬鬼神的神权思想意识,更深层的方面是利用鬼神麻痹被统治阶级。“敬鬼神畏法令”(《礼记·曲礼上》),一语道破了“神判”的实际用意,“敬鬼神”是为了使人们“畏法令”。统治阶级的法令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后,就可借鬼神之名,“以教民事君”(《国语·周语上》)。进入封建社会后,神意裁判作为一种审判方式虽然已由明确的司法程序所代替,宗教信仰对司法审判制度的影响渐渐归隐幕后,司法官吏一般不会像夏商时那样直接让鬼神介入司法审判,但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神灵的痕迹,神判与人判往往交织在一起。有的司法官吏借助神鬼虫兽助狱断案,依靠祈祷来求鬼神指明侦查方向。《论衡》载,东汉有个叫李子长的司法官吏,为了验证被告说的是否是真情,制作了一个代表被告的木偶,放在芦苇编的筐子里,据说如果被告真有罪,木偶就不会动,如果是无罪的,木偶就会动。[2]P216《晋书》、《折狱龟鉴》等书也记载了不少神鬼断案的事例。至清代,有些偏远的地方还有“神蛇断案”、“沸油裁判”等迷信方式断案的遗迹,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类似这种落后的做法,流传的时间更久。如清人笔记《子不语》载,贵州平越府(今贵州福泉)衙门有个七尺高的石台,衙门里还藏有十六只写着“梵”字的佛经。按当地的惯例,凡有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肯招供的,就请出佛经铺在高台上,要嫌疑人从佛经上滚过去。据传凡无辜者滚过去平安无事,而有罪者滚到一半就会全身抽筋、目瞪身僵。这个习惯从元朝一直延续到清朝。
“神判”制度,使司法实践活动与宗教信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性、协调性,法律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借助宗教的神秘性而得以彰显。但法律实践的客观规律性也被拖进了神秘的偶然性沼泽之中,难以显示法律实践本来的面目和力量。
(二)司法时令制度
司法时令制就是古人的天道观念在司法实践领域最主要的体现。古人认为,在司法活动中,行赏施罚必须顺应天时,合乎时令,否则天将降灾。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则是肃杀蜇藏的季节,人间的司法活动也应与天道相配,顺于四时,利用秋天的肃杀之气强化行刑的严肃与震慑力。《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古之治民,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记载。《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元和二年)秋七月庚子,(章帝)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后汉书·陈宠传》载: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 (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十二月阳气上通,……十三月阳气已至,……若以此时行刑,……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异自为它应,不以改律。”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此后,历代帝王在确定大刑之日,要考虑阴阳节气,唯恐违反时令会给国家带来不利灾害,以秋冬作为行刑决狱的传统时间。《旧唐书·刑法志》记载: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金史·刑法志》记载:(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不待秋后。“顺天行刑”、“刑以秋冬”,成为历代“秋后处决”的依据。自秦汉至明清,历朝都有关于死刑执行时间的明确规定。唐律还把佛、道教的一些教规认可为法律,有关“十直日”的规定即是其中之一。《唐律疏议·断狱》“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规定:“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其中的“禁杀日”就是“十直日”。十直日又称“十斋日”,是佛、道教中有关每月中有十天禁止屠宰牲畜、钓鱼及不准施刑的规定。此条在“疏议”罗列了这些日子,它们是每月中的“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在这些日子内行刑,唐律都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杖六十”进行处罚。唐律还规定: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凡遇有大的祭祀活动、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以及皇帝生日、元夕等法定假日,都不得奏决死刑。凡处决死刑犯人,都不得超过一天中的申时 (约下午三至五时),后世执行死刑的时间都习惯在正午前后。宋明以后基本沿袭不改。
(三)确立城隍的司法审判职能
在古代鬼神谱系里,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城隍了。城隍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是非常著名的阴间司法官,执掌审判世人善恶是非。但城隍神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审判的职能,城隍神在唐以前,尚未被纳入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城隍神成为冥界重要的司法官,大致发生在中晚唐以后。[6]P321唐中叶以后,地方吏治败坏,世间多不平之事,社会民众需要一个具有公平、正直品格的超世俗的“平民化”的神来执掌审判职能。随着城隍信仰在民间的逐渐传播,部分地方官员也开始逐渐增加对城隍的尊敬,城隍地位大幅度提升,世俗权力抓住这一契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城隍信仰。从唐代开始,封建政府将先前自然神性质的城隍神赋以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其监察百官的职能。例如,唐代对城隆神己有封爵之举,五代又陆续加封为王,宋代或加封号,或赐庙额 (匾额),明代更将城隍神与行政机构相配套,清代循而未改。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唯恐地方官吏不为己用,命令新官上任,必先斋宿城隍庙,参拜城隍神,向城神隍宣誓:“我等合府官吏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蠢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官吏还必须到城隍庙两次,申前誓。这类事情肇始于宋代,发展于明代,延续到近代。民国以前知县、知府等地方长官上任时,按照惯例必须到城隍庙参拜宣誓。清代地方官吏在上任前,不仅要向城隍神宣誓,而且还要在城隍庙里住上一夜,聆听城隍神的教训,向城隍神坦露心迹。[7]
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城隍执掌的职能与时俱进,逐渐从掌控阴间司法审判到常驻民间的司法官。①
自元代始,封建官吏便常把一些疑难案件放在城隍庙里审理。至明代,此风更甚。《大明会典》中十分具体地提到:“一府境内人民,倘有仵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摇,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极于城隍,发露其事;如有孝顺父母,……畏惧官府,……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8]P576这就是说,每个府州县都有一个城隍神,若有不孝犯上、奸盗诈骗、欺压良善、躲避官府赋役的不良之徒,必有小神(如土地神、灶神之类)去汇报给城隍,城隍给予惩罚;若有孝顺父母、畏惧官府的良民,小神也会报告给城隍神,城隍神则在阴间保佑这类良民。为了补救法网的疏漏,官吏们对城隍神抱有极大的期望。如清代著名的刑名幕友汪辉祖在遇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案件时,就常到城隍庙焚香黔祷,祈求神助。清代城隍神司法职能的被强化更是登峰造极,见下列案例。[4]《庸闲斋笔记》载:顺治年间,海上强盗侵扰县府,清朝总兵官王憬督战辱师,损兵折将。老百姓聚集一处,骂他无能。王憬闻言大怒,诉之当地姓周的巡抚,诬蔑民众与海寇有勾结。周巡抚以为是真,准备等到夜间鸡叫之后,派兵吏去屠杀那些百姓。这天傍晚,城隍神降至官署,站在阶下,周巡抚恍惚若见。半夜时分,周还没有放弃天亮之前屠戮百姓的打算,结果他又仿佛看见城隍神直视他,撞头数次。这下子可把周吓坏了,终于取消了屠戮百姓的决定。[9]P341
《信征录》载: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县一个姓刘的人平常无恶不作,人们对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天,他忽然自己跪到县衙门,两手自然反背,口称奉县城隍之命前来自首,求县令派人把他押到府城隍庙去问罪。县令以为他患了精神病,让人把他从衙门驱逐出去。然而他转而又来。没有绳子捆绑他的双手,但好几个人都解不开他反背的双手。如此数日,县今只好差人送至府城隍庙。刘氏来到庙前,即跪在台价下面,号呼痛苦,说城隍神在对他施刑。刑毕之后,他站起来又说城隍将他发回本县,游街示众。后来游街完毕之后,他便七窍流血而死尸。《果报类编》载:平湖进士张虎候的儿子,贪狡无赖。看到一户邻居家境富裕,便眼红,想捞一把。他编造谎言,唆使这家和冤家打官司,而自己从中周旋料理,获利百金,得意至极。七月初一,他赴城隍庙烧香,跪在城隍爷神像前,再也站不起来了,感到似乎有人猛击其背,即刻吐血数升。抬到家里之后,他自述作恶之事,并说今日遭到城隍的诛谴。第二天他就一命呜呼了。《新齐谐》载:福建莆田王监生,素来强横乡里。看到张妮的五亩田地与自家田地搭界,便伪造地契,贿赂县令,断为己有。张心中忿然,经常在王家门口斥骂。王监生让人殴杀张妮,然后让其子来看尸体,并当场将其子五花大绑,送往官府,诬告其子杀了母亲,数人作证,屈打成招,拟判凌迟。总督苏昌闻而疑之,乃下令让福州、泉州两知府会审于城隍庙。两知府各有成见,仍照县令所论定罪。其子受绑将出庙门,大叫:“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极枉,而你全无灵响,还有什么面孔享受人们的祭扫!”刚说完,庙的两厢突然倾倒。知府、判官们以为是庙柱年久已朽,不甚介意。等到其子被牵出庙时,两个泥塑皂隶 (城隍神的吏卒)忽然向前移动,两根木棒挡住门,使人不能通过。观者哗然,两知府亦惊然,赶快重新审理,判决“其子冤”,王监生依法处之。[10]175
上述四个案例中,有的是城隍为民伸冤而阻止官吏滥施诛罚,有的是城隍参与刑讯惩治恶人,有的是城隍神在阴间诛杀阳间恶人,有的是城隍督促司法官吏理冤申案的。这都说明了城隍司法审判职能的加强,更说明了鬼神迷信等观念在古代司法活动中占有很大市场。以城隍神监察官吏、在城隍庙里审理案件,这在表面上与早期的神判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仍是试图利用人们畏惧鬼神的心理,从精神上摧垮不法之徒的防线,使其自行招供或露出异常,再按照世俗的法律加以制裁。因此,实质上还是天道鬼神观念在司法审判制度上的贯彻与渗透。
二、司法审判理念层面
关于宗教文化对司法审判理念的影响,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仅是普通民众相信鬼神的存在,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是“敬鬼神而远之”;即使司法官吏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运用了,那也仅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为自己的需要服务。[2]P248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鬼神的,很多司法官吏并不是装神弄鬼,而是内心里真相信鬼神的存在。因此,在古代很多司法官吏的具体司法活动中,鬼神仍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鬼神的敬畏态度始终贯穿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如断案如神的北宋包拯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就利用人们对鬼神的敬畏装神弄鬼地把犯罪嫌疑人的胆给下破了而尽吐实话,从而获得断案的证据;清代著名县令蓝鼎元在城隍庙中利用城隍的威严而破大案。长期以来,天道鬼神观念潜在地左右着司法官的心理,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司法理念,这成为古代司法审判活动的文化根基。在中国,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影响较大的两个宗教是道教与佛教。
(一)道教的“善恶承负”观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中华民族心理特质的形成、影响是其他宗教所不可及的。“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11]道教把传统的福孽报应观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把“天道承负、现世因果报应”理论定为其教义。“天道循环,善恶承负”②这一教义,原始道教已加载《太平经》。如《太平经》卷九十二中说:承负之责最剧,故使人死善恶不复分别也,大咎在此。又说:如此言,为善复何益邪?为恶何伤乎哉?力行善,复何功邪?岂不是抹煞善恶,不能劝善规过.扬善止恶了吗?因而认为承负之说是反乱天道之辞,为天地所不喜悦,提出应以现世之善恶报应为教义。认为吉凶福祸乃是个人行为善恶的必然报应。《太平经》卷一百中说: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以类相呼,不失其身。天道无私,但行之所致。卷一百一中说:善者自兴,恶者自败。观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从其类,毛发之间,无有过差。认为上有日月照察,身中有心神与天音声相闻,有诸神疏记人的善恶,过无大小,天皆知之,到了一定的时候,天便校其善恶,予以赏罚。《太平经》卷一百十二说:得善应善,善自相称举,得恶应恶,恶自相从。……务道求善,增年益寿,亦可长生。……天责人过,鬼神为使……罚恶赏善人所知,何不自改。天报有功,不与无德。《老子想尔注》中也说: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也。不能积善行,精气自然与天不亲,生死之际,天不知也,死便真死,属地官去也。如能积善功,则精神与天通,设欲侵害者,天即救之。可以复生而长生仙寿。天上之神对善者则赐福、增寿,对恶者则降灾、减寿,还要把他的鬼魂下入黄泉,打入地狱。
道教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影响,可谓无所不至,无处不在,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庶民百姓,都受到了道教濡染,渗透入中国人思想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入中华民族心理的岩层,成为中国民族心理的一种特质。道教影响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为上层统治集团提供精神支柱。③二是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栖息地。④三是道教对于民间信仰有直接而深广的影响。许多中国人虽然没有加入道教,但对道教系统整理过的鬼神谱系却是虔诚信奉的,而且不管是哪种神仙,都可以和谐地并存在一起信奉。在许多地方,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甚至其他各种天王、罗汉、牛头马面、关公财神都可以并排放在一起祭拜,甚至各行各业都有其保护神,对着神灵不能做亏心之事,这个传统演化到司法文化中就叫“神道设教”。正是因道教具有这种广泛的上层和下层社会基础,鬼神信仰就成为中华法系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应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活动中也就不足为怪了。如在民间流传极广的《功过格》,本是道士发明、使用的,用以推进鬼神精神在民间的传播。但当它不断地与民众生活相交汇的时候,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浓厚的宗教色彩变淡,而适应民众心理需要的伦理道德性增强。
(二)佛教的“因果轮回”说与地狱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业”、“业报”等抽象教义,中国普通百姓并不懂,但经过中国化改造后,佛教的“因果轮回说”与中国古代本土宗教文化中的这种“天道承负、善恶报应观”的观念结合起来,更是深入人心。人们认为死后有鬼神存在,除作恶多端者下十八层地狱之外,一般人都会重新转世为人。但是如果那人是死于非命,并且其冤仇又未获得昭雪,则会成为孤魂野鬼,冤仇未报之前无法投生,只会在大地上游荡,有时会引起天地失衡,出现一些异常现象。“善恶报应”观进一步融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民间俗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写照。人们在这一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若被冤死,死者将会冤魂不散,不得超生,进而会对审理案件的官员进行寻仇的法律理念。⑤
(三)善恶报应观潜在地左右着司法审判理念
道教“善恶承负观”、“佛教的因果轮回说”与儒家的“天道福善淫祸”交融在一起而形成的善恶报应观念深入到民俗信仰和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当中,并产生了广泛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司法官吏相信如果因其审判工作失误,而误杀无辜,会破坏和谐秩序,引起天谴。司法官吏为有善报、福延子孙,避免祸及后世,往往以救生为阴德,在司法审判上,往往对罪犯宽肴开脱,并以怀有阴德自许。北魏时的高允就常对人说:我在中书做官时曾积有阴德,济救民命,如果阴报不差,我便可以长命百岁。[2]P167司法官吏因存在这种惧怕福孽相报的心理,一般都能谨慎办案,尤其在办理死刑案件时要比其他案件付出更多的谨慎,主张多做善事。所谓的善事是一个模糊概念,不杀生、不害人是最基本的要求,司法官吏判人刑罚,打人杀人,在传统观念上就是损阴德,不是现世折寿,就是来世报应,或者于仕途有累,或者对子孙不利。司法官吏认为宽恕罪犯是一种“善行”,多存活人命,就是为自己积累阴德,会有福报;而执法严苛、滥杀无辜是造孽行为,必有恶报。不仅司法官吏会得到报应,就是帮助司法官起草判词的幕友也同样得到报应。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讲:幕友虽没有官的身份,却暗中有官的权力,报应更为明显。清代著名的幕友汪辉祖在他的《佐治药言》中列举了很多的事例来说明因果报应的必然性,反复强调说“求生”是“千古法家要诀”。这样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每个官吏在案件审理中的态度。这点可以从古代官员对于出任刑名相关职务时的态度上得以验证。此方面最典行的代表就是清代著名的刑名幕友汪辉祖父子,他父亲当年在作绍兴师爷时犹豫万分,最后还是怕“损德”而不敢作刑名幕友。汪辉祖年轻时立志作幕,其母亲以家族三世单传加以劝阻。后来汪辉祖得中进士,三个儿子都有功名,自以为就是佐官裁判时的积德报应。这种文化上的制约对于讲求“实用理性”的中国古人来说,尤其在死刑适用上是具有相当约束力的。[12]汪辉祖在长达二十六年、历经十六个州县的作幕经历中,只处理过六个死刑案件,自己认为积下阴德不少。
这种因果福报的观念,虽然对促使司法官吏认真办理案件、限制枉法滥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成为封建司法官吏为罪犯开脱罪责、放纵罪犯的托词,往往造成“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以幸免”的后果,对古代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不良影响。
三、法律器物层面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有些符号与仪式,真实再现了宗教文化对司法审判制度的侵蚀与风化。
(一)獬豸
从神判中走来的神兽“獬豸”。⑥由于能分辨是非,决诉讼,遂成了中国古代法官的代称,如同龙象征着皇帝、凤象征着皇后一样,獬豸则象征着威严的法官,獬豸冠更成了法官的代名词。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獬豸的形象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早期的獬豸似牛、羊、猪等家畜,到了中晚期则象虎、豹、狮等猛兽,但它无论怎样变化,其头顶上那支突出的并用来抵触邪恶的锐角,却仍然是它最大的特征。《后汉书·舆服志下》载:“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因此至少从战国以后,“獬豸”一直就是中国法律的象征。秦灭楚国后,秦王将该冠赐给御史佩戴,遂称为“獬豸冠”。在汉代,专门主持纠察之职的御史所戴的帽子,也被称为“獬豸冠”。如《后汉书·舆服志下》载:“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唐宋时期,凡是执法官员所戴的官帽都称“獬豸冠”,号为“法冠”,象征着明察秋毫的獬豸神兽。唐代诗人岑参曾有“闻欲朝龙阙,应须拂豸冠”的描写。至明代,以獬豸图案饰执法官公服已十分多见。到了清代,御史及按察使的官服前后都绣有獬豸图案。直到现代社会,习惯上仍然以獬豸的形象作为法律的象征。
(二)州县衙门的布置及设施——折射出宗教文化的魅影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试图反作用于人的精神或意识,都必须有其物化的形式作为载体,如宗教的庙宇。衙门是司法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司法权正是在衙门中得到运行的。法庭及其设施的配置无不反映司法精神的必要的外化效果,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痕迹,使司法审判制度的内涵能为人所感知。虽然司法活动的神圣性没像宗教那么纯粹,然而司法活动场所及空间布置却表露出“神明裁判”隐喻下的世俗遗留,衙门的建筑结构、衙门中的设施彰显一定的文化气息与内涵。
曾在清朝州县衙门担任过刑名幕友的陈天锡先生以湖南麻阳县署为例,谈及衙署的主要建筑及陈设:“署坐北朝南,大门前有一道照壁,画一只四脚兽,其名谐音如‘贪’意思是警戒做官的不可贪婪。……。由辕门进来,正中是大门。大门有三个,一个正门和两个侧门,都是长方形两扇,画着门神。……,仪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正中有一个牌坊,横额写着‘尔体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相传是宋太宗所制的戒石铭,命令郡县立石堂前以资警惕。也有人说是宋代黄庭坚做太守时所说的话,天下州县都照此立坊。……,地板上铺着蔑席,意思是坐这暖阁的主官办事要凭良心,否则便要‘天诛地灭’,这是何等严厉的警惕。[13]作为司法场域的大堂 (这是州县衙门最为重要的办公地点)正中悬挂“明镜高悬”的匾额,堂前有一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这就是说,天意和人心,国家和百姓,都是县官必须持正平衡的东西。
古代社会衙门的设置、布局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无论是画的四角兽、门神,还是楹联中的“天”字以及悬挂着的“明镜高悬”的匾额,无不渗透着宗教文化的意蕴。门神系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司门之神,⑦旧时人们都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是民间最受人们欢迎的保护神之一。道教因袭这种信仰,将门神纳入神系,加以祀奉。《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皆有“门”、“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可见自先秦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崇拜门神。门神因其张贴在古时司法活动的主要场所——衙门,因而也就具有新的文化意蕴。“镜”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具备神秘色彩,而仅仅限于映照物象的实用器物,是后来文人赋予其“殷鉴”、“戒鉴”之意;但道家则从庄子以降,就赋予“镜”神秘化、咒术化,乃至视为神灵的思想。⑧尤其从唐代开始,“镜”的文化涵义更为丰富,唐代道士曾根据教理教义设计出许多道教铜镜,最著名的是天照、地照、人照三件道教大镜。[14]佛教的经书《佛说十王经》所说的“业镜”的功能主要是指在冥间罪人被定罪后,经常会心里不服,于是幽冥世界的审判主、诸鬼中的大王——阎罗王就会以“业镜”让他们各自观看自己所造的罪业。伯 2003《佛说十王经》:破斋毁戒煞猪鸡,业镜照然报不虚;若造此经兼画像,阎王判放罪消除。五七阎王息诤声,罪人心恨未甘情;策发仰头看业镜,始知先世事分明。佛教“业镜”遂成为阴间判官手中彰显罪人罪恶的工具。镜子成为法文化中具有高度象征意涵的一个器物。古代衙门上方悬挂着的“明镜高悬”的匾额,就是把镜子作为彰显罪恶的工具,期待法官判案能像“明镜”一样的高悬,让善恶清楚,无所盾形。类似这样将“名镜”转化为法律用语,也出现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法制文书中,如《后周显德五年 (958)押衙安员近等牒稿五件》有“伏乞令公鸿造,高悬志镜,鉴照贫流”语;又《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牒稿二件》有“伏望大王高悬惠镜,照祭 (察)贫儿”语。⑧庶民已经期待司法官员能明镜高悬,以明是非,申理冤屈。敦煌出土的《佛说十王经》出现在唐末五代,这里的两件文书,时间在五代宋初,恐怕“明镜高悬”的法律用语,也受到《佛说十王经》“业镜”观念的影响,[6]P329,与“业镜”思想的传播有关系,是冥府“业镜”的世俗化。“业镜”以其意像对后代法文化产生深刻影响,“镜”成为法文化中具有高度象征意涵的一个器物,“明镜高悬”成为高挂衙门的法宝,在朗朗乾坤中,使一切罪恶无所遁行。
四、结语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影响与渗透,宜从历史的视角客观地评价。
(一)宗教沦为辅助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实施的工具
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要服务于实现法律的终极目的——稳定社会统治秩序,而不是实现法律本身。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的,当然就可以采用各钟手段,包括宗教。在民间具有深厚影响的神鬼信仰就成为首选,宗教也就被司法所利用了。在原始宗教信仰时期,那时人的理性不发达,认识能力终究有限,在科技、取证技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当无法判断曲直又担心枉纵罪犯,只能通过一些唯心的办法来加以补充,用神灵来断案,也不失为一个无耐的却也庶几可行的办法。因此可以说,早期的“神判”制度其实就是古人用神灵无限的理性认识能力来弥补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反映。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就异化了,宗教信仰与司法审判制度互为表里,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给司法审判制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宗教沦为统治者驭民的工具,“人惟神佑,神实人依”,直接地道出了人神的相互为用。例如,古代社会司法官吏借助城隍参与司法审判就说明,随着城隍信仰的发展,城隍神格日趋重要后,世俗权力推波助澜,充分利用民间信仰,城隍成为常住民间的阴间司法审判官。人们的宗教信仰沦为工具后,人们对法律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法律信仰被宗教信仰边缘化了,我们的神道设教除了灌输给苍生黎民一点善恶观和“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畏惧感外,终究难以培养他们对于法律与程序的神圣感,这与西方宗教教义对法律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培养了西方人对法律神圣性的信仰。
(二)宗教文化对传统司法审判理念的侵蚀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审判制度的侵蚀,不只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思想层面上,对司法官员及普通民众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官员们很忌讳被人称为“酷吏”,为积阴德往往对罪人减轻处罚。《名公书判清明集》就记录了大多数案件的处刑都要轻于法律的规定,官员们在判书往往以“姑且从轻发落”、“姑寄竹篦一顿”等语句,减轻判处的刑罚。《幕学举要》(清)就说:“古今清官子孙或多不振”就是因为处事刻薄,有损阴德而得到的报应。[2]P232宗教信仰中的报应观念,严重地侵蚀了司法官吏必须依法断案的司法理念,这虽对于缓解法律的严酷性具有作用,但官员们对报应的畏惧超过了对法律的畏惧,司法与执法时斤斤于自己的“福孽之报”,对于法律公正与程序正义就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南宋的大儒朱熹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说:“现在的司法官员都被福报之说所迷惑,喜欢出人罪以求福报,该处死的改判流配,该流配的减为徒刑,该徒刑的减为杖刑,该判刑的减为笞刑。罪人免于处罚,就不能保护好人,实际上这样做正好是在做恶事,难道还会有什么福报吗?”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由于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及官场的腐败,激起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人们又无可奈何,只好借用鬼神的力量予以抨击现实,以化解心中的怨气与苦闷,反映出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追求,明确司法责任的美好愿望和朴素心理。但普通百姓遵守法律的动力也往往源于这个福孽报应的观念,这种观念摧毁了人们对法的敬畏惧,腐蚀了人们的法律意识,成为人们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一种很好的解脱之法,反正冥冥之中的报应终归会替人们实现公平。法律权威何以确立?
注释:
① 朱元璋对城陛神的封号已做了最简洁扼要的回答:“鉴国司民”(明初各级城煌神前面都要加上这四个字),用死鬼来治活人,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一大发明。此句话参见张勇:《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第 107页,中国政法大学 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太平经》卷卅九说:然,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前人有过失,由后人来承受其过责;前人有负于后人,后人是无辜受过,这叩承负。换句话说,即前人惹祸,后人遭殃;如果是善的话,则是前人种树,后人遮荫。正是因为有这种由天道所决定的承负,所以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使人从是常冤,蒙受无辜的苦难。
③ 统治者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总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办法之一就是神化自己的统治,使人们觉得皇权天授,不容质疑;另一方面,统治者总想安享荣华富贵,但生命短暂,转瞬即逝,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使生命得以延长,甚至长生不死。这两种思想取向,在道教中都可以得到满足。于是,道教成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精神支柱。唐高宗追封老子地建玄元皇帝庙,以先祖陪祀;妃嫔公主多信道教,受金仙玉真等封号 (如杨玉环等)。这些举措,一方面是借道教神威巩固皇权,另一方面是借以满足个人的精神追求。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以及一大批重臣名士,都是因为想长生不死,误吃道士丹药中毒而早死的。但百死而不悔,悲剧照样继续演下去。宋真宗另设一道教尊神赵元朗,作为赵宋的始祖,给皇室涂上神圣光彩。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奉道极虔。明代诸帝以嘉靖佞道最甚,他长年潜居深宫,日事斋醮、炼丹和服食,得宠大臣须能写青词(祷告表文),道教成了嘉靖皇帝的主要精神慰藉。
④ 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其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不死;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尸解成仙,不必等到死后才灵魂超度;它注重的是现世的幸福,主张人要活得适意、洒脱,超尘脱俗,高雅飘逸。道教的这些思想向度,很迎合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失意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便亟需一个道教这样的栖息地,所以,很多文人士大夫都信奉道教。如王勃便“常学仙经,博涉道记”(《游山庙序》),常常叹息“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梦见自己成了仙人(《忽梦游仙》);卢照邻则“学道于东门山精舍”,还到处乞讨银两和药石来炼丹(《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值书》);李白更是“清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游泰山》六首),连做梦都想着羽化飞升:“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就连白居易,也曾炼铅烧汞,学制金丹。为什么文人士大夫会对求道炼丹如此热衷呢?这是因为,他们对尘世充满眷念而又深感失望,在这种进退维谷之中,道教那种既能免除生老寿夭之苦,又能安享尘世之乐,既能满足心中情欲,又能活得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弥漫开来,使他们的灵魂能够得一些安适,所以他们皈依了道教。
⑤ 在我国流传甚广《聊斋志异》中很多鬼怪故事就可以说明报应观念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
⑥ 獬豸,又名独角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似羊非羊、似牛非牛的神兽,具有能分辨是非、判断正误的特异功能。《说文》云:“獬豸,兽也,似山羊,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后汉书》载:“獬豸,神羊,能别曲直。”相传,在原始社会末期,尧、舜时代的法官皋陶,最早开始用獬豸参加断案。遇到难以解决的案件时,就将獬豸牵到当事者的面前,獬豸用角抵触的一方就是有罪者。
⑦ 门神二字最早见于《礼记·丧服大记》。郑玄注:“释菜,礼门神也。”就是说在唐之前已有敬门神之俗,桃符上有神像以驱邪之俗也早在唐代以前就形成了。但经过唐代,门神的内容和形式有了丰富和完善。到五代,桃符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向春联演变,门神方获得独立地位。宋代,除夕之夜宫中仍有扮门神驱鬼的习俗,而在民间则悬挂门神像。百岁寓翁《枫窗小牍·下》云:“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东京梦华录》也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足见宋代春节悬挂门神之盛。
⑧ 有关道家对于“镜”所赋予的神秘思想,参看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7卷“宗教思想”,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 386-445页。
[1] [汉]王充.论衡·是应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 郭建.獬豸的投影——中国的法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6.
[3] 图 3[J].考古,1973,2.
[4] 图 8[J].考古,1973,2.
[5] 图 9[J].考古,1973,2.
[6] 陈登武.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从人世间到幽冥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 张勇.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8] 大明会典卷八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 [清]陈其之.庸闲斋笔记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1] 李养正.谈谈道教的几点特征,道教与传统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胡兴东,刘婷婷.中国古代死刑适用机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3.
[13] 张伟仁.清朝地方司法——陈天锡先生访问记[J].食货月刊,6.
[14] 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J].唐研究,2000,6.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Judicial Trial System of Religion Culture
Zhang M ing-m in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Shandong Province of the Committee for Internal and JudicialAffairs, Jinan Shandong 250011)
Itwas unquestioned that the religion culture restricted and influenced on chinese tradtional judicial trial system.Religion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trial system,but in fact it had deep issue with traditional trial system.The influence of the religion culture on judicial trial system embodied from the side of system,judicial ideology and legal tools.
the religion culture;tradition;judicial trial system
词】DF08
A
(责任编辑:唐艳秋)
1002—6274(2010)03—100—08
张明敏(1972-),女,山东潍坊人,历史学博士,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公务员,研究方向为立法学、法律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