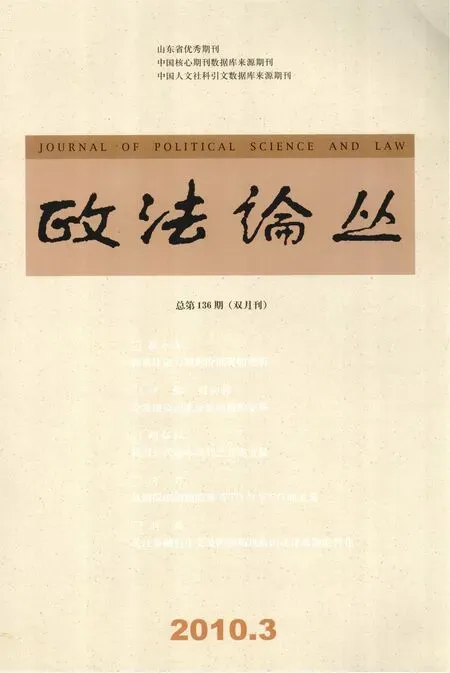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立宪发展*
胡弘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立宪发展*
胡弘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一个国家对基本权利采用何种立宪形式往往同该国的历史积淀、立宪的人文背景、当时的权利意识存在极大的关联。纵观基本权利在我国历部宪法中的发展,可以发现宪法对公民权利趋于全面规定、宪法对个人权利空前重视、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上防御性的规定模式形成、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国家义务被强调。为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价值得到实现,在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模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宪法不断确认权利的传统思维、强化国家义务、提供公民权利的救济原则和基本途径、明确公民权利受限制等等。如此才符合国家追求法治状态的价值目标、符合立宪规律。
基本权利 立宪 防御性 国家义务
在法学界,权利一词备受争议。在宪法学研究领域中,“基本权利”也并无统一认识。甚至在某些时候,学者们会混淆使用“基本权利”、“公民权利”、“宪法权利”等词汇。①本文采用基本权利一词纯粹是基于文本分析的角度,因为我国四部宪法均明确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章节的标题。自宪法诞生之日,公民的基本权利便成为宪法的一个基本范畴。权利立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628年英国的《权利请愿书》,该文件首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权利的至高地位。1789年法国《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发出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的号角始终回荡在历史的空间。后世很多国家的宪法纷纷以不同的形式描述了权利的宪法保护。荷兰教授亨利·范和格尔·范通过比较分析 1976年前的 142部宪法,发现其中的 128部宪法使用了“公民权、人权、政治权利、基本权利或个人权利”这些词或类似的词,而剩余的 14部宪法没有使用这些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包括公民权利的规定。[1]P135作为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最基本关系的宪法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包含着公民基本权利。
一个国家对基本权利采用采用何种立宪形式往往同该国的历史积淀、立宪的人文背景、当时的权利意识存在极大的关联。宪法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基本权利的立宪规律或者原则也逐步显现。本文试以新中国的宪法文本为例,梳理基本权利在我国的立宪演变,探讨基本权利在我国历部宪法发展中的特点,旨在寻求权利与宪法的基本关系规律,关注基本权利的立宪形式对公民的保护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宪法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提供良好的参考。
一、《共同纲领》的权利规定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称《共同纲领》)虽然不是一部正式宪法,但对于新中国而言却是一部划时代的文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该部宪法性文件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可从规定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考察。
在规定的内容上,《共同纲领》确认了“人民”②的如下权利:(1)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 4条);(2)自由: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的自由 (第 5条);(3)平等权:男女平等 (第 6条)、民族平等 (第 8条);(4)控告权 (第 19条);(5)烈士、军人家属生活优待权(第 25条)。
在权利规定的形式上,概括而言,《共同纲领》对人民权利的规定主要有以下特点:
1.权利较为集中地规定在总纲之中。《共同纲领》没有开辟独立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而是在“总纲”规定国家性质、国家任务之余以相对集中的条文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以及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在其他章节里规定制度时附带性地规定了相关权利,如“政权机关”一章里规定人民控告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军事制度”一章里规定烈属军属的物质帮助权等等。
2.国家主动保护地位被强化,条文极具政策性。《共同纲领》有四章直接以政策为标题,而且在具体内容上更注重政权的力量而不是法律的力量。如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第 25条:“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第 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共和国初期的宪法更多是“一个国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突出政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共同纲领》在权利分类上并无过多考虑,③如人身自由、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等皆无明确的条款对应。它十分重视人民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不仅权利的主体需要以人民这一政治概念来指称,甚至人民与国民的差异也较多地体现在政治权利的差异上。④在这个意义上,将《共同纲领》定性为政治法也不为过。
总体而言,《共同纲领》所确认的权利呈现出集中性与分散性相结合、普遍性权利与特殊性权利相结合等特点。它所规范的内容为以后出台的宪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尽管在结构体例上后来的宪法做了重大变化。
二、四部宪法的条文比较
从形式结构而言,1954年宪法以全新的面貌宣告了中国的宪政时代。⑤它以“宪法”为名,明确“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单独的章节,自此“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获得独立的宪法地位。但 1975年宪法却对权利义务一章作了大幅度的删减,它不仅将义务放在权利之前规定,而且简化权利规定,也不再对应性地规定国家义务。1978年宪法有延续 1954年宪法的痕迹。1982年宪法则旗帜鲜明地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至“国家机构”之前“总纲”之后,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延伸,同时也意味着公民地位的提高。在条文总数上,四部宪法也有不同。1954年宪法有 15条规定权利,4条规定义务;1975年宪法有 3条权利,1条义务;1978年宪法则有 12条权利,4条义务;1982年宪法有 18条权利,6条义务。宪法对权利规定的形式结构表明公民权利日益受到重视,“宪法作为权利保障书”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从权利的内容来看,试分述如下:
(一)在权利的原则方面
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1975年和 1978年宪法则完全删除了这一规定,仅明示了男女之间的平等,1982年则科学的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直接道明平等的前提,避免了立法上是否平等的追问。当然,当我们更强调实质的平等时,是否需要牺牲形式的平等呢?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矫正形式平等以追求实质平等?如何平衡这一点,仍是我们现实孜孜以求的境界。
(二)在政治权利方面
四部宪法均将此作为重点。宪法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组织规则和活动规则,对于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权利、以及行使该参与权的基本原则通常都有较为突出的要求。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四部宪法均强调在我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共同的有两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十八周岁。第三个条件“没有被依法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 1982年宪法中有所改变,即表达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显然“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较“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这一变化主要缘于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明确赋予了法院可以判处的一种刑罚——剥夺政治权利。⑥另外,1954年宪法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在选民之外,后面三部宪法都纠正了这一规定。
2.六项民主自由。1982年宪法和 1954年宪法规定相似,均点明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不同的是 1954年宪法从国家义务的角度多了一句规定即“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完整地体现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对应关系。
1975年宪法和 1978年的宪法除了此六项民主自由外,还将“通信自由”并列在前述六项自由之中。这种并列可有三种解释:一是根据当下通识的中国宪法学理解,这种并列是将通信视为一项民主自由;二是从普遍的人身人格权利的角度,通信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等等均是个人的思想、行动的自由;三是笼统地将其视为自由,并不划分权利类别。
1975年宪法和 1978年宪法的共同点还在于均规定了“罢工”自由,但此后 1982年宪法却取消这一规定。1982年 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对修改稿作说明时指出:由于工人同国家的利益一致,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2]P667尽管这种解释在当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针对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多种经济形式中工人维护自身权利可能出现的多种复杂情形,罢工自由也再次被讨论。⑦
1975年宪法和 1978年宪法还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加以确认。不同的是,1975年宪法是在“总纲”中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而1978年宪法则将之规定在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中,但在内容上仍未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所幸的是,1980年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修宪决议,取消了这一规定。[3]P103
3.个人监督权。公民所享有的个人监督权是指公民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方面的监督权利。1954年宪法确认了控告权 (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和取得赔偿权;1975年宪法规定了控告权(书面形式);1978年宪法规定了控告权和申诉权;直至 1982年宪法才较为全面地确认了批评和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取得国家赔偿权。
(三)在个人的人身、人格权方面
在人身、人格权方面,四部宪法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历经由笼统到明确、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但是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⑧。
1.个人的精神自由。精神自由是一个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思维和判断的自由,不受干涉地持有、接受和交流思想、见解或观点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在我国,宪法仅规定其中的宗教信仰自由。1954年宪法和 1982年宪法均笼统地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75年宪法和 1978年宪法则更加确切地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直接以规范的方式明确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更多是依赖学理解释,即“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有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也有不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等五个方面。
与以往宪法不同的是,1982年宪法还以“不得强制”、“不得歧视”、“不得利用”、“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等禁止性规范界定宗教信仰自由的范围和限度,体现了权利自由的相对性。同时,该部宪法将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由思想扩展到宗教活动、宗教事务,为正确领会宗教信仰自由、制定相关宗教方面的法律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2.人身自由。四部宪法均强调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由于 1975年宪法取消了检察机关的设置,所以其规定为“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国家机构设置上的混乱带来的自由保护措施上的不同。其他三部宪法则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由于1982年宪法中设置的国家机构较为完备,所以该宪法也明文增加了规定,逮捕“由公安机关执行”。同时还列举数项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并加以明文禁止,如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搜查公民身体。2000年的《立法法》更是以明确的条文排除了非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法律不得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措施的规定,延伸了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
3.人格权。个人独立人格的尊重意识在 1954、1975、1978年三部宪法中均无反映,直到 1982年宪法制定时才得到集中体现,该部宪法庄严宣告: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权利是不断被认知和发现的。这一条款得之不易,可以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严重践踏人权的惨痛教训换来的。
4.人身移动、人的私立空间的自由。四部宪法均不约而同地规定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尊重物化的私立空间。1982年宪法除了防御性的规定外,对可能较为常见发生的侵犯公民住宅的行为进行突出的禁止性规定,如“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公民“居住、迁徙”自由仅在 1954年宪法出现,直到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加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人身的地域依附性受到较多的理论抨击,公民的迁徙自由入宪又被重提。⑨与之相应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也一再被重议。⑩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实质上是一个人私立空间的延伸,是指公民自由地与他人交往以及通信受到法律保护。1982年宪法更多地是将其视为个人人身人格权利的内容,对此作了全面规定,并规定了除外条款,即因为“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有权对通信进行检查。
(四)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
对于公民财产权,四部宪法比较一致地均将之规定在宪法“总纲”之中,作为经济制度的范畴之一。但是需要指出一个细节,1954、1975、1978年三部宪法在规定国家保护公民财产权时明确其范围是生活资料,(11)1982年的宪法则仅仅指出是“合法财产”,并没有做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之分,通常学理解释我国宪法所保护的合法财产是指生活资料,但是却未能给出充分的理由。
公民的劳动权、劳动者的休息权在四部宪法中有着较为一致的规定。作为社会主义宪法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同样的,在关于物质帮助权上,除了 1982年宪法规定物质帮助权的享有主体是“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的”公民外,其余三部宪法均确认的主体是“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的”劳动者。劳动者权利保护至 1982年宪法表现得更为全面,如退休制度的确立等。而社会保障的权利保护意识 1978年宪法有所体现,至 2004年宪法修改时才予以贯彻直接表现为“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公民的受教育权也同样是在四部宪法中均有规定。对其他文化权利 1975年宪法规定得较为狭隘,只字未提公民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其余三部均有规定。
(五)其他权利
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权利的类型无外乎政治权利、人身人格权以及经济文化社会权利,所谓其他权利主要是指特定主体的权利,主要有三种情形:
1.四部宪法毫无例外地一致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1982年宪法更是以禁止性规定强化对此的保护,专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2.1954年、1975年宪法均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1978年宪法则增加了侨眷的正当权益,而只有 1982年相当精确地表述为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种规定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华侨居住在国外,所保护的权利若为“合法”的权利,则容易为合“哪国”之法产生纠纷,归侨和侨眷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3.前三部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章中均含外国人的政治避难权。1982年宪法基于逻辑原因将之从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章节剔除放置于总纲的最后一条,符合我国宪法关于“公民”一词的界定。
三、基本权利立宪发展之特点
自从有了宪法,基本权利就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或在总纲中体现,或直接表现为专门的章节。从 1949年《共同纲领》到 1982年宪法,我国宪法共有三次全面修改、两次部分修改,1982年宪法作为现行宪法又经历了 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部分修改。总体看来,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立宪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宪法对公民权利趋于全面规定
这种全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利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对象;二是权利的属性;三是权利的内容。现行宪法首先弥补式地给予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公民以内涵,使得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宪法规定更为完整。因为“公民”一词首次出现在1954年宪法时没有任何解释和界定。其次,现行宪法也强调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即“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从规范上宣布了权利义务的相互依存这一法理属性。权利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如前所述,四部宪法在权利规定上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其形式上。而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权”第一次成为正式的宪法语言。“人权”入宪可以防止由于宪法明文列举权利带来的弊端,权利的内容可以因人权一词而得以不断延伸,同时也可使国家在与西方人权对话中不再处于言语上的被动局面。除此之外,宪法对具体权利的认知也越来越丰富,比如说宗教信仰自由不仅包括思想上的表现还有仪式活动的内容;物质帮助权还衍化出社会保障权、退休保障权等等。从最初的人民权利到公民权利再到人权,权利主体的范围一再扩大。从一一明确权利的具体形态到概括式的规定,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宪法在权利主体以及权利范围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权利规定模式上的确认思维没有改变,对未明确的权利保护力度还很弱。政策性修宪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权利规定上的家长思维。当权利变成某项制度的附属品,权利对抗国家权力的特性无法彰显,相反权利的实现却要依赖于国家权力。这种家长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
(二)个人权利得以回归
有学者认为“不同时代立宪的基点和重点各不相同,它经历了人权立宪——政治立宪——经济立宪的漫长过程,并正向知识立宪过渡”,[4]P278体现了立宪规律。而所谓的政治立宪主要是指“立宪的重心从传统的人权保障转移到政治自由上,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和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4]P282这里权且不讨论立宪规律的科学与否,但是可以断定我国公民权利的宪法发展并不适用于这一规律。因为我国宪法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公民的政治权利,强调公民中的人民为主人的一切权利甚至包括义务。(12)在新中国最初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参与非常重要,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确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政治国家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基础,也是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所在。此后的历部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视始终没有游移过。
与之对照的是,公民作为个人的权利逐步被发现、渐渐被确认。如 1975年宪法第一次出现“个人”,强调一个“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再如人格尊严的保护是在 1982年宪法中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除了人的身体上的自由,对于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仍然鲜有规定。2004年宪法修改增加“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彰显我国宪法回归到“人权立宪”。“人权就其本质来说是人性的政治要求,充分发展人性是全人类的永恒价值,这种价值在政治上体现为不断实现人权。”[5]P106公民个体的地位得到空前重视。
我们还饶有兴趣地发现前社会主义国家新、旧宪法关于各类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顺序上有很大调整:原有宪法一般是按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而现行宪法则是先规定个人权利,后规定政治权利,再规定社会权利。[6]P444或许这也是个人权利回归的必然体现。
(三)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上防御性的规定模式形成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从最初主要采用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性规范,偏重于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保障功能,转变为重视对国家强权的防御性规范。防御性的规定侧重强调权利本身的不可侵犯性,以防御来自国家、团体或其他个体的非法侵害。它不同于直接保护模式,强调权利的被保护性。当然如果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13)的话,那么防御性模式主要是适用于消极权利。如我国宪法在人身人格权上更强调其防御性,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等三项权利是以“不受侵犯”这种防御性的方式表达了自由的范围。它排除了一切侵犯的可能性,抵御来自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的一切可能的非法干涉。这种规定模式相比那种规定国家保护的模式而言更加具有保护力度,更加体现权利为中心的宪法语言,契合宪法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符合世界各国宪法的权利规定模式。
(四)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国家义务被强调
在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规定上,除 1975年宪法外,其余三部宪法均坚持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义务相结合的规定原则。公民的劳动权与国家劳动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与国家发展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物质帮助权同国家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受教育权与国家的培养义务、公民文化活动的自由与国家发展文化的政策等等构成公民权利与国家义务的对应关系。建国初期的宪法文件就体现出国家主体意识强于个人主体意识。如《共同纲领》第 48条:“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954年宪法更是在规定公民的劳动权、劳动者的休息权、物质帮助权以及公民的受教育权的同时紧接着规定国家的义务,第 95条国家“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则直接以国家义务的方式规定公民的权利。
这种规定模式一方面鲜明地体现出宪法的调整对象,另一方面也极易产生强烈的暗示,即权利的行使是个被动的过程,权利的实现是国家的事情。而后者所滋生的消极的权利主体意识根本无法满足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需要。
四、基本权利之立宪矫正
立宪者的观念对于权利规定模式有着强烈的引导作用。反观基本权利的宪法确认所带来的实践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转变立宪观念以完善权利之立宪确认,从而最终有利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呢?试述如下:
(一)改变宪法不断确认权利的传统思维
纵观我国历部宪法对于权利的规定,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确认权利的传统思维,那就是将新认知、新发现、认为很重要的权利不断地增添到宪法文件中。许多学者在撰文研究具体权利时,常常将宪法典没有明文列举某些具体权利视为立宪之不足。有学者认为,“通过我国现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对比,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落后于世界潮流,内容不够全面。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相比较,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或规定得不全面或不明确的公民基本权利多达 30项”。[7]有学者指出:“权利普遍性原则、生命权、生活方式选择权、出入境自由权、迁徙自由权、担任公共职务权、救济权等等,宪法典没有或较少提及。”[8]也有学者直接提出应增加的权利类型,[9]以此提升该权利的地位,扩大该权利的保护。
权利入宪在各国立宪表现并不一致,如美国1789年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就没有列举权利,也没有专门的权利章节,即使 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 ”,虽然“包含了各种最重要的个人权利”,[10]P3但是它并非全部个人权利的清单。因为在缔造者心目中,权利并非来自宪法,无需—一列举,《权利法案》所列举的仅仅是他们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认为最应由宪法提供保护的重大权利。第 9条修正案还专门提醒:“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同时,它所使用的语言是“国会不得……”,“士兵不得……”,“……不得侵犯”,是以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方式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1791年的法国宪法在设定公民基本权利时采用的立法例亦是概括式。该宪法直接以 1789年法国著名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作为序言,对宪法确认、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价值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宣示,但宪法文本中具体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并不多。以后的法国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规定的立法例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国家采用列举式的,如德国基本法,可是该部宪法仍然具有许多防御式的规定。
总体说来,权利应“不断入宪”还是无限保留需要提高到是否有助于权利获得实现的标准上考虑。首先是因为权利不是发明创造,而是不断被认知、不断被需求才获得普遍性地位。人类永远不可能言说权利的尽头,基本权利不能无限增多,因此不断列入从哲学意义上并不科学,宪法典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其次,将母体性权利和派生性权利等不同属性、不同类别的权利交错并列规定,易产生逻辑上的混乱。在实践中,也会导致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是藉宪法予以调整或藉普通法予以调整的难题,宪法规定的权利之间产生冲突时哪种权利的效力优先的窘境。第三,具体权利的入宪不利于我们保护更多的权利类型和更深层次的人权。人类基于自身必然具备的权利,与生俱来,无论国家是否明示,皆不可剥夺。具体权利的入宪易使人们误读所有权利皆是通过法律赋予,必须取得国家的许可才能够拥有及行使。确认性的规定方式,有一种排除未明确权利的嫌疑。
相反,宣告权利免受来自任何方 (包括国家)的侵犯,能够避免上述的弊端,可以对抗来自国家或来自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改变我们的确认思维,引导权利立宪进入防御性的规定模式,最终体现权利本位的价值。
(二)约束国家权力、强化国家义务
宪法关系的核心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基本权利的对应方一定是国家权力。宪法的本质是规制公权力运行,“宪法、国家、政治关系已经变成了特殊的一种三位一体的东西……宪法是为国家和政治的关系确定方向的。”[1]P373宪法是用来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以及国家权力行驶的轨道,不是划定、圈定公民权利的范围,因此规制的对象应该以国家为主,基本权利规定中增加对应性的国家义务规定或者增加国家权力的限制性规定是宪法本质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增加国家对应性的义务。虽然公民权利极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但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也有赖于国家义务的履行。国家义务的不履行即带来国家责任,如此明确规定国家义务也为公民权利的救济提供了路径指向。《共同纲领》是以国家主动保护地位来规定国家义务,但是更多是出于国家“家长”主义理念而不是出于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对等角度的考虑。由于对新兴政权寄予无限信任,将对权利的保障寄托在绝对可靠的政权和政权的建设上,疏于对权力本身的质疑与警惕,所以 1954年宪法虽然有一些条款是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性规定,但是在思想认识、规范条款及制度上削弱了宪法基本权利固有的免于国家侵犯的属性。[11]P214-215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义务在承担能力上也是不同的,所以规定国家作为义务需要结合国家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则可在权利立法上采用法律限制的原则,如国家或国家机关“不得侵犯”或“不得非法干涉”或“未经正当程序”,或者增加强制限制国家权力的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4条第2款明确规定:“不得根据本公约关于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克减基本权利之规定,而克减以下基本权利,如生命权、禁止或反对酷刑等。”美国宪法修正案第 5条规定:“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不得受判处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行之审判,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现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在我国历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中充满着“公民有……的权利”的语句,似乎暗示着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是国家以某种权力的方式赋予的,国家强势地位跃然纸上。
(三)提供公民权利的救济原则和基本途径
有权利必有救济,或者说无救济就无权利。青岛考生状告教育部[12]、北京海淀 42名下岗女工就选举权起诉民族饭店等等已经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能怎么办[13]?安德鲁·内森指出:“任何一部中国宪法都没有为公民打开一个通道,使他们能对抗可能给他们造成损害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从而维护个人利益”,中国“没有确立独立审查法律的合宪性的有效手段”。[14]P56权利的救济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是完整的基本权利的应有之义。缺少权利救济保障的基本权利,根本就不能称为基本权利。[15]P238
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理应给予保障与救济。但是由宪法直接规定救济手段、救济途径和方式也不合适,故宪法至少应该明确公民寻求救济的权利、确立救济原则或者是诉权的享有。有学者建议,在基本权利救济模式上,建立和完善基本权利可诉性的诉讼制度,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更为广泛而有效的救济机制。[16]笔者对此十分赞同,作为国家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当事人,公民申请救济的最佳对象是中立裁决机关。基本权利的可诉性对公民而言就意味着诉权的存在。诉权是一种救济权利的权利,将其列入宪法,能够保障公民接近正义的权利,即接近法院、接受司法裁判的权利。它应当是法治国家人民享有的一项由宪法保障的最基本性权利。[17]《世界人权宣言》第 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18]P961第 10条规定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18]P962尽管我国现行宪法第 41条规定了公民有申诉、控告、检举权等等涉及到部分诉权的内容,但是还不够明确。反观我国港澳基本法的规定却较为细,如香港基本法第 35条、澳门基本法第 36条规定,居民有权诉诸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得到律师的帮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获得司法补救。居民有权对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无论是从基本权利的现实保护还是从世界人权保护的基本规律基本要求来讲,保护诉权都是必须和必要的。其他法律可以依据宪法出台明确规定基本权利获得救济的具体程序和步骤,使基本权利的保护具备可操作性。当然,由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既有可能受到来自国家机关的行为侵犯也有可能受到来自法律法规的侵犯,如果公民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到了法律法规的侵犯,此时救济途径则有赖于我们的备案审查制度,有赖于违宪审查体制的建立。
(四)明确公民权利受限制的原则
通常我们认为,宪法是权利之法,宪法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但保障公民权利并不必然表现为一味地扩大权利范围,也不意味着权利至上不容限制,相反在某种情形下,限制公民权利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何华辉先生早在其《比较宪法学》中写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形式有共同之处:[19]P204(1)在宪法规范中直接加以具体的限制。即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某种权利和自由,同时又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限制。(2)在宪法规范中不做具体限制,只规定依法限制的原则。“所依何法并不在宪法中明确”。(3)在宪法规范中对公民的某些具体权利和自由不作限制,但对各种权利和自由加以总的原则性限制。实际上我国宪法已经具备三种方式,如第一种,在规定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就规定了“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第二种,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时做出例外规定,即在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是有权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的。第三种,则是宪法第 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应该明确公民权利受限制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不能太过抽象。从各国和国际实践看,在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卫生和健康而限制个人的某些自由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条:“承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是限制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合法根据遵循了公共卫生需求优于个人权利的历史传统。”《日本国宪法》第 22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移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在我国,特别是近几年的突发应急事件如非典、甲型流感等疫情蔓延期间公民权利必须为了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受到克减和限制。墨西哥总统曾指责中国隔离墨西哥游客事件,实际上“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但是在传染病爆发期,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人身权利必须受到更大的限制。”[20]在根本大法上确立一个限制原则也为突发事件、应急法提供宪法依据。
当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是必要限度内进行,因为“基本权利的本质是不得限制的。”[21]我们应尽能选择一种对公民利益损害最小、最有利于保护公民权益的限制措施。
权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人类的发展必将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但是这种丰富的内涵是否必然通过宪法确认予以体现的确值得再思考。梳理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立宪过程也有利于我们提高对科学的立宪标准的认识,促使我们与时俱进地修改宪法。公民权利的立宪模式不仅应符合国家追求法治状态的价值目标,也应符合立宪规律。当规范有利于人的自我实现,有利于人的自由,人的自由也就具有实证意义。
注释:
① 关于基本权利、公民权利、宪法权利,首都师范大学的郑贤君教授颇有研究,参见郑贤君:《宪法与基本权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当然仍然有不少学者还在孜孜以求从学理上对这三者进行分析并准确地表达它们各自的内涵。
② “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有一段独特的历史,《共同纲领》并未采用“公民”一词定位权利主体,而是以“人民”这一集体概念来指称权利主体。参见馨元:《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 5期。
③ 当然只是在第 5条笼统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可见,其对权利类型的潜意识分类。
④ 关于“人民”和“国民”之间的分别,在周恩来所做的《关于〈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中作了辨析。“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的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造以前,他们不属于人民范围,但仍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参见许崇德:《中国宪法参考资料宣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6页。
⑤ 尽管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程序论”最终被抛弃,但是建国前人们仍然意识到宪法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在成文法传统的国度里,有宪法才可以谈得上宪政。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⑦ 参见李林:《如何看待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下),载《学习时报》2003年4月 7日;周永坤:《“集体返航”呼唤罢工法》,载《法学》2008年第 5期。
⑧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马克思曾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⑨ 迁徙自由的论文曾经非常之多,甚至可以用“泛滥”一词来形容。
⑩ 参见苗连营、杨会永:《权利空间的拓展——农民迁徙自由的宪法学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 1期;姚秀兰:《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 4期;王怀章,童丽君:《论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实现》,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 4期。
(11) 1954年宪法明确使用了“公民个人财产”以及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
(12) 所谓“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排除了被法院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承担此义务。
(13) 所谓消极权利,即是指个人要求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得侵犯的权利,而国家则对这些个人的权利有依法保护和不加侵犯的义务。所谓积极权利就是个人要求国家加以积极行为的权利,也就是社会福利权利,主要指各种受益权(如工作权、受教育权、社会救济权等等)。对这些权利国家不得消极无为,而必须积极地实现和加以保障,对此,它有不可推卸的实施义务。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05页。
[1]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M].陈云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3] 许崇德.中国宪法参考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5]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 刘向文,宋稚芳.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 杨海坤.公民基本权利修改应作精良设计[J].法学论坛,2003,4.
[8] 于立深.我国宪法典公民权利条款分析[J].长白学刊,2002,4.
[9] 齐彬.中国宪法有待增加十项人权—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EB/OL].http://www1.china.com.cn/chinese/OP-c/243614.htm.
[10]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11] 张庆福,韩大元.1954年宪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12] 李艳.全国统考录取分数却相差悬殊,青岛三考生告教育部[EB/OL].http://edu.sina.com.cn/l/2001-08-23/14545.html.
[13] 胡锦光.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EB/OL].http://www.cctv.com/program/bjjt/20031010/100830.shtml.
[14] [美]安德鲁·内森.中国权利思想的起源[A].黄列译.夏勇.公法[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5] 张千帆.宪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6]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J].江汉大学学报,2008,2.
[17] 刘晴辉.诉权约定的效力与公民诉讼权的保护[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18] 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19]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20] 陈欢.马怀德受访:防控甲型 H1N1流感的法律根据[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5-19-06.
[21] 韩大元.基本权利限制界限[N].法制日报,2003-06-05-09.
Development of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hinese C itizens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s
Hu Hong-hong
(Law Schoo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
A country’s choice of constitutionalism forms concerning fundamental rights is often related deeply to this country’s history accumulation,constitutionalism humanistic background,and the temporal awareness of rights. Through the overview of the fundamental rights’improvement in our all constitutionswe can find thatChinese constitutions tend to comprehensively provide civil rights,pay an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citizens, shape the defensive provision pattern for personal rights of citizens,and stress the State obligations for those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f citizens.We need to change the Constitution’s traditional idea of recognizing the rights,to strengthen State obligations to provide relief principles and fundamental ways for civil rights,and to nail down a clear restriction to civil rights,etc.,and so as to be consistentwith State aim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ruling of law,to accord with constitutionalis m orderliness.
fundamental rights;constitutionalism,;defensive;State obligations
词】DF2
A
(责任编辑:黄春燕)
1002—6274(2010)03—018—09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008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宪法视野中的公民制度》(08JHQ0017)的阶段性成果。
胡弘弘(1970-),女,湖北大悟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公民制度、地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