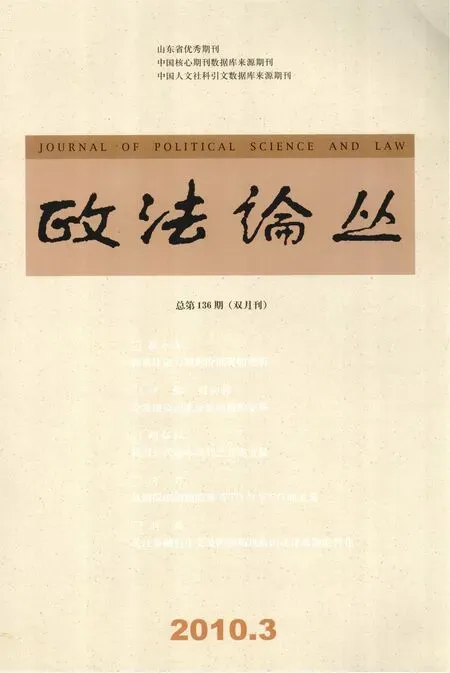论基层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裁判合法性与公信力之统一*
——传统中国法官的难题与当代中国法官的难处
张 镭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论基层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裁判合法性与公信力之统一*
——传统中国法官的难题与当代中国法官的难处
张 镭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在基层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民间习惯和国家法律的矛盾是传统中国很多朝代的法官必须面临的难题,他们常常要解决这对矛盾,以实现裁判合法性与公信力的统一。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的取得与儒家学说的解释力、社会规则的认识、国家—法官—社会之间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以及法官的考绩压力等因素有相当的关联。当代中国法官也面临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却有着与传统中国法官大不相同的现实困难,包括国家—法官—社会三者之间意识形态的非同一性、法官知识体系构建的非本土性、司法目的的非现实性以及司法活动的非社会性等四个主要方面。这些困难的解决将是中国司法达致和谐的真正开始。
民间习惯 纠纷解决 合法性 公信力
通过对传统中国司法材料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司法过程呈现出目标定位的实用主义倾向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不以寻找或者确认法律规则为目标,而是以消弭纠纷、恢复秩序、促进和睦为目标。此种司法过程的目标定位恰好与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谐观相一致,至于用何种方法消弭纠纷则需要充分展现传统中国法官的学识、智慧、经验和技巧。其对法官的首要要求是尊重国法,不得枉法裁判,这是对法官裁判合法性的基本要求;另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通过司法活动解决纠纷,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和谐,这要求传统中国法官对裁判公信力予以高度关注。但是,我们也发现,传统中国的法官既面临法律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必然困境,也常常会面临社会主体弃国法而尊习俗的现实挑战。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运用智慧和技巧不断追求裁判合法性和公信力的统一,从而通过纠纷的解决不断接近秩序和谐的目标,其经验我们认为是值得借鉴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当代中国的法官与传统中国的法官所面临的职业压力具有相当的同构性,只不过当代中国法官实现裁判合法性和公信力统一的难度要比传统法官大很多。本文首先将对传统中国法官所面临的难题以及他们对难题的消解进行详细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解构当代中国法官在构建和谐司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我们认为这些现实困难的解决是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前提。
一、传统中国法官的难题及其消解
在传统中国的司法过程中,一般认为不应忽略法律制度对法官行为的约束力。传统中国大部分朝代都有明文规定,法官必须按照法律进行裁判,①在司法实践中,传统社会的法官绝大多数也是依法裁判的。②唯其如此,才能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体现皇权的不可动摇性,也可以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意识形态。可以认为,是否依法裁判成为传统社会法官裁决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严格判准,只有最高级的法官——皇帝也许才能例外。③不过,虽然绝大部分基层纠纷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顺利的解决,不会对传统社会的法官构成事实上的困难,但是,从现有的传统社会司法裁判资料中发现,还是有不少疑难案件在裁判过程中使传统社会的法官面临至少两种情形的难题 (虽然这两种情形的难题并不总是同时出现):
第一,有时法律的规定并非十分具体,或者也不十分完善,无法适应多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体的利益冲突。④当社会经济或者其他因素发生变迁的时候,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随之发生变化,而法律不能及时反映这种社会变迁的时候,基层法官在解决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利益纠纷的时候就必须颇费思量,以便获得裁判结果的平衡。清代司法实践中,曾经出现了“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官员可以有多种解释”[1]P77的现象。清人袁枚认为此情实为必然,因为:“盖人之情伪万殊,而国家之科条有限。……若必预设数万条成例,待数万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余。”[2]
第二,即使法律有规定,但是基层社会的主体可能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而不愿意遵从法律,甚至有的地方风俗与法律大相抵触。国家法律不能产生预期效力的地方往往具有浓厚的区域性色彩,其民间习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控制力。例如从宋代至清代,江西、陕西和安徽一些地区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健讼风气;而在宋代和明代末期,江西的一些地方存在着杀婴的习俗。这些地方风俗 (或者是风尚)既有悖于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在当地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顽固性。基于这些风俗习惯而引起的法律纠纷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既十分烦恼,又需要谨慎处理。例如清代樊增祥在陕西为官时就察觉了陕西的健讼现象,曾经指出:“陕西各属上告之案十控九虚,本司知之稔矣。”[3]P454在“批陕西紫阳县民马家骏控词”中提到:“尔以紫阳县民,不远千里,来省上控。而所控者无非买卖田地钱财胶葛之事,辄敢指控被证九人之多。其健讼拖累,已可概见。本应惩责押递,姑宽申饬。……”[3]P4
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法官不可能在第一种情形下依法裁判——因为缺乏法律规定。在后一种情形下,法官则不能机械地依法裁判,否则判决既不能在当地获得社会主体的认同,判决的执行也可能会受到阻碍,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酿成民变。如果从法官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角度而言,第一种情况下,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在法律中得到反映,因而法官的判决无从形成,更加无法照应社会意识形态;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不能相互呼应,法官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裁判均可能造成合法性或公信力的危机。此时,法官应当采取何种进路,来解决已然实际呈控的纠纷呢?实际上,这一过程的处理才真正显现了中国传统法官的才智,彰显中国传统司法过程的魅力和特质。
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官面临的压力是没有合法性规范以解决纠纷。通常,法官可以使用类推方法进行处理。⑤如果类推也不能解决问题,则有两种途径可资使用:
(1)化审理为调解。因为调解可以动用多种规范资源,而不局限于法律规范。调解过程以化解矛盾为目标,一般由家族或者保甲处理即可,如果法官参与,那么他首先关注的将是纠纷调处的公信力问题,而不是裁决结果的合法性问题。⑥
(2)在很多时候,正如一些学者已经发现的,闹到衙门需要法官解决的案子一般都已经经过了至少一次的基层调处行为,只是这些调处行为要么没有实质效果,要么当事人始终不服,才会闹到基层法官那里。⑦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实际上被逼到了墙角——他不能不判了,但是又没有现成的法律规则可资直接适用。更为困窘的情况是:甚至连可资类推的法律规则可能都不存在。我们发现,传统社会的法官此时将会运用另一种技巧——他会以儒家学说为理据,诠释国家法律的立法精神,进而从上往下不断诠释立法的意义,最终勾连到当事人行为与立法精神之间的关系上。⑧此时,大前提是被解释 (实际上应当说是被诠释)的立法精神,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法律的一般原则,并以此形成最终的判决。在这里,最能体现法官技巧和水平的是:1)对立法精神的诠释,这是根据不同案件的事实所做的“个案诠释”,而不是欲求形成具有普适性的“一般诠释”;2)将立法精神与案件事实的勾连,这种技巧对于传统社会的法官来说并非出人意料,而是每一个合格的法官都应当能够熟练运用的技巧。
更为复杂的情况出现在第二种情形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两难抉择:依法裁判可以解决合法性问题,但有可能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认同,从而可能形成地方现实秩序的紊乱;依俗裁判解决了公信力问题和现实秩序紊乱的潜在威胁,但却难以取得国家权威的支持,还容易面临上级官员和监察部门的责难。⑨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检阅,我们发现传统社会的法官在处理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主要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民间习惯的性质的判断问题:良俗?抑或恶俗?
第二,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相互抵触的情形如何应对?
第三,法律缺失,但是民间习惯存在,应该如何处理?
第四,法律和习惯并不冲突,但是社会主体选择习惯而不是法律的时候如何解决?
以上四个问题中,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具有同构性,现有的文献表明,如果民间习惯与现行法律相冲突,法官一般均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尤其在民事纠纷(一般属于户婚田土债的“细故”案件)中法官会适度迁就民间习惯,以获得裁决的公信力,维持秩序的稳定性,因为毕竟“平治道涂,地方官所有事也”。[3]P442除非法官认为特别需要,一般不会轻易宣布一种民间习惯为“恶俗”。但是,一旦对“恶俗”做出宣布,法官均会通过儒家学说对其理由进行阐明,这一部分非常类似于一篇驳议文章,充分体现法官的文字功夫和论理水平。从大量判例发现,对习俗的良、恶之分的论证均以儒家学说为理据,此部分更加体现儒家学说中的自然法倾向。⑩作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解决社会规范的价值评价问题对于从小浸淫于儒家学说,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法官而言,往往并不呈现为一个法律 (或者法学)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对问题的回答也不属于“法学”的范畴,而属于“策论”的范畴。故而许多法官都能够轻车熟路、手到擒来。此番裁决如果不能在基层获得公信力,法官则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要么法官屈服于习俗,要么采取威权手段执行裁决,两者都需要颇费考量和平衡。
第三个问题类似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形 (有时法律的规定并非十分具体,或者也不十分完善,无法适应多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体的利益冲突),法官通过诠释立法精神形成大前提,然后解决习俗的良或恶的判断问题。结果有两种:恶俗则被明确禁止,良俗则直接进入第四个问题。
在第四个问题中,风俗不是恶俗,但是又和法律不一致,社会主体不愿意遵守法律,而愿意遵从习惯。此时法官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做到既依法裁判,又能够照应民间习惯的公信力,从而使得判决合法性与公信力并举。从大量判决遗存中可以发现,法官此时会进行这样一种论证:首先,法官会用儒家学说诠释当事人的行为,然后再对当事人遵从的民间习惯进行诠释,并运用儒家学说进行价值判断,这主要是寻求行为与规范中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情”和“理”,如果能够诠释出行为和规范都合情合理,那么行为和规范也就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在传统中国法官的心目中,作为国家的法律本身实际上已经是既合理,又合法的规范,所以无需论证。如果能够论证民间习惯也是合理的,那么民间习惯和国家法律就具有了同样的根基。此时,运用法律或运用习惯进行裁决就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法官往往会以民间习惯既合情、又合理为理由直接进行裁决,从而使裁判获得公信力。此时,裁决的合法性被隐含在裁决的论证和诠释过程中,而无需被特别强调出来。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法官才通过一个判决满足了行为上的民本主义和目的上的秩序和谐。
二、传统中国法官消解难题的基础
虽然传统中国的法官在面临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矛盾的时候,能够完成纠纷解决过程中合法性与公信力的统一问题,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法官能够消解难题的背后至少还有存在几个值得关注的基础性因素:
首先,具有自然法色彩的儒家学说所能够提供的巨大解释力使得法官面对民间习惯的时候拥有非常富裕的解释空间,使得法官有可能完成此项工作。儒家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以后,在传统中国的法律思想层面上,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天人关系、天理人情成为衡量法律、习俗以及主体行为的超验标准;制度体系上反映出的则是儒学为体、儒法并用的法制体系。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法律的解释进路也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从这一点来说,儒家学说的核心既可以被理解为整个传统中国法制体系的“高级法”,又可以理解为传统中国任何一个具体法律规则的合法化依据。由于儒家学说自身论题范围的广大性以及其所奠基的基本伦理要素,使得儒家学说可以赋予传统中国的法官以几乎无限的解释空间。加之儒家学说形成以后,其本身也不断被扩充和发展,强化了儒家学说的解释力,终而使得传统中国的法官在解释法律的时候能够契合以儒家学说作为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构成法官司法过程的合法性理由。
由于传统中国儒家学说的官方化地位,国家利用其宣传和选拔两大工具,使之同时成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大多数社会主体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对于社会秩序的理解非常契合于以家庭生产为社会基本生产单元的小农经济模式中主体对生存以及生活之基本态度,因而很容易为普通的社会主体所接受,从而导致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获得了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由此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传统中国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以儒家学说对法律、习俗和主体行为等进行解释的时候,比较容易获得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接受,从而构成法官裁判的公信力的基础。(11)
其次,在传统中国的法官那里,法律和习惯具有准社会学上的意义,它们都被视为一种行为规范。任何一种社会规范都必然地应当受制于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都不能违反天理、人情,法律应当如此,习惯也应当如此。(12)既然社会规范都是天理和人情的反映,那么习惯和法律就都被预设为应当符合儒家的基本理念。这样,习惯和法律就应当具有同一性的超验基础,这一点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法官的前见认知。至于法律和习惯的同一性解释的结果则因案而异,甚至因人而异,解释的结果可能决定于法官的学识、经历、认知能力、办案态度、办案压力、民风民情等诸多因素。
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官对于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规则、风俗习惯以及主体行为等的理解显然与其知识体系有很大的关联。从传统中国法官的知识体系而言,由于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学正统,更在后世逐步成为官员选拔的科目,因而作为官员的法官对于儒家学说的了解和掌握应当被认为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不同的是不同时代的法官可能受到当时代儒家学说的影响,有人上承孔孟,有人师法荀子,有人修习程朱,有人心仪阳明,不一而足。甚至即便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法官也会因为师承关系不同而追随不同的儒家流派,例如清代儒学中就有不同的门派。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传统社会法官在运用儒家学说进行解释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除非依法裁判,否则考虑了天理、人情、国法之后的判决往往使人感到明显的个性化倾向,其结果取决于法官本人基于对“情”“理”的理解而做出的司法裁判。
再次,国家、法官、社会三者在古代中国具有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构成法官能够完成此项工作的内在基础。绝大部分法官大体上具有非常类似的人生经验体系的构建经历:生于乡土、学于私塾、游于儒林、试于科举、务于政事、牧于地方……他们的经验体系构建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是核心内容,因而官员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具有很类似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吻合于乡土社会主体的认识和判断。选拔考核的内容主要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大部分朝代的官员都是经过这种选拔程序选拔出来的,因而官员们就与国家达成了意识形态上的默契。大部分官员都出生在乡里,因而又熟悉乡土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乡土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在传统中国整体上可以认为是同源同构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中国的法官几乎无需专门学习就具有了解决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初步能力。正是从这个角度,本文认为国家、法官、社会三者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形成了法官解决此类问题的内在基础。
通过对若干传统中国裁判资料的阅读和分析还可以发现,无论法官的解释如何存在差异,其所掌握的儒家学说又是如何地观点殊异,进路分野,也无论哪个朝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倾向于某种儒家学说派别,有一个因素始终是不变的,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变化的。这个因素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和核心观点,用现代语言表述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以民为本”的行为原则以及“秩序和谐”行为目标,二者相连构成传统中国几千年儒家学说中官方秩序治理的“行为—目标”体系,所有的制度及其运行都被要求在这一框架中去产生、实践和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民本主义与秩序和谐二者相互照应,既构成统治集团考核官员的“行为—效果”的判断标准,同时也能满足社会主体对于个人生存和生活的愿景,因而也会构成社会主体对于统治集团和官员行为的一个判断标准。社会主体的这种判断是通过对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法官)行为的评价直接勾连到对统治集团的评价的,也就是说,通过对当地官员行为的考察形成对政府的一种整体价值评价,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官员 (包括县、府、州等)的行为成为了勾连朝廷与地方的纽带。在司法过程中,只有当法官的裁决既能契合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又能满足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裁决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才能同时实现,这一实现意味着通过法官 (国家的代表)通过对纠纷的解决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共同的和谐目标。正因为如此,传统中国法官的行为就成为以解决纠纷为核心的一种官方行为,并且该行为又受到来自国家(上级官员直到皇帝)和一般社会主体的双重评价,失去其中一端,则其行为要么合法性受到质疑,要么裁决的公信力难以达成,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形,对于传统社会的法官本人而言都会构成即时的或者潜在的实质影响。
最后,传统社会法官的考绩标准形成了法官必须完成裁判合法性和公信力统一的外在压力。传统法官从身份和职责上来说首先是行政官员,其次才是裁判官员。对于行政官员而言,其政绩考核的基本要求是“秩序和睦”、“治下和谐”、“民风纯朴”(也就是无讼抑或少讼(13))。如果因为法官的判决引起秩序紊乱甚至激发民变,那么无论法官是否依法裁判,他都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对于判决与秩序之间的关系而言,构成或促进秩序稳定的判决必然要照应其自身的公信力,以求裁判合法性与公信力之间的合理平衡,这种平衡的追求我们认为与儒家思想深处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等方面的和谐有很大的关联,也可以说是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对于和谐的追求在司法过程中的反映。正如敦煌残卷研究者王斐弘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体现在情理法中,同样追求三者的和谐。这种和谐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从文化根基上一脉相承。”[4]P212滋贺秀三也认为传统中国的法官“听讼并不以使尽了程序的手段而告终。它拥有的是当对事实本身当事者已不再争执时即告终结的构造,而以这一特定争讼的平息为目的。通过争讼发现什么是法并不是听讼的目的。”[5]P15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中国的法官经常强调要查访民情、体察民风、了解民俗的重要性,并且在司法过程中重视民间习惯(14),甚至在一些案件中明知习惯有悖于法律规定,依然按照习惯进行裁判的现象了。(15)对于传统中国的法官而言,判决书中最后的依法判决是合法性的需要,判决书中的说理教化部分则是公信力的需要,能够做到既唯于上,又足于下的判决才是最佳的判决。要想做到合法性与公信力并举,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俱佳,则必须完成对法律和习惯两种规则的超验基础同一性的解释。(16)
传统法官在面临民间习惯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矛盾时,运用诠释的技巧寻找民间习惯于法律规则之间的同一性基础,从而尽其所能保证司法效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的实现,其在传统社会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不仅局限于司法过程本身,而且还会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效果。
首先,合法性的判决能够体现皇权的权威性。无论何种情形下,司法判决的合法性维护的总是国家权力的权威。只不过这种权威性通过一种特别的程序和方法得到了表达。
其次,判决公信力的大小往往影响判决的执行力,并进而对因司法活动而受到调整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并进而既影响司法的权威性,也影响法官个人的名声和前途,。
再次,法官对法律抑或民间习惯的诠释过程既表达法官本人对规则的理解,也表达了法官的文字和论理能力。作为判决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国家对某种规则的态度和结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份有论证过程的判决具有典型的宣教意味和普法作用。从宋朝至清代的大量判决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此种端倪。
复次,一份论证充分、逻辑有力的判决不仅具有强烈的普法宣教效果,经由公开的宣读或者张贴,该判决将直接接受社会主体的评价,从而展示法官本人的基本态度。同时,法官以其文字的处理、逻辑的展示和判决的公允向其治下展现了其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人格魅力,使其获得广泛认同。我们认为,在传统中国绝对不能忽视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这样一个卡利斯玛型的传统社会中,地方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的个人魅力往往是获得秩序和谐和稳定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可以认为这是传统中国法官兼具司法裁判与行政管理双重职能的基本要求。
最后,通过法官对民间习惯的诠释,实际上宣告了民间习惯的合法性,从而必然使得一部分民间习惯具有了合法性的“官方”身份,规则合法性的宣告意味着该规则所体现的法权关系的制度性认同。而对于“恶俗”的宣告同样是对此类规则所体现的法权关系的制度性否定,其结果是,这些规则将不能作为合法性依据出现在法官的裁决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涉及民间习惯诠释的裁决对传统社会民间习惯的发展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当代中国法官的难处
传统社会法官既是裁判官,又是行政官员,承担着秩序治理与解决纠纷的双重职责。法官面临的最大压力在于要使得判决在合法性和公信力两个方面均能够得到满足,既要充分体现皇权的权威性,又不能因此丧失秩序的稳定性。如果按照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话语来表达,传统中国的法官的判决应当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兼顾,从这一点来说,传统中国的基层法官与当代中国的基层法官所面临的职业压力具有相当的同构性。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基层法官在应对这种职业压力的过程中存在几个方面的现实困难,使得他们在完成裁判合法性和公信力统一的过程中难度更大。
第一,国家—法官—社会三者之间意识形态的非同一性。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类似于传统社会那种一统天下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形式与控制机制,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通过形式合理性的政治统治模式保持基本的一致。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民间习惯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与法律所表达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还是存在殊然的差距。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民间习惯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中不仅有非理性因素,还有很多非科学的因素,历史的、伦理的、宗教的、迷信的因素杂存其中。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司法机构,被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保持一致。在这一要求下,法官实际上不可能完成对民间习惯和国家法律超验基础的同一性诠释 (因为往往根本不存在同一性的基础)。因此,对于当代法官而言,纠纷的裁决要么契合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要么满足于民间的意识形态。从裁决效果来说,合法性指向的是法律效果,公信力指向的是社会效果。而当代法官常常面临的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其结果是法官的裁决要么具有合法性,要么具有公信力,二者很难兼顾。在要求基层法官的裁决应当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兼顾的前提下,基层法官于是就面临一个实际上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们认为,这也是导致大量的案件由审判转化为调解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第二,法官知识体系和经验体系构建的非本土性。当我们考虑到国家—法官—社会三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发现司法过程的结果与法官本人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联。传统社会中法官的意识形态由法官本人的生活、学习和为官经历所决定,并逐步形成了传统法官们基本类似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能够契合国家的意识形态,又基本勾连基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的法官才能够做出对国家法律和民间习惯超验基础的同一性解释,从而比较容易平衡国家法律和民间习惯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当代中国的法官出生差异较大,就学以前的生活状态差异明显;就学以后学习的基本上是受西方法律理论所严重影响的理论知识。同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现代法官由于对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掌握大多非常有限,因此,其往往很难容纳所谓的非科学因素和非理性知识了。他们多年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求他依法审判,多年现代西方知识的灌输告诉他们民间习惯中大多是封建的、迷信的、不科学的东西,是不能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现代的法官遇到国家法律和民间习惯相互矛盾的时候,其往往就不会(基本上也没有能力)去考虑民间习惯的文化内涵和现实地位问题,而是本能地对民间习惯产生抵触。于是,我们这些生于本土、长于本土、学于本土的法官们在经过了貌似现代和貌似科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以后彻底背叛了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面。他们常常用貌似科学的预设得出非科学的前提;用貌似理性的思维推导出非理性的结论;用貌似严密的逻辑证成出非真实的事实;用貌似合法的理由宣告出公信力缺失的判决。我们认为,这种结果的出现基本上不是由法官本人造成的,而是由我们培养法官的理念和机制造成的,因而这个现实困难也不是法官 (甚至法官队伍)自身所能够解决的困难。
第三,司法目的的非现实性。现代司法被认为是国家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程序适用法律的行为,其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但是从司法这一活动本身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司法活动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解决纠纷的过程。庞德曾经说过:“我们必须牢记:法官出现在法律之前;没有法律的司法出现在以法律为依据的司法之前;裁决出现在习惯法之前。”[6]P336司法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解决纠纷的问题。司法过程依靠的是国家权力,是以国家的名义解决利益纠纷的一个过程,适用法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当我们将司法理解为适用法律的时候,一个直接的认识就是没有国家法律就没有司法活动。从这一逻辑前提出发,一切未经国家法律认可的社会规则都不能成为司法过程中适用的对象,都是非合法性的规范,因而都应当被排除在司法过程之外。也因此,按照这一逻辑,一旦法官完成三段论的推理,适用了法律,法官的任务即告完成。至于当事人是否服判,是否愿意息讼,社会秩序是否会因此和谐还是恶化等等问题都不是法官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样的逻辑下,程序正义成了正义的全部,实质正义成了正义的多余。体现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要求被一再提高,甚至有可能成为司法的唯一目标。我们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涉讼上访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也是当前提出司法工作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举的主要诱因之一。
对于当事人而言,如果司法裁决不能使其服判息讼,那么他可能会放弃 (或者被迫放弃)司法救济。此后,他们所能够选择的权利救济手段除了私力救济之外,就只能依靠其他权力资源。(17)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司法裁判公信力的缺失,实质上导致了秩序治理中司法权力的退却,使得司法场域发生萎缩,行政权力作为补充填补进来,结果就是行政权力的愈发膨胀,司法场域愈发萎缩的恶性循环。原来应当承担行政权力制约的司法权主动地缴了械,放弃了其应有的制约功能,而行政权力却不断地挑战、侵蚀甚至取代司法权。司法机关最终可能成了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徒有虚名。正如笔者曾经提出过的,当代中国司法权的退缩不仅仅损害了司法权自身的公信力,更为重要的是会潜在威胁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当事人会因为法官的行为而对法院丧失信心,因为对法院丧失信心而对司法救济丧失信心,因为对司法救济丧失信心进而丧失对法律的信心,直至对法治产生困惑。[7]P185-193
第四,司法活动的非社会性。司法活动是掌握并履行国家司法权力的一种机制,司法机构承担着国家司法权的运行,同时也承担着运用司法权进行权利救济的职能,古今皆然。但是,当代中国的司法活动过分强调其运行国家司法权的职能,忽视其权利救济的职能,造成司法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发生断裂。此种状况的出现既与司法本身的目标定位的非现实性有关联,更加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以来对西方法律文化的继受缺乏理性、盲目移植有关。西方的法治理念在西方社会的土壤中逐步生成的,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渊源,更与西方长期的社会生活现实与宗教信仰相互交织。西方的法律制度 (包括司法制度和机制)引入中国以后,在一个异域环境中是否可以直接引用、付诸实践并取得理想效果,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司法本身的双重职能都有其历时性的根据。因此,将司法从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就背离了司法活动本身的意义。也正因为司法活动与社会主体的客观生活渐行渐远,导致当代中国社会主体对于司法机构乃至司法活动越来越缺乏信任和信心。司法活动的非社会性特征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法院判决的执行力低下,而执行难问题的增多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主体对于司法机构和司法活动的失望甚至反感。许多人不再相信法院是他们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相反,他们往往愿意把法院看做是他们权利的第一道屏障,随之而来的可能步骤还有申诉、上访、再上访等等。
经过近 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司法工作的定位终于从法条中心主义的司法向以民为本的司法开始转变。虽然从上述四个方面的现实困难以及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进展而言,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对于这些困难的消解绝非一日之功。不过我们也认为,如果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沿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继续前行,那么我们有信心认为上述问题的消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注释:
① 传统中国法律的形式渊源繁多,不过能够作为裁判大前提的一般都是出自官方的权威性文件,有的时候皇帝的口谕也可以成为裁判的依据,但是这种情况在基层纠纷的司法化解过程中显然是绝少发生的,至少目前还缺乏实际的证据予以佐证。
② 这一问题在拙文《传统中国基层民事纠纷解决中的习惯与法律》(《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 1期)一文中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从现存的大量传统中国的基层判例中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基层案件是通过依法裁判取得结果的,只有少量的案件涉及地方风俗进入司法过程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这些少量案例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洞悉传统社会法官如何解决民俗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其背后存在哪些因素能够解释传统法官的司法行为。
③ 不过,就笔者目前掌握资料来看,似乎并未能够证明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基层法官的裁决,如果说他具有理论上的“自由裁量”权力的话,那么其自由裁量的过程也显然是谨慎的。
④ 这种难题几乎成为从法律诞生之日至今任何社会或轻或重均会面临的难题,在传统中国多个朝代也都出现过。以清代为例,康熙朝以后,由于人口快速增长,耕地很快短缺,大量的人口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提出了更高的和更多的要求,促使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化。而大清律明显不能满足社会变迁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例,最终导致例多于律。其中一例就是,由于民间习惯现实的强势性和顽固性,迫使清朝对于立嗣的规定不断修改,以满足基层社会秩序治理的现实需要,这一点薛允升曾在《读例存疑》中有过描述,反映了从秩序治理的角度而言,清代国家法对于民间习惯的容忍和让步。(参见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 2007年 8月版,第78页。)这一现象成为社会变迁促进法律发展的典型事例。
⑤ 清代由于人口急速增长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大清律例》也无法及时适应,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比附案例。参见[清]许槤、熊莪纂辑:《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何勤华、沈天水等点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⑥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清代纠纷解决中的调解问题,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和日本学者滋贺秀三都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解说。滋贺秀三认为清代法庭对基层民事纠纷的裁决过程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教谕式的调解”过程,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载于[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9~54页。黄宗智则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清代的基层民事纠纷实践中,理想的纠纷化解路径是民间调解而不是法庭的"教谕式调解",并且认为当事人一旦走上法庭,那么从法官到当事人对于通过严格的法律解决纠纷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并非打算到法庭去调解。法庭调解制度主要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参见[美]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3~198页; [美]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53~358页;[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 2001年版,第 107~162页;[美]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08-164页。
⑦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佐治立人和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都有过研究,拙文《传统中国基层民事纠纷解决中的习惯与法律》(《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 1期)对二人的观点曾经进行了介绍和归纳。
⑧ 应当注意的是,传统法官对立法精神的解释与今天所说的“立法解释”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传统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立法精神进行直接的阐述,他们对立法精神的解释体现在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尤其是天理、情理和法理的阐述中。从大量传统司法判例中看到的是,整个司法过程有时呈现为法官欲求并努力践行天理、情理、事理和法理的逻辑统一,这种统一仍然而且必须是在儒家正统思想的框架内完成的。正像宋胡石壁所说:“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参见胡石壁:《典卖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见钱或钱会中半收赎》,载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311页。)本文认为,汉武帝之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有的规则与行为都逐步被纳入儒家学说的应然标准中,受到儒家学说的价值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的法统几乎可以看作是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在制度上的体现和实践。
⑨ 一些学者发现,宋朝法官依法裁判的现象比较多见,而清朝法官在法外解决纠纷的例子比较明显。张小也就曾经指出“在户绝财产纠纷的审理中,宋代的官员更倾向于有法必依,而清代官员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依律例审理,特别是法律规定与民间习惯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参见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 2007版,第 79页。)此种现象依然说明在清代社会发生明显变迁的情况下,法官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注重以事适法,而不是以法论事,此举显然受到上级官员的肯定,至少是默认,否则类似的判决就会被批回,基层法官也会受到批评。
⑩ 在儒家看来,有法律和无法律的意义分殊并不明显,儒家虽然不反对法律的存在 (在这一点上区别于老子的道家学说),但是它更加理想的状况是"刑措"--法律置而不用,终极的理想社会是"去刑"的社会。因为有一个超验的"天理"存在着,社会规范和社会主体的行为的善或恶的价值判准便不在法律之中,而在法律之外。正是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我们认为儒家法律思想具有明显的自然法特征。
(11) 上述观点似乎更容易解释稳定时代的司法过程司法判决,但是,如果适逢乱世的时候,法官是否还能够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一以贯之地作为社会规则和主体行为的解释工具呢?乱世的法官是否更多地运用非儒家的学说或者会用其他的学说(比如法家)理论进行解释?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资料均显示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因此,即便我们仍然可以假设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总体上我们仍然有信心认为传统社会的法官在解释社会规则和主体行为的时候是运用了儒家学说进行解释的。
(12) 不过,法律是否符合天理不是基层法官需要论证的问题,他们只是(而且只能)将法律符合天理作为前提的,没有那个基层法官敢于论证法律是否真的符合天理,至少从现有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
(13) 至少从本人掌握的传统诉讼资料来看,似乎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传统中国法官一概反对诉讼,更多所见是反对和责骂那些"健讼"的现象和健讼的人。例如明代颜俊彦在“越占孀产董士昇等”一案中,就审理妇女申告的案件并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参见[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越占孀产董士昇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85页。)而樊增祥对经常代人告状的“健讼之徒”则显然非常痛恨,在“批咸阳县民沈隆杨治福等控词”中,指出:“尔沈隆著名健讼,往往事不干己,案害人。本司痛恶刁民,严治讼棍,岂能任尔刁诬?仰西安府查明沈隆历年讼案,照讼棍办罪,以除咸阳之害。杨治福形同瓦狗,全听沈隆支使,无足深责。……”(参见[清]樊增祥:《樊山政书》(批咸阳县民沈隆杨治福等控词),那思陆、孙家红点校,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49页。)
(14) 由于缺乏传统法官大量直接引用民间习惯进行判决的证据,而常见的是对习惯规则所进行的解释以契合于国家法律的规定的事例。因此,滋贺秀三先生认为:“虽然体察民情的地方官赴任后,努力了解当地风俗是事实,但作为普遍原理,这是为了加深了解作为通情达理前提的事实认识,即通晓人情,而并非是为了精通习惯法这种实定性的规范。”这一观点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
(15) 卞利认为,对于田宅重复典卖的处置,虽然明清法律均有明文规定,“但我们在资料中发现,徽州各地宗族族长、里老人、文会、里甲或保甲基层组织甚至县、府政权机关,在处理此类民事纠纷与诉讼时,并未完全执行《大明律》或《大清律例》的这一条款,通常只是要求重复典卖之人立下具结、重复典卖之人立约退还,并不追究重复典卖者的法律责任。……这一做法,并非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而无意为之,而是有意为之,它与明清最高统治者所倡导的‘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是一致的,符合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设置里老人以广行教化、保甲以维护社会治安,进而保持基层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参见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张小也以邱煌所审“凤翔县民邓连璧控告邓和璧”案为例指出,清代“民间习惯中立异姓子威嗣却是常见之事,对此,官员做法多是依从民间习惯。那些未依从民间习惯而是按照律例办事的,反而显得不近人情,而且引起更大的争执。”(参见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80页。)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曾经指出,在传统中国有关找价回赎的案件审理中,“作为有关找价回赎审判的感情照顾的倾向,在州县的判词、衙门档案中相当显著。”(参见[日]岸本美绪:“明清时代的‘找价回赎’问题”,载于寺田浩明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0页。)“法律在找价回赎的判断中未必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既不是贯彻执行形式合理的规则,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弱肉强食,清代中国人似乎共同具有一定的十分精炼的公正感觉。”(参见[日]岸本美绪:“明清时代的‘找价回赎’问题”,载于寺田浩明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7页。)
(16) 樊增祥在“批盐城县详”中,就注意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矛盾的问题,并做出了略有倾向于社会效果的判决。“……至刘李氏(即虞李氏,又即潘李氏)淫荡无耻,本应断离,然归虞不可,还李无路。若在二十年前必应与淫僧断离,此时则必不可离,何也?当初次构讼之时,男女年未三十,两情过热,故敢于犯法而不顾,彼时理应判令虞廷干等主婚嫁卖。及潘姓退归,再经堂断,刘前令假淫妇以守寡之名,而阴遂其寻僧之计,是直以父母而兼媒妁,深堪痛恨。至于今侵寻甘余年矣,既生女,又生子,奸夫奸妇彼此形容老丑,爱情之薄可知,儿女婴缠,身家之累益重。若此时断离,是前既遂该僧淫恶之私,今反割弃附骨之疽,而使脱然无累也。应令该僧永远供养。若该奸妇因饥寒而诟谇(sui),是天报淫僧也;若该奸夫弃前好儿远飏,是天报淫妇也。非官府所能过问矣。仰淮安府转饬王令迅速遵批结案报夺,勿延。缴。”(参见[清]樊增祥:《樊山政书》(批盐城县详),那思陆、孙家红点校,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596页。)
(17)例如通过上访寻求行政权力的介入,从而获得救济就是一个被普遍运用的司法外救济手段。为了获得行政权力的关注,当事人有可能选择任何他们认为有效的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极端的方式。
[1] 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M].中华书局,2007.
[2] [清]袁枚.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说[A].袁枚全集(第二册第十五卷)[C].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3] [清]樊增祥.樊山政书(批西安府禀)[M].那思陆,孙家红点校.中华书局,2007.
[4] 王斐弘.敦煌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 [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A].[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6] [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三卷)[M].廖德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7] 张镭.论习惯与法律——两种规则体系及其关系研究[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On the Un ification of Legit imacy and Credi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C ivilD ispute Resolution——The Puzz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Judges and the Troubl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udges
Zhang Lei
(Law School ofNNU,Nanjing Jiangsu 210097)
In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nongovernmental customs and state laws of contradiction is traditional Chinese judges must face the problem in many dynasties.They often have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in order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legitimacy and credibility.In this process,they have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connection with huge explanatory space of Confucianis m,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ules,the ideology identity among the state,the judge and the social,and considerable pressure of judges.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judge also faced the conflict between nongovernmental customs and state laws,but they have really difficulties in four major aspect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judges,including the ideology non-identity among the state,the judge and the social,non-aboriginality of the judge knowledge system,non-feasibility of the judicial purpose and non-socially of the judicial activities.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is the real Chinese judicial achieving harmony.
nongovernmental customs;settlement of disputes;legality;public trust
词】DF08
A
(责任编辑:张保芬)
1002—6274(2010)03—040—09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间习惯与和谐司法研究”(07FXB009)、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民间习惯与农村民事纠纷的司法化解”(07SFB2008)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间习惯与基层民事纠纷的司法化解”(07JD82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张镭(1967-),男,江苏盐城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及纠纷解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