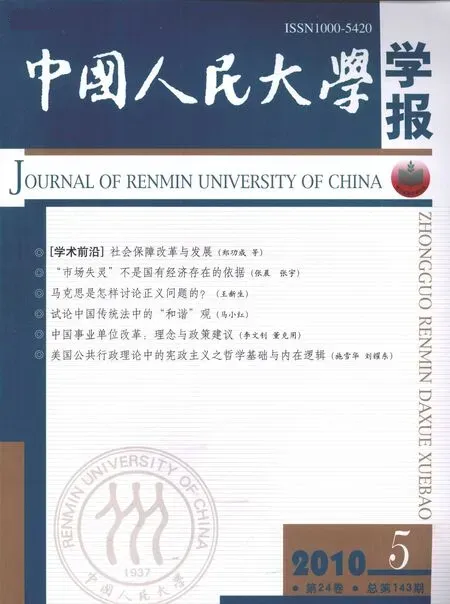中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与非典型担保的命运
高圣平 张 尧
中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与非典型担保的命运
高圣平 张 尧
从《经济合同法》,经《民法通则》、《担保法》到《物权法》,我国担保物权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虽然它大胆融合了两大法系的担保制度,但仍然无法满足信贷实践的需求。非典型担保是在法典之外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担保形态,但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非典型担保实难取得担保物权地位。在我国已经承认一般意义上的动产抵押制度,几乎所有动产均可设定担保权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引进让与担保这一具有体系异质性的制度。
担保物权;非典型担保;让与担保;按揭;物权法定
世纪之交,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所催生的大量融资需求,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担保制度进行了革新,中国亦不例外。肇始于1993年的中国物权法起草工作[1],至2007年终于尘埃落定。其中对于担保物权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但就物权法施行近三年的情况来看,其制度设计仍然无法满足资本市场和信贷实践的需要。本文不揣浅薄,拟就中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及非典型担保的命运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家。
一、从《经济合同法》到《物权法》:中国担保物权体系的形成
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法上债的担保制度从1981年《经济合同法》首开其端,但该法中除了规定加工承揽合同中承揽方的留置权之外,并未涉及其他类型的担保物权问题,没有形成普遍意义上的担保物权制度。及至1986年《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抵押权和留置权(其中,抵押权涵盖了大陆法上的抵押权和质权),但该法并未承认“物权”,且把抵押权和留置权规定于“债权”部分,导致抵押权和留置权的权利性质颇受争议。由此可见,《民法通则》仅仅构成了担保物权制度的雏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保障信贷资金和商品交易的安全基本作用的担保制度愈发重要。为应对日益严重的“三角债”问题,1995年《担保法》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对担保制度作了具体化[2],对抵押权、质押、留置权等作了相对细致的规定,为中国担保物权的实践应用和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在中国尚未建立物权基本制度,担保物权的相关制度设计和体系整合均显不足,因而担保物权的实践价值或生命力大打折扣。[3]
2007年《物权法》在物权体系内以4章71个条文的篇幅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担保物权制度,对1995年《担保法》以来的制度发展和司法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至此,中国担保物权体系基本形成。这一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担保物权的类型化而言,仍然维系传统民法上的权利结构,坚守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类型区分。虽然通过对担保物的宽泛规定,解决了经济生活中的财产资本化问题,但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担保物权的种类有限,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之外,实践中无法创造出新类型的担保物权,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的适法性缺失即为一例。
第二,在各类担保物权内部依担保物的类型的不同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比如,抵押权分为不动产抵押权、动产抵押权和权利抵押权;质权分为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权利质权又依权利的不同类别再进行细分。同时,还依所担保的债权性质的不同分为一般抵押权和最高额抵押权、一般质权和最高额质权。这些规定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担保物权体系。
第三,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法上承认普遍意义上的动产抵押权,并大胆引进了英国法上的动产浮动抵押权制度,突破了大陆法上“不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的二元担保物权结构。虽然在不动产抵押权与动产抵押权之间制度设计差异较大,将两者混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加以规定不利于厘清相关特别规则的适用范围和效力,但从一般意义上承认动产抵押权,且对可以抵押的动产不作限制①《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七)项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均可设定抵押权。,为以后动产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第四,就以“权利”作为标的的担保物权,中国物权法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其中,权利抵押权中的“权利”限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②《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二)、(三)项。在解释上,这里的“权利”应仅限于(不动产)用益物权。虽然“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可以抵押,当然包括“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权利”也可以抵押,但是,这里的“财产权利”应限缩解释为仅指(不动产)用益物权,主要包括《物权法》用益物权编中规定的“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等。而权利质权中的“权利”应是除了(不动产)用益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这两种不同模式分际的理由大抵在于:中国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其他国家作为抵押权主要标的的土地在中国无法进入交易领域,不能在土地所有权之上设定担保负担,而且,就中国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用益物权的制度设计本身而言,其权利内容等已经大于其他国家的用益物权,起到了类似于土地所有权的作用。因此,在类型化上自然将(不动产)用益物权归入了抵押权的标的范畴。
第五,权利质权准用动产质权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与英美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相合。但是,中国既承认动产抵押权,又承认动产质权,权利担保权究竟应准用动产抵押权的规则,还是准用动产质权的规则?从中国物权法现行规则本身来看,权利质权置于质权章,在体系解释上应属质权之一种,但其中规则设计却与动产抵押权相似,诸如登记等,而登记的效力又大相径庭,权利质权中登记均为生效要件,但动产抵押权中登记为对抗要件。由此而引发了中国动产担保物权体系内部的不协调:动产质权中,占有(交付)为其生效要件,而同属动产担保权的动产抵押权中,登记却是其对抗要件,占有和登记同为物权公示方法,效力上应无区别,但中国物权法在继受了大陆法上登记(公示)要件模式之后,又继受了英美法上和法国法上的登记(公示)对抗模式,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法在体系内得以化解。
第六,在担保物的立法方法上,采取了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有重复之嫌③在已经以反面排除的方法规定了不能作为担保物的情形之后,对担保物的正面列举即成赘文。,但正面列举有利于为市场主体的担保行为提供向导,反面排除又有利于克服正面列举无法穷尽所可能造成的挂一漏万之嫌,使更多的财产(权利)的交换价值得以利用。就抵押物而言,《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可以抵押,使得几乎所有动产均可作为融资担保工具。就质物而言,《物权法》第223条第(七)项虽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可以出质,没有采取反面排除的立法方法[4](P277),但同条第(六)项规定“应收账款”可以出质。应收账款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未界定的概念,足以涵盖以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权利类型,为以后权利质权制度的发展留下了解释空间。
由此可见,在中国物权法之下,除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作为担保物的财产(权利)外,几乎所有种类的财产均可充作担保物。
二、中国非典型担保制度的学说争议和司法态度——以让与担保为中心
在物权法定的理念之下,担保物权的种类越多,当事人可以选择的担保手段也就越多,信用的授受也就越容易达成。由于物权法规定的担保物权的种类过少,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融资担保方式多样化的需求,因此,让与担保、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附条件买卖)等非典型担保遂逐渐进入实务界和理论界的视野。
非典型担保与典型担保相对而称,两者是依其是否属物权法已规定之类型为标准所作的区分。物权法中已有规定者称之为“典型担保”,物权法中未作规定但在实务和判例法上已经得到确立者称之为“非典型担保”,又称变相担保、变态担保。在比较法上,非典型担保已在动产担保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5](P57)考察其他国家的非典型担保制度可知,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为弥补典型担保之缺陷与不足而在判例和学说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以担保物权之方法为其权利架构,但该制度却足以实现担保债务履行的目的。在中国法之下,非典型担保制度是否合于物权法定主义是其取得合法性的关键,同时也是担保物权立法是否将其典型化并纳入其中的关键。
物权法定主义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物权,既不能创设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学说上称为类型强制),也不能创设与法定内容相异的物权(学说上称为类型固定)。[6](P46)物权法定主义是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奉行的物权法基本原则,理由在于:第一,确保物权的特性,建立物权的体系。物权本与债权不同,债权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由的结果,且仅拘束当事人,只要与公益无涉,法律自不应干预其效力。物权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排他性权利,具有绝对性,事关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如果允许当事人以合同任意创设物权的种类与内容,必将妨害物权作为绝对权的特性。第二,促进物的利用,确保国家经济稳定。物权本身权利的享有与否,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物权的种类,所有权之上权利负担必将变化多样,直接增加了当事人的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易的顺畅进行,影响了物的使用和流通。第三,便于物权公示,确保交易安全与迅速。为使第三人正常评估交易风险,必须将物权关系为第三人所知悉,物权即有了公示的必要。物权法定化,即便于物权的公示,第三人通过外部之表征即可探知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关系,无须另行调查标的物的权属状况,使交易简便迅速。第四,整理旧有物权,适应社会发展。封建时代的物权制度多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使物权制度成了支配他人的工具,同时,同一土地之上由于身份特权的不同需求,成立了重叠的所有权,有碍物权绝对性的确保。通过整理旧有物权,可将其中仍有价值的物权形态予以保留,而将落后的物权种类予以剔除,并可透过物权法定主义,禁止任意创设物权,以防止旧有物权的复辟。[7](P56)
对于非典型担保而言,有学者通过法解释方法而论证其有效性。[8](P52)主要理由在于:第一,非典型担保与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意旨并不抵触。物权法定主义的立论基础已如前述,贯彻物权法定主义的意义并不只是表明立法至上,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因债权自由所产生的交易上动态发展而引起的具有排他性的物权相互之间的冲突,以确保社会财产秩序的静态安全。虽然公示是物权之所以是物权的基本方法,但公示方法的存在并不是承认非典型担保物权性不可或缺的要件。公示的目的在于使第三人知悉标的物之上的权利负担,从而评估交易风险,维护交易安全,因此,如果新的物权对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救济途径已经作了充分的预备,则不能仅以这种权利没有公示方法就否认其物权性。日本学者认为,在赋予非典型担保以物权性的前提下,为了缓和第三人在欠缺公示方法时所遭受的不利益,可以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94条第2项之规定。①《日本民法典》第94条规定“:与相对人串通做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无效。前项规定的意思表示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严格而言,由于让与担保并非虚伪表示,所以为了保护信赖其外观之第三人,只能类推适用该条第2项之规定。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5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仅此而言,在解释论上应当认定非典型担保与物权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秩序并未抵触。[9](P34)第二,非典型担保已构成习惯法上的担保物权。各国民法的法律渊源不尽相同,直接影响了物权法定主义之“法”的外延的界定。日本学界普遍认为,物权法定主义之“法”包括了习惯法,非典型担保即具有习惯法的性质,从而非典型担保并未违反物权法定主义。正如德国民法学者赖泽(Raiser)所言:“民法所以采物权法定主义,其目的非在于僵化物权,而旨在以类型之强制限制当事人的私法自治,避免当事人任意创设具有对世效力的新的法律关系,借以维持物权关系的明确与安定,但此并不排除于必要时,得依补充立法或法官造法之方式,创设新的物权,因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始能适应社会之需要。”[10](P162)非典型担保也就成了成文法之外经由习惯法创设的新型物权的著例。
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是否应将以让与担保为中心的非典型担保纳入中国担保物权法体系,使让与担保成为一种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其他典型担保制度相并列的担保制度,学术界仍然存在许多争议,并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肯定说主张在中国物权法中规定让与担保,其目的主要是用让与担保制度来规范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按揭交易。梁慧星教授认为:“我国民法立法和实务本无所谓让与担保。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房屋分期付款买卖中推行所谓‘按揭’担保。这种担保方式系由我国香港地区引入,而香港地区所实行的所谓‘按揭’担保,来源于英国法上的mortgage制度,相当于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的让与担保。而德、日等国迄今并未在立法上规定让与担保,只是作为判例法上的制度而认为其效力,学说上称为非典型担保。因此,中国物权法上是否规定让与担保,颇费斟酌。考虑到许多地方已在房屋分期付款买卖中采用所谓‘按揭’担保,所发生纠纷因缺乏法律规则而难于裁决,因此有在物权法上规定的必要。如果物权法不作规定,将造成法律与实践脱节,且实践得不到法律的规范引导,也于维护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不利。因此,决定增加关于让与担保的规定”。[11](P416)
否定说不同意将让与担保纳入中国物权法体系。在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物权法建议草案》所列的典型担保形式中,没有给让与担保制度一席之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让与担保本质上违反了物权法关于流质契约的规定。王利明教授认为:“让与担保的情形比较复杂,在不同让与担保中,权利人的权利效力有所不同。就日本法上规定的让与担保来看,弱性让与担保,债权人优先受偿时应为结算,更具有担保物权的特性。但让与担保毕竟缺乏公示性,债务人在清偿债务后,向债权人请求返还标的物的请求权只是基于债权的请求权,而非基于其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因此,在物权法中可不规定让与担保。”[12](P419)“无论是让与担保还是所有权保留,抑或是买回等制度,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交易的需要,而基于契约自由原则产生的具有内在担保机能的新型制度。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出现相同,由于现代信用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型的担保债权实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从传统的物权与债权二元体系的角度确实无法将这些新型的保障债权实现的方式归入适当的位置。如果非要人为地将这些新型的制度与抵押权、质权等历经千年历史发展而非常成熟完善的制度规定在一起,不仅存在技术上的障碍,而且可能限制它们的发展。”[13](P339)
中国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②重要的文献还有:贲寒《:动产抵押制度的再思考——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对动产抵押与让与担保制度之规定》,载《中国法学》, 2003(2);刘保玉《:担保法疑难问题研究与立法完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姚辉、刘生亮《:让与担保规制模式的立法论阐释》,载《法学家》,2006(6);高圣平《: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与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载《法学家》,2006(5)。,但中国物权法最终没有将让与担保法典化。此点与中国台湾担保物权编的修正几乎完全相同。在中国台湾物权修法过程中,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已为学说和判例所承认的让与担保制度成文化,但终未成功。[14]
理论上的争议无法阻挡信贷实践的发展,让与担保的制度优势日益为实践所接受,并渐为实践所采纳,由此而引发的纠纷也在拷问中国的司法态度。我国司法界普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非典型担保没有法律规定为由,否定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并进而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第二种观点以尊重意思自治为核心,不仅承认担保合同的效力,而且承认具有物权内容的非典型担保的完全物权效力[15](P21);第三种观点认为,当没有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时,应承认非典型担保的合同效力,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并不因此承认其具有物权担保效力,不能产生物权,除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明确承认外,非典型担保仅为债权担保方式,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16]“当事人创设的物权类型不符合法律规定,将导致物权不能设立、不能产生物权效力的后果,但旨在设定物权的合同仍然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将当事人设定的权利看成债权。例如,当事人约定设立让与担保,因物权法未规定该担保物权类型,使该让与担保不生物权效力,但因让与担保合同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的,如一方违反约定将承担违约责任。”[17]
中国司法实践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甲公司欠乙公司1000万元,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甲公司将其楼房产权过户给乙公司;甲公司在3年内偿还乙公司全部欠款,乙公司收到欠款后将房屋产权证及产权还给甲公司;如果甲公司不能按期偿还欠款,乙公司永远取得房屋产权。后甲公司没有依约偿还欠款却进入破产程序,其清算组提起诉讼请求乙公司返还房屋产权。对该案,一审法院认定为抵押,但因违反禁止流押之规定而无效,判决乙公司返回房屋产权。二审法院认定为让与担保,并认定双方约定合法有效。但同时认为,诉争的房屋价值超过欠款,如果因甲公司不能偿还欠款而使乙公司取得房屋所有权,有失公平。因此,判令乙公司返还甲公司产权,乙公司对该房产在甲公司破产程序中享有别除权。
笔者认为,就上述个案而言,让与担保制度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担保物权之地位,大抵还是在违反物权法定的法效上进行考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让与担保的非典型担保(物权)地位不同。在中国司法现状之下,尚无法通过解释而证成让与担保的物权地位。
让与担保在便利融资的同时,有利于发挥物之效用。它是一种没有被物权法正面认可的制度,如欲适用该制度,必须在运用防止暴利行为手段的同时,努力赋予让与担保契约以担保制度所必需的一些法律内容。但仅依解释是无法轻易达致理想状态的,因此催生了相应的立法诉求。[18](P544)然而在我国,若对其进行立法规制,不仅会对原有民法体系造成冲击,也面临着潜在的市场风险。况且,在我国现有担保物权体系下,动产担保的完善也对让与担保成文化的合理性提出了疑问。
三、让与担保的成文化及中国法上的应有态度
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国家沿袭罗马法上的信托行为理论并吸纳日耳曼法上的信托行为成分,经由判例、学说所形成的一种非典型担保制度,其特征是以移转所有权的方式作为担保。这种制度各国民法一般都未加以明文规定,但在担保实务中被广泛利用。“作为私法领域中私生子的让与担保制度,在长期遭受白眼之后,终于获得判例法承认而被认领。”[19](P241)
让与担保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担保物权的概念。大陆法传统的担保物权机理是在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有之物上设定定限物权以为担保,担保权人对担保物只享有担保物权(定限物权)。而让与担保的担保机理是在债务人所有之物上设定担保,担保权人对担保物享有所有权,但此所有权只起担保作用,担保权人不能为担保权之外的处分。让与担保制度初创时,由于其突破了物权法定主义,尤其是突破了传统民法对集合动产、将来取得的财产设定担保负担的限制,被实务界所广泛采用。让与担保的设定无须移转担保物的占有,使其克服了不承认动产抵押制度国家的制度缺陷。
就让与担保的成文化,各国由于立法传统和经济现实的差异,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日本法上,针对特定动产所制定的特别法,已完成其时代使命,或因被其他(如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等)后起制度取代,实际上利用情形甚少。为克服民法规定中债务人无法兼顾动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弱点,非典型担保确立了动产担保的非占有化,但因取代移转占有的公示方法并未确立,非典型担保仍然停留在实务针对个案解决的阶段。经过长期的累积及学说的整理,其虽已形成独立的领域,但像动产范围的确定、流动动产让与担保、对第三人保护等重大问题,并无较为一致的见解。在未取得多数共识的情况下,各国对于制定一般性的动产抵押法多采消极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泡沫经济逐渐显现出趋于破灭的端倪,日本民法学界认识到了处理泡沫经济后遗症与担保法制度改革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因而展开了旨在修改担保法的大规模学术研究,并积极推动担保法制的改革。日本从2001年正式开始对担保法及其相关民事执行法进行修改的工作①关于日本担保法制改革的介绍,参见段匡《:日本近年担保法的修改对我国担保法修改的若干启示》,载渠涛《:中日民商法研究》,第5卷,16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范纯《:日本担保法制改革》,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迄今为止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民法典中的担保物权以及与其相关的程序法改革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以动产、债权让与担保的公示制度的完善以及最高额保证制度的创设为主要内容。另外,在这两个阶段之间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改革环节,这就是不动产登记的电子化改革。[20](P439)
以西方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同时注入现代民法的修正原则的《韩国民法典》,深受《日本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和《伪满洲国民法典》的影响[21](P278),其担保物权体系仍然坚守动产质权与不动产抵押权的二元格局。②《韩国民法典》第八章质权和第九章抵押权。中文译文参见金玉珍《:韩国民法典》,载易继明《:私法》,第3辑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本文所引《韩国民法典》条文均出自该处。但企业融资规模的日益扩大所产生的降低融资风险的需求,直接导致了动产的担保化。与日本相似,韩国先是在判例上发展出动产让与担保制度。虽然《韩国民法典》第339条明令禁止流质契约③《韩国民法典》第339条〔流质契约的禁止〕规定“:出质人,不得以债务清偿期前的契约,使质权人代替清偿取得质物的所有权或不依法律所定方法,约定处分质物。”,但并无直接禁止流抵押契约,因此,当事人在不违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即不构成暴利),可以设定流抵押契约,如此,让与担保制度取得了其存在的空间。此后的判例学说发展出现了《韩国民法典》第607条与第608条④《韩国民法典》第607条〔代物返还预约〕规定“:就借用物的返还,借用人预约以其他财产权的移转代替借用物的,该财产预约当时的价金不得超过借用额与附加利息的合计额。”第608条〔不利于贷与人的约定的禁止〕规定“:违反前两条所定当事人的约定,不利于贷与人时,即使为还买及其他名义,亦不发生效力。”与让与担保关系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集中于让与担保实行时所可能出现的暴利行为是否适用《韩国民法典》第607条和第608条的问题。学界通说认为,让与担保亦应受第607条和第608条的限制,由此,让与担保权人在实行其担保权时即有清算义务,准此以解,韩国仅承认相对的让与担保(清算型的让与担保)。由于适用第607条和第608条,债权人不能通过流抵押特约获得超过债权额的利益,因此出现了债权人利用起诉前和解制度来谋求超额利益:一则可以自主解决争议,回避复杂的裁判程序,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时间和费用;二则债权人可以在起诉前和解,直接办理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登记,利用其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回避强行规定。[22](P246)这显然有违债务人设定让与担保的本来意图。同时,债权人实行担保权时,债务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与债权人的清算金返还义务的履行并不存在同时履行关系,债务人先将标的物交付给债权人后才发生债权人的清算金返还义务,债务人的清算金返还请求权即无保障。由此而引发了依特别法调整让与担保关系的呼吁。韩国于1983年参照日本《假登记担保法》制定了《关于假登记担保等的法律》。⑤《韩国关于假登记担保等的法律》于1983年12月30日公布,1984年1月1日起施行。与《日本假登记担保法》仅调整假登记担保、不调整让与担保的情形不同,《韩国关于假登记担保等的法律》调整范围包括了假登记担保⑥这里的假登记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担保债权人为担保债权的清偿,以债务人或物上保证人的不动产为标的签订代物清偿预约或买卖的预约,其预约内容是为了以后债务人在清偿期间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行使其预约完决权以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为确保所有权转移请求权的实现而在履行期之前设定假登记的担保方式。、让与担保和卖渡担保,遂使韩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将让与担保成文化的国家。
中国法上是否应引进此制度?本文的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比较考察承认(即使从判例上承认)让与担保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不难发现,让与担保制度之所以被认可,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没有从普遍意义上承认动产抵押制度,而动产担保化的需要日益紧迫,传统上的动产质权又无法满足担保人继续利用担保物的需要,让与担保即进入实务家的视野。但是,让与担保制度至今未被主要大陆法国家成文法所采。[23]中国在创制担保法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了动产抵押化的重要性①《民商法论丛》在第2卷、第3卷分别登载王泽鉴教授、梁慧星教授的专文(《动产担保制度与经济发展》、《日本现代担保法制及其对我国制定担保法的启示》),以为呼吁。,进而突破了传统的担保物权体系,引入了英美法上的动产担保制度,在担保法中明文规定了动产抵押。该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无法否定其先进性。既然中国已经承认了普遍意义上的动产抵押制度,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引进具有同样制度功能的让与担保制度。
中国物权法最终没有规定让与担保制度,主要理由是:让与担保主要涉及动产担保,而物权法对动产担保已经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如动产抵押权、质权,可以解决动产担保的需要。[24](P367)这些制度比让与担保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完全可以满足动产担保融资的需求,没有必要再设立让与担保制度,造成制度的“闲置”和功能重复。[25](P281)
第二,引进让与担保对中国物权法的体系构造将造成极大的冲击。
首先,在传统物权法之下,物权体系以所有权为中心,然后推及至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由此而形成自物权与他物权的格局。其中,自物权(所有权)是物权体系架构的前提和基础,而他物权只不过是自物权的不同利用方式而已。准此,所有权即具有“至上性”,其权能丰满、结构完整,而他物权之中的担保物权则是利用所有物的交换价值的定限物权,担保权人对于担保物并不享有所有权,仅享有就其变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其权能远不如所有权。但让与担保是将所有权作为担保工具,担保权人对担保物享有所有权,但这一所有权又不同于作为物权体系基础的所有权,并不具有完整的所有权权能,担保权人除了具有就所有物的变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之外,并不能为担保权之外的处分。在维系担保物权的定限性之下,植入一个“所有权”权能残缺的让与担保制度,与所有权的整体性相矛盾,破坏了物权体系的完整性,也使得该担保制度与其他担保物权制度在逻辑上难以协调。[26]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2002年12月17日)第26章和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0章虽然规定了让与担保制度,但是依其制度设计,让与担保权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且登记为让与担保权的生效要件;在让与担保权的实现时,担保权人需要履行清算义务。相较其他担保物权制度,这些内容并无实质区别。两者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让与担保权以“所有权”作为担保,“所有权”的至上性决定了让与担保权与其他物权相竞存时具有绝对优先于其他物权的效力。但仅此并不足以作为引进让与担保之理由。绝对地赋予让与担保权以超优先顺位并无正当性,让与担保权既属担保物权,自应适用担保物权竞存时的优先顺位规则。通说认为,同一标的物上的数个担保物权之间依其取得对抗第三人效力的时间先后确定其优先顺位。准此以解,让与担保权的优先顺位应依其取得对抗第三人效力的时间(公示之时)来确定,并不因其以“所有权”作担保就当然具有超优先的顺位。
第三,引进让与担保将面临潜在的交易风险。让与担保虽然可以弥补典型担保的不足,有其正面的社会作用,但其利用超过担保目的的“所有权移转”作为手段,存在着典型担保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交易风险。就债权人而言,由于标的物由债务人占有,让与担保又无需公示,债权人无法对第三人主张其“所有权”,如果债务人擅自处分标的物时,债权人即无法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有丧失标的物所有权的风险。就债务人而言,由于标的物的所有权由债权人享有,在逐利本性之下,债权人极易利用债务人的窘迫需要,迫使债务人就主债务的履行订定苛刻条款,在主债务得不到清偿时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使债务人蒙受极大的损失。就第三人而言,由于让与担保具有隐蔽性,没有以一定的公示方法让第三人知悉,第三人极易蒙受不测之害。同时,让与担保当事人之间易于就其债权额或标的物之估价造假,因此,设定人的一般债权人的权利极易受到损害。[27](P900)
第四,以调整“按揭”为由引进让与担保,理由不充分。正如前述,大多数学者主张引进让与担保制度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实务中房地产按揭纠纷处理上的于法无据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实务中的按揭究竟是什么?现有规则是不是不敷适用?
按揭一词本是香港人根据广东话的发音将英文对应词“mortgage”音译而成。在英国法早期,“mortgage”是指债务人将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于债权人作为担保,债务届期不获清偿时由债权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债务届期获得清偿后该财产的所有权再移转予债务人的一种物的担保形式。但其后的发展史上,“mortgage”并不置重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权利人依“mortgage”往往并不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而仅仅只享有定限性的权利。此时的“mortgage”已与大陆法上的抵押大致相当。[28](P9)香港法承袭英国法,同时将英国衡平法上的“charge”译为“抵押”。在香港,“按揭”和“抵押”被严格的区分:(1)按揭的标的物是楼花,是未来的房地产,而抵押的财产是现存的房地产,而且是法律承认的;(2)按揭的设立要求担保人向按揭权人移转其房地产权利,而抵押的设定并不要求担保人转让标的物的权利。按揭转变成抵押之前,担保人须将按揭财产以信托形式交银行持有,并将有关业权文件交银行存放。[29](P13)
按揭制度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就不断出现的房地产按揭纠纷,审批机关一度陷入裁判的误区,对按揭性质的讨论开始成为房地产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热点。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其一,抵押说。该说认为,银行作为按揭权人对按揭担保的期房或现房享有监督管理权,当按揭人违约时,按揭权人有权处分被按揭的楼花,以该财产折价或变价、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从按揭的设定目的和法律效力来看,按揭与抵押是大致相同的,在性质上并未超出抵押的范畴,与英美法上的传统按揭相去甚远。①参见费安玲:《比较担保法——以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和中国担保法为研究对象》,23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程力:《楼花按揭对我国抵押权制度理论发展的影响》,载马原:《房地产案件新问题与判解研究》,15-16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窦玉梅:《探索于民法中最活跃的领域——最高院民二庭庭长奚晓明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载《人民法院报》,2000-12-15;李晓春、林瑞青:《重新认识商品房按揭的法律属性——以按揭是否转移商品房所有权为中心展开》,载《西部法学评论》,2009(4)。其二,权利质押说。“楼花预售合同中的预购人在与银行签订按揭合同时,事实上对作为担保标的的楼花并不享有任何物权,而仅仅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和获得将来利益的期待权。此时,购房人向银行提供的贷款担保标的不是楼花所有权,而是对开发商享有的债权。所以,楼花按揭明显不属于不动产抵押的法定范围,而更符合权利质押的特征。”[30](P6)其三,信托说。主张期房按揭是一种担保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所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法律制度”,并把期房按揭定性为积极信托和消极信托两种形式。[31](P3)其四,让与担保说。按揭担保必须转移房地产权益予银行,同时,按揭担保人须将房地产买卖合同和按揭担保之房地产权证正本交付银行执管,因此,按揭通过权利的转移达到担保债务清偿的目的,在性质上属于让与担保。[32](P131)其五,新型担保说。按揭具有自身的属性,是我国银行在抵押担保实践中吸收、发展、变异英美法和香港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形式,是我国现行的抵押、质押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也是大陆法系的让与担保制度所不能替代的,它是与传统的典型担保和非典型担保皆不相同,又与它们并列的一种新的担保。[33](P190)
中国内地房地产实践表明,《房地产按揭合同》或《楼宇按揭贷款合同》大体包括了两种担保方式,即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抵押担保是购房人以向开发商所购得的房地产向银行提供偿债担保,但并不移转房地产的所有权;保证担保则是由开发商向贷款银行提供的担保购房人按期还款的保证。同时,购房人、贷款银行与开发商还签有《房产抵押贷款收押协议》,约定在房屋产权证办妥之前,应将购房人持有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交由银行收押。在房屋产权证办妥之后,直接将产权证交由贷款人收押。由此可见,中国内地所说的“按揭”与香港法上所称的“按揭”已大相径庭,上述观点均有失偏颇。[34]笔者主张,按揭在性质上属于抵押和保证的联立,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担保形式。
那么,现有规则对于按揭是不是不敷适用?是否需要将其类型化为一种新型交易呢?就按揭中的抵押部分,我国物权法已作相应规定(登记部分还应参照《担保法》第42、44条的规定);就按揭中的保证部分,《担保法》及相应司法解释已作相当规范;就按揭中抵押人和保证人的责任优先和分担问题,《物权法》第176条已是相当完善,即购房人、贷款银行和开发商可以在合同中作出约定,未作约定时,先由购房人提供的抵押物承担担保责任,不足部分由开发商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准此以解,现有规则对于按揭足敷使用,没有必要引进让与担保这一具有体系异质性的制度。
担保物权制度既是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基本手段,也是社会经济的有效调节工具。我国加入WTO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仰赖于相关制度的供给,担保法制即为其中重要一环。由物权法所构建的担保物权体系实不足以达致这一目标,法典之外的非典型担保制度无疑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要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重新审视物权法定主义?如何重新考量担保物权的体系化方法?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1]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7(3)。
[2] 顾昴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5(5)。
[3] 邹海林、常敏:《论我国物权法上的担保物权制度》,载《清华法学》,2007(4)。
[4] 高圣平:《担保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 Phillp R.Wood.Comparative L aw of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itle Finance.London:Sweet&Maxwell,2007.
[6] 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台北,自版,2004。
[8][32] 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 杨汉东:《让与担保制度之研究》,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89年度硕士论文。
[10]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1]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2] 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3]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4] 陈荣隆:《非典型担保物权的立法化》,载《月旦法学杂志》,1999(49);蔡明诚:《民法担保物权修正对于未来理论及实务的影响及再思考》,载《月旦法学杂志》,2007(146)。
[15] 曹士兵:《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根据物权法修订》,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16] 曹士兵:《对非典型担保的司法态度》,载《人民法院报》,2005-8-31。
[17] 刘贵祥:《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的创新及审判实务面临的问题》(下),载《法律适用》,2007(9)。
[18] 我妻荣:《新订担保物权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19] 费安玲:《比较担保法——以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和中国担保法为研究对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0] 渠涛:《最新日本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1] 郑钟休:《韩国民法典的比较法研究》,东京,创文社,1989,转引自苏亦工:《韩国民法典的修正及其背景》,载易继明:《私法》,第3辑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2] Zhang Tae Huan:《裁判上和解的探讨》,载《成钧馆法学》,2004(1)。
[23] 高圣平:《大陆法系动产担保制度的法外演进对我国物权立法的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06(4)。
[24] 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5] 杨红:《担保物权专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 胡绪雨:《让与担保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兼议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当确认让与担保制度》,载《法学》,2006(4)。
[27]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8] 高圣平:《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9][31] 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30] 刘晋:《楼花按揭的理论研究与法律调整》,载马原:《房地产案件新问题与判解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
[33] 陈耀东:《商品房买卖法律问题专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4] 高圣平:《地震所引发的按揭房贷问题之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5)。
(责任编辑 李 理)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Interest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Non-typical Security
GAO Sheng-ping,ZHANG Yao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system of security interests in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primarily in the Real Right Law of P.R.C.Before that a series of laws on security were enacted,which starts from Economic Contract Law that has ceased,then to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and Security Law.Although it has mixed security interests together which root in the two legal systems,the needs of credit activities still cannot be satisfied.Non-typical security,beyond the code,develops from commercial practice and judicial practice.However,it cannot be a kind of statutory security interes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Numerus Clauses.Since chattel mortgage in the common sense has been adopted in our country,almost every kind of chattel can be encumbered with security right.There is no need to establish title finance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urrent system in China.
security interest;non-typical security;title finance;mortgage;numerus Clauses
高圣平: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2010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物权法担保物权编的不足与立法完善》(CLS-C1032)和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科学研究课题《中、日、韩让与担保制度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东副教授在日文资料上的协助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朴淑京在韩文资料收集与翻译上的协助。本文也是作者在“中日法学教育研讨会”(2009年3月)和“韩国与中国:民事法的现实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3月)的演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与会专家的批评减少了本文的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