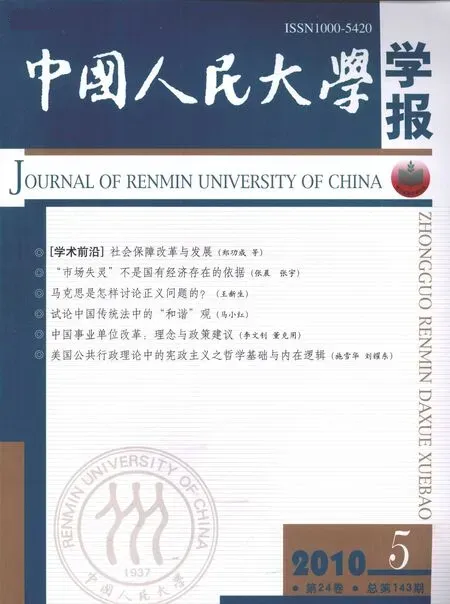马克思是怎样讨论正义问题的?
王新生
马克思是怎样讨论正义问题的?
王新生
通过与自由主义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展现出马克思的正义原则和他为这些原则进行辩护的方式。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权利原则,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存在着一个正义原则的序列: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马克思以贡献原则反对权利原则,又以需要原则批评贡献原则。在讨论正义问题时,马克思确立了一种以物质利益和客观关系等客观性的东西说明正义原则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能够在强调正义之历史性的同时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依据这种方法,正义原则的客观基础在生产制度等客观性的东西,因此,只要使得特定正义原则发挥作用的那些客观条件仍然存在,即使以较低级次的正义原则调节社会生活,仍不失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次优替代方案。
马克思;自由主义;正义;方法论
一、马克思正义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许多讨论,都是在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评中进行的,而且,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相互对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19世纪下半期之后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发展的方向。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阐释,原本是可以直接通过解读他批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文本完成的。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开辟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路径,就使得人们对自由主义批评的方向发生了转移,即从批评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向了批判其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就使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就不能不在呈现马克思文本的同时,考虑当代正义问题讨论中马克思正义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在政治哲学的当代讨论中,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群主义和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复古派的保守主义联手,开创了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语境。在这一语境下,自由主义的“核心错误”发生了转变,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仅仅止步于“形式自由”的保守性,而是相反,转变为要对现代性的破坏性负责的激进性。具体地说,这体现为:它专注于个人而遗忘了社群,专注于程序而忽略了它们得以建立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根基。而从更根本的方面看,这种现代性的激进性源于它诉诸世俗理性的工具性思维方式;这种工具性的思维方式在毁弃了理性的神圣性追求的同时,不仅未能为现代社会重建理性的根基,反而促使现代人对世界以及在彼此之间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从而败坏了正义的根基。
作为自由主义的捍卫者,霍尔姆斯将当前流行的这种批评自由主义的新语境称之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语境。他认为,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实际上处于同样的被批评的位置,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激进性,都是现代性的谋划和推动者。例如,马克思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赞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样是“科学权威和物质至上主义”的信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俗性甚至超过了自由主义,是比自由主义更具激进性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只不过想使宗教非政治化,而马克思主义则要消灭宗教;自由主义无非想要削弱种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则要消灭种族主义。[1](前言)总之,在现代性批判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性质消失了,成为同质性的政治哲学。霍尔姆斯说:对于这种现代性批判语境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表面上对立,但共有一个祖先,并且秘密结盟。它们是一种独有的、精神上徒具其表的启蒙传统的两个分支”。[2](P2)无论霍尔姆斯在看待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时具有怎样的实质性主张,至少可以说他并没有错误地领会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旨趣。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看做具有同质性的政治哲学,这听起来有些怪异,但当问题转换到保守与激进的关系、语境转换到现代性批判路径上时,问题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了。
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同类项合并”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否真正揭示了这两种政治哲学的某种同质性关系?如果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新视角的话,我们又当怎样在不忽略这一视角的情况下把握马克思正义理论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的区别?我们甚至不能不这样设想,如果在面对保守主义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确同样具有现代性指向的“激进性”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在激进的诉求尚未走到分歧点时,它们在政治哲学上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进而言之,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道义根据上的差异并非不可沟通?在当代正义理论的新视角下,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如果说这些问题本来就包含在马克思的思想语境之中,那么,它们在今天才呈现出来这一事实已经表明,这些问题只有通过20世纪以来思想的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才能呈现出来;它同时也表明,假如没有20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这些问题是不可能以目前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二、正义关乎制度而非关乎德性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19世纪的文本,考察他是怎样通过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评来阐发自己的正义理论的。
权利理论是自由主义正义论的基础和核心。一般来讲,自由主义是通过机会平等的权利说明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正义性,通过政治权利的平等说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正义性的。它假定,当且仅当人们之间存在着平等的权利时,个人收入和名望的不平等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易言之,如果存在着机会平等的公平竞争,人们经济收入或名望上的不平等也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在强调权利平等这一点上,新老自由主义是一样的。例如,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美德,一是仁慈,二是正义。它们分别与人的两种情感相关联。仁慈来源于高贵的情感,正义来源于最低限度的同情,而最低限度的同情是靠权利平等的人们共同遵守法律体现的。虽然仁慈之心盛行的社会是人们所期望的,但不义行为的盛行却可以使社会彻底毁灭。“因此,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存在的基础。”[3](P106)罗尔斯则更明确地将其“正义两原则”的第一原则表述为:“每一个人对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都有一种平等的要求。该图式与所有人同样的图式相容;在这一图式中,平等的正义自由才能——且只有这些自由才能——使公平价值得到保障。”[4](P5)可见,权利平等的原则在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论证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所依据的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权利原则。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评首先就是对权利原则的批评,它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对权利原则的直接批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主义主张的权利平等看起来是一种平等主张,实际上却是在主张不平等。对于平等的正义主张来说,不是平等的权利,恰恰是不平等的权利才是合理的。他说:“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5](P22)虽然没有使用正义的字眼,但马克思这段关于平等权利的著名言论表达了他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基本批评。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第二种批评形式是对权利原则的间接批评。马克思论证了根据权利原则必然得出资本主义中存在着的剥削,即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是合理的结论。《资本论》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主义的权利原则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允许实际不平等的存在,允许资本家窃取工人的剩余劳动。
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权利原则和以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这些批评所依据的是什么正义原则?埃尔斯特和金里卡等人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批评实际上援用了两个不同的原则,一个是贡献原则,另一个是需要原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批评对象。金里卡说,在批评自由主义权利原则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剥削时,“马克思的这个结论依据于他对‘贡献原则’的分析——贡献原则断言,劳动者对自己劳动产品享有权利”。[6](P307)而埃尔斯特又说,在批评自由主义权利原则所导致的实质不平等时,马克思有时也援引需要原则批评贡献原则。“因此,贡献原则似乎是一个双面神式的概念。从一方面来看,它是一种把资本家的剥削谴责为非正义的正义标准;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它本身又被需要原则中所表达的更高的标准谴责为不适当的。”[7](P217)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着一个正义原则的序列:权利原则、贡献原则、需要原则。马克思一方面用贡献原则反对权利原则,另一方面又以需要原则批评贡献原则。而当马克思以需要原则对贡献原则提出批评时,不仅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包含了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加以改善的要求。这种多重批判的复杂性为阐释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增添了困难。为了明晰的需要,我们将把其中的一些问题留在下文中考察,在这里集中对金里卡所谓马克思的“贡献原则断言”进行分析。
金里卡的确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与自由主义正义论的根本区别:只要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不合理的剥削,实质上就是主张了一种贡献原则的正义论,因为只有根据贡献原则才能认定剥削是窃取他人劳动的不合理行为。不过,这仍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允许资本家窃取工人的劳动是制度性的,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人性。所谓剥削的制度性,在这里是指:剥削之所以是非正义的,并不是因为资本家违背了不当获得的道义原则,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性地违背了劳动者应当享有自己劳动产品的贡献原则。因此,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说明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资本运动”是如何产生出与贡献原则相违背的非正义逻辑的。
具体地说,在理解马克思依照贡献原则对权利原则以及资本主义所实施的批评时,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
第一,从源头上讲,权利原则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首先涉及资本“出身”可疑性的问题。如果说在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中权利问题占有基础和核心位置的话,那么权利问题中的财产权问题就是论证的难点,因为在财产权问题上资本出身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难题。无论是对自由主义自身还是对它的敌人而言,资本出身的合法性问题都是考察以权利原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正义性问题的逻辑起点。自由主义的先驱亚当·斯密将这一问题称为“预先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则将这一问题称为“所谓原始积累”的问题。
对于必须合理说明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的合法性,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证是诉诸“勤劳—懒惰”的解释模式,以此为资本运动找到一个干净的起点,为后来的资本—劳动的对立找到一个原罪式的起点。马克思说:“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轶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了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8](P820-821)马克思说,通过讲述资本原始积累的故事,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要证明的无非是“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惟一的致富手段”,但“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9](P821)
在这里,马克思的论证逻辑是:根据贡献原则,来源于勤劳的所得是正当所得,因此,从勤劳—懒惰模式出发,当然是可以解释资本原始积累所造成的不平等的。但是,这种解释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依照贡献原则的资本来源的正当性之上,原始的资本必须是勤劳积累的结果。事实是,资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不干净的出身,因此,资本从一开始就不具有这样的正当性。
第二,从根本上讲,权利原则的错误和以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在于它们支持着资本家窃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社会机制。自由主义既然要以贡献原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也就必须说明权利原则是合宜于贡献原则的,是不与其相违背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反驳的正是这一点。至于怎样理解贡献原则在马克思正义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只需引证他在考察了剩余价值问题之后对剩余价值的积累违背了贡献原则的说明就足够了。马克思说:“资本不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0](P611)
马克思的意思是:既然从劳动者有权享有自己劳动产品的贡献原则中可以合理地推论出“有酬使用他人劳动”的正当性,也就可以合理地推论出“无酬使用他人劳动”的非正当性。剩余价值占有的并不是“有酬劳动”而是“无酬劳动”。“无酬使用他人劳动”之所以是非正义的,是因为它不正当地拿走了本属于他人的东西,是一种非正义的盗窃行为。所以,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的资本运作机制是非正义的。
第三,正义关乎制度而非关乎德性。马克思是否依据贡献原则将资本主义判定为不正义的?在这一问题上,当代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如罗默、柯亨、埃尔斯特等人进行过多方面的讨论,存在着许多分歧。这些分歧甚至关涉是否可以合法地谈论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问题。关于这些争论,如果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依据,似乎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埃尔斯特说,马克思的这些文本允许我们进行不同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非常含糊不清”。例如,马克思有时说剩余价值就是“盗窃”,有时又说绝不能将他的观点归结为“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11](P205-206)实际上,理解这些表述差异的关键,是要对关涉制度的正义和关涉个人德性的正义加以区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清马克思所说的正义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从个人层面看,正义是一个与人性的发扬相关的德性问题;从社会层面看,正义则是一个与基本制度安排相关的社会基本结构问题。准确地说,前者是一个关于善的一般伦理问题,后者才是现代社会所谓的正义问题。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古希腊城邦,由于私域与公域、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未分化状况,个人德性与公共伦理实际上是统一的,符合善的个人德性就是正义。近代以来,公域与私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瓦解了善的这种统一性,使德性之善的问题退隐于私域,使制度正义的问题走上前台。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要将古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定位于“一种引人向善的、合理追求我们真实幸福的至善理念”,而又将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定位于“更严格地限定在明辨政治价值而非所有价值的范围内,同时,提供一种公共的证明基础”的基本原因。[12](P10)
马克思所讨论的正义问题只关涉制度而不关涉德性。以此处所谈的剥削问题为例,当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是对工人劳动的“盗窃”时,他并不是要强调个别的资本家有违善的德性,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有违正义。资本家作为制度职能的执行者,无所谓善与不善,更与正义无涉。站在这一区分上,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无含糊不清之处。马克思在澄清人们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误解时所说的话,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我的论述中,‘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13](P401)马克思的这个或类似的言论,常常被一些人用来作为马克思反对用正义的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证据,有时甚至被当成马克思为资本家的剥削进行辩护的证据,但实际上,它们只能成为马克思反对用与个人相关的德性之善批判资本主义的证据。这反过来说明,马克思所理解的正义关乎制度而非德性。
三、问题在于什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正义理论所要讨论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正义原则的问题。一种政治哲学把哪种正义原则看做是根本的,就意味着它在这种正义原则与其他正义原则之间进行了优先性区分。这往往标明了这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上文所论及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就是这一意义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具有相同正义原则的政治哲学就是相同的,它们完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在正义原则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他所批评的乌托邦主义并无根本的区别,它们都以实际平等为优先的价值主张,并且都以此价值主张构想未来社会,但是,它们却是根本不同的。再例如,和极力强调自由价值的近代自由主义者不同,罗尔斯对平等的强调几乎超出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可以容忍的限度,但他的理论仍然是自由主义的。这些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价值主张,同时也在于以什么方式为自己的价值主张进行正当性辩护。因此,要想清楚地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仅仅说明他的正义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他是如何为这些原则辩护的。
马克思为其正义原则辩护的方式非常特别,以至于许多人将他的正义理论与他的唯物史观分割开来,将它们看做是相互冲突的。例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斯特就认为,这二者的差异使马克思的思想显示出某种矛盾性。不过,他较为温和地将这种差异看做是其中的一种张力。[14](第四章)而霍耐特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对社会历史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一种是“按照伦理分裂的模式来解释阶级斗争”,即从正义原则出发解释社会历史;另一种是将作为伦理目的的正义原则还原为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模式”,即以利益冲突解释社会历史。他认为这两种模式是相互冲突的。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使用第一种模式,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了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而不是将其看做为了获取物质资料和权力工具的策略斗争。而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解释就转向了第二种模式。不过,虽然有了这种转向,马克思却常常在后期的著作中背离“功利主义的解释模式”,回到前一种模式中去,从而使这二者之间发生冲突。他断定这是因马克思方法论上的矛盾所致:“马克思本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经济学著作的功利主义途径与历史研究的表现主义途径系统地联系起来,尽管这两种模式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发生了冲撞。……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把他所设计的规范目标安置在他一直都用‘阶级斗争’范畴加以考察的社会过程之中。”[15](P157)也就是说,作为相互冲突的解释社会历史的方法,这两种模式是不可能无碍地兼存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之中的。
对马克思思想方法的这些讨论,开辟了一个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从伦理的角度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新视野,为阐释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提供了许多启示。但是,将马克思的这两种思想内容从方法论上分割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最终只会导致三种可能的结果:(1)肯定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两种不同质的理论,就像上述霍耐特所理解的那样;(2)肯定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仅仅属于科学认知的理论模式,马克思理论的全部任务仅仅在于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能从所欲的道义目标上阐释问题;(3)肯定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在正义原则上批判现实和解释未来的理论,由此认为他关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知路线只是一种错误的决定论观点。这三种理解都将逻辑地得出下述结论: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要么是一个道义目标,要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可能同时是这两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谱系中,对马克思的这三种理解方案都可以找到现实的对应物,这里无需详细分析。在这里需要考察的问题仅仅是: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阐释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方法论之上的?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上述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争论。
如果说我们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与自由主义的比较,才能清晰地揭示出马克思所主张的正义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也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与乌托邦主义的比较,才能清晰地揭示出马克思为这些正义原则辩护的方式。
我们知道,早期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因而他考察社会生活的方式也只能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式的。这一方式以抽象的人性论预设为基础,从应当的道义原则出发说明全部社会历史问题,并未脱离乌托邦主义说明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受伦理应当支配的说明问题的逻辑。在这一逻辑内,具有支配性作用的正义原则既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它的最后依据是抽象的人性论预设,除此之外无需寻找其他的基础。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方法论中走出来的过程,就是超越这一说明问题的逻辑、建构新方法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物质利益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提出在研究国家现象时不应当以“善意”或“恶意”为根据,而应当以“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为根据,应当“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16](P363)以物质利益、社会关系的客观本性为基础,而不是以伦理动机和人的本性为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他摆脱了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限制,建构起考察社会历史的新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确立了物质利益和客观关系的先在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它还超越了从应当的伦理原则出发说明社会生活的目的论路径,确立了以物质利益和客观关系等客观性的东西说明伦理原则的新路径。这一新路径使马克思能够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基础上,将对共产主义的道义目标的正当性论证建立在关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使他摆脱了在事实与价值裂解的思维模式下分割价值尺度与认知尺度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纠缠。[17]这样一种新的方法论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为其正义原则辩护的特殊方式。
在这一新的方法论中,正义原则不再是从抽象人性中推演出来的超历史规范,而是受生产制度制约的历史性原则,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只能从生产制度的历史变化中寻找根据。这样,对生产制度历史性变化的科学认知,就为阐释正义原则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奠定了基础,为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说:“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18](P146)他的意思是,正义原则是历史地变化着的,是因不同的利益主体而有差异的,因而是历史的和相对的,但这些历史的和相对的正义原则却有其客观的基础,这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制度及其变化。这些可以通过认知把握的生产制度的变化,才是我们考虑公平正义问题的关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不同的价值主张,哪些是正义的?哪些是非正义的?我们无法通过它们本身的比较得到答案,只能通过它们与生产制度的关系来把握。马克思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9](P379)
通过对正义原则的这种特殊的辩护方式,马克思把他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与乌托邦主义区别开来,他说:“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从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中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20](P604)在这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他所主张的未来社会虽然与乌托邦主义在道义目标上相同,但理论却完全不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说明规范性的道义目标时,是否以“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为认知的根据;在实现这一道义目标时,是否“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
四、马克思的超越性正义及其次优方案
当马克思说“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时,他实际上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由于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级次系列,而正义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因此,正义原则也就存在着一个级次序列。也就是说,正义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性的,对于当下合理的正义原则来说,一定还存在着具有更高合理性的正义原则。第二,对于具有更高合理性的正义原则而言,当下合理的正义原则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可以用高一级次的正义原则批评低一级次的正义原则。第三,虽然从高一级次的正义原则看低一级次的正义原则是不合理的,但在它仍然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时候就没有理由推翻它,因为它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
依照这一解读和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理解:第一,马克思认为,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正义原则是权利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的正义性需要将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出身的可疑性问题悬置起来,否则它就无法合理说明这一原则。第二,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正义原则的贡献原则是与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适应的正义原则。第三,适应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正义原则是需要原则。
马克思是怎样为他所主张的最高正义原则——需要原则辩护的?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看一看马克思为此原则所进行的辩护,然后再来分析关于这一辩护的争议。
同样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阐述了他最高的正义原则——需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以及与这一原则相匹配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1](P22-23)在这里,必须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在这里主张的正义原则是需要原则,而它的制度体现形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另一方面,与这种正义原则相匹配的社会条件有五个:(1)生产力获得了充分的发展;(2)作为集体财富的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3)奴隶般分工的消失;(4)劳动成为第一需要而不再是谋生的手段;(5)个人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这个著名的正义原则所遭到的非议和引发的争论比他的任何其他观点都要多。不过,这些争论和非议大多不是针对马克思这一正义原则的合理性,或是针对马克思关于它的辩护方式,而是针对与这一正义原则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实现的可能性的。由于马克思对其正义原则的辩护正是根据与其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因此,这种混淆不仅容易发生,而且似乎在很多情况下也并未降低批评的效力。但是,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批评者都是从马克思的论辩方式出发批评这一正义原则的。对于那些一方面不认可马克思将正义原则与社会制度相关联的考察方式,另一方面又将这两者相混淆的批评者来说,即对于那些主张不应通过现实的生产制度说明正义原则的批评者来说,这种混淆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些批评者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不应将正义原则消融于历史的必然之中,另一方面又从需要原则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上批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于这种批评,需要的不是论辩,而是找到论辩的同一标准。实际上,马克思为其正义原则辩护的方式,已经为他的批评者规定了批评的路径:要么说明需要原则并非合理的正义原则,要么说明正义原则不能够与上述条件下的未来社会相匹配。至于与需要原则相匹配的未来社会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一论辩的范围,属于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需要认真对待的倒是另外一类批评,即认为马克思的需要原则违背了他自己关于正义只能是历史性的和相对性的观点,因为在这类批评者看来,诉诸需要原则就是诉诸一种抽象的正义原则。埃尔斯特认为,在马克思说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时,他已经彻底地否定了“抽象的正义原则”。但是,“当谈到贡献原则的‘缺陷’时,马克思明显地乞求于一种更高的正义原则——按需分配。无疑,马克思相信,他在这一段中已经提出了对任何一种抽象正义理论的致命反驳,但他没有注意到,在这样做时,他却乞求了一种他想摒弃的理论”。[22](P210)埃尔斯特所说的“这一段”,是指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引用过的那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平等的权利”的话。在那一段话里,马克思不仅指出“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而且接着说:“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3](P22)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弊病”,是指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匹配的权利原则的弊病,也是指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匹配的贡献原则的弊病。也就是说,马克思是根据一种既超越于权利原则也超越于贡献原则的最高正义原则——需要原则来批评“这些弊病”的。埃尔斯特认为,在这段话里,本来“马克思意在对各种正义理论提出一种一般的反驳——主张‘任何一种体制在它们通过一般规则而运作的意义上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任何一种一般规则都完全忽视了个人之间的相关区别”。[24](P210)但是,马克思的需要原则仍然是一种抽象原则,因为它要求人们在需要原则面前得到抽象的同等的对待。他说,马克思反对谈论抽象的正义原则,在这里又诉诸最高的正义原则,“这反映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些踌躇”。[25](P211)
我们无需再对埃尔斯特的这种批评费太多的笔墨,而是只需指出,适用于为贡献原则辩护的理由也同样适用于需要原则。在马克思那里,需要原则同样是历史性的正义原则,只能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制度和其他客观的社会条件相匹配,或者说,需要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制度和其他客观社会条件来说明它的合理性。马克思在讲到“按需分配”时所谈到的那些社会条件虽然是极为粗略的,但却清楚地说明马克思贯彻了自己的论辩原则。根据他的论辩原则,需要原则依据的并不是抽象的需要,而是生产制度等客观的社会条件。埃尔斯特虽然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正义原则历史性的思想,但却未能完全理解马克思通过把握现实社会条件的历史性为正义的历史性进行辩护的特殊方式,因此,将诉诸需要原则看做是对正义的抽象理解。
对正义原则的抽象理解,就是将正义原则从它所属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抽离出来,使其成为抽象的概念,而对马克思来说,正义原则的历史性就是指它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获得单独的理解,因此,也就不存在某种独立于生产制度之变化的抽象不变的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正义原则的历史性并不是仅仅说它们是一种历史性的前后替代关系,而是指正义原则将会依照包括生产条件在内的各种社会条件的历史发展而变化,即使在同一形态的生产制度之内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说需要原则是对贡献原则的超越时,就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了与其相匹配的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可以原则性地对它们进行区分;同时,它也以这种方式说明,现实条件之间的区分并非如同概念区分那样截然分明,这种阶段性并不是阶段之间的僵死界限,因而也就不存在需要原则与贡献原则之间的抽象对立,就像不存在贡献原则与权利原则之间的抽象对立一样。
这样看来,当马克思用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匹配的贡献原则批评了与资本主义相匹配的权利原则,并站在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相匹配的需要原则的立场上指出贡献原则的“弊病”时,固然是指明了正义原则的暂时性和相对性,但是,当他将这些正义原则的依序替代与生产制度等社会条件的客观发展相联系时,也就使自己在坚持正义原则历史性的同时避开了相对主义的陷阱。问题不在于人们的正义原则是什么,而在于“什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只要那些使得权利原则能够发挥其作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权利原则就不会被贡献原则所替代。同样,对于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与需要原则相匹配的社会物质条件的积累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贡献原则乃至权利原则对社会生活进行制度性的调节,当然也就不失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次优替代方案。
[1][2] 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12]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13][21][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 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7][11][14][22][24][25]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9][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5]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王新生:《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载《哲学研究》,2007(8)。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李 理)
What Is Marx's Way of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Justice?
WANG Xin-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By comparing with liberalism,the theory of justice and the discussion way of Marxism can be clearly demonstrated.“Right principle”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core of liberalism,while in Marxism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s in such sequence as right principle,need principle and contribution principle. Marx used the“contribution principle”against“right principle”,and he used the“need principle”criticize“contribution principle”.In the discussion of justice issues,Marx established a special method which focuses on“material interests”and“objective relations”.This enabled him to emphasize the relativity of justice and avoided running into the trap of relativism at the same time.According to this method,the objectivity of justice is basis on the objective things such as production.So if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a society still exist,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for it will play its role.Even if a lower level justice regulates social life,it is still a social justice,and we can say it is a second-best alternative.
Marx;liberalism;justice;methodology
王新生: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