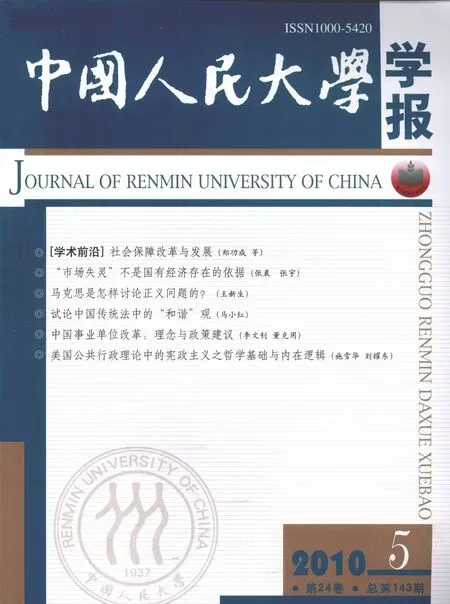古代性和现代性,还是中国与西方?
——对中西哲学比较的一个考察
聂敏里
古代性和现代性,还是中国与西方?
——对中西哲学比较的一个考察
聂敏里
长期以来,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的错误,这就是将本来属于时间性的文化差异错误地解读为属于地域性的文化差异,并且将中西哲学带入到地域性文化的视野中予以考察,结果造成了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在根本上的扞格和不可沟通。如果我们对比中西哲学中同属古代世界观范畴的一些普遍的思想范式就可以发现,长期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传统因素的理性,尤其是理论理性和科学理性,在古代中国也有其最初的表现,同时,它们作为萌芽在古代西方也同样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观察视角就优越于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比较模式,它使得我们可以对无论是中国的古代和现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和现代,都取得一种基于历史的批判的视野。
古代性;现代性;地域性文化;中西之别;古今之争
一
长期以来,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存在着一个极大的思想误区,这就是学者们都不假思索地将中西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思想上的差别看成是“中国的”和“西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域性文化的差别,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表面上看来属于文化的地域性的差别,实际上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却是古今思想的差别,在任何一种文化比较中都必然会发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各种地域性的差别实际上是处于次要的地位的。可以说,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在进行比较时都忽略了他们实际上用以进行比较的思想对象是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的。比如,被用来比较的“中国哲学”实际上经常限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哲学,而被拿来进行比较的“西方哲学”则往往多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且不说这样一种忽略了比较对象的时间差异的简单并列的比较方法,对于比较对象的考察必然缺少一种思想史的批判的眼光,单就表面来看,构成比较的双方在时间上就是不对称的,一方实际上属于现代的范畴,而另一方则属于古代的范畴。由此发现的种种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古代的中国思想和现代的西方思想之间的差异。比较的这种时间上的不对称就使得所进行的比较本身成为很可怀疑的。
人们会认为,也许通过比较对象的调整,例如,如果拿中国的古代哲学和西方的古代哲学进行比较,那么,中西之别而非古今之别在中西哲学比较中的首要地位就仍然会被确立起来,而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基于各自地方传统而来的思想文化的根本差别也就可以显现出来,从而文化的地域性的差别就被证明仍然是中西哲学比较中的根本差别。但是,这样一种侥幸的想法也被证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知道,古今之争的问题自17世纪以来就成为西方思想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①1688年,法国学者Charles Perrault发表的《古今比较》(Parallèle des et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是这一讨论的一本标志性著作。维柯1708年发表的《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以及他的一系列演讲也集中了这一主题上的讨论。扩而言之,像培根的《伟大的复兴》、笛卡尔的《谈谈方法》等著作,都是开古今之争风气之先的著作。,而这个问题的提出毫无疑问是根源于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人自己强烈地感觉到,无论是一般的社会生活,还是基本的世界观,同古代相比都发生了根本不同的变化。古代的世界观被现代的世界观所取代,与此相适应,古代和现代,古代性和现代性,古今之别、古今之争的问题,就都被提出来了。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来思考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古代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的根本不同,有关这一主题的思想书写可以说构成了自16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书写的主流。②有关古今思想的比较就不用多说了,就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来说,贡斯当的《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就专门对古今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韦伯本人所进行的关于新教、犹太教、印度教、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从社会制度范式的角度出发对当时正处于深刻的现代化变革之中的德国所发生的古今之争的具体理论回应。而德国文学史上的狂飙突进运动、浪漫派也都可以看做是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对开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上的反映。
西方的现代开始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但中国的现代却开始于20世纪初。从14、15世纪起,一个现代化运动开始萌芽于意大利,然后渐次波及西欧、北美,接着又返回来影响了中欧、东欧,到19世纪中叶,这场现代化运动开始呈现出一种强劲扩张的态势。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尚处于古代。这样,当19世纪下半叶,发轫于欧洲的这个人类的现代化运动越过辽阔的海洋而与尚处于古代社会的中国发生猛烈的碰撞的时候,一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也就相应地发生了,而这同时也就是中西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的开始。但不幸的是,与此同时,一个比较上的时间的错乱也就被铸成了。很显然,实际发生碰撞和比较的是人类的古代思想和人类的现代思想(我下面将说明这一点),但是,由于进行比较的双方都忽略了各自的时代属性,使得本来属于人类古今思想的差别就被误读成了中西思想的差别,而文化的地域性的差别被看成是这一比较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实际上,只要我们拿同属于人类古代思想范畴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古代哲学稍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在这一比较中,文化的地域性因素是次要的,而真正重要的是文化的普遍性的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各自的古代和现代,它们除了在结束和开始的时间上不同之外,在基本的世界观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举例来说,气本论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它开始于先秦,在宋代朱熹的理气一元论中达到顶峰,在清代王夫之那里仍然得到发扬。人们通常会说这是“中国的”。但实际上,稍懂一点古希腊哲学的人都知道,早在米利都学派那里,阿那克西美尼就已经把气当成世界的本原,并且按照气的凝聚和疏散(这里请试对比中国哲学中的概念,例如盈虚、开阖、翕辟、消长,等等)来理解宇宙生成的内在机理。在希腊化时期,斯多亚学派还发展出了一个系统的、以所谓的“火的嘘气”(Pneuma)为世界本原的宇宙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Pneuma不仅被认为是宇宙运动的物质基础,而且被认为是logos,即宇宙运动的理性法则,此外还是宇宙生命的内在灵魂。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被叫做气本论的宇宙论体系对西方思想影响深远,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被注重数学和实验的近代科学的宇宙观所取代。③请参考培根的如下一段话“:人的脑袋上都长有7个小孔,通过那些小孔,元气才得以流遍全身,并且给身体以启迪、温暖和滋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培根紧接着还谈到了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对应关系“:那么,这个小宇宙的这些部分是什么呢?它们是两个鼻孔、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巴。因此,在天上,在大宇宙里,也存在着两颗吉星、两颗灾星、两颗发光的天体以及一颗飘忽不定且不吉不凶的水星。从这件事情中,以及从大自然的许多相似物中,诸如7种金属等等(这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可以断定:行星的数量必定是7个。”转引自查尔斯·泰勒《:黑格尔》,5、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通过这一比较,我们很明显地就可以建立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古代哲学思想之间在基本世界观层面上的一种思想类比关系,而属于人类古代思想的普遍性也就很自然地可以被发现。
当然,人们实际上可以在自然目的论的体系、生机论的自然观、封闭循环的宇宙图景等多个方面对古代中国的思想和古代西方的思想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一致性,而地域性的文化差别则会被证明是次要的。除此之外,像天人感应的观点、天人合一的观点、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观点等等,这些在通常的对古代中国思想的观察中最容易被发现,也最容易被作为特征物提取的思想因素,假如我们考察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晚期希腊哲学,那么,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在斯多亚学派那里,我们同样可以找到近似的理论模型①例如,关于大宇宙、小宇宙的观点,除上引的培根的那段话外,我还可以提供一条更古的材料。在一部从风格上可以确定起源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伪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论七天》()中,在其前十一章,世界被分成七个部分,以与人体的七个部分对应。(参见 G.S.Kirk,J.E.Raven and M.Schofield.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2rd edition,p.5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除此之外,我们当然还可以举出盛行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以赫尔墨斯为名的炼金术士的神秘学派及其丰富文献,其在自然观上有着更多的东方元素。,尽管我们不应当忽略它们在术语方面以及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因为,毕竟在古典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由于工商业的繁盛,西方有一段长达两三百年的比较成熟的理论理性思维发生、发育、发展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比较牢固的理性传统。但是,如上所说,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在基本的世界观方面是近似的。那种万物交感的观点我们不是同样可以在新柏拉图主义充满了精灵鬼魅的世界图景中找到吗?同样,在新柏拉图主义的个体灵魂摆脱肉身桎梏最终达到与宇宙灵魂、理智、太一的完满统一中,我们不是也看得到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非常接近的东西吗?这种天人合一的追求,这种完全自然主义的道德观,不是也同样体现在斯多亚学派的虚己待物的圣人理想之中吗?而在“合乎自然而生活”这一经典的斯多亚学派的格言中,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典型的中国思想的元素吗?所以,在这里凸显出来的不是别的,仅仅是古代基本的思想模型,是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根本差别,而不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根本差别。
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中西方诸多的一致之处。在库朗热的《古代城邦》这部研究古希腊前古典时期城邦社会结构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其在信仰、礼俗、仪轨、制度等等方面和中国战国时期以前的社会生活有诸多可比之处,而事实上,作者经常拿来进行有效对比的就是古希腊的各种礼俗、法典和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中的相关内容。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礼记》各篇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早期宗法社会的种种仪轨同古希腊罗马法典中所记载的种种礼俗内容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是一个极好的学术生长点,而且我们一定会在古代人的社会生活方面有惊人的发现。
二
在这里,人们也许可以针对上面的考察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反驳,即:西方思想从古希腊以来就是注重理性的,而中国思想却似乎缺少这种理性的特质,就此而言,中西之别仍然可以成立,而且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观察视角。
对此,我们的回答首先是,指出这一点是正确的,而且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科学产生于西方而没有产生于东方。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科学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传统,或者理性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当人们指出理性萌芽于古希腊、科学也萌芽于古希腊时,不要忽略了这种理性的萌芽形态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于中国的先秦,例如,出现在墨家学派、名家学派、阴阳五行学派以及儒家的荀况学派那里,并且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因素事实上一直存在于古代中国的思想之中,而理性的特殊一维即伦理理性和政治理性则始终存在于居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和从未断绝过的法家学派那里。同时,当人们把理性特别用来指称科学的理论理性时,人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古希腊得到初步的繁荣和发展的这种科学理性,也只是科学的萌芽形态,必须把它同近代以来的科学在基本的世界观方面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正像这种科学理性虽然也在中国的先秦萌芽,但却由于宗法制在汉初迅速地恢复了其牢固的专制统治地位,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样,萌芽于古希腊的科学理性在古代西方也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它不仅被毁坏在了如培根所指出的重神秘的思辨和玄想的古代思想方式中,而且也受到了西方古代世界晚期同样牢固的宗法社会结构的压制,否则,我们就不能谈论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近代理性主义的兴起,而培根的《伟大的复兴》连同他所倡导的“新工具”也就失去了伟大的历史意义。
除了不要混淆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差别以外,一个可以进一步补充的证据就是,进入到公元6世纪后,也就是在古典世界衰微的时期,不仅科学甚至一般的理论理性在西方也同样走向了衰微。人们通常把这一古典文化在古代晚期的衰微归结于蛮族的入侵,从而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偶然的事件,但是,正如《剑桥中世纪哲学指南》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成见性认识。事实上,蛮族对古典文化的破坏是极其轻微和外在的,相反,是基督教的兴起并最终取得了在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才直接造成了科学理性在西方世界趋于停滞和消失。随着基督教在公元6世纪以后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西欧普遍的精神信仰形态,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神权统治,基督教由最初对理论论争和理论建设的重视,转向了更为注重宗教实践,也就是说,在这时,理论思辨的声音沉默了,对世界的向外的、积极的理论探索活动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向着内心生活的回转。我们看到,在早期的经院中,被奉为精神偶像的不再是像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这样的古代德行和智慧的典范人物,也不再是奥古斯丁或者波埃修这样的基督教的思想大师,而是以克制情欲、战胜自我而闻名的圣徒;诵读的文字也不再是古代的文化典籍,而是圣徒传、布道书。①参见Steven P.Marrone.“Medieval Philosophy in Context”,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Philosophy,ed.by A.S. Mcgrade,p.17-18,Cambridge,2003.显然,在这样的时代,要发展科学理性是极其困难的。从公元6世纪到公元10世纪,科学研究在西欧停顿了,西欧人不再尝试对世界进行理性的沉思,不再企图对世界从整体上予以基于理论理性的说明和解释。在他们看来,对世界的理论认识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过一种圣洁而虔诚的生活。
面对这样的事实,再强调科学理性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固有特性是很困难的,而我们有关它在古希腊那里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萌芽而存在的主张也就得到了直接而有力的证明。尽管科学理性萌芽于古希腊,但其根本的发展却是在近现代。在近现代,由于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得科学理性突破了古代世界观的束缚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萌芽于古代的科学理性恰恰成为现代性的标志。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读一读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中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化运动的描述就立即可以明白了。恰如韦伯所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活动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活动,同样,萌芽于古代的科学和巨大发展于现代的科学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宜将它们毫无区分地等同起来,并归之于某种地域性的文化传统。
可见,科学理性所代表的并不是中西地域性文化的关键差别,科学理性是普遍的,它在现代的发展取决于现代特殊的社会发展条件,因而成为古今之别的关键因素。假如我们非要把科学理性置于文化的地域性差别的模式中,那么,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就会是:中国文化缺少科学理性的文化基因。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自然科学自现代以来在中国的发展?对于“科学理性的”西方文化我们又如何能够达成普遍的而非“中国的”理解?由此可见,这种将文化比较陷于地域性差别模式之中的做法,存在着根本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它将最终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不可能,使每一种文化的地域性都成为封闭自身的囚笼。但文化的特质恰恰在于它是开放的,是多元的,而这根源于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即:文化不是别的,就是人们以社会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同世界的交往活动,因此,它不能不是开放的、多种因素交融的。
在阐明了上述观点之后,我们可以附带提及的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中国思想家,由于身处“古今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文化碰撞的震撼之中,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古今思想之别误读为中西思想之别,尚有情可原;而21世纪的思想者如果再将具有普遍性质的古代思想作为特殊的中国思想,把同样具有普遍性质的现代思想作为特殊的西方思想,并将二者作对比,企图用这样的古代思想来为现代社会的难题开药方,那就不可原谅了。因此,在中西哲学比较和广义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在重视地域性差别的同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应当将古今的视野加入进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批判的视野下来进行考察。
三
在中西哲学思想比较上采用这一历史批判性的方法,一个直接的成果就是,我们不再局限在文化的地域性模式下来思考问题,而是以普遍的方式、在普遍的历史思想的范式下来谈论问题。我们可以谈论普遍的古代思想和普遍的现代思想,谈论西方的古代和现代以及中国的古代和现代,并且在这样的思想张力中进行普遍的哲学思考,进而产生普遍的思想效应。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正处于具有普遍性的现代进程之中。从14、15世纪起在西欧兴起的现代性运动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地域性的特殊的历史运动,并且由于某种特殊强势的原因而成为一场普遍的世界历史运动。只要我们考虑到即便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个现代性的历史运动也是从他们自己的古代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同他们自己的古代思想范式、古代世界观存在根本的差异和转变,并且同样经历了一个剧烈的从社会结构到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而这毫无疑问在根本上属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仅仅是属于西方的,而必须认为它同样也在中国发生,中国也同样面对着一个从古代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社会的、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在根本上属于普遍的现代性问题,而非所谓的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问题。
从这样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普遍性的历史视角出发,置身于一场普遍的现代性运动中,我们不仅可以基于中国的现代来批判性地审视作为自身传统的中国的古代,而且可以基于中国的现代来批判性地审视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现代和西方的古代,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有效的思想资源,而这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性本身深化的过程。反过来,相同的思考对于西方人自己也同样成立。西方人不仅需要基于西方的现代来审视作为自身传统的西方的古代,而且需要基于自身的现代来审视作为他者的中国的现代和中国的古代,这样的思考过程也同样促进了现代性本身的深化和发展。由此,无论是中国思想家从中国的现代出发所进行的思考,还是西方思想家从西方的现代出发所进行的思考,就都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思考,都具有普遍的现代思想价值,它们实际上是现代性作为一场普遍的世界历史运动在其自身历史进程中的深化和发展。这样,文化的地域性差别的狭隘视野就被打破了,文化的带有普遍性质的思考成为主导性的因素,而有关“中国思想如何能够成为世界的”以及反过来“西方思想如何对于中国思想有效”等问题也就成了伪问题。它们的虚假性就在于,已经事先将中西思想根本对立了起来,在这样的前提设定下再来提出中西思想如何对话、中国思想如何对世界有益的问题,就成为根本不可能被解决的伪问题。
除此之外,一个更富理论意义的结论就是,站在普遍的现代性历史运动的立场上,不仅中国的现代性和古代性应当纳入这种批判性的思考中来加以审查,而且西方的现代性和古代性同样可以纳入这种批判性的思考中来加以审查。只有在这样一种绝非地域性的普遍的思想批判的审查中,我们才可以谈论所谓的“更现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摆脱狭隘的地域性文化差异比较的思路,而进入一个更为深广、普遍的现代性思考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对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历史运动领会得越深,也就越能够深入地推进这场运动,进而能够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任何一个思想者的思想,只要他锲入这一普遍的世界历史进程足够深,便都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便都具有一种基于普遍世界历史的特殊的远见卓识。这样一来,中国的和西方的差别便不重要了,它们成为真正“地域性”的了,而思想的普遍文化价值就以格外鲜明的方式凸显了出来。现代性不再是属于西方的,现代性是世界的,它属于一个深广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处于一种“更现代”的位置,提供一种更具普遍性质的思想。①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现代的”立场,针对这种立场的任何地方性的反应,以及种种挂着“反现代”名号的“古代的”立场,我的一个完全基于现代性立场的回答就是:事实上,它们已经置身于现代性的一个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了,它们尽管诉诸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和古代的思想资源,但仍旧是“现代的”,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现代的”更趋深入的解答。它们并不像它们自身所标榜的那样完全是地方性的,例如“中国的”,或者完全是“古代的”,而是现代性历史运动自我深化的表现。它们诉诸地方性传统或者古代思想资源对现代性的批判,正是它们的现代性的体现,因为现代思想文化的本质就是批判,古代诚然是不批判的,而任何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传统也是缺乏自身批判性的。就此而言,这样一种批判恰恰是现代性自我深化的表现,是对现代性的历史运动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从现代立场出发的一种更深入的文化思考,在根本上仍旧属于“现代的”文化策略,依然是在现代对现代问题的一种现代的解决方式而已。
由上所述,当代中国的思想者立足于自身现实,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审视,其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它对西方思想者立足于自身现实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审视具有思想借鉴意义。反过来,当代西方思想者从自身现实出发,对无论是自身文化传统还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进行的思考,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思想者的思考产生积极的意义。这样,在这里始终活跃着的是本身就具普遍性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思考,而文化的地域性因素就被扬弃了,它们成为相对次要的,并且可以从有关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
(责任编辑 李 理)
Antiquity and Modernity,or China and the West?——Rethinking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NIE Min-li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For a long time,there is a basic methodological mistake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That is to say,people wrongly read chronological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local cultural differences,and observ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ulture.So,it causes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cannot communicate each other essentially.This paper not only explains the reason of this mistake,but also argues for the chronological element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as well as the univers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rld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Furthermore, as regards reasons,especially theoretical reason and scientific reason,well known as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culture,this paper emphatically points out that it also sprouted in Chinese ancient times,and also was just a seed in Western ancient times.At last,this paper provides a universal cultural perspective which surpasses that local model of cultural comparison.
antiquity;modernity;local culture;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聂敏里: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