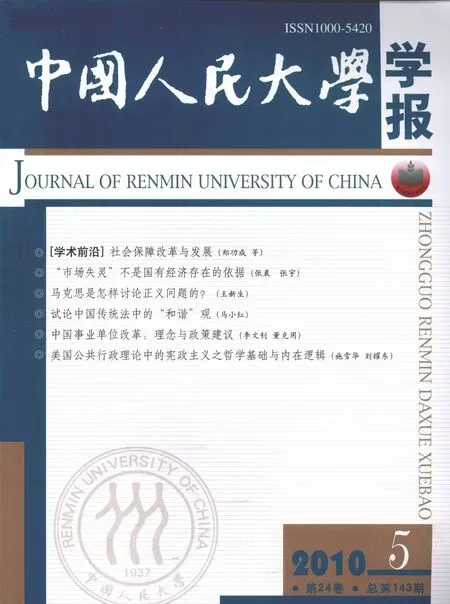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动态与发展趋势
金炳彻
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动态与发展趋势
金炳彻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支撑着欧洲传统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福利与社会投资论等劳动型社会保障政策和保障基本收入等非劳动型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实行,传统福利国家走向衰退。工作福利与社会投资论强调加强劳动与福利之间的联系,而基本收入论则相反,它们围绕劳动与生产的理念差距形成了对策上的对立结构。虽然这些制度在联系劳动与福利的关系上是对立的,但在通过福利国家达成社会统合目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相互融合,以达到新福利国家政策的愿景。
欧洲社会保障变革;工作福利;社会投资;基本收入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西欧国家借助持续型经济发展进入了“福利国家时代”。经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工人为核心的市民阶层势力不断壮大,国家又无法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福利国家应运而生。福利国家立足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旨在消除市场中的不公平和不稳定,建立一种社会机制实现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由全社会共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福利国家的理念不再是济贫法时代的慈悲与稳定,而是根据市民权提供福利。但是,福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得不面对各种批评,如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官僚主义、无效率、“福利病”等,立足于有效需求理论的凯恩斯社会经济政策濒临瓦解。1979年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1980年美国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货币主义政策(即通过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压缩了社会保障政策,作为福利国家最大受益人和支持者的高收入劳动者和中产阶层对此表示默认,最终导致福利国家进程倒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发达国家提出“福利国家危机”,由此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开始出现社会保障民营化趋向。有关民营化的讨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工作福利(workfare)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一概念旨在联系劳动与福利,努力通过社会保障恢复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纪律。工作福利的表现形式可谓是多种多样:美国的AFDC改革以工作为条件,而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工作福利则更多地重视劳动力价值和社会投资,两者中间还存在标榜“由福利到劳动”的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工作福利是由工作(work)和福利(welfare)两个单词合成的,换言之,亦即“welfare to work”,本质上是重视人类劳动的意义,将劳动(生产)与福利联系在一起。
作为劳动为主型的收入保障政策,社会投资论(social investment)是在西欧不断变更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环境中和福利国家体制受到攻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环境中诞生的。事实上,在西欧,社会投资政策的登场一般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1]相关,重点在于探讨新社会风险出现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如何克服其局限性。与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意图相同,社会投资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增加国民个人的人力资本,提高就业率,并通过这些方式刺激经济增长。
工作福利和社会投资论是两个新型社会保障政策,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理论则以欧洲为中心展开讨论。工作福利意味着“不工作、没饭吃”,旨在强化劳动(生产)与福利之间的联系;社会投资论通过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引导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提高经济发展潜力,联系劳动与福利;而基本收入则与之完全相反,不论工作与否或受助资格,向所有具有市民权的人提供一定收入。如果由劳动与福利的联系来看,基本收入理论与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是明显对立的理论。
对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迥然不同的评价与基本收入等对立方案有关,而且与联系劳动(生产)和福利的构思本身的合理性及其问题也有关系。本文将考察以福利国家改革的福利战略为中心而提出的各种理论,探求福利国家的新政策方向,重新审视以上三种社会保障政策的妥当性和可行性。
一、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背景
在探讨欧洲社会保障改革历程中登场的新福利战略——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以及基本收入论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新社会保障政策出现的背景。具体来说,我们应当看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内,大部分欧洲国家支撑传统福利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是如何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发生变化,并在什么样的变化压力中逐步解体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支撑福利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所经历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西欧国家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建立了传统的福利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可能会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两个目标。根据泰勒—古庇的理论,西欧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呈现出以下特点[2](P1):第一,大多数国家中存在大规模、稳定的制造业,这种经济模式不但可以提供高水平的家庭津贴,还可以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第二,形成可以有效地为儿童和体弱的老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照顾的稳定的核心家庭结构。第三,拥有通过新凯恩斯主义政策保障低失业率和稳定增长的工资,由此有效管理国民经济的政府。第四,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结成同盟,为满足其需求而组成了就福利工资和服务提供提出要求的政治体系。上述因素中包括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经济结构变化和家庭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支撑传统福利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基础逐步瓦解,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支撑着传统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表现出相当巨大的压力,最终传统福利国家走向瓦解。导致传统福利国家瓦解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因素可谓是多种多样,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第一,在人口结构上,传统福利国家要求努力维持适当的老年人赡养率,然而,低出生率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国家不得不面对迅速的老龄化,并且稳定的人口和家庭结构也在逐步崩溃。第二,在家庭结构上,传统的福利国家一直遵循着男性家长模式,女性一般参与家务劳动等,这是传统福利国家的家庭结构设计的前提,而现今西欧大部分国家中离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率不断增加,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正逐步走向崩溃。第三,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上,传统福利国家的前提是稳定的工薪阶层不断增加、低失业率、个体工商业者逐步减小,而现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是雇佣不稳定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增加、失业率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率持续上升,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传统的家庭正走向衰弱。第四,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可概括为经济全球化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竞争、制造业大规模转换为服务业(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等。这些变化都加大了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了生产率,侵蚀了传统福利国家的前提——雇佣稳定性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最终导致传统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五,由经济结构变化的延伸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作用及能力的缩小。经济全球化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竞争强化,则要求为了保障民间企业的生产力而缩小国家的作用和能力,由此,大部分的发达福利国家逐步缩小自主政策决策及实行能力,使得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自主能力的传统福利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中的新福利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欧洲传统福利国家的解体,针对变化了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出现了若干新的福利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和基本收入论。
1.工作福利
工作福利这一概念,是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在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的同时,为了摆脱当时自身面临的经济危机而提出的概念。由于福利制度被滥用,当时出现了对社会安全网不利于刺激劳动者的工作热情、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的各种批评之声。英国国内失业人员为了领取失业津贴,在失业期间必须学习新技术或者提高原有知识能力。只是收入援助项目的提供标准并不与有无职业挂钩,而只提供给需要最低生活费援助的人。失业者需要主动到职业中心去找工作,并且要表现出自己希望工作的强烈意愿。如果他们拒绝了职业中心介绍的职业教育、面谈,或者不参加职业计划相关项目的话,失业津贴就会中断或者被减少金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工作的意愿或者准备不充分的人是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津贴的。因此,始于英国的初期工作福利的概念,是追求整体社会福利削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社会救助会受到周围环境对贫困层的看法和认识的影响,而工作福利正与这种社会价值紧密相关。就算认识上有一些差异,但总体上对贫困层的认识并不好。很多人认为,贫困层一味依靠由国民缴纳的税金而建立的社会救助系统、不愿意工作,长此以往,就会助长贫困层的依赖心理。此外,还有人提出由于有劳动能力的女性获得社会救助直接导致了福利费支出增加的观点。也就是说,工作福利是在如果无条件提供社会救助就会导致贫困层的工作欲望降低的前提下展开的。而工作福利的例子正好向我们展示了随着主流社会对贫困层依赖社会救助的认识变化,社会救助的领取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的事实。
欧洲特别是英国在过去的20年间失业家庭数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奖励努力寻找劳动机会的社会保障津贴领取阶层的措施,失业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因此,为了建立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补贴制度,英国社会保障部主张必须引入更多与工作福利密切相关的措施。具体而言,劳动福利在英国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需要更多的措施来面对那些第一次申请社会保障补贴的人;第二,在各个机关的密切配合下,一方面向受助者提供援助,一方面需要实施类似“new deal”那样的劳动连接福利措施。强调工作福利的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也有出现。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虽然看起来确立了保障平均生活水准的普遍主义原则,并且呈现出把劳动与福利分割开的表象,但是,在福利国家内部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中却包含了过剩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再配置的举措。也就是说,完全雇佣是普遍主义原则存在的前提。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模型中福利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尽管较弱,但它可以看做是一种国家同时提供了福利和劳动的系统。[3](P13-14)
在许多国家中,工作福利是与公共事业参与联系在一起。例如,一些国家规定了参与公共事业是社会救助受益者的义务。有劳动能力者为了获得补贴,必须参与公共—民间机关的一些活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实现工作福利。另外,工作福利并不是单纯地追求让人工作,那些为了上岗而作出的努力、参与的职业技术教育、尝试无偿为社区服务等等也是工作福利所追求的。[4]工作福利的赞成者认为工作福利终结了那些依赖社会救助的行为,反对者则认为工作福利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减少社会救助的财政压力,特别是一些活动所需的费用很多,照此下去,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会难以推行。
2.社会投资论
“社会投资论”作为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改革方案被称为“对人的投资”或“对未来的投资”。按照这一理论的内容和范围,可以将其划分为社会投资政策、社会投资战略、社会投资国家。但是,按照社会投资国家的出现背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第一,可以从传统福利国家已经发展的前提下发生的环境变化,由此导致的人口、家族结构的变化,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政府的职能与能力的变化,政治体制的变化等层面来考察。第二,关注在初始与延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风险问题。
实际上,有关社会投资的思想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迈尔达尔(Myrdal)的理论中发现。他批评将社会政策视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支出因素的观点,认为社会政策是可以循环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投资因素。他主张就算没有生活殷实者的实质性牺牲,也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提供平等的机会。紧接着,英国著名社会学者吉登斯(Giddens)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概念。他对新社会政策的必要性和实现这一政策理念的政治势力的认知可以说“超越了左派和右派”,形成了“第三条道路”[5]。1994年,英国社会公正委员会(Commission on Social Justice)提出了新的国家战略——社会投资政策。根据该委员会提议,“对娴熟、研究开发、技术、儿童扶养及社区开发的投资,可以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思路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盟的发展中也可以发现。
社会投资国家是从欧洲福利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中区分出来的,如图1所示。

图1 福利国家的发展阶段与社会投资国家
一般来说,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阶段有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传统福利国家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投资国家等。
在社会投资论中,社会投资政策根据其覆盖面可分为如下三种。(1)包括劳动相关型福利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刺激型政策,旨在通过失业津贴和教育培训等措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2)保护儿童和女性的社会福利服务项目,其核心不同于过去儿童福利中强调儿童人权的观点,而是认为因儿童是未来的市民劳动者,需要积极的人力资本投资,女性保护方面的福利政策则需要在国家和企业层面同时建立。(3)资产型政策,它起源于美国的社会政策,正逐步扩散到英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这一政策的基本思路不仅包括向低收入阶层或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方面的现金,形成作为“积累”的物质财富,还包括向成年低收入阶层和儿童提供可以适应劳动力市场要求的物质基础(居住费、教育费等),可以说,这是一种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受助人的劳动积极性的战略。
上述的社会投资战略的核心内容与构成传统福利国家核心内容的收入保障制度有明显不同。最先使用社会投资国家一词的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的福利国家中市场经济是滋生不平等的机制,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市场是万能钥匙。第三条道路将市场经济视为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保障市场能力才能在长期中保障财富再分配。[6](P34-36)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政策是经济的“负担”或反生产力的因素,与此相反,社会投资战略则认为社会政策是强化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7](P2),在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机制完善的知识经济时代将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社会投资战略在平等与市民权的认识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福利国家的观点。社会投资战略并不把重点放在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平等上,而是更强调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机会平等。[8](P106-107)社会投资论还对传统福利国家的争论点——平等、义务、收入再分配等传统左派观点和新社会投资论的观点进行了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投资论与将社会福利作为排他性权利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不同,认为社会福利权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可见其与传统的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
3.基本收入理论
以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福利国家表现出其社会经济的局限性,这直接引发了对于对策型收入保障的各种讨论。这些讨论大体上可分为工作福利和非工作福利,前者如“工作福利与社会投资论”,而后者的代表型事例则有“基本收入”理论。基本收入论与工作福利论一样,都是由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在风险结构变化导致现有福利国家功能出现障碍后提出来的。这种思路直接导致了对生产主义福利国家的信任危机。具体而言,在新技术或新产业无法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时,教育或再教育也就无法帮助技术水平或技术能力低的劳动力摆脱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命运,而国家要负担的成本就不单是教育、再教育的成本,还有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劳动者的福利费用。这一思路与收入保障相反,将劳动者从劳动力市场参与中分离出来,意味着在不强调劳动义务的前提下提供最低收入费用这一现金给付[9]。基本收入政策从不设立财产调查的方面来说,与过去的社会救助不同;就没有劳动义务这一点来说,与劳动收入税额控制(EITC)等工作福利式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区别[10]。从这种基本收入思路不以正规劳动参与的市民权为基础来看,它指向脱离劳动的社会,不强调劳动伦理或产业主义,与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存在根本上的不同。
“基本收入”是最近在欧洲非常流行的理论与政治流程模式,其内容为“向所有社会成员无条件地提供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收入,并根据年龄等额支付”。1986年,van der Veen和Parijs初步形成了关于“基本收入”的理论体系。与此相类似的主张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的弗里埃,到20世纪前期还有拉塞尔(Russel)。20世纪6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曼(Friedman)也提出过相似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后期ATTA (金融关税市民联盟)德国支部开始接受“基本收入”理论。2006年是“基本收入”理论再一次飞跃式发展的时期。德国资本家沃纳(Werner)在报刊、广播中广泛传播了“基本收入”理论,提出了废除所有劳动收入税等直接税收、提高消费税,以作为基本收入的财政来源的新主张。“基本收入”理论还通过互联网站 BIEN(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在全球迅速扩大影响。到2006年,欧洲的基本收入论者还主办了杂志——BIS(Basic Income Studies)。
基本收入的主要内容,就是与劳动与否无关,根据其年龄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基本收入,它强调现金给付。基本收入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此,笔者将通过间接工资、转移支付、无条件支付等方面考察其根本差异。第一,间接工资。这与间接的劳动贡献(labor contribution)相关。对“收入”的权利仅限于无法工作或未能就业的人,与发达国家的失业年金大体相似,以过去一定量的工作为前提,可扩大到自愿不参与工作的人。劳动或至少有劳动意愿为基本收入受助人的资格条件。第二,根据最低生活费与劳动收入向其家庭差额支付生活费用即为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它与劳动贡献和收入联系是完全割裂开的,补偿其差额的保障收入(make-up guaranteed income)度将会使工资待遇在保障收入以下的工作完全不被劳动力市场所接受。第三,所有个人不论是否有其他收入都享有无条件支付(unconditional grant)的权利。也就是说,现在劳动收入高的人群也可以附加接受。第三种形式的无条件式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意味着政府无条件地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转移支付。不充分的收入保障强迫劳动者在非正规或临时的工作岗位等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劳动,并接受低工资。因此,基本收入政策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并克服非人性化的劳动条件,将市民从劳动力市场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自我或决定用于娱乐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在基本收入制度下,个人直接将基本收入用于生活开支,正当化就业机会被剥夺的现象、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或创造就业岗位的义务和费用将消除,在雇佣者的立场之上雇佣保障责任将减少,可建立一种有弹性的劳动力管理机制。从制度方面来看,复杂的资格审查消失会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费用支出并且向所有人无条件地提供,可以解决效率和贫困陷阱问题。[11]基本收入是将公共年金、失业津贴、社会救助、养育费、住房补贴等统合为一体的现金给付型福利制度。
但“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的局限性在于未能消除资本关系的情况下,将前提作为目标或将消除资本关系放到了久远的将来。因此,“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式的非劳动收入——利润和投机收入,其规模自然会具有很大局限性。如果不包括资本主义式的非劳动收入(资本收入、财产收入、投资收入等),第三世界国家或非西欧福利国家中“基本收入”的财政来源将非常有限,根本无法保障人类的基本生活要求,仅处于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无条件式的基本收入对财政的负担之大可想而知,这一方案会提高直接税率,所以,还会增加因调节税收而导致的行政管理费用。
4.三种社会保障政策的适当性和可行性
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和基本收入保障围绕着劳动与生产的理念差距构成了对策上的对立结构。整理以上以收入保障为中心、有关福利国家改革的政策性对立结构,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各福利国家都没有放弃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对立,但危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完全就业变得不现实。工作福利和社会投资论不论是宽容(胡萝卜)性手段或强制性(大棒)手段,都在努力发挥引导联系劳动(生产)与福利的作用,并与这种制度相反的彻底分离劳动(生产)与福利的基本收入制度形成了对立。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一味地强调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强化劳动与福利的联系;相反,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会一味地通过基本收入制度来破坏劳动与福利的联系。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政策和基本收入政策也许存在以某种形式共存的可能性。所以,在现实的福利国家中,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和基本收入制度的未来可能是强化劳动(生产)和福利的联系,也可能是弱化劳动(生产)和福利的联系,或许各国还会探索出更加多样的理论和思路来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三、结论
我们对欧洲福利国家改革中实际进行着的工作福利和社会投资论等强化劳动与福利联系的收入保障政策和基本收入保障等非劳动中心型收入保障政策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考察了这两种对立的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交集和展开过程。从现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基本收入中选择其一的福利改革论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围绕福利给付的水平和形式是由劳动(生产)与福利的相关程度来决定的。仅以考察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和基本收入来整理出所有欧洲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的收入保障政策的发展方向也是天方夜谭。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根据地区具体情况将劳动与福利密切联系起来,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分权化;与此相对应,基本收入对刺激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且对小规模的志愿组织的发展会有更加积极的作用[12]。虽然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主张强化劳动(生产)与福利之间的联系将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可谓是一石二鸟,但考虑到贫困阶层人数的增加、两极分化加剧、社会保障制度的死角地带等社会风险及其变化和社会安全网的不成熟等,很难令人相信强调劳动(生产)方面的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会消除社会不平等和排斥。反倒是掐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向非生产社会成员提供适当的市民福利(例如自由和生活保障),即在制度中扩充基本收入的原则显得更加必要。
不论是倾向于强调劳动与福利间联系的工作福利或社会投资论,还是钟情于掐断劳动与福利间联系的基本收入论,都不取决于政府介入程度,而是根据劳动(生产)与福利的相关程度和理念、原则、政治上的差异适度调整的,这将对欧洲福利国家改革方向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上所述,工作福利、社会投资论和基本收入在福利国家改革中都是致力于克服社会排斥的方案,这是共同点。虽然这些制度在联系劳动(生产)与福利的关系上是对立的,但在通过福利国家达成社会统合目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相互融合。为确保劳动者和市民的生活收入,通过劳动自由和生活保障解决生活问题并自我实现,以达到福利国家政策的愿景。我们不能单纯在工作福利、社会投资、基本收入中选择一样,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调整、融合而定。因此,深化对工作福利、社会投资和基本收入的研究就变得更加必要了。可以说,越过工作福利、社会投资的批判型、负面意味,将这些政策与基本收入政策融合为一,并付诸实施将成为我们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
[1] Pierson,Paul.“Post-Industrial Pressures on the Mature Welfare State”.in Pierson,Paul(ed.).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 are 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Taylor-Gooby,Peter.“New Risks and Social Change”.in Peter Taylor-Gooby(ed.).New Risks,New Welf are:The Transf 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Welf are 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 Goodin,R.E.“Something for Nothing”.in P.Van Parijs.et.Al..What's W rong with a Free L unch?.Boston,Mass.:Beacon Press,2001.
[4] Quaid,M.Workf are:Why Good Social Policy Ideas Go Ba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2.
[5] Giddens,Anthony.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Malden,Mass.:Polity Press,1998.
[6] Giddens,Anthony.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Cambridge,Uk:Polity Press;Malden,Mass.:Blackwell Publishers,2000.
[7] Perkins,Daniel,Lucy Nelms and Paul Smyth.Beyond Neo-liberalism: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Social Policy Working Paper No.3.Brotherhood of St Laurence and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University of Melboune),2004.
[8] Diamond,Patrick and Anthony Giddens.“The New Egalitarianism”.in Patrick Diamnond and Anthony Giddens (eds.).The New Egalitarianism.Cambridge,U K:Polity Press,2005.
[9] Van Parijs,Philippe.“Basic Income:A Simple and Powerful Idea for the 21 Century”.in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 V 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Berlin,2000.
[10] Offe,Claus.“A Non-Productivist Design for Social Policies”.in Van Parijs Philippe(ed.).A rguing f or Basic Income:Ethical Foundations f or a Radical Ref orm.London:Verso,1992.
[11] Fitzpatrick,T.Freedom and Security:A n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Income Deb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
[12]Beck,U.The B rave New World of Work.Cambridge;Malden,Mass.:Polity Press,2000.
(责任编辑 武京闽)
The Current Trend of Social Policy Reform in European Countries
Byung-Cheol Kim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Since the mid-1970s,ther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economic,social,and political structure,which maintains the traditional welfare capitalism in European countries.Along with social policy reform introducing labor-centered social policy such as workfare,social investment and non-labor-centered social policy such as basic income,the traditional welfare state has been dismantled. Workfare,social investment emphasizes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welfare,whilst basic income conversely bears lit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The contrasting difference of these programs in the idea surr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welfare has brought about confrontational structure in its policy formation.Although these programs are confronted with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welfare,they might be mutually integrated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ccomplishing the ideal picture of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policy reform in European countries;workfare;social investment;basic income
金炳彻: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福利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讲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