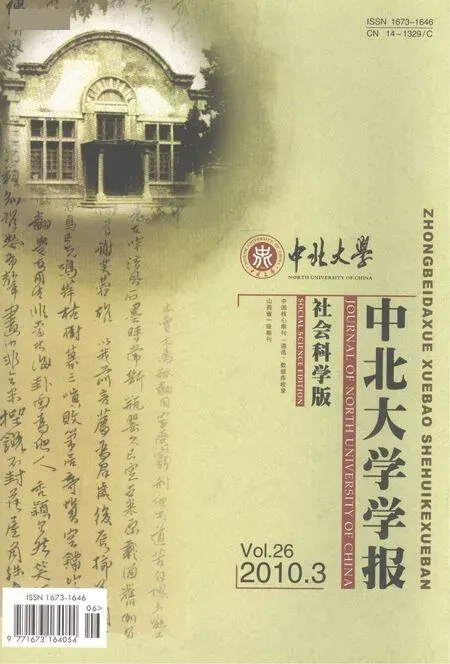论《在路上》的叙事技巧和主题意义*
罗 全
论《在路上》的叙事技巧和主题意义*
罗 全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在路上》讲述了战后美国青年寻找“美国梦”以及“美国梦”破灭的故事。这部小说形式独特,一反结构性叙述的工整与严谨。小说使用展示性情节反映了当时人物行为与思想混乱,反思了战后青年人“美国梦”破灭的原因。本文在叙述学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对小说特殊的叙述结构进行探讨。在探讨叙述结构的同时也分析了小说所蕴含的丰富的主题思想——即战后美国人过度追求物质的欲望是梦碎的根本原因。
凯鲁亚克;《在路上》;叙事技巧;主题意义
0 引 言
《在路上》[1]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①杰克·凯鲁亚克(J a c k Ke r o u a c)1 9 2 2年3月1 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城,1 9 6 9年1 0月2 1卒于佛罗里达州圣·彼德斯堡,是加拿大法国移民列奥·凯鲁亚克和加布里尔的第二个儿子,排行老三,作者注。的第二部小说。这本小书主要描写了追求个性的“我”(萨尔)与迪安、玛丽卢、雷米·邦库尔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多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的荒唐故事。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讽刺美国时政,畅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到纽约,最后作鸟兽散的故事。
评论家吉尔伯特·米尔斯坦曾这样评论这本书:“《在路上》……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1]”在当时,尽管这本书很畅销,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书中详述“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方式。没有人分析书中“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的原因。更没有人意识到这句评论暗示了这篇文章的独特叙述风格。本文试图结合一些叙事学理论分析这本书的叙事技巧与主题意义。
1 反“结构性”叙事
1.1 “即兴式”写作
如果说写作在别的作家那里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那么在凯鲁亚克那里更像是游戏。因为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从1951年4月2日到22日,只花了不到三个星期。杰克是用一部打字机和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完成的。正是由于这样前所未有的写作速度,杰克·凯鲁亚克还遭到了当时著名节目主持人斯蒂芬·艾伦的挖苦。他说:“宁可花三个星期旅行,花七年写书,也不会像凯鲁亚克这样本末倒置”[1]1,这正好说明了凯鲁亚克“即兴式”的写作特点,即随兴而至,不顾及什么结构。因此,作品就是他思维的碎片,时间的碎片。正因这样,《在路上》没有传统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整体感,也缺乏皮亚杰所说的结构性的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2]”小说按照作者亲身经历的顺序,更多地是按照记忆的顺序进行的。比如:
“第二天早上埃迪亚去了,我没去。梅杰买来了许多食物,作为交换,我只得做饭,洗碗。我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一天晚上,罗林斯家要举行一个大型晚会,他母亲旅游去了。罗林斯邀了所有的朋友,并让他们把威士忌带来,然后他又给一些认识的姑娘发了邀请。他让我主持晚会。晚上来了很多姑娘。我给卡罗打了个电话想知道迪安现在干什么,因为迪安清晨三点总要去卡罗那里。晚会后我也去了。[1]60”
“在此期间,我开始频繁地去旧金山;我试遍了书上说的怎么搞定姑娘的办法。我甚至同一个姑娘在公园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天亮都没有结果。那姑娘来自明尼苏达,长着一头金发。那儿有许多同性恋者。有几次,我带着枪去旧金山,当一个同性恋在酒吧里凑到我面前时,我就取出枪。[1]93”
可见,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他并不是像传统小说家那样预先设置文章的结构,然后根据结构安排人物和结构情节。在他的这部作品中,时间、空间的转换以及人物安排毫无逻辑可言,作家凭着自己记忆的流动任意挥洒。
1.2 叙述的“非等时”性
所谓“非等时”性即叙述的节奏。热奈特十分看重叙事的节奏。在他看来,叙事可以没有时间倒错,但是却不能没有“非等时”性。米克·巴尔也认为叙事节奏是引人瞩目的,又是难以捉摸的。她认为节奏“由素材诸事件所包括的时间总量与描述这些时间过程中的时间的关系”[3]来把握。通过对小说非等时叙述的把握就能感受到小说的节奏效果。《在路上》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故事的时间跨度有几年时间,但是写作的时间却不到三个星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因“非等时”性造成的独特的节奏效果。
凯鲁亚克曾说自己是“奔跑的普鲁斯特”。因为他和普鲁斯特一样,靠着自己的回忆写出了这本《在路上》,但是他的文章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有着截然的不同。这种不同的表现就是:普鲁斯特的叙事速度要远远慢于凯鲁亚克。普鲁斯特写《追忆》花了十年,而凯鲁亚克写《在路上》的一稿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追忆》是二百多万字,《在路上》只有二十多万字。如果这样一比较的话,凯鲁亚克的叙述速度是普鲁斯特的三百倍。在叙事速度上,他的确是奔跑着的,这跟热奈特所说的叙事的“非等时”有关。热奈特在论“时距”时总结出4个叙述运动,那就是停顿、场景、概要和省略。他分析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普鲁斯特的图表中没有概要叙事,没有描写停顿,只剩下两个传统性的运动:场景和省略。”按照热奈特的分析,详尽场景和概要叙事之间是对立的,普鲁斯特不断地叙述场面,扩充作品使得作品变得异常冗长,而不断省略时间,因此出现了“叙事越来越大的间断性”,即一个场景和一个场景之间出现很大的空白[4]。而这种不断的扩充使得信息量达到最大,而叙事速度也变得缓慢起来。
《在路上》却相反。他的叙述时间短暂,却要叙述长达七年的故事。所以,他只能使用概要叙事、省略叙事。同时,他尽量减少信息量的扩充,这就使得叙事速度加快了。于是他的作品出现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节奏效果:作品在整体来看是连续的,但缺乏对场景必要的描写和扩展,尽量减少信息量的摄入,整个文章就变得像是流水帐一样,让人觉得乏味和枯燥,行文有一种过于快速、眼花缭乱和跳跃般的感觉。
1.3 由人称代词“我”造成的混乱
《在路上》是一部“故事内—同故事”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在路上》的叙事者“我”——萨尔·帕拉迪斯既担任着叙述者的角色,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所以,读者看到的既是关于萨尔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在听萨尔讲述人物的故事(他所看到或者听到的事件)。比如,“我第一次遇见迪安是在我同妻子分手不久之后。[1]1”。显然这是故事中的叙述者萨尔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是一九二六年,他(迪安)父母开了一辆汽车途经盐湖城去洛杉矶的时候……”[1]1;“我之所以把旧金山的一切,事无巨细一一说来,就是因为它们同许多事情有关。雷米和我是多年前在预备学校认识的……[1]79”这时候的“我”——萨尔显然是在以人物的身份讲述他人的故事。
萨尔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这就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当他作为叙述者叙述自己的时候说话显然是不需要引号的,他处于第一个叙述层。但是,作为人物参与其中,他和其他人物往往又处于同一个叙述层。因此具有双重身份的“我”——萨尔不停地跨越于两个叙事层之间,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迷失方向,注意力被分散。但是,读者的麻烦显然还不仅于此。作为叙述者的萨尔,他在叙述时使用第一人称“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本无可厚非,但是,其他人物也使用第一人称“我”叙述,并且,作为叙述者的萨尔在叙述作为人物的萨尔与其他人对话时,并不为作为人物的萨尔——“我”与其他人使用“我”的叙述做标记而用直接引语。因此,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很难判断“我”到底是谁,容易把小说中其他使用“我”叙述的人物混淆为人物萨尔。
叙事理论家热奈特说:“当代小说已经越过了包括这条界限在内的许多界限,毫不犹豫地在叙述者和人物(们)之间建立起可变的或不稳定的关系,用令人目眩的代词转换表现更自由的逻辑和关于‘个性’的更为复杂的观念。[4]”《在路上》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在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没有标记却频繁使用,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障碍。比如,萨尔在叙述迪安讲述自己的情况时,他并不转述,而是客观地、文献式地引用。“……我得了灵感——我得告诉你,大萧条时期,我父亲、我,还有拉里默街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一起到内部拉斯加去卖苍蝇拍子……[1]266”
这种由第一人称“我”造成的混乱导致读者的注意力被分散,但是,我想作家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并不是故意要造成读者阅读的困难,而是潜在地告诉读者:“我”既是一个故事的参与者或者观察者,同时又是一个思考者,在这二者之间更是一个自我反观与反思的过程,即多年后作者对当年的“我”的一种反思。
2 “展示性”情节
如果抱着要在《在路上》中读到特别的故事,或者发现新奇的情节模式的想法的读者读完此书,那么,他肯定会十分失望。因为,《在路上》不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除了几个人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不断地流浪之外,他们总是在野外、旅馆和汽车上度过的。而且,全书分为五部,内容十分类似,除了地点变化外,人物和故事、情节基本不变。小说完全不是按照传统小说以因果关系联结而构成情节,而是按照时间和空间的不断转移联结起来的。人物旅游到哪儿写到哪儿,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全文共分为五章,每一章之间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基本独立,每一个故事与前一个故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故事具体时间并不真实可靠,但是它是按照自然时间规律向前发展的,是连续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总之,《在路上》抛弃了传统小说具有的情节完整性和戏剧性。
按照查特曼的说法:“一个叙事作品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没有情节。”不过他把情节分为“结局性情节”和“展示性情节”。按照他的区分,传统小说是以结局为目的基于因果关系之上的完整演变过程,是结局性情节。而现代小说则是作者生活琐事引发人物心理变化或意识变化,达到展示的目的[5]。《在路上》实际上就是展示那一时期被人们认为“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展示人物“寻求”满足精神领域的过程,展示他们为寻求特定目标所表现出来的彷徨,以及他们的心理变化过程。比如,主人公迪安吸毒嫖娼,东游西荡,居无定所,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小说中处处展示了他的内心想法。他在旅途中对萨尔说:“噢,哥们,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家庭、婚姻,以及有关心灵的种种美好的东西。”这样来看,《在路上》采用了反传统的“结局性情节”和具有现代性的“展示性情节”。
3 对“美国梦”的深入思考
在这本书出版之时,人们认为这部书就是在宣扬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方式。本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凯鲁亚克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宣扬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种种行为上。文中的萨尔其实就是凯鲁亚克自身。萨尔始终扮演着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思考那些年轻人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思考了所谓的“美国梦”。萨尔自从遇到了迪安后,他一心想去美国的西部,他向往西部那种开阔和辽远。但是当他一路向西到了西部后(丹佛),他发现和东部没有什么区别,依然是没有想要得到的。于是又回东部,再去西部,最后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似乎是寻找到了在美国所没有的东西,在精神上得到了洗礼。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发展让社会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正是人们对于金钱的极度渴望使得人们有时变得无比冷漠。精神上的空虚必然就会带来身体上的放纵。迪安吸毒、酗酒、偷盗和无数女人性交、无所事事、没有责任感、癫狂。但是在萨尔的眼中,迪安就是英雄,是无数青少年的偶像。尽管人们精神寂寞、空虚,没有希望,但是只有迪安能够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生存。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社会的浮华和奢靡,所以,他就是英雄。当萨尔去了西部,再次回到纽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身在时报广场。我在美国大陆旅行了八千英里,又在交通最拥挤的时刻回到了时报广场;以我闯荡江湖却又不谙世故的眼睛看着纽约的绝对疯狂和浮躁,看他的数百万居民为了钱而你争我夺,疯狂的梦——掠夺、攫取、给予、叹息、死亡,只为了日后能葬身在长岛市以远的可怕的墓地城市。[1]135”正是从纽约离开,有了在路上的经历,使得他再次回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能够透过那些虚华的表象,重新审视着人们所谓的城市繁华,思考这“美国梦”的实质。这种清晰的认识既让“垮掉的一代”们不断地上路,同样,在路上的履历让他们对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垮掉的一代”显然没有垮掉,那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放纵自己的思想。在一九四九年新年,迪安对萨尔说:“噢,哥们,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家庭、婚姻,以及有关心灵的种种美好的东西。[1]150”他们放纵身体,心灵却很健康,对于短暂的生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美国梦”是美好的,是让人向往的,但是那纸醉金迷的生活总会走到尽头,死亡总会来临。对于死亡来说,任何人得到的都会失去。萨尔说:“死亡必定在我们达到天国之前赶上我们,我们活着时渴望的东西,使我们叹息、呻吟、经历各种甜蜜的厌恶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在母亲的子宫里经历过的、惟有死亡中才能重现的某种遗忘的狂喜(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1]161”这是对于表面虚幻美好的“美国梦”的深入思考,也是对于它必然破灭的一个终极论断。
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出现,一反当时美国主流价值观。人们对“垮掉一代”也因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也正是这部小说,引起了人们重新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思考。迄今为止,这部书还在引导着人们思考,因为,还有更多的人沉醉在“美国梦”之中。独特的写作方式、展示性情节、深入的价值思考使这部书愈发显示出它不竭的魅力。
[1][美]凯鲁亚克.在路上[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
[3][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M].谭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7.
[4][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8.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问题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3.
Narrative Skills and Theme of On the Road
L UO Quan
(Chinese Department,Xinjiang University,U rumqi 830046,China)
Jack Kerouac's On the Road is a story about several American young men seeking their“American dream”and the disillusion of their dream s.The form of this novel is inimitable,reversing the regularity and rigor in structural narration.The novel uses displaying plots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s' behaviors and their ideological confusion.It reflects the cause of the disillus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exp lores its uniqu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analyzes its theme——postwar American excessive pursuit of material desires is the root of the disillusioned dream.
Kerouac;On the road;narrative techniques;theme
I106.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0.03.014
1673-1646(2010)03-0056-04
2010-01-23()
罗 全1984-,男,硕士生,从事专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