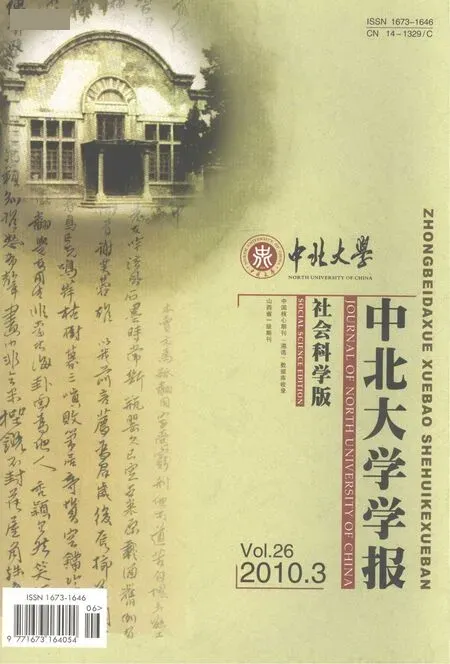心灵的自我救赎
——谈伍尔夫与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张丽燕,王晋华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51)
心灵的自我救赎
——谈伍尔夫与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张丽燕,王晋华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51)
本文通过对伍尔夫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反映了她们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伍尔夫与丁玲创作的重点在于女性形象对自由意志的执着追求,她们始终将其强烈的女性意识渗透于人物的形象中,让这些人物形象经历了孤独苦闷、彷徨迷惘、坚定执着的新的人生发展之路。伍尔夫与丁玲的作品全力发掘女性意识,显示了她们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形成了中西小说最有价值的特色。
伍尔夫;丁玲;女性人物形象;自我救赎
0 引 言
丁玲与伍尔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朵奇葩,他们的小说是从女性生活的海洋里汲取的浪花,是对当时女性经历的反映。尽管她们的人生历程千差万别,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反映不同的民族意识领域中的女性意识,但她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孤独叛逆的莎菲,让一大批处在困惑、迷茫中的青年洒下了同情的眼泪。随之一系列鲜明、独特的女性形象在丁玲的笔下诞生,莎菲、丽嘉、贞贞、陆萍等等成为中国20~40年代女性形象中一组不可忽略的风景。纵观丁玲的创作,不同时期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早期塑造的孤独、苦闷、彷徨的莎菲们,“左联”时期创作的走向社会、寻找希望的丽嘉们,延安时期创作的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陆萍们,在丁玲的笔下她们一步步走出了自我的救赎过程。而在西方,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一向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先驱。她提出了女性要从事写作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不仅指物质上的私人空间,也指精神上心灵的空间,物质上的空间是心灵空间的基础;女性必须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能谈得上精神上的独立。伍尔夫强调:“女性写作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是心灵的自由、艺术的提高”[1]。同时,她还强调了创作的焦点应由外部客观条件转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她指出,小说家的职责是探索“心理学暧昧不明的领域,捕捉人物瞬息万变的心理印象”。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接近生活,更能真诚确切地表现生活”[2]。正因如此,伍尔夫开始了她的小说的实验,将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体现在她的文学实践中。从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开始探索女性的经济地位开始,继而创作《远航》展现主人公蕾切尔的心灵航程,到探索作《夜与日》中主人公凯瑟琳接近婚姻的追逐,成熟作《到灯塔去》中的莉莉完成画作进行价值的自我实现,都在向我们描述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女性觉醒的过程。伍尔夫和丁玲创作的孤独苦闷、涉世未深的蕾切尔与莎菲都经历了彷徨与迷茫。作者通过寻找希望的丽嘉、接近婚姻的凯瑟琳、自我价值实现的陆平、完成画作的莉莉,勾勒出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对女性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层面和历史境界,实现了作者对女性意识的突破。
1 远航中的希望与彷徨,在孤独中停滞
《远航》是伍尔夫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它在描写主人公远航的同时,也展示了作者的初次心理航程。主人公蕾切尔幼年丧母,父亲常年在外,是两个姑姑将她带大。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只是喜欢音乐,生活圈子异常狭窄,几乎连像样的街道都没有走过,这导致了她在成年后对社会、政治、爱情、婚姻、两性关系等一无所知。为了拯救蕾切尔,海伦自愿担当起领路人的角色,将蕾切尔带到南美去旅游。于是,蕾切尔开始了她的离家远行。离家就是主人公脱离家庭的庇护,进入无数充满未知事物的复杂世界。海伦带领她看到了真实的人生,蕾切尔开始慢慢觉醒,获得觉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开始了进步的人生之旅。她开始重新审视周围的人和物,追求生命中的真实,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同时,她与作家特伦斯的交往促进了蕾切尔对两性关系以及对婚姻和爱情的认识和了解。这种建立在平等交流基础上的与特伦斯的爱情,让蕾切尔受到了尊重,并使她充满了极大的自信。但是就在他们想要订婚之际,各自却陷入了矛盾的思考中。特伦斯憎恶婚姻的虚伪,蕾切尔害怕婚姻会让她刚刚建立的自我意识散失。小说最后以蕾切尔的突然生病死亡为结局。迫于当时社会对大龄未婚青年的压力,作者对婚姻产生恐慌,只有通过死亡来逃离现实,获得解脱和幸福。
丁玲这位中国现代女作家,像伍尔夫一样也发出了对异性世界的呼唤。作为丁玲的代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记录了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一群以男女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与落后迂腐的封建势力相抗争的过程。他们打破封建家庭的禁锢,摆脱世俗的观念,发出了觉醒的呼唤,表现了对自己命运的不屈服和对未来的抗争。但同时又因为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在孤独绝望中彷徨、徘徊、失落。对于莎菲而言,父亲是她温馨迁就的港湾,姊妹们也“都能如此盲目地爱惜”她。尽管如此,倔强而执着的她即使面临失败的结局也没有想到要回去,而是决计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因为在那个时代,回去就意味着走过去的路,意味着失去真正的自由。执着、倔犟的莎菲身上体现出了当时进步势力反对旧势力的那种“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决心[3]。文章通过对莎菲形象的塑造,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女性在黑暗环境下的挣扎和呐喊。尽管作者心目中的莎菲并没有受到封建束缚,但从她对毓芳、云霖恋爱的嘲讽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企图挣脱婚姻家庭束缚的知识女性的形象。而这样一个只有十九岁的少女要想在如此灰暗的环境中摆脱整个压抑的时代所带来的苦痛,对她来说无疑是心灵上的一次挫折,是一种对人生绝望的呐喊[3]。她发出了叛逆的绝叫,表明她要摆脱困境,追求新的道路,但她又无法最终挣脱时代的禁锢。
莎菲与蕾切尔都在试图冲破各自的束缚中进行心灵的航程,但她们都经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和挑战,最终迷失了自我。莎菲决计南下,蕾切尔在孤独中走向死亡。作者探索的脚步在迷茫中停滞。
2 追逐中的困惑与超越,实现自我救赎
伍尔夫与丁玲的心理航程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解脱,她们创作的形象也在孤独中停滞了,但她们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伍尔夫创作的《夜与日》即是在寻求另外一次新的解脱。书中的三位女性(凯瑟琳、玛丽、卡珊德拉)有着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凯瑟琳出身在高压奢侈的贵族家庭,过着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的生活,但是却思考开辟新的道路;卡珊德拉是一位贤妻良母,是伍尔夫想要承托的人物;玛丽是一个献身科学事业的独立女性。通过对这三位女性对婚姻的看法与选择的描写,伍尔夫展示出了女性不同的婚姻和生活模式:凯瑟林实现了自我解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走向了婚姻。从蕾切尔到凯瑟琳的塑造,作者进行了一次由少女时代步入婚姻的尝试。随即创作的《到灯塔去》,开始探讨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即“爱战胜了死,人类的奋斗战胜了岁月的流逝。[4]”伍尔夫借助莉莉诠释了她心中女性思想的变化发展历程。像《远航》一样,《到灯塔去》也是一次表面意义和象征意义的远航,但它又高于远航的层面。作为一部作品,它是拉姆齐夫人十年后实现愿望的航行,可以被诠释为一次以远航为目的地的胜利的登陆点。在路途中经历了困惑,同时又在现实中迷失了方向,最终这位航行者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也是作者自身的一次飞跃。
《到灯塔去》是伍尔夫对逝去的母亲的怀旧,也是对女性美的颂扬。这本书的结构展示了两个女性持续的自我实现的两种突破类型。第一部分是以拉姆齐夫人的意识为主宰,以晚会作为实现自我的突破。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她成功地战胜了她的丈夫。第二部分时光流逝里,女性的视觉渗透在混乱中,被转接到莉莉身上。在她的值得纪念的画中,她不仅获得了艺术的突破,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因此莉莉的人生和艺术的胜利又综合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拉姆齐夫人和莉莉通过艺术的传承在精神上联系在了一起。
莉莉是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代表。她用全新的眼光对父辈们的生活和人品进行审视和评价,感悟着自己的人生,构建自己的生命价值理念。她用一支象征男人特权的艺术画笔作为武器与男人在家庭外展开斗争,拒绝婚姻,抗拒男权社会为女性安排的传统角色。这种描述既是作者对凯瑟琳人物角色的继续,又是其内在精神世界的提升:莉莉对人对事积极、独特而又清醒的认识正是伍尔夫所认可的女性独立健全精神气质的投射。莉莉不同于代表传统女性的拉姆齐夫人,她们在精神上有着巨大的差距。莉莉对拉姆齐夫人经历了从崇拜、赞美到困惑、质疑,再到理解、认可的发展过程。她对拉姆齐夫人的崇拜和赞美是因为她看到了拉姆齐夫人作为一个女性在和男性相比较时的性别优势;她的困惑则来自于她对传统的理想女性的批判和反思;她对拉姆齐夫人的认同、理解则反映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否定之否定后的一个上升。为了艺术,莉莉牺牲了自己的婚姻。虽然深知作为一个独身女子的难处,她依然为了艺术而与班克斯先生保持一般关系,从而锻炼了她一双锐利的眼睛和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在生活中发现了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尽管作为一个印象派画家,她在生活中无疑会受到现代派的影响,但小说即将结束时她仍旧不能把孤立的碎片转化成色彩和图案,使之平衡、和谐地表现在画布上。在艺术的道路上要想由混乱达到和谐是很艰难的,但莉莉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用画笔证明了自我的价值,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神圣的艺术创作中去,终于找到艺术的真谛,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到灯塔去》通过描摹莉莉的精神奋斗历程,表现了作者对艺术领域的永恒形态、秩序与真理的探求,以及对理性与感性、时间与死亡、个人与群体、自然与人类文明关系进行的再认识。让读者“用心灵的眼睛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和艺术真实的形态,并为他们指出用以摆脱时间束缚以致达到永恒的道路。[5]”为了摆脱虚无的内心世界,故事描述了一群以莉莉为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人物形象。她们看清了灯塔的真实面目,走出了虚无的世界,找到了生活的真谛。
同样,作为对莎菲呐喊的继续,丁玲创作的《韦护》也展现出了五四运动前的社会背景,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丽嘉和革命者韦护的恋爱与冲突。丽嘉作为莎菲的延续,表现出了猖狂、孤傲的一面,而且有着更为勇敢与彻底的性格。为了继续追寻出路,作者并没有停滞不前,“将用笔端斗争的勇气表现得更加勇猛。[6]”丽嘉似乎比莎菲要幸运一点,她感情的寄托物似乎非韦护莫属。但是,正当她沉醉在这表面幸福的时候,韦护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她。她原本平静的内心、满足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冲塌。这时丽嘉猖狂、孤傲的一面得到更加淋漓的释放,她从昏昏然的梦中醒来后,擦干泪水,即使有着多少隐忍与不舍,还是发出发自内心的呼喊:“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好好地做点事情出来吧”[6]!韦护所走的道路,暗示了丽嘉前进的方向。从苦闷、感伤的莎菲到向往革命的丽嘉,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伍尔夫对蕾切尔、凯瑟琳的塑造如出一辙,都标志着作者创作思想的飞跃,我们可以从中听到作者艰苦探索的足音。另外两篇短篇小说《一九三O年春》和《上海》与伍尔夫的《夜与日》的题材相似。作品的主人公美琳与凯瑟琳都是知识女性,追求过莎菲和蕾切尔所追求的一切,在即将得到幸福、找到感情归宿时候,发现自己要寻找的理想中的伴侣实际上是“比旧家庭还厉害”的“专制者”和道貌岸然的小人物的时候,她们对爱情有了重新的审视与觉醒。正当美琳苦闷之时,是革命的力量使彷徨中的她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她断然抛弃了新式太太的安逸生活,勇敢地走向社会,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同样,凯瑟琳也抛弃了原来的追求,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
3 结束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来自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贵族。这些人群的兴趣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7]。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没有生活的负担,有的只是精神上的烦恼。在性别意识上,她更加强调保障女性的权利,提升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为我们展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灿烂一笔[3]。丁玲笔下的梦柯、莎菲、丽嘉和美琳等知识女性形象,既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知识女性在黑暗的环境下艰苦探索的历程,同时也揭示了她们心灵探寻的过程。梦柯和莎菲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不惜放弃一切,毅然地前行。她们的表现既是对社会的宣判,也是最后的呐喊。丽嘉、美琳更具有进步意义。她们在经历失败后依然能够冲破桎梏、寻找光明,获得重生。她们经历了从理想破灭、苦闷彷徨,到最终冲破牢笼的束缚,走上光明的革命之路的过程。通过对一系列知识女性的塑造,丁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妇女拯救自我、贡献社会的光明道路。
丁玲和伍尔夫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寻求女性的内心呼唤。不同的人生经历折射出她们不同的性格气质和人生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独具魅力而又自成体系的文学风格。
[1]王家湘.二十世纪伍尔夫评论[J].外国文学,1999(5):67-69.
[2]L EEH.TheNovels of V irginiaWoolf[M].N ew York:Holmes andM eier Publishers,1997.
[3]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黄宜思.“前言”远航[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武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许华斌.丁玲小说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7]L ee,Herm ione.V irginia Woolf’s essay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 irginia Woolf[M].Cambridge: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2000:327-328.
M ind S a lva tion——Fem a le I m ages in V irginia W oolf and D ing Ling
ZHANGL iyan,WANG Jinhua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North U 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China)
V irginia W oolf and D ing L ing,British and Chinese fem inist w riters respectively, create characters,which reflect the the process of female-consciousness awakening.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characters in V irginia W oolf's works w ith the characters reflected in D ing L ing's works to show the reflection of the female fates.They are based on the pursuit of freedom.They make due efforts to grope for a way of women goals,which is the unique features in British and Chinese novels.
woolf;D ing L ing;female characters;female-consciousness awakening
I106.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0.03.015
1673-1646(2010)03-0060-03
2009-12-13
张丽燕(1977-),女,助教,硕士,从事专业: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研究。
——重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解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