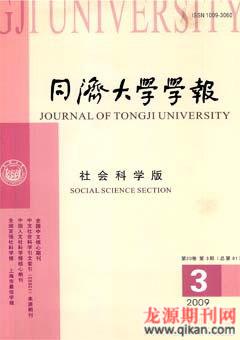符号与象征:古典小说人物意义阐释
金鑫荣
摘要: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在历史的演进和大众的阅读认知中,人物角色转型为社会角色,并超越其文本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伦理、道义、情感等多重社会边际意义。道义宣示、劝惩主题、自我隐喻、角色认同等阅读感受寄寓着大众的审美体验,其意义的传承则在时空的转换中历久弥新。
关键词:角色转换;文化符号;审美体验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63-06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诗歌与小说扮演的文化角色与符号象征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大美之言”,是文人学士疏筲性灵、抒发情感、表达个人遭际和家国情感的艺术载体;后者则被目为“小道”,属于寄寓“载道”之言和“劝惩”之旨的艺术畛域。诗歌的文化符号是模糊的,它没有具体的形象展示,更多的是表现“象外之旨”,意象之美;而古典小说则或以世情,或以历史的宏大叙事,塑造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形象,展现的是人物形象的审美特征。前者表达的是形而上的情感体验,后者叙述的是世俗故事,表现的是人世间一幕幕生活的活剧。尽管它们有时也融合在一起,但在文化特征和社会边际意义的区隔上却是泾渭分明。千百年来,古典小说人物和故事已不单单是人们娱情乐性的工具,而是逐步演化为一个个不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它们承载了艺术审美和道德价值判断的双重意义,甚至影响并规范着人们的现实行为。因此,其文化符号所表达的深层含义值得我们去解码、审视。
符号的“能指”——小说人物的角色定位
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因其历史的鲜活性和道德的多重承载而成为民间的一种文化符号,并贯穿到人们的社会日常社会的边际行为中,尤其是古典名著中的人物类型,更是各有“能指”的文化意义。如称赞某人智多、聪明,便誉为“小诸葛”;公平断案、为民请命的则是“包青天”;形容生死相许的兄弟之情,就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面容黝黑、脾气火爆的可称为“黑旋风李逵”;面容姣好、柔弱无力的戏称为“林妹妹”;胖态可掬、带点愚憨气的呢称为“猪八戒”;老实无用、只会卖傻力气的则是“沙和尚”等等……可以说,现实中各种类型的人物性情都能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可以类比的对象,并通过历史演进和文化积累而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种集体记忆。如果说,古典小说的功能表达和社会意象是小说整体的艺术阐释,那么,古典小说的人物记叙及其文化符号则是其艺术功能的“散点透视”,它们构成了小说的文化具象,并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古典小说人物的角色定位除了文本意义的形象创造的感染力之外,还在传播过程中被民众认知和充实后形成“拔高”和“贬斥”的意义申衍。小说的故事和小说人物的历史本原在小说家的敷演中发生变异和扭曲,而民众则以道义的标准来为小说人物“补妆”和“整容”。就以《三国》为例,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文武兼备的政治、军事家,但在小说家秉承汉室为正统的前提下,曹操被描绘为一个历史的无能败将,在舞榭歌台上也是一个敷白脸的跳梁小丑;“流氓政客”刘备倒成了一个知才善用、有情有意的一代明君,其虚伪无情、刻薄寡恩的一面却被过滤了。对关羽、张飞,强调的是他们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衷心护主,却忽略他们不顾原则的“捉放曹”、走麦城、鞭督邮之类的不当行止。“一代贤相”诸葛亮,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记载中并不十分凸显,但在小说中,则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人间万象的无所不能的神祗,“借东风”、“空城计”、赤壁之战等经典故事成就了诸葛丞相的一代英名,无限的“拔高”以致被鲁迅称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全不计诸葛亮还有失街亭之用人不当、六出祁山皆无功而返等军事败笔,导致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奈结局。同样的评判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英雄,如对《水浒》英雄武松,大众的记忆是他的武松打虎、兄弟情深,却不计他在狮子楼追杀西门庆时的滥杀无辜;对《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我们记忆中定格的是他大闹天宫、降妖伏魔的神奇和英勇,却不计他有时善恶不分、嗜杀无度的行径……总之,古典小说人物角色的定位是文学形象和民间道义和伦理观的叠加,其角色的认知过程也就是小说人物的定位过程,他们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洗和岁月的检视,定型为集体的思维认知。事实说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英雄崇拜”是一个民族积极的思想和文化的凝聚力,今天的我们自然没有必要去计较在历史和文学的界限中些微的是非曲直,因为它们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图腾,铭刻在民族文化的集体认知和记忆中,是一种积极的文化推力。
为了感性的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对古典小说人物的某些文化符号的“能指”列表展示:

表中都是一些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小说人物,其他人物还可以不断地延伸。如《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各有其“声口性情”,《红楼梦》中描写的几百位人物也各有其性格,但只有如图示那样的代表性人物才能通过角色的定位显示其文化符号,并为大众所熟知、认可。他们是一群人物的“类型”,是人性中善、恶、美、丑的感情的聚焦和集释,而且在道义范畴内被人们当作评判的准绳和标尺。通过列表可知,这是两类对立的意义视域,而意义的分界,即是道义的区分。只有极少数人物跨越两者之间,如猪八戒,民间总是把他当作亦正亦邪的滑稽人物,“象征着缺乏宗教追求和神话式抱负的粗俗的纵欲生活”,“是一位双重喜剧人物”。其他人物,通过他们所依附的文化符号的“能指”,演变为民众心理的角色符号。他们在角色的定位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内涵:就像贾宝玉和西门庆角色定位不同一样,人们也绝不会将岳飞和秦桧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对立的意义视域,人物的正与反、美与恶有着显豁的意义分界,而没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复杂和多视角的情感体验——这也许正是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的审美区别,但这种善恶分明、非此即彼的情感宣示却符合中国民众的审美心理需求。
这些小说人物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的文化符号和意义象征,是因为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人性的特点和大众的审美体验,并成为共同的心理认同,例如在社会纷乱之际,“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民众需要寻找一个心理的依凭,而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则成为他们的情感诉求。诸葛亮这样能定国安邦的“贤臣”自然成为大众仰慕的人物。邦国无道、贪官污吏横行之时,则幻想有包公、《水浒》众侠客英雄来除暴安良。无论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还是家国恩怨、历史情仇,也无论是风花雪月之感、俯仰天地之叹,小说人物的喜怒哀乐,都会激活起潜伏在他们心底的情感脉动。读《水浒》,滋生“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豪情侠义,读《儒林外史》时,慨叹士林的堕落与世态的炎凉;读《西游记》,有降妖伏魔、两协生风的快感;读《红楼梦》,则有伤春悲秋、世情无常之感叹……多少年来,这种情感体验成为心理的定格,深深地刻印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按照接受美学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与文学中的人物产生心灵的共鸣和共振,是因为我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对审美对象产生情感的体认与融合。几千年来文明的演进日新月异,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体验不会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情感,照样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跨越时
空的心灵之约中感悟人生,而文化符号的形成和人物角色的定型,正是历史潮汐的推进中民众心理的熔铸与沉积。
超越“文本”——小说人物的社会边际意义
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白话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社会意义早已超越了小说本身,在小说人物的角色定位中还显示其社会边际意义。也就是说,小说人物已不单是文学人物,他们身上还承载着道义、伦理等社会边际意义。这一方面与明清小说本身渊源于民间有关,如明清话本小说原本就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在流传的过程中经文人加工润饰增添了艺术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小说的社会边际意义的形成更多的还是小说的大众性和娱乐性的合力构建,并通过在市井勾栏、瓦肆书堂的说唱、演剧等更有效的传播方式为民众接受。当然,要成为一种社会边际意义的首要条件是其流布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点毋庸置疑,文学史上没有哪种文学形式的传播度可与小说相比拟,因为明清小说是真正的“市民文学”;第二是民众的认知度,这一点在小说人物的角色定位中也已确认。
小说人物的社会边际意义表现在:
道义的宣喻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往往是某种道义的化身,并演化为正义和非正义、高尚和卑鄙、人性和非人性的两极。有卖国的奸雄(秦桧),对应的有精忠报国的忠臣(岳飞);有力拔山兮、莽撞使气的盖世英雄(项羽),对应有为攫取皇权不择手段的鄙陋之人(刘备);有孔武伟岸、一身正气的打虎英雄(武松),对应有沉溺色欲、欺男霸女的卑鄙小人(西门庆);有一身正气、一路降妖伏魔的齐天大圣(如孙悟空),对应有西天取经路上的各路妖魔鬼怪;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名臣名将(诸葛亮、周瑜),也有月黑风高、大漠平野杀人越货的水泊“英雄”(梁山泊众英雄)……这些小说人物身上,已然铭刻了人们的道义的意义象征。“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秦桧和岳飞,就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认知爱国与卖国的截然不同的意义符号。梁启超甚至认为,“然自元明以降,小说势力人人之深,渐为识者所共认,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说明元明以来的通俗小说对民众思维的深刻影响。这是因为明清之际的许多通俗小说的故事本原,原来就来自历史和民间,因而具有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通过小说形象化的展示,激活了这种集体的记忆。古典小说的这种道义宣喻在历史上甚至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宣言,如历代的农民起义,总是把《水浒传》里面的“替天行道”作为起义的宗旨和方略,也把小说中的人物作为他们追慕的目标;而自清朝至民国时期,许多帮会、行会乃至现代的黑道组织,也把历代小说中的狭义英雄作为他们膜拜的“偶像”,从而形成角色的转换,即小说的文学形象转化为道德偶像,文本意义转变为道德意义,文学意义转化为民众的思维方式。
审美的对象如果说,诗词是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象,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通俗小说,则是“引车卖浆”者流的审美视域。民众往往将这些小说的人物作为自身的审美对象,如:一身狭义、肝胆相照的英雄,生死相许、惺惺相惜的好汉,为民请命、舍身救主的忠臣,嫉恶如仇、公平正义的“青天”,当然还有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孝子贤臣、披肝沥胆的忠义将领、侍亲至孝的烈妇贞女,义薄云天的义士侠客,也不缺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姻缘……他们的故事中蕴藏着许多为广大民众关切的俗世情怀。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水浒充斥的是鸡鸣狗盗、杀人如麻的梁山英雄,有些“英雄”自然不应是效仿的审美对象;而三国弥漫的是奸诈和权谋,“宁可我负他人,不可他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生存哲学,这些则是小说“审丑”对象。而“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则是一种审美形象,是集形神为一体的审美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往往是一种文化意象”。民众则以道义作为他们审美意象的评判标尺。
多少年来,古典小说所创造的一个个生动人物形象,早已超越了小说文本意义的解读,而成为中国儒家道德和伦理的一种形象诠释,它为原本空洞无序的道义律条充实了极为丰富的意义表征,使儒家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建构外化为普通民众认知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正因为小说的这种审美特性,所以梁启超在近代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中,就特别强调小说的“熏、刺、浸、提”的审美功效,他特别强调在小说阅读过程中给人们带来的情感悸动和精神愉悦,甚至要使小说成为改良社会的良方。
劝惩的主旨古典小说在张扬小说的道德意义时,很多是以人物的命运遭际和最终结局作为人物标签,而意义的结果则是以佛教的因果报应的形式完成的。如《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众多白话小说。从《喻世》、《警世》、《醒世》三书名的含义上就能昭示这种劝惩的意义,“可谓钦异拔新,洞心诫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其善者知劝,不善者亦有所惭而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三言》、《二拍》中,往往采用“开篇张其义”的方式,开头的回目中即要说明小说所要申张的道理,然后以一篇现实的故事铺叙,阐述道义的合理性,这几乎成为明清大部分白话小说的叙事套路,同样套路的还有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就像《红楼梦》中贾母所描述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小说的人物谱系也就分为简单的善恶两种形态——行善之人是花好月圆般的大团圆,行恶之人则是受尽人间地狱的种种苦楚。这也几乎成为明清小说的一种创作常态。明人就说《金瓶梅》“然小说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戒淫”之意即为小说的劝惩之旨。《红楼梦》中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对小说人物命运作了谶语式的暗示和隐喻,其意义内核其实也是一篇劝惩的宣喻,“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滚滚红尘,极世繁华,最后却是一切归于虚无,红楼一梦,何尝不是一篇警世、喻世之文?也因此,古典小说的崇善弃恶的道义一直为后世民众所接受:崇高的,德配天地,嗣享宗庙,香火不绝,如包公、关羽、诸葛亮;丑恶的,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如秦桧、李甲(陈世美)、西门庆等。正因了小说的渲染和敷演,并使小说人物贴上道义的标签,才使得文学的人物远超历史人物的本相,在小说的传播中代代相传,成为社会大众善恶认知的共识。
自我的隐喻小说是一种形象的艺术,经典的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往往会达到物我两忘的艺术效果。中国古典小说之所以在流传的过程中其小说人物的行为和事功成为社会的集体思维模式,除了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读者在小说中对应或寻找着自己的影子,即所谓一个“隐含的作者”,即“第二自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因为小说“铸鼎象物”、“毛发毕现”。的艺术描叙触动了读者心底的感觉,从而引起相应的情感脉动。吴敬梓笔下的士林群像,勾画出一代儒林之士的心灵历程。马二先生一边卖力地编选本,一边游西湖看女人之类的愚憨;杜少卿一边饮酒,一边携手娘子游清凉山的疏狂;王冕式遁居山林、不为物累的隐逸,其实都可以在士林当中激起心灵的涟漪。鲁迅讽刺上海滩的“才子”和鸳鸯蝴蝶派作家们读着《红楼梦》,于是就想象自己是“贾宝玉”,到“四马路”和“堂子间”去找“林黛玉”去了,这固然是刻薄的讽刺,
但也道出了小说的阅读心理的接受过程。就如当代的琼瑶类爱情小说,明知是爱情的乌托邦,人们依旧热衷一样,因为它构建了青春少女们对爱情天堂般曼妙虚幻的美好想象,这类描述人类情感心灵的小说能够激发起心灵的共鸣。如果说,《水浒》推崇的是游侠仗义,《三国》弥漫的是权谋争斗,《西游》追求的是心灵的无羁,《红楼梦》表现的则是对真挚爱情的追慕,这些正是人类一生所经历或向往的共同的情感诉求,人们当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毛泽东在说到革命的经历时就说自己身上有孙悟空的“猴气”,即反对强权、不从权威的反抗精神。评介《红楼梦》,不管是胡适之的“自传”说还是蔡孓民的“索隐”论,都是试图在小说中找到一个自身艺术投影的幻象,在古典小说中追踪这种情感的投射和反应。
融古知新——小说人物的现代意义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古典小说所蕴含的社会边际意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充实,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它们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历史的尘埃,而是在时空的转换中历久弥新,成为大众认可的精神建构和伦理规范。古典小说人物角色意义的思想内涵包容了传统儒学的人世精神和家国意识,糅合了道学提倡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心灵的无羁和任适,融会了释学的善恶区分和因果报应观念,民众在角色的认知中则自觉地摈弃人物身上的瑕疵,扩充、延伸了小说人物的善举和人性的光辉。古典小说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诚信守义、豪侠仗义、扶危济困、弃利趋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等中华民族的可贵品格对重塑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价值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在当下因物欲的膨胀和追逐而导致心灵的失魂和道德失范的今天,可以起到“力矫时俗”的积极功效。高居庙堂之上者,当力践并师法诸葛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重诺,为当今民生的改善竭尽心力;为官者当如包拯,公正廉明,为百姓请命,肃奸惩贪,为社会营造“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朋侣相处,当若君子之交,少些利益的挂碍,也不可一味庇护;志得意满时,不可见异思迁;落魄失意时,也不要妄自菲薄,轻言放弃……当然,还要以“反面”的人物范本为戒:不可贪一己之私利而忘却家国之大义,落下历史的骂名;也不可在色欲和物欲的拘牵中丧失本性,成为欲望的奴隶。除却一些封建主义如愚忠贞节之类的糟粕,古典小说人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生动的文化范本,他们对民众思维方式和思想的影响决非是《太上感应篇》和《道德经》之类的说教可比拟,他们以其形象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并成为传统价值和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谢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