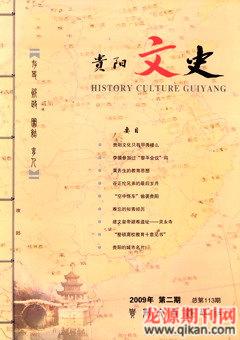郑珍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
宁夏江
在郑珍的诗歌创作历程中,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歌值得关注。“当时海禁已开,国家多故,具有敏锐感的文人更觉得前途暗淡不安,于是言愁愈愁,其表现力量,也就更能深刻而真挚。黔中诗人莫友芝和郑珍,尤足为代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于诸多原因,郑珍反映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数量不多,以至成为一些论者攻击他耽于诗艺、不问时政的把柄。探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可以修正对他不应有的一些成见和偏见,而且可以管窥到他感时忧世之情和经世济用之志,领略到他诗歌质朴感人的艺术风格。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国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满清军队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赫赫天朝上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动摇。在侵略军隆隆的枪炮声中,那种“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一下了被猛烈地激发出来,爱国诗人“每谈海氛事,即激昂慷慨,几欲拔剑起舞”(温训《射鹰楼诗话序》),掀起了一个规模颇大的鸦片战争爱国诗潮。
但是远在祖国偏僻腹地的贵州却几乎没有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没有感觉到帝国根基强烈的颤动,隅居在贵州遵义的近代诗坛大儒郑珍也没有汇入到这次爱国诗潮中去,据此,一些论者攻击他游于诗艺,不问时政,直接证据就是“连鸦片战争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几乎没有反映”。
郑珍本是一位关心时局的诗人,为什么没有加入到鸦片战争爱国诗潮中去呢?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1840年3月,母亲郑太夫人病逝,“古人在丧服中,三年不作诗。何也?诗乃有韵之文,在衰毁时,何暇挥毫拈韵?”郑珍恪守封建礼制,“为棘人,不作诗”。直到1842年6月,撢祭完毕,他才动笔作诗。自居丧至释服,凡二十七月,他可说是“三年不事吟咏”。
二是鸦片战争时期,郑珍几乎没有走出过地处偏僻的贵州。母亲久病之时,郑珍不敢远行,偶尔出行,也是“出谋生计足奉一月甘旨,即归”,最远的地方也只是遵义府。母亲病逝后,他忙于敛殡墓葬,又在墓旁建一草庐,且垦且读,为母守墓。在当时信息闭塞的情况下,自然对外边的事知之不多。鸦片战争发生在东南沿海,他可能仅凭邸报、朋友来信以及与郡府官员的交往中零星了解到战争的一些信息。1843年冬在父亲督责下,他带疾赴京应礼部试,本来这是开阔眼界,了解时局最好的机会,但抵达京师时,他目渐失明,“至不辨壁间径尺字”,又染上瘧疾,卧床不起。勉强人闱应试,不得不交白卷而出,稍愈便如同大难不死,匆匆而归。身体和心态都不允许他逗留悠游。
三是这段期间,受遵义前后两任知府平翰和黄乐之的邀请,与莫友芝等在遵义郡署之来青阁修《遵义府志》。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冬至二十一年(1841)冬,这三年间,他同莫友芝“悉发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翻遍了所有可得的图籍资料,访遍了可能有价值的断碑残垣,“穷年掎摭不闲闲,漫诩蓑衣与画斑。地赖《桑经》求鲴部,水须《班志》定狼山。游心上下职方氏,搔首西南天地间。寄语邦人莫金玉(指莫友芝),怀铅相待[食鬼]刍还。”该志“古今文献,搜罗殆尽。间涉全黔事迹……所征引前籍,至四百余种,并导源究委,实事求是。然苟旧说不安,虽在班志桑经,亦力正传本之误,纠作者之失。其纪载纤繁皆具,宁详勿遗”(黄乐之《遵义府志序》)。辑纂的艰苦与成纂的完备耗尽郑、莫二人精力心血(笔者认为郑珍的眼病和身体虚弱与此间修《遵义府志》用功太甚有关),这三年郑珍除母病回家看望,以及母亲病逝耽搁了些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府志的修纂中。由于公命在身,郑珍不得不困守一隅,无法出游,诗境为眼界所局,他所能获得的有关鸦片战争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像生活在东南沿海亲眼见到侵略者的凶残横暴的姚燮、贝青乔、朱琦等人用大量诗篇详细真实地记录这场战争。
主要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有关鸦片战争这类题材的诗歌在郑珍诗集中确实不多。
郑珍诗歌没有太多地反映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事出有因,不能据此认为他是个远离现实、埋首于经籍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书蠹。
郑珍对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侵略有较深刻的认识,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他在《送潘明府光泰归桐城序》中说:“记少年时闻言者道苏、广货,相诧极矣。十年来乃咸尚洋货,非自洋来者不贵异。今日英吉利即洋货所由来者也,其于中国为何如耶!自去年扰秽海疆,至今大半年,积半天下兵力而犹未能荡涤,是何由致之然哉?”指出西方侵略者发动对中国的这场战争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商品市场;这股远涉重洋的侵略军,竟能在中国沿海长时间的侵扰,政府劳师伤财,一筹莫展,根本的原因是腐败无能,而非敌之船坚炮利。郑珍在国门轰开之初就能对西方侵略者作如此深刻的洞察,这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做到的。
郑珍的诗歌也不是对鸦片战争“几乎没有反映”,除丧服后,他在《有感二首》其二中写道:“太祝瞎无翳,仲车聋有灵。海澄何日见,世议皱目听。烽火通龙国,楼船断鲒亭。黄头方选壮,鸡肋愧刘伶。”他听到西方侵略者在东南沿海烧杀掠夺,满清军队损兵折将,深感痛心疾首,他本想投笔从戎,杀敌建功,无奈身羸体弱。再如他的《五岳游侣歌送陈焕岩归南海》中云:“南楼日出见海东,五朝风静玻璃钟。何物蠓蠓一虮虱,不值关矢天山弓。富哉中原亿万镪,拱手掷向波涛中。君归试看五色羽,迩来恐化青趺去。更寻喑虎今在无,终古衔碑奈何许。”他认为英国侵略者势若虮虱,本是不堪一击的,满清政府怯弱而割地赔款,只会虚耗国力,助长侵略者的野心,他们贪得无厌,必然还会来进犯。形同虚设的海防,是抵抗不住侵略者的。他对鸦片战争中的决策者颇为不满,不无揶揄地说:“海内宽大极,安攘尽豪英”。(《和渊明(饮酒)二十首》)
他除丧服后的诗笔更多的是对耳目所及的现实生活的记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所遭际,山川之险阻,跋陟之窘艰,友朋之聚散,室家之流离,与夫盗贼纵横,官吏割录,人民涂炭,一见于诗”(唐炯《巢经巢遗稿序》)。郑珍的诗,还记载了战后中国自然灾害肆虐。旱灾时,“祈甘无半滴,种早不全空。水远珍于米,云生化作风。东来时借问,愁道故乡同”(《旱》;水灾时,“城门出入惟鸟鸢”,“鱼虾为谷罛网耕”(《江边老叟诗》);盗贼横行,“不论士与官,商贾更待说。吹叶作号令。麇至魄已夺。稍难刀妨下,乞命解裤袜”(《自大容塘越岭快至茅洞》);民不聊生,揭杆而起,鸦片战争前夕在贵州仁怀、綦江之间爆发了温水起义,“狼星射东井,羽檄忽纷披”(《愁苦又一岁赠邸亭》),一向以天下为念的
郑珍,“那能更修文,日夕念仁綦”(《愁苦又一岁赠(吕阝)亭》)。
他的诗歌抨击和讽刺了官吏的平庸无为和厚颜无耻。面对灾情民瘼,不但不能主动救灾,还要瞒灾邀功,如“井井泉干争觅水,田田豆落懒收萁。六旬不雨浑闲事,里长催书德政碑”(《酒店垭即事》),“官家岁岁程堤功,而今江身与河同。外高内下溃尤易,善防或未稽考功”(《江边老叟诗》)。“守土饰安治,掩著不敢泄。大吏信其然,更为最其伐(伐:功劳政绩)”(《自大容塘越岭快至茅洞》)。
在乱世之秋的鸦片战争时期,郑珍的诗歌表达了自己的经世之志以及壮志难酬的感慨。郑珍年轻时就不以文人自命,欲成就一番事业,“男儿生世间,当以勋业显。埋头事章句,小夫已翦翦。何况夸文词,更卑无可善,居常每念此,心若波涛卷。百年大概见,素志未必闻”(《樾峰次前韵见赠兼商辑郡志奉告》)。但在腐朽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广大志士却无缘施展自己的才华,“太平不假腐儒术,吾亦盱衡奈何许”(《江边老叟诗》)。他对有才之人备加压抑,恬嬉机巧之辈得意直上的官僚体制深为不满,“庸子福所聚,志士病所欺。天道有难识,此心终不移”(《君子何所悲》)。
郑珍此时年近四十,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还在为生计问题奔波,诗人未免感到憔悴伤感,“少志横四海,夜梦负天飞。将老气血静,少乐多所悲”(《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四))。“以兹朽方寸,谋生到畺蔗。烂稿过十种,闲抵许郑罅,径舍既不能,欲理却还罢”(《至仁怀厅五日,》)时光易逝,人生易老,“我年近四十,老日登头巾。约去五十年,当为觅替人”。(《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他不由得感事悲发:“一上一回老,红颜能几回”(《三坡曲三首》(其一))。他曾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经世的理想,但自中举后科考屡屡受挫。1843年冬,他再一次上京赴礼部试,达京时身染重疾,人闱应试,“卧两日夜,缴白卷出”,这对他是一种莫大的打击和伤害,“[革勺]骥苍凉断鸿哀,廿年九宿试官槐。掷将空卷出门去,王式从今不再来”(《自清明人都,病寒……》(其三))。“名场遍走历纷纷,水尽山穷看白云。三十九年非到底,请今回向玉晨君”(《自清明人都,病寒……》(其四))“挽须问事子娇成,解抱图书从我行。归云誓携诸葛姊,鈕花冢下过余生”,(《自清明人都,病寒……》(其六))。
从此他彻底地断绝了通过科举人仕的念头,安慰自己安心于训导、教谕等薄宦,甘于淡泊,“违已求薄宦,亦为无食故……劳劳百年中,会有贵生处”。(《子午山诗七首》(其七))致力于教书育人,兴教一方,以汉代乡里先人尹珍自期——尹珍生于黔地。自以厜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许慎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教授,黔人始知学。“汉朝道真公。贻今贵州书。盍即字其姓,子岂西家夫。九原怆已矣,瓠落无我如。讵知试手处,即是毋敛区。茫茫念渊源,此事岂在余”(《往摄古州训导,别柏容、鄙亭三道》)。“未敢望前哲,终期启童孺” (《子午山诗七首》)。
郑珍这段期间的诗歌不只表明了自己的经世之志,而且阐述了自己的经世策略,如他为家乡贵州如何摆脱贫穷,发展经济提出三策。
第一策是大力发展林业。黔地是山多地瘠的喀斯特地貌,滥垦只会收成低而水土流失。他把遵义的过度垦荒而穷和黎平育林植树而富做了个对比,提出黔地必须从农耕转向林业,发挥地区优势,才能守土致富,“遵义竞垦山,黎平竞树木。树木十年成,垦山岁两熟。两熟利诚速,获饱必逢年。十年亦纡图,缘林长金钱。林成一旦富,仅忍十年苦。耕山见石骨,逢年亦约取。黎人拙常熟,遵人巧常饥。男儿用心处,但较遵与黎。我生为遵人,独作树木计。子黎长于遵,而知垦山弊”(《黎平木赠胡生子何》)。
第二策是开山辟岭,改善交通状况,才能与外商平等交易,繁荣贵洲经济。如《厓堑口》写贵州依赖川盐,受压堑口等陡峭地势的阻挡,川盐无法以舟车运进,只能依靠运夫肩掮背驼,其来也不易,则值便不昂,值昂则民之食艰。“一朝会平荡,茶盐得通易”,诗人认为只有打通与四川的通道,才能免去搬运之苦,黔茶川盐才能顺利贸易,繁荣黔地经济。在《吴公岭》提出要为“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改变“越山三十里,驮负费其财”的状况,呼吁开凿赤水河吴公崖一段险滩。
第三策是发展桑蚕业,为此郑珍曾作《樗茧谱》,详述桑蚕之业,认为养蚕业“金帛满山那苦贫”。贵州养蚕业以遵义为盛,完全可以在黔地其它地方推广,“昔我与妇论蚕事,本期博得弥黔区”(《遵义山蚕至黎平,歌赠子何》)。
郑珍的诗善言骨肉手足之情,姚永概《书郑子尹诗后》云:“平生怕读莫郑诗。字字酸人心肝脾。鄙亭犹可柴翁酷,愁绝篇篇母氏思”。1840年母亲郑太夫人的去世,使郑珍对母亲的挚爱之情受到强烈的刺激而一下进发出来,情感激烈的震荡催生出精妙绝伦的艺术境界。他呼天抢地之悲、牵肠槌心之痛流露于笔端,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读之无不为之悲且泣也。他在鸦片战争时期创作的哀母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一是数量多,首首都可以说是精品;二是感情真挚哀婉,篇篇都以啼血哀鸣的方式流出,“深挚真切”,“孺慕之忱,可格天地”。中国古典诗人写哀情诗很多,但有其情者却无其才,有其才者却无其情,有其才情者却无其诗之多,“在郑珍以前的诗史上,似乎还没有人像郑珍这样大量地、充分运用平易畅达,而又雅健洗炼的诗笔朴实细致地表现家人骨肉间的挚情至性……郑珍的笔墨渗透到了家庭生活和骨肉亲人的许多方面,在整体上,他超越了前人,这是郑珍对是中国诗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