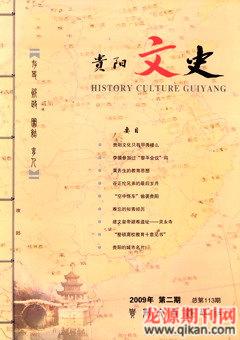郭沫若“跟风”后话
赵修朝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的成就和贡献是世所公认的。遗憾的是,解放后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身居“红墙”之内影响遍及全球且惯于“跟风”的郭沫若既不甘寂寞,而且有时候形势也不容许他保持沉默,他每每闻风而动,迅即以诗作配合政治形势。可惜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待到事过境迁,颂歌时或变为笑谈。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的文艺工作方针以后,郭沫若及时创作了以101种花卉为表现对象的诗歌,结集为《百花齐放》出版。如此图解“最高指示”,未免失之于牵强附会。而作品的直白无味,与他早年的那部《女神》,似乎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大跃进,堪称违背科学规律极左冒进的“壮举”,与当时那种政治气候相呼应,很多带有浓厚时代痕迹而且粗制滥造的民歌应运而生。郭沫若与周扬共同主编了大跃进颂歌集《红旗歌谣》,把一些严重脱离现实,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盲目歌颂“浮夸风”、“共产风”的顺口溜儿,诸如“跃进歌儿唱十年,粮食堆堆堆上天”;“不用一块钢,不用一度电,我要在破擦布里,炼出金刚钻”;“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天空”之类的糟粕,也当成艺术珍品编到集子里,为后来日甚一日的极左文艺提供了范例和“营养”。
郭沫若在主编《红旗歌谣》的同时,还情不自禁地“亲自”挥动“如椽巨笔”,为大跃进呐喊助阵。1958年9月2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讴歌安徽省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的诗:“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过了几天,媒体传来麻城县中稻亩产五万二千斤的“新纪录”,郭沫若在9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惊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要求把几天前发表的那首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看来这位科学院院长当年似乎也被大跃进那惊涛骇浪冲击得忘记世界上还有“科学”二字了。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三次谈话,指责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等人,称吴晗、翦伯赞为“学阀”。郭沫若见势头不妙,赶忙“拿自己开刀”,于4月14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表态:“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发自肺腑也好,违心“作秀”也罢,反正人家这态度够“难能可贵”了。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亲手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那会儿,郭沫若紧跟伟大领袖,及时唱出“一分总为二,司令部成双。右者必须炮打,哪怕是铜墙”那样高昂的赞歌。其“革命豪情”,比之当年那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们一点儿也不逊色。毛泽东“8·15”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郭沫若就发表了歌颂“文革”的诗作,热烈欢呼“火炬雨中红,千万人潮涌”那样的狂潮,大声疾呼“扫荡牛鬼蛇神,除去害人虫”。事后多年笔者才闻悉,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不光是扫荡了成千上万的“牛鬼蛇神”,除去了很多从来就不害人的“害人虫”,就连郭沫若这位一贯“冲锋在前”的政治运动热心人,也被“扫荡”得灰溜溜的,而且他的一个无辜的儿子也同其他“害人虫”一起被“除去”了。这位老前辈,也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
郭沫若解放前著《十批判书》,高度评价“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那个上升阶段的先驱者”,把秦始皇定位为集权主义者进行批评。待到毛泽东发动“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前夕,这位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伟大领袖在他那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大作里,以严厉的口气教训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郭沫若雷厉风行,其史学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小心翼翼地检讨自己的“十批大错明如火”,“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这行为全然不像是年过八旬的学界泰斗。
在“文革”的烈火尚未烧到郭沫若身上的运动初期,他还没有感受到多少切肤之痛,对运动还缺乏认识,那样高唱赞歌还不难理解,但直到全国人民深受其害,他本人也深受其害的1976年5月,其大作《水调歌头》,依然闭着两眼高歌“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并且火药味儿很足地批判“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这就匪夷所思了。时隔不久,神州大地一声春雷,“四人帮”束手就擒,一向机灵的郭老随即发表一首新的《水调歌头》,高度称赞这是“大快人心事”,旗帜鲜明地表态:“紧跟华主席,紧跟党中央。”他老人家真不愧为“跟风”的高手,当国家骤然发生政治巨变的重要转折关头,年迈体衰的郭沫若机敏不减当年,只将大笔那么轻轻一挥,一下子就跟上时代潮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了。
解放后长期担任国家领导要职的郭沫若,按规定他的骨灰是有资格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当时举国上下正热火朝天地“学大寨,赶大寨”,他便留下遗嘱,死后将骨灰撒在大寨,这无疑是他“跟风”的“绝笔”。然而,严峻的现实却跟他这位聪明绝顶的文化巨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没过多长时间,大寨这面“红旗”就随着改革的大潮而风光不再了。看来这位史学权威虽然以“博古”著称,却未必真正“通今”,任他恁般聪慧过人,也未能准确预测中国发展之大势,最后这一步棋似乎又没走好。倘若他老人家九泉有知,说不定会像当年作《蜀道奇》的时候那样,仿着诗仙李太白的口吻仰天长叹一声:“噫吁戏!累乎难哉!跟风之难,难于上青天!”呢。
有人以为郭沫若要是不那样“跟风”,也许会少留下一些笑柄,其实,这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高见”罢了。胡适曾发过一通高论:“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分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吧?有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郭沫若身分恁般非同寻常,目标恁般引人注目,影响恁般举足轻重,若不时时表示“紧跟”,若不紧扣时令变化唱“四季歌”,置身于云谲波滚的政治漩涡之中,何以能够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而得以善终呢?其“跟风”行为不足称道,却不难体谅,因为无论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天马行空”。好像很多人都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真理,殊不知现实中的“俊杰”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作者单位:贵阳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王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