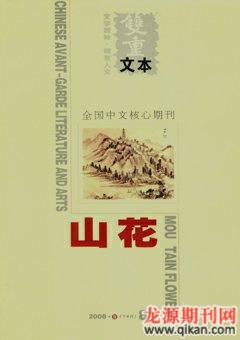"东方主义"视野中的《等待》
张志刚 常 芳
长期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以“东方主义”者的眼光看待华人以及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华人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成为定型的刻板形象。东方女人充满了异国情调,她们顺从、温柔、乐于为爱献身;东方男人则愚昧、无能,只能听别人的摆布。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那本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中这样写道:“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1999:1) 而对美国人而言,“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萨义德,1999:3) 在萨义德看来,“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位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都会假定某个先驱者、某种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的存在,这些东西成为他参照的来源、立足的基础,”(萨义德,1999:27) 萨义德的这些话虽然针对的是欧美“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但在哈金的《等待》中,我们却在这位来自中国的作家笔下,发现了某种西方对东方“假定”的观念、视角、立场和传统的遗留。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华裔作家有责任和义务打破“东方主义”的束缚,以自己的文学创作颠覆“东方主义”,而不是为解脱自己
东方人身份而自觉不自觉地称为“东方主义”的附和者。
一、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爱德华•萨义德在他那本《东方学》中,将本杰明—迪斯累里的一句名言置于卷首,他说:“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萨义德,1999:1)这句话用在哈金身上真是恰如其分。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大连金州,在黑龙江大学完成大学本科,在山东大学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后,于1985年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与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赴美后继续用华文写作不同,哈金在美国以英文写作著称,至今已用英文出版了两本诗集,三本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在哈金的这些作品中,以《等待》的影响最大,该作品一出版,就获得了1999年美国“国家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因为《等待》的成功,哈金得到了美国主流文学的认可和肯定,被认为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刘俊,2003:13)
说起来,哈金的写作动机相当平常,甚至够得上平庸,平庸到可能会让当今的中国作家们吃惊:他是为了生存而选择写作的。他有妻子孩子要养活,而他在美国得到文科博士之后,想不出自己有能力在美国干什么,于是只好选择写作,因为“写作的成本最低,你只需要笔和纸。”(哈金语)他称自己想留在美国,而英语作品在美国有更大的读者市场。此外,哈金还承认用中文写作的海外华人作家有了固定的读者群,他很难跻身其中。写作语言的选择不仅出自作家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语言直接决定作品的目标读者,影响作品的主题、题材、视角、情感表现等的选择。一些美国批评家不断提及哈金是被迫来到美国,暴露了包括文学奖项评选人在内的相当大一部分西方读者对中国移民作家的阅读偏见,(应雁,2004:32)而从另一方面也影响甚至预设了作品可能表现的内容。
《等待》讲的是一个部队的军医孔林,花了十八年时间和农村妻子刘淑玉离婚,最终和自己部队上的护士情人吴曼娜结婚的故事。(王瑞芸,2004:13)孔林离婚的理由很简单,他的结发妻子是在父母主张下娶的,是一个没有文化,一个容貌枯槁的农妇,而他自己却是一个相貌清秀,喜欢读书,非常知识分子气的人。这样的夫妻走在一起,妻子看上去倒像是丈夫的妈。他们从内心到外在都很不班配,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对她没有感情。再加上孔林在城里做医生,刘淑玉在乡下种田,造成了实际的分居,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而他在医院认识的护士吴曼娜,是一个城里姑娘,有文化,活泼开放,正合他那种知识分子的脾胃。两人好上之后,一直想正正当当地通过合法手段离婚结婚。但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环境里,离婚是一件困难的事,孔林和他的情人不得不等了十八年的时间才终于达到目的,做成合法夫妻。但结婚之后,情况并非如“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单纯。孔林反而感到新建的家庭让他失去了过去十八年单身生活的安静和轻松。新妻子旺盛的性欲,然后又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出世,弄得他身心疲惫,于是他想:我花了这么多年做成的事,究竟有什么意 义?
《等待》在美国英文文学世界的成功,哈金出色的英文写作能力固然功不可没,但小说所呈现出的“东方”世界,是其大获成功的关键,因为这种呈现,在相当程度上,符合了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想象、认知、组构和描述。小说最独特之处都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为内蕴、为空间展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作者以杜撰和虚构的方式将“东方”最大限度地“东方化”,以迎合西方人对东方的期待视野,从而把呈现东方文化变成了一种“谋生之道”。
二、永恒不变的精神乌托邦
赛义德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朱立元,1997:418)东方主义者总是将改变东方的未来面目使其神秘化,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是为其所信仰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后按西方的趣味和利益重组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因此,这种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自古以来,西方对于东方就有一套不成文的定义:异国情调的,色情的,女性化的,神秘的等等。凡是符合这个定义的,就被视作是东方美而加以接受。所谓“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其潜台词为东方是个一成不变的世界,是静态的文明,远离进步。“神秘”一词则更是一种虚假的定义,神秘的根源在于缺乏理解,而缺乏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拒绝去接受或了解东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因此将东方的事物和现象看作“神秘”。“古老”加上“神秘”,便臆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方精神乌托 邦。
《等待》是一部绝唱小说,是关于男女情感在酷严政治下被夺一净的绝唱,也是一部虚无小说。小说叙事以1966~1984年这18年发生的爱情等待作为一次情感标本考量,没有高潮,没有浪漫,甚至到最后没有感动,爱的冲动和本能都被这18年太长的等待消磨的毫无激情可言,男女双方等待来的只是麻木和乏味,一段“文革”动乱夹缝里生成的艰难爱情,最后来得如此苍白,让人不寒而栗。(周冰心,2006:61)小说的主要故事应当是发生在文革期间,但孔林妻子淑玉居住的吴家塘镇鹅村也同样出人意料的平静,孔林所在的部队医院仿佛是世外桃源,整个中国的暴风骤雨都能被挡在医院的围墙外。
在西方,人们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认为中国是由鸦片、辫子、小脚和多妻制等“元素”构成的。而辫子和小脚更几乎成了中国的象征符号。英文版的《等待》封面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条辫子,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语境。小说中,小脚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正顺应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和描述。主人公孔林的妻子刘淑玉就是一个小脚女人,她在出场时的形象是这样的:
淑玉又瘦又小,而且还十分老相。细胳膊细腿地撑不起衣服,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除此之外,她裹着小脚,有时打着黑色的绑腿。她的头发挽成素髻,使脸显得更憔悴。她的嘴唇有些塌陷,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并不难看。(哈金,2002:4)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