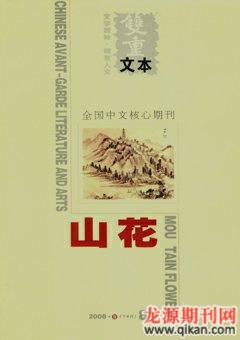归去来兮
爷爷躺在床上,已经五天滴水未进了。老黑狗趴在床脚下,它耷着耳朵,半眯着眼睛,满脸委屈。妈妈刚踢了它一脚,它缩着尾巴呜呜叫了一通,呻吟声在寂静而空旷的木屋里回荡着,格外凄惨。爷爷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一丝涎水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挂在他花白的胡须上,几天来,一直都这样。冬天的天气那么冷,我看到涎水在胡须上结成了晶莹的水珠儿。如果不仔细看,你完全看不到爷爷的花白胡须上有那么一串水珠儿。
妈妈说,“他快要死啦!”
“爷爷快要死了……”我心里在默默地回味着这句话。人快要死的时候,乌鸦总是在那株老枞树上彻夜地哀嚎,令人毛骨悚然。
爷爷不吃也不喝,他仿佛要成仙了。他甚至一声也不吭,厚重的被子盖在他身上,像座坟墓一般。冬夜的风从屋后的山岗呼啸而过,地皮都要被掀起来似的。他偶尔也睁开一下眼睛,偷看我们一眼。妈妈说,“瞧,他还没死 哩!”
他上了一次茅坑。那是在妈妈刚好不在家的时候——她正在通往菜园去拔白菜的路上。他说,“我要上茅坑!我都要快憋死了!”
他口气像被喷上雾水的玻璃,含糊不清。“我要上茅坑!”他又重复了一句。甚至,他还叽里咕噜地骂了我一声:“小杂种!”
我听清楚了。爷爷要上茅坑。
“妈妈!”我喊道。我幼小的身子无法扶住中风后摇摇欲坠显得异常笨重的爷爷。但是,妈妈在通往菜园的路上,并没有听到我那充满恐惧的呼唤。——或许,她是故意不听。我突然害怕极了,生怕爷爷在通往茅坑的路上或者在茅坑里死掉。但是,爷爷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一个翻身从床上滚了下来,“小杂种,快扶我起来,我要上茅坑!”在他面无血色的脸上,我看不到任何一丝犹豫。我只好扶他起来,他那件厚厚的黑色棉袄在被尿水湿润了无数次后显得格外沉重与刺鼻。“哼哼,我快要死了,你们心里肯定高兴了吧!我晓得的……”他说。
他倒地的身子是如此地笨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扶起来。“我自己来!不用你扶!”他说。
当然,最后还是我扶他起来。“我死了,你们心里才高兴呢!哼哼!”他边走边说。
在通往茅坑的漫长的道路上,我感觉就像人的一生那么漫长。可是,我却不知道人的一生究竟有多漫长。爷爷摔开了我的小手,他扶着墙,慢慢地走着,像钟摆一样晃动。我惊恐万分地跟在他背后,如果他摔倒了,我想,我愿意替他死去。死亡是那么的陌生,让我暗暗激动且不安。
他走得那么慢,可是妈妈一直没有回来,或许,她被菜园里那几只偷吃白菜叶的母鸡缠住了。她肯定在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顶上扎着一块花花绿绿的尿布片,像举着一面旗帜一样,在菜园四处追赶着馋嘴的老母鸡,把它们赶得走投无路屁滚尿流——这是有可能 的。
我将小手从温暖的裤兜里抽了出来,万一他突然摔倒了,我的小手便可以立刻发挥作用。可是,他一直走得很平稳,甚至让我产生了他根本就没有中风的错觉。
“别跟着我!小杂种!”他骂道,“你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的,屎尿都拉在床上,让人捂着鼻子盼你早日死掉!”
我停了停脚步,但是并没有停止下来。
从卧室,穿过房门,走过走廊,尽头便是茅坑了。
“到啦爷爷!”我朝他喊道。
“叫魂啊,我拉了那么多年屎尿了还不知道么!”他并没有领情。
我便停了下来。我仿佛看到了他衰老的屁股在蹲下的一瞬间在我眼中产生的幻觉,就像往昔一样清晰。以前,他蹲茅坑的时候,我总是好奇地尾随着他来到茅坑的门口,看他解下裤子,露出有些发黑的屁股。“滚开!”他总是这样朝我吼道。
爷爷走到茅坑前了,在即将踏上茅坑的瞬间,却摔倒了。
“呜呜呜……”他四脚朝天地躺在茅房的那条小水道里,哭了起来。我头一次看到爷爷哭。他光着头,头上一根毛发都没有,也许是脱掉了,也许是剃掉了。
爷爷之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是一个在石门享有崇高地位的和尚,石门死了人,他们都请爷爷去给死者打道场超度亡灵。但是,后来他却突然对佛教不感兴趣了,在多年前五月的下午,被一本谁也读不懂的书迷住了,奇迹般地信起了鸡毒(基督教)来——石门人都称爷爷学的是鸡毒教,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基督。“只有上帝才能把人带到天堂去!”他信誓旦旦地对石门的人说。可是在之前,他一直说观音才是最灵验的菩萨。“观音——哼哼,那算老几?!”他后来的语气显得有些不屑,甚至,他还说,玉皇大帝只不过是耶和华的远方侄子而已。
在世纪末的那一年里,爷爷不止一次站在石门的桥亭上和来来往往赶集的人说,世界快要毁灭了,再过不久,人间将呈现一番悲惨的地狱场景。他奉劝所有经过他身边的人,包括卖豆腐的阿张三,“你要是不去卖豆腐,跟我一起信耶和华,诚心恳求天父免除你的罪行,那么你才不会下地狱!”卖豆腐的阿张三被他扯住了豆腐担子在桥亭上悠悠晃晃,像马戏团里的表演者一样。可是,他最后还是走掉了:“我还是卖几块豆腐挣点钱,能吃几块算几块吧!”爷爷对此嗤之以鼻,“哼哼,他的修行还没到家,就算他悔悟返回来求我,上帝也不会原谅他!”
一个常年在石门的桥亭上靠算命为生的瞎子常拉着凄惨的二胡。他替爷爷算命,对爷爷说,“你赶快去买棵洋参吃吧,那样你可能还会多活两年。”爷爷的愤怒就像桥亭底下波涛起伏的河水,“就是我不吃洋参,你也肯定比我死得早——你迟早要被召下地狱去的!”爷爷撅着屁股边走边说。
爷爷躺在水沟里,我赶紧跑上前去。他的额头在倒下的时候刚好碰上了水沟边沿上的瓦砾,流血了。暗红色的血从他的额头上洇出来,像红墨水透过纸张。他仰面躺在水沟里,好在水沟里并没有水。茅坑就在他身边。他没有迈过窄窄的水沟,便已经躺倒了。
“唔唔,我要死了。”爷爷躺在水沟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我被吓坏了。这一具体的恐惧真实且残忍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像风中呼呼飘荡的旗 子。
早几年在爷爷还能打得动道场的时候,我还看见他舞着一把刀把缠着红绸丝的驱鬼磨刀劈得风声呼呼而响,可是,他现在却要死了。
这是一件多么恐惧且不安的事情!我不敢离开他,我生怕在离开他的一瞬间,他便断气了。按照石门的规矩,临死的时候,晚辈都会准备好几块对准了北京时间的手表,看着指针滴答滴答地转动,直到躺着的人落气为止。
爷爷半开着眼睛,依旧哼哼地呻吟着。我望着他,既担心又痛恨,要不是他执意要起床去茅坑,或者等妈妈回来他再去,这事便不会发生。
死了活该!我心里甚至有了一种可怕的念 头。
我去拉他,扶他……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妈妈,稚气的呼叫在冬天阴暗的上空回荡着,久久不息。可是,妈妈像死了一样,许久也没有回来。
我累极了,精疲力尽,结果爷爷还是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他的棉袄像屋子里摆的那具棺材一样黑,颜色阴森。
我开始绝望,一屁股坐在水沟边上,抽泣起来。
这时,爷爷却笑了!他脸上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笑容,像一圈圈水波一样荡漾着。他望着我,“你哭什么?我还没死呢!”
他脸上诡异的笑容开始慢慢凝结起来,嘴里的哼哼声也突然转变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声响。“别怕,我死后会变成鬼保佑你考上大学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然后,他站了起来!他像游泳的人从河水里突然冒出头一样,呼吸了几口空气,然后摇摇晃晃地朝房间里走去。额头上的血也不流了。
妈妈回来了,她其实只出去了一小会儿,回来的时候,爷爷的额头又出血了。所以,妈妈指着爷爷的额头狠狠地骂着我,“这是怎么弄的?!”我想分辩,但是妈妈的气势咄咄逼人,让我没有喘息的机会。后来她不骂了,但是我心中想说的话,突然像膨胀的气球里被放掉的空气一样,全没了。爷爷躺在床上,他在妈妈转过身子的时候,朝我偷偷地笑了一下!是的,在笑,他眼角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但是妈妈转过身来,他就闭上了眼睛,死了一般的沉寂。
晚上,月亮发着毛边儿,没有下雪,但是天空昏暗暗的。
四周一片寂静,方圆几里都是荒山,我家房子孤零零的像朵蘑菇一样立在山岗上。据说,山岗上曾经埋了不少土改时被镇压了的地主。地主的老子、妻子和儿子……大大小小的坟茔像馒头一样在光秃秃的山岗上凸 起着。
我和妈妈坐在木火厢里烤火。冬天的气候,虽然没有下雪,可是下雪是迟早的事情,或许,它们早就蓄谋已久了准备来场突然袭击。爷爷躺在床上,他一声不吭,闭着眼睛,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沉思,又回到了几天前的状态中。几天前,爷爷还没有中风的时候,他戴着棉帽,穿着大衣,提着小火箱,在队里的仓库里还谈笑风生、和人扯乱弹。《旧约全书》已经被他翻得稀巴烂了,他几次都嚷着要妈妈用那把纳布鞋底的钻把他这本厚厚的书用麻线重新装订起来。但是妈妈一直无动于衷,所以,爷爷在扯乱弹的时候,便穿插了妈妈的种种不是。“这个臭婆娘……”他总是在第一句话的开头提 起。
很难想象,爷爷会在晚年那么强烈地贬斥佛教。年轻的时候,当他还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和尚时,他总是将风流的种子在石门年轻的寡妇中间播撒,就像春耕时朝秧田随手撒一把谷种般利索。爷爷很快成了石门风流且深谙佛经的和尚之一——这样的和尚还有好几个。
结婚了,他总是将奶奶打得团团转,用通红的旱烟管去烫她,直到她很快病死掉。这样,爷爷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单身生涯。爷爷对佛教之前的那种痴迷就像春蚕附息在桑叶上那么眷恋。甚至,文革破四旧的时候,石门的小伙子们用抬猪用的担架把他从家里抬到队里批斗,他也没有动摇过丝毫的信念。“你们会被打入第十八层地狱的!”他狠狠地朝抬他的小伙子们咀咒着。
但是后来,他让石门的人开始目瞪口呆起 来。
爷爷撕掉了所有手中保存的藏经,《法华经》被他撕来当了手纸,之前,爷爷一再强调,把书当手纸会患痔疮和遭天谴的,但是,他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他改信了基督耶和华,张口闭口全部都是石门前所未有的新鲜名词:天父、圣母、诺亚方舟、所罗门……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从枫树来的担货郎破箱子里那本破书:《旧约全书》。这些新奇又陌生的名词在石门一度广为流传。
爷爷便自称是天父之子,做什么都是奉天行事。甚至,他开始不吃肉了,也不吃鸡血鸭血和猪血,吃饭、睡觉前后都要眯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做祷告。这是在他当和尚的时候都未曾有过的事情。爷爷预言:1999年,世界将迎来末日。
爷爷躺在床上,一脸平静,看不出一点儿波澜。甚至,连呻吟声也没有了,妈妈走向前试探了一下爷爷的鼻息,“还没死哩!”她 说。
她总是这样说,把死这个充满恐惧和不祥的字眼常常挂在嘴边。但是爷爷仿佛故意在和妈妈开着玩笑,在未来的几天里,他除了偶尔习惯性睁一下眼睛趁我们不注意偷偷瞥我一眼外,看上去就像真死了一般。实际上,他依旧仔细认真执着地活着,呼吸着房间里充满着浓烈的尿碱味的空气。
“外面那株枞树皮最近突然剥落了。”妈妈 说。
那株古老的枞树,就长在山岗上的石缝里,迎着山风,在我爷爷还没出生之前或许更早就出现了,——猫头鹰肯定就立在上面!这几天它一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呜呜呜地唱着凄惨的歌。
“妈妈,猫头鹰是益鸟,它抓老鼠呢!”我说。
“谁说的!一派胡言!难道你没有见过,死人的时候它就来了,没人死的时候它怎么不出现呢!?”妈妈对我课本上的描述几乎充满了愤怒。
是的,妈妈说得不无道理,石门死人的时候猫头鹰总是会从一些遥远的地方飞过来,带来差点让人遗忘了的、深深恐惧不安的凄惨叫声。在连续几夜的叫声里,石门人的耳朵高高竖起,他们在聆听叫声的方向——它朝哪家叫,预示着哪家的某个人就快要死 了。
“听!它又在叫哩!”妈妈用眼光示意我仔细去聆听。果然,它又立在山岗上的那株枞树上,凄迷的叫声划过冬夜寂寥的夜空,在山岗上传出去老远。
“该死的月亮怎么总是长毛呢!”妈妈 说。
从枫树请来的赤脚医生瘸子李背着那只小皮箱来到了爷爷的床前。
他打开小药箱,我睁大眼睛,恐怖地看到了里面的钳子、针筒、玻璃瓶儿……浓烈的药味在充满尿碱味的小木屋里迅速弥漫、中和,最后空气中充满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味 道。
瘸子李坐在我家的火厢边沿,他甚至不去仔细看爷爷一眼。他坐着抽老旱烟,烟雾顺着他的脸往头上的毛线帽升窜,弯弯曲曲像条小白龙。我讨厌这个人。我看到他的小药箱,我的屁股蛋就隐隐发痛。
“他会不会死掉?”妈妈问。马上快要腊月了,妈妈不止一次朝我说,“要是腊月死去,多不好呀!”
“唔唔……”瘸子李含糊不清地应付着妈妈。我感到一阵愤怒。
他终于吐掉了嘴中的烟卷,伸出手来替爷爷把脉。爷爷闭着眼睛,脸上如水面般平 静。
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说话了。打一针试试吧,只打一针,如果还不行,那就准备料理后事吧。妈妈说,“打吧打吧!”
我看到他用针筒在玻璃瓶缓慢地抽取着蓝色的液体,满满的一针筒。
……血液是红的,而这却是蓝色,我想这一针筒下去,爷爷肯定会被毒死的!对,毒死的!我被自己的突如其来的想法吓了一跳。——他会毒死爷爷!
可是,我并没有用行动去阻止这次谋杀。
我看到爷爷身上的被子被掀了起来,他持着针管慢慢地在爷爷的手臂上寻找着最佳谋杀路径。爷爷瘦小的手臂在寒冷的空气中裸露着,我看到上面虬结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正当瘸子李的针管快要插入爷爷的血管时,爷爷醒了!
他突然睁开了双眼,眼睛闪射出来的光芒把瘸子李吓了一大跳。“你这个混账……给我……滚开……”爷爷迟钝着说。他的眼睛混沌不堪,就像快要下雨时的天空,乌云密 布。
妈妈走向前去,按住他说:“瘸子李给你打针来啦!”
“滚开……”爷爷依旧说。
显然,爷爷力气衰竭得厉害,他盯着瘸子李手中的针筒,浑身颤抖得如漏筛里的黄豆。快要下雪了,天气阴暗。妈妈不得已提前点燃了马灯。这让小木屋显得更加昏暗。爷爷最后说:“求……你,别……别打……针……”他环视了四周一眼,目光渐渐落在我的身上。我看到马灯中的灯芯在煤油中逐渐燃灭掉,最后化成黄豆大点的一束灯苗。我所有的目光全部聚集在了那盏马灯身上,爷爷喃喃地叫了我一声,我才猛地回过神 来。
爷爷的手臂无力地摆放在了被子上,衰老的皮肤青黑发紫,上面还有着暗麻色的斑点……这只手臂,年轻的时候一定孔武有力,像树桩一样结实,把奶奶打得嗷嗷叫,可是现在却像发霉了一样,正面临着腐朽。
“要是你不打针,你挨不过多少日子了,你会很快死掉的!”瘸子李威胁着爷爷说。
“——他肯定是怕痛,他从来都没有打过针,肯定的,他怕痛!”妈妈快言快语,像小孩子向大人告状般和瘸子李说道。
瘸子李示意妈妈去按住他的身子。针尖冒着水珠,闪着寒光,我尖锐地感觉到了自己屁股突然不寒而栗地痛楚。
终于,爷爷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就像一只死了的动物一样——对了,妈妈每次宰掉一只家禽,它们流尽最后一滴血时,眼睛也是这样闭上的!
那只装满了蓝色液体的针筒终于插进去了,暗蓝色的液体渐渐地注入到爷爷的血液里。我想象着这股暗蓝色的液体会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在爷爷的鲜血中融合——是像一滴蓝墨水滴入水中一样渐渐被淡化?抑或他鲜红的血液全染成了暗蓝色?
整个过程,爷爷始终一动也不动,像处于冬眠期的动物。针管终于从爷爷的血管中抽了出来。爷爷被它在身上扎了一个微小的洞。瘸子李用一根药棉堵住了那个朝外面洇出血液的针洞。爷爷不流血了。
“如果他能挺过晚上,或许便还能继续一段时间。”瘸子李收拾好行李接过妈妈手中的八块钱说。
爷爷又开始动起来,我看到他迅猛地瞥了一眼瘸子李,最后终于睡着了。
晚上的爷爷,病情并没有因白天的那一针而好转,相反,情况似乎更加难以预测。他呼吸沉重,打着呼噜,但仔细听又不是那么回事儿——鼻子似乎被堵住了般。他花白的胡须露在被子外面,几天下来,胡子一点变化都没有。妈妈把马灯拨亮了些,坐在火厢里,望着床上的爷爷。爸爸还在千里外的地方干活挣钱,昨天发去的紧急电报可能还没有接到,或许他接到了正在往返家的路上赶。我和妈妈都借来了别人家的手表,时间调得准确无误。我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在嘀答嘀答地走着,小木屋外面已经漆黑一团了。子夜时分,外面好像飘起了小雪。妈妈在火厢里添了把炭,然后就开始打盹儿。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心里异常的清醒。昏黄的灯光下的爷爷,鼾声依旧,灯火摇曳,爷爷的面容越来越模糊不清……
最先听到的是一阵轻轻的脚步声!
脚步声从远处传来,那么熟悉和亲切,踩在子夜时分的地上,格外清晰。我感觉到脊背一阵发凉。脚步声越来越近,多么像爷爷平时走路发出的声响!我望了一眼爷爷,可他好好地躺在床上。
……已经走到了小木屋的晒坪上,如果我大胆朝窗口张望一眼的话,我想一定能望见他!可是,我害怕极了。老黑狗迎了出去,它一声也不吠,像迎接主人一样,在晒坪上欢快地哼哼,摇着尾巴,我想它的两个前爪一定在晒坪上刨出了几个梅花印。
……似乎还有咳嗽声,偶尔为之。我听到了!那么熟悉的咳嗽声!一阵细微的窸窣声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朵,我听到平日熟悉的开门声!小木屋的门随着一阵钥匙的响动后似乎开了!之后,仿佛一个人走了进来……堂屋里的茶壶在响动,有人开始倒茶,烧火,甚至饭桌上的那只瓷杯仿佛因被人挪动了位置而发出了声 音……
我哭了。妈妈醒来,她望着一脸惊恐的我说:“爷爷还没有死哩,哭什么哭?”我没有和她说刚才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看到了她眼角堆着眼屎。她呵欠连天,这些让我莫名地感到一阵厌恶,那一刻,我决定什么也不告诉她。但是,在她醒来的后半夜里,我缠着她想方设法不许她睡去。
我们都听到了那只该死的猫头鹰在后面山岗的那棵老枞树上凄厉地叫唤。一只我们从未见过的硕鼠——足足有五六斤重,花白相间,像只猫一样!它围着爷爷的床爬了两圈才匆忙逃走。
我盯着昏暗的马灯,感觉到满屋子都在动。最后睡着了。
天明了。外面下了一夜的雪,全部白了!在我正对着外面洁白的世界发呆的时候,妈妈在小木屋里尖声叫了起来,比猫头鹰还凄厉:“他死啦!!”
我飞快地跑了进去,妈妈正一屁股焉坐在地上,一脸惊恐。“白借手表啦,都不知道是什么时辰走的!”她说。
我走到爷爷面前,他还是像昨天一样,躺在那里一声不吭,但是,他的确死去很久了。我跪在他身边,感觉那么的陌生。
“等你爸爸回来,我一定要砍掉山岗上那株该死的老枞树!”妈妈狠狠地朝我说。
作者简介:
郑小驴(1986-),男,湖南隆回人,湖南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青年文学》、《江南》、《清明》、《上海文学》、《西湖》、《黄河文学》、《文学界》等刊物发表小说等作品若干。有作品入选年度小说、诗歌选本,被《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文艺报》等转载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