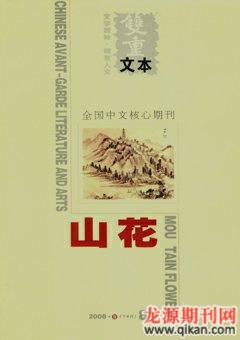女人报
出事那天,是大华和夏小满的结婚纪念日。
傍晚,大华回家见茶几上摆了凉菜,一拍脑门说,该死该死,把老婆的礼物忘了。说完就往外走,小满没拉住,便趴在窗户上吆喝,早点回来。大华应着,一转身消失在低垂的夜色里。事后小满想这是有征兆的,要不大华怎么说该死该死呢?她有些恼恨,恨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放着淡淡的日子不过,非要整什么结婚纪念日。
夏小满和大华是二十年前认识的。那时两人都在市钢铁厂上班,大华是工人,小满是厂托儿所的保育员。见第一面的时候,大华比小满还腼腆,不说话,只一个劲儿地削苹果,削完一个就放在小满面前的盘子里,说:吃苹果,吃苹果。那天小满身子不方便,不能吃。大华不知道,还削,连着削了七个,要不是苹果没有了,他一准继续削下去。后来,介绍人张大姐回来,小满把她叫进里屋,问:这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吧,不说话,光削苹果。张大姐听了笑弯了腰,说:大华见不得女孩子,我怕他紧张,就给他支招,说要是不知道该说啥了,就削苹果,谁知道他死心眼,削了一晚上苹果。这样一说,小满也笑了,觉得这人傻乎乎的,挺可爱,就答应处下去。这样,俩人处了大半年,都觉得满意,便挑了日子结了婚。
其实,大华一点都不愚,熟悉了,俏皮话也不少,有的话还让人琢磨,让人感动。比如结婚那天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小满说起来削苹果的事儿,大华就咬着小满的耳朵说:我要为你削一辈子苹果,只为你削,不为别人削,说得小满心里暖洋洋的。
结婚纪念日是小满提议过的。他们结婚没几年,市钢铁厂就被另一家企业吞了,改成了有限公司。公司要不了这许多人,大华他们就下岗了。大华不怕下岗,他有手艺,会修车,不是汽车,是修摩托车。大华沿街开了家修车铺,每月好歹有两千多的毛收入,比当工人那会都强。小满她们的托儿所也撤了,归了一家幼儿园,不少老师都下了岗,小满没下岗,她不是老师,是保育员,先前的不足沾了光,那家幼儿园缺的就是保育员。小满工资低,每月八百多。这也不少了,比起那些下岗的人来说,她和大华的日子过得算不错的。不富裕,也缺不着,小满很满足。
那家幼儿园的老师们时尚,净过洋节,情人节、圣诞节,还有专骗人的愚人节,经常有人收到鲜花。小满对这些节没兴趣,倒是觉得结婚纪念日该过,结婚是大事,纪念一下是应当的。她回家给大华说,大华也觉得该过,说如今生活好了,儿子也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两口子是该浪漫一下了。于是,去年他们就浪漫了一下,大华给小满买了把梳子,还偷偷摸摸地写了封信,搁在小满的枕头上。小满拆了信,见纸上写满感谢,感谢小满嫁给大华,让他不至于打光棍;感谢小满给大华生了个好儿子,让他延续了香火;感谢小满对大华的照顾,让他修车累了就想起有个家……这不是情书,倒像封感谢信,全篇没有一个爱字。可这感谢信却比情书更让小满心里热乎,她看着信,流着泪,看完信,扑到大华怀里哭。他们约定,每年都要这么浪漫一次。
大华推门出去后,小满就在厨房里忙。其实也没啥忙的,菜都整好了,三荤一素,儿子在学校寄宿,这些够两个人吃的了。她打开酒,倒进壶里,又把壶放在汤碗里,倒了开水,烫上。这些都完了,小满跑到镜子前,看自己的鱼尾纹是不是密了,深了。她沾了水,用手在脸上拍打了一阵子,拍得都有些木了,鱼尾纹也没见浅,倒是顺着水痕一条一条地清晰起来,清晰得真像鱼的尾巴摇了,心里便感叹岁月无情,便琢磨要是有瓶祛皱霜多好。
小满擦干了脸,跑到窗户前向外望,没见大华的影子,只有夜幕顺溜溜地垂着,上面缀着路灯橙红色的光花。这次大华会买什么礼物呢?一个精致的头花儿,一条仿玉的手链?小满趴在窗台上琢磨来琢磨去,没琢磨出个头绪,倒把自己琢磨笑了,笑自己傻,笑自己四十几岁的人了,还矫情得和个小姑娘似的。
这样想着,小满心里就美滋滋的,甜腻腻的,仿佛年轻了不少。趁大华没回来,她跑进卧室把那东西拿出来了,那是件衣服,她给大华买的——夹克,棕色的,板板正正,大华一定喜欢。小满一进商店就看上了这件夹克,一问,二百多。一件夹克二百多,真贵!她转身向外走,可脚不听使唤,不就二百多块钱吗,一年就这一次,值。
大华还没回来。小满给他打手机,大华没接。小满想这木头买啥高级玩意要这么久?她坐不住了,一趟一趟趴在窗户台上向外望。外面黑漆漆的,风吹树影晃来晃去,像池塘里一群缺氧的小鲫鱼。等着等着,小满就有些心焦了,没啥原由地心焦。她一遍遍地打电话,又一遍遍地被听筒里传来的盲音掐断。后来,电话终于通了,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小满问:你是谁,大华呢?
那声音说:我是交警队的,你认识赵大华?
交警队?大华的手机怎么会跑到交警手里呢?小满有些蒙,她不敢深想,我是他老婆,大华呢,大华咋了?
赵大华出了点事儿,在市医院,你过来一下。
这话像炸弹,把夏小满炸蒙了,把她的骨头炸碎了炸软了,她有些站不起来了。夏小满扶着墙,心里一遍遍地想,大华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他怎么会有事儿呢?不是还在医院吗?这样念叨念叨,小满就站住了。她披了衣服出了门,骑上单车,扎进夜色里。
再过几天就是霜降节气了,风已凉了,可还湿润。湿润的风扬着小满的头发,撕扯着她的纽扣,向后拽着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呢?小满想不通,其实她也没想,她的脑子木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她只觉得头发湿了,粘歪歪的,贴着额头和脖子,脸也湿了,粘歪歪的,糊着她的眼。小满想哭,可哭不出来,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出不了声,只有泪流着,冰凉的,粘歪歪的。
路不远,但小满却觉得自己骑了很长时间。她怕,怕赶不上什么。这怕也是下意识的,是说不出来的。她只是怕,说不清怕什么,只是拼命地蹬。路上有司机探出头来骂,奔丧啊。有车扯着喇叭叫,那也是骂,骂听不懂的话。有红灯闪烁,挡住去路。小满不管,她只拼命地蹬,怕一停下,就赶不上什么了。
小满还是晚了,再拼命地蹬也没能赶上。大华死了,在急诊室的病床上,盖着白单子,不是平常那种盖法,是从头到脚都盖了。有人掀开单子让她看,只让她看一眼,她看到了,没看清面貌,只看到大华头上的洞,血都凝了。小满还想看第二眼,可还没等看,她就昏过去了。所以,大华最后的面貌,小满没看清。事后小满心里后悔,恨自己晕的不是时 候。
过后几天,夏小满都浑浑噩噩的,哭都不会了。有人劝她,哭啊,小满,哭出来就好受了。可她哭不出来,再往后,她连泪都不会流了。不会哭的夏小满一个劲地削苹果,削完一个,就摆进灵牌前的盘子里,没有苹果了,就握着刀满屋子找。有人说,小满魔怔了,魂让大华带走了。
小满的魂是一周后回来的。这魂儿蹊跷,说回来就回来了,有了魂儿的夏小满和正常人一样。她想起一件事,大华是怎么死的。
儿子说是被车撞死的。在交警队,小满看到了那天车祸发生时的录像。录像不清晰,但小满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大华。大华从西往东走,走得很快,走到了路口。小满知道他要拐弯了,拐弯穿过公路就到家了。大华在路口等,等红灯拦住汽车,他穿过公路就到家了。红灯亮了,录像上朦朦胧胧的,可还是亮了。大华拐弯了,小满憋住一口气,心扑通扑通地跳。小满看到有辆大货车突然从黑影里冲出来,她急了,她能看到,可大华看不到,他还在公路当间走。小满叫,大华,来车了。晚了,那辆车闯过红灯向大华猛冲过去。小满“啊”地一声,瘫坐在地上。等她爬起来的时候,大华已经躺在路边了。那辆车停下,有人下来看了看,只看了看,就上了车一溜烟逃进了黑夜。
小满瘫倒在地上,交警队的人拉起她说,放心,肇事车辆已经找到了,肇事司机跑了,但也有了线索,很快我们就会抓到他。
在那个路口,夏小满坐在大华躺着的那个地方,哭了。她会哭了,不但能哭出泪水,还能哭出声来。这个地方只淡淡地留了条刹车印,除此之外,没有血,没有碎片,一切都没了。大华的命就在这里像泼在地上的一盆水,蒸发了,蒸发得彻彻底底,毫无保留。也不是彻底没有的,在路边的草里,小满还是发现了一个摔碎的瓶子,里面乳白色的液体已经干了,只有瓶壁纸上的字还能说话,它说,我是瓶祛皱霜,是大华送给小满结婚纪念日的礼 物。
交警队的工作效率挺快的。下午,就是当天下午,他们把电话打到了小满家,说肇事司机抓到了,正关在市刑警队。小满想见见这个人,他们说这时候是不让见的,他们告诉小满,这人是郊区西村的一名农民,名叫赵三 旺。
张大姐来了。这是个好人,大华出事后,她三天两头地往这儿跑。小满告诉她肇事司机抓到了。张大姐说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她让小满合计一下,丧葬费、抚养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怎么也得二三十万。大华出事后,小满昏头昏脑的,没想过这事儿。张大姐说,不想咋成,大华没了,该想想身后的事儿了,孩子上学,大人养老,都得指望这笔钱。张大姐说这叫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小满似懂非懂,只一个劲儿地点头。
张大姐走后,小满想自己多亏遇到了明白人,要不然,两眼一抹黑,倒便宜了赵三旺。赵三旺让人恨,小满一想起在交警队看的录像,就恨得牙根痒痒,就想把赵三旺撕了,扯了,给大华偿命。偿命是不可能的,小满心里明白,车祸枪毙不了,关上几年,出来还是生龙活虎的。可大华呢?大华没了,再也回不来了。小满想那也不能饶了赵三旺,是得要笔钱的,为了儿子,也必须得要的。
晚上,小满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大华,一会儿是飘来飘去的钱。她怎么能把钱装在脑子里呢?那是大华卖命的钱,是不该盼的。可小满赶不走,那钱直往她眼前落,雪似的。小满觉得愧疚,就披了衣服下了床,在大华的遗像前上了香。小满踏实了,靠着桌子睡着了。
第二天很早就有人敲门,是对门的邻居,说,下楼看看吧,一个女人带个娃,披麻戴孝在楼下跪半天了,说是给大华戴孝呢。
小满跑到窗户前向下望,楼梯口聚了很多人,中间跪着大小两个人,都用白布裹着身子包着头,那个小的手里还拄了棍子,也缠着白纸。小满想不起有这样的亲戚,她想即使有,也不该在丧事都办完了才来。她穿好衣服下了楼,分开围观的人,奔到那两个人面前,问,你们是干啥的?跪着的大人听有人问,便抬起头来说,俺娘俩是给赵大华戴孝呢。这是个女人,也许因为风吹日晒的缘故,面相很老,像野地里横着的一小截枯树皮。旁边的孩子是个女娃,脸黑跄跄的,八九岁的样子,跪在那里,骨碌着两只大眼睛。这俩人小满不认识,她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围观的人中有人搭腔,这就是大华的媳妇。女人听了,急忙摁住女娃的头,说,妮儿,磕头,快磕头。两个人嘣嘣地磕着头,许是磕疼了,女娃大声哭起来。
小满让这俩人磕蒙了,上前拉住女娃问,说清楚,你们是干啥的?
女人不磕了,跪在地上哭起来,边哭边说,那声音有些滑稽。小满听清了,听明白了。女人是赵三旺的媳妇,女娃是赵三旺的闺女。俩人披麻戴孝跪在这里,就是央求小满饶了赵三旺,就是央求小满找找公安,放了赵三旺。
好有心计的女人,小满想,这是苦肉计啊,夺了大华的命,还有脸来央求。这是仇 人。
小满几乎撕破了喉咙哭喊道:早干啥去了,那红灯明明亮了,他赵三旺还是猛地向前撞,撞了人还跑,可怜我的大华啊!小满哭着跑上楼,跪在大华的遗像前。不知道哭了多久,小满听到楼下那女人的尖叫声和女娃的哭声,她侧着身向下瞄,见两个保安把女人往外拖,女娃踢打着保安的腿。小满抹了把脸下了楼,叫保安松开那女人,说,你们回去吧,以后也别来了,来了也没用。说完不顾女人的哭喊,径直回家关了门窗,拉上窗帘,把嘈杂声隔在了外面。
张大姐打电话说她给小满找了个律师,据说打这样的官司挺有把握的,能多要点钱。小满一边感谢,一边把赵三旺女人的事说了,张大姐也觉得这女人有心计,劝小满莫心软。小满应着,大华的命都没了,她怎么会对仇人心软呢?她们约定了与律师见面的时间,又寒暄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晚上,小满没梦到大华,也没梦到钱,倒是梦到了赵三旺的闺女,哭着喊着向她要爹,还拿着棍子打她。醒来后,小满心里乱乱的,说不出啥滋味。在幼儿园里呆了这么多年,她对孩子有种特有的敏感。白天的事让她恍惚,确切地说是那女娃让她恍惚,假如赵三旺被判了刑,这女娃一定是恨自己的。小满有些惶恐,但她为什么惶恐呢?她无法左右司法机关对一个罪犯的判决,即使能够左右,她也不会去的,那是她的仇人,是夺走她丈夫性命的人。但她为什么惶恐呢?这样一想,小满更加怨恨赵三旺的女人,是她把那女娃扯进来的,是她把自己的闺女当成了工具。同时,小满也怨恨自己,恨自己软弱,恨自己面对那女娃时的一丝惶恐。
小满努力想让自己的思路清晰一些。事实上,她已经很清晰了,她需要那笔钱,需要法律给个说法,这是给大华的说法,也是给自己的说法。好在,现在有了律师,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她决定天一亮就去找张大姐,就去找律师,她有点迫不及待了。
天亮的时候,夏小满努力把自己整理得体面些。她甚至照了镜子,大华出事后,她还是第一次照镜子。在镜子里,她发现自己的鱼尾纹又增加了不少,要是有瓶祛皱霜多好啊,想到祛皱霜,小满的眼圈又红了。
小满又见到了赵三旺的女人和闺女,只不过不是在楼下,而是在小满家的门口,也没有穿孝服,女人穿着件灰色的上衣,女娃穿了件土黄的夹袄,都打着补丁,脏兮兮的。俩人依旧跪着,见小满开了门,依旧磕头,央求。
我说过,这没用的。小满强压着火说,赶紧回去吧,否则我叫保安了。
大姐,大姐,俺是来送钱的。女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沓子钱,一两千的样子,说,卖牲口的钱,不多,俺再想办法,求您放过三旺吧,他被判了,俺娘俩就没活路了。
小满突然有些厌恶,说,这点钱能买我丈夫的命吗?!你没有丈夫没法活,我呢,我怎么办?拿着你的钱走吧,别做梦了。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小满想自己的表情一定是狰狞的。她感到女人把自己看轻了,看俗了,看傻了,她不会上女人的圈套的,现在,她的决心比前一天更坚定了,一丝恍惚和惶恐都没有了。
说完后,小满关上了门。过了片刻,她透过门上的猫眼向外看,没看到人,便想那女人走了,被戳穿了阴谋,还呆在这里做什么呢?小满开门出去,见那钱就摆在自家的门口,赵三旺的媳妇和闺女都没了影儿。她犹豫了一下,弯腰拾起来,回身拨通了张大姐的电话。
在电话里,张大姐让她把钱先收着,点清楚,记下来,等开庭了,从赔偿款里扣就成了。小满一一照做了,心里佩服张大姐英明,要不然,自己真是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两千多块钱呢。
下楼后,小满左右望了望,没见到那娘俩,心里安稳了不少。在张大姐的带领下,她见了律师,并从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保证,二十万是没有问题的,有了这笔钱,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就有了保证。小满像吃了颗定心丸,回家的时候,顺路买了几袋方便面,步子也轻快了不少。
那是谁?是赵三旺的闺女。
离得老远小满就看到那女娃趴在垃圾堆里翻着,还不时地往嘴里捏着什么。女娃的娘呢?小满没看到,这狠心的女人。
小满走过去,问,你娘呢?
女娃指着路对面,说,那呢,卸沙子,挣钱。小满顺着女娃指的方向望过去,见路对面是个工地,两辆卡车停着,上面爬着七八个人,正一锹一锹地卸着沙子。小满看到了那个女人,可看不清楚,沙子的灰扬着,灰蒙蒙的,把人模糊了。
小满想,一起车祸,祸害了两个女人,该死的赵三旺。她扔给女娃一袋子方便面,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样,连续几天,小满早晨开门的时候都能见到那女娃跪在门口,手里拿着零零碎碎几十块钱。只那女娃跪着,赵三旺的女人不在。小满叫女娃到屋里来,女娃不干,小满说不要你的钱,叫上你娘快回家吧,那女娃也不干,扔下钱就跑。没办法,小满到工地上找到了那个女人。女人更老了,更黑了,也瘦了不少。但小满能看出,女人的精神好了许多,兴许自己收了钱,给了这女人一丝希望。小满想,她误会自己了,自己已经请了律师,正在取证,很快这女人就会听到二十万这个天文数字的,那是她卸沙子无法实现的。见到女人的那一刻,小满差一点就动摇了。她稳了稳自己,才勉强使自己安定下来,是的,那钱是她和儿子的未来,也是对赵三旺的惩罚,如果可以偿命,她即使不要这笔钱也是愿意的。
你带孩子回去吧。小满大声喊,声音小了,会被工地机器的轰鸣声吞没的。
不,俺不回去。女人站在车上,也喊,除非你答应俺救救三旺。
那是不现实的,他犯了罪,杀了人。
他不是杀人,是车祸,他不是故意的。
那他跑什么,他跑了就是杀人。
就不是杀人,三旺不是杀人犯,他害怕才跑的,三旺胆小。
……
两个女人一高一低,你一言我一语,大声地,缓慢地争吵着。小满见说不通,就离开了。她告诉看门的保安,不要放那女娃和女人娘俩进去。但说了白说,那女娃机灵,一条缝,一个洞都能钻进去,保安也奈何不了,她还是准时在小满家门口跪着,还是放下钱就跑。
这期间,小满真的就快被这女娃征服了,想算了,大华已经没了,有多少钱也回不来了,想赵三旺这样的家境,即使法院判了也是没钱给的。她把这想法告诉了张大姐,被张大姐狠狠地批了一顿,说要不要是一回事,能不能要回来又是另外一回事,说人家就等你松口呢,这时候心软就败了,大华的在天之灵也是无法瞑目的。有了张大姐压阵,小满活跃的心绪又安稳了许多,配合律师做了许多取证的工作。她所在的幼儿园也是不错的,开误工证明的时候,是按每月两千块钱算的,这样一来就多算了不少。小满觉得有点过,可又不好驳领导的好心,便一声不吭地把盖了红戳的证明信拿了回来。律师还调查了赵三旺的家产,据说他那房子值些钱,位置很好,市里已经规划在那里建开发区了,这是内部消息,当地的农民还不知道。律师还说要追加车辆的所有权单位宏兴运输公司为第二被告,他们对雇佣司机赵三旺是有管理义务的,也能争取些钱。对于这些,小满不懂,只听律师安排。
那天,小满早晨开门的时候没见到女娃,心里觉得怪,想是不是太早了,便等了会,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到女娃。她从窗户里向外看,没见到,再看,还是没见到。小满心里便怪怪的,似乎是有些空,也似乎是别的什么。她出了门,留意了几个垃圾堆,都没看到。她到工地上,也没见到赵三旺的女人。
一整天都没见到女娃,没见到赵三旺的女人。
又过了一天也没见到。小满不知道咋了,心里竟慌起来,为仇人慌,她自己也想不通。小满给张大姐打电话说这事儿,张大姐笑了,说,这有啥怪的,她们知难而退了呗。以往有啥事,张大姐一说小满就安稳了。可这次不,小满还是觉得蹊跷,觉得有些不安。不安了整整一天,有时候竟莫名其妙地听到女娃的脚步声,开了门,却什么也没有。小满想,完了,自己咋就魔怔了。
小满突然想去赵三旺家看看。这想法很突然,刚冒出来的时候,小满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儿子来电话说学校要交二百八十块钱的资料费。小满翻了翻,家里的现金不多了,她取出了赵三旺女人卖牲口和卸沙子的钱,这钱小满本来是不想动的,可儿子学校要得急,也顾不上了。小满取了钱,送到了学校。回来的路上,她突然想去赵三旺家看看,是用了他家的钱的缘故吗?小满不知道,她只是冒出来这个想法,并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样,她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
再有几天就霜降了,出了城,小满见外面的原野已经枯了大半截,很是空旷。车上有人打孩子,象征性的,但言辞却真的严厉,骂道:吃吃吃,撑死你个狗崽子。小满回头看,见那孩子手里握着个长条面包,边哭边往嘴里填。小满就想起了赵三旺的闺女,心想那女娃乖,手里握着她娘卸沙子的钱,却跑到垃圾堆里打食吃。这样一想就刹不住车了,小满又想那娘俩在城里晚上是怎么过的,之前她没想过这个问题,没在意。那时候,她只想让这娘俩快走,怎么会想这个问题呢?现在也不该想的,大华没了,只凭她每月八百块钱的工资是不够的,连自己都顾不过来,怎么还想仇人家的事呢?想到这里,小满就后悔,觉得自己不该来,可晚了,车已经到西村了,站在路口,小满已经能听到村子里的狗叫声了。
夏小满向里走,走得缓慢,走得迟疑。走到村口,她碰到有人牵牛出来,就打听赵三旺家的位置。那人用手指了,说得很详细,末了,又说家里不知道有没有人,好几天没见人了,他家吃了官司,正走背运呢,只苦了妮子,连学都没得上了。
夏小满听了,就有些忐忑,似乎是自己让那孩子辍学的。她谢了那人,七拐八拐,找到了赵三旺家。
赵三旺家里有人,透过篱笆,小满看到赵三旺的闺女正站在屋门旁边,手拿着块小砖头往墙上写字。那字写得极大,歪歪扭扭的。砖色暗,不仔细看看不清楚,小满定睛看了,依稀认出“人”、“文化”、“生”、“立”几个字,还有一个字是小满猜出来的,是个“爹”字,那女娃写错了,下面的“多”少了个“夕”,像人被砍掉了一双脚。
小满没见到女娃的娘,院子里只有女娃一个人。兴许院子大了,兴许人少了,兴许东西少了,赵三旺家的院子有点空,墙角的地方,斜放了锹和锄头,地上放着牲口的笼头,其他的,则没有了。那女娃写得专心,没看到篱笆外的小满。小满想叫她,没等开口,屋子里就传出来女人的声音,说,妮儿,时候不早了,该烧火了。女娃应着,把手里的砖头放在窗台上,转身向院外走。
在院门口,女娃见到了小满,她一愣,赶紧跪下磕头。女娃的动作出乎小满的意料,她心里像被什么戳了一下,赶紧拉起女娃,问,妮儿,干啥去?抱柴火,烧火,做饭。女娃答道。你娘呢?你娘怎么不做?娘从车上摔下来了,沙子滑,娘做不了饭了,妮儿做。小满心里又疼了一下,她抬眼望了望屋门,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不该进去,进去也许一切都完了,小满知道自己的定力不足,以前有大华、张大姐撑着,现在没人能够提醒她了,她要小心才成。小满掏出二百块钱,说,妮儿,拿着,给你娘看病。女娃不要,说,娘不让要,娘说俺家欠你的,娘说一辈子也还不完。女娃说完想挣开小满跑,小满扯紧了。这动静惊动了屋子里的女人,她喊,妮儿,谁啊?小满趁女娃搭话的功夫,把钱往女娃手里一塞,快步离开了村子。
回到城里,小满没有给张大姐说这事儿。如果说了,张大姐会失望的。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想来是不对的,但她不后悔,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她没有告诉张大姐,但她把这事儿告诉大华了,遗像上的大华微微笑着,似乎对她的做法并没有感到不快,即使在梦里也没有怨恨她。
平静下来的夏小满似乎有了主意,在上班的同时,她把大华的修车铺盘了出去,盘了三千块钱。那铺子临街,地段很好,有不少人抢着租,最后她租给了一个卖水果的,每月有五百块钱的租金,这在那个地段,也不算最贵的。张大姐是个热心人,在街道给小满争取了救济,每月二百多块钱。这样算来,虽比不上大华在的时候宽裕,但也差不了多少。不富裕,也缺不着,小满很满足。
后来那案子开庭了,赵三旺由于肇事逃逸,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民事赔偿十二万四千元,卡车的所有权单位宏兴运输公司作为第二被告,判赔八万两千元。宏兴运输公司不服,上诉到中院,中院维持了原判。开庭的时候,小满没去,是张大姐代替她去的。回来后,张大姐像打了个大胜仗,很是兴奋。为了这案子,为了小满今后的生活,这位老大姐没少操心。她说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赵三旺的女人都吓瘫了,说那女人也真是不容易,拄着拐棍去的。小满听了心里酸酸的,她问张大姐那女人是不是带着一个女孩子,张大姐说没注意。
案子结了,夏小满带着儿子到大华的坟上烧了纸。那天天气很好,天蓝瓦瓦的,连丝云彩都没有。她告诉大华,案子结了,赵三旺被判了刑,运输公司的钱也赔下来了,她们母子今后的生活大华该放心了。她还告诉大华,赵三旺家的赔偿她不打算要了,他家赔不起,真要让他女人赔,会出人命的。小满说自己打算好了,不但不让那女人赔,还要把女人送来的钱送回去,那女娃是无辜的,要是不上学,一辈子就完了。她说大华你要是答应就显个灵,让烧的纸灰往上飞,别弄得到处都是。大华答应了,纸灰翻滚着向上飘,飘得痛痛快快,干干净净。
把儿子送到学校,夏小满又坐上了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在西村,她没有见到赵三旺的女人和闺女,那个院子的门锁着,屋子的门也锁着,墙上用砖头写的字还在,那个“爹”字已经更正,是个真的字了。
夏小满在村里找人打听这家女人和孩子的下落,村民说赵家输了官司,欠了一屁股债,三旺的女人领着妮儿进城打工挣钱去了。小满听了有些失望,她不知道自己口袋里这两千九百多块钱什么时候能塞进那娘俩手里。
想起这事儿,夏小满又不安起来。
作者简介:
徐国方,山东博兴人,供职于胜利油田,2003年开始诗歌散文创作,2006年尝试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于《诗刊》、《青年文摘》、《青海湖》等刊物,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并选入年度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