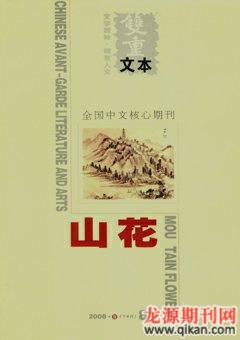洗浴
李钢音
王兴明和蔡三妹坐在澡堂大厅的沙发上,等着服务员给他们拿拖鞋。沙发很软,他们的身体陷了下去,不好动弹,脖颈和眼睛倒格外灵活。
“王兴明,你看这种鱼,最好玩,长得像一个个土财主,鼓眉鼓眼的,好像看到了金元宝!”大厅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柱型玻璃鱼缸,直贯屋顶,水中旋游着一群奇特的猩红的鱼。鱼的游动是安静的,这家澡堂的气派也是安静的,蔡三妹略微沙嘎的声音有一种回荡的效果,整个厅都能听见。
王兴明用鼻子笑一下,应了她的话。神色肃穆的男服务员拿来拖鞋,提走了两人脱下的鞋子,他身上的黑马甲和弓腰俯身的样子,加深了客人受尊崇的感觉。
王兴明一眼瞥见了蔡三妹的脚,蔡三妹并不胖,手和脚却是肉嘟嘟的,指甲油是一种古怪的油绿色。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伸过一只手,压在她的手背上。蔡三妹倏地缩回手,“啧”一声,瞪他一眼,但是,她又恨恨地笑 了。
王兴明觉得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他更深地向沙发仰进去,含义不明地微笑着,一只翘起的脚晃荡着拖鞋。蔡三妹这样的年纪,是经过了男人的,和男人在一起,她有许多的小板眼,像荆棘丛里的花,又像水草深处的鱼,而终归,她还是要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是他王兴明就是别人。他其实并不急,她只要愿意跟他来澡堂,后面的一切就该顺理成章了。
蔡三妹比她妈有脑子。她妈是个泼辣的老太太,在新北副食品批发市场,她的摊位紧挨着王兴明的,中间用高高堆起的货箱做隔断。王兴明近来打通了一条广州的进货渠道,生意渐好,忙得有些昏头,没留意那隔断一寸寸地向这边挪动,竟移了一块地砖的大小。待他发现了,笑嘻嘻地去质问,平日有说有笑的蔡老太太,顿时变了脸色,一下从竹躺椅上跳起来,拍着两腿骂他,声音像嘣豌豆,他好半天插不进话去。王兴明并不把蔡老太太放在眼里,她在这个旮旯那个犄角做了一辈子小买卖,虽然养大了几个儿女,毕竟鼠目寸光,大一点的账都算不清楚的。她嫉妒他生意好,在背后嚼舌头,他都能理解,但这样蚕食他的地盘,那绝不能容忍,批发市场可是寸土寸金的地界。王兴明见众人围上来,越发笑嘻嘻的,等蔡老太太喘气的功夫,沉嗓道:“不要吵,不要闹。现在是法制社会,泼妇骂街解决不了问题。我说你占了我的地方,你不承认,你的箱子压过这根线,我也不同意,那么,我们就有三种办法来解决嘛!”蔡老太太听得新鲜,紫涨的脸色褪了下去,声音仍旧不依不饶:“你说,有本事你说,一百种办法老娘也不怕!”王兴明说:“你听好。第一种,大家把营业执照拿出来,上面有各家摊位的面积,我们请管理人员来量,尺子说了算。这该公平吧?”蔡老太太有些心虚,硬撑道:“量就量,谁怕谁?第二种呢?”王兴明用脚尖在地上划拉一下说:“从这根线算起,我30平米的摊位,你起码占了我半个平米。你要硬占也可以,拿钱来买,多的我也不要,5万!”蔡老太太一拍巴掌,怒笑道:“5万!把你王兴明卖了,问问谁肯出5万?”王兴明说:“你不肯出钱也可以,让你家蔡三妹陪我睡一觉,我们就两清。这是第三种办法。”人群哄笑起来,有人喊:“明星就是明星,智商就是高!”蔡老太太抓住了由头,又是一通的叫骂。王兴明不理她,高声喊来了打杂的下手,让他去通知管理员。
第二天午后,王兴明半靠在藤椅上打盹。他的西装外面套了一件蓝布褂,脚边搁一罐热茶。蔡三妹来了。
她的高跟鞋像一把尖头的地质锤敲打着地面,王兴明知道是她,闭目不理。那橐橐的声音到他面前时慢了下来,最后停住。一时的静默中,人的心倒一点点地悬了起来。
王兴明沉不住气,睁开眼睛,见蔡三妹抱着手,倚在货堆上,似笑非笑、自上而下地睨视他,并不言语。王兴明坐直了身体,讪笑道:“三妹,你来了?哎呀,昨天和蔡姨有点小误会。这个事情呢,也不能怪我,本来大家熟人熟事的……”蔡三妹自顾冷笑,一字一句地道:“王明星,我蔡三妹别的本事没有,只要伸个手,你这种男人,我大把大把地抓!”这话像根蜂刺,刺了王兴明一下。他安慰自己说,她这是虚张声势,她这样的半老徐娘,怎么抓,也抓不过满街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姑娘。他不自然地笑道:“那是,那是。”蔡三妹移开眼睛,又拖长声道:“我们蔡家再没有人,也轮不到你王明星来欺负。你以为你算老几?你以为你真的是个明星?哼,一个汗臭兮兮的小老板,窝在这个30平米的臭地方,还把自己当周润发呢。好笑,我一排牙齿都笑酸!”她说着,咧一下腮帮,仿佛真的浸了 牙。
王兴明这一阵对自己的感觉,前所未有地好。那些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些穷形极相的时候,那些满世界无处哭诉的时候,他都熬过来了。这个30平米的批发摊位,帮他慢慢找回了做男人的一切,他对这摊位的感情,比当年和前妻恋爱时候的感情,还要结实,还要深厚,是一种饱经漂泊后的荣辱与共。蔡三妹实在老辣,处处踩着他的痛处。
可是,蔡三妹宝蓝色的睫毛膏下的眼光,幽幽地移开去,那一刹那,王兴明忽然很心疼她。心疼一个女人的感觉,是很能叫一个男人屈服的。他们蔡家还能有什么人呢?她那个妈,年轻时就守寡,拖家带口这些年,只懂得一味地跋扈蛮横,像母鸡守着鸡崽和口粮。这城市里的老太太们,有的早晨去公园里舞剑,有的晚饭后到广场跳舞,还有的儿女去了国外,老两口飞来飞去做国际候鸟。蔡老太太,只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她的摊,夏天摇把蒲扇,冬天瑟缩在石英炉边,趁人不备时,将货箱一点点地偷挪过去,以为这就占了天大的便宜。蔡三妹的哥嫂下岗多年,嫂子患了一种难治的慢性病,哥哥到市郊的一家加工厂打工,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她的姐姐还算好,拆迁后,搬到市郊临街的房子里,开了家麻将馆,也就是有了份营生而已。蔡三妹原来在百货公司里做营业员,公司垮了,吃着劳保。她嫁人早,离婚也早,仗着姿色还在,便有一种悠哉悠哉的作派。心情好了,她会来帮她妈搭把手,更多的时候,不知她在这城市的哪个角落里游逛着。时间是专供男人积累资粮的,对于女人,是一个无情的漏斗,把饱满的生命的汁液一滴滴漏空。王兴明吃透了这城市的日子,他比蔡三妹更能清醒地看到她的将来。
“哦,牙酸了?是哪一排?我看看!”他涎着脸凑向她。
“恶心!”蔡三妹蹙眉挥手,像要赶走一只苍蝇。她当然知道王兴明对她的意思,但这意思是长久的,还是短时的,她拿不准。王兴明本来并不在她眼里,他个头矮了些,鼻子塌了些,肚子圆了些,就是逢场作戏也少了点吸引力。当然,现在她是明白了,男人,最重要的是那一点真心,还有养家的本事,这才是一个女人真正要的东西——似乎是最简单的,往往又是最难的。
蔡三妹迟疑着,脸上厌憎的表情也迟疑起来。王兴明看见了她的迟疑。
这家澡堂叫“新感觉洗浴中心”,从闹市区不起眼的大门进来,兜头是豁然一片的豪华。灯光半明半暗,照在墙壁高大的西式裸女的浮雕上。大理石的地面映着人影,踩上去倒稳稳的。身着制服的男女服务员无声地走动,来到人面前,脊背挺直,眼皮垂下去,有一种训练有素的恭谦。
王兴明没想到蔡三妹这样爽快就答应他。在手机里,他故作轻松地问:“三妹,去不去洗澡?我请客,新感觉。”那头的蔡三妹似乎正在逛商场,手机里有促销什么的声音,她立即应道:“新感觉?当然去,不去白不去!”她的毫不推诿,让王兴明有些怅怅的:他不希望她过分地拿捏,更不希望她是那类来者不拒的女人。其实,他有些误会了蔡三妹。在她这里,每一天,都悠悠长长,需要拿许多东零西碎的杂事来填补,尤其是好玩的事情;有人邀她洗澡,正是何乐不为。至于男女之间,她自信到时候相机而行,能够拿得住分寸。
他们方才坐下时,瞥见一个男人穿了一套浴衣从洗浴部出来,趿着拖鞋,走路略微地八字步,头发湿而乱,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解下了装束的男人。这功夫,他走出了更衣部,若不是他那张标准的国字脸,几乎要认不出了。他戴一付隐框的眼镜,腋下夹一个皮包,陡然变得衣冠楚楚,神情郑重,是个做大事的男人的模样。他们目送这男人在服务员“谢谢光临”的话音里出了旋转门,门玻璃一晃,又一晃,门外有一个车来人往、活色生香的世界。他们一时没说话,都有些感触。王兴明想,所以说,男人,关键还在个气质。蔡三妹想,男人进了澡堂,都一样是褪了毛的公鸡,穿上了衣服,就那么不同。
蔡三妹把身体从沙发上支起来,解开发卡,甩了甩染成黄褐色的卷发道:“去洗嘛,又不是来看戏,老在这里傻坐!”
王兴明拍拍沙发,自在地说:“忙什么?有什么好忙的?来这里就是享受嘛。你好好坐着,喝点热茶,听听音乐。”
蔡三妹深究地看他片刻,“扑哧”一下笑了。王兴明问:“笑什么嘛?”蔡三妹扭脸扬眉道:“不说!”王兴明道:“女人的心,天上的云。你不说,我也猜不到,干脆不猜。”
蔡三妹听了,又一次别过脸来,深意地看 他。
王兴明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周身找不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地方,可他那么放松了手脚坐在那里,自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态度。她认识他好几年了,过去他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老婆带着孩子,嫁给了一个湖南来的生意人,王兴明衣衫邋遢,神色委顿,又想撑着做人,跟人说话用一种毛毛躁噪的大嗓门,眉间有一个明显的发黯的川字,绝望而好斗。现在,他的脸舒展了,他本是一张带几分憨厚的脸,展开来,就变成了宽厚和练达。这自然跟他的生意有关,听说他每月的毛利已经近万,刚在温馨国际买下一套房子,这样下去,他的日子不说大富大贵,也该是稳妥的。
蔡三妹的心模糊地动了一下,她捕捉不到那原因,一张涂满花哨的自卫的桃脸,瞬间显出了迷茫。她又坐直了一些,感觉自己的胸脯挺了起来,今天她本该穿那件玫红的毛衣来 的。
她用手指作梳子,慢慢地捋着头发,闲闲地说:“你不猜,我偏要告诉你。王兴明,我发现,最近呢,你特别地拿自己当明星!”
王兴明仰头哑笑,问道:“是吧?”他不要她回答,笑咪咪地看向她,有点不置可否的意思。
王兴明被新北批发市场的人叫做王明星,跟几头猪有关系。批发市场一侧,是一家颇有规模的生猪屠宰厂。听说里面的猪被宰杀前,一律洗温水澡,听音乐,不知不觉就生死两隔了。但各地送猪的车,常常堵塞了惟一的通道,是很让人烦心的。王兴明那天早上骑着摩托去摊位,发现那条路格外地堵,不仅有车,还拥着一簇簇的人。他不耐烦地掀着喇叭,有人斥他道:“前面出事了,你还想过去?省长来了都过不去!”王兴明喜欢看热闹,他锁好车,向人群中心挤,一路打听。原来,一个农民拖了几头肥猪来,刚把猪赶下车,路边屠宰场的一根电线突然断了,从猪身上扫过去,几头猪当场倒毙。农民不依,要屠宰厂赔偿全部损失,屠宰厂只愿赔一半,两下吵闹了起来。王兴明好容易挤到猪跟前,就见一个长发的男人扛着摄像机,另一个穿红条衬衣的,将一只毛绒绒的话筒伸到一个农民的嘴前,问着什么。那农民真是伤心了,他的一条裤腿胡乱地卷起来,露出灰脏的筋脉鼓突的小腿,黑瘦的刀条脸上,有一种被烈日灼伤的神色。他的声音是激忿的,说出的话却夹缠不清,连不成句,一会儿说这路多么难走,光是过路费就交了一百多,一会儿又说猪不好养,饲料涨得厉害。“我把猪给你拖来,又不是来遭电打的,我是拖来给你杀的,是不是,是不是啊?”他反复地说这句话。这是他最重要的意思,听来却是一句废话。王兴明替他发急,隔着一圈人,恨铁不成钢地瞪他。他回头去应一个老头的议论,谁知再转过身来,那话筒竟伸到了他的嘴边。王兴明有一时的惶急,小腹向下猛地坠了一下,但他曾经是车间里的小组长,又刚和徐建强去海南旅游回来,见了世面的。他很快稳住了阵脚,替那农民说了一通慷慨激昂的 话。
第二天,批发市场的人就在电视台的新闻里看见了王兴明。他是批发市场第一个上电视,并且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他的衣领没翻好,有一边裹进去了,因为前一夜打麻将,眼袋也很明显。只见他忿然道:“当然应该是屠宰厂赔,一分钱都不能少人家的!”镜头一换,另一位派出所的年轻民警则温和地说:“这件事情,我们会尽量协调的。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这白面书生样的民警,把王兴明反衬得像一个楞头青。其实他当时的话,岂止这一句,他还说了“法律、公民、公正、同情心、调查取证”之类堂皇的字眼,却被电视台掐了。
王兴明想,笑话,他哪会在意别人叫他明星。他活了四十多年,若说最大的本事,就是知道自己是谁,这本事,并非人人能有。但是,人看着电视上的自己,大约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那另一个自己,总是和真实的自己有区别的。王兴明一时琢磨不透那区别,往下过着,一些事就不请自来了。
比方那天,他坐出租车去城南找一个买家。溽热的天,他和司机都懒懒的,一路无话。收音机里正播着一档“城市热线”的节目,一个女主持柔声细语的,音乐也是缓缓的,打进的热线,却都带了天气难耐的热度。王兴明透过车窗看着街景,渐渐听了进去。他忽然看见车驶过的一条新铺的马路,又被挖开来,难看地翻着泥石。这事堵着他的心,开始只是淡淡的一点,越想越甩不掉。下了车,他找个树荫下站着,掏出手机,拨了“城市热线”的电话。导播让他等着,等了足有一分多钟,接通了女主持。王兴明说:“喂喂,是我吗?”他知道,这城市的许多人都听见了他的声音。女主持温婉地回话:“是你,这位听众,你好。”王兴明直直地当街站着,不知是心里,还是身体里,腾出了一种奇怪的感动。他说了发现马路被挖开的事,义正辞严道:“我就是希望加强规划,不要修了挖,挖了修,一方面浪费钱财,另一方面呢,也影响市容,是不是啊?”女主持仙音袅袅地说:“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情况,我们‘城市热线,会及时向有关部门反应的。”然后,音乐响起来,女主持又道:“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如果大家都来关心我们的城市,那么,我们的城市一定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家园。”王兴明关了手机,依旧站立了片刻。他看一街的人和车,都不真切,如同坐在影院里看电影。
以后,王兴明打过110,打过市长热线,打过夜间的“蓝调情感”、“芳草天涯”,甚至还打了专说男女性病的“健康伊甸园”。他特意买来一副耳机,一只耳朵听收音机,一只耳朵听电话。深夜里,他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回来,总是那不真实的奇妙的效果。这日子,有时候复杂得一团乱麻,有时候,简单到百般无聊。王兴明过得太久了,心像一件银器,一天天地,镀了灰垢,败了色,但是,打一回这样的电话,仿佛给这银器刨了一次光,又可新鲜一阵。这才是他做了王明星以后最大的变化,但这是他自己的秘密,不必告诉谁。
“——是吧?”蔡三妹学了王兴明的语气,忽地脸一板,在他肩上捶一拳道:“是不是你自己明白!那天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坏了我的名声,对你有什么好?”
王兴明稍作夸张地斜身躲她,笑道:“狗急跳墙,人急上房嘛,你妈那个泼劲一上来,天王老子也惹不起。再说,你动脑子想想,我还不是把自己的名声也赔进去了?”
蔡三妹娇俏地“哟”一声,不认识一般看他:“你们这些男人,馋猫一个个,只要能偷到那一口,还管什么名声!”
王兴明长声叹道:“蔡三妹啊蔡三妹,你知道几个男人哟!”
蔡三妹受了他一唬,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她轻蔑地笑一下,掩了过去,想一想,毕竟不甘心,一侧身对着他,眼光灼灼的:“实话告诉你王明星,没有几十个么,几个,倒是有 的。”
王兴明保持着脸上的嬉笑:“哦?说一下,哪几个?”
蔡三妹抱起胳膊,身体是骄矜的,脸上倒有一种难以抉择的烦恼:“一个呢,是个煤老板。钱倒是大把的,就是岁数大了点,跟他前头那个的孩子太多了,二女一男。还有一个,是个老师,正牌中学教化学的,人还本分,不过有点呆。第三个,是个科长,比我小两岁,人家都说看起来比我大十岁,太会缠人,我怕靠不住。”
王兴明似乎听得津津有味,问道:“还有呢?没有了?”
蔡三妹撇嘴道:“就这几个,还不够我烦 的?”
王兴明把一条腿曲到沙发上:“照这么说,都是你挑人家,人家就不挑你?”
“挑啊,”蔡三妹道:“他们挑了半天,就挑了我。”
王兴明轻轻笑一声,看着对面墙上的浮雕裸女,一脸的暧昧。蔡三妹想,这个话,说到了这里,该让他自己去回味了。她站起来,竖起一根手指,转着刚才服务员分发的储物柜钥匙,说:“我要进去了,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把这里当咖啡厅呢。哎,你到底走不走?”
王兴明慢吞吞地起着身:“走嘛,咋不走。哎呀,人老了,腿脚不灵便,这一脚插得慢了点。”
蔡三妹咯咯地笑起来。这当口,王兴明的手机响了,是国际歌的铃声,惹得前厅里有几人向这边看。王兴明向蔡三妹挥手道:“你先去,女宾部,左边。”蔡三妹说“知道”,扭身走了。
电话是徐建强打来的。他正无聊,声音也惫懒:“星哥,在做什么嘛?过来喝茶。”王兴明重又坐回沙发上:“来不了,今天有点事。”徐建强不相信:“少来这一套,你是经理吗,老总吗,CEO吗?忙个鬼啊!”王兴明道:“谁敢骗你?跟一个客户吃饭。”徐建强嗤之以鼻:“男客户么女客户嘛?”王兴明不答,看着蔡三妹进了女宾部的门。门内仿佛有水汽卷出来,让人生几分遐想。他问徐建强:“哎我说,你跟那个,咋样了?”徐建强说:“还不是那么回事!”王兴明道:“抓紧点,我预计,你再过两年就人老珠黄了。”徐建强说:“就你会预计?你聪明?好好,你忙,不敢打搅,我收声!”他那边挂断了电话。
王兴明还是坐着,脸上一点一点地浮出了 笑。
王兴明平生就坐过一次飞机,是往海南的打折航班,徐建强约他去的。他们两人都穿一身西装,提个黑色的仿皮公文包,商务旅行的样子。徐建强还打了条领带,灰蓝底,银亮的点。他们在海南玩了一个星期,最后的两天不仅索然,而且难熬,说完了几辈子的话,抖落了许多半真半假的心事,看了些最初新鲜、但很快变得无关痛痒的风光,再也呆不下去,急忙地打道回府。回来的飞机上,王兴明总结道:“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去不去都无所谓,坐在家里想想,说不定比去了还好!”
海南之行浮光掠影,毕竟给王兴明提供了一点聊天的资本,坐了飞机,住了酒店,洗了海澡,喝了直接从树上取下来的椰汁,吃了一种形似古代盔甲的、当地人叫做“海鸳鸯”的东西。而飞机腾空和落地时的景象,才算是深深地刺激了王兴明。
那一刻,他那张圆实的、常常嬉笑着的脸,是真正严肃的。他贴近机窗,看着机场边低矮的建筑物眨眼间就消隐了,然后,无边无际的楼房和街道,铺满了整个的视线,像巨大的迷宫。飞机再高一些,迷宫不断地缩小,变成了棋局,棋局的边缘被空中掉下的云絮遮掩。终于,天上地下汇成了浑茫的一片。王兴明费劲地找着他小时候在那里长大的丁字口,他现在住着的南帆家电厂宿舍,但是,都没有找到。没有这两个地方,他王兴明这个人,就像从没来过这世界,只是一片被飓风刮到天上的树叶,心里空空的。突然地,他从几百米的高空,看见了每天守摊的新北副食品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像一块横倒的麻将牌,黄色的屋顶清晰可辩。王兴明向窗玻璃贴过去,可那小小的黄条,一掠而过,不容他看第二眼。不管怎样,王兴明总算看见了批发市场,心也变得踏实了,还有点发热:原来这个大沙盘一样的城市,还是有他的立脚之地的。过去他心猿意马,觉得守摊太枯燥,赚不来大钱,从天上下来后,王兴明对自己的生意有了新的认识,他想,说什么,也要守好了它。
徐建强这个人,就是吃亏在没有自己的据点。倒腾了这些年,他倒想通了,依仗自己英俊的脸蛋,吃女人的饭。他那几个富婆,王兴明也见过,觉得索然寡味。自然,人家也看不上自己。不过,大千世界,各人有一份日子,男人自己站稳了,不愁没有女人靠上来。
蔡三妹这时候还端着她的架子,那也就是些花架子,经不住生活和时间的磋磨。让她端着,端累了,她会来靠着他的。
王兴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穿过大厅,刚要进男宾部的门,听到蔡三妹一迭声地喊他。他停下来,见蔡三妹穿着澡堂里的浴衣,头发湿了一半,往肩头滴着水,脸有愠色:“我们那边的热水管出了问题,不是烫得要死,就是冷得要死。洗不了!”王兴明道:“不会吧?人家这里很正规的,是不是你自己没调好?”蔡三妹道:“我又不是乡巴佬,比这里还高档的地方,我也去过!我们退钱走人,不洗了!”王兴明不愿走,道:“你等一下,我去服务台问问。”蔡三妹道:“我在里面已经问了,是管道的问题。算了,下次再来吧,今天先去吃点夜宵,霞飞路那家,韩国烧烤。”王兴明想一想说:“也行。你去换衣服,我去退 钱。”
服务台内站着两个女服务员,穿着红马甲,头发抿得溜光,面带微笑。她们称王兴明“先生”,说来说去,就是不肯退钱。争执了好一会儿,终于同意了退蔡三妹的,但王兴明的不能退,因为男澡堂的热水管是正常的。王兴明听她们一口一个“这是我们新感觉的规定”,忍不住冒火了,声音高起来,一拍柜台:“规定个屁!我不管你们什么规定,退票是我的权利。你们今天不给我退了,我马上投诉你们,信不信?”
他的肩膀被人从后面狠狠地推了一把,一个男声道:“我就不信,你咋样?”
王兴明猛回头,刚看清是给他们拿拖鞋的那个男服务员,头上又被另一人粗暴地撸了一下,狼狈地偏下去。他叫起来:“好啊,光天化日的,你们敢动手!”
他的身边围着四个穿黑马甲的。其中一人给了他一耳光:“打的就是你,不服气?去啊,去投诉啊!”
王兴明背靠柜台,知道自己不是对手,除了脸颊上火辣辣的痛和耻辱,他的心里多少有些发懵。他一一瞪着他们,他们年轻平滑的脸,却是平静的,好像打人只是澡堂里的一项服务。其中一个,嘴角还有未退去的戏谑的 笑。
王兴明站直了一些,尽力镇静道:“现在已经不是投诉的问题。你们打了人,那就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是法制社会!”
他的话音一落,几只胳膊一齐伸过来,将他又推又拉,搡过大厅,挤出了旋转门。王兴明屁股上挨了一脚,他无法回头去看踹他的人,甚至来不及叫喊,已经到了门外。
天色全然暗了,灯火像撕碎的天光,东一块西一块地落在街上。他们几人扭扯成一团,稍远一点就辨不清面目。王兴明跳着脚大叫一声:“打人啦!报案啦!”街上稀疏的人闻声看过来,但不敢靠近,他们的面目也暗而模 糊。
王兴明的喊叫引来了又一顿拳脚,他忍不住“哎哟”地叫唤。他发现他们都是老手,专打他肉厚的地方,出手的动作也不大,声气都听不见。他每叫一声,拳脚就从四处落下,迫得他只顾哼痛。混乱中,他掉了一只拖鞋,后来,他被裹进了澡堂外的一条背街,在一个路灯照不到的墙角,他们把他掷到了地上。其中一个人拍拍手,拍掉灰土的样子,俯下身逼近王兴明的脸道:“你去告,哪一天告,哪一天我们就来给你的灵堂烧香。”另一人用脚踢踢他的大腿,语重心长般说:“老哥,收敛一点,不要一痛就叫,更不要乱叫。”然后,他们哈哈一笑,转身走了,走得也很从容。
王兴明伏在地上。水泥地面吸了一天的热气,并不显凉。他动了动腿脚,腿脚也是伸曲自在的。但是,他的脑子嗡嗡地响着,那是被各种翻涌上来的反应震的,他竟然不想爬起来,蜷在那里,试图分辨混杂在一起的激怒、羞辱、惊震和后怕。
他听见蔡三妹在街口破声地叫他:“王兴明——!王兴明——!”但他顾不上理会,心里哆哆嗦嗦地想:我要记住这四个人,我要记住这四个人。过了片刻,蔡三妹拐进了小街,高跟鞋的橐橐声一串凌乱。她看见了黑糊糊的王兴明,嘶喊着扑了上来,跪在他面前,两手在他身上摸索着:“啊!打哪里了?伤哪里了?咋回事啊?我才去换衣服,咋出来就这样了……”王兴明抚住她的手道:“四个人打我一个,好像还没有伤筋动骨。”蔡三妹哭道:“没有王法了?我听人家说了,根本就不相 信……”
她一哭,王兴明倒清醒了。他坐了起来,伸手掏出手机,准备拨电话。蔡三妹摁住他的手道:“你做什么?”王兴明说:“打110。”蔡三妹道:“哎呀,不能打。你没听说吗?这些地方有黑社会背景的,洗黑钱的!等警察走了,他们还能放过你?”王兴明“嘶”地抽口气,看住她说:“照你这么说,我今天这顿打就白挨了?”蔡三妹道:“没有伤到筋骨就算万幸,你还想咋样?来,我扶你起来,打个车,先回家再说!”她说着就要扶王兴明。他甩开她道:“蔡三妹,你怕,你先走。我打110,然后在这里等人来。”蔡三妹的眼睛在黑暗中盯住他:“王兴明,我劝你不要只图一时痛快,还是要为一家老小想想。”王兴明说:“我光棍一个,怕什么?今天这事不解决,我再叫王兴明,我就不是人!”
他打开手机盖,荧光幽暗地映着他的脸。他的头破了,一道血迹从额头挂向鼻梁,看上去有些吓人。刚要拨电话,王兴明突然停下,脸上起了古怪的笑,柔声道:“蔡三妹,刚才,你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