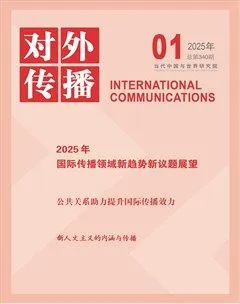新人文主义的内涵与传播
【内容提要】在当代国际传播秩序中,“文明等级论”与传播霸权依然明显,打破这种格局需要从文明观的顶层树立崭新的传播观念。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的成功实践与先进理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时,要把这种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理念——新人文主义,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为世界交往提供新的思想公共品,重点是传播全人类意识,传播中华人文精神,传播文化多样性。
【关键词】新人文主义 人文精神 文化多样性 国际传播 文化传播
2024年6月,笔者率团访问法国,开展中法建交6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访问期间与法国汉学家白乐桑(Jo?l Bellassen)教授进行了深度交流。白乐桑之所以学习中文,是因为汉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激发了个人的挑战感。令笔者惊讶的是,这位汉学家来过中国数百次,对中国的许多文化内容非常熟悉,对于怎么让中国的“文化内涵”而不仅是“文化形式”走进世界有着深入思考。这次交流的启发性在于,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仅仅是表演性、生活性的内容还远远不够,而是要把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特别是对当代世界有意义的文化价值观提炼出来,既要讲清楚“是什么”,更要讲清楚“为什么”,还要讲清楚中华文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与世界交流对话,为当代人类文明作贡献。
作为一个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有着历史的文明厚重;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持续增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着现实的文化魅力。对于世界各国的学者、民众来说,中华文明无疑具有极强的陌生感,也因而具有吸引力。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美好未来前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新模式,彰显着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美美与共、命运与共等价值理念,倡导不同文明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开展交流互鉴,不同国家超越政治差异携手合作发展。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形象与声音,就要基于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结合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针对当代突出的全球性挑战,提出具有最大共识度与对话性的文明理念。
一、新人文主义的提出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普遍以物质之丰富作为根本追求,而将文化之丰富置于其次地位。如果颠倒次序,把文化之丰富作为根本追求,以物质之丰富作为手段,或许世界之纷争会减少许多。人亦如此,以人文底蕴为根本追求,则内心之纠结会减少许多。从2000多年前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从孔子到苏格拉底,对人文主义的精神都有着共同的追求,而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以民为本的文化,更有着数千年的丰富实践,可以成为21世纪人类新人文主义建构的坚实基础。巴基斯坦学者萨义德·贾瓦德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软实力海洋”(a vast ocean of Soft Power),这种软实力的价值体系已经发展了5000多年,至今几乎是完整的、也是经过验证的。中国人的“积极主义”(Positivism)和“共赢理念”(Win-win)在全球化时代具有超越性的优势,让中国获得尊重、热爱与利益。现在的中国继续在为一个平衡与和谐的世界寻找“中庸之道”。①
中国要为世界找寻新的中庸之道,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人为本和天下为公,传播全人类意识,传播中华人文精神,传播文化多样性,建构与传播21世纪新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度复兴,表现了走出中世纪欧洲的“人的意识”对神权的反抗。这一思潮不仅带来了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并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人文主义伴随了西方力量从大航海时代崛起至今的五个世纪,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与思想观念,不论是公元前的苏格拉底、西塞罗,还是15、16世纪的伊拉斯谟、蒙田,奠定了今天西方乃至全人类许多共同的政治哲学与文化价值。人文主义在西方知识界具有普遍的共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专门为蒙田写作了传记,并认为,“在伊拉斯谟领导下的人文主义展望着一种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文化”。但遗憾的是,面对世界纷争的现状充满失落。②20世纪的人类社会既有科技革命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人文主义出现了式微,但面临新的人类共同挑战,这一思想观念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在返本开新中可以、也理应绽放出新的旺盛生命力。
当代政治运行的突出特点是认同政治的形成。自从民族国家概念形成后,基于民族形成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实体成为普遍现象。不论是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的形成,还是20世纪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独立,都是基于民族认同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关键。而文化认同的边界常常成为政治实体的边界,文化认同的内核是价值观认同。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文化认同愈发重要,在文化认同支撑国家认同的作用愈发显现的同时,出现了文化中心主义、文化封闭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现象。原本柔软的文化成为了刚性的“铁盒”,把自己与外界区别开来;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成为了“异文化”,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族群成为了被排斥的“他者”。
进入21世纪,当人类的技术能力愈发先进、物质水平愈发提升的同时,各种全球性挑战、国家间冲突依然让人类面临巨大挑战,贫困问题依然无法彻底根除,和平世界依然无法完全实现,地区冲突、种族矛盾此起彼伏。人类通过科技与工业增加了各自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没有全部用在共同的福祉上,而是许多被用在了彼此竞争乃至杀戮上。价值观的分化让“全球化”的世界愈发成为“半球化”“碎球化”的世界,而技术崇拜让机器更像人,并且人也更像机器,同时也让技术成为了政治与武器。
在这种时代问题下,需要重新反思当代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构建,而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的成功实践与先进理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时,要把这种关于人类新文明的先进理念——新人文主义,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为世界交往提供新的思想公共品。
二、新人文主义的内涵
(一)全人类意识是新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一
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③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的哲学基础,也是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不同的理论基点。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对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基于全人类视角的崭新理念,体现了鲜明的全人类意识。
当代世界人口超过80亿,尽管同属人类,但由于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区隔,让各个族群在认同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常常会忘记了不同的人类族群属于同一种生物,拥有同一个起源,都从东非大陆走出来。正因为忘记了人类的共同起源,缺乏了人类的整体意识,近代以来当人类不同族群相遇出现利益冲突时,往往没有同胞之情与共同愿景。
以全人类意识理解人类,理解的是人类的共同特征,即人类拥有共同的能力。人类具有意识,会使用工具和语言,尽管工具的先进性不同,语言的规则不同,但这些都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与生物。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人类意识不等于全人类意识。全人类意识的形成并非自然而然之事。人类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展既带来了人类意识中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性存在的认识,也产生了价值评判上的高低之分与情感评判上的敌友之分。
尽管人类有着共同起源与共同特征,但不同族群之间真正开始交往始于从15世纪欧洲航海家们开辟新航路,由此不同的大陆联系在一起,不同的人种彼此发现。遗憾的是,自从不同族群联系在一起,人类内部的差异性常常超过了一致性,等级性常常超过了整体性,彼此间只有形式上的共同存在,没有意识上的共同命运。由此才会有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与战争,直至当今世界依然纷争不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用1800年前中国诗人曹植的诗句来评价全人类意识下的人类之间的冲突,无疑是贴切的、令人深思的。
面对人类之间无穷的纷争,何以相处,相处为何,是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全人类意识体现了一种跨越民族国家利益和文化观念差异的思维方式,凸显了人类的整体性与不同文化间的共同性与共通性。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人们在一起都是同胞,与万物也都是同伴。这一境界无疑是美好的人类相处之道。全人类意识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结合了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解决世界问题提出的具有引领性的观念。
对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来说,将全人类意识作为一种总体性观念来指导传播实践,可以有效推动不同国家间、族群间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互相理解与彼此共情。对提升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实践探索来说,全人类意识不仅是理想主义的构想,更是具有战略意义、根本意义的创新观念。
(二)中华人文精神是新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二
托尔斯泰认为:“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是令人惊异的,老子的学说——执行自然法则——同样是令人惊异的。这是智慧,这是力量,这是生机。”④在21世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仅仅为了说明“中国如何好”,而更是要说明“中国好带来世界好”。后者相较前者,具有更开阔的世界眼光与全人类意识。事实上,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世界的意义,就要看到“这是智慧,这是力量,这是生机”。这种智慧与力量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中,焕发出更大的生机。
中华文化是具有高度伦理性的文化体系,充满人文精神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鲜明的精神标识,对于理解、传承与传播中华文脉至关重要。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⑤中华人文精神突出特征表现在“向内求”与“向外和”,即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与对外界的和谐追求的结合。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血脉,是其持续发展的精神主线。立足中华人文精神形成对中华文脉的自觉认知,成为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着力点。
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⑥以人为本的观念贯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影响了庙堂也影响了江湖,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影响了历史也影响了当代。应该说,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参与世界文明百花园建设的进程中,人文精神是最重要的对话基础。
(三)文化多样性是新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三
文化多样性对于理解当代文化发展、当代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可以进入文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深处找到各种问题症结所在;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实践理念,可以为文化发展与世界发展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对文化多样性问题给与了高度重视,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宣言》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同样,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也贯穿着鲜明的文化多样性精神。
文化发展的规律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形成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如果把文化比作花园,只有一种花朵的花园显然是单调的,也是不符合生物界自然规律的,好的自然生态也是需要生物多样性的。因而,文化多样性之于文化界的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之于生态圈的意义一样,都是为了获得内在的、持续的生命力。人类文化的繁荣不是因为某种单一文化的普及,而是源于多种文化各自的生命力及其相互影响。
对于世界发展来说,文化多样性是关乎文化的观念,也是关乎政治的观念,更是关乎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观念。经济是政治的身体,文化是政治的灵魂。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重大冲突的深层次根源就是价值观问题。只有当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时,世界的联系才会更加紧密,世界的对话才会更加通畅,世界的发展才会更加和谐。
三、以新人文主义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以新人文主义开展与世界的对话,在国际传播中凸显这一精神,对于处理国际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物质与精神、先富与共富等关系都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展示出当代中国具有共情力与感染力的国家形象,也能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追求,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共同机遇。构建融合中西人文传统的新人文主义,可以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世界学术界更好地交流对话。新闻传播学界在新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可以进一步探索信息传播与人文价值的融合之道,推动新闻传播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是以新人文主义展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对和平的追求是发自内心的,植根于文明深处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最具复杂性、宏观性和实践性的一个方面,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与一脉相承的直接体现,更是中华文明独树一帜与独特品质的内在原因。和平性充分体现了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历经几千年连续发展,因循时代特点和变迁而不断创新,终成全球与人类的共识和憧憬。”⑦因此,在推动新人文主义国际传播的进程中,要把和平性作为一个突出内容来体现。这是有着坚实的中华文明历史基础的,也是有着强烈的当代世界现实需求的。
二是以新人文主义展现当代世界的新发展观念。新人文主义既承认少数国家先富裕更追求所有国家共同富裕,既要有彼此竞争更追求合作发展,既提升智能化更追求人文化。没有人文精神的发展只是冷冰冰的物质堆积而不是暖洋洋的社会生态,没有人文内核的智能只是机器智能、资本智能而不是人类智能。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精神。
三是以新人文主义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追求。这种新人文主义既反对神权也反对霸权,既追求物质富足也追求精神富有,既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新人文主义具有理性、和平、包容的精神。理性精神是以科学方法为主要内核的,和平精神是以对话原则为主要内核的,包容精神是以文明多样性追求为主要内核的。新人文主义的实质是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以合作为方法、以自由为追求的新文明观念。建构与传播新人文主义,可以滋养人类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基于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的不同文明,共同推动建设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中,把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充分展示出来,将会极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与世界影响。
新人文主义既来自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也来自中华人文精神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也具有广泛的世界基础。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来说,新人文主义既体现了扎根传统的文化主体性,又体现了面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性。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中,从深层次上传播新人文主义的理念与精神,这是可以被世界所认可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在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传递中华文明关于人类共同发展的追求,无疑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意味着走出中世纪的人类内在性的自我意识觉醒,那么,新人文主义的认知与传播则成为当代人类整体性的自我意识的新启蒙,前者意味着走出“至上之神”的控制,后者意味着走出“自利之我”的束缚。人类对自身意识的认知范围需要不断扩大,从“小我”到“大我”,从“个体”到“整体”,从“民族国家”到“共同人类”,如此才能接近更真实的人类本质。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传播新人文主义是为了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整体性实质与碎片化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面对当代人类的复杂处境,基于新人文主义的塑造与国际传播,才有可能消弭误解,才能在以和平、合作与共赢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构建过程中达成人类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如果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广泛接受的人类行为的古典“黄金律”,那么,新人文主义应该是在全球化时代被广泛认知的人类行为的现代“黄金律”。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作出的新的贡献。
2024年11月,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获得了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这部影片以细致的考证工夫还原了二战时期运送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船“里斯本丸”沉没前后的真相,描述了中国渔民冒死营救落水盟军的事迹,整个片子没有直白的煽情,而是不断还原事实,展示了浓浓的人文情怀。在片子最终,许多年逾八旬的英国老人来到中国东海之上与各自70多年前离去的父亲告别,充满了敲击人心的人文力量。可以说,这部片子是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作品中充分展示中国创作者的全人类意识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佳作,体现了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这样的作品无疑会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2024年12月,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同时新增口岸并进一步扩大停留活动区域。目前中国已经对54个国家实施过境免签政策。这一看似很小的政策带来了极大的效果。2024年免签入境人次数以千万,推动了以中国为旅游目的地的国际人文交流,展现了中国开放性的姿态,为分化、纷争的世界注入了充满人文友善感的强大暖流,体现了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直接交往、外国游客在中国的亲身体验,可以最大限度破除媒介偏见、政治偏见,无疑会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化解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性,不能仅仅在“强”字上做文章,让机器更智能,让武器更强大,也会让资本更肆虐;人类更要在“和”字上下功夫,让情绪更平和,让技术更向善,让沟通更顺畅。新人文主义则是可以推动世界更和谐的共同观念。基于新人文主义开展国际传播与世界对话,既要传播中国之美,也要传播世界之美,既要让世界看到更加真实的中国,也要让中国看到开阔的世界。
在全球南方力量兴起的当代世界,作为全球南方中的坚定一员,新人文主义的国际传播可以更加依靠全球南方传播力量,更加注重以全球南方的视角来传播世界,形成传播中国的“世界矩阵”,形成传播世界的“南方矩阵”。这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份关于《2025年全球人道主义概览》发布的声明中谈到,这份报告“是对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失败的一次控诉”。创纪录数量的武装冲突正在造成巨大的痛苦和苦难,约有1.23亿人被迫流离失所——这是连续第12年增加,人道主义危机导致全球3.05亿人需要援助,气候危机每年都在使气温飙升到新纪录,导致全球范围内发生洪水、干旱、热浪和野火。在声明最后,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让我们把2025年变成减轻人类苦难的一年,治愈分歧,并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和平、更有希望的未来。” ⑧阅读这一报告是令人揪心的,想到世界上那么多的地区依然战火频仍、杀戮盛行、饥饿蔓延,这是令人不安的。究其原因,全人类意识还没有真正形成,人文精神还没有充分展现,文化多样性还没有认真贯彻,而武力崇拜、价值观划线、自我利益优先依然盛行。为此,建构与传播新人文主义,通过各种组织化、多样化的对话平台与协商机制,通过广泛的国际人文交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或许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扎实推进。
培养并传播新人文主义的意义是深远的,影响是无形的。在多样性的世界里,人们需要彼此了解,才能认识真实的世界,保持理性;在分化感的政治环境中,人们更需要彼此直接接触,才能超越政治偏见,保持团结。在布鲁塞尔机场,笔者曾看到一块标识牌,其上的话语恰好展现了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探索世界,重新探索彼此。(Discover the world. Rediscover each other.)”为了灿烂的世界新面貌,为了和谐的人类大家庭,中国学术界与传播界要弘扬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关注人类,关注人民,关注人文,以中国之诚团结世界之力,以中国之思启迪世界之智,为世界创造新文明,为未来探索新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战略研究”(23VRC006)的阶段性成果。
胡钰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注释」
①Syed Hasan Javed,China,West and the Islamic World,Karachi:Paramount Books(Pvt.) Ltd,2021,pp.264.
②[奥]斯蒂芬·茨威格:《随笔大师蒙田》(舒善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4-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④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5页。
⑤钱穆:《人生十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60页。
⑥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6页。
⑦中国历史研究院:《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270页。
⑧Secretary-General’s message to launch the 2025 Global Humanitarian Overview,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4-12-04/ secretary-generals-message-launch-the-2025-global-humanitarian-overview.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