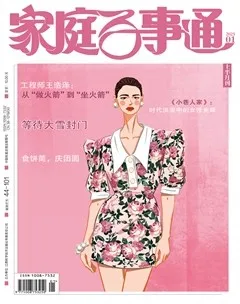一鱼一饭半瓢水

年关将近,忽忆起小时母亲做的煎刀鱼。那时候,家里穷得像水洗过一样,什么都没有。过年前半个月左右,母亲会用省下的玉米粒换半袋苹果和几条瘦骨嶙峋的刀鱼。我偶尔嘴馋,她会抛给我一个有点烂的苹果打打牙祭,可那几根刀鱼,她东掖西藏,不到大年三十下午,绝不会让我发现。她美其名曰:“眼不见,心不馋。”
大年三十下午,母亲的花棉袄上蹭着冰碴,她笑呵呵地捧着刀鱼出现在灶台前。我和大姐的魂儿仿佛都被勾走,心急火燎地围着灶台转,盼望母亲快点做,好让我们大快朵颐。
刀鱼被一层“水晶铠甲”包裹,需要缓慢地解冻。我化身侦察兵,一会用手按按,一会儿用鼻子闻闻,一会儿用木棍捅捅,随时跟母亲汇报冰融化的进度。母亲实在受不了我们馋虫泛滥的样子,没待刀鱼完全化开,就系上围裙,将鱼去头、开膛、清洗,收拾起来。
收拾刀鱼的时候,我们都躲远了。刀鱼味道极腥,特别是表面一层银色的薄膜,粘在手上,腥味仿佛能渗透到皮肤里。为了去腥,母亲会拿着剪刀在鱼身上刮两下,将鱼剪成小段后,洒上些许父亲不舍得喝的白酒。之后放上切好的大葱,放点酱油、盐,拌匀,腌渍一下。天下的母亲,或许都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一刻钟后,再凑近细闻,刀鱼全然没了腥味,只剩下青葱和酱油混合的淡香。
母亲喊:“烧火。”我飞似的奔过来,把豆秆塞到灶膛里,听一阵阵噼啪作响。母亲斟酌好豆油的量,倒入锅底,然后将一段段腌渍好的刀鱼用筷子“排兵布阵”。她告诉我们,刀鱼肉质松软,煎时不可随意翻动。要等到一面金黄,肉质紧致的时候,才可以换到另一面,否则刀鱼会变得七零八落不成形。说这话时,母亲郑重得如同布置一道人生命题,而我们哪有那么挑剔,只盼望刀鱼早点上桌。
开饭了。我和大姐互相看一眼,一人夹起一块刀鱼,咬了咬外表金黄的鱼段,咂摸一小口,又同时皱了皱眉头。刀鱼本身的肉香,混着葱、油的香味,外加一股咸味,巧妙而强烈地刺激着喉咙。软软的肉质在嘴里久久回味,要混合充足的口水才能中和盐分,然后下咽。虽然我们都快馋死了,但刀鱼实在太咸,想多吃一些,又不自觉地有所节制。
一盘煎刀鱼,我们四个人只吃了一小半,母亲说不爱吃鱼,父亲说刀鱼的骨头好吃。收拾桌子的时候,我感觉意犹未尽,快速跑到水缸旁边喝了半瓢凉水,然后又抓起一块刀鱼,摘去边上的细刺,放到嘴里,没让人看见。
长大后,有次跟母亲闲聊,问起小时候的煎刀鱼为什么口味那么重。母亲先是沉默,继而叹息:“我也不想做那么咸啊,没办法。菜少只能多放盐。”母亲说完,我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我将眼光射向别处,让眼角的轻雾散开。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饮食哪有那么讲究,吃饱穿暖,已是理想。父母苦自己也不会苦了孩子。母亲并非不爱吃鱼,鱼骨头也没父亲说的那么美味,他们无非是想让我们多吃几顿,让新年的余味,能慢慢地延续下去。
如今,我家的餐桌上饮食丰富多样,时常做煎刀鱼,咸淡适中,管够。可是吃起来,只觉是平常食物,那种满足感和奢侈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怀念小时候,吃母亲做的煎刀鱼,一块鱼一碗饭半瓢水,一家人清贫的小幸福。
编辑|龙轲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