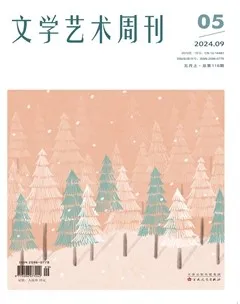“无穷的远方”与心的归途
1935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二集》导言中,以“散文批评家”的身份直言他对于散文这一文体的认识。在他看来,散文写作尤为重要的是“散文的心”,其后才是“散文的体”。郁达夫所说的“散文的心”生发于五四运动中对于“个人”的倡导,进而他" 指出:“个人终不能遗世而独立,不能餐露以" 养生,人与社会,原有连带的关系,人与人类,也有休戚的因依的……”时光荏苒,反观薛青峰的散文集《无穷的远方》,依旧可以从其“散文的心”以及“散文的体”去切入这位终身朴实的散文歌者,去体味散文的“实性”与“诗性”。
一、心之“透视”——在记忆的边界漫游
当面对尼古拉 ·哈特曼那句经典的质问:“为了在世界的充分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我们将把我们自己塑造成什么?”我们更多的是要直面社会,完成当下时代的质询。在薛青峰的散文世界中,他选择通过行走与写作不断打开自我并最终完成了“自我指认”。这一彻底敞开自我的方式首先落实为其散文对记忆地理学的构造。在其散文中遍布着主动或被动的记忆,它们在地理的边疆和精神的旷野之间不断闪回,裹挟着作者对于生命的感知和超越。在其散文 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记忆的宫殿是以自然为边界,依偎着与老人生命共续的杏林、记叙着牧羊人生命幸福的石屋、勾画出怀念的苹果树……作者将对于生命的思考融于自然流淌的时光岁月中,任其肆意生长。不过,作家的笔锋并未放任自我去无目的地游荡在记忆的边界,取而代之的是极尽展现作家的创作主体性,以文观其“文心”。
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就将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性。所谓精 神主体性“是指作家内在精神世界的能动性也就是作家实践主体获得实现的内在机制”,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发挥主体价值,充分发挥作家主观能动作用,以人的方式去思考和认识客观世界。并且刘再复还特别强调精神方面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是作家主体性的最高层次。因为精神属于内宇宙、内自然的范畴,它具有追求自由和反抗束缚的特征。一个散文作家如果他意识到精神主体性并为实现这种主体性而努力那么他的创造就有可能“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使内宇宙与外宇宙相通从而使散文产生质的飞跃。
在《无穷的远方》中,不乏关于作者精神主体性的篇目,例如《寻找墓地的天鹅》一文,作者于山水间偶见孤独的天鹅在薄暮时分低回,进而由天鹅这“没有辉煌追念”的临终孤独,联想到被囚禁在公园内的天鹅,进而对高贵做了新解。这是作者对于自然生命的崇敬精神,更是由物及人的生命的反思;还如《学生给我一张字条》中,面对学生关于文化、写作所提的四个问题,作者给予了生动的回应,这既是日常工作真实的记述,更是作者内心作为师者耕耘的点滴;再如在《摘酸枣》一文中,从假期摘酸枣的故事说开去,进而由酸枣之刺联想到人之“心刺”,并直接将人性中的“合理正直”与“无理邪恶”的面纱扯开,文笔间悦动着作者对人性的审视精神;最后在《从“天地书屋”到〈移动的故乡〉》 一文中,作者在轻描淡写“天地书屋”岁月的同时,借微信朋友圈售卖《移动的故乡》为由头,追根溯源地回到对于文学的敬畏精神上。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文学书写都是作者在记忆的边界擘画“文心”的体现。
当然除却这些在内容上体现出的“文心”的真实性,“文心”蕴藏的情感真实性也是《无穷的远方》值得称道的地方。楼肇明先生在《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一书中认为,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不独散文所专美。同时,真情实感有多个层次,人与人的真情不尽相同。虽然这句话指出了真情实感并非散文独属,但在《无穷的远方》中随处可寻真的“原生美”,而这种“原生美”增强了作者的笔力,其一则是在作家笔下尽显“真味”。《草木礼赞》一辑中的自然之味,《课堂内外》一辑中的工作恬淡,《人生经年》一辑中的杂陈交叠,《书行时光》一辑中的“智性”沉思,《八月日记》一辑中的向生之境以及《腊尽春 来》一辑中的意趣的绝笔,都是作者对于人间的真实体味。再者,《无穷的远方》是一部渗透“真思”的真作。在《沙尘暴的日记》中,作者对于人类生存环境进行深入探究,体现作者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在《山水朋友》一文中,由一次旅行中与陌生旅人的相遇,进而上升到对无扰自然亦是无扰他人的关怀之反思;在《消逝的后街》一文中,对石嘴山街道变迁背后的故事进行描摹,可以说其思见于作者对于所处环境的“心之透视”,却又明了于行走的途中。最后是阅览“真情”。在《思念的土地》中,作者将动人至深的笔触伸向养育祖辈的大地,直抒对于土地的留恋之情;《初恋咖啡屋》一文,记录了作者在少年时期对于爱情的青涩遐想;《红雪花》中,由青年情侣在冬日谈书意趣,情之深醉倚怀相视的情境描写,联想到自身与妻之数年相扶的真挚亲情,都浸润着作者对于人间真情的感悟感知。可以说,作者的“文心”是在其记忆的地理中最终实现对于“真”的文学哲理体味。
二、文之“孕化”——在“诗性”铺陈中盈落
散文是一种最自由自在、最不受约束规范的文学品种,倾向于心灵的艺术。《无穷的远方》中,文学空间既是作品呈现的远方,也是作者理想的文学的诗意的远方,使其作品呈现出一种朴实的诗性美,进而在作者之“我”与“诗”的询唤间构成深层的文之“孕化”,建构了作者个体经验外化于世的另一重维度。
中国的文人写诗作文都讲究诗言志、诗缘情,用心去感受、去统摄天地万物,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把握散文中的诗性,自然就需要借助于感悟,通过对生命的感悟来品味散文中的诗性,或者将感悟与分析结合起来,既追求审美上的鲜活灵动、生气灌注,又讲究学理上的通脱透彻。因此,在《无穷的远方》中,其诗性体现首先应当得益于散文对于生活场景的诗意本真的还原。“大小不一、线条分明、圆扁可观、长短无绳、宽窄有序、薄厚可触的石头组成了石屋古朴浑然的结构。”(《石屋》)关于石屋与人之间生命的故事,也就在这样朴实无华的审美诗意中展开,作者并没有赋予石屋太多的变形以及夸张,使得石屋发生的故事具有了更强的真实感。对空巷、陶瓷巷、后街的描述亦有着紧贴岁月又超越岁月的场景还原的延伸。例如夜深的空巷,袅袅炊烟的绝唱不禁勾起归人的遐想;废墟留下余音,却诉说不完对岁月的衷肠;窑洞随着时间的变迁生发了文明,最终却成了一个时代文明的标志。在作者笔下,他从不愿意让他生活的环境有丝毫“破碎”到在还原本真的基础上去渗透作者的思考,这便是散文家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者的写作记忆是本真的,因此他的关注点也不仅仅在于其生活的哲理空间的描摹,场景还原的诗意还借助于对身边真人的记叙中。在其散文集中,对于朋友、亲人尤其是学生的真实的“工笔写意”历历在目,看似作者在描述与主人公之间的故事,落笔于朴实的人物描述上,恰恰在这人际交接的缝隙场景中体现出一种真实情谊的还原,进而使得本真还原的环境有了“人味”。
其次“诗性”盈落凝聚在作品呈现的“智性”审美上。所谓“智性”强调的是作品语言透射出的哲理意味,这种哲理像诗歌透出的诗意美在绵延的韵味笔意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着眼于《无穷的远方》, “智性”的展开首先借助于文本蕴含的知识容量。在《桃之夭与吊儿郎当》中,由介绍“桃之夭”的命名缘由,进而延展到对于中国酒文化的梳理中,在文化中观照现实,从祝酒诗词进而到作者日常生活中喝酒引发的爱妻的情绪,浅淡隐藏着知识的线条;又如《“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一文中,作者夜读《陶渊明集》对陶渊明隐逸于世精神的赞许可见一斑;而这种精神的仰望也是基于对于知识的深思细悟中。其次,“智性”印落在作品内蕴的哲思的语言中。“我们一生都在寻找生活的监护人。”(《带着记忆下课:岁末备忘录》)“如果说快乐让身心得到短暂的刺激,疼痛则是沉淀以后的快乐。在疼痛中承担风险是生活的全部意义,而疼痛总是悄悄走开,隐藏起来,吞噬着时间的胶囊,让笑脸绽放。”(《身体里的黑客》) “这个时空给予我的,是人生这纸页上将要书写的追求都是乌托邦的奢侈品,我想得到的是平安和健康这两件人生基本的必需品。”(《命运这东西》)在《无穷的远方》中,作者用直截了当的饱含哲理的语句赋予作品智性美,让诗意萦绕在哲理间。最后,“智性”的诗意理应涤荡在哲理化的散文建构中。作品试图通过散文的诉说去探寻人生乃至世界运转的哲思。如对于一棵树的怀念比任何事情的怀念都会使老人动情,树的消逝像是老人与离别的次次挥手(《杏林》);苹果树的死去亦是对大地的悼念,人们因为过分的索取而忽略了表达逝去的关心,而哀悼这一生命的消逝——雨露、泥土、阳光、冰雪早已送去了对于苹果树的礼赞(《逝去的苹果树》);生活也可以在苦苦菜弥留的岁月中变得别有滋味(《苦苦菜道情》);由朋友圈里无朋友说开去进而到有了说真话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孤独,在困难时就不会无助地阐发(《朋友无价》);橱窗背后浸 润的享乐主义、快乐主义,隐藏着人性精神的荒原(《橱窗》)。
《无穷的远方》透射出的诗性不是单纯地紧贴作者感悟表层的韵律,它更多的是在作 者自然与外在环境融合的前提下凌驾于自身体验,呈现出的袅袅余音。这种诗意不仅美在文之皮相,更刻在文之骨相。
三、形之“询唤”——在守与寻之间游弋
作为一名散文园地的耕耘者,守其散文之心是作者坚守生活本真的文脉,作者也没有故步自封,反而带着创作的“无意识”,游走在无穷的远方。陈继明在谈《无穷的远方》时指出,他曾建议作者尝试写小说,但作者说他不能做小说,更无法用另外一种笔调写散文。其实细读《无穷的远方》不难发现,虽然作者没有明示,但是个别篇目的落笔处依旧可窥见小说的掠影。《桃花劫》中老师凝望逝去的桃林时的无法言说,恰恰近似于小说人物无奈的人生低语;《身体里的黑客》以“身体突然黑屏了”为引子,颇有科幻小说创作的可能性;《给小偷的“压缩钱”》一文中,也能感受到冥冥之中小说人物在特定的年代展开的人物故事以及关系的钩沉。因此,其中暗含的是一位散文家在坚守散文创作的同时对于文体创作多元化进行探寻的表象,我们不能理解为他只是单纯的“散文作家”,恰恰是其无意识的问题探寻更使得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多元作家。
薛青峰的散文创作形式也呈现出多元面向的趋势。除了前文提及的“智性”特征以外,拟人化手法的使用也是作者在面对自然万物呈现出悲悯情怀的依托。作者曾说:“我也需要物质享受、适当消费、轻松娱乐,但我更注重享受快乐生命过程中成熟心志的完善,我还注重历史逻辑,我也注重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没有必要经历老一辈人的苦难,但必须有一颗感受民族苦难、个人灾难的悲悯之心,没有这颗悲悯之心,过往的事情还会再来。”在他的笔下,悲悯赋予万事万物以生命感,尤其在《草木礼赞》一辑中,记忆中的自然草木俨然生动了起来,春草能听到人的足音,杏花能开出老 人的记忆;石屋随意地躺在地上,游荡着牧羊人经历过的岁月兼程;羊圈柔顺地等着归途的羊群,庆祝这对于当下生命的赞叹;桃林躺进 了难以言说的无言可说;纯朴的苹果树裹挟着自然的声音与人们并进。这只能是一位满怀悲悯情怀的作家才能写出的世界,情感就在这种平等中蔓延。
除此之外,在作品中文本“对话”的设计,联想手法的使用都能略见。可以说人、事、物浮光掠影,都成为点燃作者心绪的一颗火种。通览文本,可见《无穷的远方》既有着作者人到中年行走在俗世对于自身的祈愿,更有着作者在文学世界对于其所蔓延的文质的诗意尽头的追寻,这不仅是作者本人的旅程,更是作品对文本自我价值的边界的拷问,回荡着作者心的归途的余音……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以来黄河流域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BZW160。
[作者简介]刘潇靖,女,汉族,宁夏石嘴山人,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