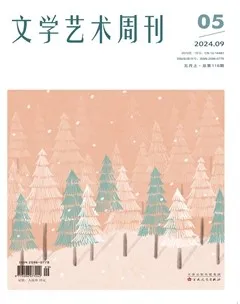元戏剧理论观照下皮兰德娄作品中的幻觉与真实
戏剧随着时代而变化,现代戏剧对西方思想中的传统美学也进行了重新定义。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视角被定义为碎片化的、幻觉的,它提供了一种洞察人类心灵真相的能力。元戏剧就是一种审视幻觉与现实的艺术方式,元戏剧中的现实是我们通过自身的经验所理解的不合逻辑的世界。本文以皮兰德娄的作品《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为例,通过对超越观众的表演或舞台剧本形式的反映,展示元戏剧是如何强化舞台作用的;同时通过探索戏中戏的元戏剧手法,阐释幻觉与现实的融合,进一步分析观众是如何通过感受幻觉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来体验元戏剧的。
一、元戏剧和戏中戏
元戏剧提供了一种观察思维幻觉的方式,使人们了解到自身所经历的现实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人们对世界的反应是基于自身感知的,而这种感知基于自身已有的经验。如果在戏剧表演中人们把虚构的角色看作是真实的,这样人们就能看到自我意识的现实,看到实际存在的现实以及感知世界的方式,从而看到我们头脑所制造出的幻觉。元戏剧可以揭示现实生活中被遮蔽的任何方面,任何一场揭示戏剧技巧的表演都会在脑海中唤起对现实的幻觉,这会对人们的感知产生影响。元戏剧将幻觉与现实结合在一起,通过打破幻觉与现实边界的戏中戏的手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纯粹的自我意识。
戏中戏通常被剧作家用来揭示戏剧的运作方式及其本质。它以多种形式出现,要么是伪装在戏剧本身的简单表演中,要么是用一个角色伪装成另一个角色,要么是一个角色假装疯了,要么是戏剧与现实的复杂融合等。所有这 些戏剧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矛盾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剧作家自觉写作过程和演员表演本身的自我反思。戏中戏是一种生活形式,通过让观众参与戏剧,教育他们在舞台上辨别幻觉与现实。
二、《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中的幻与实
皮兰德娄是著名的意大利剧作家,曾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十分擅长使用戏中戏的技巧。对他而言那不仅仅是有效的戏剧手段,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戏剧的整体性质和未来发展的观点。其代表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被誉为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戏中戏。在剧中,父亲把儿子送到乡下的奶妈那里后,就离开了母亲。母亲爱上了一个为父亲工作的男人,母亲和这个新情人又生了三个孩子——继女、男孩和女孩。这个家庭始终生活在贫困中,母亲在佩斯夫人开的一家商店里做裁缝,继女成为佩斯夫人经营的妓院的妓女。不幸的是,一天父亲来到佩斯夫人的商店,要继女为他服务。在父亲发现妻子的绝望处境后,他让她和家人回到他的房子和他一起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快乐,儿子恨他们所有人,因为他已经和他们分开很多年了;继女和父亲的关系一团糟,她最终逃跑了;最小的两个孩子都不幸死在家里,女孩淹死在男孩面前,男孩随后用左轮手枪自杀。
这部戏首演于1921年的罗马,首演当天直接导致了罗马街头的战斗,它激怒了罗马的观众,以至于演员们几乎被轰下台,观众们大喊着“manicomio”(意大利语,意为“疯子”),皮兰德娄也勉强从剧院脱身。当时罗马观众如此评价该剧:“毫无形式可言,缺乏连续的情节,完全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模式和结构。”
在传统意义上,观众不得不接受舞台实际上不是舞台的伪装(比如布景、道具),而皮兰德娄打破了这种惯例,让观众真实体验到了没有演员的现实。他试图让观众接受舞台只是一块木板,演员在上面既是演员也不是演员的真相。他用这种形式向观众提问:“幻想如何结束,现实从哪里开始?”在《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中,剧院的演员和导演在一个空舞台上准备排练,六个剧中人进入剧院,以真人的身份接近导演和演员。这正是皮兰德娄对幻 觉与现实概念的一种反映。幻觉与现实的对比是该剧突出的表现手法。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区 别在戏剧的一开始就确立了。皮兰德娄让观众沉浸在他所创作出的幻和实中,角色试图向导演和演员解释自己,展示他们的故事,试图说服他们把它改编成戏剧。戏剧的创作就是为了混淆舞台幻觉和现实生活的区别,本质上就是让戏中戏看起来更真实,作者利用呈现矛盾的语言来揭示幻觉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从而使戏剧更加真实。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中的演员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物,作者试图让观众相信这些角色都是在模仿真人。他要唤起观众去分辨谁" 更真实——角色还是演员。在戏剧中,作者有意模糊了现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为读者和观众创造了不同的感知。即使被认为是真实的,实际上也可能是幻觉,真实总是在舞台上缺席。在剧中为了让佩斯夫人出现在舞台上,父亲使" 用演员的帽子和衣服来布置舞台场景,把舞台作为佩斯夫人的车间。当佩斯夫人出现在舞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骗局。父亲声称这是真实的情况,演员是无法扮演的,因为演员是真实的,想通过" 化妆来表现真实,但作为剧中的角色,不需要伪装,这才是真正的真实。演员们把舞台上佩" 斯夫人的存在看作纯粹的幻觉,而角色们则将其看作纯粹的现实。女儿一看到佩斯夫人,就" 以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身份去看她,而舞台上的演员则视她为父亲的把戏。佩斯夫人的身份" 飘浮在现实或幻觉之间,舞台上的每个人对佩" 斯夫人的外貌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他们的观察都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对现实的不同看法。虚构的人物活了过来,试图拆除现实的幻觉,以支持现实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支持幻觉本身,这是他们唯一的现实。该剧中的戏中戏都是间断的、不完整的、碎片化的,但从所呈现的内容上看,观众能够" 辨别出角色故事的关键事实。人物对彼此的看法因他们所处的环境而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徘徊在舞台上,极力表现真实生活的虚假的一面。角色在演员的现实之上主张他们的现实,因为自我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发展出新的经验。因此,艺术远比生活更真实,因为它不像生活那样容易变化。
皮兰德娄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取决于一个人的处境;真实事物的幻觉意义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他相信真相存在于角色身上,而不是存在于导演或身份不断变化的演员身上。导演对自己的看法与他在过去的另一段时间所看到的不一样。在作者看来:真理的荒谬本质就是它在毫无意义的地方寻找意义。作品中演员的现实、剧作家的现实、角色的现实和观众的现实,都被看作是对现代主义世界的一种表达,一切都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揭示了剧中人虚构的叙事深刻性,他们渴望与世界交流,成为真正的人物,而不是作者心中的想法。该剧贯穿着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人类交流的困难。这个家庭的真正悲剧不是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的悲剧故事,而是他们无法与他人分享他们的痛苦。
无论《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是一部闹剧还是一部情节剧,它都能吸引无数的观众,尽管演出期间被无数次干扰和打断。很明显,这出戏将以悲剧收场,但结局是如何实现的,却是个问题。角色之间就叙事事件的确切性展开争论,同时又与经理争论如何用理想的方式来呈现它们,继而在谈判的过程中,所有的叙述又被一次次反悔,等等。这种叙述所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同步性,而这恰恰是作者打破幻觉与现实之间界限的一种手段。在该剧的最后,皮兰德娄再次利用排练的同时性,即多重身份对单一艺术自我的共存和斗争,来展示现实与幻觉之间的差异。在经理的坚持下,角色生活中的悲剧事件由角色自己在光秃秃的舞台上表演,剧院坚持认为这些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虚构的角色,这些角色存在于某种边缘空间,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构的,而是简单的,是不受时间和空间法则约束的。对于皮兰德娄来说,“现实一旦被感知、过滤和解释,就会变 成一种幻觉”。
三、结语
戏中戏的本质就是唤起现实主义的假设,只要虚构的世界代表了现实世界,它就有价值。虽然虚构世界的边界确实可以超越现实世界中的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皮兰德娄在《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这部复杂的戏中戏中,关于真实和幻觉所引起的混乱和困惑为观众带来了特别的感受,作者利用戏中戏的方法唤起了舞台上的一种秩序感,通过将虚构的真相定位于现实,来限制这些边界。他的戏剧并没有试图说服观众,它不是一个戏剧,戏剧不需要遵循任何惯例或规则。很明显,在皮兰德娄看来,客观现实实际上是不可接近的,它是主观思维制造的幻觉。现实的这种矛盾本质是存在的,但只能被体验,却不能具体地描摹。
皮兰德娄想通过一场同时兼具现实和荒诞 的表演,挑战剧场内外观众对现实和幻觉的看法。通过该剧,皮兰德娄试验了人们所感知的现实和戏剧营造的幻觉之间的联系,很显然现 实就是一种幻觉。戏剧文本不再是构建另一种现实的场所,真实与幻觉界限的模糊是皮兰德娄强调外部现实的终极文本策略。
基金项目:2021 年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基于英语赛事的线上学习资源建设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21JG004Z。
[作者简介]杨丽敏,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副教授,本科,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