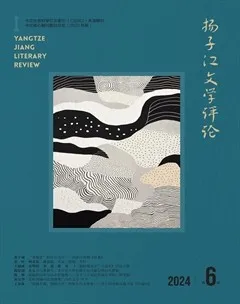时间与作品
一、时间里的乔叶
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和乔叶做了“鲁三”同学。所谓“鲁三”,即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那时的鲁院还驻扎在八里庄,校园比较“瘦小”,50个房间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作家。这些作家握有手艺,气神充足,行走在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其中有两位同学貌似与小说无关,一位是刘亮程,已出版《一个人的村庄》,散文家的名头自然响亮。另一位是乔叶,发表过不少轻盈的散文,年龄又小,似乎已是散文界的醒目新秀。不过既是新秀,就不能过于老练、过于昂首,于是,在同学们眼里,乔叶比较内敛、比较自谦,笑起来还喜欢低头,有些腼腆的样子。又过了不久,同学们才知道,这乔叶并不浅嫩,因为她竟然自生主张,把创作的主攻方向从散文转为了小说。对写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战略转移,相当重要、相当有挑战性。所以在一段日子里,乔叶进入了求艺练功的状态。她先是降下身段,逮了机会就缠住同学聊小说,像是虚心请教,其实是探秘他人技艺,对自己的写作想法进行验证;随后又暗自用力,尝试着构思小说,尝试着把脑子里的故事放到电脑上。
那时候我比较懒散,把一个已进行一半的中篇小说写完,便自我批准放闲,平日里除了听听课、翻翻书,就是坐在小房间里发发呆。有时发呆久了觉得心虚,就慢着脚步上到五楼电脑室,坐在椅子上做用功状,实则是浏览网页打发时间。周边的同学一般不会太多,其中经常有乔叶的身影。她噼噼啪啪地打字,很投入的样子。待打字打够了,她会起身主动凑过来,就小说行进中的若干问题发起提问。既是小说探讨,且是与女同学的小说探讨,就不能不认真一些,所以我的说话是严肃的,大约也是干巴的。许多年后,乔叶回忆起这个情景,调皮地写道:“我那时候刚开始学写中短篇小说,特别喜欢兴致勃勃地和人讨论分析小说问题,很多同学都受过我的折磨,钟求是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从不嘲笑和敷衍我的幼稚懵懂,总是非常认真的给我解答,诚挚恳切,字斟句酌……想要逗逗他,于是就故意挑一些古怪刁钻的问题和他理论,他回答吃力起来,不免有些磕磕巴巴,红头涨脸……”a呵呵,自己的红头涨脸我已记不得,但我能记得乔叶使劲眨着眼睛,一副勇猛又怯羞的模样。勇猛表现为不惧任何文学议题,怯羞则是一种小说新人的姿态。
总的来说,乔叶那会儿是低调的、安静的。鲁院一学期,我们奋力吃遍了八里庄附近的大小餐馆,聚会时多为男同学,有时也有女同学加入。许多日子下来,我从未见过乔叶在酒桌上高谈阔论或者举杯豪饮。后来我们两次外出采风,去了江西井冈山和内蒙古锡林郭勒,途中也没见到乔叶制造出热闹话题或者笑点行为。但在沉静之时,乔叶心里并不安定,似乎做着发力前的准备。这种发力当然指向的是小说。
鲁院学习结束后,同学们散去全国各地。不过我有一个判断,这种半年培训对同学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培训后似乎形成了两种创作心理:一类作家本以为自己在省里挺牛的,到北京开了眼,原来文学天地如此之大,心理上受到挤压就退缩了;另一类作家则觉得文学天地既然这么大,那我何不提起神儿闯一闯。乔叶无疑属于后者。她迈出鲁院之后,三五年内产出不少中短篇小说,并大摇大摆登上各种重要文学杂志,其中最亮眼的是《最慢的是活着》。《最慢的是活着》先取郁达夫小说奖,后收鲁迅文学奖,据说连获七奖,可称为“奖霸”。在此期间,我与乔叶一直保持着联络,互通一些简短消息。之后我主持《江南》杂志,便时不时向乔叶约稿,她到底抵挡不住,给了一个小说作品。《江南》举办文学活动,她也会应邀而来,坐在江南文学会馆的大树下,一边饮茶一边聊文学。又有一次,一个杂志社让我找个作家写人物印象记,还怂恿说女作家忆事比较细腻,于是我就找了乔叶。乔叶没有推辞,写了《求是实事》一文。再之后,我们时不时也会在一些文学采风和研讨活动上遇到。细想一下,这么些年我与乔叶的各种交集还是不少的。把这些记忆从时间里捡起来,我看到了她的变化和不变。不变的是她依然实在质朴,总归没有跌进世俗里。变化的是她的写作如树,还在不断生长。
时间来到了2023年。这年8月,乔叶凭长篇小说《宝水》摘取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鲁三”班刘亮程的《本巴》。到了深秋时节,颁奖典礼在浙江乌镇举行,那天我也去了。当时礼堂里灯光辉煌,气氛饱满,各种感谢和感悟的话在舞台上发表。乔叶是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女性,自然备受关注。典礼结束后,几位获奖者留在了浙江,被各种活动拉来拽去。直到几天后的晚上,我才有机会把乔叶和刘亮程唤到餐桌上宵夜。吃喝的同时,大家的嘴巴往当下文学里说了说,又往以前日子里走了走,碰撞出不少笑声。随后我把三人合影发到“鲁三”微信群,引来了点赞和感叹。同学们也许会想,这两位当年的散文写作者,现在却抵达了小说大奖,这挺有趣的。
是呀,时间可以制造奇妙。譬如乔叶,穿过近二十年的时光隧道,从小说初学者生长成小说杰出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时光隧道的前头,有一束生命的亮光在招引吗?
二、作品里的乔叶
谁都知道,文学作品里总是藏着写作者的身影与心迹。探知一个作家,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访问其作品。
我忍不住要先说一说《最慢的是活着》,因为这部中篇小说里的奶奶非常打动人。一个普通的老人,过着普通的日子,却接二连三遇到不普通的生活事件,终在穿过许多悲欣之后,生发出不普通的人性光芒。在我看来,该小说能够如此出色,是因为乔叶在叙事中“打通”了自己。
首先是散文与小说的打通。乔叶以散文出道,擅长纪实思维和实景手法,此次无意中把散文之气带进来,便有了文字的真切感。有的作家是将非虚构作品小说化,她的这次创作行动是将小说非虚构化。其次是奶奶与“我”的打通。乔叶从小就是被奶奶带大的,有过青春期的抵抗,有过困难中的互相取暖。对老人的深情怀念,是这个小说生长的重要根据。由此出发,她搀扶着奶奶走进小说,让生活中的奶奶成为文学中的奶奶。更重要的是,在奶奶的故事中,乔叶一直在成长,两个不同年龄的女人在生命行程中进行着心灵对话。再次是小时候乡村经验与眼下生活思考的打通。乔叶的父母不是种地农人,但其家庭没离开过村子,所以她的少儿岁月是在豫北村庄里度过的。从当时的照片上看,乔叶身上有着乡村姑娘的纯朴和“土气”。为了丢开这种思想上和身形上的“土气”,乔叶努力了许多个年头。可在生活中走走转转,她才发现乡村的经历是如此的重要,几乎成了生命的根。而所谓“土气”,即是地气,这地气正是她小说中所需要的。到了此时,她跟过去的自己和解了,等于打通了自己的过往和现时。
这几种打通带来作品的成功,让乔叶很受用,也很受鼓舞。对一个已有心得的作家来说,这个中篇还只是小试,接下来更应该做一份大餐。一些年后,这份丰富优质的大餐做成了,名号就叫《宝水》。在《宝水》里,上述“打通”所产生的力道仍在延展,青萍以“我”之名非虚构式地进入,九奶身上聚集着奶奶的不少气息,而小时乡村经验在作品中则有着基奠作用。当然,这部作品有着一个更重要的打通,即村庄的“小”和时代的“大”之间的打通。在这方面,评论家和读者们自然会给出许多点评。
而作为一个写作者兼同学,我在《宝水》里还看到了什么呢?
乔叶终于让故乡拥抱了自己。在给《宝水》备课期间,她下了苦功使劲“跑村”,逮着机会就去看全国各地的乡村,包括浙江嘉兴、温州、安吉的村子。同时又在河南南部的村子泡着,泡了很长时间。之后又回过味儿来,将注意力投放到小时候生活过的豫北村子里,于是以前的乡村记忆就被重新激活,蓬蓬勃勃生长起来。占有这么一大堆积累的材料和记忆后,乔叶显示了出色的调度能力,她把各种素材撒布到各个故事环节上。她的手里可能有一些材料还剩着,但好的材料可能都已用到了小说的有效部位。我觉得,乔叶能够做到这样,正是因为自己打造的村子和故乡的村子是同质的,有着很相似的内里,所以心里到底是不慌的,是有根有据的。可以这么说,一个作家要是愿意依偎故乡,故乡一定也会拥抱她。
乔叶在技术处理上没有掉链子。在《宝水》里,四个季节时段的结构相当扎实。在此框架中,几十位小人物演出着鲜活有趣的生活故事。贯穿在这些故事之中的,是一种稳定的讲述腔调。这腔调以普通话为底子,掺入河南方言,产生了有味道的地方语感。我在看《宝水》时,不知怎么还看出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的味道,似有一种地域特色和古典小说交杂的细腻感。在情节设计方面,小说做得相当丰富而且贴切,并拒绝一般化。仅举一例,在青萍与老原情投意合地度过首夜时,小说中有一处大胆的闲笔描写,让场景变得有趣而生动。闲笔并不闲哟。
乔叶遇到了属于自己的运气。《宝水》写的是小村庄,小村庄里活动着的是小人物。但大小打通,从小见大,这个“小”里自然呈现出“大”的气势背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这样的时代需要在乡村生活中展开。乔叶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时可能还没想到这一点,经过几年的往前行进,刚好与这个时代的某个点相遇了。这种相遇是偶然也是必然,可说是属于乔叶的命缘。另外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故乡的距离。乔叶离开老家先去县城,后去郑州,前些年又到了北京生活,《宝水》就是在北京创作完成的。不用说,故乡是需要距离的。站在北京打量故乡,目光远了,却更精确了,也更丰富了。这也是此部作品的生命机遇。
在微信聊天时,我一直称乔叶为乔妹。这样的称呼让她无论到了何种年龄,都会显得年轻。年轻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可能性。我期待乔妹向更远的文学之地走去。
【注释】
a乔叶:《印象|钟求是:求是实事》,“收获”微信公众号,2014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