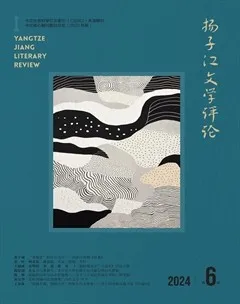“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恢宏历史想象
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如同邱华栋这样阅读视野极其广阔的、身兼理论家素质的作家并不多见。这一点,自有其出版不久的《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为突出例证。该书选择对象的时间起讫点分别是1922年和2022年,前后跨度整整一百年时间。全书共由三大板块组成,第一卷是欧洲作家的作品,第二卷是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作家的作品,第三卷是亚洲、非洲作家的作品。依据一般的阅读常识,虽然整部著作的入选作品是一百部,但作家实际的阅读篇目却绝对会大于这个数字。既有可能是二百部,还有可能是三百部或者更多。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对思想艺术品质的判断与选择。正因为在阅读之前任是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所选择的一定是小说佳作,所以他才必须在远远多于一百部的更大范围内作出相对精准到位的理解与判断。关键处在于,邱华栋不仅极其广泛地阅读了这些现代小说佳作,而且他还以理论家的敏锐见识写下了洋洋洒洒的阅读笔记。诚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里所强调的那样,“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一个作家,只有在大量地阅读世界范围内众多同行的优秀作品之后,方才能够拥有一种开阔而高远的文学眼光。虽然说如此广阔的阅读视野的存在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作家创作出优秀的小说作品,但如果缺少了对同行优秀作品的必要了解,如同井底之蛙一般地在一种短视的盲目状态下进行创作,要想写出富有原创性的小说作品,其实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我的理解中,这么多年来,邱华栋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数量很是可观的优秀作品,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具备那与广阔阅读视野紧密相关的高明文学见识。
然而,具体到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译林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则更需要作家下足广阔阅读视野之外的其他一些功夫。比如,踏踏实实地以脚丈量的“行万里路”。依照邱华栋在小说后记《盛代元音》中的说法,这或许与他出生于新疆天山脚下的一座小城有关,年少的时候,他就曾经造访过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那时还很年少,我去了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当地朋友说这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a此后的人生中,邱华栋又陆续造访了新疆的其他很多地方:“高昌故城、交河古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尼雅精绝国遗址、于阗约特干古城、米兰遗址、楼兰废墟等等。昆仑山以南、天山南北、祁连山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b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类似于《空城纪》这样的丰厚之作,之所以只能诞生于邱华栋而不是其他作家之手,或许与邱华栋那得天独厚的新疆人身份紧密相关。其他且不说,单就作家在后记中所罗列出的这些古城、遗址和废墟,其中个别地方,我近年曾经有幸到访,另外一些地方,虽不能至,却也曾经有所耳闻,更多的几处,则大约处于第一次听闻的无知状态。设若邱华栋出生于内地的中原地区,如果不是对西域的地理文化有独特的关注研究兴趣,那么,他的情形恐怕也大概率会和我一样。也因此,同样是一种出于大概率的判断,正因为邱华栋有幸出生在新疆,所以,在他未必就已经明确以写作为志业的成长过程中,才会有很多机会去造访如此之多的古城、遗址以及废墟。至于他所特别强调的“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云云,虽然肯定不是妄言,却也不宜做过于凿实的理解。由于造访时间的前后不同,其中一些时候,邱华栋肯定会产生“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但在另一些时候,却也未必就一定如此。尽管文学想象在当时的生成与否尚需三思,一个不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对作为《空城纪》故事发生地的新疆那些一般人难以抵达的古城、遗址、废墟,邱华栋不仅都有过实地的真切踏勘,而且有些地方的踏勘肯定也不止一次。虽然小说创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想象虚构,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位历史小说的写作者,总还是应该去哪怕已经时隔千年之久的故事发生地实地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地理气息。古人之所以一直都在强调“行万里路”的重要,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与“行万里路”同等重要的,还有“读万卷书”。请注意,这里的“读万卷书”却又不同于本文开头处所指明的邱华栋那简直浩如烟海的广阔文学阅读。具体到这部《空城纪》,与其紧密相关的“读万卷书”,就是指作家一种在相关史料阅读上根本就不容藏拙的田野调查功夫。上下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中,西域那些早已湮灭许久的诸国遗留下的各种相关史料肯定也称得上是浩如烟海。要想高质量地完成《空城纪》这样一部宏阔的历史画卷,虽然不是以考古为志业的历史学家,但邱华栋却仍然不能不如同严谨求真的历史学家一样下足史料阅读上的田野调查功夫。对此,写作经验丰富的邱华栋自然心知肚明:“一部作品的酝酿和诞生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久而久之,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缀成了可以穿梭往返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呼唤。”c在邱华栋的表达中,看似只是“得闲了,就翻一翻”,但只要是此道中人,便会真切了解那翻阅古代典籍的不容易。其他不说,我们在这里且举《空城纪》中的一个具体例证。第二卷“高昌三书”中的“砖书:根在中原”这一部分中,叙述者曾经专门引述过《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铭并序》。开头的一段文字是:“君讳雄字太欢本南阳白水人也天分翼轸之星地列敦煌之郡英宗得于高远茂族擅其清华西京之七叶貂蝉东土之一门龙凤则有寻源……”d因为古代典籍多没有句读,且不说做深入的开掘与研究,单只是能够从头至尾地读下来,对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来说,就已经是足够为难的一件事情。也因此,邱华栋为了《空城纪》的写作而付出的那种“读万卷书”的努力,无论如何也都称得上是史料上一种难能可贵的田野调查功夫。倘若不实际接触那些古代典籍,阅读的艰辛程度的确非想象所能得知。就这样,一方面是因为广阔的文学阅读保证了邱华栋可以拥有高明的文学见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切实做到了古人所强调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以《空城纪》的诞生于世,才不会仅仅是依凭于作家写作天赋的一呈才气之举,而更是邱华栋付出了万般辛苦之后的一种文学回报。当然,这其中肯定也少不了会有写作者天才文学想象力的必然参与:“人在大地上短暂寄寓,是浩渺星空中孤独的存在。因此,在倏忽而逝的生命旅程中,人才会对历史和记忆、时间和空间产生敬畏感。面对西域古城的废墟,就更有了沧海桑田、波诡云谲的复杂感受。在我脑海里,公元纪年后的第一个千年,汉、魏晋、隋唐史书里的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起来,演绎成无数场景;一个个人物,开始有了生命,有了表情,他们内心里的声音冲撞开了那些本来覆盖于其上的风的呼啸、沙的呜咽,越来越响亮和清晰。于是,我为这个世界命名‘空城’,就是想复原这些废墟。紧接着,废墟之上的人们重新来到这里,就像创世纪似的,远古的精神依靠自己充沛的底气矗立起来。我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是为‘空城纪’。”e既然那些故城或遗址早已经空无一人,那当然是空城无疑。然而,一旦邱华栋凭借自身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力,在既有史实的基础上,通过长篇历史小说的方式将其复原或者还原,那一座座原本的空城,顿然间便会变得人生鼎沸起来,一时间就会充满人世间的漫天烟火,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有了《空城纪》这样一部史诗性煌煌的力作訇然问世。
我们注意到,关于文学创作的构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有这样一段特别重要的文字:“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f这篇文字中,刘勰所集中思考的,就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艺术思维问题。在他的理解中,艺术思维或者说构思问题,乃是一个写作者“驭文”“谋篇”的最核心要素。质言之,“要想真正做到为文之神思,创作主体就必须能够‘思接千载’‘视同万里’,必须做到‘神与物游’,也即把作家的主观精神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达到高度交融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作品真正做到‘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也即把身外的万事万物积极有效地纳入到相应的文学文本中来”g。然而,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有很多研究者都会对刘勰的所谓“思接千载”和“视同万里”做一种过分拘泥的狭隘性理解,也即必须把“思接千载”里的“千载”理解为一千年或数千年,必须把“视同万里”中的“万里”看作是一万里或者数万里。但其实,刘勰这里的“千载”和“万里”,在更多时候,恐怕只能被当作虚数来加以理解。只有在如此一种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恍然大悟,刘勰的意思实际上不过是在强调,一个试图抵达某种高远思想艺术境界的作家,他的构思或者说艺术思维一定要拥有足够辽阔的时间和空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说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种说法在很多作家那里只能被当作虚数去理解,那么,到了邱华栋的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这里,却一下子就可以被当作能够落到实处的实数来加以理解,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从古老的汉朝一直到当下时代,已然是足足的两千多年。从空间的角度来说,从遥远的西域古诸国一直到中原腹地,十足的空间距离何止千里万里。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这部气势恢宏、气象万千的《空城纪》,自然也就只能够被理解定位为一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想象之大书了。
但书写的难度也由此而产生。一部时间上跨越千年,空间上超过千里万里的长篇小说,那么多的西域诸国,那么多的人和事,邱华栋怎么样才能够把他们(它们)有效整合统摄在一起,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长篇小说呢?这一点,邱华栋在“后记”中也曾经给出过明确的交代:“千卷书我已读过,万里路我已走过。五六年过去了,如今我完成了它,心里得到了一种安慰。在表达形式上,我这部小说采取了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芦式样的结构。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写六座古城废墟遗址的故事,如果再拆解开来,则又能分解成三十篇以上的短篇。相当于我在尝试着‘装配’这个小说,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中篇组装成长篇小说。”h阅读邱华栋的这段话,首先引起我高度兴趣的,是作家关于“装配”的那种说法。之所以会对“装配”特别感兴趣,主要因为我此前从未看到过这种说法。“装配”——“装配小说”,倘若邱华栋的说法能够成立,那其原创性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容置疑。既然是“装配”,那就意味着整部长篇小说极类似于一部完整的机器,这个体量庞大的机器是由很多个零件以一种内在有机的方式被作家“组装”或者说“装配”而成的。“组装”或“装配”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如果依照一定的程序将其拆卸开来,那就会化整为零地变成若干个中篇或短篇小说。这样一部可整可零的小说作品,因其最早只是诞生于中国作家邱华栋笔端,其思想艺术一定程度上的原创性,自然也就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但在充分肯定“装配”小说原创性色彩的同时,必须提出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台被“组装”或者“装配”起来的机器,其内在的结构原理或者说足以把所有的零件都有机整合在一起的那个核心要素到底又是什么?虽然无法从邱华栋那里获得确切的证实,但依据我先后两次认真阅读之后的感受,在我的理解中,能够把这一切全都整合统摄为一个艺术整体的唯一核心因素,不是别的,正是由龟兹、高昌、精绝、楼兰、于阗这五个历史上的小国,再加上敦煌地区构成的历史上那个辽阔无比的西域地区。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西域国家和地区到底处于怎样的一种生存状况?它们与中原汉民族的各个王朝之间构成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或长或短的存在过程中,它们各自又走过了什么样的一种演变发展过程?所有的这些,全都可以被看作是邱华栋试图以浓墨重彩加以关注表现的核心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小说在上下两千年的时间与纵横几万里的空间里先后出现了那么多的人物和故事,但真正应该被看作是小说主人公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物,而只能是历史上那个幅员辽阔的西域地区。虽然邱华栋在后记中也曾经强调《空城纪》可以被拆解为若干个中篇或短篇小说,但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这部作品却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部中篇或短篇小说集,而只应该是一部拥有内在恒定思想艺术指向的长篇小说。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空城纪》不仅有着幅员辽阔的西域地区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主人公形象,而且这个看似具有抽象色彩的主人公,也还有着足以整合统摄全篇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文本中那些以零散的方式存在着的人和事,全都如同向日葵永远向着东方一样,指向了西域地区这一核心形象。在我的理解中,区别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内在统摄性的有无问题。正因为《空城纪》凭借着西域地区这一主人公的形象而获致了内在的统摄性,所以它的文体归属就只能是一部长篇小说,而不是中短篇小说集。
在叙述人称上,虽然邱华栋采用的是很多人都已熟练使用过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但他的某种不同寻常处,却在于他竟然一下子就征用了多达31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为了研究的精准到位,且让我们把这31位叙述者的情况具体罗列在这里。首先是第一卷“龟兹双阕”。“上阕:琴瑟和鸣”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汉代的龟兹国,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后来成为龟兹王后的乌孙国公主弟史,她的母亲是历史上著名的解忧公主。到了“下阕:霓裳羽衣”这一部分,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就已经变成了唐代繁华异常的长安城。第一人称叙述者白明月,乃是龟兹王室白氏的一个王子。“尾曲:龟兹盛歌”部分,时间一下子就由遥远的古代跨越到了当下时代,第一人称叙述者李刚,是一位特别热衷于民族乐器收藏的业余收藏家。然后,是第二卷“高昌三书”。“帛书:不避死亡”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汉代的高昌国,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班超的儿子班勇。“砖书:根在中原”故事发生的地点虽然同样是在高昌,但时间却已经是很多年之后唐代武则天执政期间,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名叫张怀寂的参军。到了“毯书:心是归处”中,故事的发生地虽然没有变化,但时间却已经是北宋的太宗时期,第一人称叙述者乃是那位肩负使命专程出使高昌回鹘国的宋使王延德。最后的“外篇:高昌对马”部分,时间仍然是当下时代,那位被命名为张刚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刚,是中国美术和剪纸史的一个发烧友。紧接着,是第三卷“尼雅四锦”。第一部分“序章:马的一族与鹰的一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长期往来于长安和康国之间的无名粟特商人。第二部分“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汉代的精绝国,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细眉公主,她的使命是代表汉朝远嫁到精绝国和亲。第三部分“二锦:‘长乐大光明’锦裤与‘河生山内安’锦帽”中,虽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但依据其中曾经被反复提及的“临川王”,以及结尾处专门提及的“刘姓小皇亲兄弟”这两个因素来判断,则故事发生的时间与上一部分一样,同样可以被认定为是汉朝那个时候。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张标,是一位身手利落、身负绝艺的武林高手。第四部分“三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与‘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被”中的故事时间,依然是遥远的汉朝时候。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帕特罗耶,是那个浪荡子沙迦牟韦的好朋友。第五部分“四锦:‘万事如意’锦袍”同样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但假如我们考虑到这一部分集中讲述的,乃是精绝国灭亡的故事,而精绝国的具体灭亡时间,乃是东汉时期,就不难断定故事的发生时间,正是中原腹地的东汉时期。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名叫雍格耶的精绝国士兵。第六部分“尾章:前往尼雅废墟”的故事时间依然是当下时代,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赵刚,可以说是一位废墟考古方面的发烧友。再往后,是第四卷“楼兰五叠”。“一叠:泽中有火”的故事,应该发生在相对原始的渔猎时代,故事的发生地则是罗布淖尔周边地区,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名叫巴布的青年人。“二叠:幸毋相忘”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汉朝。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傅介子,他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代表大汉出使楼兰国。“三叠:比龙化影”的故事发生时间,是南北朝的北魏那个时候。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楼兰国的末代国王比龙。“四叠:沙丘无尽”的故事时间,已经是公元1900年,第一人称叙述者,是瑞典那位著名的冒险家斯文·赫定。“五叠:尸女复生”的故事发生时间,依然是当下时代。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王刚,是一位对废墟考古有着浓厚兴趣的摄影家。然后,便是第五卷“于阗六部”。“钱币部:汉佉二体钱”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枚前后分别印有汉和佉卢两种文字的铜钱。由于汉佉二体钱是汉朝那个时候在西域于阗国流通的钱币,所以,故事的发生时间就应该是在汉代。“雕塑部:佛头的微笑”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已经脱离了身体的佛头。故事时间跨度很长,从三国时期的曹魏,到西晋太康三年,到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到北魏熙平三年,再到大唐贞观、则天时期,一直到唐景云二年,再到后来北宋年间的彻底灭国。“文书部:一封粟特文书”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则是英国人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发现的一封粟特文书的写作者,一个名叫纳耐·凡达克的粟特商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则是西晋时期的于阗。“绘画部:于阗花马”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匹出生在于阗的身姿漂亮的灰白色花斑马。最早的故事时间,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接下来一个明确的故事时间,是隋唐时期,再往后,则是五代时期,后梁画家赵喦把“我”画到了他的名作《调马图》中,然后是大宋时期,宫廷画家李公麟又把“我”画到了他的名作《五马图》中。“简牍部:流沙坠简”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则是一块被收藏在展柜里的于阗语木简。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四块出生在不同时代的简牍就会在一起讲故事。先是由最古老的汉简讲述发生在两千多年前汉朝的故事,然后,由那块有底牍和封牒的简牍讲述发生在曹魏年间的故事,接下来,由直体佉卢文健陀罗语木简讲述发生在隋开皇十年的故事,最后是由这块最年轻的于阗语木简讲述发生在唐大历十二年的故事。“玉石部:约特干的月光”的故事时间,仍然是当下时代,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陈刚,是一位热衷于各种遗址的探访者。这一次,他与画家朋友柳晓东所一起到访的是盛产和田玉的和田,也即当年于阗国所在的约特干遗址。最后,是第六卷“敦煌七窟”。“第一窟:第275窟,一个沙门”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名叫令狐安的富家子弟。虽然另一位富家女子赵娉婷特别迷恋于他,但他还是执意出家,成为敦煌第275窟里的一个沙门。故事时间虽然不详,但洞窟的开凿时间,却是北凉时期。“第二窟:第285窟,一个凶徒”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杀人后无意间逃到敦煌的无名凶徒,主要讲述这个凶徒后来的出家皈依。故事时间同样不详,洞窟的开凿时间是西魏时期。“第三窟:第296窟,一个女子”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小名叫梅娘,大名叫贺梅朵的被凌辱女子。这一部分的内核是一个不无凄楚的爱情故事。故事时间虽然同样不明确,但洞窟的开凿时间却是北周时期。“第四窟:第420窟,一个士兵”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张君义的大唐军骁骑尉。故事的发生时间可以被明确为大唐时期,但洞窟的开凿时间却是早于唐朝的隋朝。“第五窟:第158窟,一个商人”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往返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做生意的中原汉人。故事时间虽然不详,但洞窟的开凿时间却是中唐时期。“第六窟:第98窟,一个国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尉迟苏罗的于阗国王。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大宋开宝三年前后,洞窟的开凿时间为五代时期。“第七窟:第17窟,一个学者”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名叫吴刚的工艺美院毕业生。由于受到同学赵娉婷的精神感召,为了爱情,他最终选择了到敦煌研究院和她一起并肩工作。故事时间是当下时代,洞窟的开凿时间是晚唐时期。
细细地打量这些第一人称叙述者,就不难发现,其中既有人,也有物。不论是一枚铜钱,还是一匹花斑马,都有可能被赋予叙述的功能,成为某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从出生的阶层来看,被征用为叙述者的人物当中,既有皇亲国戚,比如于阗或楼兰国王,比如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或者细眉公主;也有普通平民,比如帕特耶罗、雍格耶、贺梅朵等。从真实与否的角度来看,既有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比如,弟史、班勇、傅介子、斯文·赫定等,也有纯然出于想象虚构的人物,比如张君义、令狐安、巴布、白明月等。这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前后六卷里最后一个当下时代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命名问题。六个部分中的叙述者,除了姓氏有别,六个人居然都被叫作“刚”。从李刚、张刚、赵刚,一直到王刚、陈刚、吴刚。现实生活中,六位第一人称叙述者,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全部被命名为“刚”。既如此,邱华栋这种命名方式背后那格外具有幽默性的戏谑意味,自然也就会油然而生。
除了多达31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之外,邱华栋《空城纪》在艺术形式层面上的另一特点,就是除了第六卷“敦煌七窟”之外的其他五卷中,都会有某一物体的实体或意象贯穿于这一卷的始终。比如,第一卷“龟兹双阕”中,是那一把最早曾经被细君公主弹奏过的汉琵琶。细君公主哭哭啼啼地从中原腹地远嫁到西域的乌孙国之后,一方面是不适应当地的地理气候,另一方面是更加不适应乌孙王室夫死后从子从孙的婚俗习惯,长期处于闷闷不乐的状态之中,若非有这把汉琵琶助她排遣,她恐怕连四年多的时间也都未必能够支撑下来。细君公主去世后,这把汉琵琶先是传递到了解忧公主之手,然后又很快传递到了解忧公主的爱女弟史,也即第一卷中“上阕”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手中。由于自幼即生长在乌孙国,弟史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能歌善舞。既然能歌善舞,那她的拿手好戏之一,自然也就是出神入化地弹奏这把汉琵琶。到最后,因为意外遭受到黑死病袭击,弟史不幸身亡。临死前,“我的怀里抱着那把细君公主的汉琵琶,我相信,以后只要有人弹起这把琵琶来,我的生命就会在旋律中复活”。这是“上阕”,到了“下阕”中,龟兹王室白氏一个名叫白明月的王子,为了躲避王室里残酷的政治斗争,远远地隐居在大唐开元年间的长安城。表面上开着一家香料铺的白明月,其实是一位筚篥演奏高手。在善于演奏筚篥的白明月之外,这一部分的另外一个器乐演奏高手,是同样来自于龟兹的粉衣女子火玲珑。她不仅演奏得一手好琵琶,而且手上所拥有的,竟然是原本属于细君公主的那把老琵琶:“这得归功于她手里的这把汉琵琶,它是她父亲珍藏多年的老琵琶,据说汉代的细君公主使用过,一直在龟兹流传着,后来落到她父亲的手里,现在在她的手上。”当是时也,唐明皇唐玄宗为了迎接即将从感业寺还俗归来的杨玉环,不仅亲自创作了大型歌舞节目《霓裳羽衣曲》,而且还要组织一个庞大的演奏乐队。筚篥高手白明月、汉琵琶高手火玲珑,他们俩全都在被征招的演奏高手行列之中。到后来,返国后坚决拒绝担任龟兹王的白明月,如愿与火玲珑结为夫妻,过着非常幸福的乐舞生活:“我组建了龟兹乐的乐舞班,专心整理音乐。我吹筚篥,火玲珑弹琵琶。她把细君公主那把汉琵琶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不再拨弄,平时弹得有五弦琵琶、曲颈琵琶和西域小琵琶。”“尾曲:龟兹盛歌”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民族乐器收藏家“我”(也即李刚)和琵琶演奏家王雪。那一次,他们俩一起前往新疆阿克苏。当地文化局的沈毅局长握了一下王雪的手:“你是李刚的女朋友?他指着我问。”“王雪笑了,还不是呢。除非他在这里找到了细君公主的汉琵琶。我们都笑了起来。”但就在李刚以为此行肯定会与汉琵琶无缘的时候,在库车老县城木合塔尔所开铜壶作坊的后院的一堆柴火棒子里,“我”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东西:“琴身乍一看,就是一块年代久远的木头,发白,有很多裂纹,不细看,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的心砰砰跳了起来,我判断我找到了汉琵琶。兴许就是细君公主当年用过的那把琵琶。”到最后,在库车老县城进行表演交流的那个星光无比灿烂的夜晚,从热闹的演出现场溜出来的“我”和王雪,顿然间陷入某种幻觉状态之中:“她笑了,我是弟史啊,我又是火玲珑。你呢?你知道你是谁吗?/我喃喃地说:我?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是谁?/你是绛宾,你又是白明月。走,你跟我走进去,在大殿里,正有一曲最美的歌舞等待着我们去演出。我们要进去了。/我再一看,真的啊,我现在华服在身,我难道是绛宾?我手里拿着一支银字管筚篥,难道我是白明月,她是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或者是龟兹琵琶高手火玲珑?”就这样,伴随着原本属于细君公主的那把汉琵琶的再次被发现,“我”和王雪竟然在某种幻觉的状态中穿越时空,似乎重新返回到汉代或者唐代时候的龟兹国,似乎一下就变身为绛宾或白明月,弟史或火玲珑。那把穿越两千多年时空来到当下时代的汉琵琶,自然也就由此而变成了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见证物。
再比如,第二卷“高昌三书”中,是那一只因为中空设计所以能够迎风鸣叫吟唱的铁鸟。先是在“帛书:不避死亡”这一部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班勇,在龟兹它乾城的一家铁匠铺里,意外获赠了一只铁鸟:“这只铁鸟不大,拿在手里比较沉。它是中空的,体形像是一只鸽子,或者一只大号的麻雀。只要把这只鸟放在有风的地方,风就会穿过中空的铁鸟的身体,它就会发出声音,就像是鸟在鸣叫一样。”关键的问题是,虽然铁匠在当时已经把这只铁鸟送给了班勇,但等到班勇要离开它乾城的时候,却并没有想着要把它带走:“离开它乾城的时候,我把这只铁鸟放在了它乾城郊外的一个烽火台上。”然后是“砖书:根在中原”这一部分,在一场战斗获胜后,“我”也即张怀寂驱马走到一个烽火台前:“忽然,我听到了一阵尖厉的、持续的鸟鸣声。很奇怪,此时,下午的光线变得很慵懒,我听到这鸟鸣一阵阵从汉代修建的一座残破的烽火台上发出。我去寻找,发现有一只铁鸟,安详地在烽火台的一个小洞里蹲着,就像是在等待我来临,就像是我要找它,而它也在等待我一样。”意外地发现这只铁鸟后,张怀寂在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自己的背囊里的同时,内心认定这只铁鸟极有可能是来自于汉代的一个遗存。虽然张怀寂非常喜欢这只曾经给他带来过好运的铁鸟(在一次张怀寂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正是铁鸟的鸣叫为他召唤来了自己的坐骑),但等到他某次陪着王孝杰将军在交河城内观览,在看到一座微笑着的佛陀像的时候,背囊里的那只铁鸟却突然鸣叫了起来:“我感觉心明眼亮,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走过去,踮起脚尖,把那只铁鸟放到佛陀像边上,之后,我就快步走起来,跟上王孝杰的大伞队伍,前往北大寺。/那只铁鸟就这样被我放在交河城内的一处佛陀像的脚下。”接下来是“毯书:心是归处”这一部分,行走在回程路上的宋使王延德,突然感到背囊里的那只铁鸟似乎在动:“我都差点忘记这只我在交河城的一处佛龛中找到的铁鸟。我把铁鸟取出来,中空的铁鸟发出尖厉的鸣叫,我把它放进背囊,正在纳闷,就听到远处的山沟上方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一定是山洪冲下来了。”在这里,铁鸟所发挥出的,毫无疑问是一种对于危险的及时预警功能。若非铁鸟及时鸣叫,王延德未必能很快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山洪。然而,虽然内心里特别留恋这只铁鸟,但考虑到它并不归属于自己,所以,等到后来要离开交河的时候,王延德还是断然把它留在了北大寺那座佛像的脚旁。如此一来,也才给紧接着的“外篇:高昌对马”部分的张刚和这只铁鸟在当下时代的意外相逢提供了逻辑可能。意外相逢倒也还罢了,关键问题是,到了结尾处,邱华栋所特别设定的,同样是一种极具浪漫色彩的处理方式。在“我”也即张刚意外获得这只穿越千古时空而来的铁鸟的同时,一路同行的杨泓月也应导师之命,完成了共由十六对栩栩如生的骏马组成的剪纸作品《对马》。不无神奇色彩的一点是,就在那个梦境一般的夜晚,那只铁鸟竟然可以真的鸣叫着在空中飞,而张刚和杨泓月,则各骑一匹骏马也在并驾齐驱地朝着高昌故城的方向努力奔跑。正如“龟兹双阕”部分的结尾处,李刚和王雪可以穿越回遥远的古代,化身为弟史、白明月他们一样,“高昌三书”结尾处的这种浪漫化处理方式,在赋予汉琵琶、铁鸟以及剪纸作品《对马》灵性的同时,邱华栋凭借着自身出众的艺术想象力,其实一方面既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沧海桑田,另一方面却也完成了对历史的某种现代重构。实际上,在其他几卷中,作家也都有类似的颇具匠心的艺术设计,篇幅原因所限,恕不一一展开分析。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在文本中并不具备普遍性意义,但作家在个别章节中极富艺术感的潜对话设计,却仍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或者为此而发出会心一笑。比如,第二卷“高昌三书”中的“帛书:不避死亡”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东汉时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班勇。班氏家族在东汉时期的确是一个显族,曾经出现过多位历史名人。“我”的大伯班固,是东汉的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两都赋》等,曾与司马迁一起被并称为“班马”。祖父班彪,同样是东汉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后传》六十余篇。其父班超,为东汉时杰出的军事家和外交家,不仅曾经在西域驻扎留守长达三十一年,而且还出任过西域都护,为东汉时西域的平定安稳作出过巨大贡献。其姑班昭,是东汉时罕见的一位女史学家,不仅曾经续写《汉书》,而且还著有《大雀赋》等,史称“班大家”或“曹大家”。而班勇自己,虽然没有建立父辈那样的卓著成就,却也不仅是一位曾在西域驰骋疆场的东汉将领,而且还著有《西域记》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邱华栋的匠心独运,乃集中体现在某种潜对话结构的设定上。故事开始的时候,班勇已经因为约定讨伐焉耆但却不幸后至而被判罚入狱。在狱中,只要一想起那些曾经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前辈,他就会倍感郁闷无聊:“我多么想效仿当年的傅介子和张骞,在西域立功封侯啊,整天坐在这里抄抄写写,太没意思了。”事实上,身陷囹圄的班勇,百无聊赖之际,不仅想到了傅介子和张骞这样的前辈,而且更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班超。就这样,从第二节开始,整个故事情节就是在班勇想象中他们父子俩的一种潜对话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比如,“父亲班超的身影飘动了一下。在监牢里,他的影子很轻。他咳嗽着,说,儿子,什么帛书?我写了什么?我记不得了”。然后,便是班勇的回答:“父亲,你记得的,你不会忘记。你看,这帛书就在我的怀里,我拿出来让你看看,你看你写下来的四个字——‘不避死亡’。这就是你写给我的帛书。”一生在西域戎马生涯的班超,当然深刻地洞察了解所谓的时乖命蹇与旦夕祸福。或许正因为他对命运有着某种不幸的超验预感,所以,他才会为爱子班勇写下“不避死亡”这四个字。既然人生无常,死亡的阴影不可回避,那唯一正确的应对姿态,恐怕也就是坦然地“不避死亡”。实际上,正是在他们父子俩的潜对话过程中,班勇在“不避死亡”的同时,也更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自王莽篡权那个时候起始,西域和中原之间堪称曲折的“三绝三通”过程。
再比如,同样是在这一卷的“毯书:心是归处”这一部分。同样的潜对话方式,这一次的两个对话者,竟然全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那位专程出使西域的宋使王延德:“我有时会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王延德,一个是王德延,这两个人总是在争辩。王德延,我现在谁都信不过,只能和你说话。你就是我的分身,我的亲兄弟,我的心腹,当然我也是你的心腹和兄弟。我们每天都要对话。很多事情就只能是王延德和王德延对话。”明明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好生生地自我分裂为两个人呢?原来,所有的这一切,全都与王延德的身份与经历紧密相关。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作为“烛影斧声”这一成语具体由来的宋太祖赵匡胤的突然驾崩。那一次,由于曾经帮着太医给很快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私下准备过一些具有毒性的草药,王延德便深切意识到保守秘密的重要性:“王德延,你说说,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秘密都需要保守,就像是宋太祖是到底怎么死的?那天晚上,他和弟弟见面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看见,我也没看见。可赵匡胤忽然驾崩了。有人看到了蜡烛的影子里,有斧头的起落声,这就叫‘烛影斧声’。”由于赵匡胤突然驾崩前身边只有弟弟赵光义一人,随即登基继位的赵光义便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驾崩的真相究竟如何也就成为一个问题。正因为他一方面亲身经历了“烛影斧声”这一事件,另一方面身居充满阴谋和险恶的官场,所以便意识到了保守秘密的格外重要。怎么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守秘密呢?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能够保守秘密。很多事情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那当然最能够保守秘密。如此一种情形,持续久了,王延德自然也就养成了一种自我分身后的两个自我对话与辩驳的潜对话习性。也因此,在“毯书:心是归处”这一部分,正是借助于宋使王延德的自我对话,创造性地完成了关于自己如何受命出使西域且最终不辱使命的相关叙述。
形式即内容。邱华栋《空城纪》艺术形式建构上的种种努力,不论是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芦式样的“装配”结构,还是多达31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多层面设定;不论是某一物体的实体或意象的贯穿于某一卷始终,还是潜对话方式的创造性运用,所集中围绕的都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位居中原腹地的汉文明与位居西北部的广大西域地区的文化碰撞与交融这样一个宏大的思想命题。或许与这一时空过程的过于漫长和辽阔有关,在其中,总是会不仅伴随有某种文明的兴起与湮灭,而且也还伴随有记录者与书写者的由衷慨叹。虽然整体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说似乎是那些社会政治强人们意志主导下的游戏,普通人更多只是以被动的方式卷入其中,但这些普通人那悲欢离合的人间烟火故事却同样有在文学的意义上被关注的理由。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一种观念的烛照,也才会有第六卷“敦煌七窟”这一部分所集中讲述的那些独属于普通人的人间烟火故事。比如“第三窟:第296窟,一个女子”中那位在现实生活中饱经凌辱与伤害的风尘女子贺梅朵。由于被卖到沙州后受尽来自男人们的欺凌,贺梅朵虽然寻死的决心已定,却又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自我了结。因为很多人在提到莫高窟时眼里都会有光芒闪烁,所以她就准备专程到莫高窟去寻找自己的安身安魂之所。没想到的是,等她赶到莫高窟之后,却意外地在第296窟中遭遇到了《微妙比丘尼因缘》这样一个以绘画形式展现出来的女尼故事。佛教传说中的微妙比丘尼的故事,就这样与贺梅朵自身的悲惨遭际遥相呼应。也正是在这遥相呼应的过程中,贺梅朵的凄苦心境稍获慰藉。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微妙故事的感召,贺梅朵期盼自己也能够得到佛祖的度化,岂料那尊佛像却只是“安然端坐,并不理会我”。万般失望之际,贺梅朵试图高挂在佛像高大的身子上自尽,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被一个名叫张户的来自瓜州的开窟人发现后救下。在后来的相处过程中,由于强烈感受到救命恩人张户就是自己生命中必然要遭遇到的阿难,贺梅朵最终还是选择了嫁给张户,追随张户回到瓜州去,共同生活。虽然从表面上看佛祖似乎的确没有度化贺梅朵,但她由沙州专程到莫高窟,并且在296窟先与微妙比丘尼遥相呼应,后又被张户救下的整个过程,所充分彰显出的,或许也正是佛祖那无处不在的博大慈悲。更进一步说,潜隐于其后的,其实也更是作家邱华栋的一种悲悯情怀。
不仅是贺梅朵这样的虚构人物,即使是如同王道士这样一类看似已经被盖棺定论了的真实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上的普通人,邱华栋在《空城纪》里也给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王圆箓王道士,因为曾经把两万多卷经卷卖给了英国的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的探险家伯希和,而被以“卖国贼”的名义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结论果真就不可更易吗?对此,邱华栋在《空城纪》中显然有所质疑。其一,他是第17窟也即藏经洞的第一位发现者。具体时间是1900年的5月26日,祖籍湖北麻城、一心向佛的王道士,在一次清理洞窟内外流沙积土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发现了第17窟,同时也发现了藏于其中的那么多卷佛经写本文书。如果不是王道士当年不经意间的发现,这个第17窟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到底会不会被发现,恐怕都是问题。无论如何,王道士的发现之功不容埋没。其二,发现第17窟之后,希望引起官方政府高度关注的王道士,曾经拿着部分经卷、文书和绢画,找过当时的县令与省学政等人,只可惜相关努力并没有引起注意,最终无果。其三,王道士本人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是研究专家,见识实在有限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第17窟里发现的,其实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正因为他并不了解这些经卷的具体来由和真实价值,所以他才会任由斯坦因和伯希和以连骗带卖的方式弄走了两万多卷宝贝。其四,王道士所想方设法募集到的二十多万银元,不仅没有丝毫的挥霍贪污,而且还全都用在了整修莫高窟的过程之中。也因此,虽然肯定并非要为王道士辩护,但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够更加公平合理地给出相应的评价,邱华栋的《空城纪》很显然意在于此加以探索。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倘若我们自己是王圆箓王道士,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恐怕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与王道士、贺梅朵这样的普通人相比较,因为与作品的思想主旨紧密相关,邱华栋的如椽巨笔更多时候还是停留在了那些对历史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人物身上,通过对这些大人物的聚焦而淋漓尽致地书写表现两千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文明进程。比如第一卷“龟兹双阕”中的上阕“琴瑟和鸣”,借助于第一人称叙述者弟史的口吻,所集中讲述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细君和解忧两位公主虽然并非出自情愿,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朝与西域紧密关联的历史故事。一方面是她们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西域从地理,到文化,再到饮食、习俗的各种不适应,远嫁到乌孙国的细君公主很快就香消玉殒。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雄才武略的汉武帝再次指派解忧公主继续未竟的和亲事业。与娇弱的细君公主相比较,解忧公主对西域各方面的适应能力明显要强许多。由于出身于一个戴罪家庭,“我母亲知道,从此她的命运将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眼泪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还会是软弱的象征,她的心渐渐变得像铁一般坚硬”。既然内心坚硬,那解忧公主当然也就可以在西域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这其间,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乌孙国王室那样一种夫死后从子从孙的婚俗习惯。这种婚俗习惯,严重违背了汉民族的伦理观念。但尽管如此,解忧公主还是入乡随俗地先后经历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的对象,是乌孙昆莫军须靡。第二次婚姻的对象,是军须靡的堂弟翁归靡,这是一次伴生出了爱情的婚姻,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弟史,就是这次婚姻的产物。第三次婚姻的对象,是身为她子侄辈的“狂王”泥靡。从根本上说,正是依仗着解忧公主的精明强干和她那种自我牺牲精神,乌孙和大汉之间才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到后来,由于解忧公主密谋斩杀泥靡而未遂,乌孙和大汉的关系严重恶化。值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是那位曾经长期追随解忧公主并深受她熏陶浸染的冯嫽冯夫人:“在这个时候,冯嫽冯夫人发挥了她的胆识和巨大作用。她的丈夫是乌孙右大将,和乌就屠是从小在草原上一起长大的,西域都护郑吉了解这个情况,希望冯嫽能够在这个紧要关头,劝说乌就屠投降。”事实上,也正因为有了冯嫽冯夫人在各种势力之间的巧妙周旋协调,乌孙的局势不仅被稳定下来,而且与大汉的关系也重归于好。尽管在派出去和亲的时候,如同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这样的汉族女人不过是被当作物也即工具来使用,但在客观上说,一个确凿无疑的逻辑是,如果没有包括出现在第三卷“尼雅四锦”中“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部分里的细眉公主这样一些和亲的女性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就根本就不会有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之间长期友好关系的建立和保持。
再比如,第二卷“高昌三书”中的“帛书:不避死亡”这一部分,借助于亲历者班勇的第一人称叙述口吻,邱华栋所真切讲述的是东汉时期中原和西域地区“三绝三通”的历史故事。第一绝,是在王莽新朝的时候。由于匈奴人感觉到王莽有轻慢之意,所以便出兵攻打并最终占领交河城。一时之间,周边的西域小国遂纷纷依附,“西域和中原的通道断绝,匈奴人也没有东进。这就是‘三绝三通’中的第一绝”。第一绝发生后,班勇的父亲班超就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提着匈奴主使的脑袋面见鄯善王,迫使鄯善王首先臣服大汉,然后又相继采用计谋迫使于阗、疏勒等西域小国也都归顺汉朝,“汉朝和西域再次相通,这是‘三绝三通’西域的第一通”。没想到,等到后来汉章帝即位之后,却不仅下诏把耿恭他们迎接回玉门,而且还在取消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设置的同时,命令班超返回洛阳。这样一来,中原和西域之间的通道再次断绝,是为“三绝三通”中的第二绝。一方面是由于多年在西域经营,班超已经和这块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妻子西仁月本身就是疏勒人,所以在应召返国途中,班超便停留在了疏勒。正是以疏勒为依托,班超不仅先后平定西域南道各国,而且还成功收复龟兹和焉耆,到了汉和帝永元三年的时候,汉廷重新恢复西域都护,继续派出戊己校尉,这就是“三绝三通”中的第二通。然而,班超离任后,由于他的继任者任尚过于刚愎自用,性情粗暴,在大失民心的情况下,被匈奴反扑成功,西域都护的地位和作用处于急剧衰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汉廷遂决定把西域都护、西域长史再次取消,这就造成了“三绝三通”中的第三绝。这时候,接替班超粉墨登场的,就是他的儿子班勇。正是在班勇的努力下,汉安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我为西域长史,率领五百刑士,也就是被司法判决的刑徒,前往柳中屯田守卫”。正是在父亲班超精神的鼓励下,率部重新返回西域后的班勇,不仅首先将车师六国全部平定,而且还“宜将剩勇追穷寇”地继续北进,攻击匈奴呼衍王所部,最终把他们赶到了漠北深处。因为“西域北道的龟兹、鄯善、柳中一直到河西四郡,再也看不到匈奴人的影子”,所以,班勇自然也就如愿实现了“三绝三通”中的第三通。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建立了不朽军功的同时,班勇虽然已经是身陷囹圄的状态,但他却仍然坚持书写自己的西域经历,最终完成了《西域记》,为后世的西域研究提供了一部特别珍贵的历史史料。
不管怎么说,正是依凭着傅介子、张骞、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班超、班勇、王孝杰、王延德等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凭借着如同那个无名的粟特商人一样的经商者们的不懈奔走,凭借着钱币、玉石、丝绸、锦帛等一众物品的不断流通,凭借着历代执政者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两千多年来的中原腹地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才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得到加强。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有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才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共同体。正因为作家邱华栋以其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力,令人信服地以恢宏气势在《空城纪》中书写表达了历史长河中中原和西域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所以它才真正称得上是一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史诗性长篇力作。
2024年8月25日晚上22时16分许
完稿于并州书斋墨香房
【注释】
abceh邱华栋:《盛代元音》,《空城纪》,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681页、681页、682页、682页、682页。
d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邱华栋:《空城纪》,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不一一做注。
f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8-249页。
g王春林:《“思接千载”或者尖锐的历史诘问》,《海派长篇小说十论》,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