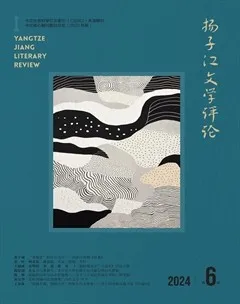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史论的别样建构
几年前读韩春燕的专著《风景颗粒——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小说解读》,便被其独到的见解所吸引。作者用如诗如画的语言,娓娓评述着她钟爱的作家和作品。像微微春风,吹拂着白山黑水,似霏霏春雨,滋润着读者心田,使人在审美的熏陶中,接受了论者的批评理念,实现了对作家作品的认同。如今,读她的小说史论《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以下简称为《启蒙的风景》),又一次受到审美的震撼。不过,这不只是因为史论的诗意论述和远方风景,更是因为其在前辈既有乡村小说研究的基础上,对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史论的别样建构。该史论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和站位,以启蒙作为纵贯叙事研究的中心题旨,运用多学科的理论,通过六个必要的审视角度,考察中国百年乡土小说,观照其在嬗递流变下的历史沧桑,拓展了乡村小说研究的新视野。基于此,该史论对百年中国乡村小说的风景,作出了科学的梳理和公允的评判,并为其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正态发展,探索了可资借鉴的路向和经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量和评估,《启蒙的风景》不啻是新时代乡村小说研究中弥足珍贵的收获。
一、站位:现代文明观照下的研究视野
思想站位是史论的灵魂,是文学批评的坐标。众所周知,一部史论作品的价值、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者的思想站位,取决于论者是否追随时代潮流,与时代同频共振,对文学历史作出与时俱进的研判。《启蒙的风景》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作者运用现代化的视角和理论,重构乡村小说的启蒙话语体系,从建设现代文明的高度观照百年中国乡村小说生态,并以此开拓新视野、探索新思路、推出新观念、建构新史论。
《启蒙的风景》站在新时代思想和现代文明的前沿,突破了以往碎片化的研究格局,构建了严整的乡村小说谱系。长期以来,学界对文学史的分期十分刻板,将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按照政治运动、政权更迭等因素,割裂为三大阶段,命名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相对独立的子学科,并赋予每个学科不同的研究重点和学习方案。尽管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都共存共生在百年时空之内,而且都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征程之中,但是它们却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且壁垒森严。因此,既然百年来中国历史前进都是以现代化作为革新关键,百年来中华民族都是为达至现代化而搏战,那么,就没有必要对文学史进行眼花缭乱的拆分了,把它归依在一个文学史集合体中,统摄为一个广义的现代文学学科,应该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事。文学体裁的分类史亦应如此。《启蒙的风景》正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看来,“中国乡村小说的百年嬗变历程实质上是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百年,尤其是中国乡村社会百年现代化历程的一个文学记录”a。据此,作者以穿越时空的史学机制和纵横捭阖的理论分析来践行这个研究整合。在《启蒙的风景》里,百年人物齐聚一堂:阿Q与陈焕生“晤谈”,闰土和许茂“相聚”,祥林嫂与水生嫂“派对”,老通宝和白嘉轩“交流”。这里,百年乡村共同登场:未庄与刘家峧、鲁镇与元宝屯、贺家坳与蛤蟆滩、陈四桥与赤杨岗演绎于同一区域。他们以荡气回肠的共同发声告诉读者,百年来的中国乡村、中国农民,其改变贫穷面貌的炽烈希望,是一般无二的;其追求现代化的崇高理想,是毫无二致的。基于此,《启蒙的风景》呈现了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上独特的政治风景和时代表情:从塞北草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域戈壁到东海渔村,古老的村镇、辛劳的村民,其坚韧不拔的前仆后继,都是朝着无限憧憬的现代化愿景砥砺前行的。因此,史论没有对百年乡村小说按照传统的三段进行爬梳,而是以嬗变为研究基点,拆解那些有形无形的学术障壁,弥合那些广阔绵长的时空界限,将百年乡村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析。全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六个专章观照六种百年小说嬗变,六种嬗变折射出百年的小说态势,条块分明、条分缕析,形成了一部体式新颖的现代小说史论。这种对乡村小说的立体式记录写真,开拓了小说研究的新领域,扩大了小说史论的新天地,无疑是对往昔模式的冲决和超越。其思想站位、前瞻意识、创新思路都令人称赞。
《启蒙的风景》以纵贯百年研究中的启蒙话语为核心,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探索了中国乡村小说的嬗变途径。史论选用“启蒙”作为主题词,颇有深意。因为,“‘现代’最大的表意符号就是‘启蒙’”b,所以,作为20世纪初的热络词语,作为当时响亮的文学口号与此后衍生的研究模式,启蒙在这里绝不是指时下的研究依然要袭蹈当年的路径,而是指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应有的使命担当。须知,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升华民众素质、改造国民根性仍是不可推卸的要务,“五四”时期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启蒙任务还要继续完成。故而作者这里指涉的“启蒙”,当是一种乡村现代化的启蒙,一种赓续传承中华文明的启蒙,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现代化启蒙。何谓现代化?“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c,“是指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d。“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e根据这些认知定义,作者认为,“百年中国乡村小说的嬗变过程实际上暗合了中国乡村社会追求现代化的诉求与探索”f。在此基础上,史论广泛寻觅乡村小说中的中华文明元素,探索它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天然联系,讨论它融入中华文明新质的必要与可能,并将其作为构建现代文明的参照和要件,从而在纵向观察中勾勒出现代文明发轫到崛起的曲线,在百年背景上描绘出中国乡村小说嬗变的具象风貌。如第一章在论析乡村小说的“自然”与“风景之变”时,作者就以现代文明为标尺,借用茅盾先生提出的“地域差异性”来考察和评判乡村文明的优劣水平。又如第二章对新时代以来自然空间之变的分析,作者在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满渴盼的同时,流露出两难心境生发的隐隐担忧:“当时间来到21世纪后,经济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冲击成为中国农村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中国正在逐渐走向城乡中国,因此,作为传统农业时代的产物——土地,正在被不断侵蚀。正因为如此,乡村小说的书写也同样面临着如何书写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样貌这一时代难题。”g在第三章主题之变的讨论中,作者在对蕴含中华文明因子的嬗变予以肯定和希冀的同时,也对那些愚昧落后的旧质元素予以彻底否定和无情鞭挞。比如细读赵树理的乡村小说,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赵树理乡村小说主题内涵反映了乡村社会新的生活、新的制度、新的政策,以及农民新的面貌……赵树理乡村小说揭露的往往是与政治要求相违背的思想观念,或是对新的制度与政策具有阻碍作用,甚至是产生破坏力量的现实问题。”h不仅如此,作者用大量笔墨对20世纪后期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冲突,对与之互联互动的乡村小说书写立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肯綮的评断。比如对陈忠实、贾平凹、陈应松、孙惠芬、莫言、张炜、尤凤伟等作品的解读,均生动地展示了城市文明的蒸蒸日上,乡村文明的急剧转型,告别旧有生产生活方式的艰难彷徨,现代文明之路的曲折漫长。满怀复杂情愫的作者用深情的笔调昭示:在农耕文明与村庄的夕阳西下中,现代文明的莅临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华民族迅速升腾的现代文明曙光,必将普照广袤的神州大地。
二、切口:嬗递流变焦距里的历史沧桑
治史作论,需要找好切口,即准确的进入点位。众所周知,面对宏富浩繁的史论对象,论者必须筛选出论析的重点,然后再根据重点确定楔入区。在汗牛充栋的百年中国乡村小说中,在千姿百态的乡村小说文本里,《启蒙的风景》只是选择了六个具有典型意义、普泛价值的切口,以一斑窥豹、一叶知秋,从小窗口瞭望大世界。正是秉承小中见大、点中有面的传统手法,史论从这六个切口观瞻了乡村小说的流变趋赴,透视了历史沧桑与时代涅槃的全程全貌,从而寻觅、获取了精准的关键评语和公允结论。
《启蒙的风景》以百年嬗变为视点,点面结合,以点带面,逼近了乡村小说的艺术真谛。作者认为:“在中国乡村小说百年的嬗变历程中,‘变’才是常态,唯有掌握这一‘锁钥’,方能破解乡土中国与中国乡村小说的百年互动关系。”i百年以来,现代化一直是古老中国的首要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致力谋划的美好愿景。在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苦跋涉中,乡村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乡村小说作家不断探寻现代化的多维面貌,并上下求索以文学参与时代变迁的方式,倾力耕耘乡村小说沃土,向时代奉献了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形象地记录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悸动:憧憬、焦虑、困惑、彷徨和奋起、拼争、博弈、攀登。《启蒙的风景》就以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抓手,打通六个关键的栈道,破译乡村小说的走势之谜,还原乡村小说的文学真谛,逼近乡村小说的艺术内核,宣泄乡村小说的美学理想,显示了作者敏锐辽阔的史论眼光。作者选择的这六个嬗变,一是自然风景之变,二是空间之变,三是主题之变,四是语言之变,五是民俗之变,六是器物之变。这些嬗变都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参照,是中国社会变革起伏跌宕、坎坷多艰、风雨兼程中的闪光路标。其中的主题之变、语言之变,是作家创作主体之变,其他四个之变是乡村创作客体之变。主体客体相辅相成、相汇相融、互联互动,互为鉴证,共同皴染了百年乡村小说的嬗变风景。比如第一章,对不同阶段自然风景强烈反差、巨大变异的不同书写,及其包含的审美意蕴、叙事方式的分析,真切地反映了乡村向现代化前进的艰辛步履。第二章空间之变中,对物质空间、精神空间、自然空间的诠释,则是对中国乡村文明全方位、多维度的冷静审视。作者指出,穿越幽深的历史隧道,这些空间,已经不是外部直观的先天表象了,而是时空交融的现代生态图景,是社会嬗变的表征。在第六章对器物嬗变的分析和考辨中,作者着力开掘器物的文化隐喻意义和文化衍生价值,认为“中国乡村小说对于器物的书写如同双面镜,它既对百年来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实现了显影定格,也成为作家寄寓审美价值观念的载体”j。这是非常深刻的见地和睿智的发现。第三章对主题之变的考察,更是作者对创作主体审美意识的深度剖析。同是小说家的作者,认同“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是文学话语的谈论对象,而是文学话语本身所显示的核心意味”k。这之中蕴含着作家对生活的体认和思考,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美学判断,是潜隐在作品中的深层次主旨。总之,作者回望百年乡村小说的精确视点和文本论析的恰当切口,对这部史论的成功裨益极大。
《启蒙的风景》以文本细读为铺垫,提纲挈领,纲目相融,摄制了乡村小说的流变景象。可能有读者会对史论没有为人物之变设一专章而困惑,窃以为,这是没有悟出史论的终极意图。作者说:“中国乡村小说对于现代化的追寻实质上是对于作为独立的‘人’的价值的追寻。在中国乡村小说的百年‘主题’之变的引领下,无论是‘风景’之变、‘空间’之变,抑或是‘民俗’之变、‘器物’之变,中国乡村小说百年创作的核心要义仍是对于书写对象即以农民为核心的中国乡村启蒙的诉求。”l一语破的,这样的疑问应该迎刃而解了。诚如斯言,《启蒙的风景》多角度多侧面地分析林林总总的乡村嬗变,其最终指向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绘。以此为钥匙,就能够明晰作者的巧妙布局和科学运筹。展读全书可以看到,支撑《启蒙的风景》论点和观念的,是代表性小说文本;破译小说艺术与内涵的,是海量的文本细读。而这些,无疑都是为人物分析所做的铺垫和功课。在《启蒙的风景》撰写中,除了几十部参考文献之外,作者细读的小说文本就达七八百部(篇)之多,分析的人物也达数百个。无论是观照乡村小说的发轫期、初创期、丰收期,还是透视其转折期、停滞期、高潮期,作者都针对自然风景之变、空间之变、主题之变、语言之变、民俗之变、器物之变,细致地解读了诸多代表作品,走近了诸多典型人物。六个专章中,有的着重分析小说的立意主旨、思想指向,有的系统论述小说的时代背景、故事经营,有的细腻阐释小说的内涵包孕、潜隐寓意,有的努力辨析小说的结构形式、叙事手段,有的深度评判人物的个性特征、人生命运,有的热情透视乡土的民风民俗、自然风貌,有的冷静梳理作家的话语创新、语体特色,有的全面总结乡村的文化形态、文明样貌,有的倾情追溯人物的心路历程、英雄壮举……在此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将细读感受升华为审美结论。其结论提纲挈领、纲目相融,新见迭出、各有侧重,直击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些提炼出来的新观点、新结论,使得这部百年乡村小说嬗变的史论内容更加丰沛、意蕴更加深厚、语言更具风采、观点更为公正,具有显见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三、模式:多学科理论介入的乡村叙事
做好史论,需要选择模式,模式决定史论的良莠。史论的写作实践说明,论著的成功大多得益于科学模式多元化的采用。因此,成熟的文学史论无不重视多元模式的选择和汰滤,《启蒙的风景》就提供了这样的案例。它引进多学科理论的因子和元素,采取了宏微结合、纵横交错、多维多元的论述模式,搭建了这部乡村小说嬗变史论的坚实框架,对中国百年乡村小说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分析,推展出一幅乡村小说起伏跌宕、五彩缤纷的历史长卷,给乡村小说风景的升华树立了参照系。
以宽广的学术场域,引进多学科的学理,参与乡村小说的阐释,是《启蒙的风景》的鲜明特色。著者在开拓了崭新的研究视野之后,寻找合适的创新研究模式,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村文学研究的模式日趋多姿多彩,在不同的角度中各逞其能、各擅其妙:从传统的启蒙研究切入者有之,从文化学视角切入者有之,从两种文明冲突切入者有之,从农民、知识分子立场切入者有之,从全球化浪潮切入者有之,从中外乡村对比切入者有之……虽然这些模式都各有千秋、成绩斐然、不可小觑,但《启蒙的风景》没有照搬照用,而是取其精华、革新借鉴,然后独出机杼、另辟蹊径,直面中国百年乡村小说研究的艰深课题。作者深知,对乡村小说美学建构的独特性以及内蕴涵纳的丰富性进行深入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乡村文学文本中,“地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已经转换成了某种文化结构……它携带着作者的主观认知、社会理想、美学趣味,携带着一个时代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信息”m。因此,百年乡村小说研究必须调动多学科的理论资源,齐抓共管、协同作战。“从乡村文学中具体而微的乡村入手,把乡村作为研究标本,期望通过对现当代小说中不同时空下的乡村世界的分析,来探究中国当代乡村文学的面貌以及嬗变的轨迹。”n这样,除了文艺学之外,《启蒙的风景》还大量运用美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民俗学、比较文学等多学科理论。如在分析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时,作者大多采用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原理,阐述鲁迅小说的写作姿态、启蒙意义、艺术价值和勇开先河的巨大贡献。在分析沈从文的“京派”小说时,又多采用美学、宗教学、文化学、民俗学理论,探究其“人性小庙”“桃花源”中批判现实、崇尚美好、期盼天人合一、回返自然的创作初衷。在分析赵树理的小说时,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杂糅其中,使解放区乡村小说的文学史地位一览无余。对“东北作家群”救亡文学主题的乡村小说,“十七年”的革命书写、合作化叙事,“新时期”乡土小说,作者更是以多个学科的学理来为其溯源、析理、比较、定位。又如在分析“空间之变”时,作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使得“‘空间’的哲学内涵、社会学内涵、政治学内涵,文化内涵等都被挖掘出来”o。其中包孕的文化学、美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的内涵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至于“民俗之变”“语言之变”的分析,除了主要运用民俗学、语言学理论进行学理的深化、开掘,其他学科的理论也隆重登场,与之协同作战。总之,多学科理论的深度介入、强烈参与,多维多元的分析论证、解读诠释,大大增强了《启蒙的风景》的理论深度、观念高度和论析力度。
以深邃的学理分析,运用宏微结合方法,进行乡村小说的解读,是《启蒙的风景》的亮点。作者在运用多学科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始终采取宏微结合、纵横交错、多维多元的方法,对五彩缤纷的乡村小说进行“全方位”的透析。这既是对研究对象精确观照的要求,也是提高文学研究水准的必然。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论,虽然不可能面面皆优,但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是必须注重的。《启蒙的风景》在这方面就上下求索、刻意为之,努力通过各种方法的运用,达到对理论深度的追求。如果检视全书整体的架构内容,史论无疑做到了宏微结合、纵横交错。宏观上,史论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乡村百年小说史;微观上,史论则是乡村小说分类评论的集群。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分工和密切连缀,构成了中国百年乡村小说嬗变的史论。如果考察史论各章的论析阐述,史论也完全做到了宏微结合、纵横交错。宏观上,各章都有对各类百年嬗变的总的评估和论断;微观上,各章中也都有不同案例的细腻分析。两者紧密相融,无缝对接,深化了史论的中心论点。在宏微结合中,有的章节从宏观论断入手,首先将宏观的结论推出,然后进行微观举例,通过引证大量翔实资料,纵向横向交错叙述,宏观微观对比分析,有力地证明了文本的论点。有的则逆向而行,先是微观论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卒章时进行宏观的概括总结。这些宏微结合的论述,多以纵横交错的个案叙事、多维多元的反复求证来取得论点的确立,讨论器物之变的第六章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本章的第二节中,作者对“十七年”器物书写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分析,角度新、篇幅长、举例多、论述精,几乎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其中《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最。这里的器物,不只是指形而下的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囊括了在生产活动当中使用的各种器物,如机具、石碾、铧犁、竹竿、百日黄稻种、金皇后玉米等。这些器物与主人公一起,成为读者了解那个时期农村面貌的重要表征。如潇潇春雨中,梁生宝背着稻种在泥泞的关中大地蹒跚行进的描写,猎猎寒风中,他在重峦叠嶂的终南山中砍竹子的叙事,经过作者细腻的、形而上的分析,同原著文本一样震动读者的心灵。古华在《芙蓉镇》中的器物描写,伴同豆腐西施胡玉音店面的扩大,更让人们看到了“新时期”农村改革者付出的血汗辉光。这些宏微结合、纵横交错的论析,无不彰显了这部史论学理的深刻意义和不俗价值。
《启蒙的风景》对中国乡村小说的百年历史进行了一次细致探究和深入发现,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小说嬗变的魅人风景。这是一次文学历史长河的追波逐浪,也是一次乡村世界的旅行观光,更是一次浓郁乡愁的消解分享。然而,当读者沉浸、瞻望乡村嬗变的幻梦时,作者却语出惊人:“在尘土飞扬的现代化路上狂奔,落寞的乡村还能够被我们想象多久?”p这不能不让人们陷入淡淡忧伤和深思考量,倍加怀念那渐行渐远的、魂牵梦绕的原乡。
【注释】
afghijlmnop韩春燕:《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春风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页、10页、100页、126页、12页、221页、10-11页、9页、14页、58页、255页。
b孟繁华:《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学里——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题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
ce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14页。
d刘晓峰:《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理论与现代化》2014年第1期。
k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