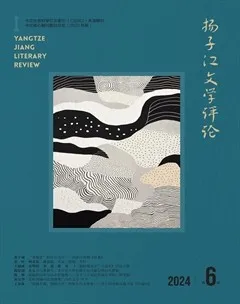共时、乌托邦冲动与真理时刻
在王安忆晚近的作品序列中,“自我与历史”的辩证被纳入乌托邦之形式与乌托邦之欲望的辩证中,人物似乎不足以承载乌托邦冲动并将其形式化。相较将乌托邦置于过去的《天香》《考工记》,在《一把刀,千个字》中,讲故事的人与故事搏斗,人物“以追寻来避免追寻”,质疑了追寻真实的可能性以及“真实”的建构。有关《一把刀,千个字》,“神话讲述的年代”是20世纪60至90年代,而“讲述神话的年代”却是21世纪的十年之后。文本之外,讲述与追忆的动力何在?21世纪之初,吴俊提出王安忆的创作瓶颈在于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哲学化倾向,“小说表现技巧的匠气和结构形态的封闭性以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偏执,构成了王安忆在近期创作中的瓶颈特征”a。
若暂且搁置“瓶颈”与“突破瓶颈”的二元框架b,可以说,王安忆有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后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文学才能。在晚近的作品中,“自我与历史”的辩证被纳入乌托邦之形式与乌托邦之欲望及冲动的辩证中。前者指“形诸文字的书面文本或文学形式”,后者则是“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乌托邦冲动及由特定的解释或说明的方式所实现的乌托邦实践”c。若将王安忆的作品分为在历史的“阴面”与“阳面”写作,前者如《长恨歌》等,以小人物悲欢沉落切入大历史的接续点,“日常生活”是激进政治的对照面;后者则如《启蒙时代》等,正面处理“思想者”如何将革命从概念落实到生活,如何在思想与行动间建立有机关系,“日常生活”是辩证法的一环。
《一把刀,千个字》可归入“阴面”书写的序列,却也将革命先驱、革命二代与“外人”设置在家庭空间与饭局场景内,迫使其展开“复调”对话,实现了“重复与差异”。在“历史的阴面”的序列中,“自我”似乎不足以承载乌托邦冲动并将其形式化,亦不足以作为使辩证法运作的容器。人物往往沦为无名、匿名状态而进入“微物”层次d,其极端状况便是《匿名》中的“他”“那个人”;而以“知识考古学”引入前现代文化资源,亦是为乌托邦潜能构造形式的努力。对此,重要的不是考察王安忆的考古学运作是否彻底,而是关注乌托邦的形式化本身。如詹姆逊所说,“有趣的不仅仅是构建乌托邦的社会和历史的原材料,还包括建立在它们之间的表现关系——如封闭、叙述以及排他或颠倒的关系”e。若“在叙述分析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不是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而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那些在叙述构架中压根儿没有被提到的东西”f,那么在《一把刀,千个字》中未被说出的事物,便可能比在《纪实与虚构》《天香》《考工记》中已被说出的事物更具症候性。
在“讲述神话的时代”,假定了历史终结的作品如何转化历史推动力以完成叙述?(反)追寻的动力学作用于溢出了社会结构的“外人”,或可反视结构如何成立,共时与历时的系统如何被缝合。在“外人”身上,“净化”(“叙述者突然感到一种与小说中的苦难相悖逆的解脱感”g)与“真理时刻”(“被冠以初始的自反性的整个运动,一种对于乌托邦过程本身的自我意识的降临”h)使叙述与追忆的机制闭合,最终,逃避叙述的“外人”获得了自己的传记。
一、乌托邦形式:(反)追寻的动力学与“外人”
《一把刀,千个字》分为上下两部。小说上部由“法拉盛里旧时代的人”、淮扬厨师陈诚的移民生活写起,插叙引入陈诚在上海弄堂的童年时光、在高邮乡下的少年经历,以及陈诚嬢嬢与父亲杨帆的前史;下部则让全家福上“黑洞”般的母亲显影,以母亲由反动派到被追称为烈士的人生经历,透视革命的幽灵如何在后革命的年代缺席而“在场”(甚至通过缺席而“在场”)。小说中大多以“他”将陈诚置于匿名、无名状态,汉语书面语不易区分自由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王安忆亦以“说话”而非“对话”来处理言谈i。叙述与追忆高度同化,现实从被叙述的事实成为有待追索的记忆,而记忆因叙述的稳定有了事实般的质地。
王安忆曾自陈对《追忆似水年华》及其追忆诗学的欣赏j,不过,与其说此类叙事手段确保了“追寻”的客观性,“让位于一个主观视角下对更深刻甚至更‘真实’的追寻”k,不如说是强化了“追寻”本身,在追寻的过程中揭示“反追寻”的构造。区别于以“追寻”本身为动力的“元追寻”l,“反追寻”即人物“通过追寻来避免追寻”,是对追寻真实的可能性、对“真实”之建构的质疑。
追寻的动力将叙述推得越接近历史将自身结晶化的时刻,人物便越向叙述所不能及之处逃逸。对于这逃逸中的、反追寻的主体,可用“外人”加以命名,以区分于更极端的《匿名》。在《纪实与虚构》的“纪实”部分,王安忆以普通话与上海话、“同志”与“小市民”的差异处理革命二代与上海本土秩序的张力。《一把刀,千个字》中,时空格局进一步拉大,“外人”从家庭内外区隔、“差序格局”中的不同位置m扩展到海外流散(diaspora)中的个体。“外人”这一概念来自克里斯蒂娃对自我/他者辩证法的改造:“外人栖居在我们身上:他是我们身份被遮盖的一面,是毁坏我们处所的空间,是融洽与同情分崩离析的时间。”n外人的面孔正是“反追寻”的动力,它“仿佛永远地邀请我们踏上某场无法抵达的、让人恼怒的征途;外人不谙这场征途的规则,却保留着对这场征途的记忆——静默的、有形的、可见的记忆”o。
若从陈诚可疑的孤儿身份出发,分析革命的弑父与后革命的恋母,便可能落入作者的疑阵:陈诚择偶时的“恋母情结”在小说中作为他人的评价而出现,恰恰属于“我们”对“外人”的同化而非“外人”的自我认知。姐姐“划清界限”的绝情与母亲的理想主义实则一体两面,外人则“是自己母亲的陌生人。他从不叫唤她,也对她无所求,反倒是傲慢地依附于他所失去的、他所缺乏的,依附于某些象征”p。一如书中所写,“他自觉做不了母亲的孩子。姐姐才是呢,虽然划清了界限。他连‘界限’都没有,谈何‘划清’?”q若姐姐的回避是出于遗忘的反作用力,那么失却了记忆的陈诚连压抑的机制亦不曾有,因为回避、压抑的对象并不实有,起作用的并非反作用而是无作用。
为了让这一“连‘界限’都没有”的“外人”维持在叙事者的视域之内,《一把刀,千个字》中的历史因果律从历时性悄然演化为共时性。历时性的因果律“是原因的单弦,是关于变化的撞球理论,它倾向于隔离出一条可能不同的因果线,隔离出一击命中的有效性(甚至是一个终极决定性例证)”r,共时性因果律则是事物反映在自身内又映现于他物中,形成了一个原因与后果互相依存的世界。
于是,有限的主人公视点中,“历史变成了一股令人困惑的纯生成的洪流”s,这洪流在书中则体现为“饭局战争”。姐姐说:“我们这种人总是错的。”当德州人问“什么才是对?”“姐姐说:历史。”历史永远正确,历史中的人则只能负担其后果,历时、线性因果论撤销了虚构艺术甚至日常存在的合理性,如安敏成在讨论现代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时提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小说的摹仿机制,“在中国,历史本身就执行了被亚里士多德归之于史诗和戏剧的典范性的功能,其结果是虚构性的叙述艺术从未获得独立存在的根据”t。但正如汉学家观看中国,王安忆为这一判断设置了一个共时的观看者,即姐姐的美国男友:“他似懂非懂,来回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仿佛在想,这些不可思议的中国人!”似乎人人皆为彼此的“外人”,人人皆是历史内部之中的外部。
王安忆笔下,结构往往在建立后便被拆解,乌托邦冲动溢出已完成的乌托邦形式,共时的观看者、叙述者、评点者——一个始终存在的“外人”——的发言解构了历时因果律的唯一性。女同学与母亲辩论时说:“夹缝就夹缝,你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里的草籽和泥土!”铁路线旁,杨帆劝女邻居放弃和自己重组家庭,这一空间设置别具意味:滨绥、京哈、哈佳等线路连通起外部世界,“在那里,发生着多少大事情,像纪念碑样的,石缝里的泥灰,细沙,偶然落下来的草籽,就被疾驶的风带到这里,这里就像世界的终端”。在“那里”/“这里”的间隙,杨帆了悟“母亲”是“纪念碑”,而“他,他们,都是驮碑的龟”。对外力的无反应、无作用,对追寻历史真相、弥补缺位者的放弃反而产生了一个“我们”,以及以本能搭建的“共同的日子”:
一些共同的日子从眼前过去,快乐和不甚快乐,甚至恐怖惊惧,在历史的洪流中,越来越渺小,直至看不清。他们都是面目模糊的人,可依然认真地走着自己的路,凭的多是本能。本能也是了不起的,从原始的驱动发生,服从宿命。她呢,她却是更高一筹,从本能上升到自觉,哥伦布竖鸡蛋的那一磕,鸡蛋碎了,却立起来了。而大多数的本能,却变形了,在纪念碑巨石的压力下,躯壳缓慢地迸裂开来,长出狗尾巴草。
与纪念碑/草类似,书中还存在星空/平凡的对举。在母亲的学生时代,“女同学说:我们都仰望你,就像仰望星空。你们才是星空!她说。我们是凡间的人,我们相信平凡的真理”。母亲事发后,女同学来杨帆家搭救儿女时说:“她的真理在星空,我们的,在日复一日之中。”不过,“纪念碑”与“狗尾巴草”、“星空”与日常并非王安忆“自我与历史”这一辩证结构的转喻,而须纳入乌托邦之形式与乌托邦之欲望及冲动的辩证中考量。在“外人”眼中,“纪念碑”与“狗尾巴草”并不处于同一个时空。悬置“星空的真理”不等于选择“生活的真理”。一如《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男性角色的处境,杨帆是女性亲密关系的局外人。母亲与他结合是“从天上回到地下,由他引入普遍性的日常人生,那里也有着真理一类的存在”,然而,当女同学举出“日复一日的真理”以对标“星空的真理”,杨帆的反应却是“‘真理’也出来了,他不由瑟缩一下”。作为偏正结构的“生活的真理”,可能暗示“真理”吞没了“生活”。“平凡的真理”“日复一日的真理”与“星空的真理”并不势均力敌,在语法和象征层面,它们都被“真理”统摄。如果真理存在,也并不在日常中,而在日常与星空的对举中,在这一对举结构被发明、使小说得以继续的“净化”时刻中:“女同学按灭台灯,窗帘上却有光掠过。船进港了,女同学说。”
除了“外人”疏离的视点,王安忆又在历时结构中加入前现代的非线性时间,让叙述进一步扩散增殖。法拉盛宴席上,陈诚暗示“今天人的品味抵不过昔日一介车夫”,“贵宾嗖地起身:谁说又不是呢?古人道,礼失求诸野,如今,连‘野’都沦落了”。乡下葬礼上,听亲人喊“老祖宗躲钉”,“舅公说了一句:这就是周公说的‘礼乐’!”皇历上的“沐浴”“扫舍”等字样让舅公不时赞叹“多么古啊!”“‘古’,是师傅对事物的极高评价。有一回,向晚时分走在路上,太阳正往后落,光着膀子的男人在地头上摇轱辘井,一畦畦的田垄从男人脚下辐射过来。师傅停下脚看一会儿,说:真古!”陈思和曾指出20世纪中国从“共名”到“无名”、从一言堂想象下放为民间多元的想象之转变u,但在此处,被重新发现的民间再次成为景观。舅公以仪式化的“古”遮蔽了乡村实存的政治经济状况,以《易经》和皇历的抽象律替换了劳动者可感的精神世界,“真古”的赞叹甚至危险地接近胡兰成的“亦是好的”。如此的“古”并不具备与现代性时间对抗的能力,“光着膀子”的劳作亦不比“那天使就是绿色纸币”。
不过,王安忆也并非要以某种时间取代另一种时间,她力图展示的是多种时间的并置及其引发的“众声喧哗”,在书中,这往往演变为“饭局战争”。围绕“学洋人酒会小点,插上牙签”的糟香鸭舌,客人以“离散”为题讲起“革命家史”:解放战争后,已在台湾的母亲回大陆寻找淮海战役时被俘的国民党军人父亲,讲述者则“看马路上人流冲突,惶遽骚动……丢了包裹的,丢了孩子的,被车碾压,被马蹄踩踏,遍地哀鸿”。杨帆以“看”的真实反驳“讲”的真实:“这不是事实!”“请问这位先生,是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看见?……上海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秧歌队伍,本人正在其中,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看到了吗?”讲者则以“眼”的复数性为历史与真实的复数性辩解:“你有你的眼,我有我的眼,这就是历史的多重性。父亲说:应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无论多少重,主流唯有一支!”这看似以历时的单一因果论压倒了共时的多元决定论,但唇枪舌剑中不时插入“外人”陈诚的疏离,“父亲的声音仿佛在很远的地方”,师母和胡老师则以陈诚的茶点打岔:“民以食为天,这才是历史的硬道理!”“大叙事”似乎不断被小叙事拆解。在后革命的历史创伤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被替换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饭局战争”并无输赢可言,有的只是共时的横截面。这一截面的喻象化身为东北凌汛:“先只是互相推挤,你叠我,我叠你,底下的水仿佛地火一般往上拱,闷响着。然后,突然某一时刻降临,轰隆隆震天动地,冰凌子就像脱缰的马群,直朝下游奔腾而去。”
同样是为历史的“无名”之力寻找喻象、为乌托邦冲动寻找形式化结晶,丁玲将水描写为“飞速的伸着怕人的长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颜色,成了不见底的黑色巨流,响着雷样的吼声,凶猛的冲了来。失去了理智,发狂的人群,吼着要把这宇宙也震碎的绝叫”v。冯雪峰称《水》为“新的小说的诞生”,而《一把刀,千个字》中的水则位于彼时“新的小说”的终点,主体“甚至连一次也不可能踏入这条河流”w。在凌汛面前,以“他”指代的“外人”如同“叙述的扩散增殖”中的个体,他“身上起了寒战,被吓住了……人变得无限小,心却变得无限大,藏在里面,找也找不见。凌子的流淌持续有数个昼夜,终于远去,消失,归于空寂。随即沉渣泛起,众声喧哗”。“众声喧哗”和“千个字”这类共时性的截面,是否当真是“外人”所能把握的一切?
二、乌托邦冲动:言语与饮食的“共时”
在乌托邦既有形式解离后的“众声喧哗”里,“外人”借助言语与饮食调试自己的存在状态。书中,陈诚不是在追寻历史真相,而是在不知失落何物、需要追寻何物的模糊状态中,于种种“正确”的形式间游离:陈诚对依然信仰革命的父亲而言太落后,对“划清界限”奔赴异国的姐姐而言太优柔寡断,对行动先于思考的师师而言太耽于抽象。“外人”的存在本身即是以局外状态检验既有结构的合理性,对于陈诚,这种检验落实为言语与饮食。罗兰·巴尔特认为,通过对日常生活组织形式的观察,可以推测社会中个人时间与集体时间的关联方式:“乌托邦的标志就是其日常性;或者还可以说,日常性的一切内容就是乌托邦:时刻表,饮食配方……”x书中,言语与饮食是“共识”横截面中最鲜明的记号。
类似《纪实与虚构》中的“我”,在陈诚的主体结构中,语音是前视觉、前主体的构成元素。婴儿陈诚的蒙昧意识中起先有几种孤立的语音,“渐渐地,互相渗透,融会贯通。就在语音的更替交叠中,视觉的世界成形,有了初步轮廓”。多种异质语音“融会贯通”“更替交叠”,说明对于陈诚来说,言语的胚胎已然是一个多语而非单语的凝缩态,已然包孕了“南腔北调”“众声喧哗”的可能性。进入社会关系后,陈诚的语言杂糅着父亲的历史阴影。作为插队东北的上海知青,“他一直和尖团音以及四声做斗争,结果,普通话没练好,家乡话也不成了。于是,他常以明人徐渭的话自嘲:‘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但杨帆尽管“南腔北调”,却具备向外输出的能力和意愿。他始终相信“没有革命就没有我”,统摄性的单语系统异化了他的家乡话,却也是维持其言说欲望的“大他者”,陈诚则是单语系统崩解后在“众声喧哗”中选择静默的“外人”。
正是这个语言的外人让众声喧哗显影。陈诚被生长在上海的师师和从东北归来的姐姐左右牵起,“都是普通话,但语音却不同。为了互相靠拢,都修改了吐字吐词,听起来有些造作”。姐姐和师师吵架时,“炒豆子般的语音中,姐姐响脆的普通话显然占压倒之势”。对某种语言的习得亦是对象征资本的掌握。激进革命的语境中,姐姐求师师教自己上海话,“师师说:上海话有什么稀奇,最不上台面,我们班里有个北京转学来的小孩,朗诵、发言、演戏、叫口令,都是他!姐姐说:全国人民都知道,上海人把北京人也叫作乡下人!那是他们没眼界!师师说”。上海话“不上台面”,是由于普通话推广运动将方言反身构筑为民间的、前革命的。姐姐在批判大会上代表全连朗读因加入革命词汇而“拗口得很”的稿子,“操场上大喇叭里传出她的声音,在厂区上空回荡,字字响亮,真如古诗中的形容:大珠小珠落玉盘”,是近乎去内容化的声音操演。参与斗争时,姐姐对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等概念一知半解,但“唯因为不懂才有号召力……完全不明白什么内容,可是滔滔如洪水,直下三千尺……两军对垒,是实力博弈,也是气势较量”。陈诚的沉默更显示出象征性暴力(“气势”)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认知能力都不再必需,相反,正是能指的空洞使其成为象征符号的容器。
作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姐姐以言语(parole)而非语言(language)的方式去实践政治和哲学概念,概念之于她,是直接的身体经验和情动感染。无法掌握革命语言的“外人”则选择方言作为政治的回避之所。母亲回杨帆老家时发现,借助淮扬方言的顽强惯性,“这一众人,就像侥幸规避了时代的更替,从历史的接缝中遗漏,竟也能够自给自足,自生自灭”。杨帆的大哥本是上海交大船舶系毕业,却爱好扬州评书,满口方言,“似乎有意为之,格外夸张”,且“和时间脱节”。在插队环境中格格不入的“外人”老杨,凭借方言将母亲转换为“外人”,“因知道她不能与家人调和,索性退到那一边”。然而,“那一边”和“这一边”本是同一边,在母亲与杨帆家人对待官话/普通话/革命语言的不同选择之下,是对待语言的同样态度。他们皆以语言中的位置获得身体经验并确认自己的存在状态,只是前者通过普通话-革命词汇,后者通过方言-民间形式(评弹)。但对陈诚而言,语言与存在不再同构。
这一点可在陈诚与师师的对比中进一步明晰。同在后殖民语境中,《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自居为凝视客体以获得爱的幻觉,师师的英语对话则“是在假设的前提下建立交流,就是自信对方完全听得懂她,她也完全听得懂对方”,语言不再表意,产生意义效应的是交流的意愿本身,这在旁人看来滑稽而感动,“因双方的态度如此诚挚,流淌着真实的哀伤。谁知道他们哀伤什么,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哀伤什么”。如果说师师“不知道哀伤什么”,陈诚则是并不知道自己在哀伤。“多语者”和“多余者”往往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似的位置,正是“多余”使主体不得不以“多语”的方式来频繁地自我转译,而“多语”很可能对母语造成磨损,加剧了“多余”,以至于实际上的“多语(言)”者成为了寡言者。陈诚“不像姐姐开口早,他两岁了还不怎么会说话,可他有自己的语言”。当父亲与姐姐、姐姐与师师、父亲与胡老师明交暗攻时,陈诚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成为“语言的他者”,语言“通过它来寻找一个让自身从中消失的出口,或一个让自身得以反思的外部”。y
陈诚先是成为语言的他者,进而连他者的语言也放弃,其日常的乌托邦冲动由言语转移到饮食之中。母亲平反后,姐姐和父亲频频争吵,陈诚则寡言少语,“其实他有他的乐趣,那就是做饭”,“厨事给了他安宁,更有满足感”。陈诚的“一把刀”连接起父母双方的记忆,连接起上海、高邮、淮扬、山东、东北、纽约、爱尔兰,连接起革命年代、后革命年代与前现代,如此才有“千个字”。“一把刀”串联起不同的时间以及时间逻辑:黑皮吃螺蛳“嘬一颗,送一口饭”,是“古风”的遗留,这“古”则因上海包饭作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老杨老家的亲人做蛋饺、划鳝丝,“这地方有一股享乐主义空气”,但当嬢嬢带陈诚见老先生,点一客红烧小黄鱼配白饭,虽然“分明是过去的味道”,可这激进革命中的日常伦理也如俗话以“黄鱼脑袋”代指空无一物,“这‘空无一物’都吃净了”。“一把刀”引带人物在空间流转:炊事引人物走入北方,“从物种出产而涉及寒温带风土环境”,学会了“一口酸菜暖锅为首,煮着大棒骨,小鸡仔剁块,口蘑木耳黄花菜”的“一锅炖”。纽约饭局上,父亲由水土问题对比起爱尔兰难民与闯关东……食物是时空的凝结,亦是日常的乌托邦冲动的肉身化实践:单先生“说的菜谱,其实是人间世”。
王安忆在将饮食历史化的同时,也将历史饮食化。这似乎是共时性的极端呈现,历史变成了一股令人纯生成的、欲望化的美食洪流。历史如同分布不均的菜谱,取代叙述的是描写,接纳多元的形式是进食。这种共时性的历史似乎导向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如詹姆逊的警戒,“历史编纂学式的建构越成功——相信所有事物都只是碎片,相信存在与事实的关系强过它们与不再存在和尚未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可能的关系,相信现实存在是一个严丝合缝的网络,而过去(或传统)不过是现在的一种理性建构——这种情形在理性上也就越牢固”z。为了避免共识性的极端沉落、维持叙述的动力,便要穿过言语与饮食的洪流,回到历时与共时的交汇处,回到识别出历时与共时并为其赋予形式的“净化”与“真理时刻”,分析作为“外人”的主体如何诞生并获得姓名。
三、真理时刻:净化、认出与外人之“名”
“净化”借自安敏成对鲁迅小说结尾的分析,即“叙述者突然感到一种与小说中的苦难相悖逆的解脱感”,并通过对“净化”时刻的自觉揭示,“在小说中对自己的写作以及现实主义的整体方案进行了激烈的批判”。@7《一把刀,千个字》中频繁插入人物前史,插叙的结尾大多以“净化”时刻将历时与共时铆合。王安忆并非有意以悖谬的解脱感构造道德反讽,但重复的“净化”机制不免导向对净化之有效性的怀疑。和师师关系僵化,陈诚躲入现代文学诞生以来经典的“看风景”装置,隔窗看为面包排队的顾客,在间离中得到暂时的净化。如同王安忆的“窗户情结”@8,“净化”时刻以主体的非介入、非行动为前提。陈诚在夏令营独自离开食堂,“空着手走出,身后的光唰地灭了。在突然降临的黑暗中停了停,四边景物渐渐浮凸轮廓,抬头看,巨大的穹顶下,流星向纵深飞去,天空在升高”,然而这一“净化”发生在意识到“现在再做‘母亲的孩子’来不及了”之际,在个人从血缘关系、革命身份中脱序之际,也是人成为“外人”之际。
这套净化自我、衔接历时与共时的机制不只作用于陈诚这一“外人”,也作用于其他偶然占据“外人”位置的人物——外人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个位置。杨帆的家人对母亲礼貌而疏离,“她穿上大衣,悄悄出了院子,从夹弄上去廊桥,看屋顶上的炊烟”。时差如“成年人的魔术”,在“炫”与“虚无”的转化中使杨帆体验到了“净化”:“生物钟因循东半球的轨迹运行,四下里一片静谧,可听见夜的叽哝,那是由鼻鼾、耳鸣、昆虫的皮蜕、树叶子和纸屑摩擦地面、肌肤与肌肤的亲昵……交相呼应,回响共鸣。”
在“净化”时刻之外,还有“认出”时刻。在《匿名》结尾,老新落水后看到一个孩子“沿着苏州河,跑啊跑啊”,“他认出来了,那就是自己”。@9《一把刀,千个字》的“认出”时刻并未出现在濒死的极端时刻,而是“外人”将自己意识为主体的过程之一环。王安忆在小说中以水与镜展开自我与镜像之辩证:
水面盖满浮萍,有个小人影,走动起来,才知道是自己……一仰一俯,对望着,就像隔了千年万载。
合起相册,原样放好,推回抽屉,关上橱门……这间朝北的亭子间里倏忽充满姜黄色的夕照,人在其中,又像在远处,一个自己看着另一个自己。他很少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刻的客观性也转瞬即逝。光线变得平面,物体的三维变成二维,再成一维的线条,暮色降临。
陈诚试图由姐姐在冰面上几经反射的滑行身影、夜行列车的双层窗户上的侧脸追忆母亲,但姐姐并未继承母亲的相貌,“找到的全是父亲”。英雄母亲的形象从亲人的面容和照片转移到话剧院舞台、中学生作文、报告文学,在纪实与虚构之间,“他再也想不起母亲是什么样的”。众人都说陈诚像母亲,“结果是,他从此不敢照镜子”。陈诚通过自我消解否认了面容与自己相似的母亲,但“认出”的时刻仅仅被延宕,而不会被取消。结尾处,陈诚重回改造为艺术园区的钢厂,叙述与记忆重叠,“外人”被补全为主体。在这一刻,历时与共时的结构闭合,日常的乌托邦冲动被收拢入小说文本的形式中。
王德威提出,王安忆的“匿名术与微物论”能超越唯物主义机械二分法,“从匿名思考种种名相所带来虚妄与怅惘,藉微物解构机械唯物所曾物化的世界”#0。如果说《匿名》和《考工记》分别是匿名术与微物论的极致,那么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通过反复的“净化”与“认出”,使无名的“外人”自我识别为有名有姓的主体,虽然这一过程需要一部书来完成,虽然完成之后人物仍然是“语言的他者”,只能以泪水来代替匮乏的语言:“那里面的液体不晓得蓄了多少时日,又是怎样的成分,滚烫的,烧得心痛。”
与非行动的“净化”相比,“真理时刻”是“被冠以初始的自反性的整个运动,一种对于乌托邦过程本身的自我意识的降临”#1,它将“净化”时刻中叙述者的道德悬置、对现实主义整体方案的怀疑转化为朝向乌托邦的行动。“真理时刻”让作为“外人”的人物获得主体感,如“文革”之于姐姐有奇异的升华效应:“一九六六年的革命,在某个方面,不仅对这孩子,也包括许多悲观主义倾向,都有拯救的意义。它将终极问题拉回到现实中,无解变成有解,纯思辨变成可实践。”詹姆逊认为,乌托邦冲动寻求着确定自己的“真理时刻”,从而分解出并占有其特殊的乌托邦能量,“真理时刻的作用并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可以激进地否定它的替代方案的能力”#2。王德威认为“拟想‘人之初’的逆向冲动是王安忆近年创作的主轴”#3,其原因或许在于,后革命语境下,“再出生/出发”的可能性、“存在的源头”不再由“翻身”“时间开始了”许诺,个体的生理起源因此成为“真理时刻”的起点,并“激进地否定它的替代方案”。对于作者,小说开头与结尾的循环构成了叙述的动力;对于人物,人物起源与终点的闪回、闭合实现了对乌托邦过程本身的自我意识的降临,一种“外人”拥有自己传记的时刻。
《一把刀,千个字》中,次要人物的名姓有着直接而详尽的交代,如姐姐的初恋“大名栾志超,和当年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那个丑角同姓。按起绰号的常规,应叫‘栾平’,或者‘小炉匠’,可是却不,人们都称‘老超’。这个‘超’其实是那个‘操’,粗人的谐趣,也看得出大家不把他当外人”。正因不是外人,栾志超的名姓才得以细致交代。反观书中的“外人”们,父亲的姓名杨帆、姐姐的乳名鸽子均直至下半部才揭露,开篇明确出场的“陈诚”则显示着命名的不可能性:
这地方的人,叫什么的都有。诨号,比如阿三阿四;洋名,托尼詹姆斯;或者借用,也不知道何方人氏,只要和证件登记同样,证件的来路就更复杂了。陈诚,六○年代初生人,籍贯江苏淮安。在中文没错,换作英语却差得远了,“籍贯”这一栏叫作“BirthPlace”,出生地。可是,谁会去追究呢?外国眼睛里,中国人,甚至亚洲人,总之,黄种人,都是一张脸。
“外人”之名是中文与英文、黄种人与白人之间的占位符,是存在的零度。叙述者间或以“鸽子”“兔子”(“兔子”亦出现在《启蒙时代》中)指代主人公姐弟,但彰显亲密的乳名却反而具有疏离的象征义。这对姐弟没有排行,亦不是谁家的“囡囡”“弟弟”,而是两个动物、两个“非人”、两个“外人”,甚至互为彼此的外人。克里斯蒂娃将外人分为“冷嘲者与信徒”,前者是“中立之信徒,空虚之拥趸;不管是故作强硬还是涕泪交零,他们的幻想永远是破灭的;他们不一定自认失败,却往往成为冷嘲者中的佼佼者”。后者则“超越着:不是在从前,也不是在当下,却是在彼世;他们所怀有的激情诚然永不能满足,却根深蒂固,向着另一片始终被允诺的乐土——某种职业、某场爱情、某个孩子、某种荣光。他们是信徒,有的在成熟之后,变为怀疑论者。”#4
若姐姐是由极端信仰转化为极端怀疑的信徒,弟弟便是“在那些不复存在的和永远成为不了的之间无所适从”的冷嘲者,是“反追寻”的实践者,是“在本原与奔逃之间:一道脆弱的界线,一种暂时的平衡”。#5做饭的是他,但“做厨子的往往缺乏食欲”;阐释饮食美学的是舅公和单先生,是展开“饭局战争”的读书会诸众,而制造了宴席这一共时截面、让不同的历时体系进入话语斗争的他却往往沉默,以此相对化自己、相对化他人,在他人深陷历时的单一价值牢笼时从中脱身。“东主或许有些金银细软,外人却倾向于认为,拥有传记的只有他自己。”#6已有论者指出,王安忆偏爱让人物冒险#7,但相比“冒险”这一经典类型,《一把刀,千个字》或许更接近“外人”的传记。传记并不必然要求惊险和奇遇,而是指“生命中的行为都能算作事件,因为它们必然包含选择、意外、断裂、适应或计谋”#8。
拥有名姓的是栾志超式的他人,而拥有传记的是“他”这个“外人”。在反追寻的记忆动力中,在历史的单一因果律与共时的多元决定的缝隙,外人“仍有对存在的确信:确信自己能够以一种温柔却晦暗的镇定,在自我中安顿——这种镇定一如潮水中的生蚝”#9。王安忆也是如此抒情地写及“软兜”,一种和“鸽子”“兔子”一样处于“外人”状态的生命。在新大陆,“软兜”无处寻觅,而在旧大陆,它最可能的近亲鳝的命运却是被千刀万剐制成鳝丝,但即便不得不承受历史的伤痕,它却能以“针似的,在幽微中穿行”,在“历史的阴面”书写自己的传记。
【注释】
a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关于〈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b有论者认为,《一把刀,千个字》表明王安忆突破了创作瓶颈,“在此前的三部长篇小说《天香》《匿名》《考工记》中,王安忆似乎已经放弃了先前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想象,开始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拓展与实验”。王振锋:《历史缝隙中的生命絮语——论〈一把刀,千个字〉》,《当代文坛》2023年第2期。
cefhrswz#1#2[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6页、6页、235页、122页、123页、123页、123页、235页、235页。
d#0#3王德威:《请客吃饭,做文章——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gt@7[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21页、80页。
i“我要求小说对话,严格讲不是‘对话’,而是人物的说话……因小说本来是间接的传达,即便用分行的对话依然缺乏直观的生动性,将它作叙述的处理倒有一个旁观的视角,更有意思些。这也是逐渐形成的方式,曾经我也是直接呈现对话的,后来就厌了,书面的对谈总也比不过舞台上实景实地实人的有表情。”王安忆:《王安忆谈〈一把刀,千个字〉》,“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16日。
j“要与时间并进地复述显然不能够,所以只能追忆,承认事情发生在过去。我以为,这是作者试图将时间打回原型的总体规划,也是首要条件,放弃和时间赛跑。其二,放弃情节的紧张度,代替以大量的细节,将情节在倒溯中还原于时间的序列,事实上,时间还是在变形,对抗变形也许是徒劳,但却产生预期之外的结果。”王安忆:《小说的载体——浙江大学文学讲稿》,《江南》2021年第2期。
k陈婧祾:《异乡的孤儿——〈一把刀,千个字〉和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上海文化》2022年第1期。
l参见[美]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225页。王德威提出“原乡”与“时序错置”(anachronism)和“空间位移”(displacement)有关,“原乡”不是对原来故乡的写实,而是作者在原乡图景丧失后对故乡的后设追溯。
m“胡老师到底抢上话来:家庭内部的事情,外人不得而知。我是外人吗?你的意思,我是外人了!”“现在,他只能保持中立,做局外人。其实呢,他就是局中人。”《一把刀,千个字》发表于《收获》2020年第5期,单行本分别于2020年、2021年由麦田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nop#4#5#6#8#9[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我们自身的外人》,陆观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7页、8页、16-17页、7-8页、11页、11页、13页。
q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不一一作注。
u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v丁玲:《水》,《丁玲全集》(第3卷),张炯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x[法]罗兰·巴尔特:《萨德傅立叶罗犹拉》,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y[法]莫里斯·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58页。
@8“窗户似乎是潜伏在我心中的一个情结”,窗内的封闭空间与外界的联系“是局部的,带有观望性质,而不是那种自由的,可走出走进的联系,所以它决不以门的形式出现,而以窗的形式”。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9王安忆:《匿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1页。
#7“写冒险,写冒险中的经历,是王安忆钟爱的小说‘模型’,‘模型’是她本人的说法,指的是‘叙事的基本构成法则’。这个模型甚或还能装下想象中的冒险,或者就是想象在冒险,以想象建立的叙事在冒险。”参见陈婧祾:《异乡的孤儿——〈一把刀,千个字〉和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上海文化》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