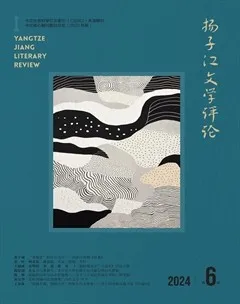革命、身体与日常生活
在王小波去世之后,关于他的作品与思想的讨论不断,王小波之死成为1990年代重要的文化事件。1998年,《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出版,其中收录了15位人文学者对王小波的评论,许纪霖从王小波推崇欧美经验理性出发,指出其“消极自由”与反乌托邦立场a;秦晖认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小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b这些学者的观点对后来的王小波评价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着王小波成为1990年代自由主义文化英雄谱系“陈寅恪、顾准、王小波”c中的一环;除此之外,1990年代的大众媒体也极力渲染王小波“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房伟指出:“正是由于媒体的命名,‘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才真正成为一个公众话题。而同时,传媒借‘自由主义作家’的塑造,也在不断完成‘自我定位’。”d无论是学界的定位还是媒体的宣传,对王小波自由主义或消极自由的推重往往同时意味着将其置于革命的对立面,并强调其超历史的倾向。但是,在王小波小说与革命之间具有复杂而紧密的内在关系,如果仅在立场和观念层面对这层关系进行揭示,则将问题简单化了。王小波的美学世界在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断裂之中形成,对其小说言说之复杂性的揭示必须回到革命、回到历史的断裂之中。
本文从空间美学的角度切入,揭示王小波小说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将从叙事时空结构、身体空间和日常生活三个方面展开,力求揭示王小波叙事的多重内涵,剖析王小波在历史断裂之中对过去与当下的言说如何开拓出自己的空间美学。
一、都城:神圣的二元性
革命是王小波小说世界永恒的想象力来源,其对革命之权力运作模式进行抽象与再直观,这构成小说空间的元结构,贯穿古代都城、革命北京与后革命北京,形成对“神圣”之形而上意义的解构;而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哺了“革命北京”的内涵,在洛阳、长安、北京的古今交叠之中,“神圣”作为挥之不去的乡愁,指向了革命中“人”的身体实践。
洛阳、长安、北京古今同构,在时空中重叠,充满了中心感和神圣感。都城的“神圣”被反复强调,洛阳“是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升起的地方”e,长安“大过了罗马,大过了巴比伦,大过了巴格达,大过了古往今来一切城池”f。对空间之“神圣”的反复强调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反讽,同时,王小波对“神圣”背后的权力机制的揭示又使得神圣空间被深度解构。
神圣都城是极端规整的,城市的整体和局部都是“方方正正”的,从外而内,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嵌套结构——“方方正正”的大空间不断被分隔为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小空间。城市的边界非常清晰和稳定,戒备森严,城市内部也有明确的分隔,并且这样的分隔不仅仅是空间位置上的区分,还有等级高低的区分,例如《红拂夜奔》中的洛阳城就有“uptown”与“downtown”之分,再如《寻找无双》中的酉阳坊“是个声名狼藉的街区”,导致“长安城里的诸君子根本就不承认城里有这一坊,有这一区”g。这是一个在权力管控之下的异化空间,它极端规整,各部分的区隔和功用鲜明,内部的管理与运作揭示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空间文化建构和运作逻辑,是统治观念和生活理念高度现实化的空间。
在“方方正正”的都城中,人也被空间形塑,呈现在小说中的不仅有精神上的驯服,最引人注目的是身体的变形,其中充满极致的想象力:
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长安城是这么一个地方:从空中俯瞰,它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在大院子里,套着很多小院子,那就是长安七十二坊,横八竖九,大小都一样。每个坊都有四道门,每个坊都和每个坊一样,每个坊也都像缩小了的长安城一样,而且每个坊都四四方方。坊周围是三丈高的土坯墙,每块土坯都是十三斤重,上下差不了一两。坊里有一些四四方方的院子,没院子的人家房子也盖得四四方方。每座房子都朝着正南方,左右差不了一度。长安城里真正的君子,都长着四方脸,迈着四方步。真正的淑女,长的是四方的屁股,四方的乳房,给孩子喂奶时好像拿了块砖头要拍死他一样。h
王小波对异化的空间与人的嘲讽是直露和触目惊心的,他直言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在对古老都城的异化进行揭示之时,其空间原型并非那个古代皇权统治之下的神圣都城,而是现代文明之中的城市样态,王小波将对现代城市的批判嫁接于对古代都城的想象之上。“四四方方”的古代都城的原型是处于全面管制状态之中的现代城市空间,具有全景敞视的结构,因此是“灰色”“窒息”和“缺少生气”的。更进一步说,这种巨大统合性和意识形态性基于高度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特质。这一点可以在王小波杂文中找到明晰的表达,《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文将北京与美国城市并置,王小波赞同意大利朋友“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的看法:“北京城里到处是现代建筑,缺少历史感。”他不无惋惜地描述小时候的居所郑王府被“四四方方的楼房”占据,指出“郑王府的遭遇就是整个北京城的缩影”i,由此呼唤真正的人文景观。《对待知识的态度》一文追忆小时候“住在北京的旧城墙下”,在历史里看到超越“现代”的无限可能性。j
这一基本构造一直延伸到未来世界,《2015》《2010》《白银时代》《未来世界》等小说所构建的未来城市的样态都是灰色北京城的延展,“漆黑的烟”和“雾气蒙蒙”之下是“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k,空间是高度同质化的,正如那个“白银时代”的谜底所揭示的那样:“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会同此凉热,就如一个银元宝。”l现代城市几乎是设计与规划图的直接现实化结果,形成一种没有任何深度而只有“欢快的清晰感”m的空间。当一切都归于同质化和单向度,人不再有痛苦和忧虑,仿佛幽灵一般飘浮在城市上空。这些对未来世界的构想受到马尔库塞的影响,单向度社会来源于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体化和内在否定性的丧失,其空间表征与王小波对古代都城的构想重叠。
除了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现代城市的内部空间还具有对立和等级秩序,这也构成了王小波小说中古代都城的特征。福柯梳理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空间的建立,指出在现代空间中,生活受制于一定数量的对立,例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对立,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之间的对立,闲暇活动空间与劳动空间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对立,仍受到不言而喻的神圣化的控制。n空间结构的扁平化与内在空间的对立相辅相成,是现代空间之神圣化的表征。通过古今同构的叙事,王小波在多个时空中对这一结构进行直观呈现,揭示了权力运作的永恒性,戳穿了“神圣”背后的权力骗局,通过反讽实现了对空间的“去圣化”。
如果说,古今同构的叙事结构使得现代城市的病症被传递给了古代都城,并延展到了未来世界;那么反过来,本真的前现代神圣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分享给了现代都城北京,尤其是“革命北京”。前现代神圣空间之所以具有本真性,在于其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其抽象与现实之间具有同一性。这一神圣空间是以直觉而非理性建立,它将社会抽象的物具体化和现实化,统一了现实与精神、自然和社会,处在其中的人将自己的城市“体验”为更宽广的东西,成为世界和大地的一部分。o因此虽然它的构造也呈现出一定的规整性,但是这一结构反映的是人真实的生活体验,而非规划者创造的便于统治的抽象真理,而后者恰恰是现代空间的病灶。前现代的神圣空间由人的直觉和体验构成,不呈现出一种与现实割裂的抽象真理,在王小波小说中,“革命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正展现出这一特质,但是,其神圣也不在物理空间或空间表征中呈现,而是在“人”之中呈现,指向人的身体实践,人的空间实践构造出了这个神圣空间。
“革命北京”之中的“我”具有绝对的浪漫主义情调,发明投石机,铸造防御工事,观看战争,想象自己是古希腊的勇士,带着长矛和铠甲参与战争,带有对革命的天然的激情和浪漫的想象。“革命北京”成了发明创造、张扬生命的重要场所,“我”也构成了这个神圣空间的一部分,个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正如《红拂夜奔》中李靖“有几分洛阳城”p一样,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虽然这种神圣几乎立刻便被“一个人被长矛刺穿”的切实死亡以及“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为他们而死,不觉得有点肉麻吗?”q的诘问所解构,但是这些战斗在叙事文本中所形成的张力却难以抹消,尤其是在几近梦幻的“革命北京”与缺少生气的“后革命北京”的对比之中,“神圣”几乎成了一种乡愁或隐或现地在文本中流动。剥离了异化的、非理性的和近乎暴行的革命沉醉,对“人”的本真性激情进行提纯,最后可得到一个浪漫主义的神圣自我。而作为权力骗局的革命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剥离,正在于叙事脱离了线性的历史时间,在古今的时空交叠之中构造出了更广阔的言说空间。
古今同构的叙事空间并非同质化的古今体验的叠合,其中的错位和差异性为主体的多重想象、情感和立场提供了言说空间。由此,革命的“神圣”便形成了二元性,其一是作为“革命北京”的骗局和幻梦,王小波对其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伴随着对空间之神圣的拆解,去圣化的过程携带着启蒙的命题,使得王小波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讽刺小说”;其二是由浪漫主体所构成的本真性的“神圣”,蕴藏在主体的空间实践之中,浪漫主体与同质化的空间之间不形成一种剧烈的对抗,而往往在传奇式的叙述之中,以游戏的方式行走。
在神圣空间的二元性之中,可以看到叙述主体的复杂性,对理性的追求与人的价值的歌颂接续了1980年代的启蒙主题,伴随着对权力的抵抗和消解,张扬人的自由与个性。但同时“革命北京”的记忆与浪漫主义也以一股潜流融合于其中,几乎成为后革命时期的乡愁,而这一层乡愁从线性的历史之中跳脱出来,指向历史的深处中“人”的重影。
二、“神奇”中的身体空间
革命的“神圣”作为潜文本,一方面随着空间表征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而被解构,另一方面在人的身体实践中被彰显。而“神奇”作为革命之“神圣”意义的世俗化和具象化,以一种景观的方式呈现于小说文本之中,它与荒诞、迷信、想入非非、幻想、有趣、诗性、浪漫等王小波精神世界中的关键词都不无关联,它意指含混、表意模糊,因此建构起有关革命意蕴的多维空间。
“神奇”首先意味着迷信,从杂文到小说,“药片穿瓶”“气功”“注射公鸡血”“祖传的秘方”“超声波哨子”等皆为王小波无情嘲讽和尖锐批评的对象,这些事例的产生或出于无知,或出于对科学的误认,或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或出于时代的政治环境,王小波的批判背后是对科学的崇尚和对理性的追求。《革命时期的爱情》就是一部关于“神奇”的小说。革命中处处有神奇,“每一天都是愚人节”r,大炼钢铁、仿佛上古神话的武斗场面与紫色的天空共同构成了童年的超现实幻境,儿童视角将革命时代集体的非理性状态以一种疏离而又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似水流年》中有关于发酵新鲜大粪的叙述:“我小的时候,曾立在坑旁,划着火柴扔进去,粪面上就泛起了蓝幽幽的火光。在我小时,觉得这蓝幽幽的火十分神秘。在漫漫黑夜里,几乎对之顶礼膜拜,完全忘记了它是从大便中冒出来的。”s这几乎可以作为“神奇”的一个隐喻,建立在非理性之上的“神奇”是一个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来的古怪世界,这个古怪世界产生“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t,让人觉得无比神秘,更让一些人错认为是神迹或光明未来的前兆,但它既不是美的,也不是正确的,它有毒且终究会破灭,然后展露出其最不堪的实质。“神奇”面目可憎却层出不穷,无论是小说中的古代世界或革命时代,还是杂文所对接的当代,“神奇”意味着理性失去、智慧不足或欺骗,在某种程度上与国民性相关,王小波对此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科学和经验理性,在这一点上他承袭着“五四”传统,又与1980年代的启蒙主题合流。
王小波对“神奇”的描绘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伤痕”的特质,想入非非和寻找神奇并非仅为迷信和狂信,它在某种情况下与人糟糕的生存境况相伴而生,它的重复与无意识构成了精神创伤的表征。《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神奇,对王二来说,神奇在小高炉中;对于爸爸来说,神奇就是在被批判的时候幻想自己“不但再不受批判,还能去批判别人”u,人们“为了寻找神奇而打仗”v,每个中了“负彩”的人都在狂想自己能中“正彩”。《红拂夜奔》中的李靖始终在逃离、发明创造和想入非非,但是他的创造力也在不断地被物化,他亲手建立的长安城最后却成了囚禁他的牢笼,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浪漫主体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匮乏和压抑所带来的异化了的冲动和需求最终不能够建筑一个坚实和自由的主体,它只能不断地陷入重复和循环,成为既存制度可悲的伴生物。王小波曾在杂文中评价阿城的《棋王》中的故事:“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w王小波对于下棋和那本被人“看没了的”《变形记》的回忆,共同拒斥了此类“神奇”中所蕴含的浪漫和自由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其中有任何生命和美学,他选择在“伤痕”的层次上去叙述和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伤痕”之下,在“神奇”退却之后,生活的悲剧底色又显现了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负彩,没有正彩”,在“神奇”烟消云散之后,“我和别人一样,得爱我恨的人,挣钱吃饭,成家立业,养家活口”。x“神奇”已经不再面目可憎地站在科学和理性的对立面上,因为当它被解构之后,生活还是一片荒芜,理性的解放理应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实际上并没有,长大只意味着接受和承担无数“得爱我恨的人”这样的事,有趣被超越了,变成了庄严凝重和思无邪。因此,“神奇”不再是那个亟待被解决的问题,它成了悲剧命运中的一个滑稽小丑,面具后面是沉重的人生。
由革命世俗化呈现的“神奇”景观是迷信、伤痕和悲剧人生的幻梦,王小波在其中不断地进行否定:以理性否定迷信,以创伤否定浪漫,最后又以悲剧人生的本质否定理性解放之后的光明。阿多诺认为“真理性内容不是直接可辨的”,因此“艺术品只有通过确然否定的中介才会是真理性的”y,否定能将人解放到文学语言的自由中来。可这是否就意味着在王小波的文学世界中一切都在否定中走向了消解,最后进入了虚无的自由呢?恐怕并非如此,王小波作为叙事主体,他身上有难以抹消的浪漫特质,他在革命的“神奇”中也提取了纯粹的生命特质,其中生与死作为辩证的两面,实现了悲剧人生的美学救赎。
《黄金时代》将“神奇”的这一维度呈现了出来。陈清扬“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虽然活了四十多岁,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z,她身在革命中,却对革命一无所知,她与王二做爱并被定性为“破鞋”,但她对性爱一无所知,因此她“相信自己是无辜的”,然而小说意味深长地结束在意识的回归:“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7因为无知,所以陈清扬的世界是“神奇”的世界,她的无知并非是理性的缺位和迷信,而是一个前理性和前意识的状态,代表尚未走出伊甸园的生命阶段,生命树统治着这个前理性的世界,其中充斥着纯粹的、完整的神圣力量,这是一个本真的身体空间,宇宙和人类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性和整体性;走出伊甸园之后,整个世界便由智慧树来统治,理性割裂了人、神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柏拉图意义上的“灵魂/肉体”的二元论形成,身体被置于更为低等的层面。因此,一无所知的陈清扬没有“罪孽”而只拥有“神奇”,“斗争差”等对其不形成压抑、干扰、欺骗和打断;但是当她的意识来临,她便来到了法的机器面前,这个机器依靠精英与统治者制造出来的抽象真理而运作,她须被处以“五马分尸”,但实际上那个宏大的历史机器只是在空转,没有人能真正对此负责,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够惩罚她。《黄金时代》就在这样的地方结尾,黄金时代的结束是走出伊甸园,这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恰巧是理性带来的生命的断裂和身体空间的坍缩。
死亡是这个本真的身体空间的另一要素。“贺先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我想在他身上了解什么是死亡,就如后来想在陈清扬身上了解什么是女人一样。”@8《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与《似水流年》中的贺先生正好代表着身体辩证统一的两面,前者代表着生命的冲动,关联着性欲,后者代表着死亡,二者在革命的经验之上开拓了一个身体空间,一个真正的“神奇”空间,王小波的整个美学空间都由此生发。房伟认为作为贺先生原型的柳湜之死“终结了王小波的顽童梦”@9,是其革命理想幻灭的象征,同时王小波写贺先生死亡之后直挺的性器官,是用一种死亡的狂欢解构悲苦和沉重。这一观点只看到了贺先生之死在线性历史层面上的否定和中断,却没有看到死亡作为生的另一面的开拓性,直挺的性器官正是“还有很多的生命力”#0的象征。在贺先生之死中,“神奇”不再是集体无意识的革命景观,而成为了一种生命冲动。童年王二想要像贺先生一样光荣死去,于是给自己安排了很多诗意的死亡,“想到这些死法,我的小和尚就直挺挺”#1,这正揭示了死亡冲动之中所蕴含的人本真的生命能量,这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向死而在”。在贺先生死亡的一瞬间,一个纯粹的身体空间便展开了,历史的暴力被超越,人的本真性存在得到确证。
作为革命的世俗景观的“神奇”是复杂多义的,反映了革命在王小波文学世界中的暧昧位置,它既代表着狂信,又承载着精神创伤,同时是悲剧人生的伴生物。但是,王小波在“神奇”中也发掘了身体的可能性,身体空间内嵌于革命的历史之中,又超脱了线性历史,达成了真正的、美学意义上的神奇,实现了对迷信、狂信与悲剧人生拯救的可能性。
三、历史断裂之中的日常生活
前文对革命的“神圣”与“神奇”进行剖析,试图指认出王小波是如何在革命的历史之中开拓出自己的美学空间。本节将聚焦于王小波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探究他如何在对物的凝视之中建立一个真正的言说空间,形成对历史“伤痕”的回溯。
王小波小说的虚构世界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伪历史写作”之上,利用历史文本的外在形式和治史的方法来进行虚构创作,并在叙述中穿插对叙述本身和历史写作的议论,不断对虚构身份和创作过程进行暴露,展现出“元小说”的特征,或按照戴锦华的说法,这是一种“元历史”#2的叙述方式。这一叙述方式并非只存在于“唐传奇新编小说”中,在古代、现代和未来题材的小说中普遍存在,以一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真实交织在一起:在“唐传奇新编小说”中,对古代世界进行“伪历史写作”;在以现代为背景的小说中,将人物的经验历史化,由此形成对其个人历史的“伪考证”;在写未来世界的小说中,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如何考古现代生活的遗迹。这种“伪历史写作”将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纤毫毕现地呈现了出来。
宏观上来说,小说的虚构空间建立在对“长时段”#3历史风貌的呈现之上,也即对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等的描述上,叙事者自言受到了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对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等的描述之所以与“伪历史写作”的创作方式密不可分,而并非纯粹的环境描写,正因为这一层建构伴随着对叙述过程和主体的不断暴露,指向对文学和历史的思考。《红拂夜奔》新编“风尘三侠”李靖、红拂和虬髯公的故事,小说以夸张和重复的方式叙写洛阳和长安晴天的尘土、雨天的泥水以及所有土坯的建筑,这可以看作是王小波“伪历史写作”的一个极佳例证,小说以还原真实生活面貌的方式剥除了“风尘三侠”之“风尘”的修辞性及建立在修辞性之上的历史和神话建构。
从微观上来说,小说建立了一个丰沛的日常生活文本。衣食住行等私人生活通过“伪考证”的叙述方式被呈现:“他们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只是:当时烧煤,烧得整个天空乌烟瘴气,而且大多数人骑车上班。自行车这种体育器械,在当年是一种代步工具,样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两个轮子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钢管架子,还有一根管子竖在此架子之上。”#4除此之外,叙述者对物具有极大兴趣,除了对虚构名物的烦琐说明,还有对各种发明创造的细致描摹。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触可感,建立在一种朴拙的、带有形式创新意味的繁复叙事之上,接近年鉴学派的历史叙事,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文学的语调汇合。
日常生活的叙述将一切历史建构还原,最本真的人也被用这样的方式展露出来,终极的“真”藏身于日常生活之中。王小波小说中的日常生活通过实证的方式被呈现,虽与科学主义的态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却不是求真的,它借用了一种魅惑的“真”的方式来建构一个虚构的世界。因此这个日常生活并非在实质上指向历史的真相,也并不仅仅形成对被建构的历史的反讽,而是借助日常生活叙事形成一个没有确定指意的美学空间。而这正因为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丰富的和空间化的,是身体实践的场所。如果不能洞悉这一点,那么王小波文学世界中性和生命的张扬只能在工具论的层面上浮现,再次回到了启蒙主义的“强权/反抗”的命题之中,而显然王小波的写作超越了这一层次。
黄平指出王小波最终将历史抽空,通过反讽走向了“虚无”,在无限否定之中获得了“脱历史”的自由。#5看起来的确如此,因为毕竟那个最终的“真”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虚构的,王小波并不惮于暴露这一点,可是问题在于,他真的走向了虚无吗?若想解答这个问题,须回到王小波写作的语境之中。
革命时代的体验常常是无意识的,革命时代的荒诞是对非理性世界的直观呈现。传统意义上的经验往往来自于连续性和重复性的刺激,但是革命时代的剧烈变动和宏大事件降临到微观个体身上,带来了一种不可理解性,这种不可理解性来自意识的防范,以防止令人厌恶的刺激的扩散,将刺激转化为无意识,于是人就丧失了意识的完整性,变得对世界冷漠和疏离。因此,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呈现出儿童视角的冷漠和疏离,面对在武斗中被长矛刺穿的人,王二心里想着“瞧着吧,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6,这种冷漠不仅是儿童的特质,而且是借用儿童来呈现出整个时代的人的状态,“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也是前语言和前意识状态的象征。
革命时代之后紧随着后革命时代,令人目眩神迷的现代性经验介入,历史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可吊诡的是,在工业化和骤然变化的时代,人在“震惊”中再次陷入冷漠之中#7,王小波看到了大众文化与工业化所带来的空间的同质化与人的异化。由此,现代性体验与革命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合流。
王小波小说叙写了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风貌,而其整个创作生涯就处于他所呈现的革命与后革命时期的断裂之中,在此间,历史的创伤尚未得到足够的言说,更多的问题又浮现出来,历史的创伤、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的症候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社会与文化生态。杨小滨富有洞见地指出“伤痕文学”的无能,创伤的无意识是主体与客体间的错连,因此历史的暴力具有“事后性”——在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感知,而在事后涌现。“伤痕文学”企图直接展示伤痕在历史背景上的苦难,想象一种意识对无意识的调和性疗救,它对创伤的呈现缺乏间距,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形态的同构而成为暴力的同谋。而先锋文学迫近了精神创伤的心理状态,因此形成了比“伤痕文学”更具效能的暴力叙事。#8
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日常生活写作的必要性,王小波通过对微观之物的凝视,将其客观化为一个生活世界及其中的各种物象,由此,日常生活并非一个理性主体所呈现出的具有直接同一性的世界,它内里是本雅明所谓的“星丛”一般的时间,能够召唤出异质性绵延的非意愿记忆——意识的碎片。这就迫近了精神创伤的心理状态,形成了对历史现场的“不可理解性”的再度体验和触及,构成一种更具效能的言说模式。
此外,在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历史断裂之中,革命的创伤与现代性的“震惊”体验交织,革命的集体无意识与在新的权力结构之下现代生活的异化重合,日常生活是“伤痕”的言说之地,亦为同质化和异化的现代生活的救赎之地。列斐伏尔将“瞬间”视作日常生活的拯救,它的革命性在于以人的身体为载体,跳脱出线性的时间,打破诗性与生活的僵硬界限而解除日常生活的异化,使日常生活获得解放。而更重要的是,诗性瞬间孕育于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能脱离于或外在于日常生活而存在。由此,我们可以再回到王小波杂文之中对人文景观的追忆:
我在教育部院里住过很久,那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傍晚时分,燕子在那里表演着令人惊讶的飞行术:它以闪电般的速度俯冲下来,猛地一抬头,收起翅膀,不差毫厘地钻进椽子中间一个小洞里。一二百年前,郑王府里的一位宫女也能看到这种景象,并且对燕子的飞行技巧感到诧异——能见到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9
“历史感”的建立来源于无数个“燕子闪电般钻入小洞”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诗性瞬间,它能够关联起和召唤出无数历史的意象和瞬间,形成一种异质性绵延。王小波正是将现代生活得到拯救的希望寄托于日常生活内在蕴含着的瞬间之中,他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0此句的真正内涵即在此。“诗意的世界”超越于“此生此世”的日常生活,但是它又内在于其中,这也就是为什么“长安城”与“革命北京”“后革命北京”在叙事时空上永远是同构的。
由此,在历史断裂之中,日常生活写作同时实现了对“伤痕”的言说,并在新时期的经济浪潮中开拓出了一个美学空间,叙事实现了双向的救赎。
【注释】
a参见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王毅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1页。
b秦晖:《流水前波唤后波——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命运》,王毅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c参见朱学勤:《1998年关于:陈寅恪顾准王小波》,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20页。
d房伟:《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ep王小波:《红拂夜奔》,《王小波全集》(第4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75页。
f王小波:《舅舅情人》,《王小波全集》(第8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gh王小波:《寻找无双》,《王小波全集》(第5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36页。
i王小波:《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王小波全集》(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j王小波:《对待知识的态度》,《王小波全集》(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kl王小波:《白银时代》,《王小波全集》(第7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12页。
m[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12页。
n参见[法]福柯:《不同的空间》,[法]福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o参见[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59页。
qs@8#0#1王小波:《似水流年》,《王小波全集》(第6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155页、106页、113页、136页。
r王小波:《积极的结论》,《王小波全集》(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t王小波:《积极的结论》,《王小波全集》(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uvx#6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王小波全集》(第6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218页、219页、205页。
w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全集》(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y[德]阿多诺:《美学理论》(修订译本),王柯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94页。
z@7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第6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43-44页。
@9房伟:《王小波传》,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79页。
#2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王毅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3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活力(代译序)》,《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ii-iv页。
#4王小波:《未来世界》,《王小波全集》(第7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5黄平:《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7关于“震惊”理论,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3-179页。
#8参见杨小滨:《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反讽》,愚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1-59页。
#9王小波:《北京风情》,《王小波全集》(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0王小波:《万寿寺》,《王小波全集》(第3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