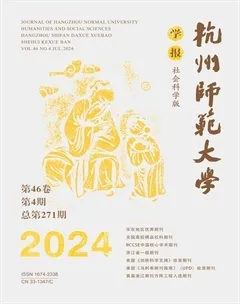重审技术自由主义:源流、发展与矫正
摘 要:通常以为,信息技术革命具有自由市场的灵魂,技术自由主义则是对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但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文化内涵的重构,一种由市场主导的技术自由主义经济叙事才被发明出来。这一叙事要求国家对数字经济领域采取“非监管”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经济上服务美国科技公司的全球扩张,政治上支持美国价值文化的世界传播。同时,技术自由主义也会导致经济分化和不平等、社会分歧和政治极化等问题。面对技术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美国出现了矫正困难的情况,欧洲则可能走向技术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相对而言,中国综合利用多种法律政策工具,形成了一套务实的做法,较好地平衡信息技术领域中个人权利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技术自由主义;数字经济;非监管原则;美国;法律矫正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4)04-0088-09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4.04.009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重提互联网自由议程,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在数字领域的政策转向,旨在争夺全球数字产业领导权与数字规则制定权。然而,要想深刻理解美国建构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首先应当廓清互联网自由政策的真实意涵,揭示技术中立背后的价值负载。其中,技术自由主义既是互联网自由原则的思想灵魂,也是理解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进行话语建构的锁钥。目前,各类研究聚焦于美国具体的施政举措居多,对于技术自由主义思想的本体论考察尚不充分。本研究旨在从技术自由主义的概念源流出发,揭示美国如何建构一种由市场和技术统治的数字经济秩序,并以“非监管原则”的政策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中国和欧洲在受容后,又是如何对其进行矫正的。
一、国家退场:技术自由主义的源流
技术自由主义是一个由古典自由主义、反主流文化、战后控制论和网络乌托邦主义建构而成的思想混合体,这一词最早用于形容美国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功经验。1998年美国国会对微软公司提出了反垄断指控,比尔·盖茨在司法听证会辩护道,“信息技术革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应归功于政府对该行业的放松管制,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世界,由市场做出的决策比国家做出的决定更可取”[1](P.9)。此后,技术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专指网络空间对国家监管的排斥和抵制。
(一)信息技术的文化内涵:从统治机器到解放工具
一般认为,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硅谷的程序员将“去中心化”和“个性化”的反主流文化理念应用于信息技术之上,由此赋予网络技术“自由”“平等”的文化价值意涵。但是,在反主流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并未把信息技术当作建立自由平等社区的手段,而是将其视为政治家和资本家控制社会的工具。一方面,彼时美国的思想文化界,正弥漫着浓厚的“技术悲观主义”情绪。无论是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所说的“技术社会”,还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新工业国》中提到的“技术结构”,抑或是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中强调的“技术统治”,无不在质疑技术发展的合法性。技术社会学在传统上有三大流派,包括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现实主义,彼时技术决定论在美国的影响较大。参见余成峰《法律与自由主义技术伦理的嬗变》,《读书》,2021年第3期,第70页。他们不仅将技术视为战争压迫、社会不公的原罪,甚至主张像当初抛弃上帝一样,对科学袪魅,回到前工业时代社会。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科技让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但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的激情也在机器的光芒中消失殆尽,个人的主体性开始丧失。[2]换言之,工业时代的社会已经成为一台无情的机器,生活其中的人都成为了提供经济生产的燃料。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64年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们高喊“我是加州大学的学生,请不要折叠、弯曲、旋转或伤害我”的游行口号,表达着对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担忧,不愿成为现代技术官僚机器上的齿轮。[3]
此外,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先前主要工业国家所提倡的技术专家统治(Technocracy)开始变得不再流行。[4]其中,反主流文化运动正是为了塑造一种与军工复合体的社会结构相对立的思想文化。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说法:“反主流文化史对冲动、探索想象世界以及免于束缚之名追求多种享受的一次革命。它自称‘敢作敢为’,要反抗资产阶级社会。”\[5\](PP.451-452)但是从结果来看,反主流文化的大量元素却被其反对的力量所吸收。具言之,信息技术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到反主流文化运动价值载体的转变,是由三个历史条件共同促成的。
第一,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为信息技术的文化内涵开辟了新的解释路径。[6]事实上,由信息技术建构的统治模式,并非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严格等级秩序,而是一个权力高度分散、人们相互配合协作的民主社会。这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实验室以及冷战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工程项目中,科学家、士兵、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打破了官僚主义的无形壁垒,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了合作。所以,“控制论”中强调的网络化合作本质上也是反军工官僚主义的,与反主流文化观念相契合。
第二,科技资本重塑信息技术的文化内涵,以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为代表的文化实践者,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乌托邦愿景与信息技术联系起来。布兰德以《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为宣传载体,提醒读者可以在不离开工业社会的前提下,改变当前的现状,强调人们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就有能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计算机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摆脱军工官僚体系的压迫。[7](PP.41-69)
第三,计算机的政治隐喻发生变化,过去房间大小的计算机被视为帝国统治世界的机器,而小型化的计算机则意味着个人从国家的手中夺回了控制世界的权力,于是,信息技术摇身一变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工具。[7](PP.41-69)正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对个人电脑的介绍:“大型的电脑机器就像客运火车,而个人电脑就像大众汽车,虽然甲壳虫没有客运火车那么强大,但它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计划,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它带来了解放,释放了创造力,它就是未来。”[8](P.193)
(二)信息技术的成功经验:从政府主导到市场驱动
人们通常将信息技术革命的胜利归功于政府对技术的宽松监管以及领导这场革命的硅谷中青年企业家们。二战后,美国不仅复活了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贸易自由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而且把这种经济自由同达尔文主义的斗争精神结合起来,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9]此外,信息技术革命之所以必须由年轻的技术专家承担,是因为硅谷的个人创业者与传统的资本家有所不同,后者思想固化保守,只关心企业的经济利润,而前者观念先进自由,专注于技术创新,并以打造改变世界的伟大产品为目标。但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一个技术世界自行分出输赢的故事。
实际上,计算机和互联网成功的幕后推手并非自由市场,而是美国政府。首先,美国政府为信息技术的研发提供了大量补贴。尤其是在里根总统上台后,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用于计算机科学研究的资金相较10年前已增长两倍多,每年流向信息技术研发的资金接近10亿美元。其中,五角大楼是最大的资助机构,围绕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进行关键投资,以支持美国超级计算、芯片设计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概言之,政府的大量资金是以国防预算的名义进入信息技术产业,这才使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的重要场所。其次,美国政府调整移民政策,向世界敞开大门,让硅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汲取人才资源。[10]二战后的美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不仅意味着其需要大量人口填补战后的劳动力空缺,而且也需要科技人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些重大的变化都要求美国在移民政策上走向更加自由、开放的立场。后来的事实证明,移民政策成为美国经济繁荣之源,大量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涌入,推动了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从数据上看,截止到本世纪初期,硅谷成立的公司中,有一半以上的创始人都是移民人口的后裔。最后,在半导体行业的全球竞争中,美国通过打压日本企业,牢牢控制技术霸权。[11](PP.39-42)美国政府不仅以各种方式迫使日本签订半导体贸易协定,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半导体产品课以高关税,以阻止日本产品输入,抑制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而且制定并出台一系列信息技术产业扶植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分发公共补贴和建立科技园区等措施,加速资本和人才流入信息技术领域,确保其半导体、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可见,美国政府通过与私营企业签订国防合同、对学术实验室拨款以及出台产业保护政策等举措,以“隐蔽”的方式完成了托夫勒所谓的“第三次技术浪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纵观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无论人们倾向于政府主导的技术革命叙事,还是更相信自由市场带来科技繁荣的故事,其实都不重要。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功原因除了“市场决定论”和“政府决定论”外,本科勒教授还提出了一种“社会决定论”。他认为互联网的兴起主要来自网络的互联互通与社会协作,而非市场与企业的力量。其对于网络法的阐述,不仅意在解释互联网兴起中的自发协作因素,而且批判对象直指科斯等芝加哥学派。参见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因为,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技术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总结信息技术革命成功的经验,毋宁说是为了塑造一种信仰,以便统合国内经济力量,同化国外政治力量。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国内的去工业化浪潮导致美国经济衰退滞胀,政府便想寻找一种更有希望的并且能够代表未来的经济叙事。然而,与传统的被认为是摧毁灵魂的“战争贩子”企业不同,美国新一代的科技公司没有受到战争历史的任何束缚,最适合担任故事主角。于是,硅谷的创业者们成功地填补了国内经济领域的“英雄真空”。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美国希望通过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功,向其眼中的所谓的“非民主”阵营传递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即这些高科技奇迹是“美国式民主”优越性的最好体现。因为只有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才能带来科技创新的浪潮,从而发展出计算机芯片和个人电脑等高端科技产品。按照这套技术主义的叙事逻辑,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功被描述成一个美国才有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成功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成功。
二、政策出场:技术自由主义的主张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和美帝国》中强调,技术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服务于科学与工业的价值中立的工具[12](PP.142-150)。美国倡导的技术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主权,建构一套由其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即以自由之名,行霸权之实。具体来说,技术自由主义早期形态在政策层面包括两点,著名法律学者杰克·古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将其概括为“反商业监管原则”和“反审查原则”。[13]前者强调技术自由主义中的经济自由,服务于美国科技公司的全球扩张;后者则侧重政治自由,有利于美国政府的文化价值输出,两者以技术为载体,为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霸权行径提供合法性基础。
首先,反商业监管原则(Commercial Non-Regulation Principle)是由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首席政策顾问马加奇纳(Ira Magaziner)最早提出,后来成为美国数字监管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国内立法和国际造法中皆有所体现,强调数字经济领域,国家应遵循市场导向的消极监管政策,不应对互联网商业进行干预。[14]在国内法层面,美国倡导为数字科技公司提供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信规范法》(CDA),其中著名的“责任盾”条款便体现了互联网领域的反监管原则。在国际规则层面,1997年克林顿政府发布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提出了促进全球互联网自由的新政策,强调“竞争和个人选择”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最大特征,反对政府对网络空间的监管。此后,美国政府积极游说其贸易伙伴和政策盟友,以支持和推动全球互联网的自由议程,建立一个市场导向、私营部门主导的全球数字经济秩序。
从21世纪初的一系列联合声明和贸易协定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新加坡和英国等国家,以及欧盟和亚太经济集团纷纷同意1997年框架中的“反商业监管原则”。[15]1998年美国政府与日本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主要内容为“两国政府应避免对数字经济实施不必要的法规或限制,鼓励互联网上的信息和商业自由流动”[16]。美国政府又以“弥合数字鸿沟和创造数字机会”的名义,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项目提供信贷额度,帮助他们发展互联网技术。其根本目的是说服发展中国家放弃建造网络空间的“虚拟墙”,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公平、透明、自由”的全球数字竞争秩序。[17]此外,美国政府还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兜售“反商业监管原则”,成功说服世贸组织取消对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施加的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18]
其次,反审查原则(Anti-Censorship Principle)以实现美国式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为目标,主张外国政府不应对在线的互联网言论进行干预和审查。反审查原则并不是数字监管领域的新观点,而是美国从冷战期间延续下来的外交政策。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意识到“信息战争”对于价值传播,以及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作用。美国一直保持着对国外电台等新闻机构的资助和控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传播西方公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19]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互联网代替传统的信息媒介,成为美国推行西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宣传工具。特别是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时任国务卿赖斯就将互联网自由确定为美国政策的优先事项,专门成立了全球互联网自由特别工作组(GIFT),不仅为境外公民组织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还帮助他们规避本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言论审查。[20]随后,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网络空间的“反政府审查原则”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从2008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国会拨款近1亿美元,以支持政府为全球各地的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提供技术支持与内容培训,旨在传播美国互联网自由的叙事,在世界掀起一波“美国式”的民主化浪潮。[21]除此之外,美国也向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积极推销“反审查原则”,既将互联网视为推动自由民主思想的最大引擎,鼓吹在线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性,甚至还把控制互联网言论的行为视为专制政府的标志,并成功促成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和便利互联网的访问”的决议。[22]
今天的网络空间仍由美国私人的科技公司主导控制,这些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决定了世界各地的数字公民在互联网中接触的内容。这意味着,只要政府不加干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制造一个世界范围的“信息茧房”,影响互联网用户的行为和观念。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技术自由主义为何要以“国家非监管原则”为内核,本质上是为了在“代码即法律”的网络空间中,实现主权国家向美国科技公司的权力让渡,最终完成布雷默(Ian Bremmer)所说的“技术极性”世界的建构。由此可知,技术自由主义的“反监管”叙事旨在推行一种最有利于实现美国霸权的信息监管政策,无论是前述的“反商业监管原则”,抑或是“反审查原则”,最终目的并非在于带动其他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或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而是服务美国商业及其价值体系的全球扩张。
然而,一般来说,网络空间的信息具有商业属性,而商业信息的传播和流动是市场行为,属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所以国家和政府不应当对其进行干预。技术自由主义的经济面相虽然服务于美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市场扩张,但也给诸多后发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的好处。例如,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硅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迪拜的“互联网城市”,抑或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经济,都是效仿或复制美国市场驱动的技术自由主义模式而取得成功。但是,技术后发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功,恰恰说明了经济系统相对于政治系统的独立,技术自由主义并非只能在美国式的政治土壤中生长。除此之外,在文化政治领域,技术自由主义还承担着襄助后发国家“反抗压迫”“抵抗威权”的道德关怀。实际上,美国借技术自由主义之名,行文明驯化之实,以此维护其商业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用葛兰西的话语来说,数字空间的再生产是为了再生产现有的霸权社会关系。
三、资本控场:技术自由主义的局限
技术自由主义希望孕育出西方文明的数字形态,即一种“信息文明”。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正是将自己的使命,定位在人类文明进化的时间轴之上,预言互联网会打破主权国家的组织形态,最终形成一个没有地理边界的“全球数字社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互联网不仅未能实现人类社会的“信息乌托邦”理想,反而造就了一个“数字利维坦”。具言之,技术自由主义除了在经济层面,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分化和不平等,还在政治层面,加剧了原有的社会分歧和政治极化,这与早期的数字梦想背道而驰。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社会的财富主要通过剥削来获得,即资本家有所得,劳动者必有所失。然而,信息技术革命仿佛打破了零和博弈在经济生活中的魔咒。新兴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不再是剥削工人劳动的工厂,而是培育一批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温床;硅谷的技术精英们不仅重塑了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且缓解了国内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人们开始幻想进入到丹尼尔·贝尔所说的,以技术和知识为中轴的“后工业社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生产全球化”才是技术自由主义神话的塑造者。彼时,在亚洲劳动力市场的召唤下,美国科技公司把生产车间迁到所谓的“南方国家”,这使得蓝领产业工人被移出人们的视线,高科技生产的实际工作区与湾区的阳光沙滩隔离开来。因此,硅谷变成了一个不再制造东西的地方,半导体在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硅谷的原材料不再是硅和铜线,而是人和思想。[8](PP.15-20)
正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中所言:“当代帝国主义全球地理的转变以及世界市场的实现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当中有一条道路。最为明显的是,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世界的空间划分已显得过时,我们不断地发现,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当中,反之亦然。第二世界几乎无处不在。资本似乎面对着一个流畅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被新的、复杂的差异、同质、非疆界化、再疆界化的体制所限定的世界。”[23](《序言》,PP.2-3)可见,技术自由主义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美好图景是虚幻的,技术自由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与社会分裂。一方面,在一定时期,技术自由主义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世纪之交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指责其加剧经济不平等,对普通人伤害巨大。人们抱怨硅谷成为技术寡头们的“游乐场”,财富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和上升机会在变少。另一方面,技术自由主义建构出一个由苹果、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主导的“无形帝国”学界将这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称为“数字殖民主义”,具体是指科技巨头在数字经济时代能够支配帝国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和影响他国的规则、文化和信仰体系。此概念最早是用来抨击美国科技寡头,如今被西方学者用来无端指责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尤其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其他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援建。,他们不仅控制着全球数字市场,而且主导着产业链分工,致使阶级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空间转移。但是,技术自由主义为何未能实现最初的美好愿景,反而扩大了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其实早已给出提示,韦伯认为,经济目的始终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内在因素,经济行为决定了目标,
而技术只是提供了适当的手段。[24]
此外,在政治层面,技术自由主义不仅未能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助推了人们的极端情绪,滋生了信息腐败,并使部分主权国家和普通民众时刻处在技术寡头的监控之下。具体表现有三。第一,技术寡头利用网络空间的虚假信息影响和干预人们的政治判断。经济学家亨特·阿尔科特(Hunt Allcott)和马修·金茨考(Matthew Gentzkow)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将“假新闻”定义为“与真相无关的扭曲信号”,这些信号增加了人们推断世界真实状态的私人和社会成本。他们发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谷歌和脸书向7.6亿用户推送这些精心策划的“假新闻”;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平台公司不仅帮助英国独立党在互联网上设置辩论基调、进行政治动员,而且允许大量俄罗斯民众上传关于欧盟的虚假负面报道,并将其内容推送给英国民众。[25]
第二,假借国家安全之名,对主权国家实施监控。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2013年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门”事件。彼时的美国政府一边倡导各国遵循“互联网不受政府干预”的原则,一边又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系统性网络监控行为。自此以后,各国才开始重视网络安全问题,我国也提出了“网络主权”的概念对互联网空间进行“再疆域化”。
第三,资本控制数字空间,规训人们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信息技术从网络空间向现实空间迁移,信息科技公司将人类的经验工具化并加以控制,从而系统地、可预测地塑造人们的行为,以达到其盈利目的。同时数字巨头也会和政府共享权力,滥用技术对公民进行监视、控制和胁迫。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工业文明的兴盛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那么由“监控资本主义”
塑造的信息文明也将牺牲人的个性。[26](PP.15-25)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在现代世界中虚构的基于自由意志而建构的世界观会被戳破,人类的情感和欲望等主观体验将不再被认为是独特有价值的,而是能够被算法计算出来,人的本质也只是生物算法的计算。过去由人类大脑完成的思想过程将转移到电子仪器之上,数据会代替人们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正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预言的,数据主义将取代人文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从过去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由此完成从智人到智神的“进化”。[27](PP.651-682)
四、法律返场:技术自由主义的矫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为代表的网络乌托邦主义者,将网络空间视为“有自由而不混乱,有管理而无政府,有共识而无特权”的理想国,主张网络空间不能且也不应被国家和法律所规制。但是,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信息环境的政治文化也受到现实世界思想观念及其竞争格局的巨大影响,现实世界从未在信息环境的虚拟世界面前束手无策。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中,提出了“法律、社群规范、市场和架构”的规制框架,其中法律是最重要的要素,能够影响其他要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信息技术产业进行规制。[28](PP.132-150)
(一)美国模式:矫正困难
美国著名学者吴修铭在《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中,便对互联网公司的野蛮生长表示担忧。他认为互联网中立的特性虽然打破了传统信息帝国的专制系统,但是当前的互联网公司正沿着“循环”的轨道发展下去,逐渐成长为新的信息帝国。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是胜者拿走一切,所以信息技术产业内部也会出现“克罗斯诺”效应;另一方面科技巨头与政府联合,以为人们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借口,消灭竞争、延迟自身死亡,以实现长久的统治。[29](PP.261-300)当然,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科技寡头变得过于强大,正在向上侵蚀国家权力,向下侵犯个人权利。因此,政府希望放弃数字经济领域的“非监管原则”,尤其是在拜登总统上台后,其不仅邀请鹰派学者吴修铭加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担任技术与竞争策略的总统特别助理,推动对科技行业的反垄断监管,而且与国会合作加强反垄断立法,以削弱科技巨头的力量。
但是,由于美国本土的科技寡头体量太大,经济惯性太强,政府和国会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限制。首先在国家层面,美国政府对科技寡头的纵向打压,必然会影响到其与中国等国家的横向技术竞争。尤为重要的是,若强行削弱本土科技寡头的力量,美国科技寡头离开后的市场真空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的平台企业填补,这会动摇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其次,因为技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被不断地强化巩固,人们还是普遍相信科技是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科技巨头宣称的互联网乌托邦充斥着色情、暴力等违法犯罪,国家也难以对其进行监管。例如,1996年由国会议员提案通过并由克林顿签署实行《通信规范法》,旨在驱逐在线色情淫秽信息,但是在法案生效当天,就被送上最高法院接受违宪审查,最终科技巨头成功说服大法官们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定法案中关于在线言论监管的条款违宪无效。[30](PP.19-21)2020年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曾呼吁采取立法行动,对网络空间的在线言论进行规制,防止科技公司滥用保护盾条款,最后也是在民主党的强烈反对下,法案未获通过。
(二)欧盟模式:矫枉过正
欧洲将个人的“基本权利”视为数字政策的基石,以此建构网络空间的监管政策,避免技术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在《数字帝国:全球技术监管之战》中,将其概括为“权利导向型”的数字监管模式。[31](P.222)一直以来,欧洲都将自己视为“基本权利保护”的世界灯塔,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例如,欧盟在2018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对隐私和个人数据权的保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要求科技公司在处理个人数据时,保持合法性、公平性和透明度。如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已成为关于如何保护个人数据免受政府或私营公司侵害的全球“黄金标准”;在言论控制方面,欧盟于2022年通过了《数字服务法》(DSA),规定了互联网平台必须额外评估和报告可能损害基本权利的系统性风险,建立了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责制度,该法案也被其他国家广泛借鉴和移植。此外,欧盟授予本土企业高度的监管权能,将本土企业视为欧洲价值规范和价值观的捍卫者以及欧洲安全的保障者,而把美国和外来的科技公司定位为需要监督和控制的对象。[32]
然而,从结果来说,欧洲并未在信息技术领域培育出成功的跨国公司。广泛的监管是否真的抑制了欧洲的技术创新还存在争议,但这些数字法规的确对科技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限制企业收集、处理或共享数据。欧洲在数字主权方面的转向,具体表现为主权担纲者的私营化。美国政府和科技公司将欧洲的监管政策视为一种保护主义,认为其动机是利益驱动来保护本土企业,旨在向欧洲本土科技公司伸出援助之手,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与美国的企业竞争。换言之,美国在科技行业的主导地位才是“欧洲怨恨的来源”,而欧盟对技术自由主义的矫正也被视为对这种怨恨的回应。[33]例如,欧洲各国的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所谓的“数字经济公平”,近一半的欧盟成员国已经宣布、提议或颁布了国内数字服务税(DST),其中法国是第一个对包括亚马逊、苹果、谷歌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34](PP.4-12)总的来说,欧洲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提高自身技术的竞争力,并开始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性,但是,这一政策目标可能会使其转向另一种极端——技术民族主义。
(三)中国模式:平衡保护
面对技术自由主义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中国政府基于问题导向进行实践摸索,超越传统全知全能型市场思维,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综合治理模式,布拉德福德教授将其概括为“政府导向型”模式。但是,在布拉德福德教授看来,中国的治理模式本质上还是一种国家控制的“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即在经济层面,追求数字保护主义,确保本国的科技公司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以进一步加快国家的技术发展,实现所有关键技术上的自给自足;在政治层面,利用信息技术强化政府对个人的控制,而不是保障个人自由。[28](P.147)其实,这种偏见不仅来自旧有的意识形态对立,还在于西方学者未能准确把握中国政府治理网络空间的真实动因,故而无法真正理解我国的网络空间治理逻辑。
网络空间的可治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可认证性上,中国互联网治理路径正是通过数字立法和监管政策强化政府的信息认证能力,抑制企业平台权力的无限扩张,实现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欧树军在《灵境内外:互联网治理简史》中将信息认证能力分为身份识别能力和行为识别能力,前者是指对标识网络用户生物特征和社会特征的识别和证明,后者可总结为工信部确立的针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三大原则,即同意原则、正当原则和安全原则。[35](PP.60-100)然而,国家强化信息认证能力不是为了监控社会,而是回应网络空间出现的具体问题。例如,因为电信诈骗的猖獗和网络暴力等问题的泛滥,政府才开始对个人信息进行认证,对在线言论进行管控。所以,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与欧洲“权利导向”模式的最大不同,并不是布拉德福德教授所说的,欧洲强调个人权利保护,中国侧重国家权力集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欧洲推行的是“价值主义”治理模式,中国则倡导“实用主义”治理模式。换言之,我国数字领域的立法体例,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借鉴了欧盟法律,但实践逻辑存在巨大差异,只有个人的权益受到具体侵害,并在对“公—私利益”进行衡量后,才会激活并适用相关法律。
当前,技术自由主义视域下的“非监管原则”正失去正当性基础,各国纷纷摒弃市场驱动、私营部门主导的监管模式,转而寻求国家法律的矫正和规制。其中,美国出现了矫正困难的情况,选择以牺牲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为代价,放任本土信息科技公司野蛮生长,以换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竞争优势以及全球数字经济的主导权。然而,欧洲以保护基本权利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则可能会陷入技术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欧洲虽然成功地阐明了其“权利驱动”的数字经济愿景,并将这一愿景写入法律,但它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削弱了本土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相较而言,面对技术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国则利用多种政策法律工具,兼顾市场开放与政府调控,有针对性地对技术自由主义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矫正,较好地平衡网络空间中个人权利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五、余论
需要注意的是,包裹在技术中立和信息自由流动话语之中的观念,恰恰忽略了信息的政治和文化属性。因此,若我们过分注重物质经济利益,就会陷入帝国主义无害论的陷阱,自愿接受被技术自由主义话语支配;反之,如果一味强调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也会趋于封闭,走向技术民族主义的极端。故而,在对技术自由主义话语进行批判和省思时,不仅要超越狭隘的经济视域,而且一定要看到其背后隐藏的普遍价值的多样可能性。换言之,我们在承认“他者”文化观念的同时,还需不断挖掘本土资源,从中提炼出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并将其塑造成一种知识产品,提供给他国选择,这或许才是摆脱技术自由主义话语支配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 Jodi L. Short,Reuel Schiller,Susan S. Silbey.et al.“The Dog That Didn't Bark: Looking for Techno-Libertarian Ideology in a Decade of Public Discourse about Big Tech Regulation.”Ohio State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22,19(1).
[2]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Vancouver, WA: Vintage Books, 1964.
[3] Roy Rosenzweig. “Wizards, Bureaucrats, Warriors, and Hacker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et.”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8, 103(5).
[4] Martin Shapiro.“The Globalization of Law.”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1993,1.
[5]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6] 诺伯特·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第2版),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
[7] Fred Turner.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8] Margaret O’Mara. 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ew York: Penguin Press,2019.
[9]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10] 周督竣、包刚升:《观念、利益与政党:美国移民政策变迁背后的三重张力》,《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4期。
[11] 卢阳旭、张娟娟:《科学应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国家治理》,2023第13期。
[12]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和美帝国》,刘晓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13] Jack Goldsmith.“The Failure of Internet Freedom.”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2018,June13.
[14] Ira C. Magaziner.“Creating 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Future Insight,1999,July.
[15] Stuart S.Malawer.“Global Governance of E-Commerce and Internet Trade:Recent Developments.”Virginia Lawyer,2001,14.
[16]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1998.
[17] Appu Kuttan,Laurence Peters. From Global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Opportunity,The White House, 2000, July 22.
[18]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WTO document G/L/160 of April 2, 1997.
[19] Kal Raustiala.“An Internet Whole and Free:Why Washington Was Right to Give Up Control.”Foreign Affairs,2017,96(2).
[20]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 (GIFT) Strategy: A Blueprint for Act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2006, Dec.28.
[21] Thomas Lum, Patricia Moloney Figiola and Matthew C. Weed.“China, Internet Freedom,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2,July 13.
[22] Zeldin, Wendy.“U.N. Human Rights Council: First Resolution on Internet Free Speech.”2012, July 12, https://www.loc.gov/item/global-legal-monitor/2012-07-12/u-n-human-rights-council-first-resolution-on-internet-free-speech/.
[23] 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婷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24]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5]" 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7,31(2).
[26]" Shoshana Zuboff.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9.
[27]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28]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29] 吴修铭:《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顾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30] Jack Goldsmith and Tim Wu.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 Anu Bradford.Digital Empires:The Global Battle to Regulate Technolo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32] Benjamin Farrand and Helena Carrapico.“Digital Sovereignty and Taking Back Control: From Regulatory Capitalism to Regulatory Mercantilism in EU Cybersecurity.”European Security, 2022, 31(3).
[33] Editorial.“Tax Affairs of American Tech Groups Come Under Fire.”Financial Times,2017,Oct.3.
[34] Louis Kaplow. “On the Choice of Welfare Standards in Competition Law.” Harvard John M. Oli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693, 2011.
[35] 欧树军:《灵境内外:互联网治理简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
Reviewing Techno-libertarianism: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Correction
XU Shen
(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the soul of free market, and techno-libertarianism is the experience summ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wever,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market-oriented techno-liberal economic narrative has been invented. This narrative requires the state to adopt a non-regulation principle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which is to economically serv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American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politically support the worldwide dissemina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Simultaneously, techno-libertarianism also leads to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inequality, social divergence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echno-libertarianis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a difficult situation to correct, and Europe may go to the other extreme of techno-nationalism. In contrast, China has adopted a pragmatic approach using a variety of legal and policy tools to better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techno-libertarianism; digital economy; non-regulation principl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egal correction
(责任编辑:蒋金珅)
作者简介:徐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社会学、数字治理、法律与基础设施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