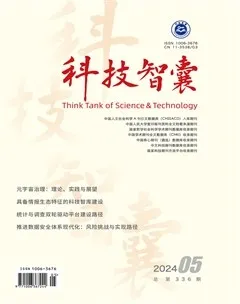现代化探索中的科技发展与文化主体性巩固
闫耀民?王烁
摘 要:[研究目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支撑,寻求科技现代化与自身文化的现代化始终是现代化探索中一对重要关系。[研究方法]考察科技与文化双重视角下对“现代化”的理解,并分析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减弱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传统文化主体性对科技发展的作用,进而提出增强创新文化主体性的策略建议。[研究结论]文化体系对科技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对科技发展道路的选择尤为重要,考察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实践;科技创新;传统文化;文化主体性;策略
中图分类号:G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4.05.09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重要命题。在通向现代化的实践中,怎样定义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追赶,然而当前西方国家不断将自身发展危机外向转移,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使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不得不对发展道路进行再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落后挨打到提出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不仅意味着中国自身开始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念,发展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同时也是对世界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贡献。科技既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也是衡量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化体系则是彰显不同类型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鲜明标志,也是影响、支撑现代化道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二者在现代化实践中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共性途径,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发展的个性道路。
本文拟通过考察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现代化历程,探析文化现代化在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探讨当前科技现代化进程中增强创新文化主体性的策略。
一、科技与文化视域下的“现代化”研究进路
长期以来,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是研究现代化的重要视角。以西方视野为中心的发展社会学将其体制、文化、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定义为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用于描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1]。与之相对的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被定义为国家或社会由落后向先进的过渡转化过程,而“现代化”就是“用于描述这些国家获得这些特征的过程”[2]。有学者将现代化看作是特定年代、特定国际政治背景下所流行的披着学术外表的意识形态,但无论现代性与现代化因何成为描述时代问题的名词,理解和探索“现代化”已经是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命题,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现代化进程也一直受到中外学者关注。
早期现代化研究中,有外国学者将技术因素置于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地位,例如,把“人工灌溉”这一技术事实理解为古代东方社会的根本,推导出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结论。对中国学者而言,落后挨打的教训则导致了“一种强大的内省式归因逻辑与决绝的行动取向,那就是彻底或矫枉过正式地批判传统及其文化,认为唯其如此,才能赶上时代,尽快实现现代化”[3]。当时流行的“全盘西化”主张既是应对民族危机的探索,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普遍性焦虑。
随着工业革命持续深入和科技进步,在率先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中,伴随科学技术运用而出现的工具理性膨胀冲击了社会的价值理性。面对由此带来的风险和技术恶果,部分西方学者企图用后现代性理论超越现代性,但并未找到恰当出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一元思维已难以协调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也难以为多种文明形态下的现代化问题给出答案。而实践证明,受到西方国家“现代性入侵”的后发国家如果放弃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反而在全球化中失去了方向。
二十世纪后半叶,本土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开始呈现出带有主体性的反思。如罗荣渠认为现代化可归纳为先进的历史过程、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四个类别,而合理化不应当仅仅是工具理性化,“在现代化阶段缺少工具理性价值的文化资源,被西方价值观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价值”[4]。
当前,我国现代化研究所体现的主体性意识进一步增强。如在对待科技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在当下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才能‘打通上下五千年”[5]。有学者从复杂性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出发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问题,认为“如果没有对现代化致思方式的焕新,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就容易陷入将中国式现代化作内容分解(分割)的片面性困顿之中”[6]。
在科技研究中,一个国家文化体系的影响往往以科技理念、科技价值、科技伦理、创新文化等形式存在,通过“软实力”的概念与科技活动相结合,并成为科技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这一思考路径在文化与科技之间建立起更为直接的关联,便于考察文化发展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从软实力角度考察文化体系与科技的关系,则意味着文化处在被选择一方,易忽视对科技发展产生更深层次影响的文化因素,以及科技发展本身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
当前,科技正深度参与国家治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成果,在中华文明探源、乡村振兴、公共安全、城市建设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科技作为治理手段嵌入国家治理格局,与文化交集日深,更需要以国外现代化过程中过度依赖技术治理及其文化体系产生的教训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问题的覆辙。“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7]。因此,文化体系对科技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对科技发展道路的选择尤为重要。考察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为科技发展提供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支撑,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化主体性减弱对科技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表现出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特征,但并未沿着由对自然现象的哲学思考引申到建立科学理论体系,进而支撑科技发展的路径。晚近以来,科技落后是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触过程中的直接表征。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失败,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后果,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以先进科技为显著特征的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使有识之士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也对传统文化体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并给科技和文化赋予了更多社会意义上的使命。由于受到西方理论及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探索中国现代化出路时更多采用“他者”视角,因而容易陷入对自身文化的否定和对西方科技体系的盲从,造成思维和实践上的误区:
(一)现象误区:把科技落后与文化落后简单等同
“明清之际接触西方文明以来,近代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就不再纯粹是自我建构的,而是通过‘西方文明这个‘镜像的中介来进行自我理解”[8],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这一标准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潜在认识。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自信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国内与国外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即西方的等于现代的。尤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西方科技进步对生产力发展表现出强大促进作用,并通过其价值体系成为殖民扩张的工具,进一步强化其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性。作为最显著的文明特征,西方科技体系不是被视作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产物,而是充当了价值标准—既是区别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标志,也是评价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价值尺度,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融入世界与追求富强的道路都在这一语境下展开和诠释。胡适、陈独秀等人主张的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等观点,都蕴含着借由西方化而实现现代化的目的,也伴随着传统文化自信的动摇和丧失。
(二)路径误区:把西方科技发展道路视为摆脱文化困境的主要手段
用发展科学技术摆脱文化危机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重要尝试。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后,以汉族士大夫为主的官僚精英发起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寄希望于中体西用,以求维护旧有统治秩序;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改革教育制度、奖励创造发明等,把科学从“器用”推向“制度”;辛亥革命则希望首先建立起现代的社会制度。技术变迁引起社会变迁,继而引发文化变迁,“当着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之时,我们还发现:卓有成效的科学技术革命,只能发生在广泛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之后”[9]。西方科学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思想旗帜,在“科学与玄学”等思想交锋中被提升到人生观高度,乃至有学者把科学等同于现代化,提出“现代化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以及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4],足见科技在20世纪初文化发展中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重。然而“西方式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本主导、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10],依靠西方式科技发展道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遭遇挑战的困境。
(三)认知误区:认知局限造成的文化断层阻碍科技长远发展
在渐进式文化发展已经不足以应对激烈变局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已经消亡的文明相比显然有本质区别。一个有生机的文明可以通过内在和外在调节继续延续,中国在应对外来文明时的迅速反应也足以说明传统文化体系活力尚存,绝非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中应被抛弃的文明。即便在向西方学习占据主流思潮的环境下,也有学者以主体视角审视外来文化,看到了西方科技和文化体系过分强调物质文明的弊端,然而在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飞跃以及摆脱民族生存危机的迫切需求面前,这些观点中蕴含的主体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关切也湮没在科学革命光环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文化断层以及社会成员对传统文化的片面性解读,对其不加甄别地全面批判,忽略了批判行为本身就是文化体系为应对危机、通过自我调节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重要方式。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打倒孔家店”式的文化批判当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也显示出在两种文化相互接触的早期,国人认识外来文化的思维还有待健全。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为社会心态对西方科技发展方向的依赖,还体现为社会成员有意或无意对传统文化根脉的轻视,传统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也随之消解。
科技发展差距是造成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主体性消减的直接诱因,文化主体性消减也给科技发展造成了一定阻力。当科技发展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面临更为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问题时,更需要发挥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性作用,对外来文化做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判断,理性挖掘传统文化主体性的有益价值,对外来文化有选择性地兼收并蓄。
三、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对科技创新的价值支撑
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术科学体系。当面临巨大的外源性变迁时,短时间内接触异质文明体系带来的全方位冲击给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了反思和机遇,促使“向西方学习”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基调。然而“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4]。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进程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如果继续根据西方工业发展模型拟想未来社会,那么伴随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数字鸿沟、贫富加剧、生态危机等将继续如影随形甚至加剧,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科技发展文化价值体系,探索更为多元的科技发展模式。
中华传统文化推崇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为应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提供了思想基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也将外来文化体系中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彰显文化主体性,并形成新的价值体系,为科技发展提供支撑。
第一,“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发展科技是人认识、改造世界的重要方式,怎样发展、为什么发展科技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答案不尽相同。科技背后的价值体系决定了科技的发展走向,科技发展目的、发展方式以及发展成果应用背后都体现着文化体系的价值判断。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已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和人本主义的特征。《礼记·礼运》大同篇最早提出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描述,“大同”理想、“天下观”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理想具有内在契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传统天人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些观念与以二元对立、一元单线进化逻辑为特征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同,面对更加多样化的文明进程,更具有超越意识形态障碍、从人的本质出发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和优势。当前对产业升级与人的关系、缩小数字鸿沟、技术使用正当性等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正是这一文化体系在科技发展中向导和约束作用的体现,对防止工具理性主义过度膨胀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道不远人”的方法论。《中庸》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就建立了“道”与人实践活动的直接联系,源于这一前提的方法论使中国传统文化更擅长从实践出发,重视经验和局部效用,避免陷入纯粹的原理、原则之争,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具有高度契合性。与西方科学的演进路径不同,在“经世致用”的文化价值导向下,中国的传统实验以应用为首要目的,围绕人的生产活动需要,在冶金、交通、陶瓷等技术领域都发展出了高度成熟的技术科学,“从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开始围绕木、铁、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技术系统,并循序渐进地进行发展。”[11]。中国古代科技这种指向实践的发展理念和路径与西方文化支撑的发展理念和路径不同,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阻碍了理论体系发展,但对当前世界发展的多元化趋势有更强包容性,具备容纳多种科技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空间和能力,避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中唯一性的发展悖论,为跨越文明陷阱,解决目前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二元对立思维以外的可能性。
第三,“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大学》认为“致知在格物”,《二程遗书》进一步阐释“格物致知”,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因而需要“随事观理”。虽然程颐、程颢强调的“理”与当代科学活动中探求的真理含义并不尽相同,更多集中在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二人在对如何格物致知的方法和顺序上也存在不同见解,但“格物致知”承认了事物存在规律,并且规律是可被认识的,对科学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二程同时把“止于至善”作为“格物”的最终目的,强调“格物”活动本身的向善性,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社会生产的目的的向善性具有相似之处。这种强调科技发展的向善性思想与当前科技活动中坚持“四个面向”具有契合性,对引导科技活动造福于人,规避当前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具有参考价值。
第四,“变易”和“求变”的创新动力。与西方哲学源头中永恒的理念世界不同,“变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易经》用“--”“—”两爻表征原先以数字组成的卦相,当用阴阳二气解释两爻后,“变易”这一概念“便不仅是占筮之象数变化及其象征的某类事物的特殊变化,而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普遍原则”[12]。马克思将科学看作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今天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影响日益深刻,“日新之谓德盛,生生之谓易”“反者道之动”“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等传统文化中对变的认识和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动力,对促进科技创新,以及调适应对物质世界带来的快速变化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传统文化不仅支撑了古代科技体系及丰硕的科技成果,并且能够在延续发展中支撑科技创新。虽然早期东西方文明接触中“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比较鲜明,但随着时间推移,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中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并未表现为根脉中断、持续冲突或相互替代,而是以共存、融合的方式形成了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价值体系。
中国科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也应当与世界科技发展保持密切联系,但支撑科技发展的文化体系应该是具有主体意识的文化体系,其文化坐标是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而不是简单的“落后与先进”“西方与东方”二元对立价值标准。这种主体性意识不仅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保证,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
四、增强创新文化主体性的策略建议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由于环境、文化、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差异而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抓住人类前几次工业革命契机、率先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西方国家在实践领域仍然推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将西方式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另一方面,一元思维方式在面对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复杂问题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将问题引向对立,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遏制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了事实上的发展权不平等。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发展契机也是新考验,需要在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衔接中既接纳现代化普遍特征,又保持发展的主体性。
2023年11月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2—2023》显示,全球创新格局保持亚美欧三足鼎立态势,科技创新中心东移趋势更加显著[1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中国拥有的科技集群数量最多(24个)[14]。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科技博弈的影响远超科学技术本身。布热津斯提出为了维持文化霸权地位应该实施的策略—“削弱民族国家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6],当前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国科技的加速发展对美国形成了多方面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追赶或超越,而是“已从安全、经济与价值观三方面对美国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威胁到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15]。随着科技竞争被引申为价值观竞争,文化主体性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也将更加明显。因此,推动科技发展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增强创新文化的主体性特质,避免在评价创新文化时形成他者依赖。
一是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明经历多次变迁而延续至今,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优秀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人本主义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科技发展范式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依据,也昭示着解决发展问题的另外出路。传统文化作为几千年积累的重要思想遗产,决不应在现代化进程中抛弃,而应与科技发展实践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16]等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将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相结合,为科技发展的原则和方向提供了价值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具备对外来文化和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判断,并在扬弃中实现传承创新。
二是强化自立自强的文化特质。自立自强是贯穿中国文明的重要文化特质,在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上古神话故事中,已表现出对人能动性的赞颂,并十分重视发挥人的能动性。《周易》开篇即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将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延伸至人格塑造,贯通自然与人文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对当前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发挥关键作用做出的深刻判断,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重要特质的继承。在当前科技发展实践中,我国一方面已经在部分领域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仍旧面临基础研究不强、缺少原创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依赖度高等问题,这也是应对美国的科技打压、建设科技强国必须解决的问题。随着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需要更加突出自立自强的文化特质,“就是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要求我们既能够解决‘心腹之患,也能够解决‘燃眉之急”[17],把创新和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Beijing,100038)
Abstract:[Research purpose] Achieving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t higher levels is the key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 without cultural soft power. Seeking modern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modernization exploration.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understanding of“modernization”from both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analyze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diminished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as well as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ubsequently,the paper propose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the subjectivity of innovation culture. [Research conclusio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cultural system for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modernization explor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raditional culture;cultural subjectivity;strategy
作者简介:闫耀民,男,1973年生,博士,科技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王烁(通信作者),女,1988年生,博士,科技日报社主任记者,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