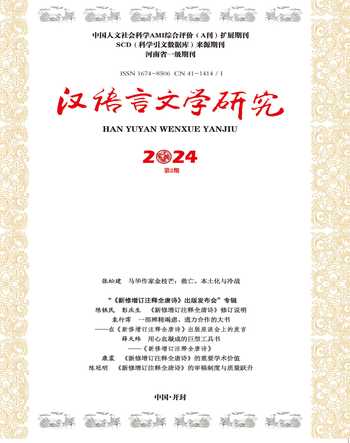颠覆与重构之间的历史:《理水》的“戏仿”诗学
① 鲁迅:《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386页。
② 同上,第386页。
摘 要:《理水》是鲁迅《故事新编》中较晚创作的一篇以“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为依托的小说。小说语言修辞和叙事方式的“油滑”风格所呈现出的间离效果、前三节与最后一节之间的断裂,体现出《理水》作为“拟史传”的“新小说”的拟仿特征。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小说传统和史传传统的脉络中考察,作为一篇现代小说,其文体混合的形式在颠覆既有历史话语的同时又以“小说”重构了新的“历史”。
关键词:鲁迅;《理水》;《故事新编》;戏仿
《理水》是《故事新编》当中人物相对复杂、情节颇富喜剧性的一篇。根据鲁迅日记,《理水》作于 1935年11月29日,以往对《理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小说中“大禹”形象反映出的价值内核以及小说情节同历史语境的关联,并从中探究鲁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心态。小说内容层面的历史与现实材料是分析文章主旨的关键,而文本的形式感同样值得关注。本文拟从“戏仿”这一诗学表征入手,对小说在语言修辞上对不同语体的具有反讽色彩的摹仿,以及在叙事方式上对“史传”传统的拟仿进行分析,挖掘其文体混合的形式中所具有的历史性和寓言性。
一、“戏仿”:从“油滑”到“间离”
《理水》取材自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传说,“理水”的行动作为小说的标题同时也是核心事件。“大禹”本应是实践“理水”动作的主要人物,然而小说前三节并没有对大禹及其理水的过程进行直接描写,大量的笔墨都在描绘文化山上的各类学者以及诸多官员。作者对人物语言进行了滑稽地模仿,形成鲜明的讽刺意味。鲁迅对人物语言的戏拟通过多种方式、多种语体实现,并勾连着指向现实语境的讥讽与批驳。
在小说开篇写到奇肱国的飞车为文化山上的学者送来食粮时,就出现了对英语“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OK”在拟声层面的模仿:
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K!”①
另一处则是对鸟头先生的原型顾颉刚说话口吃特点的拟仿: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②
以上两种情形是对语种和语流在声音效果上的拟仿,另一种拟仿则是针对人物所使用的语汇和话语形式。譬如在写到学者们向考察专员汇报灾情时,研究《神农百草》的学者称“下民”食用榆叶和海苔便已足够:“‘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①当写到长着八字胡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时,又是直接引述了人物所说的一大段文言用语:“‘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②
《神农本草》原是成书于秦汉的古代医书,身处上古时期的学者说出“维他命W”“碘质”等现代西方科学用语更加是荒诞不经;而小品文家说的文言文在其他人物的白话口语中显得十分突兀,在古典韵文中又插入了“雪茄”这样的现代词汇。在对人物语体、语词的戏仿中,鲁迅对现代医学背后代表“科学”的语言和古代文学传统中的文言进行了双向讽刺。同一语境下对不同话语系统的拼贴造成一种不和谐的荒诞感,而学者谈论民情时所说的言辞和百姓处境的对照更突出了人物的冠冕堂皇和虚伪做作,揭示了言语的不真实性。除了人物语言,鲁迅也通过像“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这样的叙述语言来拟仿英雄主义的笔法,对人物加以调侃;开篇的“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则是《尚书》中的语句,对传统典籍的叙事进行了直接引用式的模仿。
这种语言上的“穿越”造成了历史和现实的混杂,打破了叙事时空的统一性。已有学者指出,鲁迅将“过去”当成“现在”来写的方法是通过时态标记词的使用营造出在场感和即视感,从而自由地穿梭在历史和现实的共轭结构之中。黄子平认为这种现象是“叙述时间”侵犯了“所叙时间”,是当代语言对古代故事发生了污染③。叙事语言的错动尚可通融,但人物语言无法再现对话的特性则会打破写作者和读者的契约。语言惯习本身带有时代与地域的特定属性,小说中却把异国语言、典籍文言、科学专有名词等负载不同语境的语言熔为一炉,使它们平行存在于同一时空之内,在这个意义上说,叙事语言与人物语言对各类语体的拟仿是通过混合语言和文体杂交创造出新的语言范式,搭筑出某种叙事层面的“超时空结构”。
“戏仿”在鲁迅小说的诗学研究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许多作品都可以调用这一概念进行解释,比如作为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其文言小序对传统史家笔法进行了拟仿,再比如《阿Q正传》有对于史传书写传统的戏仿,短篇小说如《幸福的家庭》《伤逝》也都带有一定的戏仿色彩。郑家建在他的专著《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中分析了小说语言的戏拟特征,这一特征使同一文本内部存在着包含人物意向、旧文本意向与作家新意向在内的多层意向,而摹拟语言的意向和“他者语言”意向在同一语言形式结构中发生矛盾和冲突。④
“戏仿”是古希腊文学中就已经存在的书写方式,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侧重分析戏仿手段在引起“陌生化”效果上的重要功能,而巴赫金则进一步从诗学角度论述了戏仿在文体语言上造成的双声效果,他认为“一切非直接的话语,都是特意混合体,不过是单语的混合体,是修辞性质的混合体……在讽拟性话语中有两个风格、两种‘语言(一个语言内部的‘语言)汇合在一起”⑤。在鲁迅的小说中,也存在着这样两种“语言”的交错:写作小说使用的白话语是更新中的正常、健康的“标准语”,在这一叙事话语之下,被不断引用和反复提示的则是被讽拟的语言,两种语言汇合交错,从事讽拟的语言并不进入讽拟体,却以组织和理解讽拟体所依托的背景的形式存在于讽拟体当中。巴赫金还分析了中世纪的戏仿文学如何通过狂欢化与神圣的结合来完成对正统官方文化的颠覆,戏仿文学从虔敬的宗教范畴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欢快看待世界的开放性和更新的愉悦感。⑥戏仿叙事达成的“文本间性”往往意味着用游戏性的方式将严肃文本重新讲述,打破了语言秩序中的既有权威,《理水》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众声喧哗”的狂欢中为神圣的历史殿堂涂抹新的色彩。
这种随处可见的“戏仿”也是造成鲁迅所说的“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①的效果的重要因素,但“油滑”并不是一种负面的叙述风格。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认为鲁迅在将《故事新编》指认为“油滑”、“游戏之作”的自我批评中其实包含着对自己创作方法的自负。②王瑶用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二丑”艺术来解释鲁迅笔下的喜剧性人物和漫画性笔法,并认为其中蕴含着某种间离效果。③陈平原进一步论述了《故事新编》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之间的共同点,指出《故事新编》通过现代用语的插入割裂情节而达成了一种间离效果,便于读者从情节中抽离出来以接受一种理性判断。④从“油滑”到“间离”,学者们对其艺术效果的纵深化阐释,也昭示着鲁迅的“反讽”不仅作为一种修辞艺术上的诗学,更作为一种哲学式的理解而存在。
间离效果提供了陌生化的阅读感受,而内在于这种间离效果的是一种背反性:鲁迅正是通过将历史和现实相融合,来达成历史与现实的分离。只要不是一个完全天真的读者,他自然能知道上古时期的人不会阅读莎士比亚,也不会真的认为古代人会懂得现代医学,当读者察觉到历史和现实错动的那个瞬间,就打开了一条进入历史和现实的新路径。“戏仿”的语体在颠覆历史的同时,也在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而它刺向现实的一面则不禁令人深思:历史的阴影是否仍在现代世界中徘徊。历史和现实的互相指涉,搭建了一条抵达跨越几千年时间的漫长寓言的通道。
二、作为“拟史传”的新小说
前文提到,鲁迅在小说前三节对“理水”的主导者大禹缺乏正面描写。在前三节,“禹”的形象掩藏在沉默之下,面对水利局大员的种种意见和辩驳,禹总是“一声也不响”,说到应该用“导”的法子,他也只是“举手向两旁一指”。禹和官员在沟通上的失败体现出这一交流语境中的某种非对话性,对禹动作的着力刻画则表现出叙事者塑造禹的人物形象时在语言描写上的节制,和前文中大力铺陈并拟仿人物语言的写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到了小说第四节,叙事语调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关大禹的描写也发生了变异。首先是对大禹的称谓从“禹”变成了“禹爷”,禹和舜之间的对话也和之前与大员的交谈不同,他会说出《尚书》中的那句“浩浩怀山襄陵”,也会提醒舜:“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⑤最为割裂处出现在小说的结尾,那个“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的禹和前文中“生了鹤膝风”、“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的禹很是不同。叙事和人物语言上的参差,使得第四节和前三节呈现出某种断裂感。
小说前三节和最后一节的断裂增加了 “禹”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也造成了文本意涵的内在张力。以往研究通常将《故事新编》中的《非攻》《理水》两篇共同放在鲁迅同一时期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创作语境下解读,认为大禹的书写正是鲁迅在为“中国的脊梁”造像。⑥结合鲁迅早年对大禹“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的评判,的确容易导向对大禹形象积极方面的判断。而对于结尾的解释,一种看法是认为鲁迅描绘的是“猛人受困”的情景,与他当时的悲观心境不无关系;另一种理解则指出这一结局包含了鲁迅的微讽,是在颠覆与嘲弄的自我否定中完成对英雄主义的消解。这也是解读《理水》必然会遭遇的困境:如果将大禹视为“民族脊梁”的显形,似乎并不符合《故事新编》的总体基调,竹内好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思想中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①,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其中《非攻》和《理水》两篇透露出的亮色和他所强调的鲁迅的“无信”相龃龉。②另一方面,禹的“民族脊梁”形象和最后一节的“翻转”叙事之间也的确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痕。祝宇红关注到《故事新编》作为“重写型小说”的戏仿性,她认为结尾的翻转构成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嘲讽”而是补充意义上的“稳定反讽”。③如果聚焦于《故事新编》在整体写作上具有的游戏性质,会发现人物形象的游移与难解和小说在形式上的非确定性是相互匹配的,鲁迅或许并不是想要通过虚构的人物“禹”来引导读者作出历史的公断和道德的评定,而恰恰是用“油滑”的笔调推开了历史叙述中的“盖棺论定”,在对峙与暧昧中表达出对固有历史形象及其背后传统的破除。
根据鲁迅自述,同时取材于古代和现代的《故事新编》是对“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整体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对“历史”的摹仿。不过,在《理水》一篇当中,前三节和最后一节对于史传和传奇的拟仿力度和程度显然存在参差。前三节是较为脱出传说内容的再创造,鲁迅基本是“信口开河”,加入了大量细节和指向现实语境的语言,而最后一节则更为忠诚地模仿着传说和史传,比如写到有关“禹爷”的新闻和故事时讲到“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即是来自《左传》昭公七年中的“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④;另外,在清人马骕《绎史》的《随巢子》中也提到了这一传说,而“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⑤则是取自唐代李公佐的《古岳渎经》。第四节写到的舜向禹赐予“玄圭”、禹和舜之间的大段对话,则基本都是重述了《史记·夏本纪》中对先秦时代的相关记载。至于结尾处对大禹形象最具颠覆感的描述“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⑥,则是援引了《论语·泰伯》中的一段记述:“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⑦第四节的戏仿对象不再仅仅是进入人物语言的各种语体、语汇,而是在整体叙述上完成了对民间传说、《史记》和《论语》内容的拟仿。从这一颇有意味的细节中可以看出,鲁迅在小说中即使对禹存在反讽,也是相对柔和的,禹的定位也处在一个暧昧犹疑的灰色地带,而潜藏在祭祀之饮食、朝拜之衣物的礼节中的反讽意味,可能更多是指向了以《论语》为代表的积压在几千年历史地层之下的礼教传统。
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将诗学研究的“跨文本性”划分为五类:文本间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和广义文本性,其中他着重提出了“承文性”(hypertextuality,又称“超文性”)的概念:“从现在起,我把它重新命名为‘承文本性,以此表示任何联结文本 B(我称之为承文本)与先前的另一文本 A(我当然把它称做蓝本了)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嫁接而成。……也可以是另一种情况,即 B绝不谈论A,但是没有 A,B不可能呈现现在的生存模样,它诞生于一种活动过程的结尾,我把这种活动过程暂时称做‘改造,因此,B或多或少明显地呼唤着A文本,而不必谈论它或引用它。”⑧他将“承文性”分为“简单改造”(即改造)和“间接改造”(即摹仿)两种派生方式,“改造”往往是接续着前文本的写作模式,对蓝本进行较为简单机械的临摹;而“摹仿”则需要从原作中提炼出某种“范式”,重新书写后得到新的文本内容。承文本的作者对蓝本则往往持以或“会聚”或“分散”的态度,前者是对旧有文本中的价值伦理表达推崇、赞赏的肯定态度,后者则往往突破原有文本的精神内涵,表达某种颠覆、讽刺的否定态度。“戏仿”的文学实践正是处在“摹仿”和“分散”的交叉点上,包含着两个连续的动作,第一层是对某种语言的拟仿、摹仿,即对旧有文本和他人语言的重复、改写、再创造;第二层是用置换、增删等方式重塑他人语言或旧有文本,偏离原本的意义而赋予它新的价值,实现嘲讽、颠覆、解构等效果。
《理水》第四节对信史记载和儒家经典的引录同《史记》《论语》等“蓝本”之间正是呈现出一种隐性呼唤的“承文本”关系,通过对经典文本具有“分散”意味的“改造”进行了“戏仿”。“大禹治水”处在从传说时代到历史时代的过渡阶段,鲁迅将诸如“化黄熊”、“抓妖怪”的神话故事和《夏本纪》之语前后拼接,模糊了具有虚构性的传奇和“真实”的文献史料之间的界限。另外,《论语》中所推崇的涉及祭祀、朝拜等饮食、穿衣上的礼仪规范,反而成为小说讽刺意味的来源,在禹形象的“堕落”中传达出对被固化为制度性的“礼教”意识形态之否定。可以说,小说第四节在“戏仿”中实现了对一切崇高、神圣、正确的“经典”的彻底颠覆。
三、小说、史传与寓言的叠印
关于《理水》第四节对《史记》和《论语》等经典文本的戏仿,更贴切的解读方式或许是放入中国的“史传传统”与“小说传统”的结构中思考。小说最后一节禹和舜的谈话以及对阔绰漂亮的禹爷的刻画,背离了前三节那个不穿袜子、伸开两脚而坐的富有人性的、鲜活的大禹形象,这意味着正统秩序对“小说”之语的排除和否定,而文本对史传的戏仿则又将其放入了“小说”的元叙事行为,从而构成了针对史传对小说的“否定之否定”。汪晖通过对比鲁迅《故事新编》的“拟古史”叙述和顾颉刚的《古史辨》及其周边古史叙述,分析了鲁迅在文学实践中如何召唤出被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双重遮蔽的历史幽灵。①《理水》的最后一节将民间神话传说同信史记载、儒家经典并置,也可以在象征意义上理解为鲁迅要把被实证科学历史研究驱逐出去的神话、传说、演义重新编入“史传”的谱系。
《汉书》中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②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的地位。而鲁迅早期就颇看重神话传说的历史价值,致力于将小说的传统从正统史录中挖掘出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小说脱胎于神话,因此“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③然而,在主流的史传书写中,“神话”要么被排除在正史之外,要么被正史的话语体系收编,正如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也都“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进入现代学科的语境,“鸟头先生”要通过考证的方法抹杀禹的存在。这都意味着非书面、非历史化的神话无法抵达那个声称自身正确的“历史”,民间传说里那些带有奇幻和荒诞色彩的关于禹的故事,更无法被“真实”所统治的理性世界接纳。
《故事新编》是鲁迅从神话世界提取精神力量的尝试,而诞生于“神话”的“小说”同样是被正史所压制的文学体式,寄托着鲁迅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方式。陈平原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取得的成就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一是中国小说受到西洋小说输入的影响发生变化,二是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并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④这也是现代小说形成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系统中,小说是稗官野史、是文学和意识形态的支流,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化界渐渐形成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小说甚至承担着更新道德、改良社会的重大使命,足以和史传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小说和史传始终相互纠缠、相互映照,二十世纪以来新型小说范式的建立进程中,引“史传”入小说的文体渗透发挥了重要作用①。然而,不同于“新小说”作家取法史传以补正史之阙的写作抱负,也不同于许多“五四”小说家受史传影响而形成重实录的现实主义追求,鲁迅的现代小说在形式层面上对民间性的“神话”与正统性的“史传”进行重述与再创造,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旨归。
如果说“神话”是用来对抗在遗忘和抗拒遗忘的循环中存在的集体记忆的再现,那么鲁迅用“小说”重启的更是无名者的历史。大禹作为治水的领导者固然是英雄形象的凝聚体,是被百姓们歌颂、被载入史册的“人王”,但更进一步超越了传说和神话的讲述逻辑的,则是鲁迅写到的那些“不动、不言、不笑”的“黑瘦的乞丐”,他们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无法掩盖光辉的“中国的脊梁”②。编写新的历史题材小说不是用历史来覆盖小说,也不是用小说来抗衡历史,而是表明无论是“小说”还是“史传”都在“历史”沉淀的过程中进入了群体心理和集体意识,成为国民性格乃至民族精神的组成片段,也就是说,看似颠覆历史的新型小说反而是为了将被虚化的历史重新清洗整理,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漩涡。
“小说”和“历史”的对抗与互渗,使得《故事新编》具有了某种寓言性。“在双重或多重时间之间的闪回赋予《故事新编》中的故事/古史以双关或互指的特点,也因此奠定了这些作品的寓言性:寓言总是以过去为当代人提供道德启迪,从而其寓意总是双关的。”③代田智明指出鲁迅小说中“现在和过去常常是激烈地进行着往复运动”的逻辑构造,而“《故事新编》就是夺回包含了过去和现在的整个历史的真实感的尝试”④。“小说”以其虚构性为统摄,而“史传”形式的介入又宣告过去的真实性,当对“历史”的变形与再现皆指向现实语境,“小说”也就成为新的“历史”。作为历史题材小说的《理水》成为多重文学传统的叠印,在虚假与真实的混淆中照亮历史,在过去与当下的重合中通向未来,在小说与史传的合作中建立新的现代寓言。
余论:也谈鲁迅的历史观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依靠着某种特定的叙述话语,历史材料和历史事实需要用历史话语来讲述。历史小说的创作天然包含了参与历史的叙述冲动,对历史事件的“重写”透露出作者的历史判断。如果说鲁迅讽刺顾颉刚考证中对“大禹”存在性的怀疑以及背后的虚无主义立场,那么他自己通过“故”事“新”编完成的对历史的“戏仿”又意味着怎样的历史观?从鲁迅对“正史”的反思可以看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本就遮掩在“变戏法”的叙述者所书写的重重谎言之中,“相斫书”提供的道德价值也就不足为训。因此,在艺术创作中如果过度注重对所谓“真实”的实证性考察,就很容易又一次踏入历史的轮回当中。与其在循环的历史中拾取陈旧的思想碎片,不如对“历史”进行彻底地颠覆,从而获得用行动重构“历史”的可能。
考察鲁迅的历史观,不妨以章太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民族观作为参照。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对晚清以来科学派的疑古思潮加以批判,促进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鲁迅的怀疑主义并不是在考古辨析的意义上修补“历史”,而是在思想革命的层面重述“历史”。因为一切“本事”都只是被观看的对象,终极目的是要在历史中寻找“人”,探究被历史叙述的人该如何叙述历史,最终找到参与历史、书写历史的真的“人”。
① 鲁迅:《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第390页。
② 同上,第390—391页。
③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④ 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5页。
⑤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
⑥ [苏]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①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54页。
② [日]木山英雄:《〈故事新编〉译后解说》,刘金才、刘生社译,《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1期。
③ 王瑶:《〈故事新编〉散论》, 《王瑶文集》(第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④ 陈平原:《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09页。
⑤ 鲁迅:《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第400页。
⑥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东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颠覆与重构之间的历史:《理水》的“戏仿”诗学
① [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② 刘春勇:《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
③ 祝宇红:《论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90页。
⑤ 鲁迅:《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第399页。
⑥ 同上,第400页。
⑦ 以上对《左传》《绎史》《古岳渎经》《论语·泰伯》等历史典籍引用内容的考证,参见《鲁迅全集》中《理水》一文的注释,引自《鲁迅全集》(第2卷),第406—407页。
⑧ [法]热奈特:《隐迹稿本》,《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
① 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文史哲》2023年第2期。
②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④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颠覆与重构之间的历史:《理水》的“戏仿”诗学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09页。
②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③ 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文史哲》2023年第2期。
④ [日]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李明军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侯佳彤,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