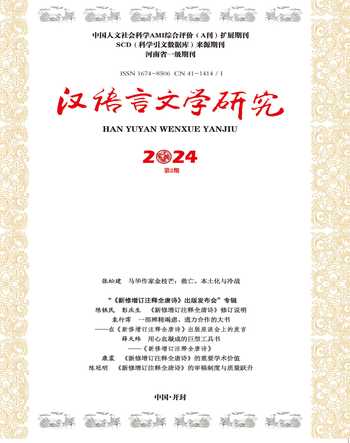成为“无告之民”
① Richard Sigurdson. Jacob Burckhardt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Division,2004,p.217.
②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 507页。
③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第196页。
④ 贺照田:《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引社会科学治史思路的限度》,贺照田等:《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唐山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页。
⑤ 罗成:《作为方法的“历史—人心”——重构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探索与争鸣》2023第2期。
⑥ [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李晶浩、高天忻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399页。
“永恒轮回”与历史认知——尼采时间美学的观念生成及其人文意义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② 钦文:《鲁迅先生的肥皂》,《文季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
③ 李长之:《鲁迅批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④ [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摘 要:《肥皂》虽然以“圆熟”的技术、“深切”的刻画受到鲁迅本人的重视,但在后来的研究中较少被关注。学界对于其文本内涵的阐释,经历了从“反封建”到“现代性”的路径转换。通过对小说的叙事形式及“肥皂”这一象征意象的分析,《肥皂》呈现出主人公四铭成为“无告之民”的过程,可以窥见鲁迅对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的心理状态的观察和体认方式。
关键词:《肥皂》;《彷徨》;鲁迅
一、“圆熟”与“热情”的消长:已有研究对《肥皂》的解读
鲁迅本人对于《肥皂》的写作非常重视。1923年3月27日和28日,《肥皂》分两期在《晨报副刊》连载,1926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彷徨》,其间鲁迅对小说文本作了多处修改。1933年,鲁迅将《肥皂》编入《鲁迅自选集》;1935年,他又将之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导言中写道:
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①
由此可见,鲁迅在自述中一方面强调《肥皂》《离婚》等小说在技巧上的圆熟、深切,一方面也注意到了它们在读者接受效果上的不尽如人意。
事实也正是如此: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一经出世便引起轰动不同,自1924年3月发表到鲁迅逝世之前, 《肥皂》的反响寥寥,甚至没有一篇专论出现。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才有了许钦文对于《肥皂》的评论。在分析了《肥皂》中体现出的鲁迅先生以幽默讽刺了四铭、何道统和薇园之流后,许钦文仍觉得需要为选择《肥皂》为批评对象而作一些自我辩驳:
我并不把《肥皂》当作鲁迅先生遗作中的最重要的部分看待,也不以为这是《彷徨》的代表篇,这样说一下,于偶然的兴致关系以外,无非因为,觉得鲁迅先生的后期作品,已为大家所共赏;以为他的前期作品,也还有着值得细心研究的地方。同时,想藉以说明,说是趣味也可以,说是幽默也可以的,在问题文学,总只是一种装饰,并非是本质的要素。②
此外,在同年出版的《鲁迅批判》中,李长之更是不客气地将《肥皂》形容为“沉闷、松弱和驳杂”,在“故意陈列复古派的罪过,条款固然不差,却不能活泼起来”。③1943年,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也将《肥皂》称为“笨拙之作”。④
或许正因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鲁迅的小说中,《肥皂》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直到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肥皂》视为鲁迅小说中就写作技巧来看最成功的作品后,这一低评价的现象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①王富仁、温儒敏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对《肥皂》进行了研究,而关注的重心则从“国民性”转向了“现代性”。许钦文在1936年曾化用“《肥皂》”这一标题,将小说比喻为给国民的精神以洗涤的“肥皂”②;王富仁则认为《肥皂》存在着“新道德”与“旧道德”之间两种价值观的尖锐对立,四铭是在“用旧道德否定新事物”,鲁迅则“用新事物否定旧道德”。③温儒敏借用精神分析理论对《肥皂》中的潜意识的心理描写进行了研究,认为《肥皂》中运用的潜意识描写,体现出“封建统治思想与道德观念是从根本上束缚与戕害人性的,当然也包括束缚戕害道学家的人性”④。进入21世纪,研究界努力打破对于鲁迅小说以改造“国民性”为目标的基本预设,为鲁迅文学的解读提供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视角。陈建华从现代性和商品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肥皂》表现的是四铭“不自觉被肥皂和小家庭所蕴含的社会‘进化过程所形塑”的过程,并以此体现出鲁迅“对都市经济秩序、个人物欲赋予某种理性且不乏包容的思考”。⑤
对《肥皂》的多种解读,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小说绵密的文本中蕴涵着多重解读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由于文学理论资源的不断涌现,为文本提供了更多阐释的可能。但直到今天,在鲁迅小说的接受和阐释史中,《肥皂》或许仍然可以称为一篇被“边缘化”的小说。本文则尝试从小说文本“圆熟”的形式出发,探究鲁迅在其中倾注的“热情”之所在。
从小说情节来看,四铭虽然经历了几个小“插曲”——在与妻子四太太和儿子学程之间的对话造成了不愉快,在与何道统和薇园的交谈中也受到了戏谑和调笑,深夜在院子里踱步,感到自己成了孤苦伶仃的“无告之民”——但第二天一早,四铭买来的肥皂被四太太正式“录用”,一切似乎重返正常状态。从这一点来看,《肥皂》可被视为一个“几乎无事”的故事——这或许也是小说“减少了热情”的表现之一。但笔者以为,在这一“几乎无事”的日常状态下,四铭逐渐感到自己成为“无告之民”的过程或许更耐人寻味: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鲁迅以其“圆熟”的技术、“深切”的刻画,隐秘地书写出20年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的精神困境。
二、视点的转移和两次空间“复写”
五四时期大量西方现代小说和文艺理论的涌入,使得五四作家们开始自觉地关注小说叙事方面的技巧。不过,正如陈平原指出的那样,“五四作家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得心应手,使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则老捉襟见肘”。在“意识到应该使用第三人称叙事与熟练运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这其间有好长一段距离”。⑥从这一角度来看,《肥皂》可被视为熟练使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典范性的小说,这一成就也依赖于鲁迅在小说文本中的苦心经营——笔者以为,对于《肥皂》中的第三人称限制叙事,鲁迅是有着充分的形式自觉的:在1923年的初刊本与1926年收入《彷徨》的成集本之间,鲁迅曾做出多处包括小说叙事形式在内的修改;这些修改使得小说中四铭逐渐产生“无告”之感的过程更显浑然天成。
《肥皂》使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但其中叙述者采用的视点——即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并不固定,而是经历了明显的转变。在小说的前一部分,叙述者以四太太为视点进行叙述。小说开始,四铭从外面回到家中,将买回来的肥皂递给四太太,大声地呼唤学程下楼的一系列行动,都在四太太的视点中呈现出来。此时的家中仍然体现出较为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四太太在家中糊纸锭,等待丈夫外出归来,虔诚而感动地接受丈夫的馈赠,并在儿子未听到父亲的叫声的时候着急地喊他下楼,属于较为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在妻子的视点中,作为丈夫的四铭也同样稳定地承担着一个传统家庭中的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在收到肥皂后,四太太感受到了来自丈夫射在她脖子上的眼光的凝视;学程迟迟不下楼,也使得四太太开始为家庭中的父亲形象保持权威提高了喉咙,尽力地叫学程的小名——或许是为了保持四太太的视点的一致,此处在《彷徨》单行本中,鲁迅将《肥皂》初刊本中的“学程”也改为了“拴儿”,可见其对叙述视点的设定具备审慎的自觉。
但四太太的视点并未贯穿整篇小说,而是随着四铭和学程的对话开始发生转移。当四铭询问学程“恶毒妇”是什么意思,并因为他不知所以的回答大发脾气时,视点开始逐渐转移至四铭。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看似传统的家庭伦理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四铭的视点中,学程表面恭敬实则敷衍,在一家人一起吃饭时夹走了他原本看中的菜心,打破了传统的“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妻子也因为孝女与他产生争执,并说出了“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的话。可见,与四太太的感受不同,在四铭看来,传统的家庭伦理正产生动摇,“父”与“夫”所代表的绝对权威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处境,而这一感受是在以四铭为视点的叙述中逐渐显现的。
视点的选择使得叙述者避免了对人物内心想法进行直白的陈述,叙述者的态度也因此不必依赖于对人物的直接评价便得以表达。这一叙事的方式,或许并非全然来自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吸收和模仿,而是有着源于传统的文化资源的借鉴。韩南曾将《肥皂》中所使用的技巧称为“性格反语”,并将其来源追溯至《儒林外史》:
性格反语的三篇作品是《肥皂》、《幸福的家庭》和《高老夫子》。这些作品里都没有明显的反语评论,却突出了造作与行动之间的反语对比。……这类技巧的来源之一则是十八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这是一切文学中性格反语最伟大的典范作品之一。①
鲁迅于1920—1922年间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并对《儒林外史》有着特别的关注,将其称为中国唯一真正的“讽刺小说”。其中最为赞赏的,是作者“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的叙述手法。②《肥皂》或许也可被视为对这一叙事技巧的尝试。在小说中,叙述者实现了最大程度的“隐身”,不再直接对人物发出议论,或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正面描写,而是通过增加人物语言与人物行为之间的参差龃龉来加以呈现。在四铭愤怒地叫着让学程去继续查字典时,初刊本并未描写学程的反应,而是直接开始了四太太的回应;成集本则加入了“学程看了他几眼,没有动”的动作描写——通过四铭的暴怒和学程的无动于衷的对比,父子两代之间心理状态的隔阂也随之暴露出来。即便是在为数不多的叙事部分中,鲁迅也在尽力减少对于人物心理状态的直接描写。在初刊本中,四铭在院子里踱步时,面对着黑夜,心中浮现出了“外面是一个孝女扶着她瞎眼的老祖母在冷酷的人海里沉浮”的场景;成集本则将其删去,改为“黑夜就从此开头”,进一步减少了叙述者对人物内心的介入,也更加接近鲁迅在评价《儒林外史》时欣赏的文本效果。
对人物的评价和介入的减少,使得叙事更多地依赖人物的行动以及对其行动的外部空间的构建来进行。在面对传统代际关系和性别关系近于失效的处境时,四铭视点中的同一空间场景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变。小说分别描写了两次堂屋以及中间的桌子。第一次是在一家人聚在堂屋吃晚饭的时候,此时桌旁吃饭的几个人的方位描述得非常清晰:
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像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③
此时的四铭处于上首居中的位置,毫无疑问地位于空间的中心。而当四铭与四太太发生争执,并与何道统与薇园拟定两个题目,以及出现了多次关于“咯吱咯吱”的调笑后,四铭怀着忐忑回到堂屋,桌子周围众人的方位发生了变化:
他一进门,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那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绞。秀儿和招儿都蹲在桌子下横的地上玩;学程坐在右横查字典。最后在离灯最远的阴影里的高背椅子上发见了四太太,灯光照处,见她死板板的脸上并不显出什么喜怒,眼睛也并不看着什么东西。①
此时,四铭带来的肥皂被放置在桌子的正中间,取代了四铭的位置;四太太、学程和招儿的方位也发生了改变。四铭甚至进一步产生了招儿在他背后说“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的幻觉。
当以自己为中心的空间布局改变后,四铭觉得“存身不住”,走到院子里来回踱步。而这时四铭的心境和看到的场景也与前文中第一次来到院子的时候有所不同。这是小说从四铭的视点对他两次走到院子里的场景描写:
(第一次)四铭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里还明亮,学程就在墙角落上练习八卦拳:这是他的“庭训”,利用昼夜之交的时间的经济法,学程奉行了将近大半年了。他赞许似的微微点一点头,便反背着两手在空院子里来回的踱方步。不多久,那惟一的盆景万年青的阔叶又已消失在昏暗中,破絮一般的白云间闪出星点,黑夜就从此开头。四铭当这时候,便也不由的感奋起来,仿佛就要大有所为,与周围的坏学生以及恶社会宣战。他意气渐渐勇猛,脚步愈跨愈大,布鞋底声也愈走愈响,吓得早已睡在笼子里的母鸡和小鸡也都唧唧足足的叫起来了。②
(第二次)他觉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烛,踱出院子去。他来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鸡和小鸡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来,他立即放轻脚步,并且走远些。经过许多时,堂屋里的灯移到卧室里去了。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白云间,看不出一点缺。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孤苦零丁了。③
四铭第一次来到院子里时,白云如同毫无美感的“破絮”,母鸡和小鸡唧唧足足的叫声并不能阻止他的脚步越跨越大——此时四铭关注的并非周围的实际环境,而是“与周围的坏学生和恶社会宣战”的感奋之情。当四铭第二次踏进院子里时,虽然也是踱步,但当他又吵醒了母鸡和小鸡时,他便立刻放轻了脚步;一地“无缝的白纱”似的月光和“玉盘似的月亮”此时进入了四铭的视线,叙述转为感伤而抒情的语调,四铭也在此处成了孤苦伶仃的“无告之民”。
由上所述,叙述者从四太太的视点逐渐转为四铭的视点,并以四铭的视点复写了两处相同的空间,呈现出了由一块肥皂暴露出的一个看似传统的家庭中伦理关系的变化,以及作为传统一家之主的四铭在面对这一变化中,由“独居一面”到变成了“无告之民”的心理转变。
“无告之民”出自《礼记·王制》:“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夫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④儿女双全、妻子康健,不愁衣食的四铭显然不属于其中之列;叙述者在此处采取四铭的视点,却通过使用来自古籍但并不符合原义的词汇,表达对于四铭的反讽;而这一感受涉及了哪些1920年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的重要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三、作为象征的“肥皂”
由上所述,在小说的叙事中,通过视点的转换和两次空间复写,四铭完成了由“一家之主”到“无告之民”的心理转变;从文本来看,这一变成“无告之民”的惆怅或许并非全然无病呻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920年代徘徊在新旧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和思想变革时某种普遍性的感受。笔者以为,“肥皂”作为小说中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将这一感受以某种滑稽的方式具像化了。
肥皂的象征意义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注意。许钦文在评论中将《肥皂》比喻为“用以洗涤人们的精神的肥皂”①,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进行阐释;吕周聚、陈建华等则将小说中的肥皂与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相联系,将小说中由肥皂引发的风波视为现代商品经济揭开个人物欲,并因此冲击传统家庭结构和伦理关系的隐喻。②上述观点都颇具启发性,为小说文本提供了更多阐释的维度。但笔者以为,“肥皂”作为小说文本中的象征性意象,其所指实际上经历了某种游移,这其中或许隐现着叙述者在两种所指蕴含着的宏大命题中“彷徨”的姿态。
在初刊本中,《肥皂》并非全文在同一期登出,而是分为上、下两期见于《晨报副刊》。其中,上期以四铭让学程查字典结束,下期则以四铭对四太太大骂“新文化”与上街时遇到的孝女为开始。这一分割或许是出于版面篇幅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但笔者以为,这也恰好是肥皂这一意象的内涵开始发生转变的节点。在前一部分中,四太太对四铭送给自己肥皂的行为,虽然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并未洗干净脖颈后的尴尬,但在叙述层面上,并未点名肥皂与“性”的关系;此时,在四太太眼里,作为现代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构成的市场竞争的产品,肥皂不仅在效果质量上优于传统手工制造业的“皂荚子”,也具有更加诱人的外观——小说开头以四太太的视点,对肥皂从包装到实物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还看见葵绿色的纸包上有一个金光灿烂的印子和许多细簇簇的花纹。……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也来得更浓了。③
在商品经济所引起的市场竞争中,即便是作为日常用品的肥皂,也为了吸引消费者的购买而被制作、包装得非常精致。文中反复出现的“葵绿色”、“细簇簇的花纹”和“说不清的香味”,强烈地刺激着四太太的感官。其后,四铭也回顾了自己在多种价格和做工不同的肥皂中挑选最具“性价比”(用四铭的话来说,最“中通”)的肥皂的过程:
我一气看了六七样,都要四角多,没有买:看一角一块的,又太坏,没有什么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绿的一块,两角四分。④
此时,无论是四太太将其与“皂荚子”作对比,还是其后四铭在价格不同的肥皂中挑选价格适中的一款的行为,肥皂主要作为现代工业制品与商品经济的象征出现于文本之中。在与四太太的交谈中,四名恼怒的原因也逐渐被揭开:在买肥皂时因为挑拣太“噜苏”受到了旁边的青年学生用听不懂的外文词汇的嘲笑。但这并非由于四铭对市场交换规则的不熟悉,反而是过于“经济”——对商品价格和质量的计较——导致的结果。可见,作为城市居民,小说中的四铭早已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逻辑(虽然四铭将其称为带有儒家色彩的“中通”)——实际上,在小说叙述中也可以看到,“经济”已经渗入四铭的观念之中:命令学程在昼夜之交练习八卦拳的行为,便来自四铭对时间之“经济”的认识。
实际上,提倡“经济”、追求效率,是五四以来现代时间意识进入中国的表现之一。这一观念也延伸至文学领域,被作为文学评价的尺度和标准之一。胡适就曾在《论短篇小说》中认为“今日中国的文学, 最不讲‘经济”;短篇小说便作为 “经济”的文学得到推崇。对此,李国华指出:“‘经济一词作为胡适论述短篇小说的关键词, 表明文章背后的时间意识不仅是进化论意义上的线性时间意识, 而且带有科学和实用的色彩。这种科学和实用的色彩, 准确地说, 乃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的时间意识。” 这一意识追求的是效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用的最大化。
而《肥皂》将学程练习八卦拳的时间定在昼夜之交称为“经济之法”,则不无包含叙述者对四铭的讽刺,也暗示着鲁迅对于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误用的警惕。虽然鲁迅也将短篇小说的流行解释为人们由于忙碌而无暇看长篇的结果①,自己也多作短篇小说与时效性较强的杂文,但李国华通过分析《狂人日记》中“文言”和“白话”所象征着的两套时间系统的拼接后指出,这两套时间系统,“一方面契合着胡适《论短篇小说》‘横截面的理论, 另一方面则通过拼接之处的龃龉挑战着‘横截面理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②当学程用看似最“经济”的时间练习复古派倡导的八卦拳时,“经济”便成为对“现代”观念不经分辨便进入传统的话语体系,并因此造成“能指”与“所指”分离的概念之一。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四铭将话题转移至对新文化的批判和围观孝女的事件,并向四太太转述两个光棍说要给孝女用肥皂 “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时,肥皂逐渐从标志着传统手工业的“皂荚子”转换到引起对“孝女”的性幻想的物品。此后,如小说开头对肥皂“葵绿色”、“细簇簇的花纹”等外观的强调的次数大大减少,而是转换为多次出现的“咯支咯支”。这一拟声词首先由四铭转述,后分别为四太太、何道统多次提及。如果说这一拟声词与四铭对孝女的性幻想的关系在一开始并未上升至四铭的意识层面,那么在他人的多次重复后,这一意识更加清晰地得到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四铭首先是反驳,认为四太太是胡说,因为 “那话是那光棍说的”;而后在何道统对“咯支咯支”哈哈大笑时,四铭的情绪则变为慌张,愤愤地制止他不停复述这句话的行为。最后回到堂屋时,四铭的脑海里已经开始产生“咯支咯支”和“不要脸”的幻听,“无告之民”的感受最终在四铭在院子里踱步时产生。
这一过程,实际上也与传统礼教中“孝道”这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断裂同步进行着。将孝女的形象赋予性的意味,是对“孝”在传统儒家伦理中的基本意涵的嘲弄和玩味。这一联想并非虚构,而有其现实来源。1927年7月,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中曾提及1920年上海某书店出版《男女百孝图全传》: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③
上海是19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商品经济的发达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和出版业的发展。虽然此时鲁迅身居广州,尚未到达上海,但对上海出版商以男女之事博取读者眼球并以此获益的行为也颇为熟悉。不过,鲁迅并未将这一现象归结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欧化东渐”,而是将其视为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的“礼”本身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绵密的研究。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
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鸣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①
此处鲁迅以后人对正史中曹娥“抱”父尸出的“抱”的动作为例,揭示了“人心浇漓”并非由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所致,而是“礼”与“情”长期分离的表征。这在小说前半部分则已经有所暗示:“孝”在儒家伦理中被视为“百行之先”,作为维持代际关系的方式,“孝”不仅是礼仪,更是情感纽带。《论语》中便将“有养”与“敬”区分开来,认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②而从四铭与学程的对话则可以看出,学程虽然遵守着四铭的“庭训”,但对四铭表面恭敬、实则敷衍的做法,并无 “孝”必须具备的情感基础“敬”。当“孝”早已是空洞的“礼”的符号时,其内涵遭到随意的填充则是必然的结果。从小说中薇园的话中可知,“孝女”实际上是一个“外路人”,由于没有人听得懂她的话,其行状根本无人知晓;她是孝女,也只是因为“大家倒都说她是孝女”——“孝”或“不孝”已经成为一种话语的建构,并没有实质的情感或行为的表达作为支撑。由此,小说文本在后半部分叙述的重心又一次回到了《怀旧》以及《呐喊》中的多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对名实不符的“礼教”的批判。
由上所述,从作为“商品”到作为引起性幻想的物品,肥皂在文本中的象征性内涵经历了某种游移:从四铭挑选肥皂的行为可以看出,西方的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虽然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四铭的思考逻辑——但四铭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以“中通”解释之。将在昼夜之交练习复古派提倡的八卦拳称为“经济之法”,也体现出了“经济”这一概念在接受过程中经历的某种程度的变形;而当肥皂与孝女和“咯吱咯吱”等相联系,并作为引起情欲的象征时,由传统礼教所维系的伦理关系中 “礼”与“情”之间的断裂也得到揭示。正是在由多重的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所引发的矛盾发生后,四铭面对本应象征着团圆的圆月,反而产生了孤苦伶仃的“无告”之感,他在新旧交替时代之间的尴尬处境也得到了更加“深切”的刻画。
四、结语
综上所述,《肥皂》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中,通过适当减少对人物内心活动的介入和评价,并精心选择叙述视点以及对空间的复写,对四铭从“一家之主”到“无告之民”的身份感知的变化过程进行了精妙的叙述,成为被研究者评为“纯客观叙事”的典范。③“肥皂”在小说中被赋予的双重意涵,则揭示了1920年代西方的商品经济和思想文化——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涌入的较为激进的新思想——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冲击。四铭曾提及自己在光绪年间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见他也曾倾心于维新派,但维新变法并未如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撬动传统的思想根基。鲁迅在《肥皂》中,通过对四铭逐渐成为“无告之民”的心理状态的刻画,展现了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礼教必然、也正在崩溃的过程。
但礼教崩坏的必然趋势是否意味着对新文化引入并提倡的新概念的全盘接受?小说中“肥皂”象征的游移或许隐现着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肥皂》中,四铭购买肥皂的商品交换行为、对“经济”的误用、四铭的家庭内外对“孝”之内涵的颠覆,不仅延续了《呐喊》反传统反礼教的主题,也同样体现出对新文化人提出的新概念的犹疑。对于四铭而言,无论是旧礼教还是新文化,似乎都已成为空无一物的能指,其所指究竟为何,或许不仅是他在庭院里不安地踱步时需要思考的内容,也是1920年代后的新文化人需要时时反顾的问题。
①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② 钦文:《鲁迅先生的肥皂》,《文季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
③ 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④ 温儒敏:《〈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⑤ 陈建华:《商品、家庭与全球现代性——论鲁迅的〈肥皂〉》,《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⑥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成为“无告之民”——《肥皂》细读
① [美]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③ 鲁迅:《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① 鲁迅:《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第55页。
② 同上,第50—51页。
③ 同上,第55—56页。
④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成为“无告之民”——《肥皂》细读
① 钦文:《鲁迅先生的肥皂》,《文季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
② 具体论述可参考吕周聚:《“肥皂”的多重象征意蕴——鲁迅〈肥皂〉的重新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2期;陈建华:《商品、家庭与全球现代性——论鲁迅的〈肥皂〉》,《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③ 鲁迅:《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第45页。
④ 同上,第49页。
① 鲁迅曾在《〈近代世界小说短篇集〉小引》中写道:“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鲁迅:《〈近代世界小说短篇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② 李国华:《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对读》,《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③ 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成为“无告之民”——《肥皂》细读
① 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36页。
②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页。
③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99页。
作者简介:刘雨佳,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