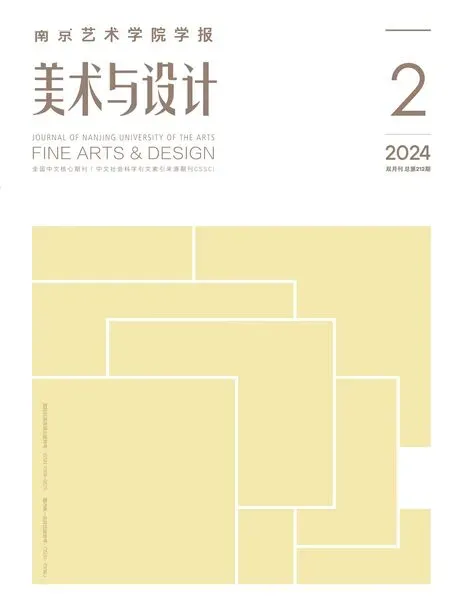《画史会要》“朱谋垔托名说”辨误
赵阳阳(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朱友舟(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与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崇祯四年(1631)编成的《画史会要》五卷,仿陶宗仪《书史会要》体例,摭取历代画家资料汇于一编,尤致力于明代画家资料的搜辑,《四库全书总目》评之曰:“宋、金、元、明诸画家颇赖以考见始末,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画家传中多引以为据,亦谈丹青者所不可遽废也。”[1]3542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评此书:“至明代画人传,则以前作者无闻,搜辑颇见勤至,后来考录明代画家者多本之。”[2]故今人考索明代艺苑人物,多借资此书。①清代的大型书画史料汇编如《佩文斋书画谱》《历代画史汇传》等对《画史会要》采录极多;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陈田《明诗纪事》等书引及《画史会要》中明代画家史料也颇多,可见此书史料价值之一斑。即如余绍宋所讥“最为无聊”的第五卷《画法》部分,也保存了邹迪光、张复、王式、徐尚德、郑元勋等人不见于他书的画论,虽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
然而关于《画史会要》的编者,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多数记载认为是朱谋垔所编,仅清官修《佩文斋书画谱》、惠栋注《渔洋精华录》、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等少数文献著录为金赉撰。②近代以来撰画史者颇有以《画史会要》属之金赉者,如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中谓舜妹画嫘有画祖之号,引金赉《画史会要》“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参见: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第4页。又有将金赉置于中国文人画史的重要位置,如卢辅圣《中国文人画史》附录《中国文人画史纲》卷十三《脱序的文脉》篇三《超越困境》章三《激进与保守》部分更将金赉与何良俊、李开先、徐渭、项元汴、王世贞、王穉登、屠隆、董其昌、李日华、詹景凤、李流芳等并列。参见:卢辅圣:《中国文人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644页。此书编著者究竟是明人朱谋垔抑或金赉,需重加稽考。
一、民国学者对《画史会要》作者归属的讨论
最早关注《画史会要》作者归属问题的是傅增湘。民国十八年(1929),傅增湘获见珊瑚阁旧写本《画史会要》五卷,谓“明朱谋垔撰”,跋云:“旧写本。题‘云岩默老金赉敷奇氏撰’‘颜巷逸人校’。卷一三皇至五代,卷二宋,卷三金元外域,卷四大明,卷五画法。前有自序,言曾续陶九成《书史会要》一卷梓行之,故更为此,则仍朱谋垔所撰,而改题金赉,不知何故。后有颜巷逸人跋。钤有‘珊瑚阁珍藏印’(朱)、又满汉文关防四方。(己巳)。”[3]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之民国二十五年(1936)排印本卷首有傅增湘题写书名,可见莫伯骥与傅增湘之关系,傅增湘所经眼之旧写本《画史会要》,应当就是在莫伯骥处所见。傅增湘以旧写本自序中言金赉有《书史会要续编》一卷付梓,而《书史会要续编》一卷著录书皆以为朱谋垔所撰,因此认为此《画史会要》“仍朱谋垔所撰”,但对其“改题金赉”,颇为疑惑。民国二十一年(1932),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出版,此书卷一《画史会要》条下注云:“《佩文斋书画谱》纂辑书目作金赉撰,《续编》作朱谋垔撰,未详何据。《续编》今未见,他书亦未见著录。”[2]其所谓《续编》,指《佩文斋书画谱》纂辑书目中所列《画史会要续编》,署朱谋垔撰。③《佩文斋书画谱》著录《画史会要续编》显系讹误,历来著录并未见此书之记载,致误原因大概是将《画史会要》归于金赉,复因朱谋垔有《书史会要续编》之纂辑而想当然地造出《画史会要续编》一书,并归于朱谋垔名下。显然,余绍宋仅据文澜阁抄本署名朱谋垔的《画史会要》著录,并未见到署名金赉编撰的《画史会要》。
最早对《画史会要》作者归属进行考辨的是民国藏书家莫伯骥,①民国二十五年(1936),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由广州文光馆印行,《跋文》收书403部,不及《目录初编》所收914部之半,然其内容有大量增补,二书字数约略相当。就《画史会要》跋语而言,二本大同小异,《跋文》仅略有增补而已,今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为准。其《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卷八著录《画史会要》旧写本云:
《画史会要》五卷(旧写本,珊瑚阁旧藏),前题云岩默老金赉敷奇撰,颜巷逸人校。此书,清四库提要作朱谋垔撰,当即吾家著录之刊本。而《佩文斋书画谱》纂辑书作金赉撰,《续编》为朱谋垔撰,未知所据。《孙氏祠堂书目》亦题撰人为金赉。伯骥得此写本,初阅题名,颇以为疑。书之前序,则刻本与写本同,而写本多后跋,为金氏表弟所撰者。[4]289
考《佩文斋书画谱》之“纂辑书籍目”、②四库本《佩文斋书画谱》之“纂辑书籍”目录中载“《画史会要》,金赉。”参见: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当是其所据抄本编者题名为“金赉”。《四库全书总目》之《画史会要》提要云:“《画史会要》五卷,明朱谋垔撰,是书成于崇祯辛未……此书为谋垔所自编,既以金列元前,稍移其次,而所列名人虽太祖、宣宗亦次于外域之后。”四库提要既然参考《佩文斋书画谱》, 应知《书画谱》著录《画史会要》之作者为金赉,然提要仍以其作者归于朱谋垔,大约以为作金赉者不确,而《书画谱》亦为御定之书,不便明言批评,仅在《画史会要》提要中特为点明“此书为谋垔所自编”。衡之提要之体例,一般仅说某人所编,此谓之“自编”,似暗含对《书画谱》的订正,此细微之处,不可不辨。此外,清代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八《经籍考》著录“朱谋垔《画史会要》五卷”,亦肯定朱谋垔的编撰权。《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六臣注文选》二函十六册”条[5]83及“《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函六册”条[5]152引及《画史会要》,均作金赉撰。随后,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亦明言《画史会要》编者为金赉。[6]实则除此之外,尚有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引及《画史会要》,也署作者为金赉。康熙丙辰(1676),王士禛作《勾龙爽蜡屐图为牧仲题》,题下惠栋注引金赉《画史会要》云“勾龙爽,蜀人,神宗时为图画院祗候。善作中古人物”。[7]考《佩文斋书画谱》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因此似于此前已有题名金赉所撰之《画史会要》抄本流传。
莫伯骥在《群书跋文》中对余绍宋的疑问进行了回应:“此书似是金氏手撰,久而未刻,遂为谋垔托名流布者。故后来惟明人流传写本,尚题金氏姓名,特留此以窥破朱氏伎俩。”[4]290谢巍在莫氏基础上坐实其说:“金氏之书撰成在前,朱氏乃取之重纂,改头换面有删有补,而以己名付梓。”[8]376
经过莫、谢二氏的考定,似乎《画史会要》为金赉所编已无疑议。然而重估此案,会发现两位前贤皆有曲解证据、强词夺理之处,尤其莫氏恃于己藏之抄本,心存先入之见,遂致冤词。
二、珊瑚阁写本与通行本文字之差异
据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卷八,知其所见珊瑚阁写本与通行刻本内容存在差异:“书之前序,则刻本与写本同,而写本多后跋,为金氏表弟所撰者。”[4]289莫氏所云讹误有二,一是刻本与写本书前之序并非完全相同,二是写本之后跋在崇祯初刻本和顺治补刻本中均有,并非写本所独有。
依莫伯骥说,珊瑚阁旧写本“书之前序”与通行刻本同,检顺治补刻本《画史会要序》云“国初天台陶九成著《书史会要》九卷,余为续一卷,即梓行之矣”。也就是说如果金赉是《画史会要》编者的话,他应该也编著了《续书史会要》一卷。然而《续书史会要》为朱谋垔所编,学者历无异议,即使认定《画史会要》编者为金赉的谢巍,也承认朱谋垔对《书史会要续编》的编纂权。[8]376而珊瑚阁写本作者署为金赉,其人生平不详,亦未见其与《续书史会要》的任何关系,可见此旧写本为伪作的可能性反倒较大。
莫跋中所谓“写本多后跋,为金氏表弟所撰者”,其实后跋并非写本独有。崇祯初刻与顺治重修本后均有朱宝符跋,与金赉表弟所撰者文字极为接近。据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珊瑚阁旧藏写本《画史会要》书后跋云:
表兄敷奇氏撰《画史会要》,令予校而录之。兄于丹青家能原本伊始,以及支裔,采摭博而比属精,立诸小传,必甄量品行,后及艺事。兄少负奇志,力自奋于膏粱纨绮中,好苦吟,为《山居百咏》,明枕流漱石之意。故其风寄高脱,驰骤笔墨间。蚤擅旭、素之长,更从双钩响搨,探得卫、王遗法。登涉之馀,即景成图,一时能者惊服其雅不可及。兄既高介自立,无世俗游,寓苍玉居,吟啸其间,其诗可求,而人不可得而识。著作日富,岁有成刻,兹其庚申夏五告成者也。[4]289-290
而朱宝符《隐之先生〈画史会要〉跋语》则云:
宗叔隐之氏撰《画史会要》,令不肖符较而授之梓。叔于丹青家能原本伊始,以及支裔,采摭博而比属精,立诸小传,必甄量品行,后及艺事,则所尚焉者端自有在,不徒丹青家考镜已也。叔少负奇志,力自奋于膏粱纨绮中,好苦吟,为《山居百咏》,明枕流漱石之意。故其风寄高脱,驰骤笔墨间。蚤擅旭、素之长,更从双钩响搨,探得卫、王遗法。今则斯、邈、宜官皆赴笔端,固草书家一大成也。又移而用之,皴斮点擢,无不争妙。登涉之馀,即景成图,若李营丘、高尚书、倪迂、米颠,不必专有宗尚,往往任其侔合,一时能者惊服其雅不可及。雅之属为清为古、为疏澹而闲远。叔既高介自立,无世俗游,筑寒玉馆,艺大竹万竿,轩楹之馀,冷碧萧然,列古彝鼎图史,吟啸其间……其笔可求,其人不可见也。……叔著作日富,岁有成刻,兹其崇祯辛未撰也。族侄宝符梦得甫谨跋。[9]
二跋中皆有“少负奇志,力自奋于膏粱纨绮中”,检阅诸种明清传记资料索引,金赉皆无考,而“膏粱纨绮”这一身份特征,与朱谋垔则颇吻合。据胡继谦《隐之先生懿行纪略》云,“隐之宗侯,宁献王七世孙也。……诰封奉国将军,赐名谋垔,号八桂,而表伟然,而髯修然,而神奕然,而度冲然。人比之瑶林琼树,宜置之瀛洲阆苑间”。[10]跋中复云“好苦吟,为《山居百咏》,明枕流漱石之意”,胡继谦《纪略》云“时贤科未辟,侯不束于帖括,因以其颖质异能,撷艺圃之英,著《山居诗》百首,韵致不减李杜”。跋中又有“更从双钩响搨,探得卫、王遗法”,这与《纪略》所云“特擅临池,上羲献,下苏米,皆作衙官曹吏,供役于楮侯墨卿,更出心工意匠,恣游矩外,鸾螀虎跃,标帜一家”正相符合。
再将两篇跋文细作比较,可知前文系从后文中摘取文字,稍作变换。珊瑚阁写本后跋中“蚤擅旭、素之长,更从双钩响搨,探得卫、王遗法”一句在全篇中孤立存在,殊为扞格。朱宝符跋文则有“今则斯、邈、宜官皆赴笔端,固草书家一大成也”,与“早擅”句前后呼应,文意畅通。如谓后者袭自前者,且有所增衍,殊难服人。
珊瑚阁写本《画史会要》与刊本的具体文字差异,因写本已佚,只能据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引录于下:
根据以上所列异文,莫伯骥断然以为“此书似是金氏手撰,久而未刻,遂为谋垔托名流布者”,[4]290谢巍亦据以认为“金氏之书撰成在前,朱氏乃取之重纂,改头换面有删有补,而以己名付梓”。[8]376实际上,上述异文皆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跋云:“刻本先子讳多,写本作朱子讳多。”衡诸此书体例,并无称某人为某子者,此处如写本系原本,为何题“朱子讳多”,而不径称其名“朱多”?此点最为怪异。可见,写本不称“先子”“先从叔”,盖为其作伪掩饰,然将“先子”改为“朱子”,实在是百密一疏。
又刻本所缺之处,盖因莫伯骥所据家藏刊本有缺页所致,因为完整的崇祯刊本《画史会要》中,莫氏家藏本所缺条目均存在。至于其他异文则多是写本的抄录讹误,如将“左仝”误抄为“尤全”,将“裴谞”误抄为“裴请”之类。而写本较刻本缺少的内容,则是抄录时脱去的缘故。
写本补充的内容也多是臆测,非考证而得。如刻本卷四“张萱”条,写本补足缺字称“官太守”,考张萱,字孟奇,好学博识,能画,书各体皆工。万历中举于乡,官至平越知府。[11]明清时常称知府为“太守”,故缺字应为“平越”。
以上二本在文字上的差异既然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则事实上并非朱谋垔剽窃他人成书,反而是抄写者伪造编者“金赉”,且在文字上或有意改动,或抄写讹误,作伪迹象,昭然若揭。
可见,所谓颜巷逸人与金赉皆虚造之人,大约明末书估射利,伪造稀见抄本以求善价,其书虽抄自朱谋垔《画史会要》,然将其中涉及朱谋垔之信息径行改窜,如易朱谋垔的“寒玉馆”为“苍玉居”,将序跋作者朱谋垔、朱宝符分别改为金赉与颜巷逸人,不过在抄录、改窜文字时又不顾文意,任意删削,遂留下作伪痕迹。
三、朱谋垔编刻美术文献的历程
厘清《画史会要》《续书史会要》等书的编刻过程,确定朱谋垔在美术图籍刊刻史上的位置,也有助于解决此书的编者问题。关于《画史会要》的编纂动因,朱谋垔《画史会要序》有详细交代:
国初天台陶九成著《书史会要》九卷,余为续一卷,既梓行之矣。客有过余者曰:书画之道可偏举乎?……今子既于羲、献、曹、陆之迹而兼综之矣,《续书史》以八法家明之天下,而遗所云“六法”者,可乎哉?余唯唯久之。[9]
可见,《画史会要》的编纂首先起于友人的建议。同时,也由于朱谋垔对于陶宗仪的敬服,在友人赞誉朱谋垔此编系“斟酌二家(按,指王世贞《王氏书画苑》和夏士良《图绘宝鉴》),芟所不急,而补其所未备”[9]的可传之作时,朱谋垔谦逊地说:“余尚友陶先生之日久,故续其《书史》,乃观夏氏《宝鉴》,实陶先生序之。岂先生有志于画史而未逮乎?是书也,谓以寄吾之尚友则可,如曰可以传也,则吾岂敢?”[9]可见朱谋垔之所以编纂《画史会要》,实是尚友前辈陶宗仪的结果。
据朱谋垔《画史会要序》中“余为续一卷,既梓行之矣”一语,《画史会要》之编纂时间当在《书史会要》《续书史会要》梓行之后。而《续书史会要》朱谋垔初刻于崇祯三年(1630),附于陶宗仪《书史会要》之后。[12]80-85因此,朱谋垔编撰《画史会要》,应当在崇祯三年之后。关于《画史会要》的编纂过程,朱宝符《隐之先生〈画史会要〉跋语》也有涉及:“宗叔隐之氏撰《画史会要》,令不肖符较而授之梓。……叔著作日富,岁有成刻,兹其崇祯辛未撰也。族侄宝符梦得甫谨跋。”[9]据此知《画史会要》约刊刻于崇祯辛未(崇祯四年,1631),朱宝符襄助校雠。结合朱谋垔《书史会要序》撰作时间“崇祯庚午仲夏朔日”(1630)及《画史会要序》撰作时间“崇祯四载辛未孟秋月”,可知《画史会要》的编纂仅耗时年馀,这当然是有所凭借的缘故。《画史会要序》称“取谢、张、朱、刘众氏之书,而旁搜于经史杂家,采其要言”,则此书主要参考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名画猎精》、朱景玄《唐朝画断》、刘道醇《五代名画记》《圣朝书画评》等画学著作,其取资既广,成书自然迅速。
崇祯间初刊本《画史会要》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似已亡佚。不过其原始面貌,尚可据朱统鉷顺治十五年(1658)冬的重修本略窥端倪。据王重民推测,《画史会要》初刊本之行款形制当与《书史会要》崇祯刊本相似,每卷下除朱谋垔署名之外,尚有朱宝符校勘署名。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画史会要》,系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五卷(十册)本著录:
明崇祯间刻本,[十行二十字]。原题:厌原山人朱谋垔隐之撰,男朱统鉷发若重较。[卷一]此本重较人题衔有剜改痕迹,例以统鉷校印《书史会要》事,是书亦当印于清顺治间。[13]
王重民著录的朱统鉷“重较本”存量较多,今国家图书馆藏本除每卷下署“厌原山人朱谋垔隐之撰”之外,各卷皆有重较题署:卷一为“男朱统鉷发若重较”卷二为“男朱统鏎通一重较”卷三为“男朱统鉷发若重较”卷四为“男朱统鉷发若重较”卷五为“男朱统鉷发若重较”。以上五卷的重较题署,确如王重民所云,显系挖改,其字形与初刊本字形并不一致,极易区分。《画史会要》重修的情况,应当如《书史会要》将崇祯刻本卷十后“侄宝符梦得较”挖改为“男朱统鉷发若重较”一样,将诸卷下的“侄宝符梦得较”挖改为“男朱统鉷发若重较”,以“凸显”朱统鉷、朱统鏎等孝子们重修先著所承担的校雠工作。朱宝符之署名虽被朱统鉷重修时挖改,但通过朱宝符在跋语中所云“宗叔隐之氏撰《画史会要》,令不肖符较而授之梓”,也提示后人不可忽略其校勘工作。
笔者曾对《书史会要》之重修本与初刊本的区别做过研究,认为顺治重修本《书史会要》较崇祯初刊本只增加了《重修诸先刻弁言》,补刻了重校者名字,同时将朱谋垔纂辑的《续书史会要》从初刊本的卷十提前到了卷九而已。[14]例此推测,《画史会要》的重修本当与《书史会要》类似,朱统鉷的所谓“重较”工作应该相当有限。
朱宝符《隐之先生〈画史会要〉跋语》称朱谋垔“岁有成刻”,前人的记载也多可征验。胡继谦《隐之先生懿行纪略》云:“搜古今名迹,替瑕陟瑜,殚心双钩,勒成《寒玉馆》正续二帙,诸名德竞为跋识。又喜陶氏《书史会要》,有益书家,乃摭我明一代,续其卷后,并薛尚功《钟鼎款识》刻之。”[10]其中提及了朱谋垔刊刻《寒玉馆法帖》正续两编、《书史会要》《续书史会要》《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朱统鉷《重修诸先刻弁言》称:“(朱谋垔)沉酣经史,日以校阅著述为事,双钩古今名迹,则有《寒玉馆正续帖》二十卷、《四体千文》四卷;较著书籍,则有《书史》《画史》各十卷、《分韵唐诗》五十卷、《钟鼎考文》二十卷、《山居诗百首》;刻而未竟,则有《删补辍耕录》《玉馆灯抄》二卷、《三韵同声》十二卷、《春秋指疑》二卷、《毛诗要旨》四卷。”[15]清王士禛撰《朱谋垔传》,专门罗列谋垔刊行之图书:“奉国将军隐之,名谋垔,号厌原山人,博雅,精六书之学,尝刻薛尚功《钟鼎款识》、陶南村书、画史《会要》及《江西宗派诗》《寒玉馆帖》。”①在[清]王士禛《居易录》(清康熙年间刊本)卷十二《朱谋垔传》中,王士禛将《画史会要》作者归于陶宗仪,有失考之过。朱谋垔家族作为明代宁藩的一支,远离喧嚣的政治中心,多寄情于诗文书画等艺事。瞿冕良所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朱权”条附及朱谋垔所刻图籍,不见于上述诸书记载者尚有元李克家《戎事类占》二十卷,汉陆贾《新语》二卷。[16]于此可见朱谋垔在古籍刊刻史上的位置。朱谋垔编刊《画史会要》,不过是其编刊生涯中的一桩细事而已,他既有能力也有财力来完成《画史会要》的编刊,没有任何必要剽窃他人。
四、近人辨伪过度之误区
通过以上考察,基本可以确定《画史会要》的编者为朱谋垔,而非子虚乌有的金赉。那么莫伯骥和谢巍何以认定金赉为编者?其考证过程究竟存在什么问题?颇值得从事文献辨伪之学者反思。
两位学者在面对文献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时,虽然也从校勘着手,比勘文字异同与条目分合,然而却未对典籍的成书过程与编者的生平、家世、著述等进行系统考察,以致所持核心证据(所藏崇祯刻本《画史会要》较珊瑚阁旧写本有缺文)并不可靠,在对崇祯刻本与旧写本进行比勘后,根据校勘异文,遽定前者据后者而来,进而蒐集有利于己的证据,最终证成其说。总的看来,二人均存在核心证据未加检核、导致先入为主的方法误区。以下从四个层面揭示其考证误区,供从事辨伪学者参考。
首先,核心证据,未经检核。莫氏家藏有崇祯刊本《画史会要》与珊瑚阁旧写本《画史会要》,莫氏首先对二本进行校勘,依常理这种方法是妥当的,得出的结论也应当可信。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莫氏所藏崇祯刊本《画史会要》是一个颇有残阙的版本,如卷末朱宝符的《隐之先生〈画史会要〉跋语》缺佚,导致莫氏认为“写本多后跋”。又如卷一“张僧繇”条下十一人(计有焦宝愿、嵇宝钧、聂松、解倩、陆整、江僧宝、释威公、释吉底、释摩罗菩提、释迦佛陀、顾野王)正好为一个版面(卷一第23页),这一整页在莫氏所藏崇祯刊本《画史会要》中恰好阙失,结果莫氏因果倒置,反而认为刻本文字不足,为伪,写本文字充分,为真。如果莫氏当时能检查页次,核实所藏刊本之页码是否连贯,必不会出现以不疑为疑的情形。
其次,结论先行,导致误判。因为过信所谓“核心证据”,导致主题先行,过早做出结论。谢巍辨伪的证据基本不出莫氏提供的材料,他首先根据莫伯骥跋文中提供的文字差异,断定“朱宝符跋乃袭取颜巷逸人之跋敷陈成篇,不免露出作假之痕迹”。最后总结说:“金氏之书撰成在前,朱氏乃取之重纂,改头换面有删有补,而以己名付梓。四库本《画史会要》显然可知乃取金氏、朱氏两书之所长而合为一体,兹本以题署金、朱二人之名为宜。”[8]376先有预期的结论,进而加之以罪,案之以辞,找出种种所谓证据来证实金赉的著作权。这显然与莫伯骥类似,以结论先行,再曲为之说,以证实朱谋垔是作伪者。在预定结论的指引下,谢巍面对两书序中同有“国初天台陶九成著《书史会要》九卷,余为续一卷,即梓行之矣”一句,不仅不承认《书史会要续编》为朱谋垔所编的事实,反而继续寻找《书史会要续编》并非朱谋垔所撰的证据,尽管他也承认“不见有书记载金氏有《书史会要续编》”。
再次,过信人言,为人所诳。古人行文,受文体、个性、环境影响颇大,又多用修辞与成语,故语义常含混不清。故引为证据时,需对其文意虚实详加辨析。谢巍考察朱统鉷重修本的编刊过程,首先引据顺治十三年(1656)朱统鉷《重修诸先刻弁言》,《弁言》中说朱谋垔编刊典籍之版片,在顺治三年(1646)“六遭兵火,几同灰烬”,顺治四年(1647)“残去十之六七”,后在谋垔故旧的资助下“遘求遗本,补葺故物”,至顺治十五年(1658)冬,“书、画《史》《钟鼎文》始克就绪”,[15]谢巍据以认为1646年时版籍已不存,1647年时藏稿已失去大半,故其书应是朱统鉷重新纂辑而成,并非朱谋垔的旧貌。[8]375-376谢氏此说,显然过信《弁言》所云。经笔者考察,崇祯刊本《书史会要补编》的版片并无大损,朱统鉷对于朱谋垔遗著的书版,仅仅作了极少的剜改,补版数叶而已。[17]《弁言》中所谓“几同灰烬”“残去十之六七”不过是夸张的修辞,旨在表彰孝子们重修先著的功劳而已。倘不如此,便无法向资助其重刻其父遗著的故旧亲朋交代。谢巍对于语言修辞现象,似太过当真。他将旧写本后颜巷逸人跋与崇祯四年朱宝符跋对读,认为其文字大同小异,其差别为:称谓不同,一为“表兄敷奇氏”,一为“宗叔隐之氏”;文字多少有不同,有改字者,如颜巷逸人跋为“兄既高介自立,无世俗游,寓苍玉居,吟啸其间”,而朱氏跋为“叔既高介自立,无世俗游,筑寒玉馆……吟啸其间”。由此,他考察金赉、朱谋垔两人身份,认为金氏自号岩默老,寓苍玉居,可知其身份为隐士,无世俗游,则与其身份相称。而朱氏虽号厌原山人,但其身份为明宗室,为奉国将军,岂能“无世俗游”?此类分析,均是将朱宝符跋语中的语言修辞现象当作事实,无怪乎其所论偏离实际。故考证之材料,需先剔出文学之想象与修辞。对于溢美奖饰之辞,需辨析后方可用为考证之资。
复次,循环论证,根基不牢。四库提要曾论及《书史会要》及《续编》刊刻之过程,认为朱统鉷“重刊是书,分析移易,遂使宗仪原书中断为二”,[1]3534谢巍信从提要之说,更据以认为“统鉷并不善于编书,此书是否重纂或为其新编亦莫能明”。其实提要谓朱统鉷“重刊是书”,其说本就不确。考四库纂修时所据《书史会要》只是统鉷重修本,此本仅在崇祯初刊本基础上补版数叶,何能称重刊?然而谢说正是建立在这一并不牢固的证据之上。而对于颜巷逸人跋中云金氏“著作日富,岁有成刻”,得出“金氏除《山居百咏》之外,尚有他书刻之”的结论。所谓“岁有成刻”,虽不必完全当真,但至少说明刊刻过不少典籍,这恐怕非一般贫苦士子所能为,而今日之版刻研究专著也并未提及金赉,其刊刻书籍更是了无影踪。反倒是作为宁藩贵族的朱谋垔,恃其财力与爱好,刊刻了大量艺术典籍。
推究二位先生的辨伪过程,或受清中叶以来学界对书画类典籍总体认知的影响。四库提要“艺术类”末附馆臣按语“考论书画之书,著录最夥”,[1]2560即谓四库所收艺术类图书特多。《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二为子部八“艺术类”,邵懿辰也说“此卷所收,多而无谓”。[18]大约前贤早就对四库艺术类收书过多有所不满,且四库所收艺术类图籍,前人多有辨为伪书者,如《铁网珊瑚》《春雨杂述》《蕉窗九录》《筠轩清秘录》等,《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等多有辨伪;民国以降,余绍宋、吴辟疆等对书画伪籍续有考辨。莫、谢二氏大约受前贤辨伪观念的影响,推而及于《画史会要》,进而出现辨伪过度之情形。
结语
前贤谓朱谋垔剽窃他人成果,有意作伪,这是相当严重的指控。然而通过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在没有充分证据否定朱谋垔的编著权之前,《画史会要》的编者还是归于朱谋垔更为合适,所谓的“朱谋垔托名说”不能成立。
辨伪是严肃的学术工作,稍有不慎,就容易滋生冤案,厚诬古人。因此在辨伪过程中,对于核心证据要严格检核,如果核心证据不足征,则其辨伪结果无异于空中楼阁。同时,辨伪也要注意方法的科学,要力避结论先行和循环论证等方法误区。实际上,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辨伪实质上是年代与作者的问题。[19]就本文来说,只要厘清《画史会要》的编刊年代与过程,考明朱谋垔的生卒年代、刻书生涯,则所谓“伪撰”问题,便可冰消雾散。每个人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年代,因此,图书文献真实作者的认定也就具有了年代意义。考证文献生成的真实年代,无疑是文献辨伪的核心要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献辨伪学似可称为文献年代学。
笔者曾对朱谋垔的家学、爱好有过考察,[12]76-80研究可证朱谋垔确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完全不必剽窃他人成果来满足一时虚荣。朱谋垔《画史会要》之刊刻与刊刻《书史会要》、编刻《书史会要续编》,实为朱谋垔尚友前贤、热衷刻书(特别是书画碑帖类书籍)的结果。事实上,朱谋垔早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开始刊刻《寒玉馆帖》,至崇祯元年(1628)完成刊刻;崇祯三年(1630)完成《书史会要》及《续书史会要》的刊刻;崇祯四年(1631)完成《画史会要》的刊刻;崇祯六年(1633)又完成《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刊刻。放在一个出版者的一生来看,这些实在是朱谋垔热衷艺事的系统工程,在时间上也是先后延续的。
事实证明,当我们对一部书的著作权产生怀疑时,首先要对这部书的成书过程详加考察,然后对照“旧题”撰者的生平,看其是否存在著书的学养、财力、时间、机缘等客观条件,如果未有足够证据否定旧说,那么暂时保留旧有的署名,无疑是一种更为稳妥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