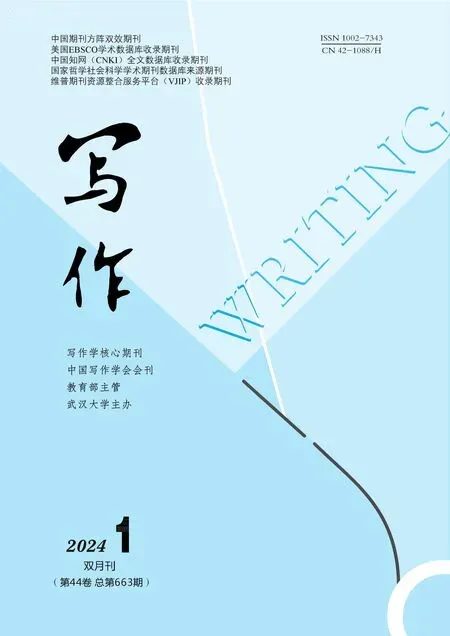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对明清世情传统的承续与转换
毛金灿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在美学实践和风格转变上都体现出新的质素,逐步脱离了早期形式革命的狂欢姿态,在语言、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趋向古典文学传统的回归。有学者曾就先锋作家风格的转变进行探讨,“如果把1989 年看成‘先锋派’偃旗息鼓的年份显然过于武断,但是1989年‘先锋派’确实发生某些变化,形式方面探索的势头明显减弱,故事与古典性意味掩饰不住从叙事中浮现出来”①陈晓明:《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纵观20 世纪90 年代后,被冠以“先锋五虎将”之名的先锋派作家,马原、苏童、余华、格非、洪峰等人,已不再执着于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生硬模仿,而是力图跳出叙述迷宫的窠臼,开掘一片独具美学气质和主体风格的作品。由此我们看到,余华由早期的《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沉迷于暴力复仇与血腥生活的奇观场面,转向书写《鲜血梅花》《古典爱情》《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承续古典文学传统、“武侠”气质和公案题材的小说。苏童由《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转向书写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妻妾成群》《米》《碧奴》。格非舍弃了叙述的复杂性,从《褐色鸟群》走向“江南三部曲”等带有古典小说叙述风格的作品。
学界对先锋文学思潮的研究,包括以下几种研究理路。一是探究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借鉴方式,分析其如何借助西方文学话语书写中国故事;二是辨析先锋文学思潮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美学风格的变化,考察其创作如何实现向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回归,进而解析古典文学传统和文学理论在当下的转换与重构;三是对作家作品的审美价值分析,从创作风格、美学呈现、文学观念与思想蕴含等角度进行多重把握。近年来,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视角渐成热点,特别是在文学批评中,将某部作品与传统文学的特点相衔接的研究思路屡见不鲜。而正如研究者所反思的,“面对一个被放大的古典传统,在当下创作中找到某一个方面的回应总是容易的。批评对此不能止步于指认的层面。古代文论如何进入批评实践,需要带着今天的问题意识,发掘它解释当下文学创作的能力”①邵部:《当下生活的“沙之书”——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先锋作家在20 世纪90 年代如何集体转向“古典”?转向了何种“古典传统”?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启示和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一、外部诱因:“通俗文学热”与先锋文学的“接受遇冷”
考察先锋文学如何实现美学风格的转变,首先应该回到80年代鲜活多彩的文学现场。20世纪80 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热闹非凡。在文化启蒙的时代语境和自由开放的文坛气氛中,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文学等创作潮流,如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地亮相文坛。他们或以反思历史的姿态观照古老的中国文化,或借助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和文学风格,对文学语言和结构进行重新调整,或以冷峻细琐的笔调呈现日常生活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又或以解构宏大主题的叙述逻辑重现当下的现实生活。然而在灿若繁花的“纯文学”场域之外,同时受到普通读者和文学市场欢迎的,是以港台文学为主流的、配合以众多通俗文学期刊和读物的俗文学场域。
“通俗文学热”的典型现象之一,是来自港台的武侠、言情等类型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的风靡。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作家笔下虚构出的武侠英雄,以敢爱敢恨、自由自在的个人气质,潇洒自如、畅快人生的世俗观念,扑朔迷离、曲折跌宕的传奇情节,征服了大批普通读者。随着漫画、戏剧、影视剧等“次文学”的改编,武侠小说的影响力在八九十年代蔚为大观。有研究显示,“金氏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他的作品先是在殖民地一隅香港产生影响,继而流布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坊间的盗版本盛行大陆,至九十年代才有全套正式授权版在大陆发行”②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同样受到文学市场欢迎的,是以琼瑶、亦舒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情爱小说。她们善于运用散文化的笔调,以诗情画意的语言风格、漫话世态的笔体语调,聚焦世俗人生中的情感纠葛,反映了港台社会中的家庭与爱情观念。其中对女性人物多维立体的刻画,对其独立自由精神状态的呈现,对其家庭婚姻观念的书写,都迥异于50 到70 年代主流文学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武侠和言情小说在八九十年代形成热潮,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其在回溯古典传统小说题材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美学风格,从而把通俗题材小说从“旧小说”的批评范式中解放出来,融入了新时期的文学现场。
“通俗文学热”的另一代表现象,是主流文坛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重新评价。五六十年代,经常受到批评而“被遮蔽”的通俗文学作家,在新时期重新受到认可。众所周知,1950—1970年代,通俗文学创作受到抑制,其往往被归结为“旧艺人”和“旧文学”,需要通过“人民”的检验加以改造。1956年,在通俗文艺出版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许多作家谈到,通俗文艺在文学领域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不仅文学批评更为严格,而且通俗文艺作品出版受限,存在定额高和稿费低的现象。例如对张恨水的严肃批评,“文艺批评的刊物对通俗文艺和章回小说的评价,是抡起大斧砍头的。比如,说张恨水先生的作品是黄色的,有毒的,要不得;这样张先生的作品就被打入地狱了”①木杲:《通俗文艺作家的呼声》,《文艺报》1957年第10期。。直到80年代初期,对张恨水的研究才回到学理性状态,其审美价值被重新发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范伯群从文本细读和文学史叙述的角度,对张恨水的创作与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重构“通俗文学的自在自律的运行规律和审美标准”②范伯群:《张恨水研究与中国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从而改变既往文学史对通俗文学的简单化理解。
“通俗文学热”的重要表现形式,还包括通俗文学期刊出版量的激增,和由此带来通俗文学市场的繁荣面貌。据学者统计,《故事会》自1984 年由双月刊改版成月刊,设置主要栏目为“新民间故事,科学幻想故事,笑话,风俗故事,谜语故事,寓言,土特产故事,外国童话等”③沈国凡:《解读〈故事会〉——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3、89页。,追求“易讲、易记、好读、能传”的办刊风貌,力图刊登具有通俗性质、语言明白晓畅、体现民间审美趣味的作品。“1985年第一期,刊物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到了这年的第二期,发行量再次攀升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④沈国凡:《解读〈故事会〉——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3、89页。此外,新创办的“故事”类报刊数量也愈渐增长,如《中国故事》《故事世界》《故事大王》《故事林》《故事家》《外国故事》《古今故事报》《今古传奇·故事版》⑤沈国凡:《解读〈故事会〉——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3、89页。等,提供给文学读者多样的文化选择。除官方邮局发行的文学期刊,通过民间发行渠道流入文学市场的各类小报、地级市刊物也热衷于增发通俗文学小说。《文艺报》编辑部曾对广西的民间报摊市场开展调查,刊载通俗小说的期刊种类颇多,如《金城》《右江文艺》《柳絮》《文艺生活》《洞庭湖》等。刊发武林、侦破类小说的小报不仅高达57种,且发行量惊人,“每张小报发行量约在100—200万之间。广西27种小报,每期销售量可达4000万份之多”⑥王屏、绿雪:《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文艺报》1985年第2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勃兴的“通俗文学热”讨论贯穿于20世纪的最后十年。1996年6月13日《文学报》刊载特稿《小说与故事,谁主沉浮?》再次重申了通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面对近年来在市场冲击之下出现的纯文学小说的萧条萎缩之势,文化界的思考已趋向冷静和理智,现在也许到了纯文学应该以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通俗小说及故事的时候了”⑦转引自沈国凡:《解读〈故事会〉——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通过上述对“通俗文学热”的历史回顾,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20世纪末期通俗文学的变动趋势。在通俗文学大众口碑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学界对通俗文学的重新关注从学术研究角度给予其合法地位,而同一时空下的“纯文学”场域,也正因通俗文学的崛起而面临现实的创作“焦虑”。
先锋作家的创作焦虑首先来自文本内部,精英化的叙述方式与受到通俗文学影响的90年代大众化的阅读期待并不吻合,从而导致了读者群的流动。从文本层面来看,先锋小说在80 年代中期过分追求文学叙述的奇观与丰富,使得作品在语言风格和结构逻辑上,均处在凌空高蹈的飘渺状态中,反而淹没了文学想象力与思想力。正如有学者曾反思的那样,“语言和技术一旦成为了作品的主体,就取代了作品对精神主体进行言说的可能性”①谢有顺:《终止游戏与继续生存——先锋长篇小说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而早期先锋作家对西方文学观念的直接嫁接,虽然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冲破文坛桎梏、追求叙述自由的创新风貌,但也常使文本的主旨超出了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产生食洋不化、望洋兴叹的阅读障碍。对普通读者而言,面对先锋小说,他们常处于“读不懂”的尴尬境地,于是,去武侠的世界驰骋想象,或去言情的空间寻求情感慰藉,从侦探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获取激情成为新的文化选择。在大众文化崛起和精英文化退潮的时代,先锋小说文本上的奇崛风貌已然不适合面向更广泛的普通读者阅读,因此必须寻求新的创作路径。
其次,这种创作焦虑还来自纯文学领域其他文学思潮的挤压。90 年代,最耀眼的文坛新秀无疑是集《钟山》和《文学评论》合力打造的“新写实小说”,刘恒、池莉、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被批评界集中安置在这个批评体系中。学界认为他们以“零度情感”介入普通人的“生活本相”,书写了市民阶层的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和生存状态。虽然他们的创作不以传奇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吸引读者,也不以追求宏大价值和人生意义为写作目的,但正是对世俗生活的还原与呈现,真实地表现了普通人凡俗的现世状态,传达出黯淡、萎靡、随遇而安的“躺平”情绪,成为吸引潜在读者、引起读者共鸣的另一种途径。相较之下,“寻根、先锋、新历史小说,虽不排斥大众作为读者,但对叙事形式、思想性的追求,明显是为了最大程度吸引文艺界、知识界以及各行各业精英的共鸣,这就导致文学潜在读者群体的缩小。新写实小说的受众群体放宽了一些”②刘诗宇:《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新写实小说”》,《文艺争鸣》2023年第3期。。此外,先锋文学过分欧化的审美风格,也与90年代回归和反思传统文化的潮流格格不入,“先锋派小说因其西化表达无法回应中国现实,身陷民族文化认同这一尴尬处境”③张冀:《传统人际关系的现代演绎——评“玉米三部曲“兼论毕飞宇中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其影响力也不及同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面对同时代的“通俗文学热”和纯文学创作的影响,先锋作家的自由实验岌岌可危。大众化想象与精英化现实的二元对峙,成为倒逼先锋作家调整创作观念的直接因素。
二、资源借鉴:先锋作家对明清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续
先锋作家回归古典文学精神的实践是有目共睹的,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谈到苏童后期的创作的“古典”特质,“他的小说有某种传统士大夫对旧日生活依恋、融入的态度,对于红颜薄命等的主题、情调的抒写,投入且富有韵味”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页。。而苏童自己则在创作谈中反复提及回归古典的创作冲动,正是来源于超脱新潮小说形式实验的再创新:“《妻妾成群》这篇小说的发生也是多种意义上的,不是由任何一个方面的因素单独决定的。我记得写这篇小说有着多重原因的启发。一个是因为马原,我当时在《钟山》做编辑,在通信过程中他的一句话对我的启发是相当大的。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他说的是他对古典叙述的看法。我理解他所说的古典叙述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一九八九年前后正是新潮小说盛行、恣意汪洋的时期,很少有人去谈论古典的叙述、白描的叙述,而马原却在那封信中跟我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有启发的。”⑤汪政、何平编:《苏童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事实上,促发作家回归古典文学的,只是欲求拓宽创作空间的朦胧感受,而其接续何种文学传统仍需从文本出发进行分析。《妻妾成群》首次刊登于《收获》1989 年第6 期。已有研究对《妻妾成群》中的古典意味进行过分析,认为小说“可视为对历史、家族、人性的沦落、沉溺、凄清、悲苦的生存基调中飘荡着的孤魂的‘拟旧’、想象”①张学昕:《为何会有“描述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苏童〈妻妾成群〉重考》,《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这个论断合理概括了小说的叙事风格与主旨韵味,但是对作家如何回归古典意味的探讨,却是语焉不详的。通过对小说叙事图景的回归,我们发现小说本质上讲述的,还是“一男四女”模式的旧家庭之中,妻妾争宠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因果报应的世情故事。这个故事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颂莲,进入陈家大院成为第四房姨太太后的人生悲剧为主线。陈府几房姨太太为了争宠,不择手段、互相算计,俨然一副“吃人”场景的再现。大太太毓如墨守成规,避世自保。二太太卓云精明伪善,工于心计,不仅伤害有孕的三太太,还致使仆人雁儿对颂莲行诅咒之术。三太太梅珊风姿绰约,泼辣跋扈,她看不惯卓云的手段,常与其针锋相对,却最终被卓云撞破了与医生的私情,坠井而亡。颂莲本是冰清玉洁的自由之女,却在人人戕害的黑暗环境中沉沦,陷入了互相伤害的染缸。她为报复卓云的暗算剪破了她的耳朵,误杀了仆人雁儿,目睹了梅珊坠井,最终失去了陈佐千的欢心,精神崩溃。对陈佐千卑躬屈膝的卓云,也在五太太进门后趋于沉寂。整个故事传递出世俗生活的规律,宿命轮回、因果报应几乎在每一次的相互伤害中得到应验。不可否认的是,将小说的主旨引申至对女性命运的观照,对家族、历史等宏大主题的重构,是一种有效且有意义的解读方式。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作家趋向通俗文学传统,特别是明清世情小说,对旧家庭中离合悲欢的世俗情感和因果报应的内在规律进行直接呈现。
何谓明清小说的世情传统呢?描摹凡俗生活,表现世态人心历来是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悠远传统,它不仅涵阔了白话小说通俗文学的共同品性,还以其贴合世态生活的审美特点,观照普通人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民间伦理,融汇成具有普范价值的审美内核。明清之际更是有《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红楼梦》等世情佳作流传至今。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总结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常以“人情小说”“世情书”和“世情小说”加以界定,“只是在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王增斌的《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有论,“世情小说显然与描写军政要事、歌颂往古先贤的军国政事、历史演义小说有所区别,亦与抒写豪杰壮举、描摹天神地仙奇才异术的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小说完全不同,它主要写的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耳闻目见的真实人生”③王增斌:《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页。。
具体到文本上,冯梦龙编纂“三言”的艺术特点,在故事主旨上偏重描摹劝善惩恶、因果报应、宿命轮回的世俗故事,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十五贯戏言成巧货》等。在小说语言上,看重白话和诗词的整合,灵活化用典故以增强作品的雅致趣味。在叙事笔法上,“三言”既用白描的笔法,照顾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保留了话本小说的通俗性,又将诗词歌赋等杂文体,融进叙事笔法之中。在叙事功能上,世情小说借助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深入民间的世态人心,以达到劝世救世和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
苏童《妻妾成群》中的叙事图景明显承续了“三言二拍”中对世情生活的细腻刻画。而格非也通过自己的创作经验,勾连了世情传统的叙事资源。格非在撰写博士论文《废名的意义》时提到,“中国小说存在大小两个传统:经由‘世俗’‘世情’‘人情’完成的‘内在超越’的‘大传统’;以及建立在对‘大传统’进行批判、确认和改写基础上,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小传统’”①参见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他更具体客观地阐明了世情的普范状态,也提出更希望在创作中践行“所谓‘不离世间而超越世间’”②格非:《文学的邀约·内在超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的创作理念。其“江南三部曲”对世情文学传统的化用,体现在叙事笔法的展开,典故的运用和古典风格的营造等多方面。三部作品以跨越百年的叙事时间,讲述陆家几代人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新时期的故事,力图完成属于个体心中的乌托邦理念。从叙事的外部风貌来看,“江南三部曲”建构的是融汇个体与家族、现实与历史、奋斗与幻灭的严肃文学主题。但具体到每一部作品的情节架构,作家又以大量笔墨,书写主人公难以忘怀、“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线索,辅之以传奇跌宕的叙事情节和宿命轮回的基本逻辑。《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因追随“表哥”张季元,因缘际会邂逅“花家舍”这一神秘世界。随之拼其一生展开的革命事业,却因女佣翠莲的出卖宣告失败。试图通过告密而改命的女佣翠莲最终自食恶果,再入勾栏,沦为乞丐。《山河入梦》不仅展现谭功达作为一县之长兴修水库,创办合作社,建构大同社会的宏伟大业,还生动地呈现谭功达与白小娴、姚佩佩、张金华的情爱纠葛。表面为县长姻缘牵线,实为讨好领导而献功的各色地方官员,也都使尽浑身解数。心怀理想主义、想办实事的谭功达因官场的勾心斗角,导致缺席抗洪救灾的现场被免职,因与姚佩佩的书信往来沦为阶下囚,最终丧失了实现乌托邦梦的机会。格非述其传奇之经历,彰其情感的悲欢离合,这恰恰是世情小说因子的另一重显现。《春尽江南》围绕主人公谭端午及其妻子庞家玉的婚姻与社会生活,演绎了浮光掠影、一地鸡毛的当代世情书,明显带有通俗小说的基调。放弃理想主义的谭端午难以招架纷扰的俗世生活,转而在诗歌中寻求精神慰藉,庞家玉则在儿子教育、婆媳关系、住房纠纷、事业发展中左右为难。格非在展现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严肃主题下,描摹出繁杂立体的现世人生。恰如已有研究对其作出的准确体认,“《春尽江南》告别了革命年代,写婚宴、写官司、写夫妻亲子、写同事朋友,写情感也写情绪,换言之,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写的是‘世事’和‘人情’”③郭冰茹:《回归古典与先锋派的转向——论格非回归古典的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文艺争鸣》2016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先锋作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汲取也并不限于世情传统。苏童在叙事中体现的古典气质仍离不开对抒情传统的内化,而格非对历史事件的传奇性表达也来自对史传传统和演义传统的再创新。只不过相较而言,两位作家对世情传统的承续都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如果单从文学的叙事要素连缀着世态人情的因子,来指认先锋作家回归世情传统的努力,那么“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④《“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似乎更能体现世情传统的基本要素。无论是呈现印家厚平凡单调的上班生活(池莉《烦恼人生》),还是小林处理家庭生活和面对人际关系的尴尬境地(刘震云《一地鸡毛》》,都离不开对人事情理的立体关注。相比先锋的转型,新写实在文学理念和创作风貌上都与世情传统有着内在的契合,那么先锋作家何以实现对同时代文学创作模式的突围,又是如何完成对世情传统的转化呢?
三、“雅俗新变”:先锋作家对明清世情小说叙事观念的转换
新写实小说确如批评家们所强调的,以不附加宏大意义的叙述逻辑展现了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更需要指出的是其对时代情绪的顺应姿态,“‘新写实’之所以得到多数作家和读者的认可和精神上的回应,是因为它所起的作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的文学是一样的——书写的是灰暗的日常生活,表达的是黯淡的精神情绪,再度返回世俗与欲望世界或坠入‘历史’虚拟空间的一种无奈,种种价值降解后的‘小市民意识心态’的凸显,还有现实感很强、富有精神隐喻意味的压抑、萎靡、堕落和变态的种种情绪”①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但转型后的先锋作家与之迥异的,不是放弃对意义的追寻,毕竟解构意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解构之后建构何种文学观念,探索何种文学风范仍然是另一种“先锋”的追寻。
从对苏童与格非小说的分析来看,先锋作家的文本实践呈现出“雅”与“俗”相融汇的文学风貌。他们既脱离了对小说意义的放逐,也常展现通俗文学和世情小说的情节特质,以“俗”文学的叙事单元,指向“雅”文学的的主题意蕴。这种叙述观念的呈现恰与明清小说“三言二拍”的文学观念有相通之处。冯梦龙以宋元话本小说和史传笔记、古典戏曲为底本编撰而成的“三言”,以其对“雅”“俗”关系的清醒认识,被评点为“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②抱瓮老人编:《今古奇观》,冯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原序”第1页。。凌濛初在创作“二拍”时,亦强调了小说中对日常生活“尚奇”与“尚俗”的要义。“三言二拍”既有通俗文学中自然人性的流露与传奇故事推衍的世情要素,又有严肃文学开掘社会人性、观照人物命运的人文精神,体现出“雅俗融合”的鲜明特质。恰如苏童发现,可以借助通俗文学的精神气韵,去勘察人物命运处境,以获取新的叙述通道。苏童曾这样描述创作《妻妾成群》时的灵感乍现状态,“新嫁为妾的小女子颂莲进了陈家以后怎么办?一篇小说假如可以提出这种问题也就意味着某种通俗的小说通道可以自由穿梭。我自由穿梭,并且生平第一次发现了白描式的古典小说风格的种种妙不可言之处”③汪政、何平编:《苏童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在这里“雅俗融汇”构成了苏童叙述的钥匙,打通了泾渭分明的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叙述脉门。
需要指出的是,冯梦龙所提倡的“奏雅”和“适俗”并重,其意义在于提升小说的文体地位,使其超脱传统文学观念对小说的偏见,与“稗官野史”“街谈巷语”的“闲谈”小说观念进行区分。基于此,冯梦龙在小说理论上强化了其社会效果和现实作用,在书名中寄寓了强烈的文学期许,“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④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而不论是冯梦龙的“篇终奏雅”,还是凌濛初“每回之中,三致意焉”的主张,都体现了对小说的功能界定,即小说的功能主要是劝诫教化,以世俗常理规劝读者谨守因果报应的基本法则,以向善劝善的叙事意图启迪读者完成尘世的修行。这些主张虽然给小说增添了“求雅”的价值,但很容易滑向说教和刻板的误区,难以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不符合现代读者的审美期待。
先锋作家的创作显然并没有推崇小说的教化作用,而只是汲取了其中通俗故事的讲述方式,通过故事揭示普范的世俗常理,再融入现代化的叙事技巧,完成“雅俗融合”。如苏童的长篇小说《碧奴》,是借“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原型,书写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境遇的复杂变动。换句话说,苏童既糅合了民间故事的通俗性,又蕴含了纯文学对价值和意义的内在要求。在这一点上,先锋作家对小说“雅俗新变”的叙述自觉,较之单纯呈现自然生存状态、传递世纪末情绪的新写实小说,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不同于苏童和格非小说对世情传统的化用,余华对世情传统的承续与转化显得更为曲折而隐秘。余华也较早地开始回归古典传统以寻求突破,其《河边的错误》(《钟山》1988 年第1 期)、《古典爱情》(《北京文学》1988 年第12 期)、《鲜血梅花》(《人民文学》1989 年第3 期)等中短篇小说与侠义公案、才子佳人题材构成呼应。这明显既受到了同时期“通俗文学热”的潜在影响,又希冀重新激活古典文学的叙事资源。但此时的创作,余华大多以短制文体,戏仿古典文学题材的叙事外壳,在意义的指向和主旨的建构上仍显得虚空和捉摸不定,因此有研究者批评,“先锋们曾一再表示认同古典价值,但那仅仅是空泛的姿态,它与本民族的精神意蕴相去尚远”①陈晓明:《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90年代中后期,余华的长篇小说表现出与中短篇创作不同的审美面向。回归现实的“贴地”写作是许多读者对其的一贯认识。就笔者阅读余华90 年代后期的创作谈和小说的感受来看,余华这一阶段善于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趋向对人性深处的开掘和俗世生活的反思。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余华谈到了写作短篇与长篇的区别。“相对于短篇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似乎离写作这种技术性的行为更远,更像是在经历着什么,而不是在写作着什么。换一种说法,就是短篇小说表达时所接近的是结构、语言和某种程度上的理想。短篇小说更为形式化的理由是它可以被严格控制,控制在作家完整的意图里。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人的命运、背景的交换、时代的更替在作家这里会突出起来,对结构和语言的把握往往成为了另外一种标准,也就是人们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训练有素的标准。”②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2页。从余华的创作经验可以看到,他在创作短篇小说时保持着先锋形式探索的自觉意识,在创作长篇小说则更偏向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脉络。对余华来说,短篇创作解决的是“怎样写”的技术性操作,而长篇小说考验的是作家如何将自我生活经验和对社会与人生的超越性认识艺术地“讲述”出来。余华坦言对现代叙述法则的熟稔,对其进入现实生活造成了不小的阻碍。重新认识到“写人物”并非写“人物符号”,重新聚焦语言传达的情感而非利用语言设置声音外壳,重新发现生活的丰富意义而非追逐冷漠的叙述节奏,是余华长篇小说回归传统叙事的重要表现。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显然成为余华叙事转型的重要作品,无论是从大众认可度还是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他都交出了较为成功的答卷。两部作品均以严肃文学的面貌现身,但其内在肌理仍然结合了通俗文学“讲故事”的基本思路。对人物波澜命运的传奇呈现,暗含着余华试图以通俗故事观照人物境遇的创作旨归。《活着》虽然是以老人福贵的回忆视角展开叙述,但文本的叙述时空基本沿着生活的逻辑,呈顺叙发展状态。余华擅长塑造具体而现实的人物,恰如他在写《在细雨中呼喊中》时提到的那样,“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因此,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当我感到理解得差不多了,我的小说也该结束了”③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2页。。福贵、家珍、有庆、凤霞等主要人物,其性格、风貌和命运轨迹都不断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赌博成性的浪荡子在败光家产后,终将面临生命不能承受之苦。作为一家之主的福贵在经历了家族破败、父母双亡、被抓壮丁后生死逃亡、儿子有庆意外丧生,女儿妻子相继去世的沉重打击后,依然以坚韧和悲悯的情怀接受命运的残酷。
《许三观卖血记》继续对人物的传奇经历和家庭的伦理关系进行放大书写。主人公许三观形象的经典性恰恰因其在凡俗中透露出高尚的精神品格。他既是卖血养活家人的平凡父亲,又以超乎常理的精神,超越了道德的准则和伦理的规约,处理与并非亲生的儿子、并不忠贞的妻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唯其如此,许三观这一形象很好地诠释了凌濛初所说的在世俗日常中发掘“奇”的要素:“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初刻拍案惊奇·序》)①即空观主人:《即空观主人批点二拍》,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凌濛初认为,侠义公案、神魔演义小说以追求奇幻色彩为“奇”的要义,但在此之外,还应发掘世俗日常之“奇”。这个“奇”并非以神奇、怪奇为审美内蕴,能坚守本道、回归庸常,进而将常理发挥到极致,才可称之“奇”。恰如王安忆对余华创作的精准评价:“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俗世中人,纲常伦理是他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向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许三观的英雄事迹且是一些碎事,吃面啦,喊魂什么,上不了神圣殿堂,这就是当代英雄了。他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喜剧式的。这就是我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②《王安忆评〈许三观卖血记〉》,《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余华通过讲述许三观的故事,在血的献祭和亲情的伦理之间,呈现了凡俗生活中的超凡特质,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开辟出新的审美路径。回归传统的世情故事,塑造鲜活立体的现世中人,这恰是其转型成功的缘由。
结语
“真正的先锋是体现在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③洪治纲:《先锋:自由的迷津——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花城》2002年第5期。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先锋作家集体向古典文学传统的转型,其根本缘由是“通俗文学热”带来的对纯文学生态的挤压,以及先锋文学接受“遇冷”的客观现实。在通俗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强势影响之下,先锋作家以明清世情小说的叙事资源为抓手,着力向通俗文学转型,以“俗”的叙事内容指向“雅”的文学主旨,呈现出“外严肃,内通俗”的基本特点。同时,先锋作家也适当择取世情小说的文学理念,扬弃了世情小说教化的社会功用和“新写实小说”中蕴含的黯淡、萎靡的时代情绪,以“雅俗新变”的审美取向对世情传统进行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品对世情传统的运用并不自然,留下斧凿的痕迹,也影响了作品的审美效果,以致作品呈现出平庸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作家仍需要一定程度调整叙事节奏和书写距离。例如苏童的《米》和晚近出现的李洱的《应物兄》,虽不乏叙事力度,但与俗世生活贴得太近,以更细密的笔触向大众生活靠拢,这在回归现世生活的同时,满足了大众读者的阅读猎奇心理,但是却缺乏对人性、历史、社会文化的更深远的精神体悟。在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先锋作家理应对世俗的生活逻辑保持必要的警惕,避免落入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的书写逻辑。应以超越性的眼光从追求叙述形式的游戏中超脱出来,以坚定的价值立场筑牢精神根基,去实现更深层的意义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