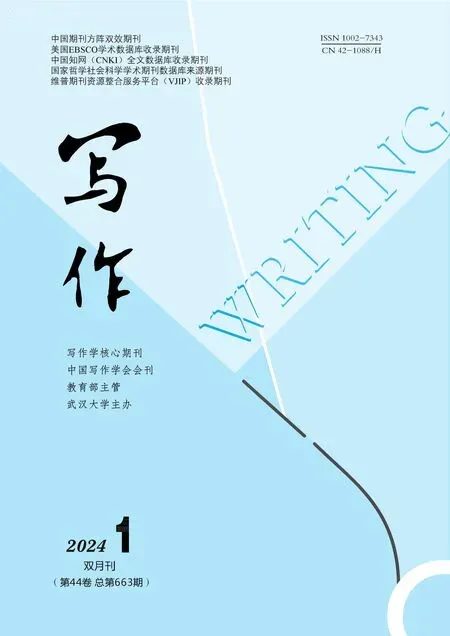顾城爱情诗的隐秘表达及成因探析
赖静怡 谢君兰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其诗歌因空灵纯净、天真自然而又不失哲思的语言,曾引起巨大反响,也赢得了“童话诗人”的赞誉。为守护其童话世界的纯真,顾城坚持用孩童视角进行写作,将成人世界划分为“你们”,诗歌中也极少出现成人世界的内容——例如爱情。学者张捷鸿认为:“在他留下的700 多首诗中,几乎没有爱情的内容……即使诗中出现女性形象,那也是抽象、隔膜的女性的幻想,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出现,只是作为童话诗中不可或缺的风景,比如小女巫之类的童话人物。”①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实际上,纵观顾城创作的诗歌,其童话诗主要出现在创作早期(“自然的我”),而这部分只在顾城作品中占很小的比例;当褪去朦胧诗的历史语境和对顾城先入为主的“童话”滤镜后,笔者发现顾城的诗歌中有大量“非童话”的因素,其中不乏关于“爱情”的表达。对顾城的爱情诗进行细分,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较为直接地表达爱情,如《我好像……》《祭》《我是一座小城》《就在那个小村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等。若仅计算这一类爱情诗,那么诚如前文所言,“爱情”在顾城诗歌中确实是罕见的题材。然而,顾城还有很大一部分诗作,是由其爱情经历激发、影响创作而成的。此类较为隐秘——或是和常见爱情诗的表达不大相同,或只有诗中小部分内容提及了爱情,但同样值得讨论,不应忽视。典型的诗作有《别》《雪人》《远和近》《泡影》《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门前》等,这一类爱情诗的特征为:情感表达不明显,通常被归为童话诗、寓言诗,需要通过文本细读并结合创作背景进行阐释。
目前学界对顾城这一部分爱情诗歌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顾城早期的童话诗(如《生命幻想曲》),以及写于20世纪80年代带有政治意味的朦胧诗(如《一代人》),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多角度探讨顾城“童话诗人”的创作特点;在激流岛事件后,“诗人之死”引发了人们对顾城“童话”释义的质疑,不少研究者发现了顾城诗歌童话外衣内部的矛盾和残忍,认为文学史把80年代启蒙的光明希望寄托在顾城身上,有意识地塑造其童话诗人的形象,并企图借其诗歌中的童话特质治愈时代创伤,忽略和弱化了顾城诗歌的死亡、恐惧意识①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许永宁、粟芳:《文学史编撰与顾城童话诗人形象建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2 年第4 期;周思:《启蒙的歧路——“童话诗人”之殇与1980 年代的“童话”话语》,《现代中文学刊》2022 年第1 期;张厚刚:《论顾城诗歌的“恐惧情结”》,《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虹影、赵毅衡总结说,在顾城的诗歌中,“死是一个贯穿主题,而且‘死’与‘童心’互相渗合”②虹影、赵毅衡编:《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代表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顾城的童心只是其摆脱恐惧的一种方式。值得肯定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界的讨论逐渐从顾城其人回归到其诗,以更客观全面的态度进行审视;同时也开始重视顾城后期的创作,出现了对顾城诗歌的整体性研究。然而,有关顾城爱情诗的研究热度依然不高,学界主要从顾城的小说《英儿》去分析其爱情观和感情心理③有关《英儿》的研究,参见谢冕、祁述裕、伊昌龙等:《绝笔的反思——关于顾城和他的〈英儿〉》,《小说评论》1994 年第3期;吴思敬:《〈英儿〉与顾城之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以顾城“诗歌”为基点去挖掘其爱情表达的文章非常少,也缺乏顾城爱情诗与同时期朦胧诗人爱情诗的比较分析。本文尝试将顾城爱情诗与其创作风格、生命经历进行联系,对顾城的爱情诗作深入探讨。
一、隐而幽现:顾城“爱情诗”文本表现形式与特点
顾城的诗歌语言纯美而梦幻,他在诗中创造了一个浪漫的童话王国,里面的场景多是童心的港口、幻梦的湖泊、温暖的花园;而这个王国的主角,往往是顾城所代表的“我”,或者是他所推崇的一切“自然”。大多数时候这个王国是封闭的,没有现实的来客,也没有黑暗和污秽,只偶尔会有孩童思考生命时多愁善感的情绪,这种封闭的源头和顾城一再强调的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1967 年,12 岁的顾城随父亲顾工下放到山东广北一个部队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在顾城的回忆里,“那里的天地是完美的,是完美的正圆形……当我在走我想象的路时,天地间只有我”和“一种淡紫色的草”④顾城:《学诗笔记》,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95-898页。。可以发现,顾城作诗强调忠于内心,他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其生命体验的复杂性,即使这段记忆很大程度上存在人为美化的嫌疑。顾城认为:“诗和生命是一体的……诗一步步由生活的过程趋向生命。”⑤顾城:《从自我到自然——演讲录之一》,《顾城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86页。当研究者谈起顾城,恐怕无法做到绕过其人而单论其诗,因为顾城部分诗作的形成无疑和他与妻子谢烨、情人英儿这两段浓墨重彩的感情生活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即便顾城基于他的价值观和诗歌追求,努力在作品中回避有关“爱情”“欲望”的描写,但他“诗即生命”的诗学理念,使其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近乎等同于诗人本身。有了此前提,本文尝试将诗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对其朦胧诗的理解基础方可成立。张清华认为顾城是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诗人,写诗属于一种精神性的自传⑥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那么,顾城源于生命的写诗冲动便一定会使他记录对爱情的感受。
(一)表现形式:从称谓“你”窥察起
顾城爱情诗最明显的痕迹是“你”的出现。上文提到顾城的童话世界很少有外界的介入,“你”的到来让这个看似平静的王国有了新的景象。“你”是谁?笔者总结有三种情况。在一些诗歌中,“你”有具体所指,如《给我的尊师安徒生》《给我逝去的老祖母》里,“你”特指安徒生和祖母;而在《小巷》《我们去寻找一盏灯》等诗歌里,“你”的指称往往是象征性的。如《小巷》:
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①顾城:《小巷》,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1页。
此处的“你”可以泛指所有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人。本诗的最初版本为:“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②顾城:《小巷》,《文汇月刊》1981年第6期。,可见此诗中的“我”和“你”可以相互替换而不影响诗歌主旨。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中,“我”和“你”是一种对话关系。“我”要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在窗帘后面”。“它在一个小站上”。“它就在大海旁边”,并点出“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③顾城:《我们去寻找一盏灯》,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63页。。从诗歌充满童趣的语言和内容看,这个“你”的身份极有可能是个孩子,亦或是顾城内心人格的表现,借虚化的“你”之口表达对生活的理想化追求。
然而有一种“你”,明显和前面这两种表达有所不同。如《雪人》:
在你的门前/我堆起一个雪人/代表笨拙的我/把你久等/你拿出一颗棒糖/一颗甜甜的心/埋进雪里/说这样就会高兴④顾城:《雪人》,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3、314页。
这首诗的语言并不晦涩,与其将其牵强附会为“寓言故事诗”,不如遵循最直接的阅读感受——这是一首爱情诗。“雪人”代表了“我”,“笨拙”体现了“我”久等“你”的痴情和期待。和前文的两种“你”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此处的“你”并不是诗人预设好的角色,不是诗人内心的传话筒,也并非理想、自由等符号的化身。“你”是脱离诗人主观意识行动的,其一言一行影响着“我”的情绪:
雪人没有笑/ 一直没作声/ 直到春天的骄阳/ 把它融化干净/ 人在哪呢?/ 心在哪呢?/小小的泪潭边/只有蜜蜂。⑤顾城:《雪人》,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3、314页。
“你”给了雪人一颗甜甜的心,但雪人却没有笑,因为“我”不想做静默守护的雪人,而是渴望与“你”相拥相伴。“春天的骄阳”喻指两人间的阻碍,雪人的坚持最终被“融化干净”,但那颗甜甜的心已融入他的身体,化为泪潭后引来了蜜蜂。这首诗写于1980 年2 月,顾城是在1979 年7 月,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与谢烨相识,随后便对其展开了猛烈的追求。“雪人”融化自我的恋爱模式,也可以视为顾城后来行为的预示:因谢烨家人不同意顾城的求婚,顾城索性在谢烨家门口一个棺材样子的箱子里连睡了几天。不管是从诗歌的创作时间背景,还是基于诗歌文本的分析,不难联想到诗人在这首诗里流露出对爱情的执着。
在与谢烨恋爱期间(1979—1983),顾城还创作了很多表达自己痴情守望、爱而不得、恋情受阻的苦闷诗句,如1980年6月《小诗六首》的《远和近》:“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①顾城:《小诗六首(六首)》,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0、171页。;《泡影》:“我像孩子一样,/紧拉住渐渐模糊的你。/徒劳地要把泡影,/带回现实的陆地”②顾城:《小诗六首(六首)》,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0、171页。。如1981 年1 月创作的《土地是弯曲的》:“土地是弯曲的/我看不见你/我只能远远看见/你心上的蓝天”③顾城:《土地是弯曲的》,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5页。,此时顾城和谢烨相隔两地,顾城患得患失,“弯曲的土地”既指两人距离上的遥远,也形容恋爱之路的曲折。除开这一时期,1985年创作的《是树木游泳的力量》更是直接谈到了爱情:“我们看不见最初的日子最初,只有爱情”④顾城:《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顾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综上所述,“顾城的诗歌里几乎没有爱情”的说法恐怕是不恰当的,其诗中出现的“第三者”“女性形象”也并不全是为其童话诗服务的背景板;相反,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是以“我”爱慕的“你”为主角,隐秘地表达诗人的爱情观和相恋中的情感。
(二)表现特点:爱情与专制的潜在对话
顾城的爱情诗带着初恋般的悸动和美好的童话色彩,语言空灵纯净,有意的克制,过分的含蓄。在爱情话语的表达上,顾城总是忧郁颓废,甚至孱弱。当面对“自然”时,他写出的是如《生命幻想曲》般开阔的诗句: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⑤顾城:《生命幻想曲》,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页。
顾城少年时代在山东的河滩沙地上写下这首诗,他曾说:“我确信了我的使命,我应走的道路——我要用我的生命,自己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存储东方会像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⑥顾城:《少年时代的阳光》,《卷一:别有天地》,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可见顾城在自己的童话王国里充满自信:他有确定的目标、积极的态度、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个世界。虽然有关自然题材的创作偶尔也会流露轻微的虚无情绪,但通常只是就“生命”“死亡”等宏大命题进行思考;顾城对生死向来报以坦然接受的态度,并不回避这类主题,而是深入探讨其本质。然而对于爱情,顾城总是将“情欲”的一面摘得干干净净,极力避免在诗中描写爱情的过程;他笔下的爱情也是简单而理想化的,不涉及爱情本身,只捕捉那点游丝般的憧憬。
当我们将顾城诗中隐秘的爱情表达集中观照时,顾城的另一个形象也随之呈现——一面是梦幻童话里的“小王子”,另一面却是封闭自我世界里专制独裁的“暴君”。其爱情诗里,顾城的“凝视”无处不在,话语中透露出他对另一半专横的占有欲望。《远和近》中,“我”十分在意“你”的一举一动,在“你”漫不经心看云的瞬间,“我”便敏感地认为这是一种分心,觉得“你”离我很远了。这一“觉得”完全是“我”内心武断的主观感受,无关事实,也不容“你”去辩解。顾城不止一次在诗中强调“我”需要“你”的绝对关注,如《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里对爱人的想象:
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⑦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工编:《顾城文选》卷1,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9页。
诗里两次强调“永远”,还用了非常坚定的“绝”字,这种强硬的态度在顾城诗歌中较为罕见。向来追求梦幻和谐、内在人格孱弱的童话诗人,在谈及想象中的爱人时却表现强烈的控制欲,甚至带有不服从便自毁的倾向。顾城的爱情诗,纯洁却并不纯粹:看似唯美浪漫的示爱诗句,背后是专制懦弱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爱之名搭建的童话王国,实则是一种自私的牢笼。
二、内在特质:顾城人格与其爱情诗之关联
顾城爱情诗之所以呈现上述特点,与顾城的人格特质相关。其人格的孱弱在很早便有所显现,它表现为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极力回避成人世界。顾城一直强调自己是个孩子,拒绝长大,即使婚后也不愿承担责任。他不愿面对生活的压力,一味沉溺于其理想的童话王国,“童话诗人”这一称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位天才诗人理所当然的保护伞。习惯性的逃避让顾城的爱情诗缺少“进攻”的锐利,大多时候,他是以隐藏的“被守护者”身份出现的,如《南国之秋(二)》:
我要像果仁一样洁净/在你的心中安睡……/我要汇入你的湖泊/在水底静静地长成大树①顾城:《南国之秋(二)》,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9页。
单看这段文字,与其说两人是恋人关系,不如说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撒娇。这种爱情观畸同顾城的女性观有很大联系。在顾城的观念里,世界分为两类,一类是充满了洁净、自由的女儿性世界,一类是充斥强力哲学的男性世界。近乎于偏执的女性崇拜,令顾城始终厌恶自己的男性身份,他认为男性污浊、渣孽,要“用自己的混乱和黯淡来反衬女儿性的光辉”②顾城:《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你是前所未有的,又是久已存在的》,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对男性阳刚一面敬而远之的顾城,自然不愿在诗中流露“我”强势的男性气质。在顾城的理解中,这样的爱无甚问题,因为他对所有的女性都怀着“博爱”的态度。他将女性分为“女人性”“女孩性”“女儿性”,妻子谢烨“像湖泊一样”宽容、温和的性子,完美符合其对女人性的期待。顾城将女子天然的“母性”归于他爱情的一部分,心安理得地享受,不去区分“丈夫”和“儿子”两者身份权利和义务的不同,也就不用面临自身角色的转型阵痛。然而不管顾城如何模糊二者的界限,他自身是个成年男子的事实不会改变。男子所固有的欲望,与他对女性纯洁的崇拜有所冲突,这种冲突使他在写爱情诗时难以保持全然不谙世事的天真。顾城本人尽力在诗歌中隐藏、融合这一冲突,因此其对爱情的描写总是表现得十分节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顾城性格中的“早熟性”。顾城常以自己是“任性的孩子”为由,希望博得对方永远的关注,虽然有学者认为这是顾城对童年母爱缺失的心理补偿,但笔者认为这种心理比“补偿”更为复杂。顾城何其早慧敏感,他的诗之所以特别,正是因为很好地平衡了天真与深刻,看似简单童稚的语言背后有着“沉默的深处”。顾城对“童心”是刻意维持的,并非其的像孩子般随意写就。通过《顾城哲思录》和顾城的相关访谈,我们发现顾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意义上“天真烂漫”的诗人;相反他有相当理性、抽象、智慧的成熟一面。他在大众媒体面前不厌其烦地解释那顶奇特的帽子,且每次说法并不一致(比如有时说帽子是自己和外界的边界,有时又说帽子是烟囱,不高兴了可以用来出气);在参加诗歌交流会时故意迟到,为了享受压轴出场时所有人的掌声;总是眨着懵懂双眼,不善言辞的他,当年竟“躲在树上,画了一些神奇的解释,哄得赞成或反对者都以为那几句诗大有思想隐藏”①转引自毕光明、樊洛平:《顾城:一种唯灵的浪漫主义》,《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原文《远帆》,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我们有理由认为,顾城通过谢烨治疗童年创伤,享受谢烨无微不至的照顾,并利用文学的创作,让自己能心安理得地做生活上的巨婴。然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做到无条件的、永远专注地望着他,哪怕他是孩子、是天才诗人、是童话世界的王。如果“我的爱人”忽然掉过头去,离开了“我”的注视范围,等待她的是什么呢?激流岛的惨案似乎已经给出答案,谢烨在那一刻看到了顾城世界里的“阴云”。
其三,顾城有着近乎偏执病态的“情感洁癖”。他对女性“纯洁”的理解便很能说明:自顾自地将女性抬上圣洁的神坛,将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标签化为女人性、女孩性、女儿性。女人性代表大度的慈母,女孩性代表活泼的情人,女儿性则是接近无欲无求的仙子。这种女性崇拜看似尊重女性,实则是对女性的一种“捧杀”:通过放大女性奉献牺牲的一面,削弱女性的独立人格,使其成为“理想女性”的刻板想象。顾城在《门前》描绘过一副和谐的画面: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②顾城:《门前》,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06页。
这个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舒婷的《致橡树》: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③舒婷:《致橡树》,《舒婷诗精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2-93页。
舒婷在这首诗中抒写了独立女性理想的爱情观,即两人各自独立而又共同成长。然而在顾城的爱情诗中,美好只存在于表面,内在却对另一半的“纯洁”作出极高的要求。顾城诗中出现过很多次“眼睛”,以这一意象为窗口,我们可以窥探到顾城眼里的理想爱人。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爱人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④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工编:《顾诚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9页。;在《就在那个小村里》里,“你眼睛的湖水中没有水草”⑤顾城:《就在那个小村里》,《顾城的诗顾城的画》,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9页。。可见,顾城心中的爱人美好到没有一丝瑕疵。他对女性的洁癖在《岛》中已然明显:
有人爱花/有人爱人/有人爱雪/而我/却爱灰烬的纯洁⑥顾城:《岛》,《顾城的诗顾城的画》,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203页。
顾城爱的是抽象的人,而非具体的人。凡是具体的人都有七情六欲、爱恨嗔痴,可顾城宁愿毁灭一切,留下灰烬,也要保存其理想中的“纯洁”。舒婷身为女性,更能体会到女性处境的不易,她在《神女峰》中直言:“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⑦舒婷:《神女峰》,《舒婷诗精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充分表达了对女性欲望的正视。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顾城对女性、对爱情的偏激。到了后期,顾城认为女儿性是一种由女儿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性别本无关系,并非女人即有女儿性。可以想见,顾城痛恨男性而喜爱女性,不过是痛恨男性需要承担的义务,更愿意用他臆想的女儿性“精神”来逃避现实世界的压力。讽刺的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身为男性的权利。1988 年7 月,顾城和谢烨移居激流岛,在《字典》一诗中写到:
在有花的地方坐下/一切将从这里开始/我的妻子要为我生育部族①顾城:《字典》,《顾城的诗顾城的画》,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页。
诗歌中流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以“我”为尊,要求妻子为他生育。回顾顾城诗中的“你”,“我”的爱人,从未拥有过“我”平等的对视。顾城实际上并不理解女性,更遑论给予女性真正想要的“爱”。更为遗憾的是,或许顾城终其一生也并未学会如何爱人。仿佛是预言般的,顾城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已经想到了自己的结局,没有家、没有同行者、只有虚幻的梦:
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②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0页。
三、外在机制:“童话诗人”的生成与阴影
顾城的爱情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童话诗”“寓言诗”所掩盖,这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由三点造成:朦胧诗时期特殊的阅读机制、同时期诗人爱情诗的突出以及童话诗人的形塑。以顾城的《远和近》被推上朦胧诗神坛这一事件为例,可以探寻该时期特殊的阅读机制如何将这首诗的意义“朦胧化”,如何成功定格了顾城“童话诗人”这一身份,最后又如何反过来,形成遮蔽其爱情诗的庞大阴影。
傅元峰对朦胧诗的定义为:“‘朦胧诗’的‘朦胧’并非是诗学效应,而是历史事件。”③傅元峰:《孱弱的抒情者——对“朦胧诗”抒情骨架与肌质的考察》,《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从时代背景来看,朦胧诗诞生于非常时期结束后的空白期,其“朦胧”形成于历史语境造成的阅读障碍上。《远和近》的主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艾青认为“评论家也各人在做各人的文章”:从阶级论出发认为这首诗用“远和近的象征表现了物理距离和感情距离的对立,表现了对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声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④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李建立编:《朦胧诗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页。;从英美新批评理论出发则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可以理解为灵与肉的对立和冲突,远和近可以象征为现实/理想、实在/欲望、精神/物质等等⑤魏天无:《怎样细读现代诗歌——以顾城的〈远和近〉为例》,《名作欣赏》2007年第1期。。诗人自己的解释也颇有意思,称“《远和近》很像摄影中的推拉镜头,利用‘你’、‘我’、‘云’主观距离的变换,来显示人与人之间习惯的戒惧心理和人与自然原始的亲切感。这组对比并不是毫无倾向的,它隐含着‘我’对人性复归自然的愿望”⑥顾城:《关于〈小诗六首〉的信》,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00页。。
有趣的是,这首诗很容易读出“你”与“我”之间的暧昧意味。把《远和近》放回到《小诗六首》组诗中去看,会发现组诗中有五首涉及“你”和“我”。在这些诗中,“你”是和“我”相互慰藉、相互依偎的对象;在《在夕光里》中,基本可以明确“你”就是“我”的恋爱对象。在众多主流解读中,却并无人提及这是一首“情诗”。虽然解释成“人与人的关系”可自圆其说,但从诗中读出“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则明显带上时代烙印。完全沉浸在自我梦幻中的爱情诗,这种解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里,还是太格格不入。情感体验层面的爱情和个人意识曾经是非常前卫的诗歌,超越政治话语的修辞也一度蒙蔽了读者。然而事实证明,许多朦胧诗的“朦胧感”在之后消失了,它们的蕴意远没有曾经想象的那般复杂。
可以进一步追问:时代背景固然是顾城爱情诗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可同时期其他朦胧诗人爱情诗的井喷现象又该如何解释?从客观上看,顾城的爱情诗本身表达不明朗,创作数量占比较小的情况下,与同期擅长写爱情诗的诗人相比,并不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舒婷的《致橡树》《日光岩下的三角梅》《神女峰》,融合了伟大的女性意识和平等的爱情理想;北岛的《雨夜》《你说》《爱情故事》,借助爱情抚慰现实的灵魂,拯救沦落的人性。顾城“朦胧”的写法,注定会牺牲一部分爱情诗所必需的原始直接的冲击,再加上同期诗人创作爱情诗的突出,顾城的爱情诗自然处于被无意忽略的状态。
那么,为何顾城坚持“朦胧隐秘”地写爱情诗?不难发现,对于《远和近》的解释,顾城也有意将其往“童话”“自然”的主旨靠拢。虽说创作者自身的阐述是解读诗歌不容忽视的参考材料,但并不代表必须要对其全盘接受和信任。一方面,创作者的解读同样会受思想背景和当时舆论的干扰;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创作者的说法也会模棱两可。顾城不只一次出现过创作内容与创作理念表达上的矛盾:例如顾城虽与众人反复讲述“诗意童年”,但实际上他并不喜欢劳作的生活,这与他想象中玻璃一样的世界有很大的距离,而这种距离让他感到痛苦。在这些“矛盾”的说辞中,顾城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意图,那便是维持其“童话诗人”形象。
可以说,顾城成为“童话诗人”,原是无心,后是顺势;既是偶然,也是必然。1980年《远和近》问世时,舒婷曾在4月赠给顾城一首《童话诗人——给G.C》,“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①舒婷:《童话诗人——给G.C》,《舒婷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这句诗奠定了其“童话诗人”的称号;彼时刚凭借《一代人》一举成名的顾城,确实以天真的“黑眼睛”形象在大众面前亮相。《小诗六首》发表在《诗刊》1980年10月号时,顾城添加了一段序言:“我生活,我写作,我寻找美并发现美,这就是我的目的。”②顾诚:《小诗六首(六首)》,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9页。这一段阐述其对美、童话、自然追求的宣言,使得当时有关这组朦胧诗的论争更加激烈,主题更为扑朔迷离。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序言实际上是顾城在《诗刊》编辑的要求下临时加上的,然而正是这段序言进一步加深了顾城在大众心中“童话诗人”的形象。作为1980年代诗坛的顶级刊物,《诗刊》在朦胧诗的发现和推广上功不可没。1980年4月,顾城在《诗刊》“新人新作小辑”中发表诗作《眨眼》,同年参加《诗刊》于7月20日至8月21日举办的第一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参与者共17人,他们的作品以“青春诗会”为总标题统一发表于《诗刊》10月号,《小诗六首》便是在第一届“青春诗会”诞生的作品。这场活动的举办目的主要是培养扶植青年诗人,据青春诗会作品组副组长王燕生回忆:当时《诗刊》的领导,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四人,“每个人负责三四个学生,除了讲大课之外,平时还要单独辅导……辅导以后,他们也要花时间修改,然后还创作新作品”③田志凌、汪乾:《青春诗会: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王燕生访谈》,《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记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然而,顾城在自我介绍时便“惹怒”了老师们,他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称“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④刘春:《海子、顾城——两个诗人的罗生门》,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语罢好几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耳光,你知道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①刘春:《海子、顾城——两个诗人的罗生门》,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虽然未有顾城分组情况的确切记录,但舒婷在回忆顾城的文章《灯光转暗,你在何方?》中曾说,江河曾在排队打饭菜时告诉她顾城被“安排的辅导老师严词厉色训了”②舒婷:《灯光转暗,你在何方?》,《2014中国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舒婷和其他成员跑去央求邵燕祥收留顾城,顾城这才“转班获释”。在青春诗会中最引人瞩目的《小诗六首》,实际上是“差生”顾城的“意外之作”。在《和顾城谈他的诗》一文中,顾城称“他的几批习作几乎都不适用。当时诗刊的领导很关心他,找他谈话,希望他写一些现实感强、光明的诗,但由于他当时头脑淤塞,就是没写出来。最后要定稿了,他便摘了一些笔记性的东西交上去”③余之:《岁月留情》,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页。。顾城曾明确表示:“诗刊的领导并不赞成这种写法。”直到1982年顾城给王燕生写信,还署名为“留级生”,信中表示自己“终于积极了,找到了光明,于是朦胧化为了彩虹”④王燕生:《我所认识的顾城和李英》,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可以看出,青春诗会的编辑理念是确保大方向的前提下,充分给予青年诗人机会。这首使顾城家喻户晓的《小诗六首》,实际竟是诗人与刊物之间互相妥协的一次“意外”。由此可看出这个组序言和《小诗六首》的内容相关性并不是太大;临时加上的“序”主要是为了“符合刊物主题”,“为了能达到‘积极、向上’的要求”⑤顾城:《顾城文选》卷1,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纵观顾城的一生,他对“童话诗人”这一称号欣然接受,并在诗歌创作中一以贯之。这既是出于其本人的创作理念及审美追求,也有一部分是缘自他逃避成人世界的私心。作为童话诗人”,顾城的诗歌成就与“童话”密不可分,该形象在诗坛、读者心目中根深蒂固,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诗中的“爱情”。
结 语
顾城的爱情诗长期被读者所忽视,或者说,读者很少有从顾城的诗中去发现爱情。在大众印象里,顾城是写朦胧诗的童话诗人,人们习惯性只关注诗中明丽纯净的童话,把其中具体的感情抽象化。另一方面,顾城的一生充满争议,他的诗歌某种程度上已论为其私人八卦的附属品,喜爱者借其诗歌“美化”他的杀人行为,厌恶者因蔑视他的行为而贬低其创作成就。顾城的爱情诗数量虽在其诗歌创作总量上不算多,但为我们还原其爱情体验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顾城其人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