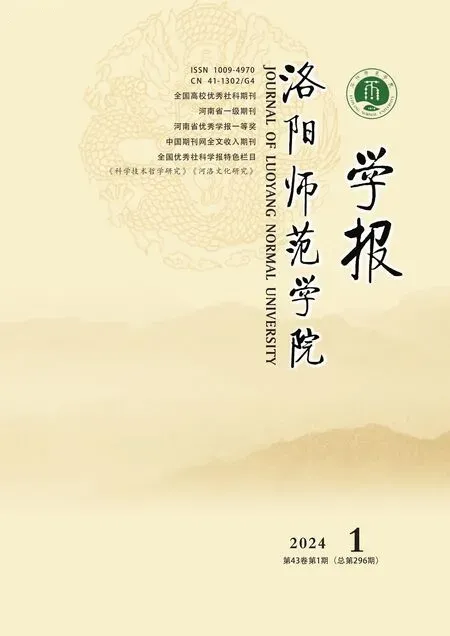新、旧《唐书》张皇后叙事差异及政治讳隐
刘思言,耿战超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重庆 400031)
皇室内部的猜忌斗争是自唐王朝开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史官“为尊者讳”的书写修饰下,客观真实的历史面向常常被有意遮蔽,整个皇室内部呈现出一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气象,往往产生很多被扫入历史角落里的人物,成为这种修饰下的牺牲品。本文从《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不同史料的书写出发,以“比较成书于不同时代的文献对同一或相关记载的异同”的方法,试梳理唐史记载中对张皇后的人物形象的建构,“由此探讨各时期政治环境、历史观或史家个人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1],从而剖析皇室政治斗争下一个女性所被迫扮演的历史角色,以期将史料的历史讯息充分真实地呈现出来,并由此管窥政治讳隐对于历史书写影响的具体样态。
一、新、旧《唐书》对张皇后的叙事分析
张皇后的祖母窦氏是玄宗生母之妹。玄宗因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所以对其一系恩渥甚隆。玄宗之子李亨被立为太子时,张氏被封为良娣。马嵬之变后,太子转移路线,动身前往朔方灵武,张良娣从军同行,其间不避危难以卫太子,并为其参赞谋划。至灵武后,太子李亨自行登基,是为肃宗。乾元初年,张氏被册封为淑妃,后被立为皇后。肃宗执政时期,张皇后与权宦李辅国暗中勾结,常欲谋害太子李豫,以立其子李侗。后李辅国倒戈,代宗登基,张皇后被废为庶人,后被杀。
张皇后其人,新、旧《唐书》的《后妃传》中皆有记载,《新唐书》在《旧唐书》基础上增删而成,但主要集中在人物列传上的增补,而对于本纪、后妃这类内府方面的材料,由于文献不足,通常以延续《旧唐书》居多。但在对于张皇后的叙述中,比较新、旧《唐书》记载,史家幽微之笔触中仍有着隐晦的差异,使得我们可以对传统历史书写中复杂皇权争斗的政治讳隐窥见一斑。
在新、旧《唐书》对张皇后叙述策略的比对中可以看出,除却开篇人物家世背景介绍,及安史之乱爆发时张皇后随军途中不顾个人安危的记载,《旧唐书》较之于《新唐书》更为详细,此外都是《新唐书》在《旧唐书》基础上加以补充。而细加比对可见,《旧唐书》在随军途中,“太子如灵武,时贼已陷京师,从官单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险难,兵卫非多,恐有仓卒,妾自当之,大家可由后而出,庶几无患’”; 以及至灵武后,“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劳之曰:‘产忌作劳,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养之时,须办大家事’”[2]2185。《旧康书》所记录的张皇后舍己为公的两则事迹, 在《新唐书》中都被简化,而诬谮皇子、尊己“翊圣”、谋徙上皇等一系列恶行,《新唐书》反而在《旧唐书》基础上或无中生有,或由简变详。
《新唐书》在交代张后家族背景之后、安史之乱随军之前,另有一段文字涉及张氏尚未专宠时事,是《旧唐书》所缺的。此段文字记述肃宗尚为忠王时,纳韦元珪之女为孺人。李亨封太子后,先立韦孺人,后为张良娣。而由于韦妃的兄长韦坚被李林甫陷害而死,太子李亨因而十分恐惧,请求与韦妃断绝夫妻关系。还在毁服幽禁中时,安禄山造反,韦妃陷于叛军之手,于至德年间去世。在对这样的背景交代完毕后,《新唐书》增补一句:“始,妃既绝,良娣得专侍太子,慧中而辩,能迎意傅合。”[3]3498《新唐书》将这段文字补充于安史之乱爆发前,给尚未登场的张皇后先树立了八面玲珑、曲意逢迎的人物设定,将此放置于战乱前,用以修饰战争中张氏对肃宗的行为,加以微言大义,意指张氏此番行为更多在曲意表演。
此外关于张皇后与李辅国暗中勾结干预国政,逾矩主持亲蚕礼,新、旧《唐书》上亦做类似叙述,但《旧唐书》叙述不及《新唐书》详细。除此之外,《新唐书》另外特意补充张皇后“讽群臣尊己号‘翊圣’”[3]3498,意欲比肩武则天与唐高宗二圣临政之事。并且例举上元二年(761)端午日,“帝召见山人李唐,帝方拥幼女,顾唐曰:‘我念之,无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当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内制于后,卒不敢谒西宫”[3]3498。这一点,可以在与《新唐书》同时期的资料《资治通鉴》中得到佐证。《资治通鉴》中,史家也以明确的文字点出,肃宗不见玄宗的原因是“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4]7113,坐实了张后操弄权柄以控肃宗的恶名。
在新、旧《唐书》对张皇后的叙述末尾,二者都提到张皇后所参与的另一涉及江山社稷的重要事件,同样《新唐书》较《旧唐书》记载更为详细。肃宗尚在灵武时期,其儿子建宁王李倓因赞同李泌主张将玄宗赐予张氏的七宝鞍分赏给将士,而遭到张氏的诬谮而死。并且认为此事带给太子李豫极大的阴影,亦是由于张氏咎由自取。肃宗病倒后,张氏意欲加害太子李豫,被倒戈的李辅国幽禁,并且在太子即位后被杀死。
新、旧《唐书》在对张皇后的叙述中,整体而言并无太大矛盾冲突之处,差别似乎只是《旧唐书》简略,《新唐书》翔实,但细究其叙事,可以看出《新唐书》在翔实的基础上,加上许多诸如“良娣得专侍太子,慧中而辩,能迎意傅合”“帝不豫,后自箴血写佛书以示诚”之类修饰性的语句。这些细节使得张皇后这个人物在呈现方式上更为曲意逢迎,以伪善的方式突出其人城府缜密。
二、新、旧《唐书》所叙矛盾及原因
上文所言,结合新、旧《唐书》在叙事上的差异,佐以《资治通鉴》作为旁证,其中文本的矛盾甚至不合常理之事颇多。概括为三点:一是张皇后人物形象的割裂; 二是上文所涉及的端午之事; 三是建宁王遭张氏诬谮而死之事。借对第二、三点的分析,我们更能分析第一点问题所产生的原因。
(一)端午事件
端午事件是指端午日时,山人李唐觐见肃宗,以肃宗念幼女,类推玄宗念肃宗。舐犊情深,肃宗泫然涕下,但苦于受制于张皇后,最终也未敢谒西宫。这段史料的记录见于《新唐书》,而《旧唐书》并未涉及。
此时肃宗是否能动身前往探望幽居西宫的玄宗,又牵扯到玄宗、肃宗二人在玄宗晚年的矛盾,而对于此事的起源,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记录并无较大差异。我们首先找到到此事的起因:上皇(指唐玄宗)多次来到长庆楼,父老和经过的人常常聚集此处参拜,群呼万岁,上皇经常到楼下放置酒食赐予百姓,又召见将军郭英乂等到楼上赐宴(1)参看《旧唐书》卷184,第4750页; 《新唐书》卷208,第5880页; 《资治通鉴》卷221,第7093页。三书记述大致相同。。而李辅国出身微贱,且在玄宗朝是为高力士养马的奴仆,他想要立奇功来巩固他的恩宠,于是上奏肃宗称玄宗处有异谋。
辅国因妄言于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礼、力士等将不利陛下,六军功臣反侧不自安,愿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时,兴庆宫有马三百,辅国矫诏取之,裁留十马。太上皇谓力士曰:“吾儿用辅国谋,不得终孝矣。”会帝属疾,辅国即诈言皇帝请太上皇按行宫中,至睿武门……辅国靴而走,与力士对执辔还西内,居甘露殿,侍卫才数十,皆尪老。[3]5880
《资治通鉴》对此叙述更为详细,且列此处作为补充:
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闾阎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上不听。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辅国矫敕取之,才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辅国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应。辅国惧。会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
……上皇曰:“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请罪。上又迫于诸将,乃劳之曰:“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4]7094
这里上演了一场李辅国幽禁唐玄宗的大戏,而史家谓李辅国目的在“欲立奇功以固其宠”,既然是为“固宠”以邀功,便只能说是投肃宗之所好。唐肃宗的态度“泣曰”“不听”“泣不应”似乎很难与李辅国的“固宠”行为相联系,唯一的解释就是唐肃宗只是借李辅国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亦是对肃宗“刚好”身体不适,辅国“矫称”上语,用五百射手兵刃相加逼玄宗至西内后,唐肃宗对李辅国却并无任何处罚,且此事后即“以功迁兵部尚书”[3]5880这一系列行为最好的注脚。另外,玄宗被迁居所在的西内太极宫甘露殿,在肃宗时期仅用于举办内廷典礼,较之于迁居之前所在的南内兴庆宫,与外官及百姓的地理距离则是一处“真正的禁宫”[5]。以迁居西内的方式从政治影响上剥夺玄宗的所有权力,又通过将陈玄礼、高力士等人皆从玄宗左右剔除的行为,彻底将晚年的玄宗与外界隔离。这种做法很难令人相信是李辅国一人所为,更像是肃宗对玄宗多次登上长庆楼引得父老瞻拜的行为的报复。由此可见端午事件的起因,李辅国只是唐肃宗借刀杀人的一把刀,真正想要幽禁唐玄宗的,正是唐肃宗李亨本人。
再回到端午事件本身:
又与辅国谋徙上皇西内。端午日,帝召见山人李唐,帝方拥幼女,顾唐曰:“我念之,无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当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内制于后,卒不敢谒西宫。[3]3498
初,李辅国与张后同谋迁上皇于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4]7113
虽然李辅国与张皇后或许有暗中勾结把持朝政的某些行为,但“迁上皇于西内”这种涉及两代最高统治者争夺权力的戏码,必然是由肃宗授意而为。且肃宗之即位,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是“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猝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6],其本身得位不正也使得肃宗即位后与玄宗关系极为敏感。而上文中则是将玄宗、肃宗二人之间权力的博弈,通过肃宗所上演的温情款款的笔触,将玄宗和肃宗的矛盾引向张皇后。但唐肃宗可以算是整个“安史之乱”最大的获益者,他绝无可能是政治上软弱的角色。况且战乱时,肃宗作为重整山河的领导者,决策北上以图兴复,又怎么可能畏惧于(或受制于)一个女人而不敢前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只能说是他本人并不愿意前去,这也是对前文肃宗借李辅国之手,幽禁了依旧妄想夺回权力的唐玄宗的解释。这两段文字中,“帝泫然涕下”“上泫然泣下”这些类似政治表演的行为,似乎都是在极力地修饰出肃宗宅心仁厚、至孝笃亲的政治形象。而为了建构起这种形象,修史者迫于压力,需要找出一个蒙蔽圣意的奸邪之人,于是这个人物前期是李辅国,后期则是张皇后。
(二)建宁王李倓事件
张皇后谋害建宁王李倓,涉及了储君直接利益冲突,较之于玄宗与肃宗之间的矛盾,似乎更加可以解释。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我们回到《新唐书》对此事的书写:
初,建宁王倓数短后于帝,上皇在蜀,以七宝鞍赐后,而李泌请分以赏战士,倓助泌请,故后怨,卒被谮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谨甚。后犹欲危之,然以子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无患。[3]3498
时张良娣有宠,与辅国交构,欲以动皇嗣者。倓忠謇,数为帝言之,由是为良娣、辅国所谮,妄曰:“倓恨不总兵,郁郁有异志。”帝惑偏语,赐倓死,俄悔悟。[3]3618
另参见《资治通鉴》对至德二载(757)的记载:
李辅国本飞龙小儿,粗闲书计,给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辅国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见张良娣有宠,阴附会之,与相表里。建宁王倓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二人谮之于上曰:“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上怒,赐倓死。[4]7013
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些文字的叙述中,都是将建宁王李倓之死归结于张皇后与李辅国结党营私,沆瀣一气。而建宁王李倓作为耿直诋讦之人,被张皇后与李辅国二人记恨,最终以“谋害广平王”的罪名蛊惑肃宗,被肃宗赐死。
单从常识上,我们很难去理解,因为一个妃子和宠臣的谗言,皇帝便赐死一个卓有建树的儿子。即便是建宁王当真耿切直言,遭张皇后算计,但肃宗何尝没有自己的判断,处死建宁王的最直接受益人便是张皇后与广平王。在这么明显的处境下,肃宗怎会对张皇后的计谋不起一点疑心呢?唯一的解释便是,张皇后所“诬陷”的李倓谋害广平王,并非空穴来风。对于前者,吕思勉提出:“张后欲立其子,碍之者乃为代宗而非建宁,谗之何为?然则建宁之死,事恐专由于辅国,谓其兼由于张后者实诬。”[7]并将建宁王之死归因于广平王与建宁王之争。因史料皆作“张后所间”说,故而笔者提出第二种可能性,即张后对建宁王的构间与构间的内容皆确有其事。
这一点在同样在《资治通鉴》有言如此:“建宁,朕之爱子……但因此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4]7036另外在《新唐书》中亦有这样的叙述:“泌与帝雅素,从容语及建宁事,肃宗改容谓泌曰:‘倓于艰难时实自有气,为细人间阋,欲害其兄,朕计社稷,割爱而为之所。’”[3]3618这里“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可见对于张皇后对建宁王的“谗言”,肃宗并非单纯听之信之,亦是有过调查,并且确信是李倓身边之人所调唆,使得李倓确实有谋害兄长的实际行动,方才赐死他。
正如前文所言,唐朝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若说建宁王作为最早提议让尚为太子的李亨前往灵武称帝的其中一人,且在史书记录为“英毅有才略。善骑射,禄山乱,典亲兵,扈车驾”[3]3618,要说其人没有任何权力争夺的想法与行为,恐怕无法使人信服。唐王朝开国以来的玄武门之变、先天二年政变,甚至肃宗本人在灵武称帝,这一系列的事件都使得皇室内部的关系更为敏感。即便建宁王本人无意争夺皇位,唐肃宗和广平王亦不可能对此不作防备。因而,与其说是张皇后与李辅国对建宁王进行所谓的诬谮,不如说是建宁王本身的一些想法和行为触动了权力集团本就敏感的神经,因而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三、政治讳隐下“张皇后”的人物形象构建
从上叙之事来看,我们似乎更能理解所谓的张皇后在新、旧《唐书》后妃列传中的人物形象的割裂。因为张皇后在肃宗病危,代宗即位后,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不免落下更多超越本人的“恶”的一面。在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博弈中,这种历史的真相在修史者的讳隐下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射到史料之中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不单是不同史料之间的矛盾,而且更应留意同一本史料之中的人物形象的割裂。因为作为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这种修成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史书,后一本史书大多参照前一本而成。而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对于张皇后这种作为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妃嫔而言,本就很难找到更多可靠的文字记述,所以更应留意同一本史书中所记述的人物形象的矛盾与割裂。
然而这并非否认人物的复杂性,也不是限定人必须只能以一种形象留存。只是在这种割裂中,不免要使我们面对更多的思索和质疑,并且将其到具体情境下,结合与人物相关的其他人物相交织的历史事件,来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
新、旧《唐书》虽有叙述差异,结合《资治通鉴》来看,张皇后本身绝非淡泊处世的形象,而是富有政治远见之人。这一点,从其能够在玄宗“西幸”的危急时刻,赞同李辅国之谋而促太子“北趣灵武”已可见端倪。再从“时军卫单寡,夕次,娣必寝前”与“驻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3]3498来看,张良娣也是个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人。后世史家所谓的“慧中而辩,能迎意傅合”的曲笔,在战场之上刀剑无眼的生死攸关时刻,与肃宗本人幽禁玄宗的“上泣不应”相较而言,张皇后的行为则更多具有真实意味。甚至在“帝不豫,后自箴血写佛书以示诚”[3]3498时,也是依稀可从无情帝王家中见得几分真心。
至于张皇后本人,她虽不是安分守己的后妃之德的典范,并且与李辅国暗中勾结妄图控制更多的权力,可以说是有野心与权谋; 但我们回到人物的具体处境来看,对张皇后所处的前朝后宫的背景而言,她作为一个女人,既无法建功立业,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否会色衰而爱弛,控制更多的权力,扶持自己的儿子或养子当上下一任继位者,是她作为一个后妃能够保全自身的唯一的方式。综上所述,在对张皇后的相关叙述中,《新唐书》较之于《旧唐书》,在保留基本事件的前提下,对张皇后的褒奖事件的记载变得更为简略,另外,对人物“恶”之事件叙述则变得更为详细。从叙事变化可以看出,超越张皇后本身“恶”的一面在修史者的经营下,呈现出显著的强化。
这种更为翔实周密的张皇后的恶行,是由修史者根据主观意图构建出来的,亦反映出其中“为尊者讳”成分的加强,其中“历史真实”与“史家修饰”两种势力盘旋交织、此消彼长。而从造成这种叙述变化的原因来看,修成于北宋时期的《新唐书》,与修成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史家修饰”较之于“历史真实”更胜一筹,这也隐晦地从侧面反映出,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的修撰者,如何审视早先的史书,以及他们意图从史料的更改与建构中,传递出对“一国之君”以及“皇室内部关系”所做的修饰与认知。
让我们再回到史书所构建的驱逐贤臣、谋害皇子、幽禁玄宗的“张皇后”,结合上文所阐述的政治讳隐的问题,修史者成功地以张氏一人的恶名,修饰出玄宗与肃宗、肃宗与建宁王李倓、建宁王李倓与广宁王这些皇室内部父子、手足之间感人肺腑的亲情,还隐约透露出些许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而我们意欲探究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就必须借助史书细节之线索,拨开史官矫饰下的面纱,方能透过浓墨重彩的“演员”面谱,看到历史人物更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