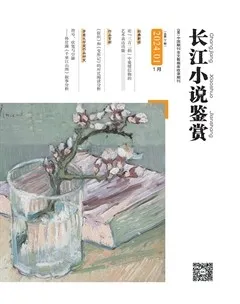身体呈现与性别建构:《水浒传》身体叙事探赜
尤佳星
[摘 要] 《水浒传》的叙事体系中,身体书写是明显性别化的,其間充斥着基于男性经验的社会性别建构。作者通过身体的符号化、隐喻化处理,塑造了两性角色迥乎不同的形象气质,折射出男权中心的话语体系下“男阳女阴”“男刚女柔”的社会定位和审美传统。此外,创作者通过大胆直露的情欲化的身体叙写,在事实上反映了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 《水浒传》 身体叙事 性别建构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18-05
人的身体是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性别文化的重要场域。性别不仅是先天的,还受到社会文化的后天建构,它可视为一种再现,而身体则是促成性别再现的一面镜子,透过两性身体的不同呈现,人们既能看到男女在生理结构上的自然分野,更能窥见性别身份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1]。《水浒传》中,身体是重要的叙事成分,创作者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境与间接的身体经验,呈现出两性的不同,共同推进着叙事的发展,一方面,身体作为个人欲望、感性经验展开的媒介而存在;另一方面,身体也是性别权力施展的一处关键场所。本文试图在社会性别理论视域下,基于文本,结合客观史实,从符号、修辞等角度,对《水浒传》中的身体叙事进行论述。
一、放大了的身体:身体符号的标出
符号是用来指称或代表他物的重要载体,它是文学语言的有机成分,能够构成特定的修辞元素与意义[2]。想要探究《水浒传》中的身体叙事,并阐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符号是一个规避不开的关键概念。
符号的性别指向,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文王姬昌演《易》,用简单的抽象符号区分“阴”“阳”,创制八卦,以垂万象,在《易传》的阐释中,“阴”“阳”已被用于诠释男女互斥的刚柔属性和主从分明的两性关系。汉代以降,以抽象符号为基础,不断敷演而成的“阴阳学说”,经过董仲舒等儒生的阐释与丰富,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男阳女阴”“阳尊阴卑”的重要命题,逐渐成了男权社会性别秩序的理论基础[3]。由“阴”“阳”两极构筑起的符号系统,对我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在《水浒传》中,具体展现为两性身体的符号化。《水浒传》的创作者在进行人物刻画时,针对两性角色的某些外部形态和特征进行了聚焦式描摹,而这些被刻意放大、频繁呈现的身体部位,无一例外都在“男阳女阴”的理论范畴之内,作为叙述对象的两性身体,在事实上被抽象为了符号性的存在。当两性的身体特征被有意识地符号化,并得到标出时,通过所指与能指的双重指向,身体叙事策略及性别符号的象征意义也就得以延续,隐秘地传达出了社会性别形塑和区隔的深层文化内涵[4]。
1.以“阴性特质”为主要内核的女性身体符号
学者朱学勤曾说,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是男性文化,“女性如有价值,也只有美感价值,而且是生理性的美感价值,不是文化意识上的审美价值”[5]。《水浒传》描述的世界是以男性群体为主的世界,其中的女性角色占比仅有一成不到,处于明显的边缘化位置。《水浒传》中的这部分女性群体总是作为被凝视、被观看的“他者”而存在,同作为审美主体的男性之间构成了一种被动的关系,被观赏性成为衡量其价值的主要标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女性角色常常作为男性的观赏对象而出现,她们的身体特征在事实上取代了内在特质,沦为了程式化的性别符号,这些符号在角色的塑造和接受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思议的定向作用。
《水浒传》对女性角色着墨不多,而有较为详细的身体描写的,更是寥寥可数。据笔者的归纳和统计,发现创作者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最常使用的身体符号是“纤腰”,其次是“小嘴”,再次是“秀发”和“粉面”,这些词语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的审美趋向,也通过反复的话语暗示和视觉刺激,对读者进行想象引导,满足了男性的心理需求。此外,“小脚”也是多次出现的特殊的身体符号之一:将女性的脚通过外力作用扭曲变形,造成足部无力、身姿袅娜柔弱之态,这在视觉上突出了她们的性体征,极大地迎合了男性的窥探欲和掌控欲。整体而言,这些符号或表征着身体的单薄瘦小,或凸显着身体的妩媚娇嫩,无一例外体现着由男性主导的、对女性身体的性别建构,即认为女性应当具有偏柔、偏弱的“阴性特质”,这些符号建构出一个以女性身体为中心的规训场域。
在这种性别建构下,即便是“一丈青”扈三娘这样的巾帼英雄,创作者在对其进行身体书写时,也要通过纤腰、粉面、素手、秀发等身体符号,勾勒出她的“天然美貌”,凸显其阴柔的一面,而将其英武超群的刚强一面弱化。无独有偶,以性别为依据的身体规训,就连被异化了的“悍妇型”角色也不能幸免——譬如“母夜叉”孙二娘,小说中一边写她“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另一边又写她“鬓边插着些野花”“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纽”,试图通过她云鬓插花、搽脂抹粉的身体符号,给恶行恶相的孙二娘补上点女性阴柔特征。又如15岁杀夫的“大虫窝”段三娘,小说中既写她“眼大露凶光,眉横杀气”,是个“膘肢坌蠢”“面皮顽厚”的丑妇,但在写她同王庆洞房时,却又刻意勾勒其腰身,描摹其酥胸,说她“敞出胸膛,解下红主腰儿,露出白净净肉乳儿”,这些具有阴性特质的身体符号,使段三娘俨然由凶悍的恶妇,倏地变作了妖娆的娇妻。
2.以“阳性特质”为主要内核的男性身体符号
论及我国古代小说对男性形象的塑造,《水浒传》堪称翘楚。这不仅在于书中涉及的男性群体规模大,范围广,还在于其对儒家文化语境中“谦谦君子”“文弱书生”式的男性形象进行了大力颠覆,以大量刚猛、粗豪、充满力量感、具有侵略性、富于“阳刚之气”的男性形象代之,掀起了一场“美学暴动”[6]。在《水浒传》男性形象的构成中,男性角色的某些外在身体特征也被提炼为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性别符号,用于指称明显区别于女性角色的“阳性特质”。
据笔者统计,《水浒传》在形塑男性形象时,最常出现的身体符号之一是“须髯”。须髯作為男性的第二性征,具有特殊文化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方面的体现。在中国古代,剃去胡须曾经是一种被称之为“耐”的刑罚,可见胡须不仅是一种“雄性装饰品”,还一度是男性尊严的象征[7]。据唐代李延寿《南史·褚彦回传》记载,山阴公主爱慕褚彦回,要求让他侍自己,彦回不从,公主说他“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8],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男子的须髯被视作其男子气概的代名词,是代表力量、权力等“阳性特质”的重要身体符号。以梁山好汉中的“三十六天罡”为例,这36人中,有22人是小说中明确提及有须髯的,占比超过60%。除却有无之别外,好汉们的须髯在具体形态上也不尽相同,据笔者比较发现,个性儒雅或形貌俊美型男子,如宋江、吴用、燕青、徐宁、柴进等,须髯大都细而少;与之相对的,个性刚猛、粗豪型男子,如李逵、索超、鲁智深、雷横等,须髯大都粗而多。由此可见,《水浒传》在塑造男性角色的身体时,倾注着传统心理上的“力量崇拜”,越是力量型的、符合“阳刚之美”的男性角色,“须髯”这一阳性符号就越容易得到标出。
肤色(包括面色)也是《水浒传》中男性英雄常被标出的身体符号,与主要女性角色多为雪白皮肤不同,水浒传中的男性角色则以深色皮肤居多。同样以“三十六天罡”为例,在文本中有肤色描写的17位“天罡”好汉中,卢俊义、穆弘、燕青、张顺、公孙胜、吴用6位是白皮肤,杨雄为“淡黄面皮”,其余全是黑、紫、红等深色皮肤,深色皮肤的好汉占比接近6成。并且,在6位白皮肤的好汉中,吴用、公孙胜、卢俊义偏儒雅,穆弘、燕青偏俊美,剩下一位号称“浪里白条”的张顺,身体则矫健灵活,通过其与典型的力量型角色李逵打斗的场面便可看出,张顺身上有种不同于一般男性的“巧慧”,而这一特点,恰是偏女性化、指向“阴性特质”的。或许这也是为何灵活沉稳的张顺与笨拙急躁的李逵,在肤色上也会形成一白一黑的鲜明对比。
除上述所举之外,刺青、宽肩、厚背等特征,也是《水浒传》塑造男性英雄时常常会使用到的身体符号,这些被放大了的身体符号,在具体的文本中,都给人以一种刚猛粗豪,充满力量感和侵略性的“阳性特质”,在此不做逐一分析。
二、隐喻化的身体:两性互异的身体隐喻体系
隐喻,又称暗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指用一个词或短语指出常见的一种物体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概念,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水浒传》常常对角色的身体进行隐喻化处理,并且以性别作为分野,分别采取了两套截然不同的隐喻体系:女性身体通常采用的是“植物隐喻”,而男性身体则通常采用的是“动物隐喻”。从这两套互异的隐喻体系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在塑造人物形象,呈现人物身体时,同样遵从了“男阳女阴”“男刚女柔”的社会定位和审美传统 。
1.女性角色的植物隐喻
植物隐喻是以各种植物及其特征为喻体,用来指称或表征需要说明或陈述的人或物。
《水浒传》对女性角色的植物性隐喻,首先从人物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如潘金莲、金翠莲、玉兰等,而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作者也常常使用隐喻手法,将她们的某一身体部位与植物相关联。据笔者统计,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类意象有桃、樱桃、柳、莲、笋等,这些意象无一例外都是用于修饰女性身体的。如《水浒传》第四回,鲁达初见金翠莲时:“金钗斜插,掩映乌云;翠袖巧裁,轻笼瑞雪。樱桃口浅晕微红,春笋手半舒嫩玉。纤腰袅娜,绿罗裙微露金莲;素体轻盈,红绣袄偏宜玉体。脸堆三月娇花,眉扫初春嫩柳。香肌扑簌瑶台月,翠鬓笼松楚岫云。”不过数行的外貌描写,就连用樱桃、春笋、金莲、娇花、嫩柳5个植物隐喻,将其嘴的小且红、手的细且嫩、脚的小且柔、脸的粉且娇媚、眉的细且长描摹得形象生动、淋漓尽致。又如第三十回,写张都监的养娘玉兰:“脸如莲萼,唇似樱桃。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纤腰袅娜,绿罗裙掩映金莲;素体馨香,绛纱袖轻笼玉笋。”对玉兰的外貌叙写,也用到了4处植物隐喻,其中,萼是指花瓣下部的一圈叶状绿色小片,这里以“莲萼”比喻玉兰的脸,凸显其脸的娇小、柔嫩,又以樱桃形容其嘴的红润小巧,金莲比喻其脚的小巧玲珑,玉笋则是形容她手的白皙嫩滑。除此之外,还有写玉莲的“杏脸桃腮,酝酿出十分春色;柳眉杏眼,妆点就一段精神。花月仪容,蕙兰情性”;写白秀英的“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写潘金莲的“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等,无一不是以植物喻指女性身体的经典例证。这些植物类的喻体,仍然是以“阴性特质”为内核的,侧重于彰显女性的观赏性,凸显其柔弱、娇小、妩媚的气质。
2.男性角色的动物隐喻
动物隐喻是一种跨域映射,指使用人们熟悉的动物性特征和行为来感知人类或其他事物的特征和行为。
《水浒传》对男性的动物化隐喻,单在角色的绰号中就有所体现,如玉麒麟、扑天雕、两头蛇、双尾蝎、混江龙、金钱豹子、插翅虎等。而在具体摹写男性角色的身体时,动物类的喻体则出现得更为频繁,除猿、燕、蚤这类侧重展现灵活性的意象之外,几乎都是以豺、狼、虎、豹等凶兽,或以鹰、雕等猛禽作喻。以书中第四十七回描写“扑天雕”李应的出场词《临江仙》为例:“鹘眼鹰睛头似虎,燕颔猿臂狼腰。疏财仗义结英豪。爱骑雪白马,喜着绛红袍。背上飞刀藏五把,点钢枪斜嵌银条。性刚谁敢犯分毫。李应真壮士,名号扑天雕。”开篇几句接连使用了鹘、鹰、虎、燕、猿、狼这6组动物隐喻来形容李应的身体形态,凝练生动地将李应高大威猛、气势雄壮、身形矫健、眼神锐利的形象特点勾勒了出来。再有第五十七回写“青面兽”杨志应出战呼延灼时的片段:“虎体狼腰猿臂健,跨龙驹稳坐雕鞍。英雄声价满梁山。人称青面兽,杨志是军班。”这里连用虎、狼、猿三种动物意象比喻杨志的外貌,“虎体狼腰”足见其身形高大、膀阔腰圆;猿臂则说明其手臂较长,而且矫健灵活。与上述所举类似的动物隐喻,在《水浒传》中比比皆是,比如第十八回形容宋江的“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第六十七回形容鲍旭的“狰狞鬼脸如锅底,双睛叠暴露狼唇”;第七十回形容张清的“头巾掩映茜红缨,狼腰猿臂体彪形”;第七十七回形容呼延灼的“皂罗袍穿龙虎躯,乌油甲挂豺狼体”;第七十七回形容吕方的“麒麟束带称狼腰,獬豸吞胸当虎体”,等等。这些动物类的喻体,仍然是以“阳性特质”为内核的,侧重于凸显男性角色刚强、高大、威猛的气质。
三、性别权力制约下的欲望宣泄
身体是感性的存在之域,它是物质性的,离不开性对身体的在体性还原,也就是对欲望的敞开,对义理的悬搁[9]。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理学体系的核心观点是“存天理,灭人欲”,其中包括对男女之欲的压制,认为无节制、不适当的情欲泛滥将带来亡身之祸。理学无疑强化了对性的禁锢,并且对女性而言,这种禁锢还要严苛得多。在男性主导的性别权力关系中,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始乱终弃,而女人必须从一而终、恪守贞洁。《水浒传》塑造了以潘金莲、潘巧云、贾氏、阎婆惜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创作者在刻画她们的人物形象时,对传统伦理体系下身体的遮蔽倾向进行了反拨,以写实性的身体叙事方式,客观上展示了女性“生的苦闷”,特别是“性的苦闷”。下文简以潘金莲为例,略做讨论。
潘金莲本是大好佳人,却只能像商品一样,被大户随意贱卖出去,嫁了个“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不会风流”的武大郎。由于武大郎“不会风流”,婚后的潘金莲除了心理上的空虚,还不得不忍受性的空虚。因此,当金莲见到英俊高大的武松后,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以身体为诱饵,试图从武松那里找回一些精神和肉体上的代偿。初见潘金莲时,武松眼里的嫂嫂是十分美貌的:“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这样美好妩媚的姿容,让武松都一时忘却了来人是自己的嫂嫂,而是以一种明显带有情欲意味的成年男性的视角,去凝视一个女性的身体,觉得她“暗藏着风情月意”“勾引得蜂狂蝶乱”。然而,正直的武松到底还是没有对嫂嫂动情,只是愈发焦躁,“欲心似火”的潘金莲不肯认输,又急于再次向武松袒露自己的身体,她“将酥胸微露,云鬟半身单”,故意敬了对方自己喝过的半盏残酒,最后却被武松一把推开,斥以“不识羞耻”。到这里,潘金莲挑逗武松的企图彻底破产,潘金莲的身体价值未能得到心仪男性的肯定,这对她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因为对于她来说,姣好的姿容是她引以为傲的唯一资本,也是她赖以生存的武器,于是身体的展现便成了她的生存方式,她企图在身体的展示与献出中找到自己及自己存在的位置。在被武松推开后,潘金莲很快又找到了下一个宣泄欲望的目标:西门庆。西门庆和武氏兄弟不同,他有財有貌,并且深谙风月。在被金莲用叉杆打头时,西门庆一看到她妖娆的姿容,“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可见他至少对金莲的身体价值是十分肯定的,而这一点也正中金莲的下怀。面对西门庆的屡屡挑逗,潘金莲先是以猎物的姿态表现出主动的迎合,又试图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掌握主动权,成为猎手,以期彻底转换身体的所属关系、找回主体性。故而,她一次次地剥开衣物,对西门庆敞开身体,希望能够在这个男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通过性行为进行权力分享,重新确认自我的存在价值。为此,潘金莲甚至不惜听从西门庆的指使,颠倒伦理纲常、违背天理人情,亲手毒杀了武大郎。但是,潘金莲以身体为武器的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杀害武大郎的真相暴露后,她“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水浒传》对潘金莲的死亡场景描摹得非常残忍而细致,她引以为傲的美好身体被开膛破肚、割头剜心,她身体的毁灭过程仿佛是一次献祭,一个被认为是英雄的男人,用极端的方式,摧毁了一个试图在性别权力制约下苦苦挣扎、试图找回自主权的女人,重振了纲常伦理,维护了男权的绝对统治。
除潘金莲外,潘巧云、贾氏、阎婆惜等也有着相似的苦闷经历和悲惨结局。在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制约之下,她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资本,扯下包裹肉身的遮羞布,通过失范、失德乃至失格的方式,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欲望,沉沦在感官世界中,最终由于对个体身体价值的误识,落入死亡陷阱,成为活时任人糟践,死时惨遭献祭的羔羊。
四、结语
在《水浒传》的叙事体系中,身体承担了重要角色,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承载着特定的思想文化内涵。《水浒传》的身体书写明显是性别化的:其一,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小嘴”“纤腰”等偏柔、偏弱的身体符号被反复标出,而在塑造男性形象时,则强调“须髯”“刺青”等充满力量感和侵略性的身体符号;其二,在对身体进行隐喻化处理时,女性身体通常采用的是凸显“阴性特质”的植物隐喻,而男性身体则通常采用的是凸显“阳性特质”的动物隐喻;最后,通过大胆直露的情欲化的身体叙写,在事实上展现出了以男性为主导的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反映了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 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2]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 余敦康.易学今昔[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 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
[5]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6] 陈迎辉.《水浒传》对男性身体形象的美学颠覆[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7]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周秦汉唐法制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
[8]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冯文楼.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10]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陆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