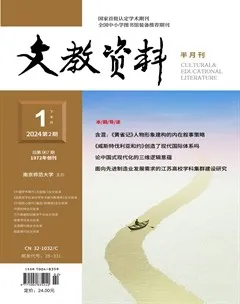浪漫叙事下的文化隐喻:《雅歌》对沈从文苗族传奇的影响探析
陈路昀
摘 要:沈从文在其一系列以苗族历史上部族男女为主角的作品中,不仅引用了《圣经》中《雅歌》的词语、句法,同时通过对人物形象、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的借鉴,构筑了人性复归隐喻之下的传奇故事模式。沈从文对《雅歌》的文学接受既是出自学习写作的自觉,又包含着对苗族历史和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展现出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审美内涵。
关键词:《雅歌》;沈从文;苗族传奇;文化隐喻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学译介风潮的兴起,《圣经》及其他基督教文学作品相继被引进,其中中文和合本《圣经》,作为目前为止流传范围最广且时间最久的汉译白话《圣经》,和同期带有实验气质的白话文学作品相比,语言纯熟优美,在推动白话文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影响。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徐志摩、老舍、巴金、许地山或多或少都曾在作品中引用或模仿过来自和合本《圣经》的经文句式。而据金介甫考证,沈从文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会每天翻阅《圣经》,如此长久的阅读习惯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虽不能说必然是深刻的,但一定是长远的。与大部分中国作家一样,沈从文对《圣经》所持的立场是基于文化而非宗教视野,但沈从文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地域文化背景又决定了他对《圣经》某些部分有所持重。凤凰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当地好鬼信巫的宗教情绪浓烈,民间神人相爱的传说故事又极多,神秘奇诡的民风在遇上集男女情爱与神圣经验于一体的《雅歌》时,便意外地契合,这便让《雅歌》成为沈从文尤为偏爱的书卷。而《雅歌》对沈从文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其一系列以苗族历史上部族男女为主角的传说故事。从词语、句法的模仿,到情爱故事的传奇性叙述,再到文化隐喻的构筑,沈从文对《雅歌》的借鉴由表及里,显示出独特的文化心理与审美诉求。
一、语言形式的借鉴与模仿
苏雪林在评价沈从文以《龙朱》为代表的描写苗族生活的作品时说过:“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1]相比于汉诗,她认为这些作品中人物对话的用词与结构更接近西洋情歌。如果对比沈从文早年搜集的《筸人谣曲》中的苗人歌谣会有更直接的观感,《筸人谣曲》用词的通俗化、比喻的生活化和表达的口语化更接近真实口传民歌的特点。而《龙朱》等作品中的对话无论在创作手法上,还是在用词上,都显得文雅、富有诗意和书面化,能明显感到其中来自异域的浪漫风情。
其一,沈从文使用了大量不同于传统意象的新奇比喻,如在描写苗族男女时,常常使用狮子、羊、鹿、光、热、泉水、果子、花朵等意象来比喻人物的美好特质。羊、鹿、狮子、百合花都是《圣经》中常见的动植物喻体。沈从文在《龙朱》中用“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2]描绘龙朱的俊美高尚。而光、热、泉水在《圣经》语境中通常与造物主本身有关,因而被赋予神圣的意味。在《月下小景》中,傩佑赞美他的恋人:“你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3]
希伯來文化中比喻的重点不在于单纯外在的相似,而在于内在价值系统的等同,即喻体本身所包含的整体价值属性的类同。例如,狮子除了象征力量、强壮之外,还强调了地位的尊贵与威严;羊、鹿除了象征温驯纯良之外,还意味着身份上的被驯服;泉水除了象征清澈柔美之外,更包含美好品质涌流满溢之意;果子也不只是形容外观上的饱满朝气,同时还意味着品性的成熟完满;光也不单是表明耀眼程度,还暗示着它是一切的本源。当沈从文在本土语境下直接使用这些比喻时,不同的文化背景带来的喻义之间的错位就使得他的表达充满了新鲜奇异之感。
其二,在这些苗族故事中,时常能看到作者使用一种欧化句式结构来组织人物对话,显然这些对话并非来自原生态的苗民话语体系。汪曾祺提到的“《神巫之爱》的对话让人想起《圣经》的《雅歌》和沙孚的情诗”[4],实为十分敏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对《雅歌》的引用随处可见,《月下》《神巫之爱》《第二个狒狒》《篁君日记》《看虹录》等都引用了《雅歌》的原文,如《月下》开篇写道:“‘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5]此外,沈从文还时常对《圣经》中的句式和语气进行变形与模仿,我们将他苗族传奇中的一些对歌与《圣经》中其他书卷的句式结构对照,即可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如《龙朱》中描绘白耳族王子:“你的富有与慷慨,是各苗族中全知道的。”[6](习惯性表达应该是“各苗族全知道你的富有与慷慨”。)还有“你的良善喧传远近”[7](习惯性说法应该是“你的良善远近宣传”),这种表述在《圣经》中就很常见。前者如《创世纪(30:29)》里的“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此处所引用的《圣经》原文来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2007 年版,与初版合和本内容上完全一致,在文中以章节名引用呈现,下同。)后者将状语后置的结构也是《圣经》中常见的固定表达,如《约书亚记(6:27)》中的“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再如《龙朱》中女人在对歌时所唱的“跟到凤凰飞的乌鸦也比锦鸡还好”[8](习惯性说法应该是“锦鸡还不如跟着凤凰飞的乌鸦”),这种以肯定表否定的让步式表达更是《诗篇》等诗歌智慧书中大量使用的结构,如《诗篇(37:16)》中这样描述:“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箴言(16:19)》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掳物与骄傲人同分。”
从比喻的借鉴和句式结构的援引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包括《雅歌》在内的《圣经》文本十分熟悉。军人家庭出身的沈从文,既没有留洋经历,也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高等教育,小学毕业后就随军辗转湘黔川。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之后,沈从文决定开始创作,而此时的他连新发布的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在摸索尝试中,沈从文所能倚仗的只有自己的阅读经验。他曾提到两本书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影响:“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习。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欢喜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初步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9]尽管沈从文主要强调《圣经》在叙事抒情方面对其写作的启发,但是与当时所风行的新式白话最为贴近的和合本《圣经》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他写作时的语言参考范本,影响了他的遣词造句。
二、两性之爱的传奇性叙事
关于《雅歌》的体裁和主题历来存在争议,主流观点有如下几种:戏剧说认为《雅歌》是根据所罗门和书拉密女的爱情写成的,还有人认为其中还存在另一个男性主角;爱情诗集说的学者则认为《雅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由若干爱情短诗组成的诗歌集,描写的是以色列民族男女之间的爱情;寓言说则是基于《圣经》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宗教典籍的地位,认为《雅歌》所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或基督对教会的救赎之爱[10]。可以看出,对《雅歌》内涵的解释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字面义出发的男女之爱,另一种是从象征寓意出发的神人之爱。对于大部分中国作家而言,《雅歌》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热情奔放的爱情书写。郑振铎称《雅歌》为“最美丽的恋歌”[11],周作人也赞同《雅歌》作为爱情诗歌的文学价值,认为其中所描写的情感“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12]。而从两性之爱这一主题来看,沈从文的苗族传奇和《雅歌》在叙述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从情节结构来看,《雅歌》和苗族传奇存在多处叙事场景的类同,如都写到陷入爱河的恋人彼此邀约,在野地里幕天席地的场景。《雅歌(1:16—17)》里新娘唱道:“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正如媚金在宝石洞中坐在石床上等待着她的情人,“石的床,铺满了干麦秆草,又有大草把做成的枕头,干爽的穹形洞顶仿佛是帐子”[13]。再如恋人们因思念对方成疾,苦苦游走寻觅的场景,《雅歌(3:2)》的书拉密女在城中漫游,“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而在《神巫之爱》中,神巫也在月下四处寻找惊鸿一瞥的女子。再如描写恋人们因为无法抑制爱意而悄悄隔窗观望的场景,《雅歌(2:9)》中良人翻山越岭来寻找女主人公,“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神巫之爱》中同样具有神巫无法克制思念,几次攀在窗边默默凝視心上人背影的情节。
其次,在人物形象上,《雅歌》和苗族传奇都通过众星拱月式的三元结构塑造了外貌、品性皆远超众人的男女主人公和其恋慕者,并且通过同族群体的衬托,极端凸显出男女主人公超人近神的英雄形象。龙朱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14],不仅如此,他还富有慷慨,他的良善也远近闻名。神巫则是有“完美的身体与高尚的灵魂”[15],豹子也是兼具勇武与美丽,地保称唯有山茶花女神才配得上他。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雅歌》中的新郎所罗门王被女主角称赞为树林里的苹果树,地位“超乎万人之上”(《雅歌(5:10)》),因他无论是外貌、威仪、地位、品德都出类拔萃,故而名声远扬。
和《雅歌》中的书拉密女一般,沈从文在苗族传奇中也塑造了一群外貌、品德都与男主人公们十分相称的女性,书拉密女在众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雅歌(2:2)》)那般出众耀眼,而苗族传奇中的女主人公皆纯洁、良善,以至于充满神性光辉。女主人公尊荣地位的获得并非因其显赫的家世,相反,她们往往身份平凡甚至有缺陷,却被男主人公奉若神明。《月下小景》中傩佑向恋人表白心意:“我不愿作帝称王,却愿为你作奴当差。”[16]神巫称心仪的女子为“我的神”“我的主人”“我生命中的主宰”,称自己为“你的仆人”“误登天堂用口渎了神圣的尊严的愚人”[17]。这也正如《雅歌》中所罗门王使用了“王女”这一王室的称谓来称呼书拉密女,从而凸显恋人的高贵。
再次,值得一提的是,《雅歌》和苗族传奇都不吝笔墨聚焦于男女主形体线条与色泽的精细描绘上。《月下小景》中以傩佑的视角来观察熟睡的女孩,他的目光逐一扫过女孩面部的各部分,最后定睛于“产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颊边微妙圆形的小涡”[18],而女孩丰满柔软的身体,在他眼里“只仿佛是用白玉,奶酥,果子同香花,调和削筑成就的东西”[19]。《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描写媚金的外表:她身材丰满匀称,“全身发育到成圆形,各处的线全是弧线”[20]。这样大胆地描写女性身体曲线美和色彩美的手法,在《雅歌》中也可以见到,所罗门王运用各种香花、美草来细细描画佳偶的眼睛、头发、牙齿、嘴唇、颈项、大腿、肚脐和双乳,女主人公成为“园”的化身,囊括了各色奇花异草: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
有佳美的果子,
并凤仙花与哪哒树。
有哪哒和番红花,
菖蒲和桂树,
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
一切上等的果品。
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
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雅歌(4:13—15)》)
基于作者大胆的形体刻画,《雅歌》和苗族传奇中的情爱书写兼具感官与精神之乐。一方面,男女恋人在生机盎然的自然中纵情欢歌,大胆直率而情感热烈,毫不避讳肉体的亲密关系,展示出健康形体的力与美;另一方面,也对爱情超越性的精神实质作出回应,强调摆脱身份门第、权力、金钱、地方习俗、道德伦理观念等限制的来自灵魂的吸引,体现出爱欲合一的特点。正像《雅歌(8:7)》中所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而苗族儿女表达爱情的方式是在对歌中袒露自我的灵魂与个性:“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21]
最后,二者对爱情超越性的描写还体现在都以死亡作为参照来集中彰显爱情之神圣。《雅歌》中清新浪漫的诗歌结尾处却风格陡变,诗人借着新娘之口发出情感最为炽热的强音,重申了新娘与所罗门王生死相随、忠贞不渝的爱情:“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雅歌(8:6)》)“爱情如死之坚强”,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直接引用了这句原文。读者们会愕然于他的许多作品中结局的急转直下,傩佑和女孩不愿意对扭曲人性的婚姻习俗虚与委蛇,带着对爱的憧憬和誓约一同前往死亡的国度;媚金以为豹子说谎失约,悲伤自戕,豹子也不愿独活,决绝地以身殉爱。这些男女主人公以殉情的方式来对抗地方邪恶风俗的桎梏,或是对命运阴差阳错的摆布作出反抗,以此维护爱情的纯洁与完整。由此,在类型化的英雄人物形象、爱欲合一的情感书写之外,沈从文通过叙事节奏的突变,使情节呈现出跌宕起伏之貌,男女主人公在神秘命运力量的阴影之下展开爱恨纠缠,这些都为作品蒙上了奇谲鬼魅的浪漫悲剧色彩,从而完成了对一般情爱故事的传奇化塑造。
三、乐园重建的文化隐喻
相比于苗族传奇与《雅歌》故事书写的耦合,二者所传达的文化母题或许更值得注意。若了解《雅歌》与《创世纪》文本的互文关系,可知《雅歌》实则来源于《圣经》文学传统中的“伊甸情结”。伊甸乐园(paradise)由古波斯语pairidaeza演化而来,意为“有围墙的花园”或“关锁的园”,而在《雅歌》中反复出现的中心意象即为“关锁的园”。如《雅歌(4:12)》中有这样的诗句:“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关锁的园”作为《雅歌》中的核心意象,建立起女性—自然的隐喻关系,有趣的是,苗族传奇中的女性人物同样存在与自然的对应关系,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被暗示为自然的神性化身。此外同样是描写人与自然以及男女双方亲密和谐的关系,《雅歌》可以说是《创世纪》第三章中人被逐出伊甸园后对往昔场景的追忆与重现。《雅歌》中描绘各色果子、鲜花、草木和香料生长繁茂,同时有源源不断的溪泉环绕,还有百鸟走兽欢腾雀跃,万物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使人联想到《创世纪》开篇记述耶和华创造天地并设立伊甸园的场景:“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牲畜、 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创世纪(3:16)》中以自我与他人和人地的关系破裂隐喻一种完满状态的丧失,亚当和夏娃由最初“骨与肉”一体的亲密转变为辖制:“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似是显示出爱情的裂痕;而后的诗句“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创世纪(3:17)》)也显示出人与自然彼此对立关系的开始。而在《雅歌》和沈从文的苗族传奇中,人类最原初的精神体验——即凯伦·阿姆斯特朗所论的万物相和、生命相感状态的获得又都在灵肉合一的爱情及和谐的人地关系中得到重铸,这一切都暗示读者,文本中优美怡人的自然风物、崇高俊美的男女主人公以及浪漫动人的爱恨纠缠并非仅意在增添故事的传奇性色彩,更重要的是呈现出一种重构昔日理想家园(不仅是肉体感官上的安息之地,更是精神上的棲身之所)的努力。作者通过封闭性的空间和非明晰的时间构筑出一个自足的化外之境,营造出从现实中抽离的永恒时空感,无论是《月下小景》中边境山脉下为历史所遗忘的山寨,还是《龙朱》《凤子》《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活在部落光荣时代的男女们,沈从文所写的苗族传奇都和现实的苗人生活相去甚远,与其说他是对苗族传说进行加工与记录,不若说他是在重新编织苗族起源的神话,追溯业已失去的历史精神传统,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种“现代文明社会业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范型”[22],即他自己所言的“优美,自然,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3]。与此相对,在西方《圣经》文学传统之下,伊甸失落与乐园重构的神话原型往往暗含道德的沦丧与重塑人性的渴望,作者们想象并描绘自己心中自然、和平、纯洁、宁静的伊甸园——实则是一种诗性的社会理想,“就像营造一座现实中的花园那样,也是‘重温创世的部分经历,这种经历既是宗教上的,又是美学上的”[24]。
沈从文对湘西乐园的构筑,同时也出于对苗族历史与自身身份的价值认同。他在《龙朱》的前言中写道:“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25]这是他少有的直接承认自己苗族身份的文字。身处距苗乡一千多公里外的陌生都市,为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虚伪庸碌等一切新式文化习气所包围吞噬的沈从文,唯有溯及与苗族英雄血脉精神之关联时,方能获得一些自信与立足的勇气。正如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后,犹太民族被迫从故土迁出流亡,却依然保持着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和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他们留存了与众不同的实践、关于他们独特起源的神话、对故土的记忆以及最终回归的希望:‘……耶路撒冷的下一年”[26]。
但正如犹太人离散的民族情结并不独属于以色列一般,沈从文对湘西乐园的复现同样有着超越地缘的意义。王德威认为鲁迅的《故乡》,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三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透出一种“原乡意识”:原乡意识相比于个人地方性的故土乡愁,更多是一种植根于群体记忆的寻根渴望,从而使得对生命源头的回望与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学母题。当沈从文借用苗族历史传说这一具体文化形态来表现他关于民族寻根理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展露出属于人类共同的永恒经验和记忆想象,当将这些文本与《雅歌》放在一起对照时,则更为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审美诉求。沈从文塑造了一批不仅是传奇英雄式、更无疑是具有人类原型意义的苗族男女,通过他们的结合,反映了人类从最初完满性中分离后,又在失落与痛苦中渴望寻求精神家园的心理体验,从而在凝滞的时空中反复演现回归伊甸的神话。
四、结语
《雅歌》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资源,为20世纪中国作家所吸收,而沈从文的文化背景和写作经历又意味着相较于其他作家,一方面,他更多关注其中的文法知识和文学手法,通过借鉴其比喻和句法结构来提升写作技巧;另一方面,《雅歌》中以两性和人地关系再现的伊甸记忆的“乡愁”也时时萦绕在其作品中。通过浪漫情爱的传奇性书写,沈从文展露出重塑美好人性、实现自身文化认同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的苗族传奇和《雅歌》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是外部叙事和语言形式层面的,这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中对《雅歌》接受方面的一个富有独特性的典型案例。参考文献
[1]苏雪林.沈从文论[M]//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85.
[2][6][7][8][13][14][20][21][2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4,343,343,343,356,324,357,327,323.
[3][15][16][17][18][19][2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29,380,229,392,219,220,5.
[4]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119.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11.
[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72.
[10][美]特伦佩尔·朗文,[美]雷蒙德·B.狄拉德.旧约导论[M].石松,肖军霞,于洋,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292-300.
[11]郑振铎.文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48.
[12]周作人.谈龙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9:144.
[22]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5.
[24]胡家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4.
[26][英]奈杰尔·拉波特,[英]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