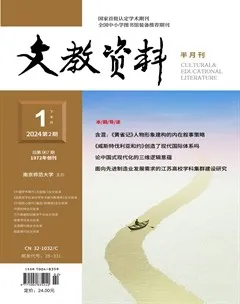《金瓶梅词话》诗词曲异文校读举隅
马佳帅
基金项目:2023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金瓶梅词话》引诗词令曲异文校读研究”(KYCX23_1606)。
摘 要:《金瓶梅词话》诗词曲文本的异文从是否需要校改的角度分析可归纳为校勘性异文和非校勘性异文两类。校勘性异文主要包括讹误式异文、赘衍式异文、错乱式异文三种,其中讹误式异文包括形讹和音讹两类。非校勘性异文则包括同词异形和词语差异两种情况,其中同词异形分为单音节同词异形和多音节同词异形两类,词语差异分为部分语素(词)相同和语素(词)完全不同两类。运用各种文献材料对《金瓶梅词话》诗词曲文本进行校理,汇集其异文类语料,考察分析其异文材料的性质,对异文材料进行取舍和辨析,是近代汉语语料建设和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诗词曲;异文字词;校读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重要的具有近代汉语研究价值的通俗小说,载有诸多诗词曲文本且存在颇多校释问题。利用《金瓶梅词话》的不同版本,如万历本、崇祯本、张评本等勾稽版本异文,并结合诗词曲的来源文献提取引用异文,可供我们进一步比勘、拣选。这些来源文献包括但不限于《元曲选》《水浒传》《雍熙乐府》《吴骚合编》《六十种曲》《缀白裘》等。结合异文校理实践可知,《金瓶梅词话》在文献校释、语词注解方面的成果甚夥,然犹有可臻完善之处; 而俗文学文献传世版本往往不甚精良且用字情况复杂,给文本校释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今取《金瓶梅词话》诗词曲文本所呈现的若干异文,对其相关校释成果进行辨析并予考释。就教于方家之余,亦尝试对诗词曲文本的异文类型作出归纳,从是否需要校改的角度将《金瓶梅词话》诗词曲文本的异文字词分为“校勘性异文”及“非校勘性异文”两类。
一、校勘性异文
结合《金瓶梅词话》诗词曲的文本实际,可将校勘性异文分为“讹误式”“赘衍式”“错乱式”三种。“讹误式”即因字形或字音相近而讹混致误,是基于文献语言的形式相似而产生的关联式错误; “赘衍式”主要体现为“衍文”,属于文本的赘余,与音义无关;“错乱式”既有可能涉及文字的形音义问题,也有可能涉及文本单位数量的增减、位置的颠倒问题,无法归并至单一分类,故设“错乱式”,谓错综复杂的异文现象。以上三种均需校改,下略陈之。
(一)讹误式异文
讹误式异文是《金瓶梅词话》诗词曲异文中字词的大宗,或因字形相近,传抄致讹;或因口耳相传,音近致误。
第一类为“形近而讹”,这是因字形相近而导致讹误的异文。字形相近体现在诸多方面,从视觉认知的角度来看,往往是两字结构相似,并且轮廓笔画以及主要部件近似,试举例分析如下。
地彻、地狱
A.死生事大宜须觉,地彻时常非等闲。(万历本《金瓶梅》第七十五回)
B.死生事大宜须觉,地狱时长岂等闲。(如卺《淄门警训》卷九)
崇祯本、张评本中均无此句。梅节谓“彻”应为“狱”之误。第七十四回“无间地狱”,“狱”亦误“彻”。
[1]今按是。另有陈东有之观点,颇具代表性,但某些解读似乎拘泥于字面意义而不顾语词通例,未免令人遗憾。陈东有解释“地彻”谓:“彻”有“通”的意思。《庄子·外物》有:“目彻为明,耳彻为聪。”又有“达”“到”的意思。《国语·鲁语上》有:“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韦昭注云:“彻,达也。”唐人刘言史诗《代胡僧留别》有:“定知不彻南天竺,死在条支阴碛中。”“地彻”一词应是到达地府之意。有待查证商确。[2]
按 “地彻”确有到达地府之意,但以“彻”之“通”义释“地彻”,其理据未免不惬。一方面,陈文引用的语例最晚仅至唐代,无法完全排除语义随时代变化的问题。由于缺乏同时代的语例支持,《金瓶梅词话》中“地彻”的“彻”可能并不具备“通”义。另一方面则是陈文在证明“彻”有“通”义的语例中所举的“彻”均为单用,系谓词性质,而非“地彻”这一凝固语词形式。“地彻”中的“彻”当为名词性质的语素,然而“彻”未见有名词性质的义项,故“地彻”似乎不辞。异文校读实不必逢字必追溯
至上古汉语时期,在聚焦字书、韵书记载的同时,应该更多关注文献中的文字使用情况,即字用事实。查检 CBETA 电子佛典语料库,“无间地狱”共检得537 笔,而“无间地彻”0 笔。充分说明“地彻”不辞而“地狱”是,陈说迂曲,有过度解读之憾,由此可知“地彻”为“地狱”之讹。“彻(徹)”“狱
(獄)”形近而讹主要是由于其繁体字轮廓形似,尤其“彳”与“犭”,均有两个斜撇和一个纵向笔画,笔画交接延伸处若不清晰或误识,则形讹生焉;“攵”与“犬”亦是,均有横、撇、捺,在笔画组合生成的结构方面也較近似;中间的“育”“言”亦形似,致使字形的相似度极高而造成讹混。
第二类为“音近而讹”。在人脑的词库中,两个词语音相近,容易在文本刻写的过程中造成干扰,从而输出错误的一项,需要校改。
飞浅、飞盐、飞琼
A.飞浅撒粉漫连天。(万历本《金瓶梅》第一回)
B.飞琼撒粉漫遥天。(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C.飞盐撒粉漫连天。(崇祯本《金瓶梅》第二回)
杨琳谓“浅”应为“铅”之音误字,指女子化妆用的铅粉。铅粉为白色,故用来比喻雪。[3]孟昭连结合草书“绵”字形“”及草书“浅”字形“”指出“浅”是“绵”字的形误。[4]
按 使用草书写法来证实文献中可能出现的讹误,是将文本还原到生成现场的可贵尝试,但此方法在使用的时候仍有掣肘之处。孟文所判断的字形讹混具有偶然性,该文使用的“绵”字草书字形,是明代王铎的书体,而大部分书家之“绵”字草书均不作该形,可知“绵”“浅”形体讹混的概率不大。故以偶见写法作为例证,未免有以偏概全之憾。结合更多诗词曲文献中的雪景描写可以为本则异文校读带来启示:
例1 天上琼花呈瑞祥,乱舞在空中降。恰便似挦绵扯絮,堆盐撒粉,鹤羽翺翔。(《雍煕乐府》卷七《粉蝶儿·四时享乐》)
例2 故教撒粉恼何郎,千片纨丝裁扇冷,一庭柳絮斗盐忙。灞桥可是胜潇湘?(《午梦堂全集》“鹂吹”下)
例3 庭空堆飞盐,院冷折大竹。(《小鸣稿》卷二《咏雪》)
由例1可知“盐”“粉”对举于文有据,且正是在“堆……撒……”的格式中,与本则异文所涉之“飞…… 撒……”义近。例2描绘了落雪情境,前有“撒粉”后有“斗盐”,亦可证“粉”“盐”对举是雪景描绘的常见表达。例3则证实“飞盐”之词语组合存乎文献,前又有“堆”字,再结合例1 可知“堆盐”“飞盐”均通。以上文例亦可证“飞铅”的说法罕见于雪景描绘文句中,杨说不妥。
由此可知“飞浅”不辞,或为“飞盐”之音讹,不排除有方言音的影響。B 句中“琼”亦可喻雪,故“盐”“琼”为词语替换原因的异文,具有修辞性效果。
(二)赘衍式异文
衍文即在文本中滋生了本不属于此的字词,需要将其删除。
低声帏枕、低帏枕
A.西门庆情极,低声求月娘叫达达;月娘亦低声帏枕,态有余妍,口呼亲亲不绝。(万历本《金瓶梅》第二十一回)
B.西门庆情极,低声求月娘叫达达;月娘亦低声睥帏枕,态有余妍,口呼亲亲不绝。(崇祯本《金瓶梅》第二十一回)
鲁歌指出“帏枕”应作“睥帏睨枕”。崇祯本作“睥帏枕”。[5]今按鲁说不确,忽视了该辞中“低声”的存在,尽管“睥帏睨枕”从词语构造来看甚妥,但前有“低声”则为不谐,详后。又梅节谓崇本作“低声睥帏枕”,今本词话“声”字当系据崇本校入。[6]今按梅节第一处校读有误,崇祯刻本实作“低声睥帏枕”;但梅节言此处本应无“声”字。文献中“低帏枕”乃习见,此语又作“(昵) 枕低帏”。
例4 愿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绅。〔昵,近也;褫,夺衣也。孔安国论语注曰:绅大带也〕(《文选注》卷十三《雪赋》)
例5 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到得低帏枕,极甚欢爱。(《六十种曲·紫钗记》第十四齣)
例6 枕低帏,不怕细君知道。(《十五家词》卷二十六《却梦调元景病次家兄仲谋韵》)
由引例可知,“低帏”“枕”两个动作前后相继而成连谓词组,两个谓语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结合文献用例可知,“睥帏枕”一语仅于崇祯本《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得见,尽管《吴震生全集》有“睨枕睥帏,际并香肩”句一例[7],但终究无法和数量庞大的“低帏枕”相比,可证崇祯本之“睥帏枕”亦不足尽信。这姑且可以用版本对校之“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统摄,在大量正面例子出现的同时,偶见孤例且并非具有关键性意义者,可以忽略。
要之,万历本“低声帏枕”之“声”字为衍文,原应作“低帏枕”。崇祯本以为脱文,而补“睥”字,或鉴于“睥睨”一词而成“睥帷枕”。实际上“睨”谓斜视;而“”系“暱”俗写,“暱”是“昵”之异体,谓亲昵,如《玉篇·日部》:“昵,同 ”。可知崇祯本误改,致语义不合。从语词组合的角度来看,“低声”后应接话语类及发声类动词,若接“观看”义动词则不协调,故“低声睥帏枕”不辞。然而前句主语“西门庆”有“低声”行为,似乎在“亦”字的介引下说明后句主语 “月娘”存在“低声”行为的合理性,实非。因为“月娘亦低声帏枕”对应的实际是“西门庆情极”,而“口呼亲亲不绝”才是“低声求月娘叫达达”的对应项。可知所谓“低声帏枕”对应的应是“情极”,结合诸多用例校正为“低帏枕”正符合与“情极”这一情态描述对应的句内逻辑。
(三)错乱式异文
文献文本经过辗转传抄刻录,未免有鲁鱼帝虎之乱。除了较为清晰的讹误之外,倒、脱、衍兼生而致使文本错乱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几种可能的致误原因扭结在一起,需要充分结合版本异文以及引用异文进行比勘、拣选。
践玷、践琼瑶
A.舞冰花旋风儿飘荡,践玷脚步儿匆忙。(万历本《金瓶梅》第七十一回)
B.剪冰花旋风儿飘荡,践琼瑶脚步儿匆忙。(《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第三折)
C.拂冰花旋风儿飘荡,践琼瑶脚步儿慌忙。(《雍熙乐府》卷二《赵太祖雪夜幸赵普》)
按:崇祯本、张评本中均无此句。审察文本可知,“舞冰花旋风儿飘荡,践玷脚步儿匆忙”前后不对仗。校改“玷”为“琼瑶”后,“舞冰花”“践琼瑶”语法格式相同、语义相关,确乎工整。致误原因犹有未详之处,即“琼瑶”何以误作“玷”费解,或有讹、脱多重兼施的可能性,犹待查考。测查语词用字情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研判相关问题。查诸万历刻本及崇祯刻本《金瓶梅》,所录“琼”字皆作“”,无一作“琼”,似可排除“琼”讹作“玷”的可能性;“瑶”亦无其他用字形式。由此可知,《金瓶梅》的任何字形环境中均不会出现“琼”字,因而不会讹误作“玷”。要之,本则异文实际上是脱文、讹误并作的结果,当属错乱式;前后文的对仗是本则异文校读的基本依据,故当以“践琼瑶”为是。
二、非校勘性异文
非校勘性异文即具有一定语言学理据的异文,并非纯粹由于载体而产生。这类异文大致体现了文献之辗转流传情况,或是时代性,或是地域性,无须校改。在出校记的时候往往以“异同校”的形式说明情况,即无法轻易按断孰是孰非,姑且将无须校改的两项或多项异文均保留下来。非校勘性异文字词大致可分为“同词异形”和“词语差异”两种情况。
(一)同词异形
在文献的产生及流传过程中,人们可能会选用不同的字形来记录同一语词,这些记录同一个语言单位但形体不同的书面符号就属同词异形。同词异形异文不涉及是非问题,主要体现了用字习惯的不同及方言背景的差异。同词异形首先表现在单音节词上,单音节同词异形主要以正俗字的形式体现出来。
、婬、淫
A.阿嫂心不可收。(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第一回)
B.阿嫂婬心不可收。(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C.嫂嫂淫心不可收。(崇祯本《金瓶梅》第二回)
按 “”系形讹产生的俗字,当然,刻本中“正”“壬”“缶”亦见混用现象,如“窑”万历本第一回作“”。“婬”出现的时代较早,且在汉字史上较为常用,而后为 “淫”所替代。《说文解字·女部》:“婬,私逸也。”段玉裁注:“‘婬之字今多以‘淫代之。‘淫行而‘婬废矣。”故此则异文B句中的“婬”为偶用之异体,可计为俗字,与通用之正字“淫”相对。依笔者目力所及,《金瓶梅词话》万历本中“婬”字仅一见,第七十八回“几番鏖战贪婬妇,不是今番这一遭”,即使是同样的组合,万历本中除上举第七十八回例句外,均作“淫妇”;崇祯本暂未见“婬”。或可知“婬”字为偶然受上下字形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俗写,而这个俗写形态恰好是汉字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字形。而容与堂本《水浒传》“淫”“婬”并用,亦刊刻于万历年间,却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用字情况具有较大区别,或许体现了不同地域刻本用字的习惯差异。
整、挣
A.下工夫将头颅来整。(万历本《金瓶梅》第七十四回)
B.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六十种曲·北西厢》第六齣)
C.下工夫将头颅来挣。(《六十种曲·南西厢》第十七齣)
按 崇祯本、张评本中均无此句。多本作“挣”而唯独此本作“整”,似乎通过版本校勘的基本原则便可确定“整”字非,然而细玩尚可有所得。史良昭注评《[中吕]普天乐·虚意谢诚》时解释“挣”道: “元人方言,漂亮。”[8]梅节校读云“整”“挣”都是记音字,又作“锃亮”之“锃”“铮”。[9]
今谓此句中“整”或“挣”似有动词实义。《元曲鉴赏辞典》载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满庭芳〕释“挣”曰:“原是方言美的意思。此处用作动词,当解作擦拭。”[10]认定该句中“整(挣)”为具有实义的动词是因在“将……来……”句式中,“来”后一般接动词。如京剧《赤桑镇》中吴妙贞唱:“想当年嫂嫂将你来抱养,衣食照料似亲娘。”又如京剧《拾玉镯》刘媒婆“我是那姓刘的人将你来看”。可知无论是单音节动词还是双音节动词均可进入“将……来……”的后项空缺处而作谓语。《近代汉语词典》释“挣”有一“打扮”义项,即引此例。[11]此则异文多本作“挣”而仅万历本作“整”,似讹。然而在确定“挣”必为动词之后,“整”的理据性也显豁了,故“整”或为“挣”之俗字。
较之单音节同词异形,多音节同词异形现象的存在状态可能更为隐蔽而不易识断。尤其在俗文学作品文本中,一些多音节的方俗语词往往本字难以考得,词语理据亦不明晰,为校勘和释读带来了困难。
粉甸、粉填、粉垫
A.粉甸满封疆。(万历本《金瓶梅》第七十一回)
B.粉填满封疆。(《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第三折)
C.粉垫满封疆。(《雍熙乐府》卷二《赵太祖雪夜幸赵普》)
崇祯本、张评本中均无此句。梅节认为“粉甸”之“甸”为“填”的同音字。[12]章一鸣对戴鸿森校点本第七十八回的“柳甸”校读时提到,《词话》中的“垫”几乎都写作“甸”,这是作者的习惯写法。[13]王夕河谓“甸”字一音与“垫”同;又“甸”字同“田”字,音又与“填”同。故知“甸”乃“填”或“垫”的借音字,三字义同。[14]
由诸多论断可知“甸”“填”“垫”语音近似,且用字选择时体现了作者的习惯,三字不存在孰是孰非的按断问题。但究竟孰为本字,即体现了词语的理据性的用字,这是校勘学不甚着意而汉语史关心的问题。王贵元谓“粉甸”形容雪地像洒满面粉一样。[15]今按王说恐非是。第一,“粉甸”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第二,“粉”并不指面粉,而是指白粉,即白色涂料、颜料。下列语例可证。
例7 于是用白粉题毕,“诏封”二字贴了金,悬于灵前。(崇祯本《金瓶梅》第六十三回)
例8 寺门虚掩,而门扉隐隐有白粉大书字,敲火视之,则“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语也。(《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
例9 红梅得雪添丰韵,绿竹凝妆带粉痕。(京剧《柳迎春》)
例10 先只想拜佛早回转,文殊院粉墙高似天。(京剧《白蛇传》)
例7、例8 中“白粉”之“白”提示了“粉”的颜色特征,结合各句语境亦可知“白粉”系白色涂料、颜料。例9中“粉”亦为白色,前句之“雪”提示了语境,谓竹子上覆盖积雪,洁白如妆。故知“粉填”为用白粉填充义,状雪貌。例10中“粉墙”当谓白墙。要之,“甸”“垫”均为“填”之记音,“粉甸”“粉填”“粉垫”为同词异形,究及字词关系及词语理据,“粉填”当为词形本字如下。
(二)词语差异
异文间的词语差异是语言层面的单位不同,即音义结合体不同,是不同词语之间的关系。词语差异异文有的体现了词际关系,而有的体现了语际关系,差异项或是词,或是语素。当然,校读时偶尔也需要模糊处理词和语素的界限,因为一些校读单位的语法性质确实不甚容易判断清楚。部分语素(词) 相同的词语差异类异文如下。
嫂嫂、阿嫂
A.阿嫂心不可收。(万历本《金瓶梅》第一回)
B.阿嫂婬心不可收。(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C.嫂嫂淫心不可收。(崇祯本《金瓶梅》第二回)
按 “阿嫂”“嫂嫂”均为亲属称谓词,这组异文体现了常用词替换问题。二者构词理据不同,“阿嫂”是前缀加词根,“嫂嫂”则是词根重叠构词。这组异文也可能反映了方言之间的差异,是为同一概念在不同地域的变体形式。褚半农认为:“喜欢用前缀‘阿字,这也是上海西南农村语言的一个特色。”[16]谭兰芳指出:用“阿”作前缀,用于亲属称谓,也是吴方言的特点。举例有“武松仪表甚搊搜,阿嫂淫心不可收”。[17]或許可以由此窥见《金瓶梅词话》的地域流布特征。
還有一类词语差异是异文两项中没有一致的词或语素。这类异文往往具有明显的修辞性,这意味着异文两项可能具有不一样的词汇色彩,体现了在诗词曲的辗转流动中,前后相继的抄刻者改易字词的旨趣。
鲜血、腥红
A.淋漓两手鲜血染。(万历本《金瓶梅》第一回)
B.淋漓两手鲜血染。(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C.淋漓两手腥红染。(《古本小说集成·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十回)
按 崇祯本、张评本中均无此句。“腥红”较“鲜血”更富有修辞效果。“腥”是血的气味,“红”是血的颜色,以血的两种性状组合成词,借代“鲜血”,生动形象。但“腥红”“鲜血”究竟是哪一项替换了另一项,这是一个较难解释的问题。“腥红”以血液的特征与性状来转喻血液,语体色彩相对含蓄,需要读者调动想象和感官进行语义激活;“鲜血”则十分直观,语体色彩较“腥红”更为通俗易解。这种不同语体色彩的异文或许正揭示了诗词曲在不同环境中的敷演方式,若是文人雅士持读,则书面色彩浓厚的一项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若是在百姓群体中“撂地儿”演说,则应直观而为,便于听者第一时间调动头脑词库中的音义信息来完成语词符号的接收和处理。由《金瓶梅词话》的整体语言面貌可知,其词汇使用往往较为俚俗,故“鲜血”可能是写定者改动后的结果,是结合语用环境对语词文体特征的一种适应性处理。
三、结语
《金瓶梅词话》诗词曲中所载的大量异文具有较高的校读价值。其价值体现在通过校勘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接近原貌的文本形态,在校读过程中,一些字词的确义得以考定,具体的校读标准和正确的校读理念也在一组组校读实践中得到了相应的规范和深化。当然,一些异文所展现的词语替换现象揭示了词汇的鲜明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但由于对相关材料的勾稽和解读工作尚未彻底展开,分析工作无法进一步进行。总之,《金瓶梅词话》诗词曲文本于校勘学、训诂学、词汇学等领域尚存在理念、方法方面的研究空间,值得学界予以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1][6][9][12] 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74,104,367,335.
[2]陈东有.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203.
[3]杨琳.“金学”基础有待夯实——以《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校释为例[J].文学与文化,2012(4):23-40.
[4]孟昭连.关于《金瓶梅》中的“形误”“音误”字——与杨琳先生商榷[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1(6):67-75.
[5]鲁歌,马征.《金瓶梅》纵横谈[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194.
[7](清)吴震生.吴震生全集[M].王汉民,编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339.
[8]史良昭.元曲三百首注评[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51.
[10]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元曲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340.
[11]白维国.近代汉语词典[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2658-2659.
[13]章一鸣.对《金瓶梅词话》几处校改的意见[J].湖州师专学报,1995(4):7-8.
[14]王夕河.《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454.
[15]王贵元,叶桂刚.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546.
[16]褚半农.《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5.
[17]谭兰芳.《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词(续)[J].语言研究集刊,2007(0):66-83.